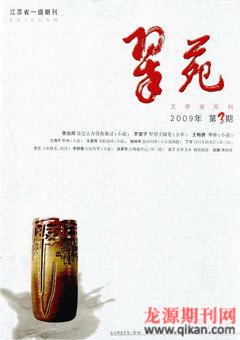佛塔缘
谈 雄
佛塔原称浮屠,最初是为了埋藏高僧肉身或火化后的舍利,是修行得道者的纪念碑。像杭州灵隐寺的“灵鹫塔”,塔内就有灵隐寺开山祖师慧理的骨灰。历史上的天宁寺也有佛塔,南唐初建时称“普照王塔”。北宋时改名“慈云塔”。俗话说“乱世毁庙。盛世建塔”。我是在今年天宁宝塔开光一周年庆典上,开始走近天宁宝塔的。这是一次绕塔礼佛盛会。几百名僧众在“梵呗念诵”中缓缓走来。在人群里,只有僧人的绛色袈裟是最鲜明最纯粹的色块。他们端正的身姿,安祥的步伐,沉稳的念诵,那些长相不同的脸容因诚挚而显得端庄,闪着清欢的神采。我似乎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了佛性。我想佛性一定是这样的:它自然而又平等,清净而又大爱。这种大爱打动了我,我的一颗凡心也在刹那间清净起来。
在天宁寺馆藏文物里,弘一法师李叔同手书的《心经》,是我最为欢喜的一件佛宝。李叔同是一位具有大爱的人,他临终的时候对妙莲法师说:“当我呼吸停止时,要待热度散尽,再送去火化,身上就穿这破旧的短衣,因为我福气不够。身体停龛时,要用四只小碗填龛四脚。再盛满水,以免蚂蚁爬上来,这样也可在焚化时免得损伤蚂蚁。”李叔同才华出众,诗、词、曲赋、戏剧、音乐、书法、绘画皆光彩照人。就在一切鼎盛之时,他却悄悄皈依佛门,过起了一领衲衣,一根藜杖的苦行生活。并且居然使失传多年的佛教南山律宗再度兴起。
弘一法师手书的《心经》,是近年一位香港居士捐赠给天宁寺的。我看他手书的《心经》,体会到的是沉静的意蕴,体会到的是他的心境、气度与学养。这是弘一法师晚年的作品,真有说不尽的香光庄严。他晚年的书法:字形瘦长,结体宽裕,涤荡俗念,宁静淡远,不工而工,浑然一体。真是脱净铅华,真气流衍,达到了他个人书法艺术的顶峰。自从李叔同出家以后,他除了念经,就是写字。他自己说,“不是经语不写,不是佛语不说”。他是在用书法来弘法。他自谓:“朽人之字所示者,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
李叔同是一个万事皆认真的人。他的学生丰子恺说:“李先生的确做一样像一样: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刊物,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李先生何以能够做一样像一样呢?就是因为他做一切事都‘认真地、严肃地、献身地做的缘故。”
我想,天宁宝塔也是这样“认真地、严肃地、献身地”做出来的。所谓“置心一处,无事不办”。天宁宝塔既然被定位为“传世之塔”,就需要建塔人具有认真、严肃的献身精神。这是精卫填海的精神。做到那里,那里就是完成。正如李叔同在一首诗里所说:
我到为种植,我行花未开。
岂无佳色在,留待后人来。
这是一种福分,也是一种缘分。
说一件建塔中的小事。
同济大学的路秉杰教授是中国的造塔专家,人称“托塔路天王”。为了给天宁宝塔梵音阁置一口仿唐铜钟,在北京永乐大钟研究专家全锦云的帮助下,一行人到丹阳人民公园去看唐代铜钟的实物。铜钟锁在一座旧房里,门是木门,涂了油漆,管理人员说钥匙已多时找不到了。就在大家扫兴欲归时,路教授竟在草丛里发现了一把锈迹斑斑的钥匙,大门果然打开了。这真是应了缘分之说。过去生五百次的回眸,才换来今生一次的擦肩而过。
造塔其实是不容易的。佛经上说,释迦牟尼行菩萨道的时候,提婆达多时常来找他的麻烦,甚至菩萨化现的帝释天也会变成魔鬼来打击他,但佛祖不为所动。
光绪二十二年,天宁寺大雄宝殿重建开工时,几位贡生,举人便哗然起来,说佛殿超过孔庙大成殿一倍多,将招致城内文气衰落,于是向府衙告状。天宁寺方丈冶开据理力争,以“会典律例均无佛殿不准高于大成殿明文”。以“寺在城外,距黉宫尚远”为由,官司整整打了三年。冶开法师最后终于打赢了。不过为了给这些地方绅士一点面子,仅将殿脊稍稍降低了两尺。
佛陀曾讲过,佛法不异世法。凡世间事物,其内在都有一重禅意。“和睦和谐,至善至上”便是天宁宝塔向世间昭示的禅意。但当今社会还是一个浮躁纷嚣的世间,终会有人不甘寂寞,想热闹地表现自己,发出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这怎么办?得道禅师便开示道:由他说去。莫问树有没有佛性。它有没有佛性于你有什么用呢?要问你自己有没有佛性。观照自己永远是第一位的。佛家讲究一个“缘”字,这情况便是佛经上所说的“逆增上缘”。你在做你的事情,他便来刺激你。打击你,你如果无法忍受,那你就不会有成功的可能。你如果能够感谢攻击你的人,以为他们是菩萨化现来考验你的。那你就真有佛性了。
天宁宝塔广场供奉了一座弥勒佛像。这尊笑佛本来是准备供奉在吉祥大厅的,只是因为佛像高出了大门,有人便说,既然弥勒菩萨不愿进去,那还是随缘吧。佛普渡众生,哪里有众生,哪里就是佛的殿堂。是傍晚时分,刚安置妥当,西南方向的天空中就现出了一道彩虹,天幕中透出深深浅浅的暖色,呈出一种祥瑞之气,微妙而不可言传。
这弥勒佛本来就是个随缘之人。民间有这样的传说,说是在五代梁时。浙江奉化岳林寺有一奇僧,是个矮胖和尚,常用禅杖挑一布袋,四出化缘。人家施舍给他的东西,他都笑呵呵地放进布袋,世称“布袋和尚”。人们就把他当作了弥勒的化身而塑像供奉了。在弥勒佛龛前常见这样一幅楹联: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慈颜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供奉在吉祥大厅里的印度檀香木雕《龙华三会》,说的也是这位兜率天宫里的弥勒佛。释迦牟尼曾经有过这样的预言:在他的过去世中燃灯古佛曾经在灵山说法:他在灵山的说法是法界的第二次:在他的来世还有一次盛况空前的法界大会,将由未来掌教的弥勒佛在此说法。福建木雕大师李凤强创作的《龙华三会》,便是描绘了这庄严神圣的第i次盛会。木雕一共刻了120尊佛像。这120个佛,一个与一个都不一样。众生不一,而成人间:佛像不一,而成佛界。
三尊大佛,佛相庄严,气定神闲。他们似在安祥微笑,义含一丝悲悯。弥勒佛在喜笑颜开地开讲说法。群佛之间,或立或动,在兹念兹;有沉思的、有打坐的,有喧闹的;有的低眉敛目。和颜而笑,有的脸面饱满,螺髻盘旋。仔细端详。满眼都是美,满眼都是动人的细节,细腻得甚至连舞动的飞天,背景上的花纹都逼真生动,栩栩如生。这一切都无碍地组成了庄严的佛界。
这是一件无价之宝。是李风强及工匠们一刀一刀刻出来的。或许他们每刻一刀,都会虔诚的默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龙华三会》能供奉在天宁宝塔,其中也有一段奇缘,这件宝物本来已经在全国博览会上得了金奖,只是在李风强有缘参观了天宁宝塔以后,这灵山群佛便到天宁宝塔聚首来了。
这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福分。
灵山法筵,至今未散。对于每一位信士,信心愈坚,愿海愈涸,法界愈大。佛祖正在灵山拈花微笑。
佛祖的家乡确有一座灵山。这座灵山位于今印度北部比哈尔邦拉杰吉尔地区。这是一座高不过数百米的黑黝黝的山,岩石裸露,没有繁密树林,点缀着一些低矮的杂树,四周被五座小山峰簇拥着。当年的释迦牟尼在青少年时代,曾经四出云游,到处参学,乞食度日,并在王舍城附近的灵山上趺坐苦修。现供奉在天宁宝塔里的一尊水晶大佛,便来自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蓝毗尼。这是一尊天然水晶佛像,是世界上最大的整块天然水晶制成,产于15世纪的尼泊尔。佛像高57公分,重50公斤。上世纪40年代由丹麦驻印度大使带回丹麦,后由旅泰华侨高培芝先生辗转出巨资购得,在中国驻丹麦大使馆文化参赞的协助下,派人护送回国,有缘供奉在天宁宝塔里。
就在天宁宝塔建造以来,各种宝物是纷至沓来,有新加坡法王赠送的佛血舍利于,有高培芝先生供奉的唐代石刻佛像。有造型别致的宋、明古佛……
我六根未净,不具备佛的法眼,无法洞悉其中的因缘。但我懂得,爱就是缘,缘便是爱。有诗曰:
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你心头。
人人有座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
每个人的心里都应该有一座灵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