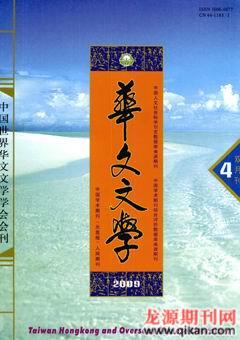王鼎钧散文的家园情愫与文化认同
彭燕彬
摘要:旅美华裔散文大家王鼎钧的散文创作颇具感性和知性,其中蕴含的家园情愫极为丰富而具有感染力,而对齐鲁文化的传承与认同,则是王鼎钧散文的一条隐含的线索。
关键词:王鼎钧;家园情愫;齐鲁风范;文化认同
Abstract:The Chinese American prose writer Wang Dingjuns proses are full of emotions and wisdom. Viewing from the angle of “home complex”, this thesis is aimed at explicating Wangs creative motive and elaborating on the unavoidability and universality of “home complex,” which has strong connections with Qilu culture and leads to the issue of cultural identity, a common theme in literature.
Key words:Wang Dingjun, home complex, Qilu culture, cultural identity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09)4-0060-04
一
旅美华裔散文大家王鼎钧先生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文坛常青树”,其作品被称为台湾散文的“崛起的山梁”。早在上个世纪,鼎钧先生就是台湾文坛公认的散文大师,他的文学创作,从大陆到台北直至纽约,可谓文学生命丰富。他的笔触向国人的眼泪与痛苦、微笑和希望,在他的多元化体例的创作中,以散文最具感性和知性,力求将小说戏剧技巧溶入散文之中,沉郁顿挫,求真唯美,儒雅有致。
遗憾的是,笔者才识浮浅,初识鼎钧先生之作,是在网上偶读工人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昨天的云》以及尔雅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碎琉璃》等书中的部分篇目,扪心的感悟即是“山梁的回望”,便急于求得先生更多原著一睹为快,无奈“洛阳纸贵”遍寻不得,忽接江苏文艺出版社小蔡编辑寄来2009年出版的《一方阳光》,称受鼎均先生之托邮寄,不禁感动有加,与鼎钧先生可称为同乡的笔者论年龄应尊先生为前辈了,承蒙厚爱方得一睹为快。掩卷后思,《一方阳光》让笔者在品读中感受到了博大精深、恢宏厚重的齐鲁风范。不可否认,鼎钧先生的家园情愫犹如一潭深不可测的清泉汩汩上涌,无论是漂浮于上世纪“昨天的云”还是现今俯视人间的“一方阳光”,字里行间始终渗透着一位久居异域牵挂故乡的山东“大汉”那不乏阳刚之美的丰厚情意。
“家园情愫”是普遍存在于中外文学作品和作家创作过程中的文学母题,是人类经历了漫长进化过程后形成的一种古老的、永恒的情结,本质上它是一种文化认同的衍生物,涵括了由于地理分割而在文学风貌上产生迥异的旅居他国华人作家与故地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内质。“家园”作为人心灵的归属地,有着极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特别是当人们遭受到挫折、漂泊异乡,处于孤独无依的境地的时候,更会对“家园”产生强烈的向往。这种力量一旦受到压抑(如漂泊、放逐),必然要表现出来,形成一种“情愫”。文化诞生以后,以“家园”借代文化,或者以文化指称“家园”,就成为一种互释关系。以“文化”为内涵的“家园”,从此就跳脱了个体的范畴,积淀为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就是“文化认同”。作为少小离家迁徙异域的作家,对汉文化,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依恋深深地掩藏在心灵中,在外在形态上它表现为:故乡、母亲、心灵归宿、精神依托等,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富有象征意蕴的意象。由于它既作为个体无意识又作为集体无意识存在于创作者的思想中,必然会影响到作家的创作和文本的形成。同时,出于多种原因,这种情结在其作品中表现得愈加明显。
因此,笔者认为,通常文学中的“家园情愫”通常主要表现为两大类:一是直接的家园意识。乡愁作为一种怀念故乡的忧伤的心情,从古至今都被文人墨客无数次反复吟唱。而细读鼎钧先生的散文,其笔下那种恋乡、恋土的情愫都建立在以“家”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体系中,抒发了对故乡的无尽思念。通过写家园来写文化,写认同感,写归属感。二是对抗异质文化,固守心灵家园。这一表现从更深的层次分析,仍要归结到对传统文化、母体文化的认同上。具体到鼎钧先生的创作层面,又包含了更多独特的文学意义和内涵。这里最为重要的体现为心灵精神家园层面上的乡愁,主要是书写人们精神家园的失守和人性的缺失,表达了作者对精神家园不懈的追寻,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具有指向性的结论:“乡愁”。作为一种“家园情愫”的外在表现形式,“乡愁”是一种文化认同感的有效表达。就心灵精神家园层面的乡愁说,它所要解决的是一个对抗机械时代和人的异化的工具问题。这种工具不是靠想当然或是随手拈来就可以得到的,它需要具备为作家和读者所熟悉的题材、具有对抗时代的力量、具备对抗物化、异化的精神状态。倘若具备这样特点,文化无疑是最优之选,而选择哪一种文化,通常情况下是作家和读者最为熟悉的那一种。这样,“文化认同”就在这里产生了。
当把鼎钧先生的散文创作作为一个主体看待时,我们发现其符合了这样的条件:第一,融入了齐鲁文化(这一过程己经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第二,与群体的分离(在这里表现为与祖国大陆的分离,如果把齐鲁文化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的话,它无疑符合这一点);第三,孤独感和疏离感的产生(长达50年之久的异域生活现状与外来文化与自身传统文化的隔膜导致了这种孤独感和疏离感的产生);第四,向往精神家园(具体表现在对文化认同、文化寻根和精神家园的追寻上)。这些必要条件就催生了鼎钧先生强烈的“家园寻根意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生成一种文化。而由儒家文化伦理政治类型所决定的齐鲁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在总体上呈现一种以人生和人心为观照的特点,它的主体精神与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有很多相通重叠处,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的儒、道、墨、法等诸家人生价值观念及特定思维方式和共同作用于民族的社会心理及价值观念。作为至今都在操着一口浓重乡音的鼎钧先生,无疑,其创作的“文化认同”表现的颇为独特:血浓于水的母爱亲情、刻骨铭心的乡愁情怀、崇尚气节的精神境界以及仁德为本的礼治之道。
鉴于此,笔者意欲从家园情愫这一角度切入,阐释鼎钧先生散文创作主旨,并从具体的文本分析中得出“家园情愫”存在的必然性和普遍性,以及与齐鲁文化的融会贯通,同时表明文化认同的不可避免性和在文学创作中的普遍性及其传承。
二
综观鼎钧先生创作领域,由于情境的差别、风格的变易和作品体裁样貌转换,以及受齐鲁传统文化的认同感的时间差的影响,使得“家园情愫”在其创作中呈现出如下模式且涵盖了其书写场域中所有表现。
(一)“仁爱”、“孝亲”伦理原则下的童趣、母爱亲情
儒家所阐发的道德伦理学说是在中国古代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上,总结了当时宗法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关系而提出的,“仁爱”、“孝亲”已成为一种浑然之德深入到民心之中。而被历代作家开掘了千百年的母爱主题丰厚精深且无不让人淆然涕下,岳母刺字“精忠报国”之爱,爱的理智悲壮,大气凛然。因而,鼎钧先生即为自己笔下的母亲赋予了“百姓母亲”的灵魂与灵性之爱,亦仍不乏母爱震慑力且更备亲和力。这种具有世界上最高贵人性的母爱元素在他回忆性散文《一方阳光》中自己母亲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双谨慎而矜持的小脚,走进阳光,停在墩旁……一只生着褐色虎纹的狸猫……跳上她的膝盖……一个男孩蹲在膝前,用心翻弄针线筐里面的东西……替母亲把绣线穿进若有若无的针孔”,好一幅温馨和谐的人猫嬉戏图,动乱年代里能展现如此这般童趣、母爱的亲情,不能不说作者心灵深处尚存的那永不铭忘的“一方阳光”的暖意了。童年时代的美好记忆总会成为成年人平衡心理、抵御现实侵压的精神和力量的源头。对处于异乡异地的成年人来说,孤寂、陌生、疏离等处境与心境,往往会很自然地促使他们追忆往昔美好的时光,以求得精神慰藉。以童年视角来看成人世界,成人世界的痛苦和不幸通过善良和天真的眼睛的过滤,形成了一种饱含着哀愁的美学力量——“猫捉老鼠的故事”、“纠正错别字”、“母亲冻坏的双脚”以及“碎琉璃的梦”。因此,他的“家园情愫”具有双重的内涵:一方面,童年在作者记忆中是美好的、快乐的、无忧无虑的,这样的记忆表现了他对现实的回避;另一方面,作者在童年的生活中从梦中解到了“一个好象琉璃做成的世界完全毁坏”的意象,也看到了生活本来的残酷面目,他在文本中思索着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因而,这种思索是文化性的,它也通过作家的笔,传达给了读者。
(二)“齐家”意识下刻骨铭心的乡愁情怀
齐鲁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始终对山东人的人生价值取向起着主导作用,其中“齐家”占中心地位。山东人讲究 “父母在,不远游”,既有“孝”的成分,又反映其家园观念比较强烈。家园是游子漂泊的终点和奋斗的精神目标,所以,找寻家园的过程是一个流变的过程,离乡—漂泊—返家的过程是一个人自我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从文化角度审视自我的过程,在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中,人往往能够确立自我评判的价值体系,确立自己精神追求的目标。
鼎钧先生大部分作品题材取自于1949年以前在大陆时的青少年时代的经历。他对山东老家有着解不开的浓浓情结。“还乡,我在梦中作过一千次,我在金黄色的麦浪上滑行而归,不折断一根芒尖。月光下,危楼蹒跚起步迎我,一路上洒着碎砖。柳林全飘着黑亮的细丝,有似秀发……”这些感人肺腑的句子都写给了故乡,但在他太长久的漂泊生涯中却没有踏上过故乡的土地,也许正如其坦言回答的那般:“因为亲人都已不在了,故乡也已经不是从前的故乡了......”。这种无奈的忧伤,正可以表明他是一个如此珍视自己记忆的人,因着太有情,太爱,而只能以看似无情的做法而完好地保留自己心目中的故乡。对此,他继续感叹到:“还乡对我能有什么意义呢?……对我来说,那还不是由一个异乡到另一个异乡?还不是由一个业已被人接受的异乡到一个不熟悉不适应的乡?……回去,还不是一个仓皇失措张口结舌的异乡人”。尽管如此,在他那沧桑回望中,执着认定“已经为了身在异乡、思念故乡而饱受责难,不能为了回到故乡、怀念异乡再受责难”,于是,就有了在纽约华人中秋聚会上的“举座愀然,猛灌茅台”之举。这种乡愁情怀更可谓刻骨铭心,创痕累累。从鼎钧先生多篇作品中,几乎都可以找到回忆的时光。对于中国人来说,乡土、家园、根是几个具有内在相关性的话语形式。对于有着独特文化传统的华夏子民来说,家,就是生命本源、根之所在、情之所归。对故乡的回忆和眷恋早己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一个不竭的源泉。恰恰鼎钧先生以传统的家园情愫作为书写内核,炽热地表现了一种质朴的乡土追求法则。一方面,它体现了远在故乡之外的人对家的渴望,如《吾乡》“好酒出在自己的故乡”,《一方阳光》里的童趣,《红头绳儿》的悲情,《青纱帐》里的冤屈,甚而还糅合了《园艺》的悟道,很难说这不是“齐家”意识的流露,字里行间中自然地唤起了人在异域的乡愁。另一方面,随着狂热的“移民大潮”迁徙异域的作者,曾经感受到巨大的心理落差,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为了慰藉倍感失落的心灵,家园情愫便骤然占据书写心灵。同时,为了避免精神空虚和无根的漂泊感,加之对故土传统文化的依赖,自然而然希冀通过文学创作消除精神的裂痕,呵护脆弱的内心,维持感情的平衡。对此,作者不无诙谐地认定:“乡愁是美学,不是经济学。思乡不需要奖赏,也用不着和别人竞赛。我的乡愁是浪漫而略近颓废的,带着象感冒一样的温柔”。
(三)“崇尚气节”精神下的与异质文化的对抗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德向善的民族。崇德向善成为中华民族自觉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成为中华民族国民性格、价值观念的重要内容,并造就了中华民族崇尚气节的精神。齐鲁文化特别强调道德人格价值,高度崇敬人格精神。孔子强调“志”之于人的重要性:“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肯定人人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意志,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而改变,不因外界的压力而屈从,鼓励人们无论贫富穷通,都要坚持道义理想,关键时能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维护道义。即使是不得志的士人也能做到“穷则独善其身”,不为穷变节,不为金易志,维护正义,表现了高尚的气节。鼎钧先生的义志笔力始终是坚韧有余的,不愧为一个道地的山东人。仅仅表现抗日战争的几篇数千字的散文,就足足让读者从沾着血泪的笔尖下重新目睹战争的残酷、侵略者残忍、国人的民族气节——碎琉璃梦中那位“先被玻璃碎片刺穿了心”却不弃怀中孩子的母亲,赤足屹立在一个琉璃做成完全毁坏了的世界里,丝毫不畏惧那几十把闪烁着着磷一般的火焰且锋利的宛如纯钢打造的琉璃刀尖无情的威吓……然而与如此“舐犊之情”大相径庭的是,鼎钧先生又将一对深明大义的父母的情怀展示给读者:面临着苟全性命的乱世,是让幼子留在家中接受殖民教育,抑或把儿子献给民族的抗战事业孤身去抗战后方求学,成为了双亲无可逃避的难题。最终,注重民族气节的父母顺应民族大义,毅然舍弃了亲情,送子到抗战将领办的学校里接受教育,望子成长后报效祖国,重整河山,收复失地。这又怎么不是另一种爱子(忠国)之情呢?亲情如此,人格价值亦为高贵,鼎钧先生笔连续触向有良知的校长和他美丽的女儿“红头绳儿”、辗转参战的舅舅、坚持信仰的荆石老师、心地善良的战地护士等人物,在有限的篇幅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战争对美的毁灭和不能愈合的心灵伤痕,刻画了一个个有骨气、有使命感的大众战士的形象。他们的血液里流淌著不屈的生存智慧,并用这种智慧延续着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文化。这种具有传承性的爱国情感和深刻的民族意识,无疑是深藏于民族文化之中并经由民族文化的种种形式层面体现出来,表现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就是民族的精神支柱,永远值得后人欣赏和颂扬的。
综上所述,可以清晰地看到,在鼎钧先生的创作思绪中,家园情愫并未因其长居域外而有所中断或减弱,对于儒家思想,无论是自觉的遵循,还是无意识的循规蹈矩,依然具有巨大的支配力量。诚然,外来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巨大震慑是他无法改变生存主流的创作现实,作为一介文人,寄寓他国的社会地位使自己不得不接受新的社会思想秩序和流行规范以适应社会结构的巨变和固有人伦关系的破坏。于是,以往烦琐的礼教秩序被简化了,以往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逐渐演变为内在精神支撑的民间道德。总之,齐鲁传承文化的发展与鼎钧先生创作倾向这两条文化轨迹的不谋而合,或许有历史巧合方面的因素,但大文化整合所带来的相互吸收和影响更应该是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正如台湾学者蔡倩茹在她的力作《王鼎钧论》中认定:王鼎钧以他的生命历程创造了一种可能性,纵然生命的年轮里,有太多时代的辙痕,在他作品中,却能将根须吸收的人生经验加以升华,复能在文路上日益精进,无论是理性的哲思,或是抒情的时代刻划,都给人宽厚的温暖、清明的指引、心灵的飨宴,彷佛那浓浓的树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