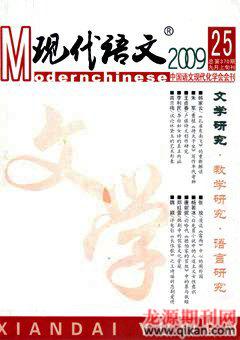《聊斋志异》的故事类型及创作动因
摘 要:本文认为根据《聊斋志异》的内容和作者不同的创作心理,可以将《聊斋志异》的故事分为志怪、劝世、自慰三种类型。其创作动因分别是由于作者具有“雅爱搜神”、“喜人谈鬼”的性格,“赏善罚恶”的文学观念以及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的欲望的转移。
关键词:古典文学 明清文学 《聊斋志异》 故事分类 创作动因
蒲松龄为《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写过一篇题为《聊斋自志》(以下简称《自志》)的序言,其中详述了自己创作《聊斋》的动机。后世研究者多根据其中“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一句,断定《聊斋》“是作者有所寄托的,而不是‘妄言妄听,记而存之的作品”[1],是“借鬼神世界反映、映射人间生活和社会现实,而加以批判、揭露、来发泄自己的悲愤的”[2]。进而将《聊斋》故事概括为描写爱情,反对封建礼教;揭露封建社会政治的黑暗,赞扬人民的反抗斗争;抨击科举制度的罪恶三大类型。这种看法,为大多数文学辞典所采用,几乎已成定论。
但究其实,这种说法不但远不能涵盖卷帙浩繁,主题多样的《聊斋》的全部内容,而且是对《聊斋》以偏概全的一种误解,是今人将按现代政治标准制作的高帽硬套在蒲松龄的头上。
其实,根据《聊斋》的内容和作者不同的创作动机,可将其故事划分为三种类型:即志怪类、劝世类、自慰类。详如下:
一、奇猎异“记而存之”的志怪作品
蒲松龄在《自志》中直言自己“雅爱搜神”、“喜人谈鬼”,记载的是“事或奇于断发之乡”,“怪有过于飞头之国”的奇闻异事。高珩在为《聊斋》作序时指出《聊斋》是“为齐谐滥觞”。邹弢《三借庐笔谈》载作者著作此书时,常设烟酒于道旁,“见行者过,必强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 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可见,搜奇猎异是作者性格旨趣所在, “记而存之”是事实。如果事不奇,闻不异,是没有资格进入《聊斋》的。此点甚明,滋不赘述。
《聊斋》中纯为志怪,别无寄托的作品篇目甚多,不下全部作品之半数。其中多为短章,如《瓜异》篇载:“康熙二十六年六月,邑西村民圃中,黄瓜上复生蔓,结西瓜一枚,大如碗”;又如《赤字》篇:“顺治乙末冬夜,天上赤字如火,其文曰:‘白苕代靖否复议朝治驰”,都只有二十多个字。有一些篇目稍长,如《夜叉国》,但较少见。
该类志怪,除了记载荒诞不经的神鬼故事外,还记述一些奇怪少见的人情物理。其中有的是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真事:如《真定女》记真定有一个女孩不到十一岁怀孕生子;《金永年》载金永年夫妇八十高龄才开始生育;《蛇癖》描述作者同乡卢奉宁喜欢生吃活蛇的情状等等。现代社会也不断有报道见诸报端,有的是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道听途说,如《蛤》篇载东海有一种蛤,肚子内寄生小螃蟹,蛤蟹之间有线相连,二物同生共死。又如《元宝》篇说广东临江山山上长着元宝,无缘者取不下来,有缘者可随手摘下,而摘下来之后,原处马上又长出新元宝。
这些作品,无论其篇幅短长,事情真假,作者在其间并无褒贬,更谈不上寄托、孤愤,只是“志而曰异,明其不同于常也”[3]罢了。这一点,作者不自讳,我们实在也无需为作者讳。
该类作品,因是作者“妄言妄听,记而存之”的产物,数量虽多,但质量不高。
二、“赏善罚恶与安义命”的劝世作品
不可否认的是,“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包含了作者的思想真实。但这孤愤,并非全是反封建、反礼教、反科举的孤愤。
蒲松龄作为一个“吾儒家自居”的封建文人,一生痴恋举业,五十多岁“犹不忘进取”(蒲松龄《原配刘儒人行实》),七十二岁时其长孙考中,他作诗勉励云“无似乃祖空白头,一经终老良足羞”。可见他并不反对科举,其作品中大量宣扬褒奖忠孝节义的故事,足证其不反礼教,更不反封建。
前人早已指出,《聊斋》“论断大义,皆本于赏善罚淫与安义命之旨”[4]。通过“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的故事模式,劝谕世人积德行善、忠孝节义、戒恶去淫,是《聊斋》故事的又一类型。
《聊斋》中的一些篇章,是直接因此而结撰的现实故事。如《珊瑚》、《曾友于》诸篇就写主人公委曲求全,孝双亲,友兄弟,而终于获得好结果。大成二成兄弟(《珊瑚》),大成孝悌,结果是“生三子,举两进士”,二成不孝悌,结果“生十胎皆不育,以兄子为子”。有些篇章,渗入神异内容,但旨归依然在于劝世。如《张不量》叙述张不量因为乐善好施,一次天雨冰雹,把周围的庄稼都损坏了,独他家的庄稼没事,是劝谕世人要为富而仁。《杜小雷》写杜小雷的妻子因不孝婆母,被神罚变为母猪,劝人孝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公式,神鬼概莫能外:《王六郎》、《水莽鬼》的主人公都因为不肯找替死鬼,救了人命而得以脱离鬼道,升为神道;《考弊司》、《席方平》中的鬼王、阎罗王都因为贪虐而受到更高一级神的责罚,被囚、被刑、被打入轮回受苦。这样的故事,其目的依然在于劝世。
有一些故事的写作旨趣虽另有所属,但作者仍然在其中加上一些因果报应来劝世。例如《聂小倩》、《小谢》等篇,主旨在写男女之情,但故事当中,却有赏善罚淫等内容:宁采臣、陶生因为“有刚肠”,经得起财色诱惑,结果鬼妖不能加害,他们也因此而得到剑仙、道士的帮助,最终赢得美人归。而兰溪生主仆,宁采臣的仆人(《聂小倩》)留守荒园的苍头们(《小谢》)却因经不起诱惑而死于非命,正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再如《马介甫》,其主题是一个悍妇故事,作者在最后却不忘点出悍妇尹氏最终“依乞者而食”的下场,以作为对不守妇道不孝公婆者的警戒。
三、“抱树自温”、“偎栏自热”的自慰作品
《自志》中有语云:“惊霜寒雀,抱树自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此语好像历来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其实,这正是作者创作心态的自道。明此语,即可明《聊斋》之人鬼相恋故事。
蒲松龄一生贫困,“惟农场住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大半生过的是远离亲人,“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大江东去]《寄王如水》)的私塾教师生涯。贫困寂寞之中,种种失意与欲望,不免时时侵扰作者,现实中得不到的金钱美女,富贵功名,作者转而求之于精心结撰的狐鬼世界。
《聊斋》中最精彩,最有文学韵味的作品,是女狐女鬼的故事。这些故事,剔去狐鬼花妖的外壳,事实是男人(往往是穷书生)和美女的故事。
《聊斋》中的女狐、女鬼、女神仙,其可爱远远超出现实中的美女,她们可以满足男人的一切欲望。首先,这些女狐女鬼“媚丽欲绝”、“肌肤流霞”、“纤腰盈掬”、“娇波流慧”、“吹气如兰”,都是“世罕有其匹”的大美人。其次,这些美女十分容易到手,往往一见钟情,立即结合,甚至“自荐枕席”,“不费一钱,夜夜自投到”。又因为这些美女是异类,男人可以随心所欲,不负任何责任,甚至可以“春风一度,即别东西”。更妙的是,这些美女一点也不妒忌,男主人公往往同时一夫共二女或三女,左拥右抱,大享齐人之福。
这些异类美女,不但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男人的色欲,而且可以满足男人的财欲以及其他种种欲望。美女自投而到时,往往同时带来大量财富,使男人过上锦衣玉食富比王侯的生活;至少也善于经营,凭着本身的术法,帮助穷书生摆脱贫困,专心举业,金榜题名,从此富且贵;甚至穷书生因之而得道成仙,永远脱离凡世苦海。
弗洛伊德说:“人们在生活中或是由于社会原因,或是由于自然原因,实现不了某些愿望,文学给予替代性的满足,使他们疲倦的灵魂得到滋润和养息。”[5]《聊斋》中的书生遇女鬼故事,正是这样的文学。男人在现实中实现不了甚至羞于启齿的种种欲望,在此都轻而易举地得到满足。这些文学故事,由于来自灵魂深处,作者写作时投入了最大的热情,所以特别的委婉动人,实在是《聊斋》中最精彩的交响曲。
参考文献:
[1]游国恩.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刘大杰.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高珩.聊斋志异·序[M].济南:齐鲁书社,1995.
[4]马振方校.唐梦贲.聊斋志异·序[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5][奥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7.
[6]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
[7]朱振武.聊斋志异的创作心理论略[J].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1,(10).
(罗朋非 广东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52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