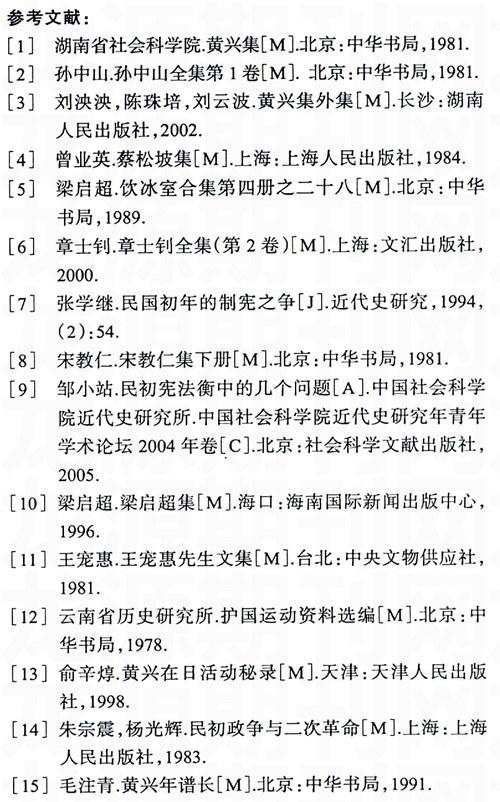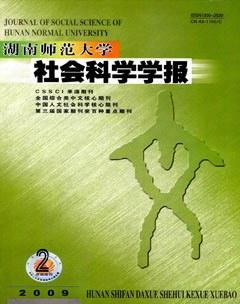论黄兴的宪法思想及实践
邓江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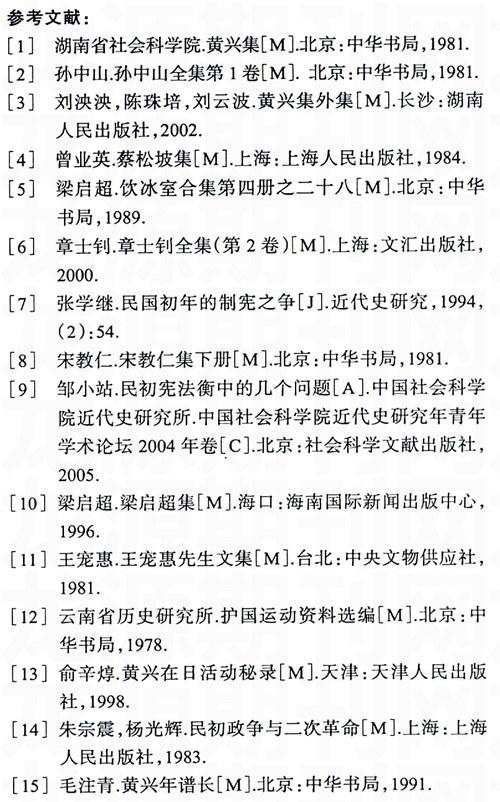
摘要:民国初年,黄兴极为注重民国宪法的问题,反复强调宪法对于中华民国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坚决主张民权主义的立宪原则,并强烈要求依法治国,希望把中国建成法治国家。黄兴的宪法思想和实践不仅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而且对于当今中国宪法的发展仍然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黄兴;宪法;民权;法治
中图分类号:K84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529(2009)02-0059-04
辛亥革命后,黄兴在强调民国以人民为主人,呼吁赋予人民以平等自由权利的同时,还极为注重民国宪法的问题,反复强调宪法对于中华民国的重要意义和作用,积极主张制定民国宪法,确立民权主义的立宪原则,为实施平民政治、推行宪政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使中国成为法治国家。由于黄兴的英年早逝,其宪法思想还不太完善和成熟,但仍不乏真知灼见,在当时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资产阶级法制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一
在研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论的过程中,黄兴对资产阶级宪法及其作用给予了高度重视。他认为,“宪法者,人民之保障,国家强弱之所系焉也。宪法而良,国家日臻于强盛;宪法不良,国家日即于危弱。因此,1906年,他在与孙中山、章太炎等人制定的《同盟会宣言》中就提出,推翻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国后,要“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辛亥革命成功后,黄兴指出,“建设共和国家之第一著,首在制定宪法”,并反复强调宪法对于中华民国的重要意义和作用:第一,宪法是立国之基。他认为,“此次革命,因全国人民厌恶专制国体。改造共和国体”,因此,民国建立后必须制定宪法,确立共和政体,以防止封建势力复辟。他说:“善建国者,立国于不拔之基,措国于不倾之地。宪法作用,实有不倾不拔之性质”。1912年3月,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的国家制度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并根据“三权分立”的原则确定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相互分立又相互制约的国家权力运行机制。对此,黄兴坚决拥护,并强调“约法为吾国共和政体之根本法”。第二,宪法是民权之本。黄兴认为,“国民生命财产权专恃法律为保护,即共和国精神所托”。他指出:“世界人类,无论黑白,均欲恢复固有之自由权。美国离英独立宣言,以力争人民自由而流血;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为扫专制回复民权之铁证。……南京政府颁布约法,中华民国人民有身体居住之自由,信教之自由,言论出版之自由,此法律保障人民自由之特权。”他还强调,正式宪法成立之前,《中华民国I临时约法》是“人人所当共同遵守者也”。第三,宪法是政治之依。黄兴十分重视宪法对政治的制约作用,认为共和国政治的运作应以宪法为依据,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他强调:“国会应注意立法,法立而政治有依据。只问政治,则政治愈纷乱而不可收拾。”
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约法施行后10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制定正式宪法。为保证正式宪法继续坚持和发扬《临时约法》的民主共和原则,1912年下半年之后,黄兴对宪法的制定极为关注。他多次指出:“现今最重大者,乃民国宪法问题。盖此后吾民国于事实上,将演出何种政体,将来政治上之影响良恶如何,全视乎民国宪法如何始能断定。”作为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强调,国民党“负建设之责任,至繁至巨,首应注意宪法,以固国家之基础”。对于民国宪法的问题,“吾党万不能不出全力以研究之,务期以良好宪法,树立民国之根本。”他号召国民党党员,“将制定宪法为吾党莫大之责任,吾党国会议员,应以平日之学问,出而为临时之讨论。而全体党员之优秀者,尤当以远大之眼光,缜密之心思,悉心商酌,发表所见,为吾党国会议员讨论之助,并以转饷一般人民。护国战争胜利后,黄兴又及时指出,国会恢复后“第一之重要问题,则制定宪法是也”。同时,黄兴汲取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深刻教训,提醒国会议员:“今日制定宪法,必须贯彻共和之真精神。而首先注意者,应加入‘凡反对国体者有罪之一条。……若宪法有此条,则处置此等刑犯可大得便利。盖国家之内,万不能无公共之是非。此等条文,实所以彰顺逆之大义,而宪法中所万不可少者也。”这说明黄兴在实践中对宪法巩固共和政体作用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二
控制国家权力、保证公民权利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宪法最根本的特征。在民初宪法的制定方面,黄兴坚决主张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立宪原则,并与袁世凯及其拥护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抵制袁世凯攫取宪法起草权。1912年10月以后,从速制定正式宪法的呼声甚高,而关于宪法问题的讨论也十分热烈。其中,对于宪法起草机关的问题,是各派争论和斗争的焦点之一。因为制宪权控制在谁的手里,关系到宪法按谁的意志制订,对谁有利的根本问题。《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但仍有一些人公然提出异议。崇尚国权主义的云南都督蔡锷认为,如果正式宪法由国会制定,“难保不偏重党见,趋于极端,徒为防制行政首长之条规,致失国家活动之能力”,于是向袁世凯建议,“密召海内贤达”,如梁启超、杨度等人速将宪法草案拟订,由他“联合各省都督先期提出,以资研究而征同意,期收先人为主之效”。梁启超则以美国1787宪法草案为例,主张专设宪法起草机关,“将国中最有学识经验之人,网罗于起草员中,使专心致志,为有价值之讨论以止于至善”,并认为“起草员不可有丝毫党派之意见杂乎其间,庶不致有所偏蔽”。章士钊与梁启超的观点相似,主张“国会以外,必设法制局,以精于法学者掌其事”,并策划由江苏都督程德全出面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建议由各省推举两名“学高行修,识宏才俊”之士,于国会之外另组宪法起草委员会负责宪法的起草工作。蔡锷、粱启超、章士钊等人的主张正合袁世凯的心意,他立即通电各都督,要他们“先各推举二员来京,在此案未得参议院通过以前,暂作为研究宪法委员,共同讨论宪法大旨。如将来此案得到参议院通过,即以此项人员作为编拟宪法草案委员”。按照袁世凯的命令,各省都督推荐代表48人,国务院推荐代表6人,组织了宪法起草委员会。这些人员,绝大多数是北洋派或政治上拥袁的人物,许多人还是总统府和国务院的秘书。袁世凯的如意算盘就是要把宪法起草委员会变成御用的宪法起草机关。黄兴等国民党人坚决反对袁世凯及拥袁势力操纵制宪权。黄兴认为,“民国成立,国民即为主人翁”,国会为“代表民意”的机关,“若夫宪法起草,拟由各政团先拟草案,将来由国会提出,于法理事实,均无不合”。宋教仁也直截了当地指出:“宪法问题,当然用于国会自订,毋庸纷扰。”国民党机关报《中华民报》、《民立报》、《国民杂志》等也纷纷发表评论,揭露袁世凯设立宪法起草委员会,乃“思攫取国会之宪法起草权”,并强调:“制定宪法为议院惟一之权,无论何人不能干预”,如果袁世凯另立机
关起草宪法,“国民必不承认”。由于黄兴、宋教仁等国民党人的坚决抵制,1913年3月3日,临时参议院理所当然地否决了袁世凯交议的《编拟宪法草案委员会大纲案》,打破了袁世凯及拥袁势力操纵制宪权的企图。
2.主张以民权主义为制宪的基本原则。1913年4月第一届国会成立后,制宪被提上议事日程。于是,围绕宪法的内容,各派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其中,以什么样的原则制宪成为各方交锋的焦点。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及其他拥袁势力主张取国权主义,扩大总统权力。蔡锷主张,“民国宪法宜以巩固国权为主义”,提出制宪必须贯彻两条方针:第一,“必建造强固有力之政府”;第二,“必适合中国之现情”,同时必须先决两大问题:第一,“大总统不可不有解散议会权”;第二,“任命国务员不必求国会之同意”。对于蔡锷的上述主张,袁世凯非常满意,授意总统府秘书厅密电各省都督,征求意见。北洋派及拥袁的各省都督都表示赞同。冯国璋称赞蔡锷主张“实为民国救亡关键”,并要求以之“为编纂(宪法)根据,毋再拘牵约法条文”。陕西都督张凤翔则进一步提出:大总统有解散议会权、制定官制官规权、法律案裁可权,总统任命国务员无须国会同意以及总统任期七年,应当写入宪法。进步党首领梁启超也主张宪法采国权主义,他在《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提出,“临时约法第二条采主权在民说,与国家性质不相容,无论何种国体,主权皆在国家。”而黄兴等国民党人士则坚持主权在民的立宪原则,坚决主张宪法以保护民权为宗旨。黄兴指出,“欲实行民主制度,必扩张民权”。“国家新订法律,事事皆求保障国民”。他还强调指出:“人民被治于法治国之下,得享受法律之自由;人民被治于专制政府之下,生杀由一人之喜怒,无所谓法律,人民之生命财产,无法律正当之保护,民权亦从此泯绝。故共和立宪政体,以保障民权为前提。”国民党内的法学专家王宠惠在《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中指出,共和国之主权,当然属于国民全体,“主权在国民,乃共和国体最要之原理”,共和与非共和政体之区别亦“全在此点”。并强调,“宪法非因一人而定,乃因一国而定,非因一时而定,乃因永久而定。”阅读了王宠惠《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之后,黄兴击节赞赏,立刻致书王宠惠,称之为“最为不刊之论”。并说:“弟久欲撮斯议通电全国,使人人皆明公义,不敢自私,所谓宪法研究会之手段及各省都督之主张,可一扫而空之。”他还坚信,“兹大著出,而宪法之真义昭如日月,其爝火自熄矣”。由于黄兴等国民党人坚持民权主义立宪原则,第一届国会1913年10月起草的《天坛宪草》基本上沿袭了《临时约法》的精神和原则,但尚未成为正式宪法就被袁世凯扼杀于摇篮之中。
3,反对袁世凯的《中华民国约法》。“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公然下令停止全体国会议员职务,解散了国会,利用“约法会议”这一御用工具于1914年4月29日通过了所谓的《中华民国约法》。这个约法否定了主权在民的原则,对人民享有的各项自由权则都加上了“于法律范围内”的限制条件,同时修改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内阁制原则,否定“三权分立”原则,把总统的权力提高到如同封建皇帝一样。黄兴认为这个袁记约法从根本上违背了宪法保障人民权利的原则,“决非共和政体的宪法”,并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袁世凯死后,梦想爬上总统宝座的北洋军阀段祺瑞按照袁世凯的遗言通电全国,宣称依据袁世凯《中华民国约法》第二十九条由黎元洪代任总统。这就与《临时约法》第五条“在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至本任大总统期满之日止”的规定相违背。表面上看,“代任”与“继任”仅一字差,似乎差别不大,但实际上却关系到袁世凯倒台之后哪部约法具有宪法上之效力的重大问题。这样就引发了1914年袁世凯“私造”的《中华民国约法》和孙中山1912年颁布的《临时约法》之争。在这场争论之中,黄兴坚决主张废除袁记约法,恢复《临时约法》。他通电全国指出:“不声明恢复元年约法,及遵照二年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由副总统继任,而蒙混提出袁氏预备称帝时伪造之约法二十九条,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是仍以伪法乱国法。”他还致电总统黎元洪,要求他“排除莠言,迅速解决,以适法之命令,废去袁氏伪造约法。”最后,在各方面压力之下,段祺瑞被迫屈服。6月29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名义发表申令:“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宪法之一部,应仍有效。”至此,历时近一月的新旧约法之争,最终以《临时约法》和国会的恢复丽结束。黄兴在这场争论中所提出的主张是其民权主义立宪思想的又一反映。
三
黄兴不仅强调宪法重要意义、重视宪法创制原则,还十分重视宪法的实施,主张依法治国,使民国成为“法治国”,并在实践中注意维护宪法权威,反对各种违法行为。
1.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剥夺任何人的权利和自由。人身自由是一项最基本的人权,公民的人身自由得不到保障,就谈不到人的尊严以及民主权利的行使。《临时约法》规定:“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但当时在一些地方,军政当局动辄以军法为名滥杀无辜的事情时有发生。这些违法行为引起黄兴的高度关注。1912年3月20日,常州军政分府司令赵乐群携私残杀常州中学堂学监陈大复。案发后,“舆论均谓可杀”。但为了“以示尊重法律,拥护人权”,时任南京留守的黄兴主张按律严办,指示第三军军长王芝祥会同有关师旅长及常州军法局局长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团“迭开军法会审,……调齐人证,悉心研讯”,“经取具确供,复汇案呈请大总统,饬交陆军部复核”之后,才依法判处赵乐群死刑,并于6月4日执行处决。事后,黄兴要求袁世凯将“将此案情形,宣布全国,使知以私意杀人,虽职官亦与平民同科,庶各地滥杀之风可以渐止,人民乃得受法律上之保障,于保护国民权之中,寓尊重国家法权之意”。1912年8月15日,袁世凯与黎元洪狼狈为奸,将武昌起义领导人之一、时任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的张振武及将校团团长方维诱骗至京,秘密逮捕并于次日凌晨枪决。张、方二人被杀后,全国舆论哗然。袁世凯遂将责任推给黎元洪,黎则以张蓄谋结党,颠覆共和为自己辩解。黄兴闻讯后,立即致电袁世凯诘问其中缘由,并严正指出:“凡有法律之国,无论何级长官,均不能于法外擅为生杀。今不经裁判,竟将创造共和有功之人立予枪毙,人权国法,破坏俱尽。……纵使张、方对于都督个人有不轨之嫌疑,亦岂能不据法律上手续,率请立予正法,以快私心?现在外患日迫,政府信用未固,益以此事,致群情激动,外人轻视,民国基础愈形危险。”面对黄兴的质问,袁世凯难圆其说,乃指使其亲信造谣说黄兴曾托张振武谋杀黎元洪并与张振武密谋第二次革命,企图借此把水搅浑,为其妄杀张、方开脱罪责。面对这些谣言,黄兴“不胜骇异”,再次致电袁世凯严正指出:“如兴果与张案有
涉,甘受法庭裁判。如或由小人从中诬捏人罪,亦请按反坐律究办。庶全国人民皆得受治于法律之下。”戳穿了袁世凯的构陷阴谋。
2.坚持国家机关必须依法行政,反对违法行使权力。1913年4月26日,未经国会讨论通过,袁世凯政府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署了有损中国主权和经济利益的《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对于大借款,早在其谈判阶段,黄兴就坚决反对,并倡办国民捐。合同正式签订前夕,黄兴就得到了密报。他认为,袁世凯政府行将签署的这笔借款,没有按法定程序经过国会承认,违反了《临时约法》关于借款必由参议院议决的规定,属违法借款。因此,他一面急电北京国民党本部,“请本党诸公力行设法反对”,一面质问袁世凯:“借款必由参议院议决,载在约法。今国会承受参议院职权,关系全国命脉之举,不容彼先事置议,立国根本之谓何?……财政事项,动与国民生命直接相关,且数至二千五百万镑之多,已溢吾国岁入之半,宁尚不足告语纳税之人邀其同意?此在国会闭会期间,犹当特别召集,今正开会而秘不与议,古今立宪国家是否有此先例?况临时政府将遂告终,国势未安,百政莫举,掌财政者全无计画足以昭示国人,骤须巨款,用途安在?此小之表示政府之不诚,大之人民得坐政府以破坏约法、蹂躏国会之罪。”最后,黄兴要求袁世凯“俯从民意,非得人民代表之画诺,一文不敢苟取”。大借款合同签署后,全国一片斥责之声。但袁世凯借口借款事宜曾于1912年底由临时参议院秘密通过,拒绝将此案交国会表决。国务院和财政部也狡辩说此项借款条件,上年已经参议院议决。对此,黄兴立即通电予以坚决驳斥:“自上年十二月以来,大借款之议已寝,事逾半载,一切停止进行,今忽重议募集,银团易式,合同易款,折扣迥异,总额大增,此另为一案,政府当重行提出,了无疑义。于时国会初成,民意待白,政府乃悍然不顾,借口于经年之废案,在临时政府告终之期,当局挥金谬辱人民之际,暮夜之间,骤加人民以二万万五千万之负担,事前不与国会筹商,事后复避国会质问,聚为秘谋,出乃规避,玩国民于股掌,视议会如寇仇,国政至此,体统安在?”并再次坚决要求大借款依法定程序交国会议决。
3.坚持司法独立,反对外界干涉。《临时约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黄兴认为,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保证,因此,在民初注意坚持司法独立原则,追求司法公正。1913年3月,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此案经过多方努力侦察,很快水落石出,原来是袁世凯指使国务院总理赵秉钧伙同国务院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布置安排的。“宋案”真相大白后,黄兴在暗中布置军事讨袁的同时,主张“将宋案交法庭公平裁决”,敦促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民政长应德闳通电公布宋案主要证据,并致电袁世凯要求组织专门处理宋案的特别法庭,以避免来自北京方面的行政干涉,保证司法公正。袁世凯假惺惺地同意组织特别法庭,暗中却又指使司法总长许世英以约法和法院编制法无此规定为借口,反对组织特别法庭,并为赵秉钧辩解和开脱,说什么“如欲凭应、洪往来函电遽指(赵秉钧)为主谋暗杀之要犯,实非法理之平”,还说,许世英拒绝成立特别法庭是“为法律保障计,职分当然,却无偏私之见”,他根据“立宪国司法独立之原则,未便过于摧抑”。黄兴又立即致电袁世凯指出,赵秉钧“是否与宋案有关,终当诉之法官之判断。……兴争特别法庭,实见北京法院陷入行政盘涡之中,正当裁判,无由而得,不获已而有此主张。此于司法独立,实予以精神上之维持,以云摧抑,兴所不受”。由于袁世凯的刁难,特别法庭终未能建立,宋案只能由上海地方检察厅受理。但上海地方检察厅级别过低,审案受到层层阻挠。尽管如此,黄兴支持上海地方检察厅依法独立办案。5月6日,上海地方检察厅依审判程序票传赵秉钧和国务院秘书程经世到上海地方检察厅接受询问和调查。袁、赵恼羞成怒,合演了一场贼喊捉贼的闹剧。赵秉钧不仅抗传不到,还反诬黄兴与应夔丞有关系,要求票传黄兴到案。袁世凯却以重金收买天津女学生周予做向北京地方检察厅“自首”,捏词诬陷黄兴派她到北京进行政治暗杀,企图借以抵制上海地方检察厅传讯赵秉钧,转移全国人民的视线。6月11日,上海租界会审公廨根据北京地方检察厅的来文票传黄兴。为了维护法律尊严,黄兴一传就到,并且保证以后随传随到,使各种诬陷不攻自破。在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下,与之谈法治无疑是与虎谋皮、对牛弹琴。尽管在张案、宋案和善后大借款中黄兴坚持依法办事的努力并无实效,但他坚持法治的思想和努力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