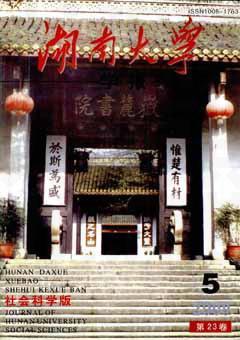文化溯源与智性对话
杨建华 黄金萍
[摘要]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春秋战国”的开源性意义不可磨灭,近年来,表现春秋战国历史也一直是历史小说创作的热点。作家们以“寻根”姿态回望历史家园。重溯传统文化源头,努力探索着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创造性转换的种种可能性。本文重点以孔子、老子以及孙子等诸子形象为例,来全面考察令人与古人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与哲思沟通。
[关键词]历史小说;轴心期;文化起源;古今对话
[中图分类号]1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童编号]1008-1763(2009)05-0081-04
一作为文化起源的“轴心期”
在新时期的历史小说创作中,出现了一股书写春秋战国时期百家诸子的热潮,代表作包括:杨书案的《孔子》(1990)、《老子》(1993)、《孙子》(1995)、《庄子》(1997),韩静霆的《孙武》(1995),姚思源的《墨子大传》(1999),李镇的《仁者无敌:小说孔子》(2002),穆陶的《屈原》(2003),杨力的《千古孔子》(2003),钱宁的《圣人》(2004),高光的《孔子》(2005)(李冯发表于1996年《花城》的新历史小说《孔子》也可算作是一种响应)。
对于春秋战国时期,雅斯贝斯提出了“轴心期”的理论。他认为,公元前800-200年发生在地球上的精神过程标志着人类历史正处于一个轴心时期。“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等诸子百家,都出现了……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都已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无独有偶,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帕森思也指出,在公元前1000年之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古代文明,都曾先后不约而同地经历了一个“哲学的突破”的阶段——即对构成人类处境的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则是从来未曾有过的。与这种认识随而俱来的是对人类处境的本身及其基本意义有了新的解释。像这种认识,在近年来的历史小说家们心中,也引起了持久共鸣。如《圣哲老子》作者张兴海在该书扉页就指出:“这是一个圣人云集、哲人坦陈、歌人放纵、情人绚烂的时代。”《张居正》作者熊召政也曾就春秋时期特别说明:“在公元前550年至公元前470年之间,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先后出现了孔子、老子、孙子、伍子胥、范蠡、文种、子产、申包胥等一大批闪耀着智慧光芒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和谋略成为了中国文化的发端。可以说,在那八十年间所产生的文化现象,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奇观。……尽管后世经历了无数次思想的变革以及文化的求新,但没有哪一种思想,更没有哪一个人有着如此神奇的力量,能够改变那八十年间一批文化巨匠所创立的中国文化的本质。可以说,那八十年间是中国文化的分水岭。此前的中国文化虽然也充满生气,但并没有产生汪洋恣肆的局面,也没有让人景仰的大师。在孔、老之后,中国文化的正脉出现了。一俟正脉出现,就意味着混乱局面的结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孔子与老子的出现。是中国文化成熟的标志”。
由此可见,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春秋战国时期的开源性意义不可磨灭,中华文明的成熟正导源于此。今天的小说家们要做的,就是依据这些大师们的精神元典,结合相关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追寻这一“哲学的突破”的起源,来一次文字的、精神的甚至灵魂的“寻根溯源之旅”。而“起源”一词的语义本身,已经表明它是逆向性的,只有在回顾中,在为自己找一个“过去”的行为中,才有“起源”二字所意味的一连串的逆向活动;为的是要形成“历时性”的到我“现在”之逆向的寻根行为,这就是“起源”。在本雅明看来,“起源从未在赤裸明显的史实存在中显露过自己,它的节律只能由一种双重认识来决定。一方面,它会被看作是修复和重建;另一方面,它又被认为具有未完成性和未终结性”。的确,无论我们今天的作家怎样宣称自己只有一个真诚的目标——要复原历史上的老子、孔子、庄子、孙子,复现历史真相,但最后形诸文字的小说表述都只会是自己心目中的古人形象,不同的作家赋予他们的意义也会有所不同,尽管作家们的价值取向有时会出现惊人的一致。于是,每一次溯源式写作的完成其实都意味着下一次重写的开始。就如吉登斯所强调的,共同的文化传统与大写的民族主义建立起相互联系乃是民族国家共同体神话建构的基本策略,其中“起源神话”扮演着重要角色:“民族主义理念都倾向于把故土的概念(即领土权的概念)与起源神话联系在一起,就是说,赋予那种被认为是这些理念载体的共同体以文化的自主性。”不过,我们在这里要追问的是,历史小说家如此迷恋春秋战国这一“源头”。除了“源头”本身对于民族国家的迷人魅力之外,对于知识分子作家本身而言它还意味着什么?
二文化溯源:精神家园的执著寻找
任何时代的思想构建的深度与广度,都取决于这一时代的人们的反思能力,以及在反思过程中挖掘文化思想、精神资源的深度。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和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又一次成为人们视野中的热点名词,它们也成为小说创作的重要精神资源。回顾历史小说对于春秋战国时期集中书写的时代背景,我们发现,这些作品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新世纪这几年。而这一时期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向深化、社会全面转型、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的关键阶段,对于知识分子作家而言,这也是他们对于传统文化自信与焦虑并存、继承与创新同在的多种心态并存的时代。作家们不约而同地选择回望历史、追溯文化起点,其用意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旨在纠正20世纪初以来直至新时期前社会上对传统文化的偏离和误读,重新树立传统文化的正确位置。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这个曾经征服过无数民族的文化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无比艰难的文化裂变中开始它的换血过程。中国传统文化确有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某些因素,“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而非打倒孔子)的口号也确有警示国人的意义,李大钊也对此补充解释:“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但是,在具体的新文化运动实践中,“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总体上还是激进主义,缺少对传统文化的认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文革”时期,不但“批林批孔批周公”,而且大量摧毁历史文物,“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观念也使传统文化遭遇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寒冬。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重述历史,重说文化起源,无疑有着疏通河床、正本清源的意义。
拉康指出:“故事起源于匮乏,故事中必定有某种事物丧失或者不在,这样叙述才能展开,如果每件事物都有原封不动,那就没有故事可讲,这种丧失是令人痛苦的,但是它也
令人激动。欲望是被我们无法完全占有的事物刺激起来的,这是故事给人满足的原因之一。”历史小说家所以浓墨重彩地书写传统文化,不仅仅因为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更是因为新文化运动和“文革”造成的文化的“丧失”与“断裂”!像杨书案、韩静霆、张兴海等亲历“文革”的作家,对这种“断裂”的伤痕更是刻骨铭心。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旧有的统一文化被多元文化所取代,旧有的价值体系土崩瓦解,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信仰缺席的盲目状态之中。文化的匮乏和精神的无依,期待富有人性内涵的文学的回归,于是众多历史小说家的“文化溯源系列”应运而生。
其次,针对国内市场经济背景下普通百姓的心灵危机以及知识分子自身精神家园荒芜甚至“无家可归”的灵魂焦虑。作家们力图借助生动形象的文学方式,通过重释元典,重述传统文化大师级创始人物,为自己、也为他人探索出一条回“家”的路。我们看到,随着中国的市场化步伐的日益加快,消费至上的大众文化潮流已逐渐形成,它在消解过去僵硬的一元化体制的同时,也弱化了中国文化追求“思想性”和“凝聚力”的传统,甚至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评论家雷达论及《圣哲老子》出现的意义时就明确指出:“在商品文化盛行的现今,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表现在文学上则是灵魂变得轻飘无根了,文字变得浮躁粗鄙了,叙事变得哗众取宠了,而欲望、犯罪、身体、时尚、娱乐至死,如潮涌一样泛滥在当下一部分文学的内里,以至要找寻隽永的诗性和雅致的思理变成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这确实是文学界应该集体反省的。而在另一方面,新历史主义文学的戏说历史风潮至今热力不减,它固然给文坛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但其解构历史、颠覆崇高、嘲弄英雄、强调偶然的戏说态度更是给文化界以沉重打击。这就如同现象学家彼得·伯格则所说的,现代人身陷“没有归宿的状态,愈陷愈深,无法自拔”,“现代人面对社会与自我所得到的,是一种流浪的经验,这与形而上意义上‘家失落,是相生相连的。不用说。在心理上这种状态难以承受。因此,它造成了一种思乡病,一种希望对于在社会中、在整个宇宙间‘有所归属的乡愁。”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一些有良知的作家自觉选择依附传统,重回文化原点,为精神找寻一片栖息之地。
最后,我们放眼世界,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的文明历史从未间断过。自尧舜禹以降,经历了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和诸侯纷争,传统文化不但未中断,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光大;此后,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南北朝时期以及五代十国时期的纷扰离乱,抑或是元朝蒙古人的天下、清朝满族人的统治,都未对中华文明产生大的冲击,反而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的大融合,传统文化更加爆发蓬勃生机。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而言,只有大力倡导民族文化寻根和文明溯源,强化民族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对于当今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意义,我们才能在外来文化的渗透和冲击中守住自己的“根”。“只有通过历史,一个民族才能完全意识到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孔子》、《老子》、《庄子》等为代表的一批旨在挖掘传统文化资源、重溯文明“起源”的历史小说接连出现并一度形成阅读热潮也就不奇怪了。对于新时期的历史小说家而言,对于传统的认识是高度自觉的,但在形诸文字并以集束方式出现,则离不开当年“寻根文学”的启发与导引。
寻根文学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由作家、评论家推动的具有自觉意识的文学潮流。寻根文学顾名思义是追寻“根”的文学,正如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所说:“文学有根,文学的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而是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希望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之谜……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重铸和镀亮民族的自我。”而当我们将寻根文学的“寻根”的概念与上述历史小说中的“溯源”理念放置一起时,就会更清楚地发现二者的内在联系。在寻根表述中,中华民族主体性表现为一个富含深情的核心词语——“根”。在汉语里,“根”与“本”是同一个意思,意为基础、实质、本源。可见,韩少功不容置疑的“民族的自我”潜藏着对“本源”的需求。而这一本源,既离不开“梳理”和“发现”,也离不开“形象建构”。在“根”(本源)的召唤下,文化传统、历史记忆、精神家园、集体无意识、民族国家、东方文明……这些概念原本各自为战,此刻却在“根”的呼唤下彼此依靠,共同组建成一支阵容庞大的寻“根”队伍。相比之下,文化历史小说同样在寻找“起源”(家)的巨大冲动面前,整合民族、传统、文化、历史中各自蕴涵的能量,来重塑(“重铸和镀亮”)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根文学无意中充当了文化历史小说的引路人角色。
三智性书写: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在现代作家中,将诸子百家思想与行为付诸文学表现的主要有鲁迅(《故事新编》)、郭沫若(《孔夫子吃饭》)、冯至(《仲尼之将丧》)、郭沫若(《柱下史入关》)等。其中,冯至的《仲尼之将丧》借一点历史缘由展开想象,通过将死的孔子的抑郁、寂寞、悲凉心态的描绘,亦在恢复孔子“人”的面目,体现“五四”时期“人的解放”的精神主题;郭沫若的《孔夫子吃饭》则通过吃饭这一生活细节揭示了孔子领袖尊严和圣人外衣包裹下的自私、虚伪本质。对于老子,鲁迅则在《出关》通过孔子“问礼于老子”和老子“西出函谷”两个历史片段进行重写,老子“游心于物”的境界全然不见,变成了郁闷、失望、懦弱的“一段呆木头”;而在郭沫若的《柱下史入关》中,则写老子回到关内,老子已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所有的信仰和信念在生活的磨难中消失殆尽,不得不回到离不得的人间。此外,还有许多作品对庄子、墨子、孟子的改写,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色。不过,现代小说中的诸子形象因其篇幅的局限,往往只留给读者一个简短的横截面,真正将他们放人长篇小说中来刻画的还是新时期的作家。这里,我们重点以杨书案的《孔子》、张兴海的《圣哲老子》以及韩静霆的《孙子》三部作品为例,来考察今人与古人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与哲思沟通。
在众多描写孔子的历史小说中,杨书案的《孔子》无疑最具影响力,也最有艺术内涵。关于杨书案《孔子》的创作特色,冯牧先生的评价简洁而准确:它“是把‘圣人平民化、生活化和小说化。作品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论语》和其他典籍记载的史料,描绘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将理性审思融注于感性形象之中”。作者的写法无疑是独特的,孔子先后提出过的一系列具体政治主张以及周游列国时与一些公卿大臣的交往事迹显然不是作家关心的重点,他着重要描写的是孔子在春秋列国推行仁政思想时遇到的种种坎坷以及由此带来的理念调整与反思。在治国方略上“知其不可为
而为之”的执著精神与沿途布道时的博爱品格都被刻画得淋漓尽致。
在杨书案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心灵世界极为丰富的孔子,同时也看到了一个痛苦而矛盾的孔子。小说中有两处描绘极为传神,一是写鲁国权贵季孙氏大宴宾客,公开招贤纳士,正居母丧的孔子不由怦然心动,但丧服未除,恪守周礼的仲尼内心在交战:进身仕途的绝好机会难以割舍,遵循孝道的礼制也不可违背。考虑再三终于出行,理由就是后来《论语》所载的“学而优则仕”,“学也禄在其中矣”等语。这种由元典生发出的艺术想象形象而贴切地展现了孔子温情的一面。另一个例子是孔子为了晋见卫灵公不得不“巴结”灵公夫人南子,南子有“丑声”在外,但仲尼跑到后宫见面时只觉膝盖不听使唤而跪下来,随即又很后悔。心中闪过一丝欲念又很快恢复平静,事后面对无意的责问孔子竟然指天发誓起来。孔子内心的情感与理智矛盾以一种无意识悸动的形式呈现出来,成为全篇最为闪亮的篇章。发乎情止乎礼,就在这一放一收之间,人物的立体形象完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当然,作者的叙述视点绝不限于这种感情的表达,小说中还有多次叙述了孔子与弟子及同时代其他哲人的哲理性探讨场面,也正是这种反复切磋玉成了孔子的思想体系。如孔子拜谒老子一节中,老子临别时留下这样的赠言:“一月晤谈,你常挂在嘴边的那些礼乐之言,创言者尸骨早已朽烂,只剩下一些空话罢了。我听说,良贾深藏苦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掉你的骄气和多欲,去掉你的恣和太盛的有所为之志吧,这些东西都是于你无益的。我所以告你的,若是而已。”这话使孔子大受震动。老子从人格上、人生哲理层次上切人孔子之道可谓一针见血,孔子在反躬自省中也不断修正自己的学理方向。这也正如黄曼君先生所说:“书案的小说以人性闪光和情志、情趣充溢的笔触,灌注生气于史实和性格命运,赋予古人以艺术生命,从而创造出气韵生动而又具体真实的历史人物形象来。”
韩静霆的《孙武》也是一部我们不得不谈的优秀小说。本来孙武的扬名天下正是因其《孙子兵法》对军事谋略的系统性布局和开拓性研究,但韩静霆作为部队作家,却独辟蹊径,为我们找到一个比军事战略战术本身更为高明的角度来叙说孙子,这就是站在中华民族和传统文化热爱和平、以人为本的高度,并以极富哲理性的笔墨道出了生活在崇尚强力和杀伐的春秋末年军事家的全部悲剧的根源。的确,孙武不是纸上谈兵之徒,他辛辛苦苦十几载研究成型的兵书谋略自然希望得到实践的机会。为此他不得不四下寻找用武之地,在多次碰壁的情况下遇到了复仇心切、慧眼识才的伍子胥,后者一片赤诚之心终于打动了孙武。在吴宫里演练宫女阵,孙武博得吴王欣赏,被拜为大将,却因杀掉了阖间爱妃而遭到吴王及太子夫差的猜忌。终于手握兵权能指挥三军冲锋陷阵时,却被战争淋漓的鲜血浇醒:原来自诩为人类的最高智慧的军事谋略竟是最快的屠杀同类的屠龙刀法,个人的功成名就必须奠基在千百万具无名尸体的累累白骨之上。小说结尾堪称全书的点睛之笔:事业上正如日中天,空有满腹才华的孙武却不得不抽身退出江湖,把军事战术变成了羊群之戏:
……但见在这万里黄河入海口,在这片黄褐色的土地上,在这红如喷血的晚霞中,孙武把“战争”真的变成了羊群之戏。而那黑的羊,白的羊,散开来,如棋枰上的黑子白子,聚拢起,成为黑白两大漩流,互相依托,互为映衬,相反相成。白羊和黑羊运动着。奔跑着,一会儿看上去如古老而神奇的河图,一会儿又似洛书,一会儿河洛合而为……渐渐地,孙武和漪罗融入羊群之中;渐渐地,那黑的白的羊群消失在混混沌沌的天地之交。
这是一种多么富有哲理性的诗性想象!韩静霆以现代军人之心,度孙武古代军事家之腹,两人可谓跨越时空惺惺相惜。通过演绎兵家之圣孙武的生命历程,韩静霆揭示了军事谋略的最高境界——智慧游戏。这不愧是一场古今智者的成功对话!
最后要讨论的是张兴海的《圣哲老子》。该书2007年刚一出版,便迅速在评论界激起强烈反响,公认的评价是:“在当代中国并不多的,却也并非空白的几种老子的书写中,张兴海的《圣哲老子》是颇为雄沉、厚重,完整、丰富的,也许是最具思想启示意义和审美价值的一种。”老子这位先秦哲人以一本传世的经典《道德经》(又称《老子》)令全世界无数人为之着迷,2500多年过去了依然热力不减。那么,道家始祖老子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的人生经历究竟是怎样的?他那玄而又玄的“道”思想的形成,他与孔子、孙子等诸子百家的交往,究竟又是怎样的情形?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包孕在这部30余万字的《圣哲老子》当中。作者毕十年之功,在甄别大量史料和传说的基础上。以文学手法再现了老子痛苦、寂寞、孤独的人生历程,揭示了其作为道家创始人的思想、心灵和人格背景,让老子这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哲人形象真真切切地矗立在读者面前。
《圣哲老子》将老子放在周室式微、诸侯崛起、战乱频发、礼崩乐坏的广阔时代背景下来表现。他曾亲自经历了周景王逝世前后,王子朝、王子猛、王子丐等人的继位之争,吴国与楚国、齐国的血腥战争;也曾去叛军营帐,营救自己的亲密朋友周大夫苌弘。正是这种对动乱时代的切肤体验,催生了老子对一种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的重新打碎与熔铸。
此书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在张兴海先生的笔下,常被认为是最难解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竟然产生自最常见不过的男女之情——老子新婚之夜与妻子希交合成卦,竟然悟出了“阴阳”、“乾坤”、“溪”、“谷”等宇宙论概念。无独有偶,作为兵家创始人的孙子也在与意中人崔旦行床帏之事时,悟出内身相谐,招招承欢,无不是交接式的显露,与诡谲多变的用兵之道天然地吻合无间。作者这一巧妙化用,可谓开启智慧的天眼,我们也一如得了通灵宝玉,顿开茅塞,惟在赞叹老子道学高不可测的同时,也不由得同时赞颂作者本人参道的智慧功夫。
总之,以杨书案、韩静霆、张兴海等作家的以先秦诸子为题材的历史小说。高扬现代知识分子与古代哲人息息相通的精神共性,以智慧的书写建构起古今对话的文化平台,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尤其是儒道文化)作了一次全息的、立体的扫描,留给我们无限的想象空间和无边的回味余地。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一道,为中国文学来自整个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昭示了历史小说创作中的一种稳健的、沉淀文化质感的新型创作风格的最终成熟。正如乐黛云先生所言:“任何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体现着^,类经验的某些共同方面而使欣赏者产生共鸣,同时又是作者本人的个人经验、个人想象与个人言说。伟大作品在被创造时,总是从自身文化出发,筑起自身的文化壁垒,在被欣赏时,又因人们对共同经验的感知而撤除了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今天,如果还有人对“后《李自成》时代”的历史小说怎么求新求变抱以怀疑态度时,那么,在阅读完上述作品后应该会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