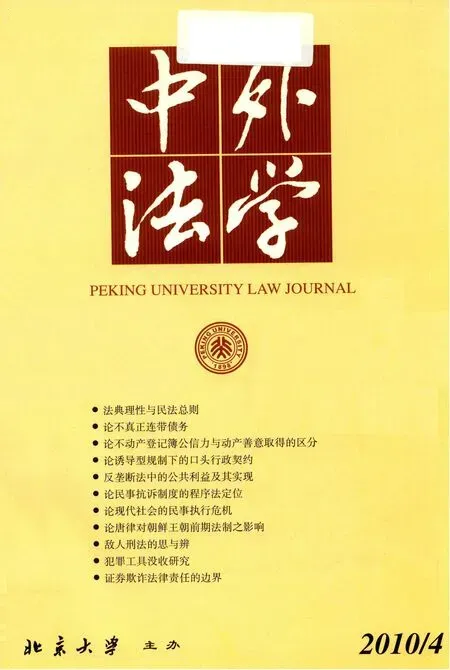敌人刑法的思与辨
蔡桂生
敌人刑法的思与辨
蔡桂生*
深入现代社会的法治国肌体,被学者揭发出来的敌人刑法 (即 Feindstrafrecht,不是敌人刑事法)问题,已经引发了不少争论。来回于现代与后现代,如果我们不能够以平和的态度对待这些争论,我们就会轻易地得出赞成或者反对的观点,这样的任何一种结论都很可能是狭隘的,而且会失之于理性思考。
早在 1985年的一场名为《法益侵害的前置入罪》的学术报告中,雅科布斯的敌人刑法概念就形成了。〔1〕Günther Jakobs,K rim inalisierung im Vo rfeld einerRechtsgu tsverletzung,ZstW 97(1985),S.751-783.当时他主要面对的是对敌人刑法的批判,并且认为无论如何“作为例外有效的紧急避险刑法”还是可以合法化的。1995年 5月 28日,在德国罗斯托克召开的刑法学者大会上,雅科布斯在《处在机能主义和“古典欧洲”原则思想之间的刑法或者与“古典欧洲”刑法的决裂?》的报告中,明确表达了区分人格体和个体的想法;以此为基础,1997年,他在《规范·人格体·社会——法哲学前思》这本小册子中,提出了市民刑法和敌人刑法这组对立的范畴;其后,他于 1999年在柏林的一场研讨会上继续阐发他的敌人刑法观念;2003、2005和 2006年,他还专门发表了三篇文章 (“市民刑法与敌人刑法”、“恐怖主义分子作为法律上的人格体?”和“敌人刑法?——关于法律性条件的考察”)集中论述他的敌人刑法理论。〔2〕参见 (德)雅科布斯:《行为责任刑法》,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页 101以下,尤其是页 125;(德)雅科布斯:《规范·人格体·社会——法哲学前思》,冯军译,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页 100以下;Burkhardt/Eser/Hassem er(hrsg.),D ie deutsche Strafrechtsw issenschaft vor der Jahrtausendwende-Rückbesinnung und Ausb lick,2000,S.41 ff;(德)雅科布斯:“市民刑法与敌人刑法”,徐育安译,载许玉秀主编:《刑事法之基础与界限——洪福增教授纪念专辑》,台湾学林文化事业公司 2003年版,页 15以下;Vgl.Gün ther Jakobs,Bürgerstrafrech t und Feindstrafrecht,HRRS 3/2004,S.88 ff;Gün ther Jakobs,Terro risten als Personen im Recht?,ZStW 117(2005),839-851;Günther Jakobs,Feindstrafrecht?-EineUntersuchung zu den Bedingungen von Rechtlichkeit,HRRS 8-9/2006,S.289 ff.
这样一个观点被认为是敌人刑法理论的核心:“根本性的偏离者,对于具有人格之人所应为之行为不给予保证,因此,他不能被当作一个市民予以对待,他是必须被征讨的敌人。这场战争乃是为了市民的正当权利,即对于安全的权利而战,与刑罚有所不同,遭到制裁之人并无权利,而是作为一个敌人被排除。”〔3〕雅科布斯,“市民刑法与敌人刑法”,见前注〔2〕,页 39。雅科布斯认为他的核心观点是:
无法让人可信地保持法忠诚者,就会渐渐偏离到陌生领域去,同时权利被克减,但其义务仍存 (即便他无法完成其义务了),否则他就因为不尽义务而成不了犯罪人,直到他不再享有权利,那也就是不作为人格体来处理了。这是我的论述的核心观点,如果去除这个观点,就肢解了我的文章,纠缠于细枝末节的东西,而未抓住基本意思。〔4〕Günther Jakobs,Feindstrafrech t? -Eine Untersuchung zu den Bed ingungen von Rech tlichkeit,HRRS 8-9/2006,S.293.
正如德国学者约亨·博恩 (Jochen Bung)在其“作为规范有效性及人格体〔5〕在雅科布斯理论中,Person、Individuum和M ensch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本文采用冯军教授的译法,分别为“人格体”(等同于徐育安所用“具有人格之人”)、“个体”、“人”。理论的敌人刑法”一文中所言,尤其是这种在极其精心构造的规范论背景中的非常的刑法,若不了解其规范论,就无法了解到底在讨论什么。〔6〕Vgl.Jochen Bung,Feindstrafrecht als Theorie derNo rm geltung und der Person,HRRS 2/2006,S.64.因此,若只注意对敌人宣战的论述,而忽视雅科布斯的规范论,容易发生理解偏差。若不赞成或理解规范论,自然基本不可能接受敌人刑法。当然,对于机能主义规范论和法益论的系列论争,因其涉及面极其宽广,而且笔者又大体同意前者,故在必要时可以另著文探讨,本文不再专门赘述。
其实,纵观敌人刑法所遇到的各式挑战,同样也不脱离如下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这也是笔者目前比较关心的问题。如果能够辨清这些问题,会有助于理解雅科布斯,从而也许能够减少误解,或把问题控制在容易理解的范围内,以便平和地进一步讨论。这几个问题是:①为何选择敌人刑法这个词?②敌人刑法到底是不是法?③敌人刑法是否脱离现代法治国框架?④描述性地阐述敌人刑法是否有违学者的职责?⑤敌人刑法是否导致战争的扩大化?
一、关于敌人刑法之用词
关于敌人刑法的用词问题,早已遭到批评,以至于敌人刑法这个词本身就被认为长着一副狰狞的面目,从而激起了各式各样的反对。德国学者阿德特·辛恩 (A rndt Sinn)超脱地说,如果人们撇开术语之见,其实在本质上没有争议。〔7〕A rndt Sinn,Moderne Verbrechensverfolgung-auf dem W eg zu einem Feindstrafrecht?ZIR 3/2006,S.117.本文则认为,敌人刑法一词纵然容易引起反对,但若反对者并非理解偏差、缺乏主见或有心反对的话,敌人刑法也是能够为人接受的。〔8〕笔者以前在“刑法知识论的体系性反思”(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 2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一文中曾出于学科纯化的目的,认为用敌人政治来对付公敌,而刑法不应涉及敌人政治的内容,现在看来可能欠妥,因为从法治国角度而言,敌人刑法的危险性较之前者应该更小。即便换了另一个词,也不见得就会减少多少争论,反而有可能削弱其特点,并引起更多不必要的误解。更为重要的是,敌人刑法本身一词的准确性目前尚还难以替代。对于敌人刑法的色彩,雅科布斯本人对此澄清道:“‘敌人刑法’这样的名称并不一定就含有贬义。当然,敌人刑法意味着一个有着缺陷的安定,这种有缺陷的安定,它并不一定就该归罪于不顺从者,也可能是由于那些一心企求和平的人所导致的。”〔9〕雅科布斯,见前注〔3〕,页 17。将这个观点视为核心者,可参阅 Jochen Bung,Feindstrafrechtals Theorie derNormgeltung und der Person,HRRS 2/2006,S.64;张超:“先天理性的法概念抑或刑法功能主义——雅科布斯‘规范论’初探兼与林立先生商榷”,《北大法律评论》(第 9卷·第 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页 187-188;(德)贝恩德·许迺曼:“敌人刑法?——对刑事司法现实中令人无法忍受的侵蚀趋向及其在理论上的过分膨胀的批判”,杨萌译,载冯军主编:《比较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页 264等诸多文献。相对符合雅科布斯在 2006年界定的核心意思的,可见 A rndt Sinn,M oderne Verbrechensverfo lgung-auf dem W eg zu einem Feindstrafrecht?ZIR 3/2006,S.107,u.a.,但阿德特·辛本人并不赞同敌人刑法理论。在这里面,雅科布斯并没有对“敌人刑法”评价为好或不好,只是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希望和平的人的手中导致了一种有缺陷的安定。对于雅科布斯的敌人刑法理论,经常有批评者将之同卡尔·施米特的根据是否信仰上帝、是否是异族人而从政治上区分敌友的“法西斯观点”混淆在一起,认为敌人刑法是纳粹思想的复活,这是明显错误的。对此,雅科布斯也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他采用的敌人刑法的“敌人”是针对被认为有危险的犯罪者,即非朋友 (inim icus)的,而不是针对施米特说的政治对立意义上的敌人 (hostis)。〔10〕Vgl.Günther Jakobs,见前注〔4〕,S.294。即言,雅科布斯所说的敌人是,而不是。〔11〕对于 inim icus和 hostis两个词 (更准确的可能是和,因为柏拉图特别强调区分二者)的中文译法,也有很多译为“私敌”和“公敌”的版本,笔者注意到雅科布斯所说的敌人,如果用“私敌”来表述,会误解他本人将部分恐怖主义者纳入敌人范畴,美国 9·11事件的这部分恐怖主义者很大程度上又是“公敌”,凸显着伊斯兰世界和美国的两群对立。因此,雅科布斯所谓“敌人”之性质,其本人的理解有可能与国内学界理解的“公敌”发生一部分偏差。〔12〕这种偏差是也就是和“公敌”的区别,可比较冯军:“死刑、犯罪人与敌人”,《中外法学》2005年第 5期,页 612;何庆仁:“对话敌人刑法”,《河北法学》2008年第 7期,页 59。台湾地区学者,如林立先生,则将 Feindstrafrecht译为“仇敌刑法”,似乎较准确。Fo rcellini的《拉丁文大辞典》(Lexicon to tius latinitatis)(第2卷,1965年版,页 684)写道:“公敌和私敌也可以做如下区分:私敌是那种痛恨我们的人,公敌则是那种与我们战斗的人”(此辞典译文摘自 (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页 110,刘宗坤译者注)。无论如何,我们目前在理解雅科布斯的理论时应注意到选词上的含义区别,而就为何用敌人刑法的“刑法”一词,雅科布斯认为:
处理规范违反者——若可这样说的话——之特别地方在于,它不仅要受到罪责上的惩罚,而是要在行为之前或附带进行保安处分。人们也许会问,为何将这种保安称为敌人刑法 (Feindstrafrecht)呢?它明明是一种保安法 (Sicherungsrecht)嘛。这种名字是立法者起的,立法者将这种保安正式表述为刑法:犯罪组织的成员将依他们的法律 (根据对和平秩序的扰乱程度)进行处罚,而并不是进行保安,而且改善和保安的规定总是只作为刑法的附件放在刑法典正文背后。〔13〕Günther Jakobs,见前注〔4〕,S.294-295.
至于德国学者许迺曼将原则性的犯罪人格认定为是不存在的,所谓的敌人其实是精神病人的观点,冯军教授已加以反对。〔14〕参见冯军,见前注〔12〕,页 612;冯军:“刑法的规范化诠释 ”,《法商研究 》2005年第 6期,页 66。用精神病人吸收敌人的观点,亦可见 A rndt Sinn,见前注〔9〕,S.115。按照雅科布斯的理论,精神病人不是规范接收者 (Adressat derNorm),其不存在给理智正常的人提供效仿榜样的危险,对他们没有遵守规范的期待,刑罚在他们那里丧失意义。雅科布斯不是根据《德国刑法典》第 20条(精神病人的规定)的标准来定义敌人的,而是在确定的犯罪领域中,将持续偏离法律而不再能提供认知性的最低保证(kognitiveM indestgarantie)的人定为非人格体,这也便是敌人。〔15〕引自 A rnd t Sinn,见前注〔9〕,S.114,115。若行为人根本就不具备负责任的能力,那也就不必对他的犯罪行为进行否定了,只有人格体犯罪,才有惩罚的意义,敌人因为根本偏离了规范,国家无法对其沟通,所以丧失了人格体的资格。虽然,精神病人和敌人都不再作为人格体来对待,但二者却不能混为一谈,市民和精神病人之间的转化是一个精神病学或医学问题,而敌人和市民之间转化却是一个刑法问题。
二、关于敌人刑法之法律性
敌人刑法到底是不是法?这涉及敌人刑法的法律性 (Rechtlichkeit)问题。约亨·博恩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敌人刑法是一种“权力刑罚”(M achtstrafe),而权力无论如何都是法之外的东西,那么,敌人刑法从根本上还是不是法?或说,这种模棱两可会混淆权力和法的基本区别?如果它应自证为法,那么它仍未说明敌人刑法是否是刑法?或者在这个程度上,这样的模棱两可至少会混淆基本的概念区分。西班牙学者坎西·梅利亚 (M anuelCancioM eliá)则认为这是自相矛盾的。〔16〕Vgl.M anuelCancioM eliá,Feind“strafrecht”?ZStW 117(2005),S.268;Jochen Bung,Feindstrafrech t als Theorie derNorm geltung und der Person,HRRS 2/2006,S.63.对于敌人刑法到底是不是法或刑法,雅科布斯在其论文中写道,“敌人刑法是符合法治国内的刑法之其他规则的,这根本没有排除敌人刑法自证为法,正如其使用的概念那样。”〔17〕Günther Jakobs,in:Burkhardt/Eser/Hassem er(h rsg.),D ie deu tsche Strafrechtsw issenschaft vo r der Jahrtausendwende-Rückbesinnung und Ausb lick,2000,S.47 ff.其实,前提是要理解他的规范论意义上的人格体理论,人格体是由其与其他人格体的关系即由其角色来确定的,一个惟一的人格体是一个自我矛盾;只有在一个社会中,从规范性的意义上说,才存在人格体。〔18〕参见雅科布斯:《规范·人格体·社会——法哲学前思》,见前注〔2〕,页 30。这里有必要澄清,此处的自我矛盾和坎西·梅利亚所说的不一样,后者认为雅科布斯之敌人刑法不是法,而雅科布斯又要冠之为法,所以自相矛盾。而雅科布斯认为单一人格体没有交往,自然没有人格,故不是人格体,因此自我矛盾。
雅科布斯在其新近的《敌人刑法?——关于法律性条件的考察》一文中重点解答了这个问题,他首先声明他的学术性写作意义:“在这里,我试图从学术体系 (W issenschaftssystem)而不是从法律体系 (Rech tssystem)方面来论证。依此,我并非想要使任何一个人成为敌人,而只是在描述法体系把谁作为敌人来处理了,以及预测谁将来会成为敌人。这并不涉及标准化 (Norm ierung),更不涉及政治假定,而是涉及存在的例外及其在将来的延续。”〔19〕Günther Jakobs,见前注〔4〕,S.289。在雅科布斯看来,存在于法律上的人格体 (Person-im-Recht-Sein)是可交往的、可沟通的,其他人必须和他共处,若他偶尔犯错,从而成为罪犯,也是可以沟通和补救的。他必须承担他的角色,这样才能保证对法的忠诚。只有保持了法忠诚,才成其为人格体,若一而再、再而三地背离规范,并使得妨碍沟通的风险增大到无法忍受的地步时,他就不再是人格体,需要进行强制。由于非人格体的存在和人力强制作为规范之保障,以及人定法不同于自然规律,〔20〕关于与社会交往和与自然交往的区别,以及违反社会交往的结果的详尽论述,参看 Günther Jakobs,StrafrechtA llgem einer Teil,2.Auf,W alter de Gruyter,1993,S.6 ff,u.a。假定可行的法律和实际奏效的法律是不同的,只有人们真正面对的后者,才会给人们提供应对各种现实问题的途径。〔21〕Vgl.Günther Jakobs,见前注〔4〕,S.290。实际奏效的法律是现实化的法律。
为了说清问题,雅科布斯区分了三个重要概念:①纯规范 (作为人格体合适交往的有效法律);②现实化的规范 (作为人格体合适的或可理解的交往的有效法律);③纯事实 (人们互相交往的实际规则)。他认为,最后一个概念中交往的实际规则可以完全是权力运作,因此讨论价值不大。这就回答了约亨·博恩的问题。第一个概念是抽象的人格体进行的各种交往的法规范,第二个概念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中可以用的法规范,可以用于损害赔偿、安抚被害人、指引行为人,当然这个法规范需要行为人认识到,需要建立规范的认知,否则就不过是一个无效的愿望,因此,如果识法,则不存在禁止错误 (Verbotsirrtum)的问题。〔22〕Vgl.Günther Jakobs,见前注〔4〕,S.290-291。这里建立规范的认知,不是仅靠规范被合适地或可理解地照做几回就够的,它是需要被建立的,正如谁会因为反正有不允许未经授权者进入住宅的规定而夜里不锁家门呢?〔23〕Vgl.Günther Jakobs,见前注〔4〕,S.292。这就涉及刑法的作用与任务,对此,雅科布斯认为,刑法的任务在于保障规范的效用,在于反映社会的同一性。在他的机能主义规范论刑法观中,卢曼的思想也是他的重要参考资源之一。卢曼同样也认为,规范的遵守代表规范的社会现实性,规范的违背也不代表规范失去社会现实性 (可以反面证立),因为二者都可以保证安全期待的机能,决定规范之现实性的不是某个人,不是行为人,而是社会。〔24〕Vgl.N ik las Luhm ann,DasRecht der Gesellschaft,1993,S.124 ff.,130-139,143;Günther Jakobs,见前注〔4〕,S.291。雅科布斯更为明白了当地指出,规范的违背无疑不可以是“无止尽的违背”(end los kontrafak tisch),因为这会导致规范“没有任何一次社会现实性”,总是只能指望下一次,这样会同时从行为人和受害人两个角度侵蚀法规范效力,规范便在社会进程中什么作用也起不了。〔25〕雅科布斯在 1985年就说过,维持规范之效力不仅考虑规范与潜在行为人的关系,还要考虑与潜在当事人的关系,因为当事人不是只有可能成为犯罪行为人的消极一面,他们还有他们自己的规范信任。Vgl.Günther Jakobs,K rim inalisierung im Vorfeld einerRechtsgutsverletzung,ZstW 97(1985),S.775.而规范信任对于规范效力和安全期待是不可或缺的。在进行人格体理论的论证后,对于以法律性为理由反对敌人刑法者,雅科布斯直截了当地回答道:
对于条件的实际分析使法律上的人格体和——至少是部分的——敌人的区分赢得了实际的导向性的法律性。这种分析也许会有瑕疵,但这种瑕疵也是现实,可能需要证明的是,实际的法律性并不建立于至少是下位的交互性 (zum indest un terstellbaren Gegenseitigkeit)上,这是到目前还没有被研究过的,也还没有被提供出来。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说,这种区分是不允许的,因为法律性是普遍的。可是这种法律性在“无止尽违背者”那里,却成为了不现实的东西,这是由上帝废除掉的,谁不现实地遵守这种规则,谁就应转行研究规范逻辑——那里有普遍适用的规范,或转行研究法政治——那里有轻易构建的乌托邦——我想,那些愤愤不平者会在后者那里感到尴尬。〔26〕Günther Jakobs,见前注〔4〕,S.294。
其实,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争论敌人刑法到底是不是法这个问题带有自问自答的性质。如果要说敌人刑法是法,那么正如雅科布斯所说,他是从一般的法律中分析发现敌人刑法之存在的,那么作为一般的法律的一部分,敌人刑法自然就是法;如果是在刑法中发现的,那么敌人刑法也自然就是刑法。只是许多人都不想要它,所以它是不符合许多人理想标准的法。阿德特·辛恩就建议立法者减少斗争词汇,并通过法学家和政治家机能性的互动,最终中断行为人刑法之路。〔27〕Vgl.A rnd t Sinn,见前注〔9〕,S.116。可是,事与愿违,敌人刑法已经确实存在于我们的法律中。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法是要普遍平等适用的,是要讲究权利的,这么狰狞的敌人刑法怎么可以是法呢?至少它不是现代的法吧?这可能是我们的一厢情愿,也许只是应然上的事情。其实,由于现实化的法律是有疆界的,这种疆界是万能的上帝定下的,认为人定法普遍适用,是不符合事实的,法律性也是有界限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雅科布斯的敌人刑法理论毫无疑问是突破近代启蒙以来既有的或者是旧的法的认识框架的,〔28〕2008年 12月 12日,西班牙刑法教授孔德来北大法学院做关于敌人刑法的报告,笔者向他问了一个问题,敌人刑法是法吗?孔德转述雅科布斯的话说,敌人刑法是无法 (kein Recht)。如果孔德的转述没错,大体上,雅科布斯的意思应该是指敌人刑法并非启蒙以来的那种假定的束手束脚的法。因此,正如敌人刑法理论的批评者所言,若以启蒙以来“自由主义为本体论 (onto logy)而在法理论层次攻击批判敌人刑法核心概念者,即是中了 Ronald Dwo rkin所谓的‘语义学之刺’(sem antic sting),并无法真正地有效反驳 Jakobs的论点 ”。〔29〕黄经纶:“对抗‘敌人刑法’——浅析 Jakobs的敌人刑法与德国法下客观法秩序维持之冲突性”,《刑事法杂志 》2004年第 48卷第 5期,页 90。
三、关于现代法治国框架
由于现代法治国是现代文明的象征,在讨论完敌人刑法的法律性问题之后,那么接下来要看,在为绝大部分人接受或被认为接受的现代法治国框架下,是否可以做敌人刑法的分析和理解,雅科布斯早就注意到了这点。〔30〕Vgl.Lorenz Schu lz,“D ie deutsche Strafrechtsw issenschaft vor der Jahrtausendwende”Bericht von einer Tagung und Anm erkungen zum“Feindstrafrecht”,ZstW 112(2000),S.662.针对启蒙以来的平等原则,即当下每个人都应当被作为拥有权利的人格体 (Person)来对待,雅科布斯写道:
最近,在一次公共讨论中,我认为这一原则过于抽象,因为这也许取决于别人的态度,有一位同事当即愤愤地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情况不是这样的,即便对希特勒,人们也是要将他作为法之人格体(Rechtsperson)来对待的。这位同事也许没有意识到,他的理由也流于抽象:究竟在何种情况下人们要和人所共唾的独裁者共处呢?是根据和他一起重新创造法的状态,而在效力范围上没有限制吗?现在,人们可以自己制造法律,而且使其到处施行。〔31〕Günther Jakobs,见前注〔4〕,S.289。
接着,雅科布斯仍然以希特勒为例,并将希特勒作为敌人来看待,认为他是需要被清除的对象。人们不愿意再和希特勒一起制定法律,因为人们已经和他不共戴天。所以,人们排除希特勒,自己制造自己认为更好或更为人道的法律。其实,这也是大多数人的看法,只不过雅科布斯把它说了出来。基于此,雅科布斯认为,每个人都作为人格体来对待,乃纯粹是一种抽象假定,它作为社会的一种理想模式,并不实际发生在社会中;如果某人遵守其义务或即便未能遵守义务,但仍认可其义务,那么他便不是危险的;反之,如果他摧毁其义务,那么人们就必须和他斗争,如果他可能摧毁其义务,那么人们对他就要提防。〔32〕Vgl.Günther Jakobs,见前注〔4〕,S.290。敌人刑法理论的支持者瓦勒 (Carlos PérezDelValle)也相类似地认为,处于市民状态者遵守市民契约,他们与偏离到自然状态中特定的人之间无契约关系,后者对于法状态的整体而言,是一种根本上不安定的因素。Carlos Pérez Del Valle,Rechtsphilosphische Begründung des Feindstrafrecht,in:FS-Günther Jakobs,2007,S.518.仔细观察,这里讨论的仍然是他的纯规范和现实化的规范两个概念。在现实化的规范中,规范才有其社会意义,市民犯罪人仍然认可其义务,而敌人却摧毁其义务,否定整个法规范。对此,雅科布斯引用了康德的最后手段 (u ltim a ratio)理论,即对于那些死都不肯接受“市民宪法”,却又要赖在人们中间的人,将其视为法律之外的人和作为讨厌的环境 (strönde Umw elt)来对待,这种人也就是敌人。因此,甄别出敌人刑法规则并将之从市民刑法中分拣出来,并不是刚刚才成为学术任务的事。〔33〕Vgl.Lorenz Schu lz,见前注〔30〕,S.662。当然,康德的敌人刑法和雅科布斯的敌人刑法是不同的,这点是要注意的。针对现行法律体系,雅科布斯则引用了霍布斯对于市民犯罪人和叛国犯的区分,并认为德国立法者本身就在进行“斗争”,比如预备犯罪、经济犯罪、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等方面的立法,〔34〕这主要是指 1876年《德国刑法》第 49条 a、第 16条,《第一次经济犯罪防治法》、《第二次经济犯罪防治法》、《不法麻醉品买卖及其他组织性犯罪形态防治法》、《性犯罪及其他危险犯罪行为防治法》、《犯罪防治法 》等。详见雅科布斯 ,见前注〔3〕,页 28、34;Vgl.Günther Jakobs,见前注〔4〕,S.295。但一个敌人未必是无条件的“完全敌人”(To talfeind),他可能是“部分敌人”(Partialfeind),正如有组织犯罪者可能是一位慈父或一位谨慎的司机一样。〔35〕Vgl.Günther Jakobs,见前注〔4〕,S.290。对于敌人划分界限不清的批判,雅科布斯是这样回应的:
关于“市民”或“市民刑法”和“敌人”或“敌人刑法”,这只是两种理念类型,它们的纯粹模式 (reine Ausp rägung)其实不会出现,现实模式则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因此现实模式也就染上了所有混合样式 (M itschtypen)的缺陷,这也是界限不清的。敌人的特征不是我随意创造出来的,我只是试图从立法者的所谓斗争法 (Bekämp fungsgesetzen)和其他规定中将之过滤 (distillieren)出来。形象地说,这种法律就像不同种类的酒的混合一样,问题出在法律的混合上面,而不是出在过滤者身上。〔36〕Günther Jakobs,见前注〔4〕,S.293。
在大多数情况下牵涉到的只是“部分敌人”,因为在自由社会中,他们被驱逐首先是因为他们自己决定脱离社会、痛恨社会,所以,他们若态度改变,敌人就又可以变回市民。对于从法律中驱逐的问题,社会是根据其日常操作及其现实状况来决定的,如果这种导向性的结果对其日常实践有益,社会就会这样干。〔37〕Vgl.Günther Jakobs,见前注〔4〕,S.294。敌人并不一定是永恒的敌人,而可以嗣后重新与市民缔结和约。敌人刑法并非是一种进行无止尽否定的操作流程,而是在精心经营的法治国之内的一种最后手段,它是要被有理性地作为例外来使用的,而不是要持续使用。为了自主地作出决定,人们有必要知道,人们在敌人刑法上都握有哪些底牌。〔38〕Günther Jakobs,见前注〔4〕,S.294。
对于敌人,要采取斗争或防治性手段,因此,正如前所提到,它还遭遇到行为人刑法的批评,〔39〕笔者略举几例,如 Eduardo Dem etrio C respo,Das Feindstrafrecht darf nicht sein!ZIR 93/2006,S.421,426;C lausRoxin,Strafrech tA llgm einer Teil,4.Aufl.,V erlag C.H.Beck,2006,§2,Rn.129;Ro land Hefendehl,O rganisierte K rim inalitätalsBegründung für ein Feind-oder Täterstrafrecht?,StV 2005,S.158f;M anuelCancioM eliá,Feind“strafrecht”?ZStW 117(2005),S.286 f。认为其违反法治国基本原则、脱离法治国的框架。对此,雅科布斯辩解道,若要将抽象的法治国完全不加限制地实践,那么这种完美的法治国会给恐怖分子提供良好的机会,使他们变得活跃起来。〔40〕Vgl.Günther Jakobs,见前注〔4〕,S.297。学者纳瓦勒特 (M iguel Po laino Navarrete)在《雅科布斯七十寿辰祝贺文集》中也阐释道,对特别危险的情况采用特别的斗争方式,这种作法可以在立法者的敌人刑法般的言说那里得到印证,这符合法治国的原则,同时,它是功能性和实践性的,〔41〕敌人刑法的规则之所以是“功能性”的,纳瓦勒特的解释是,目前已经出现了某些系统性的相关规定,而且这种规则的存在能够使对于法律之人格体和整体社会的危险维持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上。Vgl.M iguel Po laino Navarrete,D ie Funk tion der Strafe beim Feindstrafrecht,in:FS-Gün ther Jakobs,2007,S.541.此言然也。是磨炼出来的,是主张相对的法治国,而并非主张单纯、假定的法治国。〔42〕Vgl.M iguel Po laino Navarrete,同上注,S.549,552。其实,在我们所见到的现今所有的法治国家和法治模式里,法治的阳光依然有其众多盲区和死点,它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普照到每个角落,抽象而普遍的法治国乃是美丽的幻想。法治国亦有其敌人,这种敌人对法治国从根基上进行否定。为了维护公共福祉以及目前尚被大体承认的法治国,需要进行防御性的反应。〔43〕关于此点,可参考 Carlos PérezDelValle,见前注〔32〕,S.528,u.a。
复杂的现代社会使得对现实情状的仔细体察越发重要。雅科布斯冷静地说,对恐怖分子采取预防性隔离等防治性措施,虽然没争论出来一套统一的理论,〔44〕美国学者弗莱彻说道,9·11以后大家都沉浸在什么是恐怖主义和酷刑的争论中,但没有人真正知道这种概念究竟是什么,当然,也有人试图定义这些概念,但是唯一的办法还是将之交给公众常识和政治家来判断。See George P.Fletcher,TheGrammarofCriminalLaw:American,Comparative,andInternational,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64-65.这种思维似乎类似笔者以前的主张,但又不同。但其实都在做了。这种任务现在是由警察承担的。为什么刑法要将抵抗危险的威胁这一任务收归门下呢?这样做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因为首先,对一个恐怖组织的形成,警察无法长久地认为这会有什么安全的法律后果;其次,就敌人刑法而言,警察也至少会给出一个实质刑法和诉讼程序方面的法治国的保证,为的是做得使法治国能够承受以及遮掩和市民刑法的区别,只要能够和矫正、保安措施相当即可,特别是那些和实质刑法相配套的抵抗危险措施。因此,敌人刑法,尤其是反恐怖主义刑法,乃是通过保证安全来维护法效力和实现刑法目的,而作为法效力之担保的市民刑法也开始抵御危险。〔45〕Vgl.Günther Jakobs,见前注〔4〕,S.295-296。这些抵御危险的防治性措施,不排除其混杂敌人刑法的嫌疑,在德国《刑事诉讼法 》第 81条 a、第 100条 a和 c、第 110条 a、德国《法院组织施行法 》第 31条等都已经明文规定。此外,美国《爱国者法案》(2001)第 106、210条、英国《反对恐怖主义和犯罪的安全法案》(ATCSA,2001)第 21-23条、英国《防治恐怖主义法》(PTA,2005)、哥伦比亚《恐怖主义斗争法》(1988)以及欧盟宪法协议草案 (VVE)III-42、62条等地方中也有此类规定。〔46〕详见 A rnd t Sinn,见前注〔9〕,S.109-111。其中,英国被认为是“高度武装起来的欧洲国家”。弗莱彻也说,2001年后美国针对越来越令人担心的恐怖分子所采取的手段似乎超过了“古典世界”。〔47〕See Geo rge P.Fletcher,sup ra no te 44,p.175.阿德特·辛恩面对法治国之凋零现状,忧心忡忡地指出,鉴于尖锐化的危险局势,刑法基本原则已有松动,法治国有转化为安全国 (Sicherheitsstaat)的危险,这取决于刑法是否更多地守住其基本原则,否则它会丧失其强硬的说服力。〔48〕A rndt Sinn,见前注〔9〕,S.117。
在危险丛生的现代社会,与固守在既有的启蒙原则框架内不同,雅科布斯的敌人刑法大胆地承认了对启蒙原则的突破,这其实是在缩小恣意的敌人思维的规则领域,将游离或隐藏于我们法律体系的那部分的敌人政治和敌人警务收编到法治国框架下来处理,从而减少这些散杂在我们法律体系中的敌人刑法所可能带来的对法治国的破坏,正如瓦勒所写的那样,其实这也未尝不是一种维护法治国的方法,只是这种方法不那么现代了。相比较于人权和法律在现代危机面前的战栗、模糊与退缩,并注意到市民在混同着敌人刑法的法典中承受的非人道的危险,〔49〕参见何庆仁,见前注〔12〕,页 69。我们也许更应该理解雅科布斯之所谓“一个清晰明确的敌人刑法,比起在整个刑法中,四处混杂着敌人刑法的规定,以法治国的角度言之,是较少危险的”。〔50〕雅科布斯 ,见前注〔3〕,页 39。
四、关于描述与评价
敌人刑法理论的论述方法是相当有争议的。阿德特·辛恩说,敌人刑法不过是安全刑法,只是雅科布斯要把它描写成敌人刑法罢了。〔51〕“安全刑法 ”出自 Ro land Hefendeh l,O rgan isierte K rim inalität alsBegründung für ein Feind-oder Täterstrafrech t?,StV 2005,S.160。其实,将敌人刑法写成安全刑法,在笔者看来,是更为描述性 (又称为记述性)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划分敌我。对于这点,1963年,被认为是纳粹学者的德国著名学者卡尔·施米特针对 20世纪的局势曾经问道:“这个时代在抹去战争与和平的区分的同时,又在制造核杀伤武器,在这样一个时代,怎么可能停止反思划分敌友?”〔52〕(德)卡尔 ·施米特:《政治的概念 》,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页 98(吴增定译 1963年序)。有论者认为划分敌我和如何处理敌人是政治的任务。V gl.A lejand ro Aponte,K rieg und Po litik-Das po litische Feindstrafrech t im A lltag,HRRS 8-9/2006,S.300.这可能混淆了不同类的敌人。柏林墙如今虽已倒塌,但我们却仍未太平,必要的警惕是需要的,尤其是对仇敌。
描述是存在的反映,但反映不等于存在。不管是安全刑法或敌人刑法,它们都源于现代频发的危险。如何描述危险,其实就至少代表了作者的学术立场和责任,这里面实际上是很难脱离消极或积极的评价的。在敌人刑法的论述方法上,雅科布斯面临着种种诘难,比如西班牙学者克雷斯波(Eduardo Dem etrio Crespo)就批判道,反复强调构造特点的纯描述性,根本就是在为现实辩护,就像普瑞特维茨 (Prittw itz)所说的那样,是在进行确认 (überzeugung)。〔53〕Eduardo Dem etrio Crespo,Das Feindstrafrecht darf nicht sein!ZIR 93/2006,S.420.约亨·博恩则推测这种描述背后的消极性,他认为,雅科布斯的敌人刑法是一种害怕刑法 (Angststrafrecht),尤其是他主张在合法组建的社会中对规范效力之信任的认知性构建之必要性的时候;就像弗兰茨·诺伊曼 (FranzNeum ann)在其《害怕与政治》(图宾根 1954年版)中所强调的,这会妨碍我们在自己理解为人格体之时的自由决定。〔54〕Vgl.Jochen Bung,Feindstrafrech t als Theo rie derNo rm geltung und der Person,HRRS 2/2006,S.70,71.2006年,罗克辛在批判雅科布斯对敌人刑法的描述时写道:“对于一个客观的描述来说,像敌人刑法这样一个充满感情的关键词,可想而知是不合适的。”〔55〕C lausRoxin,见前注〔39〕,Rn.128。2007年,弗莱彻在他的新书《刑法原理》中“社群主义”(Comm unitarianism)一章下写道,我很难理解雅科布斯,为什么他在描述“敌人刑法”之必然性时不谴责这种发展趋势并主张根除……社群主义概念的十分宽松,使得政治理论可假社群主义之名将刑罚确认为是禁止犯罪、将限制危险者视为社会防卫措施,这种包含性的界限 (linesof inc lusion)也产生了排除效应,并产生了“敌人刑法”之样式,政治理论和道义选择之间的边界变模糊了。〔56〕See George P.Fletcher,sup ra note 44,pp.172,181。弗莱彻当然是了解规范论的,〔57〕关于此点,可见 Geo rge P.Fletcher,sup ra no te 44,pp.290-291。他说的“包含性的界限”产生了排除效应,其实也是雅科布斯所谓法律性的界限,而就敌人刑法理论的论述方法是否是描述性而非批判性的,雅科布斯本人则已有驳论:
我的评论是描述性 (desk rip tiv)的,而非规范性 (p räsk rip tiv)的。〔59〕这里的规范性是在和描述性相对的意义上使用的,其带有一定的价值评判色彩,甚至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引者注我也不是不希望敌人刑法能够卸掉其丑陋的形象,可我没有见到可以无条件地卸下的细微机会,因此我试图获取关于它的知识并告诉别人,这种情况也许也是丑陋的吧。我试图指明,恺撒的躯体,亦即国家的躯体,有的时候并不是都穿着体面的法治国的衣裳,而是裸露的,在目前的条件下,它甚至于必须裸露,如果它不要因为“过分法治国”(rechtstaatlicheüberhitzung)而受害的话。对此,常见的反对意见是,这种关于裸露的论调是伤风败俗的、政治导向的、法西斯主义的。不过,决定性的是,论述需针对事实。我敢于这样一试。〔58〕Günther Jakobs,见前注〔4〕,S.290。
可见,雅科布斯的本意是为了揭示现代社会中反对基本原则的敌人,同时充分暴露立法者的敌人思维,而并不代表对其支持或反对。雅科布斯希望区分假定的理想的法律和现实化的法律,他并不想涉及政策或政治上的争论,他将之视为是一滩浑水,他一再写道:“……我并不是出于法政治上的愤怒,在这里我并非采用法政治学意义上的,而是采用分析导向的法哲学和刑事法学来做这个报告”;“我并不是出于任何政治动机来做这个报告的 ”。〔60〕Gün ther Jakobs,见前注〔4〕,S.290,297。
雅科布斯强调其学术性的描述性分析似乎是其一贯做法,包括他对于法益的批判也是如此。他说:“根据规范保护的理论,人们也会政治性地为规范选择对人的自由生命的规定,并且,因此获得法益保护理论引以为自豪的批评性出发点,但是,这是一个政治性的出发点,不是学术性的。对此,没有更多好说的了。”〔61〕(德)G·雅科布斯:“刑法保护什么:法益还是规范适用?”,王世洲译,《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 1期 ,页 105。对于这种强调学术性,而与政治无涉的态度,罗克辛回应道:“在我看来,这里紧缩的学术概念导致法学家给立法者提供恣意和专断。如此的刑事政策肯定还不是学术。但是,来自法治国——自由主义的宪法秩序预先规定的刑法立法的内容界限的发展,肯定是法理学的学术任务,同样的任务还包括,这种发展是否在学说和宪法管辖权中得到证实。”〔62〕(德)克劳斯·罗克辛:“刑法的任务不是法益保护吗?”,樊文译,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页 164。
对于学者是否要进行社会批判或政治批判,卢曼一直在主张,现代社会已经失去了批判的潜能,社会理论家的任务只能着重探明社会的机制,即只要“分析社会”而非“改造社会”,“我们不能再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理解法律,而只能从功能上去理解它。”〔63〕引自张超,见前注〔9〕,页 201-202;(英)马丁 ·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 》,商务印书馆 2002年版 ,页 357。这也便是,我们很难再说“刑法是什么”或“应是什么”,如果不符合既有框架,就进行批判和主张变革,而更多的只能观察、认识和分析刑法如何运作。但是,从罗克辛的角度而言,如果将学术过分紧缩,自然会带来学者的批判功能削减,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由于知识乃是人的认识的积累,那么知识怎么也无法脱离人的评价,这样就必然要求做出价值判断。将关于敌人刑法的认识揭示或传播出来,这本身就代表雅科布斯的内在评价,在他看来,人们应当了解敌人刑法,这便是一种“知”的意义,同时他认为清晰界定的敌人刑法在法治国中较少危险,这其实也没有与评判完全脱离。当然,我们应当注意到,当涉及学术意义问题之时,如果过分紧缩学术概念,也就会慢慢侵蚀对于意义的判断,这种意义判断在现代社会变得尤其困难,以至于雅科布斯要求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理解他的理论,而罗克辛则仍然坚持要进行评判,以对专断的倾向保持警惕。但是,我们更应注意到,若克服对立思维,其实,最佳的同时也是最难的方案是在描述和批判中间保持动态的平衡。雅科布斯是不可能做到纯描述的,但是他可以强调他的描述性,尤其是可以强调他的非政治性。不管怎么样,我们应该承认,雅科布斯的描述至少也能让人达到韦伯所谓科学的第三个目标,使人“头脑清明”。至于雅科布斯的描述是否隐藏着害怕,尚不得而知,这种害怕是否影响了他本人的判断,我们也只能进行客观的推断,应该说,在他新近的敌人刑法理论中,还是流露出对现代法治国框架的一丝怀疑,不过,雅科布斯的表现似乎一向都是“信心满满”的,而且相信文明世界里,一切都是可以计划的,这点使得他持续地坚持他的规范论立场。
但是,广而言之,现代社会乃是令人感到陌生的人为的社会,它是一个反自然的社会,这种属性为其浑身携带的种种病症埋下祸根。我们社会的现代病是如此的深,以至于在没有诊断清楚病理病因之前,所进行的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都可能是隔靴搔痒,如果我不想说这种批判会开错药方或有副作用的话。而且,正如反恐斗争先于反恐理论一样,法律和社会实践并不一定会因为学术批判而停止脚步,它们在很多时候是脱离甚至反对理论的。因此,如果理论确实已经发生于实践之后,现代学者可能要做的更多的是先争取辨清事态,然后理性分析,最后才形成结论。多元化的现代格局瓦解了宏大体系,学术上认识和分析 (“知”)的意义也许已超过了批判和变革 (“欲”)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目前的思想理论界和社会都呈现得如此破碎的原因。执着于抽象的、假定的原则,乃是在启蒙以来的现代道路上继续前进,可是当危机毕现时,我们若不停下来认真看清危机,那么我们可能面对着更多更大的危机,这时,实践做法也许已经和抽象原则脱离,前者成为现代特征,后者成为古典原则了。后现代也就成了现代。在当下的现代,也许危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已为大多数现代人所接受,但是,至少现代社会因其多元性而仍然是宽容的社会,那么,雅科布斯对于现代法治国病症的揭发或对现代社会现象的描述至少就应该予以容忍。
五、关于刑罚与战争
对敌人适用敌人刑法,是否会导致战争的扩大化?这要看如何来认识战争,是否一切对抗、抵御都是战争?不一定。由于在法律体系中早已混杂着敌人刑法的实践,可是我们并没有认为我们的法律体系已导致战争的扩大化,故而敌人刑法上的斗争和防治,并非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国家 /团体间政治的战争。敌人刑法是针对被认为有危险的犯罪者的,这不等于公敌,而针对公敌的斗争理解为战争,问题不太大。在理解雅科布斯的理论之时,笔者比较认可基于当下的语境来思考问题,而并不完全在启蒙话语中推导结论,当然,这并不代表着对启蒙话语的否定。试想,如果我们的地球村遭到村外人的恶意攻击,村外人是否也应被作为人格体来对待呢?很可能的情况是,双方都不会互相被当做人格体来对待,甚至可能被直接消灭,同时,这里的攻击和消灭就基本等同于战争了。就根本破坏法秩序本身而言,不管攻击是源自内部还是外部,只要它被根本性地攻击了,至于这种攻击发动于哪里是没有区别的,就像是区分是无责任的小孩还是精神病人一样,区分内部的敌人和外部的敌人在破坏法秩序上没有意义,〔64〕引自 A rnd t Sinn,见前注〔9〕,S.115。不过,这里要进一步指出,只有攻击原则性地威胁或否定了法秩序,才产生持续的重大危险,这时攻击者脱离了规范,无法给人提供最低的认知性安全,则应将攻击者作为敌人处理,而这却非精神病人和市民犯罪人所为。应当注意,现代的攻击已经弥漫在诸多领域,而且时常挟带紧迫的危险,面对这些有的甚至为人类所未知或无法控制的攻击,对于克雷斯波主张的“不可逾越地区分刑事政策的、政治哲学的、法哲学、法社会学和法教义学意义上‘攻击’是人权的任务”,〔65〕Eduardo Dem etrio Crespo,Das Feindstrafrech t darf nich t sein!ZIR 93/2006,S.427.笔者表示怀疑,因为作出这样严格的所有区分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刑事政策的和政治哲学的,很难区分,而且很可能是人们的一厢情愿。就像想达到纯描述一样,当然我并不怀疑论者善良的意图,但他可以这样强调,笔者关心的主要是规范意义 (法教义学)上的法秩序破坏。
雅科布斯反复用一个关键的词——“认知”(kognitiv)。这点是与前面所提到的自然交往与社会交往之区别紧密相关的,由于每个人都必须服从于自然法则,那么在社会交往中,就要期待合作者符合自然规则(而不是法律规则),这种期待便是认知性的,亦即,在期待落空时,就代表人们进行了误算,若人们能忽略这样一个不小的落空的话,就须再学习,并通过经验变得更聪明,并在将来更好地计算。〔66〕Vgl.Günther Jakobs,StrafrechtA llgem einer Teil,2.Auf,W alter de Gruyter,1993,S.7.这种认知性世界的自然规则是由自然罚的危险保障的,而对诸人格体而言,也就是在规范性相互理解的社会中,这些认知性规则作为共同体环境的诸规则,当其由交往中的可联系性来确定时,这些规则就成为一些共同性的东西,也就是,人格体将这种环境理解成为可分离的、客观的东西了。〔67〕雅科布斯,见前注〔18〕,页 56以下。相异于这种环境,法规范乃是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当为性规范,是建立在理性基础的社会规则而不是认知世界的自然规则,若对于法规范进行自然状态的违反,无法提供认知上最低限度的保证,则成为任意地根本上违反期待的事情,这时,需要进行认知性地解决。卢曼也认为,认知性与规范性之区分出发于解决问题、处理失范的功能性需要。〔68〕SeeN ik las Luhm ann,ASociologicalTheoryofLaw,trans.by Elizabeth King andM artin A lbrow,Routledge&Kegan Pau l,1985,pp.32-33.敌人刑法是超出我们的既有假定框架而又实际存在的刑法部分,敌人痛恨我们,并以超出我们正常规范交往的理性理解方式,原则性地破坏了既有的规范,无法提供认知性的安全(kognitive Sicherheit),而这种认知安全正是规范效力和规范信任的内在意义,以至于我们要对敌人适用与市民犯罪人不同的特殊解决方法。这个既有的假定框架,就是市民刑法,正如雅科布斯所说,在市民刑法那里,认知安全只是附带地加以调整的,而在敌人刑法这里,则成为主要的任务。〔69〕引自 Lorenz Schulz,见前注〔30〕,S.661。同时参见 Carlos Pérez DelValle,见前注〔32〕,S.521;M iguel Po laino Navarrete,见前注〔41〕,S.539。敌人的活动不仅令人难以理解,而且“令人讨厌”,他在区分我们熟知的市民犯罪人和相对陌生的敌人时写道:“规范破坏者不是规范上不受约束的、由其他的人所组成的处于讨厌状态的环境这种意义上的群体的敌人,而是群体的成员。如果由外部者实施了扰乱,那么,这种扰乱将被——像所有讨厌的环境一样——认知地解决,也就是说,敌人的活动被阻止;至于人们是消灭敌人还是与敌人谈判,则是一个纯粹的合目的性问题。”〔70〕雅科布斯,见前注〔18〕,页 100。
这里的规范破坏者就是市民犯罪人,而不是脱离规范的敌人,敌人是必须被认知性地处理的。弗莱彻是这样理解敌人刑法的:针对处死累犯或对其任意的徒刑的情况,最好的描述方法是,它们并不代表着实践正义,它们是对“敌人”的战争行为。〔71〕Geo rge P.Fletcher,sup ra no te 44,pp.172-173。紧接着,他又引用尼蒂奇(N iditch)的观点写道,战争这一词也许不完全适合,因为战争是一种“替代性法律秩序”(alternative legalo rder),并遵守其本身的互利和适当处遇的规则,这种规则建立于战争会结束,且人们要重新与一度的敌人和平共处的期待之上。而对于罪犯,则没有这种和平共处的期待,因此,这里的战争是圣经中讨论的那种圣战模式下的消灭。〔72〕N iditch(1993)at28,in George P.Fletcher,sup ra note 44,p.173。由此可见,弗莱彻也许有所误解,他将对敌人的处理理解为圣战,而且似乎认为对于敌人罪犯无法重新缔结和约。雅科布斯本人则认为他所谓的敌人没有宗教意义 (比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战乃是两个群之间的战争,更类于“公敌”),而且嗣后可以和解。
那么,敌人刑法理论中对于敌人的处理是否是一种战争?这其实也是一个合目的性的问题。对于合目的性的问题,也就会不太注重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无所谓启蒙以来的种种法治国框架的限制。考夫曼描述道,在现代多元的风险社会中,人类必须放胆行事,不能老是在事前依照既定的规范或固定的自然概念,来确知他的行为是否正确,亦即,人类必须冒险行事。〔73〕(德)考夫曼:《法律哲学 》,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页 426。因此,对于马上将要用炸弹炸毁人山人海的公共场所的恐怖分子,或者对于获取核武器的恐怖分子,若通过市民刑法无法排除危险的话,则只能通过敌人刑法,即便是刑讯逼供,也要排除危险,救出无辜的市民。针对紧急情势下突破既有的法治国原则限制的做法,雅科布斯谈到,没有人会把人们有良好理由要做的事一折不扣地真正执行,有的和平主义者说,在紧急自卫下,若不想杀死侵犯者 (即便有必要),我们可以选择退缩和自杀。因此,法治国如果不想蹚着敌人的鲜血来实现其机能的话,法治国也可以选择退却和自我毁灭。〔74〕Günther Jakobs,见前注〔4〕,S.297。对于这种畏惧敌人的做法,雅科布斯不以为然,他认为:
如果要在无条件的和平主义和无条件的防卫中间寻求平衡的话,限制在必要方面上的敌人刑法是一个现实选择,这种谦抑的敌人刑法要独立于现有一些具有腐蚀性副作用(korrump ierenden Nebenw irkungen)的敌人刑法……也不是要废除每个敌人刑法条款,而是要发展出有根据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越清晰,那么敌人刑法和市民刑法交错所带来的危险性就越小。〔75〕Vgl.Günther Jakobs,见前注〔4〕,S.297。
如果我们没将雅科布斯理解错的话,其实,他的敌人刑法理论并非要使战争扩大化,他也自然没有或极少有政治性考虑,不过,可以注意到,这种敌人刑法理论所带来的附带作用可能是:在承认现有法律体系缺陷的前提下,通过区分理想类型意义上的市民刑法和敌人刑法,从而减少而不是消灭这种缺陷的四处蔓延,使法律体系严整清晰,同时也成为一种在风险社会中维护法治国的“以战止战”的必要方法,当然,这两个“战”是有区别的。因此,在正确划分敌我的前提下 (这种划分也并不是完全恒定的),对敌人进行斗争或防治,我们可以说是发动一场战争,但是,其并不完全同于我们一般所理解的针对公敌的战争。若要在战争和刑罚之间划一条严格的界线,应该有一部分属于语言学的问题。而从敌人刑法的角度言之,对敌人可以作战,也可以适用刑罚,目前现实情况即是如此。人们要做的,最多也只是基于现代社会的问题意识,进行这部分战争和刑罚的整理和转化,或更确切地说,使得对付敌人的措施清晰化、文明化或被当作清晰化、文明化,因为无论如何,敌人刑法至少是属于一种依循着一定规则的做法,而并非直觉的感情用事。〔76〕参见雅科布斯,见前注〔3〕,页 17。至于敌人刑法是否导致战争扩大化,由于政治意义上的战争场数、程度都无法进行彻底量化的统计,所以,敌人刑法也并不一定导致战争扩大化,反而可能通过常态的控制和防治,能够减少战争的发生或扩大。
* 北京大学法学院 2008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