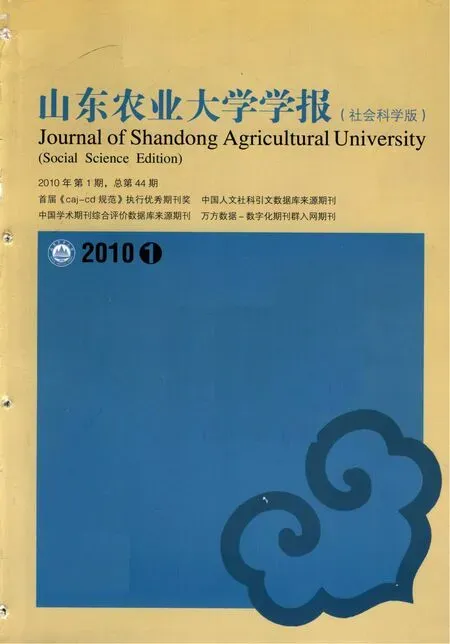斯蒂拉:一位反“男性中心主义”的女人——《欲望号街车》的女权主义解读
□赵冬梅
斯蒂拉:一位反“男性中心主义”的女人
——《欲望号街车》的女权主义解读
□赵冬梅
《欲望号街车》中的斯蒂拉历来被解读为男权的牺牲品。通过运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剖析这一人物发现:斯蒂拉并不是“女人的神话”所定义的“家中的天使”,而是具有颠覆男权力量的新时代女性的代表者;“母性”和“孕育”则是她用来解构“男性中心主义”的武器。
斯蒂拉;男性中心主义;女人的神话;母性;孕育
一、引言
美国 20世纪著名戏剧家田纳西·威廉斯 (Tennessee W illiams)的代表作品《欲望号街车》(A Street Car Named Desire 1947)是美国剧坛上唯一一部曾赢得普利策奖、纽约剧评奖以及唐纳德森奖三个主要大奖的作品。
《街车》讲述地是一名没落的旧南方淑女布兰奇的悲惨经历:丈夫英年早逝;家境衰败;因生活糜烂被所任教的学校开除并被驱逐出城镇 Laurel;投奔妹妹斯蒂拉却被妹夫斯坦利强奸,继而因精神失常被送进精神病医院。1947年 12月 3日,《街车》首映成功之后,优雅、脆弱而又敏感的布兰奇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威廉斯研究者们 (Signi Falk、RogerBoxill、Felicia Hardison Londre、Louise Blackwell)关注的焦点。相比之下,布兰奇的妹妹斯蒂拉却远远没有布兰奇引起评论家们的重视。Louise Blackwell在其撰写的文章“南方淑女之窘境”中把她归入南方淑女的第二类——从属于专横跋扈、比自己地位低下的人 (即她的丈夫斯坦利)的陨落的“南方淑女”。邓添天的“从心理学视角解读斯蒂拉”以及刘娜的“斯蒂拉:家中的天使——《欲望号街车》的女性主义解读”则认为她是男权的附属品①和牺牲品。总而言之,斯蒂拉要么被威廉斯研究者们所忽视,要么被当作柔顺的代名词。然而,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剖析这一人物,我们却发现貌似天使的斯蒂拉实际上是一个反“男性中心主义”者,“母性”和“孕育”则是她解构“男权中心主义”的武器。
二、斯蒂拉:家中的天使、女人的神话
“女人的神话”是父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精神枷锁,是男性将自己的审美理想寄托在女性身上的产物。在这个神话体系中,女性被神圣化为“纯洁的百合”、“家中的天使”,为了维护这个美好的形象,女性被剥夺了她自己真实的形象生命,被降低为男性的牺牲品。(朱立元,2005:347)尽管从表象上来看,《街车》中斯蒂拉美丽、纯洁、性情温和,但她并不是“女人的神话”中的“家中的天使”。她是一个不甘于被男人主观想象的新型女人、一个具有颠覆男权的破坏力量的女人。
斯蒂拉和姐姐布兰奇不同,她没有被男性所封予的“南方淑女”之称号所束缚,她有她自己的生活模式,她清楚自己的需求。当美国旧南方的种植园经济被北方新型的工业经济所取代时,她毫不留恋地离开了家,来到了北方的工业城市新奥尔良,开始了新的生活。和“南方淑女”布兰奇以及《玻璃动物园》中的阿曼达不同,斯蒂拉从来不以“淑女”自居。她从不用珠宝和衣服来装饰自己,她就是她自己,不属于任何人,她没必要把自己打扮得光彩夺目而吸引男性的注意。当旧南方所奉行的那套旧礼教和女性的审美已经成为历史,自己家的庄园已经不复存在时,她从容不迫地面对现实,积极主动地适应新的生活。斯蒂拉从来不嫌弃她的丈夫——粗鲁、但是富有活力的“新兴工业的代表者”(Falk,1985:56),也不抱怨生活的艰辛,还能和她的贫穷的邻居们和谐地相处。总之,她生活乐观,从不患得患失,是美国大众文化的新女性,并非男权所主观臆想的“淑女”或“百合”。
同样地,已为人妻的斯蒂拉也并没有向一些威廉斯爱好者们所说的那样变成丈夫斯坦利的附属品或者“家中的天使”。Louise Blackwell曾把斯蒂拉和斯坦利的关系定义在满足性欲的基础上 (Blackwell,1970:12)。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如此。不可否认,斯坦利具有的无限的活力和粗狂的气质深深吸引了斯蒂拉。但是,在和斯坦利的性关系方面,她并不是被动的被蹂躏者,相反,对她而言,斯坦利是满足她身体的生理需求的一个被利用者。在斯蒂拉眼里,斯坦利的阳刚之气、甚至是粗暴都是他男性魅力的展示,是活跃的性冲动的标志。所以,尽管她的社会背景和家庭出身都高于斯坦利,尽管斯坦利被她的姐姐布兰奇描述成一个“古猿”,斯蒂拉绝不会放弃斯坦利——一个让她快乐的男人。
总之,斯蒂拉并非“女人的神话”里的被男人们歪曲和想象的形象,她从不为了把自己乔装成一个圣洁的女人而放弃自我愿望。她为自己生活,并不是男性用来装点门面的标志,更不是男权的牺牲品。不仅如此,她还具有颠覆男权的力量。
三、斯蒂拉:母性、孕育
“男性中心主义”(Androcentris m)意指完全建立于男性经验为基础上的理论和实践,它是社会不容置疑的准则。长期以来,男人被定义为社会的“主体”,而女人则附属于男人,是社会的“客体”。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朱莉亚·克里斯蒂娃 (1914-)认为,女性如果想要取得社会的“主体”地位,和男性抗衡,就必须消解“性二元对立”、颠覆“男性中心主义”。为此,她提出重新审视“母性”的必要性,认为“‘母性’是对‘男性中心主义’的一种挑战;怀孕和生育打破了自我与他人、主体与客体、内部与外部的对立”。用克里斯蒂娃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剖析《街车》中的斯蒂拉,我们发现她正是一个“双性同体”的女性形象。
首先,“母性”是斯蒂拉所特有的、动摇“男性中心主义”的武器。她宽容、善良、富有爱心和同情心,是一个“母性”十足的人物,这主要体现在她和姐姐布兰奇以及和丈夫斯坦利之间的关系上。
斯蒂拉和姐姐布兰奇的关系是和谐的。她热爱自己的姐姐,同情她的遭遇,并竭力保护她。斯蒂拉对布兰奇的关心和爱护遍布于整个文本:在第一场中,布兰奇突然造访并打算要投靠斯蒂拉,斯蒂拉“欢快地”拥抱姐姐,欢迎她的到来;得知她们的亲人们一个一个地死去,庄园“美丽的梦”已不复存,善良的斯蒂拉想象着布兰奇所独自承受的巨大痛苦,忍不住哭泣;在第三场,布兰奇打开斯坦利的收音机,却引起斯坦利大怒,“他把收音机扔到了窗外”(W illiams,1959:57),为了维护布兰奇的尊严,斯蒂拉和斯坦利大吵并打算离开斯坦利;看到布兰奇在和斯坦利的朋友米奇交往时,斯蒂拉衷心地祝福她,希望布兰奇能有一个美好的婚姻;在第七场,斯坦利告诉斯蒂拉布兰奇声名狼藉的过去——她曾经和营地的士兵们有性乱行为、和一位 17岁的中学生发生关系而被任教的学校开除并被市长逐出所在城市,然而,斯蒂拉根本不相信斯坦利所说的一切,她除了表现出对布兰奇的担心之外,对布兰奇的态度却没有任何变化,仍然精心地为布兰奇布置生日晚会;在第十一场,斯蒂拉并不知道当她在医院待产时丈夫已经强奸了布兰奇,她只知道布兰奇已经精神失常,在护送布兰奇去精神病院时,她叮嘱房东尤妮斯多赞美布兰奇的美貌,不允许斯坦利粗暴地对待布兰奇。从上述来看,斯蒂拉对敏感而又脆弱的布兰奇的爱远远超过了姐妹之情,她就像布兰奇的姐姐,甚至是她的母亲,对布兰奇百般呵护,展示着“母性”所特有的无微不至的关爱。
斯蒂拉和丈夫斯坦利之间远远超过了夫妻关系。一方面,斯蒂拉欣赏斯坦利身上洋溢着的粗犷的男性魅力;另一方面,他还是她臣服的对象,是她的孩子,在第三场,当斯坦利和布兰奇发生冲突时,斯蒂拉为了维护布兰奇的尊严,离开斯坦利去了邻居家里。斯坦利哭着,给斯蒂拉打电话,求她回来。当斯坦利看到斯蒂拉出现在楼梯上时,他“跪在台阶上面,头伏在她的肚子上......”(W illiams,1959:60)。斯坦利哭泣并向斯蒂拉下跪这一剧情,从女权主义的角度进行分析,极具象征意义:它标志着男权向女权低头、男性对女性在家庭中行使权威的认同。此时的斯蒂拉俨然一位母亲的形象,“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温柔和爱意,她抚摸着他的头 ,把他扶起来 ”(W illiams,1959:60),原谅了犯了过错的“孩子”。在第十一场,把布兰奇送精神病医院之后,斯蒂拉因无法割舍姐姐而痛哭,此时的斯坦利“跪在了她的身边,手伸进了她的衣服......”(W illiams,1959:142),他已经完全被她奴役,变成了一个离开“母亲”就无法生存的“孩子”。
总之,具有“母性”的斯蒂拉能包容对立的双方——以斯坦利为代表的“男性”和布兰奇为代表的“女性”,她在双方的斗争中周旋,力图使对立的双方能够溶解矛盾,融入一体,在一个家庭中和谐度日。虽然随着斯坦利和布兰奇矛盾的不断升级,斯蒂拉的理想最终也没能得以实现——布兰奇去了精神病院;斯坦利则留在了家里,但是她的坚持和努力已经动摇了“男性中心主义”的家庭模式。
其次,具有“孕育能力”则是斯蒂拉解构“男性中心主义”的重要保证。伊格尔顿曾说过,“也许她是代表着男人身上某种东西的一个符号,而男人需要压制这种东西,将她逐出到她自身的存在之外”(伊格尔顿,1988:193)。这就表明了男人为维护这种二元对立需要压制和排斥女性。为了消解这种顽固的二元对立,颠覆男权,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提出了“双性同体”的概念。在西苏看来,女性是具有无尽包容性又不排斥差异的新的“双性同体”。在《街车》剧情开始之前,斯蒂拉就已有身孕。“怀孕”的斯蒂拉打破了女性“自身和他人”、“外部”和“内部”的对立,模糊了父权制男女界限,是一个“双性同体”形象,她包容男女于一体从而解构男女二元对立。
不仅如此,斯蒂拉的“怀孕”也打破了他人和他人之间的界限。在第二场,当布兰奇得知斯蒂拉怀孕的消息时,她非常兴奋,“斯蒂拉宝贝,有个孩子真是太好了......既然我们已经失去了庄园‘美丽的梦’,或许要靠他 (斯坦利)来传宗接代了。”尽管布兰奇和斯坦利总处于激烈的冲突中,但是她的妹妹斯蒂拉的怀孕却使布兰奇向斯坦利让步,容许他的血液融入她的家族。因此,布兰奇和斯坦利之间的血缘界限已经不复存在,他们连在了一起,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在第三场,斯坦利向斯蒂拉求饶的场景中,他把头伏在“她因身孕而微成弧形的肚子上”,此时的斯坦利不再是那个脾气暴躁的丈夫,而变成了一个温顺的“孩子”,向她腹中的胎儿一样静静地依存于她。这样,布兰奇和斯坦利之间的性别区分界限被模糊化,他们似乎变成了一个“整体”。
简而言之,从女权主义视角重新审视斯蒂拉,我们对这一人物有了更深的认识,了解到斯蒂拉是一个具有“母性”和“孕育”等颠覆男权的潜质和力量的全新的女性形象。
四、结语
表面上看,斯蒂拉是一位性情温和的“家中的天使”,她纯洁、美丽、而又善解人意。实际上,她却是一个颠覆男权、解构“性二元对立”、消解“男性中心主义”的具有破坏力的女性。然而,在运用法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来剖析斯蒂拉这一人物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斯蒂拉在经济上并不独立这一事实。这就使得她未能把批判男权中心的触角深入到社会阶级斗争方面去。
不可否认,斯蒂拉身上所洋溢着的“母性”和“女性”对于斯坦利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使得他在精神和肉体上强烈地依恋着斯蒂拉。然而,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斯蒂拉却也不得不依靠斯坦利过活。在第二场开头,斯蒂拉和姐姐布兰奇出门闲逛之前,她对斯坦利说,“你最好给我点钱以便我们在门口一些小地方逛逛”(W illiams,1959:32)。通览剧情 ,斯坦利的话语“我的家”、“我的洗手间”、“我的收音机”充斥着整个剧本。他时时刻刻都在提醒他身边的女人,他是家庭的核心和主体。每当这时候,没有任何经济基础的斯蒂拉只好默默地听他在一旁吼叫,没有任何的话语权。
加亚特里·斯皮瓦克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在《臣属民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 Speak?)中提出:只有将经济引入对女性问题的心理分析,才能去关注“谁失语和怎样失语”。如果女性想实现完全的独立,要完成消解“男性中心主义”的重大历史使命,她们就不能把消解男权中心的策略仅仅停留在主观想象和文化层面。因此,法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者所提出的以“双性同体”来颠覆“男性中心主义”的策略带有非常大的乌托邦色彩,很难与现实中的妇女解放斗争真正结合在一起。(朱立元 ,2005:359)
注释:
①邓添天的“从心理学视角解读斯蒂拉”认为斯蒂拉对于斯坦利有“俄狄浦斯情节”。而“俄狄浦斯情节”的三角关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因此,斯蒂拉被认为是“男权”的附属品。
②转引自《自成一家: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泰森公司1985年版 ,第 85-86页。
[1]Blackwell,Louise.Tennessee W illiams and the Pre
dicament ofWomen[J].South Atlantic.Bulletin,1970,(35):9-14.
[2]Falk, Signi.Tennesee W illiams[M]. Boston:Twayne,1985.
[3]W illiams,Tennessee.A Streetcar Named Desire[M].New York:Penguin Books,1959.
[4]伊格尔顿·特里.当代西方文学理论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5]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H319.4
A
1008-8091(2010)01-0096-04
2009-12-30
天津外国语学院,天津,3000204
赵冬梅 (1975- ),女,天津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杨红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