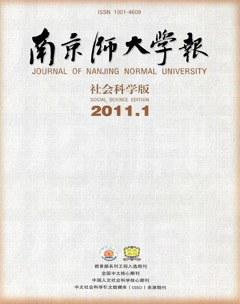“气象文学”刍议
摘要:与中医理论同样是以中国古代“气”论哲学为基础的“气象文学”,烙有中国古代先民的自然现与思维模式的印记,是最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样式。随着魏晋时期主体意识的觉醒,国人的自然观与思維模式由“天人合一”向“人定胜天”发展,呈现出题材上以天气现象为主向季候为主,体裁上由神话、寓言发展为诗词歌赋等更为丰富的样式的阶段性变化。面对现代大学教育分科体制及科学意识的冲击,尽管张君励、粱启超等发起“科学与人生观”之论战,试图坚守艺术、宗教阵地不受科学侵袭终至于落败,中国现代“气象文学”创作与研究终究被剔除精神内涵,空余形式与技巧的部分偶有表现。如今,过于关注探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而日趋狭隘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若要有所突破,传承以人与自然关系为思考重心的中国古代“气象文学”是重要途径,强化“气象文学”的创作研究也是传承中国文化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气象文学;“气”论哲学;科玄之战;必要性
中图分类:1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11)01-0155-06收稿日期:2010-11-10
基金项目:江苏省博士后资助计划项目(0901120C)
作者简介:初清华,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博士后
210044
提起“气象文学”,目前很多文学研究者大都会嗤之以鼻,或认为其囿于题材所限而不屑一顾,或误以为其是专为行业服务而不值一提。其实,与同以“气”论哲学为基础而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医理论一样,作为几千年华夏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气象文学”,才是最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现象。以“天人合一”为道统并凝结了中国古代先民的自然观与生存智慧的“气象文学”,在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大潮中,当文学被赋予救国安邦、声援革命的历史使命时,在“民主”与“科学”思维及话语的冲击下,难免被视为糟粕而遭废弃的命运。正如鲁枢元从生态批评研究视角反思中国百年文学史书写时所指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学史的书写或许可以忽略‘自然这一维度,惟独中国文学史的书写绝对不能无视‘自然的存在”,“正是在这一百年里,中国传统的自然观也已经被社会变革的主流当作古代文化的糟粕,丢进了所谓的历史垃圾箱”。
一、“气”论哲学为基础的
中国古代“气象文学”
何为“气象文学”?气象专家的答案:“文学是人们对社会、对人生体验以文字形式的艺术表达,各种气象现象作用于人体和人脑,并产生不同的精神体验,把这种体验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构成了气象文学。”这个定义中的两个概念“气象现象”、“精神体验”,内涵、外延都不周延,导致此定义太泛,不仅适用于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也适用。而我国的“气象文学”则以其源自《易经》而延至民初贯穿于整个古代社会的哲学根基——“气论”哲学为基础,与西方气象文学相区别,具有更深层的文化含蕴。因此,狭义的“气象文学”,就是指以我国文化传统中“气”论哲学为基本世界观、价值观所表达出对于气象现象的认识与想象,以思考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的文学创作。按体裁可分为气象神话、气象寓言、气象诗词、气象散文、气象影视等;按题材主要有天气、季候、物候之别。
气,在汉文化中,有着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更为丰富的意蕴,很难在其他民族的语言中找到直接对应的字词,这显示出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在中国古代先民看来,“气”是世界的本源,如《易,系辞上》所载“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郑玄给“太极”注的是:“淳和未分之气。”孔颖达疏:“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尽管后世儒道学者对于“太极”之意时有不同见解,至于宋明程朱陆王后,罗钦顺恢复了《易》中的太极就是“气”的本义,批评了前人的偏颇,指出气是自然界万物的本体,由之分化出阴阳、五行、四时,是“太极”的妙用。从混沌未分的淳和之气化生天地(阴阳)、成金木水火土五种形态,来构建万物、孕育人类、再到人的内在意识,甚至是时令、空间地域,世间万物都因“气”而联系于一体,形成中国古代“气”论哲学阴阳五行说的基本理论体系。这一系列过程清晰地呈现出中国先民思维中“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充满了东方智慧。
且不说为后世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奠定思想基础的汉代大儒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假借“天”意倡导“王”权的基本逻辑前提就是“气”论哲学中的阴阳说,如“大旱者,阳灭阴也,阳灭阴者,尊厌卑也,固其义也,虽大甚,拜请之而已,敢有加也。大水者,阴灭阳也,阴灭阳者,卑胜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贱伤贵者,逆节也,故鸣鼓而攻之,朱丝而胁之,为其不义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强御也”(《春秋繁露·精华》),“气之清者为精,人之清者为贤,治身者以积精为宝,治国者以积贤为道”(《春秋繁露·通国身》)。即使如批判天人感应论的无神论者王充,也认为“万物之生,皆禀元气”((论衡·言毒》)、“元气,天地之精微也”(《论衡,四纬》),也是以肯定物质之“气”为本源为理论前提。
因此,随着发端于《周易》并绵延几千年,以“天人”关系为基本问题而形成阴阳五行说理论体系的“气”论哲学,自汉魏始“气”由物质向精神内转的发展,影响并决定了中国古代“气象文学”的基本形态。就题材而言,先秦两汉时期的气象文学中,“自然”大多是以“天气”、气候变化为主要面目;而魏晋至唐的气象文学中则主要呈现为季候学、物候学的特征。
汉魏之前的“气象文学”以气象神话、气象寓言为主要样式,如夸父逐日、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都是对上古时期或干旱或洪涝的天气现象的曲折表达。这些先民心目中拥有非凡才能的英雄的悲剧下场,源于先民以气论哲学为基础产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认识后所作判断。人只是自然的一份子,任何试图征服自然的努力都是不自量力的行为,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否定入主观能动性的改造力。
对于“夸父逐日”等上古神话,已经有很多文化人类学研究者从不同视角作出阐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历来研究者分别从人文意义、人类学等角度对“夸父逐日”作出阐释,如袁珂的“追求光明说”,王孝廉的“昼夜循环现象”说,叶舒宪的“水几为道”哲理说,尹荣方的“利用大树阴影制定历法”说,丁世忠的女巫“求雨仪式”说,张春生的“控日巫术”说等。但大都忽视了《山海经》中“海外北经”、“大荒北经”及《列子·汤问篇》中的不同记载,存有对“夸父”明显不同的情感评价。从发生学的视角探究此神话产生原因可知,“夸父逐日”的传说,是对当时旱灾的解释:“河?胃不足”,即黄河、渭水都已干涸,却可以“北饮大泽”,说明北方还有水量充足的海洋。为什么黄河、渭水干涸,一片树林相隔的北方却有大泽?有个喜欢夸耀、自以为是的人(夸父)不自量力,想
与天上的日赛跑,赛跑就会流汗,被日灼晒也要流汗,总之,是失水很多需要补水,结果喝光了河、渭之水却还不够,又要向北去喝大泽之水,精疲力竭且又累又渴终而亡于一片树林旁。既然有树林就有绿荫,可以遮阳休息,为何夸父还会晒渴而死呢?“弃其杖,化为邓林”,就是为了表明树林不是先于夸父而存在的,《列子·汤问》记载“弃其杖,尸膏肉所侵,生邓林。邓林弥广数千里焉”,可以更明确、清晰地看出“邓林”与夸父身亡之事间的先后顺序,由此可见,夸父的形象只是一个试图征服自然而失败的狂妄者。
夸父的不自量力夸耀行为的后果,不仅是给自己带来死亡,而且造成河、渭枯竭的恶劣影响,而《尚书·洪范》所记载“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皲,鲧则殛死”,即是表明鲧也因擅作主张而招致灾祸。与古希腊神话中表现无法逃脱的宿命的命运悲剧不同,中国神话中的悲剧英雄招致悲剧结局的原因大都被归结为张扬的个性,其主要特征就是逆“天”,与现代人出于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力量而褒奖、缅怀“愚公”、“后羿”、“夸父”的反抗精神不同,这些神话所表达主题的本意,即人与“天”(自然)应和谐相处,人对“天”(自然)要有敬畏之心,这是上古先民囿于自身体力、智力所限而生发对于自然神的崇拜,是先秦时期“气”论哲学观的投射与反映。自然,在上古先民那里主要是以“天帝”的面目存在,云、雨、风、雷、旱涝等天气现象,都被视为“天意”的表达,成为早期“气象文学”的主要题材与表现对象。
随着“二十四节气”在秦汉时期完全确立,中国先民对于气象的认识由早期集中于应对短时间内的天气变化,逐渐转为对长期气候状况更加关注、敏感,从而也带来魏晋南北朝与唐代的气象文学转型,即如陶渊明《饮酒其一》中“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杜甫《春夜喜雨》中“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等诗句中对季候、物候现象的关注与表达。唐诗中的季候特征更为明显,意味着唐人的时间意识远比晋人更为清晰、开阔。如王维的《山居秋暝》中,“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则是秋雨后的一番清新景象,至于“空山”这一意象中所蕴含的“云”、“雨”等气象因子,也有论者已论及①。《临洞庭》是以田园诗著称的诗人孟浩然难得的气魄宏大之佳作,“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颇得谢诗之神韵,而无陶诗的小家子气。气象文学到了唐代,由于佛教禅宗的影响,“气”由清浊之分,进而由清而至于“空”的境界。犹如魏晋书法中的留白处,不是“无”而是有“气”蓄势之处,体现了“气韵生动”的美学要求,唐诗中的“空”也成为此时气象文学的重要美学特征之一。
同时,这种转型的实现,也离不开东汉王充《论衡》中对于社会颓风陋习的针砭,对“人”主体意识的承认所奠定的思想基础。如《论衡·明雩篇》对“雩”这一求雨祭祀行为的功用进行批驳,把人君从“天”中独立出来;《论衡·奇怪篇》则对“儒者称圣人之生,不因人气,更禀精于天”的说法提出质疑,对禹、高、后稷出生神话进行批驳。把人与“天”、自然万物相分离,进而强调“人贵”的意识。对于其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审美意识的觉醒与文学中“自然”山水的被发现都有重要意义,刘勰《文心雕龙,养气》中就有“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己而作,岂虚造哉!”的评价。魏晋时期主体意识的觉醒,首先表现为从自然中分离出的“人”气得到极度张扬,开始对“文”的技法与特征的探讨。
无论是曹丕《典论·论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文以气为先”,或是刘勰《文心雕龙》正文32篇中,“气”字共出现了79次,讲究“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的文学理论框架,又或是钟嵘《诗品序》中对“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的强调,甚至是谢赫《古画品录》中用来品评绘画技艺的标准“气韵生动”,都能看出魏晋时期“气”已不仅是自然万物的连接,人文艺术作为人“气”张扬的结果,与外在的“自然”已构建起密不可分的联系。
人极度自觉的主体意识对宋以后兴起的俗文学的主要影响,就表现为魏晋至唐文学中主要作为独立审美对象的“山水”面目,被注入作者越来越多的主观情感,感物而生情、物我交感、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思维模式。如宋词《雨霖铃》中“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秋曰“气象”不过是起兴之背景,浸润了柳永强烈的离情别绪;元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不着痕迹地化景为情,秋日黄昏的氛围饱蘸落寞之情;明汤显祖《牡丹亭》“惊梦”一折中,对后花园姹紫嫣红的春色描写,其主旨却在于杜丽娘以“三春好处”自况,如此良辰美景却是“恁般天气,好困人也”,“春色恼人”的深闺幽怨。
而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可谓明代气象文学的集大成者,单是第一回“灵根育孕源流出”讲到这石猴的来历时:白天地混沌未分时说起,讲到世外桃源般的花果山,上有一仙石,“二丈四尺围圆,按政历二十四气”,“盖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内育仙胞。一日进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五官俱备,四肢皆全”,风是气的一种形态,可见这石猴原是凝天地精华之“气”而成。途中无处不在的琵琶精、蜘蛛精、龙王等等,小说中对于各路“妖精”的想象,都是以“气”论哲学为根基的,即各种物质都是气的一种形态而已,成“精”就是气凝而成。
“气论”哲学影响下的中国古代气象文学,不只赋予了“自然”人格化的面目,体现了万物有灵的色彩,同时,也有对于“海市蜃楼”这一气象现象较为客观的描写,如南宋林景熙的《蜃说》、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山市》,成为悠久灿烂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科学主义冲击下的
中国现代“气象文学”
随着近代民族危机的加深,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下,严复所译《天演论》中传达的进化论思想,强化了“人”在自然界物竞天择中的胜利者姿态,人本主义思想在中国得到承认并传播。同时洋务运动对西方科技的借鉴及京师大学堂开启的现代分科教学的教育体制变革,使科学意识也得以传播。中国古代气象文学的思想基础“气”论哲学首先受到“科学”、“民主”意识的冲击,“天人合一”的美学观、哲学观都受到挑战。宋以来“气象文学”创作中物我关系以“物→人(情)”为主的思维模式,随着尼采超人哲学、叔本华唯意志论在中国的传播,也逐渐演变为强调“人”在物我关系中的主导作用,“道法自然”的美学观,也被“艺术之美优于自然之美”的认识取代。
众所周知,科学意识的觉醒与强化,被视为“五四”时期思想启蒙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其来反思中国文学与文化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者,首推陈独秀。他在1915年《青年杂志》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六义”,成为五四时期纲领性的口号,其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指出“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在从士、农、工、商、医等诸方面对中西文化传统进行优劣比较后,把其根源都归罪于“气”之想象的结果,更是旗帜鲜明把“科学”与“气”相对立,动摇了中国几千年文化的根基“气”论哲学。不止于此,在他1919年发表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更明确指出“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突显出“科学”与旧文学间的对立关系。
稍后发生声势浩大的“科玄之争”。1923年2月,北大教授张君励在清华作了题为《人生观》的讲演,强调科学只能在物质世界里起作用,不能解决“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人生观的问题;4月,地质学家丁文江(丁在君)发表了题为《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的反驳文章,把人生观等同于“玄学”后,把柏格森的理论与宋元理学同时进行挞伐,强调科学“万能”,拉开了论战的序幕。对于这场论战的哲学意义、文化意义,历来研究成果较多,而这场论战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重要意义,关注者不多。科学得以突破文学艺术领域的防御界限,美国康奈尔大学心理学哲学、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时任北大哲学、清华心理学系教授的现代心理学家、翻译家唐钺可谓功莫大焉!被陈独秀、胡适作序的《科学与人生观》收录了五篇论文的唐钺,在发表《心理现象与因果律》一文参战后,针对梁启超“情感是超科学的”观点,作文《一个痴人的说梦》、《科学的范围》等,指出“美和爱可否分析与他的价值的高低无关”,撇除了价值判断的干扰,认为“美不是超乎理智的东西,美感是随理智的进步而变化的。这种理智的成分,可以用科学方法支配的。其不可分析的部分,就是美的直接经验的性质;那是科学的起点,而且理智事项也都有这种不可分析的起点”,针对“爱”的情感,提出“科学的恋爱”观,认为“讲《红楼梦》之是否科学,要看他所用的方法怎样,不能因为讲的是《红楼梦》,而说他不是科学”、“天地间所有现象,都是科学的材料。天地间有人,我们就有人类学、人种学、人类心理学等。天地间有鱼,我们就有鱼学。天地间有艺术,我们就可以有艺术学。天地间有宗教,我们就可以有宗教学”。振聋发聩之言,为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理论研究相分离及文学学科体系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础。
随着现代“科学”意识对艺术、宗教堡垒的攻破,剔除“气论”哲学思想而加入科学意识的中国现代白话气象文学,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体裁样式,即以文学的形式表现气象科学、气象事业的发展。目前可知最早的现代白话气象文学,是以陈衡哲《小雨点》、《西风》等为代表的现代气象寓言,可以看出古典气象文学与现代气象科学的痕迹,如“小雨点的家,在一个紫山上面的云里”,在跟哥哥姐姐游玩时,被风伯伯“卷到了屋外”,一番游历后,太阳公公把小雨点送回了家去。就气象科学而言,她了解“雨”是由空气中的水蒸汽液化而成,但在“水”、“气”可循环转化的两种形态中,就如鸡与蛋,难以说清何为第一性的问题,她认为“云里”是家,即“气”为水的根本形态,可见传统气论哲学的余响。
在分科教育体系下发展的中国现代气象文学,主要是以科学小品及气象人物传记的形式出现,在小说、诗歌、戏剧等白话文学体裁样式中,由于心理学等科学意识、研究方法对于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侵袭,而更注重对人物心理内在的塑造挖掘,要求清晰明白的语言风格,与古代气象文学所强调物我交感、寓情于景,追求含蓄意境的表达方式难以统一。因此,在这些体裁中气象现象大都只被作为环境描写的一部分,做简单交代或描写。原本表达模糊时间概念的季候学、物候学现象,也大都在科学精神影响下,被精确具体的数字时间所取代。
因此,中国现代气象文学创作与阶段性气候条件变化关联更大。如根据气象部门统计,20世纪我国最严重的气象灾难有:1922年8月2-3日晨的强台风,最大风力12级以上,数百个乡村被夷为乎地,仅汕头就死亡6万余人;台风会带来暴雨,1931年夏季,从粤北,到关外16个省621个县发生洪涝灾害,武汉长达3个月被淹。因此,那段时间的作家如冰心、庐隐同题小说《秋风秋雨愁煞人》,周作人《苦雨》(1923)、沈从文的《雨》(1926),张爱玲《秋雨》(1936)等,大都会以雨为愁苦自是不难理解了。1980、90年代,温室效应厄尔尼诺现象的日趋恶化所引起国人对于气象学的重视,气象文学得到发展,一方面表现《气候诗歌一百首》科普文学的出现,另一方面出现以气象工作者为表现对象的报告文学。
三、加强“气象文学”创作研究的必要性
可以说,与有着深厚民族文化底蕴的中国古代“气象文学”成就相比,现代“气象文学”的创作无论是在数量、质量,体裁样式上都相差甚远。导致当前对“气象文学”的认识也被狭隘化,误以为是艺术性不高,只是为气象行业服务,沦为气象科普之类的通俗读物。加强“气象文学”创作及研究已经迫在眉睫。
首先,加强“气象文学”创作与研究是时代的迫切要求。自1975年以来,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已经上升了0.9华氏度,由温室效应导致的全球变暖等气候变化已成引起时人关注的焦点问题,2000年以来,应该说“环保”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国际上则已由对温室效应的关注发展到对整个生态环境系统的保护,国外哲学、神学、政治学、史学研究者早在1970年代就开始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强调入与自然的关系,指出正波及全球的生态危机。在分析批判理性主义和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时,关注气候变化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但只是把它作为生态问题环境污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并没有做具体研究,并且生态批评日益走向生态学属性,对文学审美属性有所偏离。影片《后天》等灾难片的创作,可以视作是对其审美属性的重要补充,而我国古代“气象文学”是一种跨学科、可资借鉴的文学现象。早在1870年代,恩格斯根据当时自然科学发展所显示的突破原有学科界限的新趋势,在分析各种物质运动形态相互转化的基础上指出,原有学科的邻接领域将是新学科的生长点,此后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天文学等原有基础学科相互交界的领域产生出了一系列的边缘学科,如物理化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等等;1960年代,福柯开始对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分科体系进行反思,科学技术史学科的产生就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结果。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是对
以往科学的分科体系所人为设置学科壁垒的修缮和补充,并为各学科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
其次,加强“气象文学”创作与研究是中国当代文学拓展表现空间的必然要求。“五四”以来,在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哲学等科学、民主意识影响下的中国现代白话文学,自鲁迅开始着眼于人与社会关系而塑造人物形象的乡土小说和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至于茅盾《子夜》为标志文学创作中“阶级分析法”的成熟,再而80年代以来现代主义对意识、潜意识的关注书写,主要被用来研究并表现社会问题,着重于探索人自身、人与社会关系的创作成为“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主体,当代文学创作由于过于专注人物内在心理、思想的挖掘及文学学科的体系化而日趋狭隘。作品中,往往充斥着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偏重于社会环境描写而疏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忽视了对于自然力的表现。要改变当前文学创作视野狭隘、生命力萎靡的现象,题材上由“生活”扩至“世界”的“气象文学”创作是重要路径。
再次,加强“气象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是借鉴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研究的必然要求。
目前古典文学批评、研究中,大多借用西方文论的批评研究方法,而中国古代文论不成体系,讳言气论哲学有很大关系。尽管1980年代新时期以来,在思想解放的大旗下,已有研究者注意到“气象”与文学关系研究并出版了部分成果:如古代哲学方面,同时期译介了日本学者的重要专著《气的思想——国自然观与人的观念的发展》,其后有李存山《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等成果,对于“气”文化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关系得到个别研究者关注;在古代“气象文学”、文论研究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林庚先生1958年发表当时被批判的《盛唐气象》一文,深入探究了南宋严羽“气象”说诗论,在新时期产生深远影响;同时,气象杂志上还发表了报告文学等“气象文学”创作。但都局限于各学科内,缺乏产生国际影响的跨学科成果。无论就深度、广度,数量、质量而言,目前对“气象文学”的关注与研究非常薄弱。
如上所述,无论是对于文学创作、批评与研究,甚至是文学学科发展,倡导“气象文学”创作与研究都是极为必要的。并且,加强“气象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对促进中国气象学科中古代气象科技思想研究、气象事业的发展都有实践意义。
(责任编辑: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