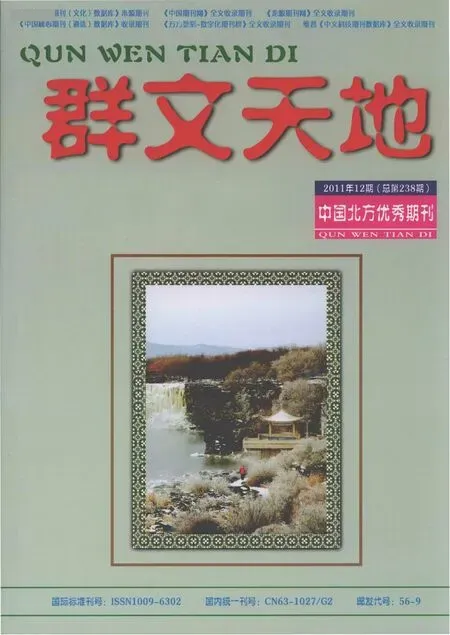试论汉乐府“死亡”主题之浪漫性表达
■殷凤姣 殷学梅
本文旨在通过对汉乐府中描写“死亡”主题的诗篇进行细读研究,探究汉乐府描述“死亡”主题的浪漫主义精神,其浪漫程度,虽不能与楚辞比肩,但是浪漫色彩斑斓闪烁其间,异常动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魔幻奇异的想象色彩;浓郁悲怆的悲剧基调;物我合一的神秘意境。通过我们的分析可以发现,汉乐府中对于“死亡”主题的表达,有着鲜明的浪漫特色。
自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曰:“自孝武帝立乐府而才歌谣,於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敢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之薄厚云。”汉乐府就以其杰出的叙事手法和现实怨刺精神闻名。诚然,当我们阅读《鸡鸣》中富贵之家的奢华生活、《平陵东》中现实之残酷黑暗、《孤儿行》中孤儿的孤苦悲哀、《东门行》中丈夫的被逼无奈时,就会联想到一副真实生动的汉代社会图景。然而,当我们仅仅拈出汉乐府中描写“死亡”的章节时,却会发现其手法是极其的奇幻浪漫,这些诗歌中不仅具备丰富生动的想象力,其语句、其造词、其所塑造的意象、意境皆具浓郁的浪漫色彩。
一、魔幻奇异的想象色彩
在以“死亡”为主题的汉乐府中,魔幻奇异的色彩非常鲜明,这当然和古人的认知程度有关,正如《礼记·祭法》中所说“庶人、庶士无庙,死曰鬼”。《礼记·祭义》中所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因此,在古人眼中,除了现实的世界之外,还有灵魂的世界、鬼的世界。同样的,大自然中的动物具备灵性。比如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因此,当面对“死亡”这样令人无法理解并且恐怖的自然现象时,先民想象的翅膀无疑展开,把这种对“死亡”的奇异感受凝化为诗歌,表达恐惧和悲哀。这就构成了诗中人鬼对话,人与动物交流,鬼与动物对话,鬼与鬼伯对峙而相交织的魔幻世界。我们先看,汉乐府之“死亡”中营造的魔幻世界:《战城南》“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这首诗描述的是死后的尸体,毋宁说是鬼魂与啄食其腐肉的乌鸦的对话,鬼魂对尸体说,我没有得到安葬啊,腐肉怎么逃的掉呢?你为我嚎叫一下吧。我是逃不掉的。这是何其诡异而又生动的画面,而正是通过这样生动富于想象力的画面性描述,作为读者的我们才能了解到“野死”是多么的悲哀,而如果是良臣为国战死而“野死不得葬”的话,那更是凄凉欲绝。前人评价这首诗说“腐肉做人语,妙。‘可’字,‘谅’字,‘安能’字,极尖极冷。‘水激深深,蒲苇冥冥’八字。浑如一幅古战场。”(顾茂伦《乐府英华》卷三)的确,正是这种用词的精准才能塑造出这样一幅动人心魄的阴冷的鬼与乌对话的图画。试想一下,苍茫阴暗的古战场上,乌鸦一边凄厉的叫嚣一边啄食着已经腐烂的尸体,鬼魂在旁如泣如诉,哀求乌鸦不要吃自己的尸体,再加上清冽、清冷的水声和飘摇在风中的蒲苇,这情景不但悲凉,更是魔幻阴暗。陈祚明评价这首诗——‘水深’八字沉郁,‘枭骑’二字悲壮,末段淋漓凄楚,‘暮不夜归’句劲,朝望军士而动感怆之心,死者诚可哀,而偷生者多。忠臣不可得,而思良臣,全师早归为上,亦《大风》之意。颇,牧之怀也。”(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乌生》亦是如此:
“乌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树间。唶!我秦氏家有游遨荡子,工用睢阳强,苏合弹,左手持强弹,两丸出入乌东西。唶!我一丸即发中乌身,乌死魂魄飞扬上天。阿母生乌子时,乃在南山岩石间。唶!我人民安知乌子处,蹊径窈窕安从通,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复得白鹿脯。唶!我黄鹄摩天极高飞,后宫尚复得烹煮之;鲤鱼乃在洛水深渊中,钓钩尚得鲤鱼口。唶!我人民生各各有寿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
全篇借“乌”的口吻来叙述故事。“乌”死后,魂魄飞扬上天。然后回首自己的出生,成长,直至死亡。又借白鹿,黄鹄,鲤鱼的故事来表达“我人民生各各有寿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的哲理。全篇借动物之口来表达生死命运之无奈之叹。因而有学者称之为“‘奇杰之调’。‘唶’读嗟叹之音也,‘端坐’字妙,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出入乌东面’写人,并且有致魂魄飞扬语,奇,正是哀其寿命。‘阿母生乌’故反言一段,若追怨乌不知避患。下乃引白鹿等,畅言之,见患至本不可避。“蹊径”句,生动!”(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二),这首诗歌犹如一个人的回忆录一般,讲述人生,叙述哲理。但主角却是一只鸟,诙谐有趣的同时又显示了作者想象力之奇崛夸张。综观两首以“死亡”为主题的诗,其都具有奇思妙想之魔幻,想象力之丰富,语句之生动夸张,令人拍案叫绝。可见古人对“死亡”之迷惑与敬畏程度之深,只能借用这种浪漫的手法进行诗化表达。
二、浓郁悲怆的悲剧基调
从人类诞生起,“死亡”就是让人恐惧而又悲痛的事件。更何况在医学、科学技术都不够发达的古老年代,“死亡”无疑是人类无法摆脱的悲剧主题。汉乐府中表达“死亡”不仅是奇异魔幻的,并且是浓郁悲怆的。这种悲怆并非展示血淋淋的事实,而是朦胧的甚至是具有着哲理的深刻,是种带有浪漫性质的悲剧。同样,这种悲通过奇妙高超的描绘手法表达出来,使其带有戏剧性、哲理性。前有借“鬼雄”以抒其悲愤的《战城南》,又有《薤露》《蒿里》这样的挽歌。“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薤露》)“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前者以薤上露为比喻人生的短暂,悲怆动人。后者又以魂魄与鬼伯的对话与对峙,凄凉委婉。先民对死亡的恐怖想象在这样凄厉的想象中被暴露无遗,凄婉而又悲恸。
汉乐府是中国叙事诗歌的一个高峰。且看简短急促的叙事诗《箜篌引》:“公无渡河,公意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全诗四句,仅16字。但其中的哀伤只仿若千言万语在空山中回响,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全诗仿若短小的戏剧故事,但对于堕河而死的公子的悲伤却无法自止。因而有学者“一句一转,一转一哭,节短调悲,其音自古。”(王尧衢《故唐诗合解》卷一)有人称之“尽人凄凉无尽”(顾茂伦《乐府英华》卷五)或“不增一语,其哀无比。”(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全诗如前所说,并未展示血淋淋的事实,但表达了无尽的悲哀。沈德潜在《古诗源》中亦评价这首诗歌“缠绵凄恻”。汉乐府中“死亡”主题的悲歌不仅具备哲理性,戏剧性,且带有朦胧的浪漫色彩。我们简单的比较一下刘兰芝和焦仲卿之死与朱丽叶和罗密欧之死。刘焦之死的结局是“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多么的富有诗意且浪漫!后来者的爱情诗歌“在天原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更是对这种原始浪漫的循环表达。这显然比朱丽叶和罗密欧那种在残酷、血腥下的死亡要浪漫的多,因为这里没有毒药、刺刀、血腥、阴谋、误会和复仇,只有五彩斑斓的鸳鸯双宿双飞,自由并行。
三、物我合一的神秘意境
意大利著名文论家维柯曾说:“诗的最崇高的动力,就是对本无感觉的事物赋予感觉和情欲”。这种原始性的诗性思维自古皆有。犹如杜甫所吟:“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的感情可以移位到没有意识,思考能力的动植物身上。汉乐府中“死亡”主题的诗不仅具有物我两化,物我合一的境界,并且这种境界是奇异而又神秘的。如《薤露》,将露珠比作人命,可显人命的异常脆弱。同样《乌生》借“乌”之口表达人之悲哀,是如此的生动,这比从人口中唱出更显得形象。在这里,“乌”是有灵性的,是思考的。其悲凉与人类的悲凉类似,且具说话能力。此时,人与“乌”不分彼此。《枯鱼过河泣》是一则短小寓言。枯鱼过河哭泣,后悔自己的死亡,写信给鲂鱼,希望后者要谨慎,不要重复当初他的下场!不仅表达自己想重回生命饱满状态的愿望,这更是借自然之物的口道出作者的心声!更甚者,这种物我合一的手法就创造出神秘的境界。再看《战城南》:“水深激激,蒲苇冥冥”二句。本为写景之语,实为烘托之词。这两句营造了一个凄厉残酷的悲景来衬托战场上这悲哀惨烈的一幕!此时,水中的蒲苇仿佛都在为死者哀鸣。这一幕让死亡让死亡显得可怖,但又如此神秘莫测。《蒿里》亦是这样一幅图景。人死精魄归蒿里,因为“人命不得少踟蹰”,在这里遭受鬼伯的催促。试想一下,大量的鬼魂聚集在蒿里,天空无月,野草摇摆,风声呜咽,如果这幅情景都不能表达死亡的恐怖神秘,那死亡又该如何表达?因而,汉乐府中“死亡”为主题的诗歌又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浪漫色彩。物我合一的境界就是将人的生命自身和自然融合在一起,将自身比对于自然,思考生死。郊庙歌辞《日出入》便是如此:“日出入安穷?时世不与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 泊如四海之池,遍观是邪谓何?吾知所乐,独乐六龙,六龙之调,使我心若。訾黄其何不徕下!”
这绝对不是一首简单的祭祀之歌,而是在抒发祭祀者对生命短促的感慨,并且向太阳神祈求个人生命的永恒延续,但是人类怎么可以和太阳比肩呢?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是四时春夏秋冬却是永恒的,以前,当我们生活其中的时候,会觉得和自然相依偎,栖息其中,与之共存,但现在体悟生命值浩荡哲理,才发现“时世不与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春夏秋冬不是我所拥有过的春夏秋冬,它亘古的存在哪里,默然凝视人间之生死离合。人们翘首云天,盼望那曾带著黄帝仙去的“乘黄”降临的时候,“龙翼马身”的乘黄,却总是渺无踪影、不见下来。此歌结句“訾,黄(乘黄)其何不倈下”,正绝妙地抒写了人们盼而不遇的一片失望之情。读到这里笔者不禁觉得人不如不要去求长生,而应该顺其自然而死,融入自然之道中。这样,生在自然,死于自然,才是生命的完美完结。因而及其赞同陈本礼《汉诗统笺》解释的这四句话∶“世长寿短,石火电光,岂可谩谓为我之岁月耶?不若还之太空,听其自春自夏自秋自冬而已耳!”这大概也许是生死之真谛吧。
综上所述,以“死亡”为主题的乐府诗,可以观照出古人对于“死亡”这一命题的疑惧性。当表述对其的神秘感受时,运用运用夸张瑰丽的想象,精炼绮丽的语言以及其高超的表达技巧使其具有悲剧性,戏剧性,哲理性,并打上深深的魔幻色彩。
[1]郭茂倩.乐府诗集[M].中华书局,1979.
[2]孙希旦.礼记集解[M].中华书局,1989.
[3]沈德潜.古诗源[M].中华书局,2006.
[4]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M].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