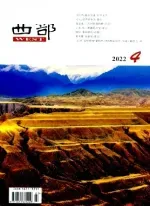昨日年少
矫健
昨日年少
矫健
1966年那会儿我正上初中,下半年停课了。一些出身好的同学,分期分批陆陆续续跑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后来乱了,我这个上中农子弟居然也混进红卫兵队伍。既然身份变了,也就能随大流进北京了。
那是深秋,天凉了,临走时母亲为我打下厚厚的铺盖。我与七八个小伙伴每人背着铺盖卷从桃村挤上火车,中途在兰村下车,等青岛开往北京的那趟车。没想到那趟车从青岛出来就满员,像塞满了虾酱的罐头盒,没什么空当了。站上的人像一群没头苍蝇,忽儿向东,忽儿往西,不知从哪儿进入车厢。好在列车不会走,再晚点也要等大家都挤上去。有人怕车开走,还特意跑到车头前面挡路,站长拿着话筒在站台上大声喊:“红卫兵小将们,大家放心,车再挤也要让你们上去,大家都能上去,都能去北京见毛主席!”
听了这话,车头前面的人陆续回到站台,很多人也不那么慌乱了。我最终是从窗口爬进去的。进去以后才知道,车厢真的是密不透风。座位底下是人,行李架上是人,连厕所都挤得水泄不通。只听得车轮发出“格棱棱、格棱棱”的喘息声,显得那么不堪重负。
记不清走了多久,反正是哪一站都要晚点,一晚就是几个钟头,好像一直晃荡了两天,在夜里到的北京永定门车站。下了车两腿僵硬,路也不会走了。张眼一看,四下黑压压一片人,不用说都是晚间下车的各地学生。一问才知道晚上没别处可去,要等到明天才有车来接。显然大家都抱有既来之则安之的想法,既然走不了,只好就地对付了。临近车站的空旷处升起点点篝火,人群自然围成一圈一圈取暖。火堆毕竟有限,更多的人则自发排成长队,在空地上转圈,边走边高唱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在寒冷的夜空下,歌声环绕着每一个不眠的人。
夜深的北京太冷。怎么度过这一夜呢?我们几个伙伴临时想出一个办法,垒“猪窝”,野外露营。说干就干,我们立马行动起来。我们将附近搁置的一堆砖块搬来,垒出一个长方形“猪窝”,而后解开铺盖,准备好好睡上一觉。躺下没多久,就都躺不住了。爬起来,坐在那里打哆嗦。没办法,不得不重新回到转圈的队伍里跟着唱歌,直到天亮。
谢天谢地,接站的车第二天上午终于来了。百人一组,排队上车,都不知道要到哪儿去,拉哪儿算哪儿。我们这拨小伙伴被送到化工路西口的一家接待站。这儿距市中心较远,不太喧闹。伙食还不错,每顿有白面馍馍,有时能吃上白面包子,还配有小菜。经常听到南方的一些学生为吃不上米饭抱怨,有人把吃剩的半拉馒头扔进垃圾筒里。贵阳的几个大学生对我很好,他们几个分别叫杨文凡、田景彬、吴如香,都是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尽管只大五六岁,但我觉得他们好老了。他们特别喜欢找我说话,临别时还送我一张他们的合影,照片背后还以“诗”相赠:“千里迢迢相逢/为了共同目标/同餐共寝朝夕/今日分别于此/只望努力奋斗/将革命进行到底。”分手那天,我们都掉泪了。我的那些小伙伴私下嘀咕,跟他们大娃娃粘糊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
不说这个了,说说军训吧。各位军官每天把训练抓得很紧,齐步走,正步走,向右看齐,向前看,天天如此。大概十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全体紧急集合。一位军官做动员:“红卫兵小将们,明天我们要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今晚要做好一切准备。明天一早六点出发,走前要系好鞋带,寸铁不带。”
接待站连夜准备干粮,每人一个煮鸡蛋,两个糖包子。大家群情激奋,几乎整夜未眠。翌日早晨接到通知,行动取消。又过了几天,某晚再次紧急集合。那位军官再次做了动员,再次要求寸铁不带,系好鞋带。他还说,昨天在天安门广场拉走了十几车鞋子,听好了,鞋子被人踩掉千万不能弯腰。另外,走前少喝水,那儿上厕所不方便。
这次看来是真的了。伙房又忙碌起来,每人一个鸡蛋,两个糖包子。第二天一早大家匆匆吃完饭,各人带上干粮排队向天安门广场出发。路上看到朝同一个方向涌流的人群密密匝匝,顾不上东张西望,我们只管跟好自己的队,急急前行。感觉走了很久,也走出很远,身边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可能是十几路纵队中的一支。我觉得口干舌燥,没办法,还要跟着走。临近中午,我看到了天安门。在军官的引领下,我们在广场国旗前面的空地上坐下来。那天不太冷,但地上很凉。有些同学想站起活动活动,军官不让。他说大家要手挽着手,老老实实坐着。毛主席出来后,要右手挥动语录本,高呼“毛主席万岁”!他这么一说,没有人再站起来了,只好老老实实坐着。不光是我们,天安门广场上的成千上万人都老老实实坐着,静静地望着天安门城楼。期间,从天安门城楼下开出一辆大卡车,车上站立着战士。后来,长安街上过去几辆摩托车。我们想见到的人还是没有出现。下午三点钟,毛主席终于来了。他在敞篷车上和大家招手,他的亲密战友随他一块儿来了。车走得很慢,自西而东缓缓离去。这天我记住了,是1966年11月26日。
北京这一趟,我的心收不住了。说是串联,其实是想到处转转。从北京回来,学校还是老样子,冷冷清清,一点复课的迹象都没有。高二有位男生叫郑克勇,约我再出去一趟,我没犹豫就答应了。其实,说起来我并不具备外出的条件。家里就父亲一个人下地,弟弟妹妹还小,家境拮据。好在学校给串联的人有点补助,家里不需要掏多少钱。不过回过来想想父母真是了不起,能把十几岁的孩子放出去天南地北到处跑,他们的心太大了。出去吧,孩子,见见世面去,不能老窝在家里。他们都这么说。
那个冬天,我和郑克勇背着行李上路了。我们手头有一份简单的地图,凭它准备试试自己的脚力。走着看吧,走到哪儿算哪儿。没有明确的目标,能走出多远不敢说,至少要到青岛吧。我们两个嘴上都这么说。从乳山二中所在地崖子出发,我们先是向南,而后向西。头一天走出六十多里,第二天没有那么多,只有三十多里。后来的几天,每天都在四五十里。到青岛走了八九天。途经的许多地名记不清了,记得有马石店、盘石店、东村、牛齐埠、流亭等等。经牟平、乳山、海阳、即墨、莱西、崂山等七县市,徒步三百多里。值得一提的是,途中有几次大卡车主动在我们身边停下来,要捎我们一段,都被我们谢绝了。我们硬是靠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走到青岛四中接待站,两人脚上都起满了血泡。后来我把走过的路在地图上标出一条线,那是一个比较规则的S形。
我们被安排在一间教室,几十人挤满了那个有限的空间,每间教室都是人。接待站饭食没问题,早餐是大米稀饭和白面馒头,还有红豆腐,中午和晚上也有白面馒头。青岛不大,没几天就转完了。我对郑克勇说,咱们再换个地方吧。他说到哪儿?我说往南走吧,北方太冷。他说行。我们当即跑去买了两张去上海的船票,回来正收拾行李呢,同房间的两个上海学生说我们老土,还要花那么多钞票吗?花五分钱买张站台票想到哪儿就到哪儿。按照他们的指点,我们把船票退掉,买了两张站台票一下窜到南京。那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没修好,江里只有一排桥墩子。火车到浦口后靠摆渡到江对岸。我头一次感觉火车跑到船上的味道,面对滔滔江水,心潮荡漾,感觉很爽。
在南京睡的也是地铺。所不同的是在青岛铺的是麦草,这里铺的是稻草。到过哪里记不得了,只记得每天一早门口的那个小馄饨摊。一毛三分钱一碗,每碗十三个,不敢多吃,只吃一碗。那馄饨皮薄如蝉翼,馅似蚕豆,十三粒下肚,对一个正在疯长的半大小子来说,也就是走走过场,但碍于囊中羞涩,只好这么着了。我后来吃过馄饨无数,都没南京地摊上的好吃。那个味道成为生命的一抹印记,永远忘不掉了。
从南京出来,到苏州转了几天,之后乘车去上海。到站时天已黄昏,打听本地人,从宝山站到接待站还有很远一段路。我对郑克勇说,我不想坐车,想走着去。他说天黑了,还是一块儿坐电车吧。我没听他的,顺着四川路一直往前走。夜色笼罩下来,身边的有轨电车不时咣当咣当呼啸而过。我心里有点急,于是就加紧脚步,有时还小跑一阵儿,试图追赶前行的尾灯。快半夜了,我终于摸到外滩附近的接待站。妈呀,累趴下了。郑克勇还在等我,看到我喜出望外,他说后悔死了,就不该叫我一个人走,黑天瞎火的走丢了咋办?明天你不能再自个儿瞎闯了,怕坐车咱不坐车,咱一块儿到街上转转。
第二天,郑克勇果然担当起大哥角色,他要带我一块儿上街看看。住在同室的西安的一位老兄也随我们一块儿去。走出接待站,这才看到街道两旁认不出本来面目了,整个是大标语大字报的天下。有打倒陈丕显的,有打倒潘汉年的,还有打倒曹狄秋的。更惹眼的是“誓死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某某某不低头就砸烂他的狗头!就叫它灭亡”!这些大标语,字比一层楼还高,人在旁边走,觉得非常矮小。被打倒的名字都划下巨大的红八叉,在萧瑟的街道上显得格外刺目。高音喇叭里嗷嗷响着,不时传出一些战斗歌曲,最使耳朵留意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
天上飘起零星的雪花,感觉出寒意。我们往前走,人陡然多起来,一问是南京路。西安那个老兄突然兴奋起来:“哎呀,我就想找这地方,换纪念章呢。”郑克勇也要随他挤进人堆,我说尿憋,到哪儿撒尿呢?没办法,他只好折转身来,陪我找茅厕。走出好远也没见到想去的地方,他也为难了,这咋办?他说朝树上撒吧,我不肯。就觉得绷不住,下面开始滴嗒了。郑老兄边东张西望,边唠唠叨叨,都说城市好,撒泡尿都找不着地场,有什么好?扭头又数落我,穷毛病,小鸡巴家家的往哪儿尿不是尿?叫你朝树上撒你还不撒,这下好,尿裤子了吧?他说得对,我阵雨转小雨了。他最终在弄口发现一个尿池时,我已经“雨转晴”了。那天不知怎么回去的,只记得裤腿泛硬,不敢看人。
回去时,西安那位老兄正在摆弄纪念章。他兴致勃勃,满脸放光,说上海没白来,收获太大了。我们凑到跟前一起分享他的喜悦,怪不得他那么高兴,五颜六色的各类纪念章把他的一方大手帕别得满满当当,他一晃动就嘎啦啦响。他在我们跟前晃了晃,像在挥动一面旗帜。之后他把手帕平铺在褥子上,给我们一一介绍。哪个是遵义,哪个是延安,哪个是瑞金,哪个是韶山,哪个是井冈山,哪种纪念章用什么材料,哪种最攒劲儿,哪种能以一换三,还有以一换五……等等,他讲得眉飞色舞,非常陶醉,把我和老郑说得目瞪口呆。听他这一说,我和老郑自惭形秽,我们只有一枚拇指大小的头像挂在胸前,太寒碜了。我和老郑都眼巴巴看着他说,因条件有限,瑞金、韶山那些地方肯定是去不成了等等。西安老兄显然看出我俩的意思,他很有恻隐之心,说分手时一定赠给我们一枚。后来看到我的裤子,西安老兄问咋回事?我不好意思说,老郑哈哈大笑,把事说给他听,他听罢也笑了。他说到上海男人日怪得很,说话囔囔唧唧,撒尿胆贼大。在弄堂口掏出家伙就撒,屁股后头有大姑娘小婆姨来来往往说说笑笑,他就跟没事儿一样。他冲我说,他们都不怕,你怕个甚?
说到上海男人胆大,西安老兄还引出另外一件“怪事”。“真是怪事,”他说,“你们没看见吗?南京路上在拥护张春桥当上海第一书记的大标语下面,有个叫孙悟空的又贴上坚决反对他的另一条标语。这孙悟空是谁?胆子咋这么大?”我们说看到了,在我慌慌张张找厕所时,偶尔瞥了一眼,当时内急顾不上细想,回过头去看此人真是胆大包天。这事成为一个谜,直到四十年后我读到一篇文章,才获悉真相。原来孙悟空不是一个人,而是以复旦大学学生胡守钧为首的一批人。胡守钧曾在上海展览馆咖啡厅当面责问张春桥,还揭露他在三十年代化名狄克攻击鲁迅的老底。这且不算,“孙悟空”在复旦大学还召开两万多人的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胡守钧作了重点发言。为此胡守钧几乎送命。昔日阶下囚,今日胡守钧是复旦大学教授。
在那个寒冷的冬季,我在上海度过了二十多天。阔绰的西安老兄很够意思,他还记着自己曾说过的话。分手前一天他送给老郑一枚“遵义”,送给我一枚“韶山”。他从手帕上取下这两枚金属物件时,我感觉他的手在微微发颤。惭愧的是我和老郑手头拮据,无以回赠,这让我好些日子难以释怀。
从南方回来,是一段长期停课的日子。百无聊赖,我用来解闷儿的是笛子和二胡。二胡好像是抄家时从英语老师陈玮宿舍拿来的,就一把。好些人围在火炉旁边,你抢我夺地争着过瘾,半天能轮上一小会儿。
后来我就不凑热闹了,找来一本陆春龄的笛子演奏法,整天揣摩。
这本书不难读,但要练好每一种技巧就不那么容易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从训练呼吸、舌头、手指循序渐进,直到熟练掌握震音、吐音、颤音、滑音、泛音、指变强弱音等等技巧。即便如此,有时为哪一首曲子中十六分音符的双吐技巧,我躺在被窝里还练舌头呢。
那年学校成立文艺宣传队,我成为笛子演奏的第一人选。宣传队排了两出舞剧,一出《收租院》,一出《白毛女》。乐队是一支简陋的小民乐队,没有双簧管。像“窗花舞”那样大段的十六分音符演奏,全靠笛子。这对我是很大的考验。距离正式演出的时间不多了,队友都为我捏着一把汗。
那是秋天的一个夜晚,天有点冷。乳山县(现为乳山市)政府广场人山人海,有人说至少有两万多人。在阵阵寒意中,演出获得很大成功。我那段“窗花舞”的吹奏尤其值得一提,为演出增色不少。演出结束时,县吕剧团一位专业吹笛子的人特意跑到后台看我,他说我吹得好,问我跟谁学的,我说是自学,他很吃惊。
之后,我们为驻军慰问演出。在部队礼堂,我独奏了一曲《奔驰在千里草原》。有“窗花舞”垫底,这回就放松多了。那一刻几近忘我,完全沉醉了。多年之后回想起来,我从内心确认那是心灵的沉醉,是生命的沉醉。
后来我学习二胡,还拉京胡、板胡和坠琴。坠琴与二胡指法不同,两音之间要空一个手指,似乎更难一点。除笛子外,我的坠琴也有点儿味道。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农二师造纸厂做工。厂里搞文艺演出,因为吹笛子的人有了,扬琴没人敲,就赶鸭子上架让我敲。我说没学过,管事的人说练练就会了,于是练了两三个月,就跟着上台演出了,没想到有人还说挺像回事儿。
时常在乐谱里摸爬滚打,我似乎对乐谱有特殊的敏感。我没学过五线谱,但对简谱却是手到擒来。即使是头一回碰到的新歌,拿到手上也可以唱出来,而且对曲谱的记忆格外精准,一首歌哼上三五遍就记住了。至于像《白毛女》、《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等等旋律优美的剧目总谱,我都能倒背如流,即便是一个滑音也不会错漏。
宣传队散摊儿时,在县城一家照相馆照过一张合影。照片出来后不知为什么,每个人的眼睛都不见了,弄得大伙儿很扫兴。还是音乐老师苏勃有主意,他说这不行,要去找他们。为这张照片,苏老师真跑到几十公里之外的县城去了。照相馆也很意外,说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本来他们想糊弄一下算了,没想到这拨人不好糊弄,就说,这样吧,给你们重照一张吧。苏老师很为难,说县城太远不方便。照相馆说,还有一个办法。苏老师问什么办法?照相馆说再修一修。苏老师就把那一沓照片留下了。
过了一些时日,照片寄来了。大家一看都忍俊不禁,每人的眼睛成了一对“玻璃球”。原来,照相馆说的“再修一修”,竟是给每人补画两只眼睛。不能不承认,照相馆为这两只眼睛下了大功夫,描画得十分用心,几近乱真,但那毕竟是描画,质感压根儿是两码事。看上去实在太滑稽了。没办法,只得重照。
1968年10月16日,苏老师率我们走出校园,在一座医院的门口留下这张合影。我们校园挺美的,石墙红瓦,绿树成荫,不知什么原因苏老师舍近求远要跑出来,至今还是个谜。
几十年后的一天,照片上有个人跑到乌鲁木齐来了。他叫矫恒田。曾当过乳山市劳动局副局长,他退休后有两样东西一直没撂下,一是写字,一是打拳。多年不改,痴痴相守。这叫我非常敬重。他不仅仅是练着玩,还果真练出了名堂。在全国太极拳大赛中,他获得中老年组冠军。此次去俄罗斯旅游就是大赛的奖励。
在饭桌上,我提起那张老照片,恒田说他搬了几次家那张照片早就没有了。我说照片上总共二十九个人,我只能叫出十个人的名字,包括苏老师。他说他可能最多叫出几个。我问演穆仁智的那个人叫啥,他说叫宋振波。长得瘦筋巴骨、演狗腿子的那个人呢?叫王庆林。李桂芹她姐叫什么?叫李翠莲。演白毛女B角的是谁?是王宪华。恒田的回忆使那张老照片慢慢鲜活起来。
我突然想起宣传队个头最高的那个人,是演黄世仁的。问叫什么,恒田想不起来了。问杨白劳是谁演的,他也说不出名字。剩下一半压根儿连姓什么都没有印象了。看来岁月挡住了许多东西。
通过闲聊,我得知部分老同学的一些近况。李振丑当过文化馆馆长,还当过吕剧团团长,几年前退休了。矫红当过报纸总编,李桂芹任中学英语老师,宫照海当过副镇长,郑法亭是律师,李振江是金矿老总……跑得最远的就是于国庆和我了。她在韶关当老师,我在新疆什么都干过,成了“万金油”。有一年我去广州参加笔会,途经韶关时曾特意下车去看望于国庆,她变的我几乎认不出来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是的,照片保留了我们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它只能定格在那个永远无法重现的瞬间了。尽管内心是多么不情愿,但这毕竟是事实。如今,他们中很多人退休了,有的不在了。恒田有个想法,说等都退下来以后,原班人马再凑到一起,搞一个业余吕剧团。问我好不好,我不忍泼冷水,嘴上说好,心想难了。
回忆往事,感慨多多。昨日年少,转眼老矣。记忆里除了影影绰绰留下一些人和事,不知还剩下什么?
栏目责编:方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