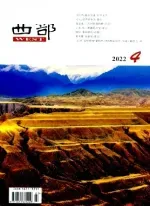灯的精神分析
王凌云
灯的精神分析
王凌云
一
“灯照亮了黑暗”——这句话既描述了灯的实用功能,同时也是一个象征性的隐喻。无论灯所照亮的是房间还是黑暗中的道路,无论灯所提供的是实际的还是象征性的光明,我们都与灯同在。这一“同在”包含着比实用性和象征性更为深广和完整的生命经验。实际上,灯的实用和象征性质都有其更深的本源:在某种意义上,它们都只是从灯与我们生命的共属关系的多重维度中截取了一重维度。
在这个演讲中,我试图恢复我们对灯的经验的完整性,亦即重新思考“灯”与世界图景、与我们的生命空间和精神品质之间的多重关联。在大多数的哲学思考中,我们对概念的专注压倒了我们对事物的热情,这使得哲学经常被理解为一种枯燥抽象的概念分析和理智推演活动。然而,在这样一种哲学方式之外,仍然存在着另一种哲学:这就是事物的哲学、形象的哲学。这种哲学将注意力和解释的热情倾注在具体事物之上,它试图理解事物与我们生命的关联,理解事物在历史性的生活空间中的位置,理解寓居于事物之中的精神和神秘。这种哲学并不反对概念,但它对概念的运用服从并服务于对真实生命经验的描述。
二
“灯”在我们心目中唤起了一个事物或形象,但这个事物此刻也在我们的头顶闪耀。我们此刻正处在一间大学教室之中,头顶这几盏灯在夜晚的黑暗中打开和照亮了这个空间,并指引出一个教学的共同体,一个由观看、说话和倾听活动组成的共同体。灯的数量、品种和样式,都从属于这间教室,它与教室里的其它器具形成了配套。而教室的器具配置从属于教室的建筑样式,每一栋教学楼的建筑样式又从属于整个建筑规划,建筑规划取决于大学自身的办学要求,而办学要求作为大学的意志,最终指向的是大学共同体的整体生活。是“我们”——大学共同体的生活在要求这个空间配置这样的灯。因此,我们头顶的这几盏灯,与我们、与由我们构成的大学共同体是不能分离的,它们指引出一个大学的空间,并在大学空间中才获得了它们此刻的位置和意义。
另一方面,这些灯无论从自身的样式、功能还是从配套设施来说,都从属于一整套现代技术的系统。灯所依赖的电力来自城市的供电系统;灯的制作所需要的金属加工、玻璃工艺、零件组装和焊接,每一道工序都有其自身的工业系统;同时,供电的技术原理和灯的制作、安装原理,都有赖于整个现代世界中取得的科学成果。这一切,无不显示出这些灯的现代特征。灯所指引出的大学空间,是一个现代世界中的大学空间,这一空间与现代技术有着完全不能分离的紧密关系。
因此,从表面上看,我们头顶的这几盏灯只是我们局部生活中的手段或器具;但如果我们看得更深更远,我们会发现,它们事实上指引出了一个历史性的生活世界,亦即现代技术支配下的大学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灯一方面照亮了一些东西,另一方面也遮蔽和让我们遗忘了一些更重要的东西。今天在这样的灯光下,我们要进行一种尝试,也就是超越给定的历史空间限制,重新言说另一些灯,并唤起我们对另一些时代的生命空间的记忆。
三
灯是一种器具,而器具有其历史性的意蕴。以往时代的灯是手工制作出来的(只要想想扎灯笼的过程),在每一盏灯上都包含着手的纹理和印迹;而现代世界中的灯则是机器生产出来的,手从灯的制造过程中退隐。那些古老的灯火,总是唤起一种亲密感,仿佛我们可以与灯进行交流,例如,那些江边的渔火总是让人油然而生思乡之情;而现代世界中的灯,大多数高高地吊在我们的头顶,闪烁着冷漠的光,我们和灯之间已经没那么亲近。现代技术方便着我们的生活,但同时又使得一切事物和器具失去了与我们生命的那种亲身性的关联。我们都知道,在希腊神话中,火是技艺之象。灯可以被看成是火的特定形态,灯的历史变迁暗示出技艺本身的历史变迁——这是一个从古代技艺变成现代技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灯中之火,从那种质朴的、由浸油的棉线所燃起的灯芯之火,变成了依赖于电线网络和供电系统的电流之火。灯芯之火照出的是一个有限的、有着浓重阴影和黑暗边缘的小片空间,而电灯之光则将空间完全充满,其中的阴影和黑暗几乎被我们彻底忽略。
在灯的历史变迁中,世界图景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对空间、对世界的经验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典型的例证是我们对夜晚经验方式的变化。在我小时候的经验中,夜晚是在油灯的光亮中显现的,浓重的黑暗像密密麻麻的黑色鸟群围着桌上或窗台上的灯火,我们吸进黑暗,又呼出被光照亮的热气。夜里,家族中的大人们往往会聚在堂前,围成一桌来谈论白天发生的事情,我坐在角落的小板凳上一边看着他们在跳动的灯火中映现的脸庞,一边听着那些我半懂不懂的故事。我强烈地感觉到这就是我的亲人们,那些冒着热气的话语有点像烟,争论的时候又像是噼啪作响的火星。我感到疲倦了,就回房睡觉,半睡半醒的时候,我经常会看到床边的油灯下母亲或奶奶在织着毛衣或缝制鞋垫。久而久之,油灯就成了一位守护者,成为了母亲或奶奶的替代。那时,人们的生命节律是自然的:白天是白天,夜晚是夜晚,该睡觉的时候就睡觉,该醒来的时候就醒来。几乎没有人会熬夜,这并不只是灯油较贵的缘故,而是因为,人们与夜晚的亲近关联使他们听命于自身的生命节律。
在我们的时代,夜晚是在电灯的光中显现的,或者不如说是被驱散和消灭了。在日光灯的强光下,没有了黑暗和神秘,也冲淡了人与人之间进行深层交流的渴望。在日光灯下,每个人的脸都那么浅表和不真实,因为它已经失去了那在晃动的火光中映现的鲜活的红晕和深影。在日光灯下,人们也很难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或争论(因为夜间的交谈需要黑暗和阴影的推动,来深入到沉默之中),在一起能做的事情似乎只是看电视或打麻将。日光灯的“日光”两字表明了它对太阳的模拟,因此,日光灯的存在,是要制造出一个虚拟的白天。现代人的生命节奏往往因为电灯而昼夜颠倒,许多人像蛾子一样只在夜晚变得兴奋。这种昼与夜、醒觉与睡眠的结构性的颠倒,已经成为了现代人的生命和世界中的基本经验。
四
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理解灯与生命空间的关系。在灯的古典形态中,除了在家的空间中点亮的油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便是在庙宇中燃起的香灯或神灯。正如宗教学家伊利亚德在《神圣的存在》中所言,庙宇是宇宙的浓缩,它是宇宙的原点,是时间和空间开始的地方。庙宇所代表的神圣时空,是人世得以存在、得以获得其意义的基础,因为人是通过对神圣的领会而成为人的。神圣构成了人世的纵深维度,它使一个民族从偶然性的风暴中获得了庇护,从盲目和混乱中获得了方向。庙宇中供奉的香灯和香火,在其火焰与青烟的上升中,将人的心灵牵引到神明所在的高处。香灯或神灯是人对神的奉献,当它燃起,一颗灵魂就将自己置于神明的眼前,无论是忏悔还是祈祷,这颗灵魂都以跳动的火焰来表示自身的虔敬。被灯所照亮的庙宇,由此向内收敛,成为灵魂自身中被神光照亮的内在空间。
家中的灯则打开了一个与庙宇完全不同的空间。这是一个温暖、安宁的亲密空间。一位农夫从夜晚的田野往回赶路,当他看到从自家窗纸透出的、如同柔软丝茧的灯光,他一定感受到了包裹在里头的温暖。那灯火仿佛是在召唤他,让他从外部世界的混乱和荒蛮中返回。他走进屋里,看到妻子在灯下缝补衣裳,还一边给快要睡着的儿女们讲着故事,有些小家伙们已经开始在灯下做梦。灯光照出了妻子和儿女们的脸,这些脸闪现在火光中也像是一些美丽的火焰。尽管灯火并不像炉火那样散发强大的热量,聚拢和温暖整个家,但它所起的作用与炉火接近。比起火炉,灯似乎更能使儿童和少年进入梦和遐想之中。在油灯昏黄的光下做着梦的少年,他可能是梦见了自己在树林中迷了路或被妖怪追逐。他在噩梦中大叫着醒来,看到了身边熟悉的父亲或母亲的脸。
在以往的世代,人们有时也会在油灯下独处,读书、写作,或者借着黑暗中的火光和火光中的黑暗来回忆往昔。往昔的形象和轮廓,似乎只适于在这样一种有限、模糊而又微微颤动的光中呈现。如果光亮太广大、太强烈,或者过于稳定,那些藏在过去之河中的事情就不愿意浮出水面。当一个人回忆往昔时,这些事情仿佛是从灯光照亮的区域之外的黑暗中自行到来,在突破光亮边界时引起了轻微的颤动,这颤动也是它们从潜意识的深水中升起时,所引发的一层又一层波纹般的颤动。油灯所照亮的区域,与回忆的意识所投向的区域不断发生着重叠。就这样,回忆之灯与交谈中的灯火一样,唤起了我们深沉的幸福感。
在夜晚的家宅和庙宇之外,是田野,是在黑暗中行路的人们。他们也需要灯,这灯便是提灯。为了抵御田野上的风,提灯必须限制自己,用灯罩把自己围住以保存自身的火焰。凭借这灯光,我们在夜的黑暗中辨认着自身的道路。灯笼或提灯其实构成了人类精神的隐喻。精神也是通过用纪律和规则来约束自己,以保持自身那专注的火焰。在家和庙宇都归于崩坏的时代,我们都行走在风雨如晦的荒野上,只有这坚定而沉稳的火光才给我们指出了真正修远的生命道路。
灯笼是最具有中国特质的一种灯具,它几乎可以用于一切场合:在家宅中,在屋檐下,在客栈中,在酒肆里。灯笼是个小小的悖论,它是纸中包裹的火。灯笼一般具有浑圆美满的形状,有时也被制成微型庙宇的模样,里面储满了神明赐予人间的福分。灯笼的奥秘在于,它用大红的灯笼纸改变了火光的颜色,使得世界的基本情调发生了转换——从黯淡的黄色转变为吉祥的红色。红色是神圣的颜色,也是世俗的颜色,在中国圣与俗是一体的,被融合在灯笼那柔和的暖光中。当节日的灯笼将整个空间映照得通红,我们的生命也进入到“热闹”的状态,这“热闹”并不同于西方狂欢节中血液的“沸腾”。“热闹”是人与人的沟通,如同成串的灯笼彼此映照;但“热闹”仍然有其礼仪的节制,如同灯笼的火焰只在纸中跳动。
这些古典形态的灯火,它们与黑暗处在一种奇特的关系中。灯固然照亮了一部分黑暗,但同时又依存于黑暗。灯只是打开一小片光亮和温暖的区域,却显露出更为深远的黑暗与神秘。这些灯归属于夜晚,它们并不破坏夜晚的静默、模糊和节律。它们并不比月光更亮,因而不会驱散夜的阴影;也并不比星光更暗,因而不会显得过于微弱。人类生命在夜晚中所具有的一切,无论是亲近的话语、遥远的回忆、深沉的睡眠还是清醒的行走,都被这些灯所守护。黑暗始终以一种沉稳的方式潜藏在它们的光中,成为了光的背景和助力。
五
现代人的生命处于极端的忙碌中,他们在夜晚行路时仍是匆忙的。车灯是现代人在夜晚道路上点亮的灯光,而路灯则是由道路自身提供的、与车灯配套的另一种灯。我们可以将车灯视为来自个体的灯,而将路灯视为来自体制或世界系统的灯,这两种灯之间的暧昧关系便是现代黑夜中个体与体制的关系的隐喻。个体打开车灯,并不是为了在黑暗中寻找自己的道路,而是为了更好地看清已经由路灯规定的道路,并严格地按照这条路的要求行驶。那些企图反抗路灯权力、走自己道路的人,他们的车子都开到了阴沟里。路灯因而具有双重性质:它既引诱你,让你在它们先行照出的道路上舒适轻松地行驶;同时它又威胁你,凡是没有被它们照亮的地方都是禁区。
我们可以更仔细地看一看车灯的本质。车灯是快速移动中的灯光,它映现出的是我们偶在的、匆忙的生命。车灯和提灯形成了对照:在提灯所照亮的路途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光亮中的田野,并把每一片光亮和阴影的空间都当成记忆本身的一部分;而在车灯照亮的道路上,其中的一切空间都被手段化,都变得毫无意义。由于车速过快,我们又被封闭在车中,失去了与世界的亲身联系,因此我们通过车灯看到的世界是转瞬即逝的。我们能看到和避开路上的事物,却根本无法记住它们。车灯,作为这种匆忙和无关联状态的标志,是对现代人个体生命的诅咒,它意味着我们永远不可能幸福。正如昆德拉看到的,慢是生命充实自身的方式,是幸福所需要的节奏,是人与事物建立起真实关联的前提。一切匆忙都使得生命变得空虚,因为其中人没有在任何事物上真正地停留,没有和任何事物建立起真实的关联。一切都只是手段,而我们只是生活在事物的表面。
当现代人回到夜晚的家中,他就进入了一个由日光灯支配的空间。多年以前,当我第一次认真观察日光灯时,我就写下了如下文字:
“哪里有灯,哪里就有回忆。”日光灯的存在反驳了巴什拉尔这句话。事实上在日光灯下我几乎失去了回忆的能力,因为日光灯带来的时间和空间是纯粹当下的,它的强光将人包围在现在的牢笼里,从而无法回视往昔。日光灯制造出一个220伏的冒牌白天(“日光”),使人们在夜晚也沉浸于白昼的幻觉之中,通宵达旦地进行着种种群体活动。我注意到日光灯特别青睐群体活动,而在个体独处时它显得过分刺目。日光灯那普照和广大的光芒使众人的集会获得一种力量和热度,并溶化个体的本质进入群体的本质中;而在个体独处时却使其显示出软弱和孤寂,因此总被个体以台灯替换。日光灯在大厅里的闪耀为主人的社交设置着良好的氛围,使之富于理智和中产阶级的风度,并制止着任何越轨和失态。而一到卧室,它便让位于微暗的节能灯或聚光的台灯,使个体能进入非理性的私己空间而不会觉得不自在。是的,日光灯的作用在于用光混合人与人,在于将个体消融于对群体的忘我加入中,在于将白天带进黑夜并剥夺人的黑暗和阴影。我对于日光灯总是心怀恐惧,我的往昔只在夜晚的微光中才向我显现。我从不在日光灯下写作,以避免那些怕受强光照射的事物从我笔下溜走。(《灯的精神分析(2000年)》,载于拙著《词的伦理》,上海书店,2007)
这些文字中的看法我如今仍然坚持。我只想补充一点:日光灯对太阳的模拟,使得黑暗和阴影的力量从夜晚中被驱散,这从微观的层面上印证了韦伯所说的现代世界的“祛魅”特征。神秘的维度从空间中消失了,它也并不能在台灯和微光灯(LED)的微光中重新建立起来。因为微光灯的光是涣散的和过于微弱的,它缺少集中,因而它唤起的不是神秘,而毋宁是凄清和恐怖。台灯虽然接近于油灯,但它的光并非来自真正的火苗,其中并没有任何火焰的上升运动。那跳动的、上升着的火焰才是灵魂的奥秘所在。台灯的光亮是从上方往下方投射,由于台灯罩的限制,它照亮的只是一个(桌面或地面上的)平面的区域;而油灯的光亮则是从火焰的上升中辐射开来,这是一个浑圆的、蛋形的区域。这圆满的形状也是生命本身的形状。在神秘黑暗的温暖包裹中,生命本身才能进行自内而外的孵化,而一切孵化都是等待——我们只能在专注中期待神的来临,像庙宇、像庙宇中的火焰期待风的吹拂。
六
前面我们已经描述了那些历史中较为常见的灯。我们不妨再来比较一下两种较为特殊的、分属于古典形态和现代形态的灯。它们就是灯塔和航空障碍灯。灯塔从本质上说具有古典性质,而航空障碍灯则是完全现代的。两者的性质刚好相反。在古典时代,灯塔的存在是为了解决如下问题:人在黑暗和虚空中如何为自身定位?古典的方式是建立一个稳定的灯塔来将人引向正确的道路。在大海般动荡、偶然和无常的世界上,灯塔的存在意味着某种确实和稳固的东西,它是一种召唤:“来,往我指引的方向走!”但现代世界中的航空障碍灯则是为了解决如下问题:人如何不会侵犯或撞到别人的东西,人如何在周围世界的黑暗中保护自己?航空障碍灯并不给飞机指引方向(这交给了全球定位导航系统),而是为了提供警示:“不要撞到我!”航空障碍灯的存在,是为了保障他人和自我的安全和财产权利。这是一个所有权利都得到清晰界定和划分的世界,每个人都有自身的地盘,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距离。航空障碍灯的存在是现代人生命方式的又一个隐喻。
七
在上面对灯的观看中,我们是处在某种哲学的光照下。哲学之光在以往总是被视为来自至善的光芒,柏拉图在“日喻”和“洞喻”中将“善”比作太阳,而“善”正是哲学之本原。作为对至善的寻求,哲学并不模仿太阳,因为“善”比太阳更是太阳。哲学之光具有一种“永恒白天”的性质,它总是想要清晰地、毫无遮蔽地洞穿一切黑暗,照亮世界和事物的每一细节。然而,在对灯的理解中,哲学却从白天来到了夜晚,它在自身中渗透了某种黑暗。这种受到修正的哲学类似于古老时代的灯光,它是赫拉克利特所说的“被死者点燃的灯”,在照亮一片区域的同时又保持着黑暗和神秘。这里发生了哲学对诗歌的某种接近。正如柏拉图所提示的,在诗与哲学之间有着古老而永恒的争执。但是,我们并不需要解决这一争执,而毋宁是要将这种争执保持在其充分的张力中。我们一方面要从哲学中汲取彻底的、毫不妥协的确定性和洞察力,另一方面也要从诗歌中汲取黑暗和神秘的力量。在哲学与诗的相互渗透中,哲学就成为了夜晚的哲学,它也是事物的哲学和形象的哲学。哲学和诗,应该成为人的两只眼睛,在其各自的观看中构成同一片视力。
从“夜晚的哲学”而来,一切恰当的、在灯光下进行的观看都需要遵循以下步骤:首先,是对灯光中的事物及其阴影的观看,这观看必须耐心、细致,看清其每一个细节;其次,是对光亮和光亮区域外的黑暗的观看,这观看注意的是光亮的有限性,以及光亮边缘的模糊、颤动的地带;继而是对灯本身的观看,灯如同人的自我,它既是光亮(或表象能力)的提供者,又是光亮区域中的一个事物(表象);最后,是对观看本身的限制,不仅因为观看中包含着观念的暴力,而且因为许多重要的东西并不在观看中出现,如果我们在看,它们就永远不会出现。许多时候,并不是灯光,而是黑暗在黑暗中照亮了黑暗。在经历这一切步骤之后,我们需要做的,是闭上眼睛等待,等待那唯一者的到来。
栏目责编:李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