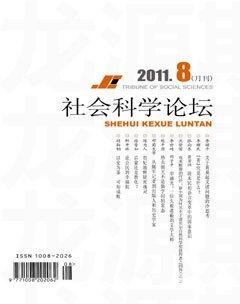台湾新电影研究述
【内容摘要】台湾新电影的理论研究视角非常多样化并且呈现出跨学科、跨文化的特点,主要的视角有历史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电影美学研究、文化研究与批评等。研究者对台湾新电影风潮的发展脉络加以梳理,对新电影的艺术形式与美学特征做了分析,对新电影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探讨。
【关 键 词】台湾新电影研究;史学研究;美学研究;文化研究。
【作者简介】张琼,武汉大学艺术学系2008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东方电影。
台湾新电影是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影坛兴起的一股创作潮流。无论从创作理念还是制片模式来看,台湾新电影对于日后的台湾电影都具有某种“范式”的意义。台湾影坛的一系列举措,如导演中心制的建立、独立制片模式的探索、官方“国片制作辅导金”政策的实施以及“国际影展制片路线”的推行等,均可以说是新电影影响之所及。台湾新电影遂成为台湾电影研究中最受关注的对象。
一、台湾学界的研究
台湾新电影兴起之初便深得焦雄屏、黄建业、陈国富、李幼新、闻天祥等影评人的推崇。他们以《联合报》 《中国时报》等报刊为阵地大力推介新电影的核心导演及作品,因此他们也被冠以“新派影评人”的头衔。“新派影评”主要论述影片的主题、形式技巧以及导演的创作风格,在批评方法上受到了“作者论”的影响。“新派影评”最重要的功能在于以“发言人”的身份阐发台湾新电影的创作理念,推动台湾电影文化的建构。1988年,焦雄屏将“新派影评”结集出版,名为《台湾新电影》。编者以评写史的意图很明确,高度评价了台湾新电影的形式探索,以及影片所寄予的社会责任感与人文关怀,肯定了台湾新电影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及文化价值。其中,詹宏志执笔、五十位台湾新电影创制者、台港两地影评人及文化界人士联名签署发表的《民国七十六年台湾电影宣言》(下称《宣言》)是一篇重要文献。这是台湾新电影的参与者们第一次以集体的声音阐述他们的电影主张。“有创作企图,有艺术倾向,有文化自觉”的“另一种电影”[1]无疑是台湾新电影的一种自我定位。
除“新派影评”之外,还有些批评家着重探究台湾新电影的生成机制以及衰落的原因,旨在总结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杜云之、梁良等学者将新电影的兴衰与台湾电影工业的现状乃至总体发展联系起来,对新电影做出了与“新派影评人”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他们指出新电影题材狭窄、内容不具备典型性、表达方式晦涩难懂,并且认为新电影在商业上的失败致使台湾电影工业不景气,势必将台湾电影引向灭亡。台湾批评界这场“新”“旧”势力的对立和争论,其焦点为电影是以艺术为本还是以商业为本,是文化优先还是娱乐优先。这是80年代台湾新电影研究中引起广泛讨论的理论问题。
90年代以降,台湾新电影研究朝着理论化、学术化的方向发展。理论研究的视角趋于多样化,并呈现出跨学科、跨文化的特点。研究者对台湾新电影的发展历史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梳理。卢非易的《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对新电影时期的政治背景、社会文化心理、电影工业体制和结构等方面都做出了详细的阐述,对新电影的文化纪录功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李天铎的《台湾电影、社会与历史》深入论述了社会历史变迁和社会文化思潮对新电影创作形态的影响,并就新电影在台湾电影史上的地位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两部著作的附录还提供了台湾电影产业研究的珍贵资料,包括历年台产影片数量、影片存目、卖座纪录、发行公司数量、电影院数量以及其他反映台湾电影事业或社会经济变迁的各类数据的统计表。90年代中后期,文化研究日益成为台湾新电影研究的主要视角。美国学者詹明信的《重绘台北新图像》一文开此类风气之先。此后,台湾新电影研究逐渐脱离了电影本体研究的框架,大多以阐释西方文化理论和表达研究者自己的文化、政治主张为目的。新电影中有关殖民记忆、族群矛盾、身份认同等内容是现时台湾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
二、大陆学界的研究
1987年出版的陈飞宝的《台湾电影史话》是大陆最早的台湾电影研究的专著、具有开创性意义,台湾新电影运动是其中一个重要章节。研究者采用传统的电影史的书写方式,探讨了新电影兴起的原因及发展历程,论述了新电影核心导演的创作特色。1989年影片《悲情城市》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后,台湾新电影在大陆学界受到更多的关注。研究者多从叙事主题、文化蕴含、形式风格、审美特质等方面介绍新电影的创作成就。
台湾新电影能引起大陆学者们的兴趣,原因在于这些影片大多具有浸染着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内容和形式。大陆学界探讨台湾新电影与中国传统文化之渊源的研究多有建树。如万传法《在思想、心灵的深处——谈侯孝贤及其电影》一文中探讨侯孝贤电影中合儒道释一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孟洪峰的《侯孝贤风格论》通过分析镜头语言、叙事手法、声音等形式因素来论证中国艺术特性在侯孝贤电影中的传承;李道新的《中国电影文化史》论及台湾新电影的家国母题以及影片对中国古典艺术表现手法的借鉴,借此追溯台湾新电影的文化根源。
由于研究资料的匮乏,再加上两岸长期政治分立与交流阻断形成的隔膜与差异,大陆学者的研究存在着较大的难度。许多研究止于背景资料的介绍和创作概况的描述。总的说来,大陆学者多立足于电影本体研究,注重从审美层面观照台湾新电影,阐发新电影的艺术探索和追求。大陆学者的研究还注重台湾新电影与大陆第五代电影、香港新浪潮电影的平行比较。陈犀禾的《两岸三地新电影中的“中国经验”》分别探讨了台湾新电影、大陆第五代电影、香港新浪潮电影所承载的独特历史文化经验,并且就三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政治的不同态度及其成因做了深入的比较研究。
三、台湾新电影研究中的主要论题
1.概念的界定。“台湾新电影”这一名称出自于小野为影片《光阴的故事》(1982年)所写的宣传企划书。由于该影片的四个导演都是第一次拍摄电影,因此,小野将“新电影人拍的新电影”作为宣传语。之后,焦雄屏等影评人用“新电影”来代称当时影坛一批新晋导演的创作潮,并且指出台湾新电影是一个类同于法国新浪潮运动的电影风潮。虽然学界沿用了台湾新电影这一概念,但对其所指存在争论和分歧。吴念真、陈坤厚、张毅、李佑宁这些公认的新电影参与者们也对这一概念存有疑虑。
首先,由于新电影兴起时并未发表统一的、明确的美学纲领,在划分新锐导演和新电影阵营的依据这一问题上始终缺乏明晰的理论阐述。新电影更多的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学界起初有两种意见:一种特指自1982年《光阴的故事》问世至1987年《宣言》发表期间新生代导演的创作,另一种则泛指1982年以降所有新生代导演的创作。最终学界在此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台湾新电影成为台湾电影史上一个特定发展阶段(1982-1987年)的指称。
其次,“新派影评”所阐发的新电影的新特质遭到质疑。李天铎指出比《光阴的故事》略早的、林清介导演的“学生电影”与新电影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成长主题、写实倾向、现实批判等。他将新电影作为一个文化现象、考察其生成机制中的各因素,提出“新电影的乡土写实风潮并非是一个有自主意识与整个美学观的运动,而是党国机器属下的经管群体在面临困局下,进用新创作群体所做的一种妥协性尝试”的观点[2]。李天铎对焦雄屏主编的《台湾新电影》提出了批评,认为该著“完全排除任何质疑异议的言论,以一种‘霸权式的书写,企图为这个风潮在台湾电影发程中做绝对正面的历史定位”[3]。对于新电影以自身实践寻求台湾电影工业体制的改变,他认为效果甚微。持相近观点的还有张世伦,他在《台湾“新电影”论述形构之历史分析(1965-2000)》一文中论述了新电影是如何被建构为一种电影思潮的问题。两位研究者指出了“台湾新电影”概念的掺杂不清以及新电影发生时的偶然性,但较忽略新电影的文本研究,且否定了新电影发展过程中创作与批评的交互影响。
2.新电影兴衰原因的探究。一般认为,台湾新电影得以产生的推动力源自趋于宽松的政治环境,台湾社会70年代的寻根理想及80年代的抗争风潮,以及60-80年代一系列的电影文化建设活动,如推介欧洲艺术电影、开办大学生影展、筹建电影资料馆等。80年代初期在港产片、西片和录像带的夹击下陷入低潮的台湾电影业界急需依靠新鲜的创作来摆脱危机和困境,这种现实环境也为那些刚从海外学成归来的年轻导演们提供了一试身手的机会。《光阴的故事》 《小毕的故事》《儿子的大玩偶》等作品在故事题材、叙事方式、人物类型、演员表演等各方面都因应了观众求新求变的要求,给他们提供了不同于此前琼瑶电影、“社会写实片”的观赏体验。因此,新电影在初兴期受到观众和片商的欢迎。
学界对新电影落潮以及台湾电影工业衰颓的原因抱持着不同看法。1985年台湾电影金马奖评选前后,理论界就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以焦雄屏为代表的一方认为现实商业制作环境的打压和钳制、官方意识形态对新电影创作的干预导致新电影由盛而衰。台湾电影的萎靡不振则是因为电影业界一味以盈利为目的,粗制滥造、跟风抢拍现象严重,从而最终失去了竞争力。以梁良为代表的另一方认为新电影落潮在于其本身内容和形式晦涩难懂、远离大众,而台湾电影的整体性衰落正是由于新电影推行的观念及其创作实践使然。双方的论战围绕电影本体问题展开,但限于问题的提出、缺乏深入的理论辨析,且都带有主观偏见。因此,双方均未能对新电影做出客观的评价。9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电影本体的论争逐渐让位于映演模式、观众策略、电影政策等外部机制方面的研究。
3.新电影的文化阐释。两岸学界都充分肯定了台湾新电影对于研究近百年台湾社会、历史、文化变迁所具有的文献价值。本土意识的觉醒和现代文明的反思是新电影文本意义阐释中最受关注的两大主题。
大陆学者对于本土意识的认知与现实主义、地方色彩等概念相关联,其思想核心是在承认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这一前提下探讨台湾文化的特质。大陆学者在论述新电影的文化意义时立足于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的同源性,论证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关系,强化台湾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一部分的意识。台湾学者则更加重视新电影中呈现出的、较之大陆不同的历史文化经验。新电影时期,台湾学界对于本土意识的理解是与寻根意识交织在一起的,重视“本土经验”从一方面来讲具有西方强势文化主导下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的意味。90年代随着后殖民理论在新电影研究中被广泛运用,台湾学界逐渐从“台湾本位”的立场来阐释本土意识,主张以“本土经验”为基础构建台湾文化的主体性。有些学者在研究中虽然并未否认中华文化对台湾文化的影响,但却割裂了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他们将中华文化视为外来的“异己力量”、置于与荷兰文化、日本文化以及美国文化同等的地位。台湾学界这种带有“去中国化”倾向的论调是非常危险和错误的。
台湾新电影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基本站在现代主义的立场。一方面认同以启蒙主义理性为原则建立起来的对世界和人自身的认知体系,认同以自由、民主、平等、科学为核心的现代价值理念。另一方面则批判现代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诸如金钱至上的标准、道德与信仰的危机,人的异化、人际关系的疏离、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等。在反思现代文明的同时,新电影还对传统文明进行了重新审视。许多研究者都指出新电影在叙事上采取了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的模式。台湾新电影对传统文明的态度同样是矛盾的,既对儒家的道德意识、传统人伦亲情予以了肯定,又对传统中与现代核心价值相悖的观念提出了批评。
4.新电影美学风格的研究。焦雄屏提出台湾新电影与粉饰现实的“健康写实电影”、逃避现实的主流商业电影不同,它“以诚挚的创作态度,以及对现实的关注,成为三十多年来以逃避主义为大宗的电影所未见”[4]。学界普遍认同这一观点,认为台湾新电影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笔触批判现实、反思历史、剖析人性。代表性的如孙慰川的《当代台湾电影(1949-2007)》对台湾电影美学观念的嬗变进行了梳理,指出真实美学观念从“健康写实电影”到新电影历经了由伪到真的转变,并且在新电影中得到进一步深化。
关于新电影的影音风格,研究重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分析新电影的镜头语言、场面调度等形式手段,特别是长镜头的运用及其美学功能,以此阐发新电影的写实风格;二是通过解析新电影反传统、反戏剧的叙事构架来阐发新电影的现代意识;三是探讨新电影在意境、时空创造上对中国传统艺术技法的借鉴和吸收,阐发新电影的民族特质。
5.导演个案研究。台湾新电影研究中,导演个案研究的成果数量最丰,已有不少研究专著或论文集出版问世,如《杨德昌电影研究》 《侯孝贤:台湾新电影的伟大旗手》 《戏恋人生:侯孝贤电影研究》 《台湾电影导演艺术》等。导演个案研究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方面,研究集中在极少数新电影导演及作品上,着力不均。研究者大多以侯孝贤、杨德昌两位为研究对象,较少或鲜有其他新电影导演如陈坤厚、王童、万仁、张毅、陶德辰、曾壮祥、虞堪平、李佑宁等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多偏重作品叙事主题和影音风格的阐释而忽略了导演主体创作机制的研究。研究者对于导演的电影理念、导演技巧和手法等问题尚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
注释:
[1]詹宏志:《民国七十六年台湾电影宣言》,载焦雄屏编著:《台湾新电影》第112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
[2][3]李天铎:《台湾电影、社会与历史》第189、196页,[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1997年版。
[4]焦雄屏:《从电影文化出发》,载焦雄屏编著:《台湾新电影》第16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