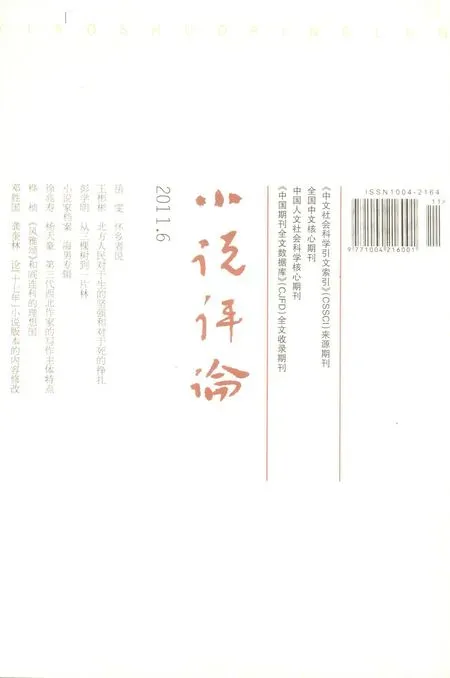当代人生存困境的深度透视——评红柯长篇新作《好人难做》
红柯是当代文坛较为特立独行的作家。之所以这么说,一是因为他漫游天山十年,选择远离尘嚣的生活,完成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天山系列”长篇小说,二是因为他的小说语言技巧极具特色,拓展了当代小说的叙事维度和修辞空间。红柯本是诗人,擅长虚构和抒情,《西去的骑手》、《大河》、《乌尔禾》等小说寄托着他的理想追求。长篇新作《好人难做》则将关注点由富于诗意的新疆天山转向充斥尘世烟火气的渭北小城,由理想回归现实。尽管这一回归并非开始,但显示出红柯在理想与现实剧烈冲突语境下的困惑和迷茫。如果说“天山系列”小说是由天山之镜映照现实,那么《好人难做》就是直观展示现实社会的众生相了。作者通过对各类人物的塑造揭示出当代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危机和在虚构与真实交织碰撞中的生存困境。
小说主要通过叙事和人物塑造营构其艺术空间,故此二者就成为分析小说时的着力点。尽管这样的分析可能老套些,但我相信对于《好人难做》还是适用的。很明显,这部小说的人物群像是有明显喻指的,而其叙事技巧也确有耐人寻味之处。红柯不是一个像路遥那样有史诗情结的作家,《好人难做》也不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全景扫描,但并不失其深刻严肃。
米兰·昆德拉在一次关于小说艺术的谈话中说:“任何时代的所有小说都关注自我之谜。您一旦创造出一个想像的人,一个小说人物,您就自然而然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自我是什么?通过什么可以把握自我?这是小说建立其上的基本问题之一。”①这也是红柯在《好人难做》中思考的基本问题,主要人物王岐生、薛道成、马奋棋就面临自我认同危机问题。这一危机的出现与他们的生存境遇、性格气质等因素紧密相关,是影响其生存状态和生命走向的内因。自我认同问题在任何时代都存在,但在社会转型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这是因为在社会文化语境相对稳定的时代被遮蔽的自我认同问题在社会转型时期凸显出来,自我与他者、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多变。《好人难做》的时间跨度有几十年,断续地写出了王岐生、薛道成、马奋棋等人的成长经历,但落脚点是当下。他们都曾有明确的人生理想并努力为之奋斗,但当代社会急剧的时代变化使他们疲于应付,逐渐迷失了自我。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指出:“自我认同并不是自我所拥有的特质,或一种特质的组合。它是个人根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②自我认同的核心问题是自我同一性,一旦自我同一性被破坏自我认同就会出现危机,集中体现为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冲突与分裂,从而形成自我破碎感。红柯没有采用线性叙事而是片段式叙事并运用大量插叙和补叙或许正是出于呈现人物这种破碎感的需要。
王岐生是小说中极为特别的人物,因为他的想法和行为方式都与众不同。他“从小就怀疑父亲不是他亲父亲”,觉得父亲窝窝囊囊,与下放干部比起来“简直是个丑八怪,比猪八戒还丑”,甚至咒他父亲被牛顶死。③他崇拜的是下放干部、小学和中学老师,因为他们有知识有文化。我们可以将这背后的原因解释为对知识的渴望,甚至是城乡二元结构诱发的进城意识。但这不能解释王岐生考上大学并在城里有了工作后为何仍然不安分。或许我们可以从他母亲身上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正如薛道成在崛山跟王岐生说的“你母亲对你期待很高,一直用她所期待的人来塑造你。”王岐生的母亲年轻时暗恋的对象就是一个小学教师,但由于对方“成分大”而未能与之结合。她后嫁给邻村大队长的侄子,但由于对方的猜忌和陷害而险些被自己的兄弟活埋,幸好被王岐生的外公外婆救下,于是嫁给了王岐生的父亲。王岐生的母亲虽然本分地过日子,但对小学教师所代表的知识分子身份仍心存仰慕,所以当王岐生给她讲起小学教师的事情时还会眼睛发亮。王岐生则从心理上拒绝接受自己是农民的儿子的事实,他“这辈子都在寻找那个梦中的父亲,有时是老师有时是领导,有时是书中人物,有时是伟人。眼前的亲生父亲他视而不见。”他对生父的疏离是基于对理想身份的渴求做出的,是自我认同危机的行为外化。一般人都有对理想身份、地位、人际关系甚至外貌特征的预期,但并不像王岐生那样过激地表现出来。安东尼·吉登斯说:“‘理想自我’是自我认同的核心部分,因为它塑造了使自我认同的叙事得以展开的理想抱负的表达渠道。”④依此观点,可以说王岐生是整部小说中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冲突最剧烈的人物。他的行为不为常人所理解,长期生活在焦虑躁动状态中,最终也未能实现其理想自我。在现实生活中的失落使他对马奋棋的《傻女婿故事集》产生了共鸣,于是全身心投入将其改编为秦腔戏《凉女婿》,并担纲主演。排演一切顺利,但他因为不能接受专家的批评意见而在兰州会演时罢演,戏也就没能获得预期的成功。他对专家怒吼:“我的戏!我的戏!这是我的戏!”这是为什么?还是薛道成看出了门道,他在看过王岐生的表演后说:“这叫寻找自我,完成自我。”所以,“王岐生同志就觉得专家说的不是戏,是他王岐生,是刚刚被薛教授强调过的自我。”他无法接受别人对他这一寻找与完成自我努力的否定。这恰恰表明他到了知天命之年仍然没有从自我认同危机中解脱出来。后来,他从农村收购土鸡贩卖到城里,这种平头百姓的生活使他暂时获得了心理上的安静。如果他就此安顿下来,我们可以说他醒悟了,从理想自我的虚幻梦境中走出来了(小说的确多次写到了他的梦和梦游),回归到现实生活的稳定场域中,明确了自我的定位。但他的困惑并没有就此结束,作者也没有就此止步,而是把对当代人生存困境的思考继续向纵深推进。至此,我们就必须分析下薛道成这个人物。
薛道成是典型的学院知识分子,他的生活环境相对单纯,在生活和事业上都一帆风顺。他与马奋棋、王岐生一样都是凭借知识改变了自身命运。他还是王岐生的大学老师,也曾影响过马奋棋。在他身上似乎不存在自我认同危机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说王岐生的自我认同危机更多地肇因于自身性格气质的话,那么薛道成所面临的困境则主要是由他者造成的。简单说,他本来有明确的人生定位和努力方向,学术研究上有一系列规划,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来自外界的冲击迫使他重新思考学术和人生的大问题。高校已不再是知识分子的象牙塔,也存在各种算计和钻营。近几年一些高校题材的小说就深刻剖析了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其中,张者的《桃李》、邱华栋的《教授》、汤吉夫的《大学纪事》、朱晓琳的《大学之林》、史生荣的《所谓教授》等是较有代表性的。但这些小说更多地批判了知识分子在物欲社会的精神沦丧而对其内心世界的价值冲突尚缺乏深入的挖掘和揭示。红柯对高校生态有直接体认,他没有停留在欲望叙事和道德批判层面,而是试图通过薛道成这一人物探寻知识分子的自救之路。
从专心致志做学问到与同事下棋、打牌,薛道成没有自我封闭,而是想改变自己以融入世俗生活,为此他写下“难得糊涂”挂在书房,将方框眼镜换成圆框的。“这种生活持续了十年,大家都不记得以前的薛教授了。薛教授自己大概也记不得当年的自己了。”但他不得不再次面对“我是谁”这一难以回避的问题,无奈地将“难得糊涂”条幅烧掉。这预示着他与那种沉闷琐屑的世俗生活的诀别,由此踏上寻找自我之路。小说写到,“知识分子的标志之一就是独立意识嘛,有没有人文关怀有没有批判精神并不重要,人格、尊严这个关乎面子的问题才是最要紧的。”这是对知识分子的反讽,其实薛道成在意的恰是独立意识、批判精神。常建、李光仪等投机钻营分子利用薛道成谋取学术资本和现实利益,已丧失了作为知识分子起码的道德操守,就连一向洞察幽微的孟云卿也难以清净自保。知识分子被胁持的尴尬处境由此跃然纸上。但好在薛道成没有放弃对理想自我的追寻。他给学生做关于周文化的讲座时说:“祈子实际上是渴望生命渴望生活,实质是创造”,“《周易》的核心就是创造”,后来也对王岐生说:“我很羡慕文王演《周易》,司马迁写《史记》,那是大发现大创造”。这是他的真实想法,也是他的困惑,反衬出当代知识分子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不足。在小说第九章,薛道成和王岐生二人在崛山相聚的情节是有寓意的,可以看作是二人寻找失落的精神家园的共同归结。薛道成整理古籍、王岐生搜寻古曲隐喻的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回归,回归到一种自然本真、与世无争的状态。正如小说中那位蔫老汉说的谚语所喻示的:得失相倚,勿劳苦求。但这样的处世态度未免消极,而薛道成、王岐生的选择也只是失落后对传统文化逃避式的昄依。这与阎连科在《风雅颂》中的思考颇为相近,只是后者显得更为荒诞,主人公杨科被“变形”成了精神病人。有研究者指出:“阎连科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一样,都身处一种文化危机当中,他们都在寻找新的语言形式,去表达他们所遭遇的危机世界。”⑤写作《好人难做》的红柯与写作《风雅颂》的阎连科一样遭遇了文化危机。如果我们把《好人难做》置于九十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书写历程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它延续了《废都》以来知识分子的出走叙事,摒弃了其欲望叙事。红柯希望能为知识分子找到一个归依之所,哪怕这种努力带有理想化色彩。
小说中有一个有意味的情节:王岐生小时候喜欢说普通话,瘸子的儿子也喜欢说普通话。普通话相对于方言具有文化优势,是知识和身份的表征。他们对普通话的认同体现出的是对知识群体的身份认同。但王岐生的经历表明知识并不能解决全部生存问题。相反,红柯通过瘸子这一底层人物的优良品质肯定了民间美好而朴素的生存伦理。
在一次访谈中,红柯说:“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表达的是作者对世界的看法,你怎么看这个世界。”⑥前述生命个体的自我认同危机是红柯对世界的看法,此外还有虚构与真实的二元对立。
在女儿马萌萌与张万明私奔前,马奋棋的生活看起来是平静安逸的。尽管只当了文化馆的副馆长,他也没有表现得太失态,只说了句“好人难做咱也得做好人”。但女儿的事让他颜面扫地,成了别人的笑柄,他可以选择的只有逃避,而他的逃避方式就是戴上眼镜、穿上风衣。同样,他也因为与女播音员的不正当关系而不敢面对瘸子和他的儿子,但当他给瘸子的儿子买了玩具汽车后就彻底放松了,仿佛这样的物质补偿可以帮助他卸下心理重担。但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虚构,女播音员的死又把他拉回到现实中。虚构被严酷的现实击碎了。不仅如此,马萌萌出事后,马奋棋担心她受不了打击,“他用文学名著以及戏曲中所有被损害的女子形象对女儿进行了极不合理的想象”,但马萌萌凯旋似的表现使他的所有想象显得可笑而多余。虚构在与现实的碰撞中再次失利了,而且那么不堪一击。
马萌萌也遭遇了虚构与现实交织的困境,只是虚构对她而言不是逃避而是主动选择。她之所以抛弃梁局长的儿子转而投入张万明的怀抱,不全然是为张万明的潇洒风度所吸引,而是根源于她心中对爱情的浪漫想象。张万明甚至连名分都给不了她,她还要在婚后与其保持来往。她不像某些爱慕虚荣的女性那样渴求名利,而是跟着感觉走。她不想要那种平淡如水、按部就班的生活。她有几分叛逆性格,但绝不是自觉的女性主义者。但虚构生活毕竟不坚实,当张万明选择退出时,她的美丽梦境就破灭了。
既然虚构无法逃避真实的冲击,那么是否只有无条件地接受呢?不然。周怀彬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行动策略——装傻和戏仿。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因为正是他给了张万明致命一击,重新诠释了虚构与真实的关系。他装作对马张私情一无所知,甚至可以将与老婆幽会的张想象为自己。这看起来不可理喻,但这一策略既保护了自己,又打击了敌人,十分凑效。他还戏仿张万明的装扮和做派,迫使张戴上墨镜、穿上风衣。这比梁局长假扮环卫工人以躲避情人的方式高明多了。因为戏仿混淆了虚构与真实的界限,彻底解构了真实,让人难辨真伪。小说最后写到:“周怀彬能把大活人张万明学得那么逼真,周怀彬就能把马萌萌生下的娃养成他自己的。到了那一天,马奋棋就可以脱下高领风衣,摘下头盔似的大墨镜,恢复原貌”。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这是马奋棋也是当代人不得不面对的尴尬处境。如果说在后现代主义文学和先锋派小说那里戏仿主要是一种叙事方式的话,那么红柯则将其上升为一种生存策略,借助其解构力量实现了对世态人心的批判。
与以上对现实世界的看法相适应,红柯有意运用了反讽、碎片拼贴等元小说的叙事手法,但远没有马原等先锋派小说家运用得那么炫目。红柯已经告别先锋,他明白先锋小说只是一种被动学习,借鉴大于创造。他对元小说技法的运用不是形式大于内容的叙事冒险,而是吸收后的再创造。技法只是手段,思想的传达才是目的。其实,源于西方的元小说也并未停留在对传统文本的解构层面,而是力图通过创新小说表现手法表达作者对世界的看法。有西方研究者认为:“在这种新小说的背后……潜藏着一种真诚的努力。对一种新的真理的寻求。一种试图恢复事物、世界以及人类的适当位置(一种更为纯洁的状态)的真正努力。”⑦《好人难做》的背后就潜藏着红柯这种真诚的努力。
注释:
①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②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9页。
③红柯:《好人难做》,《当代》,2011年第3期。
④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5页。
⑤李永中:《小说写作与自我危机——由〈风雅颂〉谈开去》,《江汉论坛》,2009年第10期。
⑥王德领、红柯:《日常生活的诗意表达——关于红柯近期小说的对话》,《小说界》,2008年第4期。
⑦转引自汉斯·伯顿斯:《后现代世界及其与现代主义的关系》,《走向后现代转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