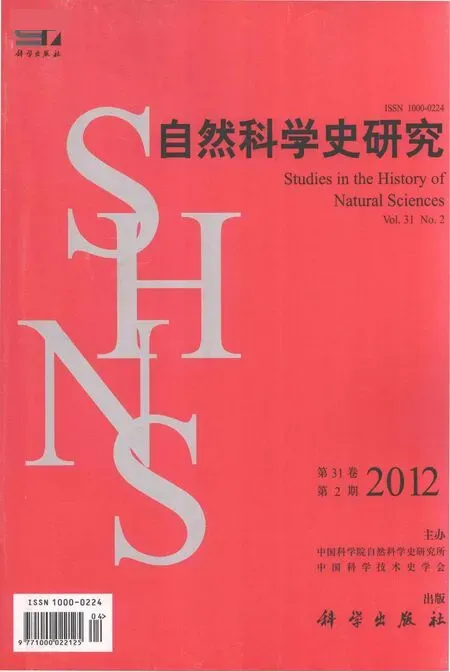新学传播的序曲:艾约瑟、王韬翻译《格致新学提纲》的内容、意义及其影响
邓 亮 韩 琦
(1.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北京100084;2.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新学传播的序曲:艾约瑟、王韬翻译《格致新学提纲》的内容、意义及其影响
邓 亮1韩 琦2
(1.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北京100084;2.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艾约瑟与王韬合译的《格致新学提纲》正续二篇先后于1853年和1858年发表,是晚清最早出现的西方科学史年表,开列哥白尼日心说以降的科学发展大事。本文介绍了《提纲》的内容,考释其中的科技人物,梳理了《提纲》与王韬《西学原始考》的关系,以及对黄钟骏《畴人传四编》的间接影响,认为编译此文的缘由是为了改变中国学者对西学的固有观念,指出它对晚清时期西方科技新知的提倡与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具有先导作用。
《格致新学提纲》《中西通书》 艾约瑟 王韬 《畴人传四编》西方科学史
欧洲天文学知识自明清之际传入中国,徐光启、李天经等人在传教士的协助下编成《崇祯历书》,介绍了以第谷(Tycho Brahe,1546~1601)体系为主的天文学。康熙末年,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Jean-François Foucquet,1665~1741)在《历法问答》中介绍了新的欧洲天文学,特别是法国天文学家新的观测成果,并对第谷学说进行了批判,但书稿只在宫廷流传,并未刊印。康熙年间编成的《钦若历书》(《历象考成》),依然采用第谷的宇宙体系。乾隆七年(1742)编成的《历象考成后编》虽加入了一些新的天文学知识,如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 ~1630)、卡西尼(Giovanni D.Cassini,1625 ~1712)的椭圆运动理论,基于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月亮运动理论基础上的月离表等,但在计算上仍以地球为中心,太阳沿椭圆轨道绕地球旋转[1]。及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蒋友仁(Michael Benoist,1715~1774)进献《坤舆全图》,介绍了哥白尼日心地动说,但影响也局限于宫廷。后钱大昕抄录图中文字,以《地球图说》之名刊印,阮元在书序中对日心说仍嗤之为“离经畔道”,哥白尼学说事实上并未得到广泛接受。而与天文学史或天文学家有关的内容,则散见于传教士编译的天算著作中。比如《历法西传·西古历法》中或详或略地介绍了多禄某(即托勒密 Ptolemy,100~170)、第谷、加利勒阿(即伽利略 Galileo Galilei,1564~1642)等人的事迹与著作,以表达西方天文学渊源有自,所谓“要皆师传曹习,确有根据者也”[2]、“历数千年,经数百手而成,非徒凭一人一时之臆见,贸贸为之者,日久弥精,后出者益奇,要不越多禄某范围也。”([2],14b)中国学者对传入的西方天算学者相关知识的收集与整理工作,直到1799年阮元主持编撰《畴人传》才得以实现,然而编者持有西学中源论,并对个别西方古代天文算学家的存在持怀疑态度①比如依巴谷条,阮元在评论中称“《月离历指》卷一谓依巴谷在周显王时,其第二卷又言依巴各在汉武帝元朔时,前后矛盾,不可究诘。然则彼所谓周时人、秦时人者,安知不皆乌有子虚之类耶?”。
自18世纪中叶以后,中西科技知识的交流陷入停顿,而西方科学却获得巨大进步,哥白尼日心说的地位已经确立,新天体的陆续发现使得有关太阳系结构的观念有了改变,光学、电磁学等新学科已多有进展。19世纪初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为利于宗教传播,必须考虑如何利用新知识打动中国人,并消除他们相对陈旧的西学知识和错误的西学观。新教传教士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通过书刊或教育等方式传播知识,希望藉此改变中国人的观念,而西方科学技术正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传播福音,传教士很清醒地认识到应该借助科技知识。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在《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中提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编辑缘由时就强调,此刊的宗旨即是结合宗教、道德以传播知识;明确提出宗教传播为首要目标,但也不会忽视其他次要事务;知识与科学是宗教的侍女,可能成为道德的辅助工具。[3]又如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 ~1851)在谈到《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编辑旨意时表明,希望通过介绍西方的工艺、科学和准则,消除中国人高傲和排外的观念,以此证明西方人并非蛮夷,并让中国人明白自己依然有许多东西要学习。[4]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例,其中有十余篇有关天文学的文章,涉及日心说、行星、卫星、日月食等方面的内容,而米怜自己也坦承,介绍这些通俗的西方知识,更多地是为了与中国人的传统天文学知识即“关于神与宇宙的错误观念”对抗。[5]同样地,有关地理的文章以及地图的刊印,也是为了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世界观。不惟如此,传教士编撰科学知识类文章,也时常加入宗教的解读。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论述星体及运行时称,“欲知上帝之全能明智,推天文之学,以算学度星之相距,日月地之转轮,朔弦节气交宫,制测量仪器”[6],并将行星及其运动均归结于上帝的创造。
随着通商口岸开放,传教士也获得相应的自由传教的权利。在西学传播方面,传教士在各通商口岸翻译出版了不少科技著作。此外还有多种连续出版物,包含诸多科技内容。这些论著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比19世纪早期有较大进步。究其原因,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于具有深厚学术素养的中国文人的参与。对于传教士早期出版物的质量,米怜自己也承认,《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行文和印刷上均很不完善,并期望在中文水平提升后再加以改善。[3]而协助其办刊的梁发,则仅受过四年的私塾教育。反观墨海书馆时期,协助传教士译书的中国学者,李善兰已是著名的数学大家,而王韬、蒋敦复、张文虎、管嗣复等无不是学术根底深厚的学者。
晚清西学传播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改变,西方天文学知识的介绍也随之改变。除了介绍某一主题的单篇短文或系统全面的专著外,也有记述西方天文学发展史的论著,比如王韬与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合译的《格致新学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王韬和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合译的《西国天学源流》、包尔腾(John Shaw Burdon,1826~1907)《星学源流》、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天学绪言》等。这些著述以哥白尼日心说为出发点,描述了不同时期西方天文学发展史,对于传播西方天文学新知、改变中国学者旧观念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其中,《提纲》分载于1853年与1858年的《中西通书》(Chinese and Foreign Concord Almanac)中,是第一部介绍西方科学发展的大事记,主要描述了西方16世纪以来的天文算学发展史,对于晚清西方科技史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影响了晚清学者对欧洲天文学的认识。因《提纲》最初刊本已极为罕见,仅欧洲个别图书馆(如牛津大学)有藏,很少有学者深入论及。故本文拟讨论此文的内容、意义,并以黄钟骏《畴人传四编》为例,探讨欧洲科学史知识在晚清学者中的流传。
1 《格致新学提纲》内容简介
1853年《提纲》的记载起自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截至道光二十八年(1848),简要地介绍了欧洲近三百年来的科技发展史,尤其是天文学发展的大事件。此文以中国帝王年号为序,按年排列。全文共87条,涉及53位科学家。除了16条涉及光学、力学、电学等学科外,绝大部分条目均与天文学、数学有关。其中哥白尼至牛顿之间的科学家共24位,牛顿之后的科学家共29位。[7]在这53位科学家中,牛顿以前的科学家有12位,已通过耶稣会传教士介绍到中国,并收录于阮元《畴人传》,因此这些人名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耶稣会士的译名或稍作改动,如歌白泥(即哥白尼)、奈端(即牛顿)、刻白尔(即开普勒)、巴理知思(Henry Briggs,1561~1630)、葛西尼(即卡西尼)、弟谷(即第谷)、加离略(即伽利略)等。另外,在《提纲》之前,新教传教士在南洋、广州、澳门等地曾刊载过一些有关天文学的论文,提及一些新的天文学家及其贡献,但从总体上说,牛顿之后的41位科学家及其主要成就,多为第一次在中国介绍,可见此文对于西方天文学(尤其是牛顿以来的天文学)的介绍具有重要意义。
1858年的《提纲》续篇,是对1853年版本的补充。此文不再使用中国帝王年号,而是改用西历年月,译者对此有明确说明,称“此卷内纪年俱用耶稣年,不改用中国者,因中西月日不合,且查彗星簿有在中国去岁见者,今俱在本年,故不改年号。”[8]此文共22条,其中1条涉及光学,1条涉及电学,其余均与天文学相关,且有18条是19世纪30年代以来的天文学新进展,尤其是小行星的发现,时间上延至1857年。共涉及19位科学家,新增者12位。具体内容及人物的初步考证,参见附录。
对于牛顿以前的科学发展,尽管耶稣会士已经零散介绍过一些,然而相关著作以历法计算相关知识为主,对科学家与科学发现不免有所忽略,《畴人传》的取材也由此受限。相比之下,《提纲》的记述更为丰富。以牛顿为例,18世纪前,仅《历象考成后编》中间接反映了其岁实测量、月球理论上的成就[9],因此《畴人传》为其立传时亦完全依据于此[10],而对他的其他重要科学成就一无所知。《提纲》对牛顿的介绍则要丰富得多。比如“康熙三年(1664),奈端初论微分法。此法及积分法为最深算术,凡借根天元等法不可推者,用此则可”;“康熙五年(1666),奈端初知天上地下万物皆有相引之理,是以重物向地心下坠,与月环地球之理同”;“康熙八年(1669),奈端作分光法,白光入三角玻璃分为七色,再加一三角玻璃,仍合为白光”;“康熙十一年(1672),奈端初作回光显微镜”;“康熙二十六年(1687),奈端著《格物原本》,中言日月星小环于大之理,所行之路,或椭圆,或单曲线,或双曲线,诸行星及地球月俱行椭圆,客星、彗星俱行单曲线与双曲线,重物向地心下坠,与太阴自东而西行,一理贯通也”;“四十三年(1704),奈端著《视学》,论回光角与原角等”。([7],34b~35a)这些记载较为清楚地介绍了牛顿发明微积分、发现万有引力、色散、制造望远镜等重大科学事件,几乎囊括了牛顿所有重要的科学活动,可以勾勒出牛顿简洁的生平事迹。
又如《畴人传》中未予立传的伽利略,实际上在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的著作中已经对其科学成就有所介绍。比如在《历法西传》中称“第谷没后,望远镜出,天象微渺尽著,于是有加利勒阿于三十年前,创有新图,发千古星学之所未发,著书一部”([2],12a);《灵台仪象志》中称“今先论纵径之力,以定横径所承之力。西士嘉理勒之法曰,观于金银铜铁等垂线,系起若干斤重,渐次加分两,至本线不能当而断”[11];《五纬历指》谓“加利娄曰,凡大光照某体,能发光之类,其所发之次光非全受本体之色,而变为他色”[12]等。《提纲》有四条相关介绍:“万历十九年(1591),以大利加离略著《重学》,始明一斤重与十斤重下坠同迟速落地之理”;“万历三十八年(1610),加离略既造远镜,始见木星旁有小月,始见水星有四附星。明年又见金星有晦朔弦望,一如太阴,又见土星有两耳,又见太阴之体有高低凸凹之形”;“万历四十三年(1615),伽离略用木星附星掩食定东西里差”;“崇祯五年(1632),伽离略专论天静地动,坐此下狱,强使反其说,乃出之”。([7],33b~34a)扼要地介绍了伽利略的主要科学贡献,如自由落体运动、重力加速度,利用望远镜进行天文观测,并提及了他因为坚持日心说而下狱,并被迫改变其观点才得以出狱等,较之明清之际的介绍更加准确。但是对其因坚守哥白尼学说而受到教会惩罚一事,艾约瑟在此只是含混一说,并未直接道出罗马教廷在其间的角色,应是出于维护宗教形象的考虑。
除了更为详细、准确地介绍牛顿以前的天文学发展外,《提纲》大部分篇幅记述了18世纪后期以来的天文学新成就。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是近代天文学的大发展时期,由于观测仪器精度的提升,天体测量学得到了极大发展,新天体的发现扩大了太阳系范围,恒星观测研究开创了恒星天文学,新的数学方法的引入而逐渐形成天体力学等等。《提纲》对这一迅速发展过程中的标志性人物与事件均有较为确切的记载。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内容,当属有关天王星、海王星和小行星等新天体的介绍。对于天王星,《提纲》中有两条记载。其中一条称“乾隆四十六年(1781),英国天文大臣侯失勒(即威廉·赫歇尔)初见土星之外有一行星,名之曰於士,译即天王星”([7],35b),准确地介绍了1781年威廉·赫歇尔(William Herschel,1738~1822)发现天王星一事。尽管在此之前,已有多种著述介绍过天王星发现一事,但是“侯失勒”、“天王星”的译名则是首次出现,并随之为王韬与伟烈亚力合译的《西国天学源流》、李善兰和伟烈亚力合译的《谈天》所采用。“天王星”一词沿用至今。此外,还有一条称威廉·赫歇尔于1807年观测到天王星有6颗卫星,则不甚准确。实际上至1851年,已确认的天王星卫星共有4颗,其中包括威廉·赫歇尔所发现中的2颗,并由约翰·赫歇尔(John Herschel,1791~1871)为之命名。由此可见,艾约瑟翻译《提纲》时,尚未了解到这一新的进展。同样地,对于海王星的介绍,也存在类似的现象。《提纲》中有三条海王星的相关纪录,称1846年法国勒维耶(Urbain Le Verrier,1811 ~1877)和英国亚当斯(John Couch Adams,1819 ~1892)分别用算术方法推算出天王星外有一颗行星,并最终于通过远镜观测得以证实,且提及1847年有人观测到海王星有两颗卫星与光带等尚待证实的新消息。但是其中却有一点错误,即是亚当斯于1843年就作出了预测,而非此文所称1846年。除了天王星和海王星这两颗大行星外,从19世纪初开始,西方天文学家还陆续发现大量小行星。1801年至1848年间只发现了9颗小行星,1853年版《提纲》对它们的发现者与发现时间都有正确的介绍,即谷女、武女、天后、火女、严女、穉女、虹神、猎师,并且在1858年版《提纲》中继续介绍了1849年至1857年间新发现的小行星,增至50颗,准确反映了小行星发现的最新进展。
天文学之所以能不断取得重大突破,与天文仪器的改进密不可分,这些革新同样在《提纲》中有不少体现。比如“伽离略造远镜,初见水星有四附星”;“英国格勒哥里(James Gregory,1638~1675)新作回光远镜”;“海特里(John Hadley,1682 ~1744)造纪限镜仪,以测太阳高弧”;“道伦德(John Dollond,1706~1761)造无晕远镜”;“侯失勒名威灵(即威廉·赫歇尔)造极大远镜,测见土星又有两附星”;“英国罗斯伯(Lord William Parsons Rosse,1800~1867)造反照光千里观星镜,长为五十三英尺”等[7]。事实上,早在明清之际,望远镜相关知识已经传入中国,比如德国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曾于1622年携带望远镜入华,且翻译《远镜说》介绍伽利略利用望远镜观测所得的天文发现。清代宫廷、民间亦屡有制造,如苏州人孙云球曾仿制远镜[13],但其时所传入的望远镜以折射式望远镜为主。威廉·赫歇尔等人创制反射式望远镜,进而在行星、卫星、恒星、双星、星云等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新的天文发现等事,则多是通过此文首次在中国得以介绍。
18世纪以来,天文学之所以取得迅速发展,与同一时期经典天体力学的发展密不可分。经典天体力学是在天体测量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其主要研究对象是天体的运动和形状,发轫于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奠基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形成于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1749~1827)的《天体力学》,发展于19世纪中叶。《提纲》中对这一领域的科学家及其成果亦有介绍。比如数学家欧拉(Leonhard Euler,1707~1783)在天体摄动、积分法等方面的成果,拉普拉斯对海潮成因、月球轨道的研究以及其著作《天体力学》,拉格朗日(Joseph Louis Lagrange,1736~1813)之解析力学,以及19世纪勒维耶、亚当斯推算海王星等等。
除了天文学、数学方面的科学事件外,《提纲》也对光学、电磁学、力学、热学等物理学分支学科的重要人物及科学贡献有所涉猎。光学方面,介绍了玻尔塔(Giovanni Battista della Porta,1535 ~1615)暗箱成像法;茅鹿理哥(Franciscus Maurolicus,1494 ~1575)研究人眼成像原理而制造远视眼镜与近视眼镜;牛顿分光法;赫歇尔研究太阳光气有热气、光气、化物气之别;艾里(George Airy,1801~1892)光的波动学说;阿拉果(François Arago,1786~1853)制造分光镜等。力学方面,介绍了伽利略有关重力加速度的力学知识;斯蒂文(Simon Stevin,1548~1620)对分力、合力的研究;托里拆利(Evangelista Torricelli,1608~1647)制造称量空气的仪器;盖里克(Otto von Guericke,1602~1686)制造真空泵;惠更斯发明钟摆之理等。电磁学方面,介绍了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1540~1605)著《磁石论》;富兰格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始明琥珀气与电气相同;奥斯特(Hans Christian Örsted,1777 ~1851)发明磁石与电气异同之理;法拉第(Michael Faraday,1791~1867)的磁力线理论。热学方面,介绍了布莱克(Joseph Black,1728~1799)发现物体相变时的“潜热”现象。除了具体的学科发展外,《提纲》还介绍了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的科学方法:“英国备根著《格物穷理新法》,实事求是,必考物以合理,不造理以合物。”([7],34a)所谓《格物穷理新法》即《新工具》,“必考物以合理,不造理以合物”即是科学归纳法。
2 《格致新学提纲》的流传与影响
《中西通书》是一种历书性质的刊物,具有时效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流传至今,已很少有图书馆藏有全帙[14],影响了《提纲》的流传。
1871年,《教会新报》上再次发表了一份《提纲》,署名“北京牧师英国人艾约瑟”。就内容来看,此文实为1853年版《提纲》,不过有所改动。绝大部分改动出现在国别、人名、术语等方面。比如将原本中“咈兰西”、“以大利”、“米利坚”等国名分别改为“法兰西”、“意大利”、“美理驾”等,将1853年本中“初”、“始”二字对换,将表示万有引力的“相引”、“相牵引”改为“相摄引”,将人名“白拉里”改为“白拉德里”等。除了在文字上的改动外,二者在文义上也有一处更改,即关于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描述,1853年本称“奈端著《格物原本》,中言日月星小环于大之理,所行之路,或椭圆,或单曲线,或双曲线,诸行星及地球月俱行椭圆,客星、彗星俱行单曲线与双曲线,重物向地心下坠,与太阴自东而西行,一理贯通也”,而在《教会新报》本中则改正为“自西而东行”。[15]
除了艾约瑟的重新发表外,王韬也对此保持了长期的关注,并在《提纲》的基础上,不断搜罗、增补新的内容,于1890年编辑出版了《西学原始考》,收录于《西学辑存》六种之中。对此,王韬在《西学原始考》序言中明确表述道“韬于咸丰癸丑、戊午两年,偕西士艾君约瑟译《提纲》,凡象纬、历数、格致、机器,有测得新理,或能出精意,创造一物者,必追纪其始,既成一卷,分附于《中西通书》之后,今俱散佚,无从搜觅。因于铅椠之暇,复为编辑,篇帙遂多,爰之剞劂。”[16]正是由王韬这段文字,得以确认《提纲》的翻译情况。
尽管王韬称《中西通书》全部散佚,因此重新编辑,然而将两者相应部分作一对比,则可以很清楚地见到:《西学原始考》有关1543年之后的内容,绝大部分来自1853年版《提纲》,但没有收录1858年的增补;在对应条目的具体内容上,除了极少删改外,基本上是一字不易;纪年方式有所改变,不用中国帝王年号,而改用耶稣纪年,与1858年版《提纲》一致。由此可以断定,王韬在编辑《西学原始考》时,手边一定有1853年《提纲》的底本,而1858年新增部分则已散佚。
相对于《提纲》主要介绍1543年以来的天文算学发展大事而言,《西学原始考》的内容大约扩充了一倍。就时间而言,上起公元前2400余年,下至1874年,远远超过《提纲》所记载的1543年后约400年时间。就内容而言,虽然此书并非单纯的科技发展编年,但无疑依然以科技知识的发展为重点,而且几乎涉及所有科技门类,如化学、物理、矿冶、铁路、电报、科技交流等各个领域,可谓是一部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世界科技文明发展简史。比如对于阿拉伯文明的介绍,《西学原始考》中较详细地记载了它从起源到强大的过程,以及其对古希腊文明的继承等。对于东西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此书也有许多记载,包括贸易往来、农作物等方面。如约在公元前970余年,即中国周昭王时,犹太人通过海路经由红海赴印度贸易,开辟东西通商之路。公元前29年,即汉成帝建始四年,罗马与印度通商,始购蚕丝,丝绸自此进入欧洲。王韬对丝绸西传还加以按语解释,称蚕丝之由东而西,实际上在春秋末年时,因为希腊人与中东地区的亚述等国贸易,见到其地的官绅、富商身皆衣绸,便求购效仿。对于农作物的交流,包括551年,东罗马始得中国蚕种;1545年,葡萄牙从中国携回橘树等。同样地,《西学原始考》也对科技知识的交流有不少记载,如公元前六百年,“埃及人始至希腊传历算之学,此为天算自东徂西之始”,“787年,唐德宗贞元三年,阿喇伯国势强大,西自大西洋,东至印度江,南自地中海,北至阿兰海,至是讲求文学,始令博士尽译希腊天算格致之书,以教其民”;“1306年,元成宗大德十年,法兰西人始以阿喇伯字码施于笔算”[16]等。
王韬《西学原始考》中的天文算学内容,后来成为《畴人传四编》“西洋附”的重要来源。《畴人传四编》由黄钟骏父子编辑,光绪二十四年(1898)成书。根据“西洋附”中每位传主后所记载的信息来源,共有《西学原始考》、《西国天学源流》、《谈天》、《几何原本》、《代微积拾级》、《微积溯源》等21种著作。《四编》共收录了157位外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其中88位传主的信息摘自《西学原始考》,而其中又有35位实际来自《提纲》。由此可见,《提纲》的大部分天算学家通过《畴人传四编》中得以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畴人传四编》中的传主信息绝大部分是照录《西学原始考》,但也有少量更正,同时也新增一些错误。比如在1858年《中西通书》中,艾约瑟对1853年版《提纲》有所更正,即“又改正癸丑年格致新学提纲,‘太阳率诸行星环绕女藏星’当改为‘太阳率诸行星,今向女藏星相近处而行’,非环绕也。又‘嘉庆二十四年(1819),日耳曼恩格(即Johann Franz Encke,1791~1865)测定彗星行度,约六年余一周天。道光四年,日耳曼比乙拉(Wilhelm von Biela,1782~1856)测定第三彗星行度,三年余一周天。’两周天年数宜互易。道光四年(1824)宜改六年,前校印书误。”([8],2b)对照《畴人传四编》、《西学原始考》中的相关描写,可以发现《西学原始考》中一仍其旧,而《畴人传》四编中除了第一条延误外,对于后两条则已根据《谈天》之语而加以改正,称“因格,一作恩格,日耳曼人,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测定彗星行度,其周时为一千二百十一日”[17],“比拉乙,亦日耳曼人,于道光六年(1826)在墺地利测得第三彗星,其周时为二千四百十日。”([17],10a~10b)《四编》所谓“比拉乙”应为“比乙拉”之误刻。
除了王韬的增补及其对《畴人传四编》的间接影响外,《提纲》的内容与部分术语早在19世纪50年代已为后续著述采纳,对晚清的西学传播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最明显的例证是天文学家与新行星的译名,例如“代加德”、“侯失勒”、“天王星”等,稍后的《西国天学源流》有相当的人名及科技术语取自《提纲》,并进而影响到伟烈亚力和李善兰合译的《谈天》,从而在晚清产生了深刻的印记。当然,《提纲》中有些条目的内容在中国并非第一次介绍,其术语也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前人的成果,比如“刻白尔”、“奈端”、“谷女”、“天后”等。除此之外,在《提纲》之后,又有少数以“格致新学”为题的论文,介绍西方科技知识。如慕维廉“格致新学”一文,主要介绍19世纪末期分光器、照像法等新方法在天文学上的使用。[18]又如李玉书译述之“培根格致新学论”一文,主要讲述培根的科学方法论。[19]尽管这些文章的内容仅限于具体的人或事,但其“格致新学”之用,应是受到《提纲》的影响。
3 《格致新学提纲》的历史意义
作为第一部介绍西方科学史的著作,《提纲》本身就具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尽管两位翻译者后来均遗失了其中的一部分,影响到其完整性。除了前述术语的影响外,《提纲》的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它对哥白尼以来的近代科学发展史的介绍,揭示出西学发展的历史线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学者对西方天文学乃至西学的观念;(2)为稍后开展的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起到了先导作用;(3)“格致新学”一词体现出对西方近代科学新知的倡导等。
首先,《提纲》的内容以天文学为主,其开篇第一条即是哥白尼的日心说,并称“西洋诸国宗之”,其后的介绍也是基于哥白尼日学说,描述天文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进程。哥白尼日心地动学说的提出,标志着近代科学的发端,但在欧洲的确立也经历过一番波折。自1543年《天体运行论》出版后,1616年被罗马教会列为禁书,而宣传其学说的布鲁诺、伽利略等人也遭受过迫害,但经过伽利略、开普勒、牛顿、布拉德雷等人的不断发展,日心说的正确性日益显现,终使罗马教廷1757年解除了对哥白尼学说的禁令。至此以后,哥白尼学说在欧洲广泛传播,并得到较快发展。因此到19世纪,哥白尼日心地动学说早已为西方各国天文学家所宗。
然而,受到清中叶禁教政策的影响,西学传播几乎中断近百年。虽然在19世纪初至19世纪50年代之间也有零散的西方科技知识传入,但并未系统完整地介绍西方科学发展史,因此当时中国学者对西学的认识尚限于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所传播的知识。实际上,哥白尼学说在明清之际也有不同程度的介绍,但相对哥白尼学说的少量介绍而言,汤若望、南怀仁、戴进贤等在钦天监供职的传教士相继为明清两朝编译官方历法,其理论基础均为第谷的折衷体系,第谷体系也成为19世纪新知识传入前中国学者的认知基础。当然,这确有其合理性,因为其时在欧洲得到一定认同的第谷体系在实测方面更为密合。由于第谷体系官方地位的确定,加之与传统的地心观念较吻合,因此为大多数中国学者接受。对于哥白尼学说,虽有薛凤祚、黄百家等人的宣扬[20],但总体而言中国学者对其认识甚浅。比如阮元即在《畴人传》中对哥白尼学说大加反驳,在哥白尼传的按语中根据蒋友仁与汤若望二人对哥白尼迥异的介绍,对哥白尼学说产生怀疑;又在蒋友仁传后评论道:“夫第假象以明算理,则谓为椭圆面积,可谓为地球动而太阳静,亦何所不可?然其为说,至于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畔道,不可为训,固未有若是甚焉。”([10],19a)《畴人传》是“西学中源说”的代表作,在晚清影响颇大,在19世纪50年代之前已有琅嬛仙馆、学海堂、花雨楼、文选楼等多个版本问世。
艾约瑟对天文学知识颇有兴趣,曾发表“关于耶稣会士对欧洲天文学的传入”一文,介绍宋君荣(A.Gaubil,1689~1759)等耶稣会士传播中西天文学的贡献[21];他还与其他来华传教士就中国古代天文学展开过一系列的争论。[22]艾约瑟对阮元《畴人传》的内容及观点也有所批评,认为阮元是为了体现其西学中源的观点而特意将中国古代天算学家及其成就分配在其所处朝代。[23]由此可见,《提纲》以哥白尼日心说作为开端,并较细致地介绍西方天文学的发展大事,可能是艾约瑟希望改变中国学者的西学观念而作。
其次,《提纲》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墨海书馆翻译西方科技著作的纲领。通过从墨海书馆19世纪50年代所刻科技著作来看,《提纲》中所涉及的内容多有专著出版。比如李善兰和伟烈亚力合译了以日心地动与椭圆论为基础的西方天文学名著《谈天》(即Outlines of Astronomy),李善兰在序言中曾开宗明义地介绍日心说,驳斥阮元关于蒋友仁的评论,并明确指出“所译谈天一书,皆主地动及椭圆立说,此二者之故不明,则此书不能读。”[24]这也可以呼应《提纲》对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倡。此外,伟烈亚力和李善兰还翻译了《几何原本》后六卷、《代微积拾级》、《代数学》等著作,介绍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等数学方面的新知识;艾约瑟与李善兰合译了《重学》,较系统地介绍了牛顿力学体系;艾约瑟与张福僖合译了《光论》,介绍了几何光学、色盘、光谱等知识。当然,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开展,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等机构已专设部门翻译西学著作,加之教会所属翻译出版团体,比如美华书馆、益智书会、广学会等,这些机构翻译的科技著作又远超过《提纲》涵盖的学科。
此外,由于《提纲》介绍的天文学家及其贡献仅限于1543至1858年间,在系统性上不免有所缺失,因此晚清其他有关西方天文学史的论述或有增补。比如《西国天学源流》,共提及西方天文学家61位,其中从古希腊至哥白尼之间有16位,哥白尼之后的天文学家共45位,较《提纲》新增了23位;除了新增内容外,《西国天学源流》还较明确地表达出进步的科学史观,以及西方天文学之所以进步的原因,如学者持续努力、天文仪器、数学方法、学会等。[25]又如《谈天》除了在序言中强调哥白尼、开普勒、牛顿在日心地动学说发展中的作用外,在内容上也有新的补充,比如对天王星、海王星的发现日期有更具体的记载,将小行星扩充至五十五颗、加入约翰·赫歇尔的传记等[24]。如包尔腾《星学源流》简略介绍了哥白尼之前的天文学发展[26];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在《西学考略》中对西方天文学发展史也有所描述,尤其对拉普拉斯的宇宙漩涡学说有深入的介绍[27];韦廉臣《天学绪言》以哥白尼、伽利略、第谷、开普勒(刻白尔)、牛顿(奈端)等五人的天文学学说为线索,描述了歌白尼以来的日心说得以逐步确立的这一西方天文学发展历程。[28]
最后,《提纲》的另一个意义应是体现在其“格致新学”所包含的近代科学含义上。实际上,明末清初时期已经有使用“格致”一词指代科学,比如《空际格致》、《格致草》等,但此时格致一词的含义并不仅限于天文、历法、算学等自然科学,对自然知识也多有涉及,更为接近传统的“格物穷理”、“格物致知”等含义。
与明清之际所传入西学相比,《提纲》中除了天文学、数学方面的若干新知识外,也包括了一些光学、力学、热学、电学等其他学科的新进展,成为晚清时期相关知识传播之先导。比如力学方面,虽然明末邓玉函(Johann Schreck,1576~1630)、王徵合译的《奇器图说》中已经使用“重学”一词,但介绍的则是伽利略、牛顿力学之前的内容,且其主要兴趣在机械技术方面的实用知识[29]。《提纲》虽只聊聊数条,却把伽利略力学及牛顿力学的主要思想勾勒出来;又如光学,尽管明清之际已有光学仪器与著作传入,如望远镜、《远镜说》等,《提纲》所介绍的分光法、日光研究、波动学说等则属新知。至于电学、热学,乃是在19世纪新兴的学科领域。至于自18世纪后期以来的天文学发现,比如天王星、海王星、小行星、卫星等,全为新知识。也许出于与明清之际所传西学区别之意,艾约瑟和王韬选择“格致新学”一词。
从艾约瑟此后对西方科技的介绍来看,其“格致”“新学”的概念又有些混淆。比如他在《中西闻见录》第二十八、二十九号中连载发表“光热电吸新学考”,即从“新学”的角度介绍了光学、热学、电学及力学等学科,目之为格致门类,但同时又对“新学”予以解释,称“近来泰西新学分为二门,一为格致学,一为化学”[30],将化学与格致学对等视之。然而在当时的其他译著中,化学显然是作为格致门类之一。当然,除了艾约瑟自身的认识不足外,这一观点也是晚清对西学分科认识尚未定型的反映。
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新教传教士已通过期刊或译著对西方近代科技知识有所介绍,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有“天文地理论”、“全地万国纪略”等篇目介绍天文、地理等知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有“论日食”、“论月食”、“北极星图记”、“月面”、“星宿”、“经纬度”等十余篇论文介绍西方天文学知识,但多以具体内容题名,并未涉及格致名义。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其他传教士还有采用“博物”、“格物”等词以表示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学问。比如《博物通书》、《博物新编》等,涉及天文、地理、生物、化学、物理、技术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又如丁韪良《格物入门》收录力学、水学、气学、火学、电学、化学、测算举隅等七卷。但从总体上看,在19世纪50年代之后,有关西方近代力学、天文学、化学、声学、光学、电学、植物学、地学等学科的专著渐次翻译,蔚然成风,且多以各自学科命名,以示各自为格致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同时,对于一些糅合多学科的著作,则仍以格致名之,比如林乐知《格致启蒙》分为天文、化学、格物、地理四卷;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创办的格致书院,课程涉及天文、历算、电学、化学、测绘、汽机、矿务等方面,其主办的《格致汇编》杂志也涵盖了几乎当时所有学科门类的知识等。
总之,“格致新学”的含义大致相当于西方自然科学,其后的“格致”、“新学”、“科学”的范围或有扩充至西方社会科学与工艺技术领域。即使在日本所翻译的“科学”一词传入中国以后,晚清仍是“格致”与“科学”并存状态。对于从“格致”到“科学”的转变,已有诸多学者有过深入探讨,在此不一一征引。[31]然而究其初始,晚清重启“格致”指代Science的用法,则应追溯于艾约瑟与王韬“格致新学”一词的选择。当然,在晚清,“新学”一词还与“旧学”相对,但此“新学”几等于西学,涉及西政、西艺、西史等方面,而“旧学”多与中学相对,或指举业,或指宋明理学,或指小学考据等,晚清学者于此多有论述,本文不再论列。
综上所述,作为晚清第一份介绍西方科学史的论著,《提纲》着重介绍了1543年以来的西方近代天文学、数学的发展脉络,内容和术语部分吸收了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教士的工作,又通过《西国天学源流》、《谈天》等著作影响到晚清时期的西方天文学传播,在晚清西学东渐史上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同时其“格致新学”的表述实则倡导了晚清科学新知之传播。
附录一
《格致新学提纲》(1853)
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波兰歌白泥(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著《天象旋转考》,始言太阳居中不动,五星及地球俱环绕之,故太阳行十二宫,诸星昼夜盘旋,皆系地球运动。西洋诸国宗之。二十四年(1545),以大利佳但(Girolamo Cardan,1501~1576)始造开立方法。三十九年(1560),玻尔大(Giovanni Battista della Porta,1535~1615)初作穴室取影之法。隆庆十一年(1577),弟谷(Tycho Brahe,1546~1601)测定客星较远于月,又明月离之道,又言金水二星附日而行,绕于地球。万历三年(1575),茅鹿理哥(Franciscus Maurolicus,1494~1575)始明人目内观物之理,而造远视、近视眼镜。十八年(1590),咈兰西肥乙大(François Viète,1540~1603)究明代数学,以西洋二十五字头代数目字,不论已知未知,俱可推之。又造开三乘方法,著《数学纪要》。是年(1590),英国奇白德(William Gilbert,540~1605)著《磁石论》。十九年(1591),以大利加离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著《重学》,始明一斤重与十斤重下坠同迟速落地之理。二十七年(1599),荷兰史德文(Simon Stevin,1548~1620)明斜面上力重比较之理,及分力并力之理,知入水愈深,压力愈大。三十七年(1609),刻白尔(Johannes Kepler,1571~1630)著《火星运动》书,论行星轨道皆为椭圆,又论行星用椭圆面积为平行。三十八年(1610),以大利伽离略造远镜,初见水星有四附星。明年(1611)又见金星有晦朔弦望,一如太阴,又见土星有两耳,又见太阴之体有高低凸凹之形。三十九年(1611),刻白尔改正清蒙气差,论气水中俱有光差,又因悟人目视物之理,如穴室取影。四十二年(1614),英国那比尔(John Napier,1550~1617)造对数,用加减代乘除,以二零七一八二八一八为元。四十三年(1615),伽离略用木星附星掩食定东西里差。四十五年(1617),荷兰师纳拉(Willebrord Snellius,1580~1626)测定地上若干里,合天上若干度,依此推之,可知地球周围多少里。四十六年(1618),刻白尔论行星行于椭圆周,时刻方之比,同于行星距太阳十字线立方之比。四十七年(1619),师纳拉造光差算术,凡光出入于空质中,必成光差角,与原角恒有比例。泰昌元年(1620),英国备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著《格物穷理新法》,实事求是,必考物以合理,不造理以合物。天启四年(1624),英国巴理知思(Henry Briggs,1561~1630)发明对数之理,始取十为元,以令一对十,二对百。崇祯四年(1631),佳生地(Pierre Gassendi,1592~1655)初见水星过日面。五年(1632),伽离略(Galileo)专论天静地动,坐此下狱,强使反其说,乃出之。十年(1637),咈兰西代加德(René Descartes,1596~1650)合代数几何,以发明直曲诸线之理。十二年(1639),英国好洛斯(Jeremiah Horrocks,1618~1641)初见金星过日面。顺治元年(1644),到里直理(Evangelista Torricelli,1608~1647)造量风气轻重之器。十一年(1654),荷兰国国里该(Otto von Guericke,1602~1686)初造风气车,能出器中之风气。十五年(1655),海更士(Christiaan Huygens,1629~1695)发明钟摆之理,始作有摆之钟,又名仪坠子。十六年(1666),海更士初见附土星两耳,实则一光带,又见一附星,作《土星考》。康熙二年(1663),英国格勒哥里(James Gregory,1638~1675)作回光远镜。三年(1664),于观天器上作远镜窥筒。是年(1664),奈端(Isaac Newton,1642~1727)初论微分法。此法及积分法为最深算术,凡借根、天元等法不可推者,用此则可。五年(1666),奈端初知天上地下万物皆有相引之理,是以重物向地心下坠,与月环地球之理同。六年(1667),穵理师(John Wallis,1616~1703)造曲线面积算术。八年(1669),奈端作分光法,白光入三角玻璃分为七色,再加一三角玻璃,仍合为白光。九年(1670),拉那(Francesco Lana,1631~1687)作寒暑表。十年(1671),葛西尼(Giovanni Domenico Cassini,1625~1712)初见土星第二附星。是年(1671),初明钟摆近赤道则迟,远赤道则速,如明地力在赤道最大,在两极最小。十一年(1672),奈端初作回光显微镜。十五年(1676),大泥勒墨尔(Ole Christensen Römer,1644~1710)初明光动之理。是年(1676),葛西尼推定木星自转九小时三刻十分。十七年(1678),海更士初知星光自远及近,如海潮迅速射及目中,人始能见其光。二十三年(1684),葛西尼初见土星又有三颗附星,并前而五。二十六年(1687),奈端著《格物原本》,中言日月星小环于大之理,所行之路,或椭圆,或单曲线,或双曲线,诸行星及地球、月俱行椭圆,客星、彗星俱行单曲线与双曲线,重物向地心下坠,与太阴自东而西行,一理贯通也。四十三年(1704),奈端著《视学》,论回光角与原角等。是年(1704),葛西尼始见土星有两光带。五十七年(1718),咈郎西国主命天文大臣推算地球经纬里差,始知地体系扁圆。五十九年(1720),革来(Stephen Gray,1666 ~1736)考正琥珀气之理,好里(Edmond Halley,1656 ~1742)考正月行之理。雍正五年(1727),英国白拉里(James Bradley,1693~1762)考正地动恒星视差之理。八年(1730),英国海特里(John Hadley,1682~1744)造纪限镜仪,以测太阳高弧。十三年(1733),西国考正地球扁圆周径。是年(1733),西国创考验万物相引法,悬物空中,近山则线斜。乾隆二年(1737),咈郎西格来罗(Alexis Clairaut,1713~1765)考明三动物相牵引之理。十年(1745),白拉里始知地球南北极有动差,十九年一周。十二年(1747),米利坚佛兰格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始明琥珀气与电气同。十三年(1748),欧楼(Leonhard Euler,1707~1783)详考各行星相引微差之理。二十二年(1757),好里预推之彗星见,每七十五年一周天,适符其数,道光十五年又见。是年(1757),道伦德(John Dollond,1706~1761)造无晕远镜。远镜透光俱有彩晕,惟此镜无,以对晕二式玻璃合而尽消其晕。二十六年(1761),欧楼阐明差等数,初造积分法。二十七年(1762),白拉格(Joseph Black,1728~1799)始明阴热气之理。三十九年(1774),英国始明地质松紧之理,测定同体地水二质,其较多五倍半。四十年(1775),咈兰西拉白拉瑟(Pierre-Simon Laplace,1749~1827)阐明海潮之理。四十六年(1781),英国天文大臣侯失勒(William Herschel,1738~1822)初见土星之外有一行星,名之曰於士(Uranus),译即天王星。四十七年(1782),侯失勒以远镜测见白气数点,如传说积尸之类,同于天河,亦系无数小星之光。五十二年(1787),拉白拉瑟讲明太阴轨道之理。五十三年(1788),拉格浪(Joseph Louis Lagrange,1736~1813)用微分法详解动静重学之理。五十四年(1789),侯失勒名威灵造极大远镜,测见土星又有两附星,并前而七。嘉庆四年(1799),拉白拉瑟著《天文重学大成》。五年(1800),侯失勒初明太阳所出之气,有热气、光气、化物气之别,穴室照影肖像法用第三气。六年(1801),以大利亚必亚齐(Giuseppe Piazzi,1746~1826)初见木星火星之间有一小行星,名曰谷女。七年(1802),日耳曼阿尔白士(Heinrich Wilhelm Matthäus Olbers,1758~1840)测见第二小行星,名曰武女。八年(1803),侯失勒测见定位星,有双星互相环绕。九年(1804),日耳曼哈尔定(Karl Ludwig Harding,1765~1834)测见第三小行星,名曰天后。十二年(1807),阿尔白士测见第四小行星,名曰火女。是年(1807),侯失勒测见天王星有六附星。十九年(1814),西国初明露水之理,空中恒有水气,遇地面冷,必垂而为露,夜中无云,地面热气易向太虚透发,故露下,如云掩地面,热气难透,必不成露,树林遮蔽与云无异。二十四年(1819),日耳曼尔士德(Hans Christian Örsted,1777~1851)发明磁石与电气异同之理。是年(1819),日耳曼恩格(Johann Franz Encke,1791~1865)测定彗星行度,约(六)[三]年余一周天。道光二年(1822),侯失勒名约翰(John Herschel,1792~1871),用大远镜测定位星,有单星、双星、三星、四星之别,各互相环绕。三年(1823),日耳曼弗伦好弗(Joseph von Fraunhofer,1787~1826)初见日光分为七色,中间有无数黑线,其相去度分俱一定。诸行星之光与日大同小异,因借日之光故也。定位星则各不同,因自生光故也。(四)[六]年((1824)[1826]),日耳曼比乙拉(Wilhelm Von Biela,1782~1856)测定第三彗星行度,(三)[六]年余一周天。十年(1830),英爱理(George Airy,1801~1892)发明光学,言日月之光,激动空气,如波浪然,千层万叠,宕漾人目,而后觉有光。二十年(1840),日耳曼德路威测得太阳率诸行星,(环绕女藏星)[今向女藏星相近处而行],一年行三千三百三十五万里。后有梅特勒测得昴宿为太阳及天河内诸星所环绕星数数千,无异象,因其轨道极大故也。二十五年(1845),日耳曼亨该(Karl Ludwig Hencke,1793~1866)测见第五小行星,名曰严女。二十六年(1846),咈兰西力佛理亚(Urbain Le Verrier,1811~1877)用算术推知天王星之外必更有行星牵动天王星,并推得其度分,其友用远镜细测,果见有海王星,与所推度分仅差四分耳。是年(1846),英国阿但史(John Couch Adams,1819~1892)亦用算术推知海王星所在度分。二十七年(1847),亨该测见第六小行星,名曰稚女。是年(1847),英国欣特(John Russell Hind,1823~1895)测见第七小行星,名花神,第八小行星,名虹神。又有人测见海王星有两附星,亦有一光带,此事尚未有确据。二十八年(1848),英国格来汉(Andrew Graham,1815~1908)测见第九小行星,名曰猎师。
(说明:录文据牛津大学图书馆藏1853年《中西通书》,随文加注公元纪年、西人原名、生卒年和个别专有名词。参照1858年《中西通书》本所附勘误,作了相应改动,以()[]标注。1871年《教会新报》本文字略有差异,详见正文。)
附录二
《格致新学提纲》(1858)
耶稣后一千六百五十六年,海更士用千里镜初见近参宿处一大星(即癸丑年所定星气,今改名)。后一千七百八十六年,侯失勒造星云表,内载一千座。后一千八百三十三年,侯失勒约翰造北天星云表,为二千一百五十五座,星林表为一百五十二座,又在阿非利加南地造南天星云表,为二千二百三十九座,星林表为二百三十七座。后一千八百十九年(注:按照时间排序,疑为1839年),法兰西国阿拉哥(François Arago,1786~1853)以光分南北方向,用颜色相配,制南北线分光镜。后一千八百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法兰西腓乙(Hervé Faye,1814~1902)推彗星轨道一周为七年百分年之二十九,轨道在土火两星之间。后一千八百四十五年,英国罗斯伯(罗斯地名伯爵也)(Lord William Parsons Rosse,1800~1867)造反照光千里观星镜,长为五十三英尺,测星云为无数,小星者甚多。后一千八百四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英国拉斯拉(William Lassell,1799~1880)测得海王星之第一月。后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英国格来汉测得第九小行星,名弥低斯,译曰猎师。后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九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合众国本特(William Cranch Bond,1789 ~1859;George Phillips Bond,1825~1865)测得附土星之第八月(Hyperion),九月十九、二十日,拉斯拉亦测见之。后一千八百四十九年四月十二日,以大利特迦斯巴利(Annibale de Gasparis,1819~1892)测得第十小行星,名海其阿Hygeia,译曰医女。后一千八百五十年五月十一日,特迦斯巴利测得第十一小行星,名巴腿拿卑Parthenope。是年八月十四日,英国拉斯拉测得海王星之第二月。是年九月十三日,英国欣特测得第十二小行星,名维多利亚Victoria,译曰胜女。是年十一月二日,特迦斯巴利测得第十三小行星,名哀及利亚Egeria。后一千八百五十一年五月十九日,欣特测得第十四小行星,名以来奈Irene,五月二十三日,特迦斯巴利亦测见之。是年,英国拉法抬(疑为Michael Faraday,1791~1867)究明养气指南北方向,以噏铁石能力加在养气之上为南北方向,其余诸气俱东西方向,并又究明吸养气之能以热气大小、体之大小为准。后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英国欣特测得第二十二小行星,名加略必Caliope。后一千八百五十三年,日耳曼阿多斯得路佛(Otto Wilhelm von Struve,1819~1905)测定织女星(Vega)离地一百三十亿万英里,所射出之光应二十一年至地,又星光较多于太阳光十六倍。后一千八百五十四年,英国约翰孙(Manuel John Johnson,1805~1859)天津五六两星中之定位星用地轨道半径差究明其星约离地六十亿万英里,所射出之光应十年至地。此星与白西勒(Friedrich Wilhelm Bessel,1784~1846)查出之数相符。后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巴黎斯哥勒斯迷(Hermann Mayer Salomon Goldschmidt,1802~1866)测得第四十一小行星,名大副尼Daphne,英国和其孙(Norman Robert Pogson,1829~1891)测得第四十二小行星,名依昔斯Isis,两行星轨道俱在火木二星之间,星等如第十一、第十二之恒星。是年,又有人究明正月内一小时见五流星,七月内一小时见九流星,八月内一小时见十三流星,九月、十月、十一月内一小时各有四流星,余月内一小时俱有三流星,如此诸流星降下数时常有之。后一千八百五十七年,泰西诸天文士测见第四十三至第五十小行星。
(说明:录文据牛津大学图书馆藏1858年《中西通书》,体例同前。)
1 韩琦.《历象考成后编》与《仪象考成》的编纂[M]∥陈美东.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708~718.
2 汤若望.历法西传[M].∥潘鼐.影印本《崇祯历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b.
3 Milne W.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M].Malacca∶ Anglo-Chinese Press,1820.154.
4 Gützlaff K F A.A Monthly Periodical in the Chinese Language[J].The Chinese Repository.1833,2(4):186 ~187.
5 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7.
6 宇宙.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J].丁酉四月.8a~9a.
7 艾约瑟,王韬.格致新学提纲[J].中西通书.墨海书馆,1853.
8 艾约瑟,王韬.格致新学提纲[J].中西通书.墨海书馆,1858.26a.
9 韩琦.《数理格致》的发现——兼论19世纪以前牛顿学说在中国的传播[J].中国科技史料.1998,19(2):78~85.
10 阮元.畴人传[M].第46卷.道光二十二年文选楼丛书本.1a.
11 南怀仁.新制灵台仪象志[M].第2卷.康熙十三年刻本.22a.
12 徐光启,李天经,等(督修),罗雅谷(撰).五纬历指[M].第9卷∥崇祯历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4b
13 孙承晟.明清之际西方光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孙云球《镜史》研究[J].自然科学史研究,2007,(3):363~376.
14 韩琦.传教士伟烈亚力在华的科学活动[J].自然辨证法通讯.1998,20(2):57~70.
15 艾约瑟.格致新学提纲[J].教会新报.1871.137a~b.
16 王韬.西学原始考[M].西学辑存六种本.1890(光绪庚寅).
17 黄钟骏.畴人传四编[M].卷11,6b~7a∥留有余斋丛书本.1898(光绪戊戌).
18 慕维廉.格致新学[J].万国公报,1892(光绪十八年十月),第46册:9a~10b.
19 马林著,李玉书述.培根格致新学论[J].万国公报,1901(第十三年第七卷),151册:10a~16a.
20 杨小明.哥白尼日心地动说在中国的最早介绍[J].中国科技史料.1991,20(1):67~73.
21 Edkins J.On the Introduction of European Astronomy by the Jesuits[J].The North China Herald.Oct.30,1852.
22 邓亮,韩琦.晚清来华西人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学起源的争论[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0(3):45~51.
23 Edkins J.The Introduction of Astrology into China[J].The China Review.1886 ~1887,15(2):126 ~128.
24 伟烈亚力,李善兰.谈天[M].上海:墨海书馆,1859(咸丰九年).
25 伟烈亚力,王韬.西国天学源流[M].西学辑存六种本.1890(光绪庚寅).
26 包尔腾.星学源流[J].中西闻见录.第2号.1872.18a~19b.
27 丁韪良.西学考略[M].卷下∥续修四库全书.1299册.影印光绪癸未同文馆聚珍版.736~737.
28 韦廉臣.圣教功效论略[M].上海:美华书馆,1902(光绪二十八年).40a~44b.
29 张柏春,等.传播与会通——《奇器图说》研究与校注[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30 艾约瑟.光热电吸新学考[J].中西闻见录.第28号.1874.16b.
31 Elman B A.On Their Own Terms:Science in China,1550—1900[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of the Outlines of New Learning on the Investigations of Things(Gezhi Xinxue Tigang,格致新学提纲)by Joseph Edkins and Wang Tao,published in two issues of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Concord Almanac(中西通书)in 1853 and 1858 respectively,was the earliest work in late Qing China on the chronology of western science.It introduced the progress and discovery of western science since Nicolaus Copernicus.This article identifies numerous scientists introduced in the Outlines,analyzes its content,and investigates its process of transmission,especially the influence on Wang Tao's The Origins of Western Learning(Xixue Yuanshi Kao,西学原始考)and Huang Zhongjun'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Biographies of Mathematicians(Chouren Zhuan Sibian,畴人传四编).It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purpose of writing this Outlines was to change Chinese scholars'old views of western learning.This helped greatly the transmission of new western science in late Qing China.
Key words Gezhi Xinxue Tigang,Chinese and Foreign Concord Almanac,Joseph Edkins,Wang Tao,Chouren Zhuan Sibian,history of western science
The Prelude to the Transmission of New Learning in late Qing China:Content,Significance and Influence of Gezhi Xinxue Tigang by Joseph Edkins and Wang Tao
DENG Liang1,HAN Qi2
(1.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cient Texts,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2.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CAS,Beijing 100190,China)
N091
A
1000-0224(2012)02-0136-16
2010-11-17;
2012-04-05
邓亮,1976生,重庆潼南人,馆员,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史、科技与社会;韩琦,1963年生,浙江嵊州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科学史和中西科学、文化交流史研究。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0110490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