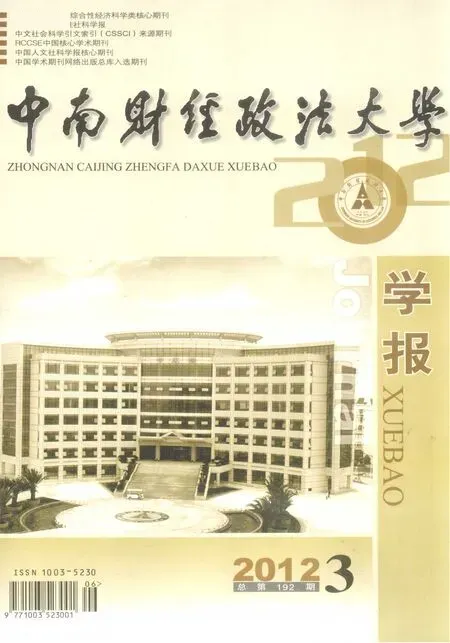企业资源与并购绩效:一个非线性分析视角
傅传锐
(福州大学 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350108)
一、问题提出
并购的财富毁灭的梦魇引发了关于并购价值创造来源的探索。协同效应论认为,并购活动能通过管理协同、经营协同与财务协同机制,创造“1+1>2”的增值效应。该理论的隐含假设是并购方能够在并购决策过程中恰当选择目标企业,并购后能够有效整合并购双方的资源要素,使优势资源能为双方企业所共享,最大化生产要素的使用价值,从而降低平均经营成本,增加收入,提升绩效。因此,并购企业是否理性决策并推动要素整合是并购成败的关键。
早在20世纪50年代,Penrose就在其著作《企业成长理论》中将企业视为一系列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体”[1](P24-25)。Wernerfelt在Penrose的基础上,提出“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是其所拥有的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的组合[2]。无形资源包括依附于管理者、员工身上的能力、知识、经验等要素组成的人力资本,以及企业文化、管理哲学、流程、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等要素组成的结构资本。这两类资源具有密集的智力含量特征,使其被归结为智力资本。有形资源则是由土地、劳动力、财务资本等有形要素组成的物质资本。作为资源集合体,企业的任何战略决策、行动的实施都立足于其所拥有的资源禀赋。智力资本学者进一步认为,智力资本是唯一满足战略资源属性的异质性资源,是企业创造价值的源泉[3]。因而,企业的智力资源禀赋成为企业决策、行动的核心驱动,决定着并购方能否理性决策与有效整合并购双方的生产要素,进而实现预期的并购收益。在这种理论预期下,新近一些文献尝试对智力资本与并购绩效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考察。Gupta和Roos将智力资本视为协同价值的来源,认为协同实现的关键取决于智力资本的迁移、共享和复制等三种交易机制,协同的价值创造是智力资本交易机制、杠杆机制与迁移惰性互动的结果[4]。Bryson将并购失利归因于不同文化的融合困难、关键人才流失等人力资源问题,认为维护工作团队的稳定有助于控制并购过程中的人力资源风险[5]。Papadakis以72家希腊企业的并购交易为实证样本,考察了外部环境、并购特征、并购公司特征和人力资源管理等多方面因素对并购成败的影响。其发现:与员工的沟通是最重要的并购成功要素[6]。Lin、Hung和Li以267家美国银行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并购银行的人力资源能力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较高的人力资源能力有助于并购后的整合,进而实现高效率的并购[7]。此外,高良谋研究了影响我国企业并购整合的关键因素,发现管理者的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有负影响[8]。傅传锐以我国A股并购公司为样本,发现并购方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都对并购后的绩效存在显著正影响,并且在绩效越好的并购公司中,人力资本的作用越明显[9]。
然而,当前的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仍存在较多局限。首要的不足在于,现有研究局限在线性分析框架下探讨资源要素与并购绩效间的关系。而在现实的并购价值创造过程中,任一要素的预期功能的发挥都或多或少地需要其他要素的配合与支持,其也不可避免地在其他要素价值创造环节中充当辅助要素的角色。不同资源要素间的磨合、搭配意味着并购价值更可能是通过资源要素的互动价值创造机制实现的,而非资源要素间相互孤立的线性化结果。此外,线性分析框架只能给出特定要素对并购绩效影响的大致方向,但是却不能进一步回答“为什么同样拥有某项资源要素的企业间的并购绩效却可能大相径庭”,“特定要素是否需要达到一定的阈值强度才能真正发挥其预期的价值创造作用”。在我们看来,并购价值创造过程是复杂的非线性系统,其蕴含着并购企业不同资源要素间的互动机制、阈值机制。已有文献在线性分析框架下给出的线性作用机制,是对现实价值创造过程的简化。这使我们无法对并购价值创造过程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另外一个局限在于,已有研究集中关注资源要素对并购后绩效水平的影响[7][9],却忽略了对并购后绩效变化程度的影响因素的实证考察。而从并购后绩效变化程度的动态视角着眼,无疑能为我们揭示更为细致的资源要素对并购绩效的贡献机制。本文以2005~2007年发生并购的171家A股并购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元非参数回归模型就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企业资源与并购后的绩效水平、绩效改善程度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二、理论假设
协同效应论认为,并购方可以通过取长补短、资源共享等方式整合并购双方的生产要素,以期产生管理、经营、财务等三个层次的协同“增值”效应。然而不论哪个层面的协同机制,都必须依托于并购企业在并购交易前所累积的智力资源。从管理协同层次看,由于并购双方间存在管理效率的显著差异,管理能力较强的并购方需要将自身高效的管理能力、经验、制度等智力资源注入目标方,进而提升目标方的管理效率,推动并购双方整体价值的增进。经营协同旨在实现规模经济或产业链的纵向一体化,横向并购的经营协同是指通过对双方的同类或相关职能部门的合并,以降低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从而获取规模效益。然而,双方部门的合并,将考验并购方的企业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同化、融合能力,以及自身研发部门对目标方技术资源的学习与应用能力、不同规格生产线的对接能力、供货与销售网络的整合能力等一系列智力资源。在将上下游企业间的交易费用内生化的纵向一体化过程中,同样需要并购方具有整合生产流程的软实力。在财务协同过程中,高成长却缺乏资金的企业与低增长但资金充足的企业的互补式合并,要求并购方具备对未来投资机会的前瞻能力、财务规划能力。
同时,成功的并购交易还要求并购方拥有与目标方、银行、政府部门、供应商、客户的良好关系,以尽可能避免目标方管理层的反收购壁垒、满足并购融资需求、获得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以及减少并购带来的供应渠道冲突与客户流失风险。因此,成功的并购及协同效应的实现,离不开并购方的智力资本积累。并购方的智力资源储备越充裕,越有助于预期并购收益的实现与并购后绩效水平的提升。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a:并购企业智力资本对并购后的绩效水平存在显著正向作用。
假设1b:并购企业智力资本对并购后的绩效改善存在显著正向作用。
尽管智力资本是并购价值创造的核心资源,但是其运作不能脱离现实的物质环境。土地、原材料、机器设备是企业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财务资本还为企业并购交易及并购后的资源整合提供资金支持。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并购企业物质资本对并购后的绩效水平存在显著正向作用。
假设2b:并购企业物质资本对并购后的绩效改善存在显著正向作用。
在价值创造过程中,智力资本内部各要素间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关系[3]。从相互影响的角度看,人力资本作为唯一的能动性资源,其推动了企业对管理哲学、流程、文化氛围等结构资本的塑造,以及企业与供应商、银行、政府部门等外部利益相关者间关系的培育与持续维护。而结构资本也通过良好的工作氛围、现代化管理流程、密切的企业外部联系,提高人力资本的价值创造效率。从相互转化的角度看,在开放、协同的企业文化中,孕育于管理者、员工大脑内的经验、诀窍等隐性知识通过团队共享模式逐步固化于企业的信息系统、文化、制度等结构资本要素中。同时,企业数据库、知识产权等组织知识也能够通过组织培训、个人学习等途径为个人所获得,进而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因此,智力资本各要素并非孤立地发挥其对并购绩效的作用,而是在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交互作用模式中动态地对并购绩效施加影响。于是,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a:并购企业智力资本要素对并购后的绩效水平存在显著正向的交互作用。
假设3b:并购企业智力资本要素对并购后的绩效改善存在显著正向的交互作用。
并购过程中,智力资本要素间的交互作用模式以及物质资本对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活动的支持,意味着企业不同资源间存在着特定的协同机制。这要求特定的生产要素应当达到必要的“阈值”存量水平以满足自身价值创造以及其同其他要素相匹配而协同创造价值的双重需求。从人力资本的并购价值创造角度看,目标方的恰当选择与职能部门的顺利合并,需要并购方具有超越同行一般水平的决策管理能力、组织能力以及较强的学习、融合能力。从结构资本角度看,只有强势的企业文化、管理哲学才能在短期内同化目标企业,重塑管理理念,整合管理流程。并购可能引发的目标方反收购、政府管制、客户流失等风险,也要求并购方能在事前建立与各利益相关者间较为坚韧、紧密的纽带。从物质资源角度看,只有足够的财务资本,才能满足庞大的并购融资需求及对后续整合的资金补给。相反,未能达到特定阈值水平的弱势的资源能力导致并购整合过程漫长,风险难以控制,成本增加。并购方无法有效实施对目标方的重组整合预期方案,并购也就无法创造价值。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a:并购企业资源要素对并购后的绩效水平的作用过程存在阈值机制,即当特定要素的数量高于其相应的阈值水平时,其才能对并购后的绩效施加影响;否则其无法影响并购后的绩效。
假设4b:并购企业资源要素对并购后的绩效改善的作用过程存在阈值机制,即当特定要素的数量高于其相应的阈值水平时,其才能对并购后的绩效改善施加影响;否则无法改善并购后的绩效。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5~2007年进行并购的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并根据以下规则筛选数据:(1)剔除在2005年及其后上市的并购公司;(2)剔除并购交易失败的事件;(3)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剔除金融、保险类并购公司;(4)在2005~2007年,发生多次并购交易的并购公司,只选取其并购交易金额最大的并购事件;(5)剔除在并购首次公告发布时未实施股改的并购公司;(6)剔除并购首次公告发布时仍为ST、*ST类的并购公司;(7)为了计算对数化企业规模的需要,剔除并购前一年年末净资产账面价值为负的公司;(8)剔除所需变量数据缺失、极端异常值的样本。最终得到171家并购公司样本。所有数据来自CSMAR并购重组数据库、锐思数据库、CCER数据库。
(二)变量界定
1.并购绩效。并购绩效的度量方法包括使用超额收益率的事件研究法与基于财务指标的会计研究法。在我国新兴加转轨的资本市场上,内幕交易、并购题材股的“炒作”时有发生,这使得股价可能严重背离并购公司的基本业绩,因此超额收益率难以客观考察并购绩效。会计研究法根据上市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数据,计算财务指标,因此能够更真实地反映企业并购后的业绩水平与变化。本文使用会计研究法来评估并购绩效。为避免不同的会计指标从不同角度评价企业业绩而造成评价结果与理解上的差异,并克服单个会计指标容易被人为操纵的局限,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能够较全面反映企业绩效不同维度的业绩指标进行因子提取,并计算因子综合得分,以度量并购绩效。我们选取分别代表企业盈利能力、成长能力、营运能力与偿债能力的20个财务指标作为因子分析的原始指标体系①。本文根据并购首次公告前一年年末的原始指标体系提取并购前的综合绩效水平F-1,根据并购当年及随后两年的原始指标体系的均值提取并购后的综合绩效水平,并定义以度量并购公司并购后绩效水平的改善程度。
2.企业资源。本文使用改进后的智力增值系数模型(value added intellectual coefficient,VAIC)度量企业的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资源要素。改进的VAIC方法通过企业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的比率(δ)衡量价值增值总量(VA)中归属于物质资本的比例,而将余下的增值部分视为智力资本的贡献,以实现对不同资源要素的增值贡献的划分。因此在改进的VAIC方法中,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价值增值贡献量VAIC与VAPC分别为VA×(1-δ)、VA×δ,并定义人力资本增值效率(HCE)、结构资本增值效率(SCE)与物质资本增值效率(CEE)[9]:

式中,CE、HC、SC分别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结构资本。根据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披露的现状,以企业税前利润、工资费用和利息费用的总和表示价值增值总量VA;分别以负债表中的“净资产账面价值”、现金流量表中的“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表示物质资本CE、人力资本HC。
3.控制变量。为避免变量遗漏导致模型设定存在误差,我们在回归模型中加入5个控制变量。
(1)每股净现金流量(CASH)。代理理论认为,管理层为满足建立企业帝国以享受更多的在职消费、特权与职业声誉,降低个人失业风险等私利,将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投入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的并购活动,从而导致并购后的业绩下降。因此,每股净现金流量对并购绩效存在负效应。文中,每股净现金流量=并购前一年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总股本。
(2)股权集中度(CR)。在一定的股权集中下,具有监督管理层行为的动机与能力的大股东的存在能够抑制管理层的私利行为,从而降低代理成本,有助于并购绩效的提高。本文使用并购前一年年末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反映股权集中度。
(3)股权制衡度(Z)。大股东在监督管理者的同时,也具有侵占控股企业与中小股东利益的动机。股东间力量的制衡能够有效抑制大股东掠夺控制权收益的私利行为,降低代理成本,提升并购绩效。我们使用并购前一年年末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之比来反映股权制衡度(反向指标)。
(4)政府关联度(GOV)。在我国新兴加转轨的资本市场背景下,政府在并购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与政府关联度高的企业的并购行为易于获得政府的支持,有利于降低并购成本。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或政府控股的企业可能在政府的主导下,通过收购“劣质资产”或“优质资产”而被掏空或支持,导致并购后业绩下降或改善[10]。本文使用并购前一年年末国有股比例度量政府关联度。
(5)企业规模(SIZE)。企业规模影响并购企业对外部资源的吸收整合能力,关系到规模经济的实现与否。本文中,企业规模是并购前一年年末企业市场价值的自然对数。
(三)计量模型
为检验前文提出的并购企业智力资本要素间的交互作用、资源要素对并购绩效的阈值作用机制等非线性效应假设,本文使用多元自适应回归样条(multivariate adaptive regression splines,MARS)非参数回归方法对企业资源与并购绩效间的关系进行估计。传统的线性回归仅将自变量的线性项作为回归项,而MARS将分段线性基函数作为回归项。MARS模型可以表示为[11](P321-329):

其中,β0、βm分别为常数项与估计系数。hm(X)是基函数集合C={(Xj-t)+}(t为结点,且t∈{x1j,…,xij,…,xNj)中的函数,或其中两个基函数的乘积。Xj、xij分别表示第j个自变量及其第i个样本观察值。(Xj-t)+是分段线性基函数:当Xj>t时,(Xj-t)+=Xj-t;当Xj≤t时,(Xj-t)+=0。MARS通过两个步骤来Z选择模型最终包含的基函数和结点位置。第一个步骤是向前增加基函数。最初,模型只包括常量函数h0(X)=1,然后将能最大程度降低残差的基函数集C中的候选基函数与上一阶段模型中已存在的基函数的积添加到已有的模型中去,并利用最小二乘法估计系数βm和β0。第二个步骤是向后删除基函数,即逐步从模型中删除引起残差平方和增加最少的项,最终得到最佳估计模型。
为考察并购企业资源要素与并购后的绩效水平及并购后的绩效改善程度间的关系,我们分别以并购后的综合绩效得分()、并购后的绩效改善程度(△F)为因变量,以并购企业资源要素、控制变量为自变量构建两个MARS回归模型:

根据基函数(Xj-t)+的定义,只有当自变量Xj大于结点t值时,其才能对因变量施加影响。这实际上描述了以结点t为阈值水平的,自变量Xj对因变量的阈值作用机制,即自变量对因变量是否存在影响受控于阈值水平t。此外,MARS回归过程中使用的交叉积回归项,体现了不同变量对因变量的联合作用。因此,我们可以根据MARS模型的估计结果中是否存在统计显著的基函数项、交叉积回归项,判断相应的资源要素是否对并购后的绩效水平、绩效改善程度存在阈值作用机制以及不同要素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机制。本文使用R软件程序包polspline实施MARS回归估计。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并购绩效因子分析
我们分别对并购前一年(t-1)及并购后()的绩效指标体系进行因子分析,结果见表1。

表1 因子提取结果
表1显示并购前一年(t-1)与并购后)的绩效指标体系的KMO抽样适度测定值都在0.5以上,Bartlett球形检验值都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这说明并购前后的绩效指标体系都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我们对并购前后年份提取足够多的公因子(都提取11个公因子),使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0%以上,以充分体现原有指标体系的信息,并使用回归法计算各因子得分。最后根据各因子得分及其相应的方差贡献率,分别加权计算并购前一年、并购后的因子综合得分F-1和F0~2:

式中,Zi,j表示第i年提取的第j个因子。
(二)回归结果
为考察企业资源与并购后的绩效水平间的非线性关系,本文以并购后的综合绩效为因变量进行MARS非参数回归,同时也给出线性回归结果以做比较,结果见表2。
表2 以为因变量的回归估计结果

表2 以为因变量的回归估计结果
注:上标a、b、c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统计显著,表3同。
多元线性回归(OLS)0.490 5 HCE -0.025 2 0.030 8 HCE 0.024 1c 0.014 1(HCE+0.04)+ 0.237 5a 0.062 0 SCE 0.000 3 0.001 8(HCE-1.63)+ -0.240 3a 0.056 6 CEE 0.428 9b 0.215 1 CEE 2.293 9a 0.585 2 GOV 0.064 2 0.104 9(CEE-0.37)+ -2.314 2b 0.937 2 SIZE 0.093 6a 0.024 0 CEE×CR -3.248 2a 1.222 9 CR 0.223 5 0.178 6 SIZE -0.024 6 0.056 9 Z -0.000 7 0.000 5 SIZE×CR 0.276 4b 0.116 0 CASH 0.031 2 0.046 5 CR -5.014 6b 2.467 4 R2 0.307 R2估计项 系数估计值 标准差常数项 -0.106 5 1.199 8 常数项 -2.162 1a非参数回归(MARS)估计项 系数估计值 标准差0.156 5
根据表2的MARS非参数回归结果,我们发现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企业规模与股权集中度对并购后的绩效水平存在非线性的作用机制。其中,人力资本对并购后的绩效水平的影响呈现为统计显著的双重阈值机制。从基函数(HCE+0.04)+与(HCE-1.63)+项可以看到,当人力资本值(HCE)高于阈值水平-0.04时,其对并购后的绩效在1%水平上有显著积极贡献,贡献的大小是人力资本值与阈值-0.04的差的0.237 5倍。当人力资本值高于阈值水平1.63时,人力资本对并购后的绩效水平的影响来自两个阈值作用机制,一个是先前以-0.04为阈值的基函数的贡献,另一个是以1.63为阈值的基函数的贡献。由于基函数(HCE-1.63)+的系数是-0.240 3(1%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当人力资本值过高时(该基函数的结点1.63处于人力资本的3/4分位数以上),反而会对并购后的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当人力资本值高于阈值1.63时,其对并购后的绩效水平的总体影响为:0.2375×(HCE+0.04)-0.2403×(HCE-1.63)。根据这个公式,只有当 HCE>143.28时,该总体影响才为负。而这一临界水平远高于样本中的人力资本最大值(11.276 7)。综合两种影响,人力资本仍然能对并购后的绩效发挥积极的正向贡献,尽管当人力资本值过高时,其对并购后的绩效水平的正面影响由于基函数(HCE-1.63)+带来的负效应的抵消而有所减弱。
就物质资本来看,其对并购后的绩效存在三种类型的统计显著效应。首先是物质资本对并购后的绩效存在显著的线性正影响。物质资本值每提高1个单位,其对并购后绩效的线性影响就提高约2.3个单位。其次,基函数(CEE-0.37)+体现的阈值效应。当物质资本值高于阈值水平0.37时,其对并购后的绩效存在负面效应,贡献的大小等于物质资本值与0.37的差的约2.31倍。由于阈值水平0.37处于物质资本值的3/4分位数以上,因此,这也意味着过高的物质资本反而对并购后的绩效产生不利影响。最后,物质资本还通过其与股权集中度(CR)的交互作用影响并购后的绩效。这种交互作用统计显著为负。此外,股权集中度还对并购后的绩效有显著线性负效应,其与公司规模交互产生显著正效应。
总体而言,尽管我们未能找到结构资本影响并购后绩效的显著证据,但人力资本对并购后的绩效水平存在总体为正的显著阈值作用机制,因此,假设1a与4a部分得到证实;物质资本亦能对并购后的绩效施加显著的正向线性影响,假设2a得到实证支持;而资本要素间交互效应证据的缺失使假设3a未能得到证实。
比较MARS回归与线性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在线性回归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企业规模虽然对并购后的绩效存在显著作用,但是却未能反映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阈值作用机制、物质资本与股权集中度的交互效应以及企业规模与股权集中度的交互效应。另外,从模型解释能力R2上看,非参数估计结果(30.7%)也要优于线性估计结果(15.65%)。因此,MARS回归较线性回归更好地解释了企业资源与并购后的绩效水平间的复杂关系。
为进一步揭示企业资源对并购后绩效水平的改善程度的作用机制,我们以并购后综合绩效相对并购发生前一年的综合绩效的变动量为因变量再次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3。

表3 以△F为因变量的回归估计结果
在表3的MARS非参数估计结果中,我们发现物质资本通过两种途径显著影响并购前后的绩效改善程度△F。首先,物质资本存在对△F的阈值效应,即当物质资本值高于阈值水平0.13时,其对△F有显著正向作用。其次,物质资本通过其与股权集中度的交互负效应影响并购后绩效水平的变化。此外,我们还发现股权集中度对△F存在显著的线性积极效应。因此,假设2b得到验证,假设4b部分得到验证,假设1b与3b未得到证实。
再次对比线性估计结果,不难发现:在线性回归中,尽管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变量都是统计显著的,然而它们的系数估计值却为负。这意味着,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增加反而导致并购后绩效水平的恶化。这显然是与资源基础理论相违背的。除了估计结果缺乏经济合理性外,线性估计结果的R2也较低。因而,线性估计难以较好地拟合蕴藏于企业资源与并购后绩效改善程度间的内在联系。
五、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多元非参数回归模型就企业资源对并购后的绩效水平及绩效改善程度的非线性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从企业资源对并购后的绩效水平的作用来看,首先,尽管人力资本对并购后的绩效水平存在显著的积极贡献,然而我们缺乏结构资本影响并购后的绩效以及资本要素间交互效应的证据。在健全的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任何一种资本要素都发挥着其特定的价值创造功能,并扮演与其他要素协同创造价值的重要角色。结构资本、要素间交互效应在并购绩效作用机制中的缺位,意味着当前我国并购企业仍未能充分关注诸如企业文化、管理制度、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等结构资本要素以及不同要素协同增值机制的重要性,未能在并购决策前、并购后整合过程中充分利用结构资本要素推进整合全面深入的发展,妥善处理不同要素间的协同关系,因而导致结构资本、要素间交互机制无法发挥其理论预期的价值创造贡献。其次,实证结果发现,资源要素不仅对并购后的绩效存在显著为正的阈值作用机制(如人力资本),还存在显著为负的阈值作用机制(如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这种负向影响出现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高分位水平上。这意味着当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过多时,其对并购绩效存在负面效应。这种现象可能源于并购整合过程的复杂性。面对整合过程中双方企业文化、管理哲学、规章制度、经营战略、对外关系渠道等多维度的潜在冲突,并购企业需要在并购交易前具备多元化的、发展均衡的资源要素组合,包括强势的企业文化、合理的财务规划、企业与利益相关者间良好的关系等。由于在特定时点上,并购企业的资源总量一定,某种资源要素的过度累积,势必会压缩其他资源的发展空间,进而导致企业内在资源的非均衡布局,从而对并购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从企业资源对并购后绩效改善程度的作用来看,只有物质资本能通过阈值机制对绩效改善施加显著正向作用,而未发现智力资本要素的作用。可见,并购企业仍依赖物质资源改善并购后的绩效,而未能真正有效推动智力资本要素进行价值增值。
此外,不论是在企业资源对并购后的绩效还是绩效改善程度的作用过程中,我们都发现了大股东对并购企业物质资源的掠夺问题。虽然在以并购后的绩效水平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中,股权集中度与企业规模存在交互正效应,以及在以绩效改善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中,股权集中度对绩效改善存在线性正效应,但是应该注意到,与股权集中度相关的这两个正效应的估计系数值都明显小于对应估计模型中与股权集中度相关的负效应的系数值。这意味着,尽管一定程度的股权集中即大股东的存在,能够承担起对管理层的监督职能,从而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并且企业规模越大,大股东的监督行为也能相应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然而,大股东凭借其对公司决策、资源的控制权,侵占并购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私利动机更为强烈。尤其是股权集中度与物质资本要素的强交互负效应表明,大股东主要通过掏空并购企业的物质资源的方式损害并购公司的利益。比如大股东主导并购公司利用财务资源进行关联并购,用“优质资产”置换“劣质资产”,从而获取控制权私利。
因此,要实现预期的并购价值增值,并购方就要注重在并购决策前对自身智力资本、物质资本要素进行培育,合理配置多元化的资本要素,以期形成企业资源的均衡发展。在并购整合期,并购方要善于运用不同资源要素应对各种整合冲突,有效推动智力资本要素间的互动价值创造机制。同时,并购方还迫切需要建立较为完善的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抑制大股东对公司资源的掏空行为。
注释:
① 盈利能力指标包括净资产收益率、资产净利率、销售净利率、销售成本率、销售期间费用率;成长能力指标包括每股收益增长率、营业收入增长率、营业利润增长率、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营运能力指标包括存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应付账款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偿债能力指标包括股东权益比率、有形净值债务率、流动比率、现金流动负债比、利息保障倍数。
[1]Penrose,E.T.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M].New York:John Wiley,1959.
[2]Wernerfelt,B.A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84,(2):171—180.
[3]Bontis,N.Intellectual Capital:An Exploratory Study that Develops Measures and Models[J].Management Decision,1998,(2):63—76.
[4]Gupta,O.,Roos,G.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hrough an Intellectual Capita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2001,(3):297—309.
[5]Bryson,J.Managing HRM Risk in a Merger[J].Employee Relations,2003,(1):14—30.
[6]Papadakis,V.M.The Role of Broader Context and the Communication Program in Merger and Acquisition Implementation Success[J].Management Decision,2005,(2):236—255.
[7]Lin,B.W.,Hung,S.C.,Li,P.C.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s a Human Resource Strategy:Evidence from US Banking Firm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power,2006,(2):126—142.
[8]高良谋.并购后整合管理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3,(12):107—114.
[9]傅传锐.中国上市公司智力资本对并购绩效的影响[J].亚太经济,2011,(3):71—75.
[10]李增泉,余谦,王晓坤.掏空、支持与并购重组——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05,(1):95—105.
[11]Hastie,T.,Tibshirani,R.,Friedman,J.The Elements of Statistical Learning:Data Mining,Inference,and Prediction[M].New York:Springer-Verlag,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