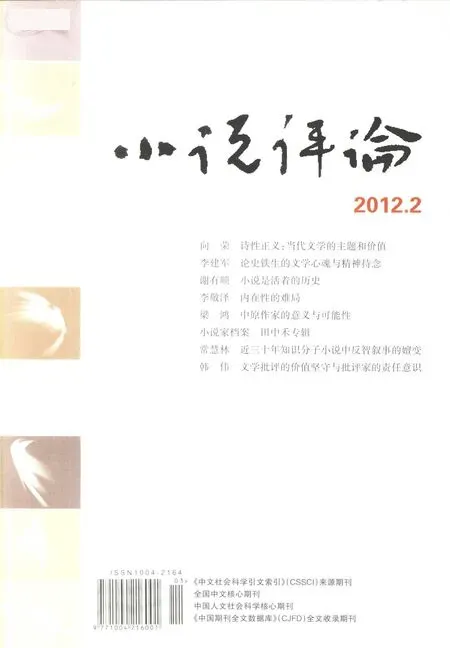现代人的抗争——评《白孔雀》的象征意义
赵春华
作为D.H.劳伦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白孔雀》可以被看成一部练笔之作,虽然其中不乏青涩之感,但该小说或许也可被视为引出之后一系列伟大作品的一个序曲——从《白孔雀》开始,作者就开始意识到现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困惑和灾难,作者也由此展开了探寻理想人际关系的小说主题。本文拟在探讨小说的主体象征——白孔雀,以说明小说家意在抨击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和人性的摧残和他志在寻找理想的人际关系这一贯穿其创作生涯的毕生主题。
一、白孔雀——贯穿全文的主体象征
《白孔雀》呈现了女主人翁莱蒂与乔治和莱斯利的三角关系,作为小说家一生创作主题探求的开始,故事在控诉工业文明异化性质的同时,也反映了现代人在自然与文明,灵魂与肉体之间的困惑与挣扎。小说中,莱蒂的自我反叛让她因为屈从于社会地位拒绝了真心爱恋的自然之子乔治,而选择代表文明的煤矿主莱斯利。正因为莱蒂的选择,这三个人物或直接,或间接地遭到毁灭。
正如小说题目所指,白孔雀作为作品的首要象征,它是对自然和生命的一股毁灭性力量。“在庄园后屋,一只孔雀突然惊起,拍打着翅膀,飞到一个古旧的弯腰天使颈上,……孔雀弯下它娇媚的颈项四处张望。然后它抬起头鸣叫,这叫声撕裂着暮色中黑黝黝的殿堂,那年深月久的野草似乎也被惊起”,也惊扰了“下面被窒息的报春花和紫罗兰”。这个废弃的教堂弥漫着硫磺和死亡的气息。当安纳贝儿吓跑白孔雀,发现它在天使头上排便时,他也从中看到前妻那种毁灭生命的虚荣心。正基于此,有些文学评论家简单地断言小说的象征就是女性的虚荣心对男性生活的毁灭。而事实上,小说还通过白孔雀给出了另一个更深层次的象征意义——人类文明异化并摧毁了原始的生命力。这里,代表原始生命力的乔治被代表人类文明的莱蒂毁灭,[1]而莱蒂被工业文明异化的同时,也戕害了自然本能和原始的生命力量。
小说中,随着白孔雀这一象征戏剧性地植入主人翁莱蒂,我们可在多处的描写中将她与白孔雀联系起来——莱蒂的手,肩,脸以及胸部被描写成白色;她写给西维尔的信,她出现在莱斯利和乔治面前时都被描写成了白孔雀的形象。
她笑吟吟地转身,面对着两个男人,让大衣从雪白的肩膀上滑下去,那一道孔雀蓝的光辉丝光闪闪,华丽眩目,落到大沙发的扶手上。她站在那里,雪白的手搁在孔雀蓝的大衣上。[2]
白色本身也常常跟死亡联系在一起,因此,小说中的白孔雀也象征着对生命力量的否定。小说中多处出现死亡的意象,如被石头打得肋骨外露,抽搐而死的狗,凋谢枯死的花,以及被滚石砸死的安纳贝尔。而作为白孔雀的象征,莱蒂身上也随时烙上了死亡的意象[3]。她宿命地认为,“今生今世,你在开花之前必须吃苦。当死亡刚刚接触到一株植物之时,它就迫使其产生开花吐艳的激情。你奇怪我怎么触摸过死亡;你不知道。这个家里总有种死亡的感觉,我相信,在我出生之前妈妈是恨爸爸的。因此,我还没出世,她血管中的死亡就传给了我。”白色的莱蒂象征着她对生命的否定态度,而就是莱蒂这只白孔雀向乔治和莱斯利的生活施加了毁灭性的力量。通过宣布跟莱斯利订婚她拒绝了自己本能爱慕的乔治,莱蒂的变心使乔治失去生命主干而趋向死亡;而莱斯利不但在车祸中差点死去,婚后还对她极度依赖。的确,这是一只“不祥的白孔雀,她象征着文明异化的力量对原始生命力的扼杀”。[3]小说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象征物——树,它象征了乔治的悲剧人生。在小说开头,乔治身体健壮,心情愉悦,这时我们看到的是,“果园里,树木长得枝缠叶绕,气派森森。”这里传达给读者的是一个如纯净的大自然般健硕成长着的自然之子的形象。而小说结尾,天天以酒来麻痹自己的乔治最终患上震颤性谵妄和肝硬化,这时的他就像一棵“正在倾倒的树,木质变得疏松,颜色变得暗淡,正在朽烂,滋长着冷湿的小菌。”任凭夕阳的余晖从他眼前晃动,他也无动于衷。此时的乔治无异于一具行尸走肉,跟之前那个体魄健壮,充满朝气的青年判若两人。两处通过树这一象征物表达了乔治的内心变化,展示了这个青年农民追求现代文明反被文明揶揄的悲剧命运。
二、由白孔雀传达的悲剧色彩——小说人物的命运
纵观劳伦斯的作品,我们都可以看出小说家试图揭示工业文明对美丽大自然的破坏,同时更控诉它对人类自然本性的压抑和扭曲。[4]在小说《白孔雀》中,通过主体象征白孔雀,作者在表现如白孔雀般虚荣的女人对男性原始力量毁灭的同时,也抨击了罪恶的工业文明对人性的戕害,其中乔治和莱蒂就是典型的例子。
1、乔治的毁灭:从一个生气勃勃的健壮青年堕落为终日与酒为伍的酒鬼
小说开头,青年农民乔治是个与自然贴近,未受机器文明污染的自然之子;他体格匀称,四肢健壮,天生的漂亮身体,“好像是个巨大的生命体”。他是“按照自己创造的生命节奏生活的生命之主”,[5]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他遵从自然本能的生命力量。然而,为了得到莱蒂的爱,乔治渴慕文明。他努力学习有关植物学,心理学,化学,诗歌,哲学以及关于生命,两性和生命起源的知识,因此受到文明的启蒙。可是莱蒂却选择了煤矿主莱斯利,把乔治撇在一边。心灰意冷的乔治选择了跟自己层次相当的表妹梅格结婚。两人婚姻初期生活平静:梅格经营酒馆,乔治致力于自己的事业。后来他选择了政治,在辩论中总能战胜莱斯利,而看到莱蒂总是支持莱斯利,他又逐渐脱离了政治活动。为了填补空虚和失落,乔治开始终日以酒来麻痹自己,甚至有时喝得烂醉回家。他认为梅格只爱孩子,不无嫉妒地说道,“梅格喜欢孩子甚于对我的感情”。久而久之,生活对他来说就是一桩“漫无目的,愚蠢至极的差事”,最终乔治自我毁灭,终究成为一名虚无主义者。
小说结尾,乔治患上了震颤性谵妄和肝硬化;跟几年前那个充满生气的乔治比起来,现在的他完全是一具行将就木的臭皮囊。虽然还处在壮年时期,但无任何生气,剩下的只有死亡的气息。就这样,原本生机勃勃的自然人乔治堕落成为异化的酒鬼,这就是现代工业文明和自然格格不入的悲剧,而乔治也成了自然和文明,感性与理性博弈的牺牲品。
2、莱蒂的命运:摧毁了乔治和莱斯利,也饱尝了失败
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的莱蒂面临两个选择:她自然本能地爱恋乔治,但又无法放弃富有的莱斯利。结果是,她在灵与肉之间痛苦地挣扎;因为对于莱蒂而言,乔治简单朴实,接近自然,他是跟“血性意识”紧密相连的“原始人”。这让莱蒂怀念过去简单的社会,人们随着宇宙的节拍生活,按照他们的血性意识行事,而远离现代文明的玷污。然而,虽然怀念“古老的传统”,莱蒂还是为了追随世俗观念而违背自己的本能:她选择了文明人莱斯利。她的最终选择是文明异化的结果,她对自然本能的压抑不仅造成了乔治和莱斯利的悲剧,同时也导致了自己痛苦的婚姻生活。可以说,莱蒂就是那只破坏男性力量的白孔雀——她让他们要么自我毁灭,要么对女人惟命是从,俯首帖耳。乔治抱怨莱蒂“唤醒了他的生命”,但最后又把他撇在一边。虽然莱斯利对莱蒂必恭必敬,但婚后的莱斯利却变成了这样的丈夫:“在他有空时就挺喜欢她,在他没时间时,就心安里得地忘了她。”
在摧毁男性生命力的过程中,莱蒂也经历着自己的不幸婚姻。表面上一切看似圆满——他们有一对双胞胎,莱斯利的社会地位也在不断上升,莱蒂好像拥有了一切。然而,莱斯利就像一个傀儡,完全听从莱蒂的吩咐。对于莱蒂而言,她放弃了诗人的梦想;她写信向“我”倾诉她的不满,告诉“我”她的生活整个就是“空洞的,无用的”。虽然表现得充满精力和激情,但莱蒂终日沉沦在日常琐事中,不得不忍受生活中那些“毫无价值,枯燥乏味”的东西。现在的她不再对自己负责,她的内心充满空虚,孤独和乏味。就这样,莱蒂非人性地压抑了自己本能的渴求,向平凡生活和传统观念做出了“妥协”。[6]莱蒂这只白孔雀在毁灭男性力量的同时,也扼杀了自己的原始本能和生命力。
三、第一个典型的劳伦斯式人物[7],安纳贝尔道出小说家向往和谐关系的渴求
虽然只是小说中的一个次要人物,但安纳贝儿的故事点出了小说的主题,揭示了孤独的个人和异化的工业文明之间的抗争。安纳贝尔有文化,有知识,他诅咒所有的文明形式,认为所有的文明都是“涂了鲜艳色彩的霉菌”。他与前妻克里斯塔贝尔小姐的经历再次让我们想起了白孔雀的象征意义,因为克里斯塔贝尔同样也唤醒了安纳贝尔的情感,但拒绝与他生养孩子。她喜欢安纳贝尔,但又居高临下地把他当作“希腊雕像”来欣赏。安纳贝尔从此意识到这个女人就像白孔雀,虽然外表优雅美丽,但她颐指气使,虚荣自负;这样的女人恐惧本能的生命力,带给男人的只有毁灭。难怪安纳贝尔要这样恶毒地攻击她们,“白孔雀是女人的灵魂——或者说是恶魔的灵魂……女人直到死都是满肚子虚荣,她们只会尖叫,再就是败坏男人”。由此,安纳贝尔主动放弃文明社会,决定隐退到山林做看林人,像一名“高贵的野蛮人”那样生活;他怀揣着这样的座右铭:“不论男人还是女人,做一个好动物吧”,从此在山林里过着“自得其乐的隐居生活”。[8]
跟乔治的自我毁灭和莱蒂的自我束缚比起来,安纳贝尔通过脱离腐朽的工业文明,回归自然,回归纯净而实现了自我;他抵制文明,返璞归真,是一个与现代文明决裂的抗争者。作为渴慕文明反被文明揶揄的乔治的陪衬,安纳贝尔的故事突出深化了现代人在自然和文明之间挣扎这一主题,也揭示了劳伦斯的另一个重要追求:“寻觅理想的生活与完美的人生”。[9]安纳贝尔作为第一个典型的劳伦斯式人物,他就像《查泰来夫人的情人》里的梅勒斯,充满生命力,痛恨虚荣的女人,痛恨异化的工业文明;他敢于修正错误,跟异化的工业文明抗争。虽然安纳贝尔只是劳伦斯探索自然与人类文明和谐关系的一个试验性人物,他开启了作家艺术创作的终极主题——理想主义的个人找寻人间伊甸园;也为后来小说人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白孔雀》作为奠基之作,虽然在艺术方面尚显稚嫩,但它提出了作家艺术创作毕生的主题探索。小说通过白孔雀这一主体象征,表现了白孔雀一类的女人(莱蒂和克里斯塔贝尔小姐)虽然外表纯洁优雅,但她们惧怕自然本能的生命力;她们虽然能激发男子的生命活力,但她们被异化的生命同时也摧毁了男人的原始生命力。男人们(乔治和莱斯利)最后要么自我毁灭,要么俯首帖耳;这就是普通人被现代文明异化的悲剧命运,它将现代人徘徊在自然和工业文明之间的困惑和他们挣扎在自然和文明之间的纠结展现无遗。而安纳贝尔的故事则说明了现代人为争取自由所进行的抗争;他远离异化的文明退隐到山林表现了理想主义的个人寻找人间伊甸园的过程,由此也拉开了作者追求和谐关系的序幕。另外,作为劳伦斯小说艺术发展的序曲,《白孔雀》也为后来小说的人物发展和小说家艺术手法的运用作了铺垫。
[1]徐崇亮,“现代人的悲剧——论劳伦斯的《白孔雀》”[J],《外国文学研究》1(1989):3-8。
[2]D.H.Lawrence,白孔雀 [M],敖莉译,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10:255。
[3]蒋家国,“精神型女人的雏形——试论《白孔雀》中的莱蒂形象”[J],《外国文学研究》2(2003):102-106。
[4]王艳文,“论劳伦斯《白孔雀》中的悲剧意识”[J],《世纪桥》8(2009):39-40。
[5]“Introduction(to The White Peacock)”,Yi Lin Press(Nanjing,1996),xxvii。
[6]David Holbrook,Where D.H.Lawrence was Wrong about Woman,London&Toronto: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1992:58。
[7]克默德著,劳伦斯 [M],胡缨译,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1986:12。
[8]郑达华,“《白孔雀》——劳伦斯哲学探索的起点”[J],《浙江大学学报》9(2001):43-49。
[9]董俊峰 赵春华,“寻找人类‘失落了’的伊甸园—— 论劳伦斯小说主题思想演变”[J],《贵州大学学报》3(199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