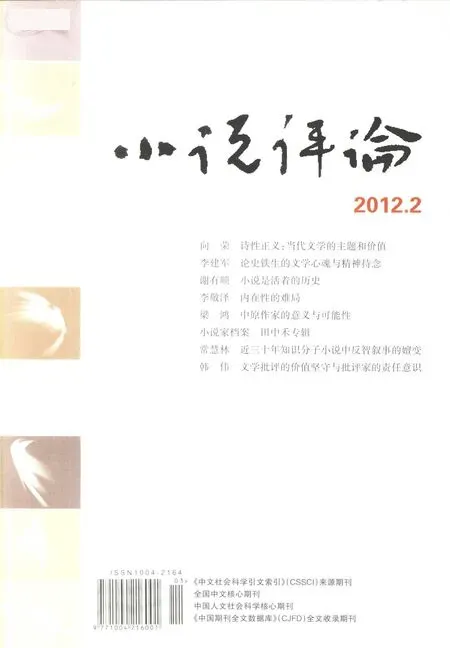新世纪打工小说的城市想象
孔小彬
农民工,来自农村又在城里做工,过往的农村生存环境、生命体验将会与新的城市境遇发生怎样的关联与冲突?这是农民工题材小说必须要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小说是作者想象世界的一种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小说的城市想象具有类同化的倾向。在这些小说里,城市的形象基本上是负面的、否定性的,它不适宜乡下人的“生长”,是充满诱惑的陷阱,甚至是令农民工命丧黄泉的“坟墓”。
一、“城里不长庄稼”
农民工进城无疑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农村经济凋蔽,农民在农村无法获取足够的生活所需;而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重要发展路径的现代化在城市里稳步推进。城市就像一张巨大的吸盘可以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涌入城市做工,于是,农民工的故事开始了。应当说,大多数农民工是充满希望与幻想来到城市的,他们要挣钱,要寻找发展的机会,他们也希望在城里扎下根来。可是,几乎所有的农民工小说都在告诉我们,城里没有适宜农民工生长的土壤。正像一篇小说的标题那样——“城市里不长庄稼”(刘思华,《北京文学》1994年第1期)农民工自始至终都无法融入城市,他们只是城市的局外人,找不到归属感。小说《糖藕娘子》(李肇正,《上海文学》)中杨莲芳温柔美丽,来到上海靠卖糖藕为生。市场管理员陈四光不过是个混混,却总是想着打杨的主意。“陈四光情不自禁就有了联想:从年龄而言,他不具有优势,他要比糖藕娘子大了十几岁,但是,他是上海人,糖藕娘子是乡下人,这身份的优势又足可弥补了。再朝下想,他在上海有房子,那么,娶她就是帮她了。为难的倒是他,讨个乡下老婆,怎么向父母亲戚交代?”这段心理描写再清楚不过地表达了城里人在乡下人面前那种无所不在的优越感了。范小青的《我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当代》2006年第5期)中的农民工胡本来,一次在小偷的手里花二十块钱买了辆自行车,被人怀疑是他偷的。从此以后就有了精神强迫症,总是怀疑自己就是那个做坏事的人,要被警察带走。一有事情就猜想别人在怀疑他,搞得精神紧张,手足无措。这个故事揭示了农民工在城里不受信任,无缘无故受人歧视的境遇。作为城市的主体,城里人对农民工的歧视、鄙视和排斥是农民工对城市没有归属感的重要原因。
在自我意识的深处,农民工不能不产生某种程度的自卑,他们对城市有着深深的隔膜。难怪荆永鸣的小说《陡峭的草帽》(《小说月报》2009年第3期)在结尾会发出这样的慨叹:“是的,无论哪个城市都像是一顶草帽。而且是一顶‘破了边儿’的草帽。聚居在这里的大多是外地人。他们是手工业者、人力车夫、街头小贩等。尽管他们怀着对高楼大厦的向往来到都市,却注定无法进人它陡峭的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包括李平泉在内,他们都是‘草帽’边上的人。”小说里的老程夫妇辛辛苦苦赚了点钱回家去了;聪明、漂亮的女服务员周月同北京人杨罗恋爱,怀孕了又不能结婚,后来还不断受到杨的骚扰,只好离开北京;忠厚老实的王栓在店里做杂工,不小心让老婆怀孕了,也不得不离开这座城市。他们就像是一只只“候鸟”,城市只是临时的迁徙地,而不是故乡,因而终有一天会飞走的。
二、充满诱惑的陷阱
如果说徘徊在城乡之间的找不到归属感的农民工还只是自我迷失的话,不少农民工小说文本描绘了农民工在城市诱惑下陷落的值得悲悯的图景。城市的诱惑主要是来自金钱的、物质的层面,可一旦进入城市,就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纯朴而完整的自我了,它会让你永远背上耻辱的十字架,永远摆脱不了遭人鄙薄、唾弃的结局。巴桥的《阿瑶》(《钟山》2003年第4期)中的阿瑶到广州做妓女,这是世界上最低贱的职业。这个在陪客人的时候还不乏幽默感,总是要逗逗客人的姑娘,似乎看得很开。然而,漫长的皮肉生涯,让她经历了很多不堪回首的事情。阿瑶虽然也赚了一点小钱,可她做人的尊严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被践踏,纵使她有强大的内心世界,也经不起这样一点一点地打击。一次,她要好的朋友,也是同事小群同男朋友木头吵架,为的是小群被木头的手下嫖了。二人和解的方式是出卖阿瑶,小群交出了阿瑶出租屋的钥匙。阿瑶简直绝望了,最后,“阿瑶动了动刚才挣扎时扭到的脖子,说,木头,戴个套吧。”到此时她做人的尊严彻底被摧毁了,她接受了这个非常残忍的现实,她的未来会走向彻底沉沦吗?《泥鳅》(尤凤伟,《当代》2002年第3期)里乡下来的国瑞单纯善良,长得酷似周润发,在吴姐的介绍下认识了玉姐,并做了玉姐的情人。这玉姐大有来头,是省长的儿媳。通过玉姐,国瑞认识了她的丈夫“三阿哥”。“三阿哥”似乎对他很好,让国瑞做他旗下一公司的老总。然而,这只不过是个幌子,是个巨大的陷阱。该公司和国瑞成为“三阿哥”用来权钱交易、洗黑钱的工具。最后公司出事,国瑞成了替罪羊,被判死刑,而且毫无挽救的可能。小说里描述的泥鳅煮豆腐这道菜可以说是小说的核心意象,当四周的水温慢慢变热,泥鳅钻入凉凉的豆腐中,以为是个好的去处,最终却难逃死亡的命运,一条条死在豆腐里,成了主人的美味。在作者看来,国瑞们不正像这些泥鳅吗?
农民工小说中还经常出现这样的故事,一些在建筑工地从事辛勤劳动的农民工,常常受到拿不到工钱的困扰,先前的许诺不过是一个个骗局。龙懋勤的《本是同根生》(《当代》2007年第5期)中的幺舅是个农民工的小老板,“我”没考上大学投奔他,进而有机会了解到幺舅发财的法门。他承包工程,招揽农民工,是个中间人,从大老板那领到钱又向农民工谎称没得到。有时也自导自演,怂恿农民工闹事,借助全社会对农民工的同情向大老板施压,而领到的钱并不全额发给农民工,而是大量截留在幺舅处。农民工上当受骗却毫不知情。王祥夫的《一丝不挂》(《花城》2004年第4期)讲述打工者“阿拉伯”和他的哥哥向老板复仇的故事。三年前,包工头“年轻老板”拖欠他们的工钱,让他们白白干了一年的活。“年轻老板”也假装破了产,开出租车。最终还是被兄弟俩寻到,兄弟俩用刀子逼“年轻老板”脱得一丝不挂,“不要你的命,就是想让你也光一回”。还有一些农民工小说讲述单纯的农民工被骗到某地从事强迫劳动,不仅拿不到工钱,还失去人身自由。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罗伟章的《故乡在远方》、刘庆邦的《卧底》等小说对此都有深刻的揭示。对于这些老实憨厚、缺乏社会经验的农民工来说,城市似乎处处布满了充满诱惑的陷阱,一不小心就会陷落进去,难以翻身。
三、城市——农民工的“墓地”
农民工小说热衷于死亡叙事,死在城里是许多农民工小说的共同结局。这也许是一种策略性的城市想象,城市——“墓地”,这样的城市想象可能是基于作者强烈的为农民工代言的需要,他要将农民工的现实处境写到极端。这就给农民工小说的城市想象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陈应松的《太平狗》(《人民文学》2005年第10期)讲述来自神农架的山民程大种到汉口打工,他的赶山狗太平紧随着他,无底怎样暴打,依然不离不弃。实际上,这条叫做太平的狗随主人来到城里,它的命运就同主人一样九死一生。在这个悲惨的故事中,城市是作为万恶的形象出现的,人情冷漠,充满黑暗与暴力。程大种入城,姑妈不肯收留,工地工作苦累而低贱,没有人道。后被拐骗到一个严重环境污染的黑厂强迫劳动,失去人身自由,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太平狗脱离险境,来解救它的主人,终未成功。最后,主人死了,太平狗只身返回神农架故乡。贾平凹的《高兴》写出了乡下人在城里的备受排挤和鄙视:“拾破烂却是世界上最难受的工作,它说话少,虽然五道巷至十道巷的人差不多都认识我,也和我说话,但那是在为所卖的破烂和我讨价还价,或者他们闲下来偶尔拿我取乐,更多的时候没有人理你,你明明看他是认识你的……你打老远就给他笑,打招呼,他却视而不见就走过去了,好像你走过街巷就是街巷风刮过来的一片树叶一片纸,你蹲在路边就是路边一块石墩一根树桩。”这还不算什么,城市还是吞噬乡下人生命的妖怪。小说中的五富善良诚实又勤劳,他留恋家乡的田野、思念家里的老婆,经常萌生返乡的冲动,最终却惨死在工地上,成了这个城市的“一个游荡的野鬼”。
农民工小说讲述了一个个这样的残忍的没有人道的故事,在作者们笔下,城市就像是一个冷血的悲惨世界。残雪的小说《民工团》,工头三点过五分就叫醒农民工去扛二百多斤的水泥包,民工掉进石灰池就回家等死,掉下脚手架就当场毙命。陈应松的《归来·人瑞》中,去城里打工的喜旺从高楼上掉下来,摔死了。李师江的《廊桥遗梦之民工版》中的工友最终没能享受到发廊女的按摩就被凝固在第九个桥墩里了。罗伟章《故乡在远方》里的石匠陈贵春到城里打工处处遇挫。最后走投无路成了抢匪,第一次抢一个大个子男人并把人打死了,然后是落入法网,被枪决。周崇贤的《杀狗——悲情城市系列》(《当代》2009年第1期)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这个华丽的南方城市,就像是一个热闹的灵堂。谁死了,谁还活着?又是谁在祭奠谁?谁在为谁哭泣?不知道。也许永远不会有答案。又或者,打有城市那天起,所有的人都死了,只是没有人知道自己早就死了,大家都沉浸在城市华丽的热闹之中,都以为,是在赴一场宏大的盛宴。没有人知道,人们之所以从四面八方向城市聚集,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已经死亡,或正在死去。他们在城市里,编织一个又一个的梦想,只不过是在为自己、为这个城市的明天,举行一场盛大的葬礼。”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中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趋势。农民工的城市生活、体验以及最终的结局可能是千差万别、千姿百态的,但是,近年来农民工小说的城市想象却往往是概念化的缺乏细致分析,甚至简单地将城市妖魔化。它们往往强化城市的排斥性而忽略城市的包容性,将城市想象成人性异化的场域。这样的城市想象自然是出于作家批判现实的策略性的考虑,但它所造成的客观效果是城市的负面性被人为地放大,而城市复杂多样的本来面目则被简化后的图景遮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