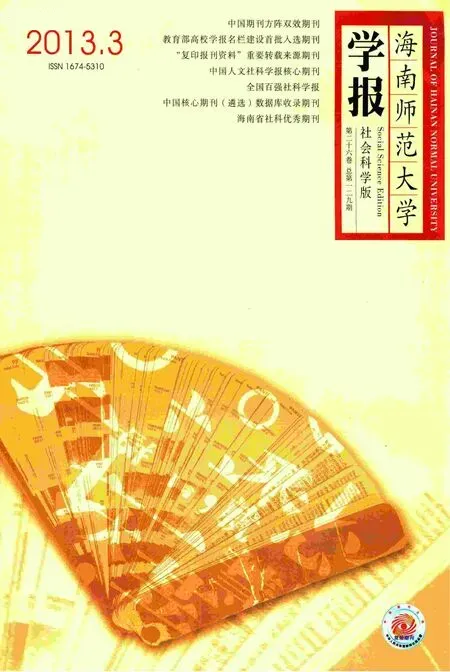悲伤之塔——对沈从文《边城》的另一种解读
张映晖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艺术学院,湖北 襄阳441050)
沟通障碍是人类永恒的悲剧和苦难之根源,因此对命运不可知的喟叹和对人际交流障碍的无奈,成为很多杰出文学作品热衷的命题。
沈从文的《边城》看似不经意却近乎完美地表达了这一命题。如果只是表现湘西的明山秀水和小儿女的朦胧恋情,也不能使《边城》成为现当代文学史上最具魅力的小说之一,是其间文字中潜伏着的隐忧和悲剧意识使得作品有了向更深处开掘和阐释的空间。小说中善良的老艄公在经历了女儿殉情的伤痛和孙女情事的种种阻碍及无端地被误解后,在一个雷雨交加之夜随着屋前白塔的倒塌郁郁而终。这是发生在东方的一个叫茶峒地方的忧伤故事。
东方小说《边城》里白塔的倒塌让我们联想到了另一个源于西方的与塔相关的故事,故事里的塔也倒塌了,它的名字叫“巴别塔”。《圣经》记载:初始人类说着同一种语言,沟通没有障碍,人类为了昭示智慧和力量,想要建一座通往天堂的“巴别塔”(babel),上帝降临视察,认为人类过于自信和团结,一旦完成计划将能为所欲为,便决定变乱人们的口音和语言,最终人类的难以沟通造成高塔的坍塌,通天梦成为泡影。巴别塔的隐喻成为人类命运之谶,尤其在经济与文化全球化大一统的今天,人类心灵的距离却在物质的富足下日渐疏远。墨西哥导演冈萨雷斯的获奖影片《通天塔》就借用了这段隐喻,分别以几个看似独立而又彼此关联的故事,来表现了一场发生在不同种族之间、同一家庭内部的不同成员之间的沟通悲剧,描述了被分散的人类在现代社会的沟通障碍。影片的主题被无限放大,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制度、民族与民族这三个维度之间设置了多重可能,共同探讨现代社会沟通障碍的大命题——巴别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耶和华变乱了人类的语言,至使人们不能齐心协力,而沟通不畅造成情感和理解上的缺失,矛盾和悲剧由此产生。
让我们再回到沈从文这里。如果按照知人论世的路子来分析开掘,他作品里沟通障碍这一充满悲剧意识的命题可能源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他的成长经历:“沈从文的生活,可说与那个当时正受西方精神和物质影响下的中国毫无关系……父亲在他童年的大部分时间中都驻守在北京,因此对他也疏于管教。他常常逃课,在家乡附近游山玩水,也因此看尽了人生和自然百态。”[1]135青少年时期曾有过一段混迹江湖的传奇经历,目睹了太多的暴力和杀戮。“个体生命的存在在这里太微乎其微了,太不堪一击了。稍稍一不留意,便不知怎的丢了去—— 因为在那个交织着野蛮、愚昧与权横的混乱时空中,个人的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生与死全都是那么突然。”[2]这段岁月,对沈从文后来的写作生活非常重要,不但因为他可以从此获得不少见识和刺激性的经验,而且,最重要的是,使他增加了对历史感和事实的认识。”[1]136二是与这个拥有高雅纯正的文学趣味和善良朴讷情怀的中国现代文人在现实中遭遇到的诸多被误读被误解有关。沈从文的一生受冷遇、被误解也归结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个体的沈从文和当时部分知名文人个体之间的沟通障碍——沈从文曾因自己创作的《丁玲传》(本意在声援丁玲)中显露的笔墨趣味和两性之间不同的观念、视角而被丁玲误解责难,以至于引发了文学史上著名的“丁沈之争”,彼此间的误解直到他们去世也未能消除;又因一位女性朋友写给鲁迅的求援信酷似他的字体而被鲁迅误解;之后也曾饱受郭沫若的政治攻击、刘文典有失公允的蔑视,生性腼腆善良的沈从文无力辩驳,误解终未消弭,为此他倍感压抑。另一层面是因追求雅正纯真的文学趣味而与当时普罗受众的阅读品位之间产生疏离,这是创作个体和阅读受众之间的沟通障碍,以至于这位自称“乡下人”的文人一心躲在自己苦心经营的文学“希腊小庙”和博物馆里,远离各种文学和政治派别的纷争。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沈从文的墓碑文和他在《边城》里设置的种种沟通障碍让深爱着作家和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的读者们不断地叹惋。我们相信每一个赤诚忠厚的读者都希望小说里的翠翠和傩送佳偶天成,但是命运就是这样的不可知,一桩理应很完美的情事和婚事生生地被断送,作梗者就是困扰人类的那个与生俱来亦永恒相伴的沟通命题。笔者试着以文本细读的方式从故事发生的机理中整理出这些沟通和交流的障碍。
一 沟通障碍与悲剧的宿命化解释
沟通的障碍永恒常在,无关语言,这是人类的宿命,即使至亲亦无处逃遁。影片《通天塔》中的无论是身处荒蛮落后地区的摩洛哥父子之间,还是蜗居摩登现代都市的日本父女之间无一例外地都在用自己家庭的悲剧诠释和演绎着这一宿命。家人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说着同一种语言,却难以实现真正的沟通,心灵极度隔膜,悲剧或早或迟都会以某种方式发生,故事的基调因此极度阴冷。相较之下,小说《边城》故事的调子要温暖柔和的多,毕竟作者的宗旨是用自己的作品铸造一座真善美的希腊小庙。《边城》的阅读体验对多数读者而言是美好的,但是悲戚的元素也并不匮乏。沈从文善良敏感的个性、幼年的成长体验和成人后的都市经历,使得作品里的悲剧意识如影随形,或隐或现。孤女翠翠与爷爷相依为命,感情至深至纯,爷爷慈爱宽容,小心地呵护着孙女的幸福;孙女乖巧懂事,依恋爷爷也总是担心爷爷的离去。但因为命运难以把握的偶然性,使祖孙两代人在翠翠的姻缘一事上出现了沟通障碍。翠翠喜欢傩送,但出于少女的羞赧、对感情的困惑和传统的束缚(隐形的束缚),从未向爷爷吐露心事。爷爷沉浸在家世、人品都不错的大老及其父亲顺顺团总极具诚意的提亲带来的喜悦里,沉浸在孙女就要摆脱其母亲的悲剧命运的欣慰里,而忽略了孙女真正的情愫所系和内心的隐秘。
祖父说:“大老也很好。这一家人都好!”翠翠说:“一家人都好,你认识他们一家人吗?”祖父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所在,因为今天太高兴一点。[3]63
祖父明显没听出翠翠的暗示!祖孙俩行船在河上。
祖父不说什么,还是唱着,两人皆记顺顺家二老的船正在青浪滩过节,但谁也不明白另外一个人的记忆所止处。[3]63
两人都想到了二老,情感所系却完全是南辕北辙,翠翠是思念远方的二老,爷爷却由远方的二老联想到提亲的大老。
翠翠对二老的情感与日俱增。
她从这分稳秘里,常常得到又惊又喜的兴奋。一点儿不可知的未来,摇撼她的情感极厉害,她无从完全把那种痴处不让祖父知道。祖父呢,可以说一切都知道了的。但事实上他又却是个一无所知的人。[3]94
翠翠因无法言说的感情困扰而哭泣,爷爷不知道那哭泣的缘由,也并不追问。爷爷因伤情的往事和对翠翠的命运担忧而落泪,年幼的翠翠也自然无法解得,实际上,祖孙俩都有自己无法启齿的隐秘,而且两者相互关联,又都不愿也不能与外人诉说,从这个意义上讲,爷爷和翠翠都是孤独无助的。沟通障碍和不断地误读使这两个可亲可爱的一老一小承受了不该有的苦痛。
翠翠不作声,心中只想哭,可是也无理由可哭。祖父再说下去,便引到死去了的母亲来了。老人说了一阵,沉默了。翠翠悄悄把头撂过一些,祖父眼中业已酿了一汪眼泪。翠翠又惊又怕怯生生的说:“爷爷,你怎么的?”祖父不作声,用大手掌擦着眼睛,小孩子似的咕咕笑着,跳上岸跑回家中去了。[3]80
类似的沟通障碍在文中不断地被呈现和被强调,如后文中爷爷先后两次很民主地问询翠翠的想法都因翠翠的不肯明说而搁置。
可是那做媒的不久又来探口气了,依然是同从前一样,祖父把事情成否全推到翠翠身上去,打发了媒人上路。回头又同翠翠谈了一次,也依然不得结果。[3]81
等老人最终明了孙女的情意之后,各种偶然和误会已然渐趋累积,悲剧已不可避免——“命运感是翠翠爱情的最大阻力,构成了她命运悲剧的深刻内涵。”[4]人类自身的局限、命运的难以掌控、无障碍沟通的难以实现,是爷爷和翠翠的宿命,是湘西人的宿命,也是人类的宿命。
二 沟通障碍与生命的主体性匮乏
翠翠和二老傩送都是沈从文带着很深的感情和人文理想塑造的极具灵气和活力的人物,读者从他们的第一次相遇就能看出彼此间的情意。湘西淳朴民风濡染下的两个自然之子,竟也不断地滋生了沟通不畅的问题。我们当然可以笼统地解释为宿命,但细读作品,他们两人间的障碍更多地源于原始生命的主体性匮乏。沈从文把翠翠塑造成为一只风日里长养着的健康灵秀的小兽物,一个天然美好的生命。边城的淳朴民风之表难掩农耕文化的蒙昧落后之实。这种蒙昧表现在湘西人对自己自由生命的浑然和翠翠对自己青春萌动苏醒的主体性把握匮乏,她的生命意识和情感自觉处在蒙昧和懵懂状态,没有人教会她去表达和传递爱的信息,更没有能力去处理和操纵眼前的这段姻缘。生命的主体性匮乏使沟通障碍成为必然。他们从第一次见面起就相互吸引,也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就误会丛生,彼此无法得到准确的情意回馈。二老热诚邀请翠翠去他家的看台,翠翠却误以为他轻薄,翠翠借黄狗骂二老,却被二老误解为是翠翠的好意。生活中就是这样充斥着如此多的小误会,不断地减弱销蚀着人类对美好的感受度和体验度。
第二次的误会出现在两年后的端午节,翠翠被邀请到顺顺家看龙舟赛,无意中听到两个妇人议论到二老今天的表现全为了看台上的一个黄花姑娘,旁观者都知道这无疑说的是摆渡的翠翠,可当局者迷——“谁是激动二老的黄花姑娘?听到这个,翠翠心中不免有点儿乱。”[3]78翠翠或者隐隐地觉得是自己,却因为碾坊家的女儿的缘故心存疑虑。因为无法确认二老对自己的感情,在其后爷爷的提亲中,她坚持不发表任何意见。主体性匮乏再次使美好姻缘渐行渐远。
二老这边,对翠翠是否真的对自己有意也并未从对方那里获得过确认。
老船夫……情不自禁的高声叫着翠翠,要她下溪边来。可是,不知翠翠是故意不从屋里出来,还是到别处去了,许久还不见到翠翠的影子,也不闻这个女孩子的声音。二老等了一会,看看老船夫那副神气,一句话不说,便微笑着,大踏步同一个挑担粉条白糖货物的脚夫走去了。[3]93
二老傩送对翠翠情感的误读再次发生:摆渡的翠翠见到对面岸上等候渡船的二老“大吃一惊,同小兽物见到猎人一样,回头便向山竹林里跑掉了。但那两个在溪边的人,听到脚步响时,一转身,也就看明白这件事情了。”[3]95翠翠因为内心慌乱而不敢面对那个令自己魂牵梦绕的少年,少年看到的却是心仪的少女不愿接近自己。“翠翠向竹林里跑去,老船夫半天还不下船,这件事从傩送二老看来,前途显然有点不利。”[3]96误会就这样渐渐地深了下去,故事的发展也渐渐偏离读者的心理期待。我们做个假设,如果翠翠在傩送那里有过一次明确的示爱和相许的暗示,痴情的少年也定不会在小说的最后选择黯然离去。
三 沟通障碍与人性的误读
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始终与都市文明保持着批判性的疏离,作为比照,他的湘西系列多表现边城人性的美善,《边城》更是弥漫着牧歌般的氛围,摆渡的爷爷古道热肠,质朴善良,与众乡里保持着一种真诚、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但在孙女的婚事处理上因为太过谨慎,处理方式上在外界看来有些流于“机巧”,导致原本的善意遭遇误解误读,也间接地构成了沟通障碍的成因。
读《边城》最难以释怀的是爷爷的孤独隐痛和被二老的误读。爷爷最初没读懂翠翠的心事,在大老提亲后,心里高兴,但因翠翠又没明确地表明态度,加之有女儿从前的伤心事作为前车之鉴,导致老人面对媒人和顺顺的提亲不明确肯定也并不拒绝,致使大老对翠翠用情愈深。一方面老人又想考察大老的真心,就提出让大老走马路和车路的选择,让翠翠并不喜欢的大老始终对翠翠抱有幻想。这些都是爷爷其实是出于善意的小小“曲折”。大老在得知真相后很受打击,恰好赶上了出行遇难,爷爷很自然地被二老误解。
大老死后,爷爷也终于明白了翠翠心里一直装的是二老,于是试图护佑和成全孙女的痴情:
“二老,我家翠翠说,五月里有天晚上,做了个梦……她梦得古怪,说在梦中被一个人的歌声浮起来,上悬岩摘了一把虎耳草!”老船夫原意只是想把事情弄明白一点,但一起始自己叙述这段事情时,方法上就有了错处,因此反被二老误会了。[3]92二老甚至因哥哥的死对老人心生怨恨。“老家伙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3]93
这无疑是天大的误解,种种伤痛、忧虑和误解集结在一处,终于超过了这个善良老人内心所能承受的极限,赫然长逝于一个雷雨之夜。
白塔业已坍倒,大堆砖石极凌乱的摊在那儿。翠翠吓慌得不知所措,只锐声叫她的祖父。祖父不起身,也不答应,就赶回家里去,到得祖父床边摇了祖父许久,祖父还不作声。原来这个老年人在雷雨将息时已死去了。[3]99
《边城》里的白塔倒塌了,《圣经》里的巴别塔也坍塌了,这是沟通的悲剧,是每个人心头都可能遭遇到的伤痛。我们为《边城》里逝去的爷爷的灵魂安宁祈福,为翠翠的最终幸福祈福,也为《巴别塔》中的不同语言、不同种族的人们祈福。
“怕什么?一切要来的都得来,不必怕!”爷爷对翠翠说。[3]99
[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香港: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
[2]黄庆.存在的无常与无奈——对《边城》“故事悲剧性”因由的阐释[J].河南社会科学,2001(1):111.
[3]沈从文.沈从文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
[4]孙荔.沈从文作品的悲剧意识[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