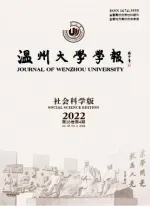“志同道不合”与“志同道合”—— 论合作化小说情爱叙事中的两种主要结构模式
于树军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25)
“十七年”小说在叙事上的模式化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叙事干预的现象也较为突出。而这于无形中强化了潜隐在小说叙事中的意识形态话语。此外,合作化题材小说大都是由一明一暗两条线索交织融合而结构全篇,主线大都集中在了“新人英雄”与落后反动分子之间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通过层层动员的方式带领群众参加互助合作化;副线则围绕“新人英雄”的情爱发展历程来展开叙述。尤其是在合作化小说的情爱叙事中,钳抑生理感性(即儿女情)而推崇政治理性(阶级斗争)恰恰成为了“十七年”合作化小说文本叙事中普遍存在的特质,其模式化、概念化的特点也最能突显出主流话语对文学创作的规约。
一、“志同道不合”的情爱模式
前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著名自叙传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直被视为“红色经典”而广为流传,尤其是为了革命事业而舍弃爱情的主人公形象——“钢铁”战士保尔·柯察金及其彰显出来的“保尔精神”,在当时的前苏联乃至中国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然而,在大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当我们再翻开那部小说时,更能引发人们兴趣点和深思的恐怕不再是保尔的那种“舍身取义”之举,反倒是关于革命与爱欲之间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问题了。
出身贫苦工人阶级的保尔与出身资产阶级、林务官的女儿冬妮娅之间产生了爱恋之情,然而,多年以后,保尔已经成长为了一个有着坚定的无产阶级政治信仰的革命战士。保尔深爱着美丽温柔、爽朗且气质非凡的冬妮娅。而在如何处看待和理情爱和革命这一问题上,保尔与冬妮娅却有着巨大的思想分歧,尽管他认为献身革命根本不必以禁欲、苦行来考验革命意志,可在他看来,自己的身体乃至情爱必须要从属于革命,即使爱情婚姻也无法与革命相提并论。可在冬妮娅看来,爱情完全是属于个人的事情,它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主义”或者自私的成分,她虽然有勇气爱工人阶级出身的保尔,但是她并不爱保尔所追寻的革命理想。与此相反,在保尔的眼中,自己虽然深爱着资产阶级出身的冬妮娅,但使他无法容忍和接受冬妮娅的这种只献身爱情而非革命的“个人主义”或者说个性意识,他因此而认定冬妮娅不是“自己人”,并作出了与之分手的决定。两个人分手的时侯,保尔对冬妮娅说:“你必须跟我们走同样的路。……假如你认为我首先应该是属于你的,然后才是属于党的。但在我这方面,第一是党,其次才是你和别的亲近的人们。”两难之中的保尔最终为了革命理想而舍弃了爱情。
对于保尔与冬妮娅在革命与爱欲之间的分歧,刘小枫有着深刻而又独到的认识,他认为:“革命与爱欲有一个含糊莫辨的共同点:献身。献身是偶在个体身体的位置转移,‘这一个’身体自我被自己投入所欲求的时空位置,重新安顿在纯属自己切身的时间中颠簸的自身。革命与爱欲的献身所向的时空位置,当然不同;但革命与爱欲都要求嘲笑怯儒的献身,这往往让人分辨不清两者的差异。”[1]确实如此,革命“圣徒”保尔一生的最高理想就是为党和革命而献身,其他一切都不可以凌驾于革命之上。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保尔是在献身革命事业中将个人主义的“小我”融入到集体主义的“大我”这一过程中而“炼成”的。“个人主义”完全被淹没在了“集体主义”这一宏大的时代主流话语之中。
毋庸置疑,保尔与冬妮娅的分手说明了一个问题:阶级出身并不会影响两个人之间建立爱情关系,但是,两个人如果存在思想上的分歧而没有共同的理想追求的话,其爱情的结局注定要以失败告终。实际上,“十七年”合作化小说的情爱叙事结构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某种意义上是同质同构的。可以说,“志不同道不合”式的情爱叙事结构在小说合作化小说《创业史》中也有着同样的体现。如果说梁生宝与刘淑良之间是因为热爱并献身合作化事业这一共同目标而结合在一起的话,那么,改霞与梁生宝的分道扬镳则是因为二人对于合作化这一革命事业的观念上的分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对立)所造成的。在合作化小说《创业史》中,改霞与梁生宝起初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美丽能干、思想进步的改霞拒绝了富裕中农郭世富之子中学生郭永茂的求爱,她不为物质财富所诱惑,在她眼中,郭永茂“根本不响应党的号召”,并且还将郭永茂的求爱看作是对自己人格上的侮辱。其实,改霞一直都爱着朴实善良、正直的梁生宝。事实上,两个人的爱情走向破裂的转折点是改霞在村主任郭振山的授意、鼓动下而产生了考工厂的想法之后,考工厂的打算使改霞陷入了痛苦的两难之境。然而,此时的她仍是如过去那样真心地“想和生宝一起搞互助合作……(并)憧憬着同生宝在一个和谐的家庭,共同创造蛤蟆滩的新生活”。尤其是在得知梁生宝怀着豪情壮志要带领群众筹办互助组时,她颇受震撼,内心中更是充满了对梁生宝的钦佩之情,并且还因此“动摇了郭振山授意(自己)考工厂的决心”……应该说,改霞与梁生宝的分手,最主要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郭振山的鼓动,在改霞而言,郭振山是蛤蟆滩最“强有力的人物”,他的话有足够的分量,因为改霞当初解除婚约以及上学读书并且成为村小学团支部委员……这一切都是在郭振山的直接启发鼓励和帮助下才得以实现的。所以,改霞感激、崇拜、信服自己的“引路人”郭振山。在郭振山开导她考工厂之后,改霞的思想骤然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唉!生宝好是好,谁知道蛤蟆滩要几十年才能到社会主义呢?几十年啦!自发势力这么厉害,一个小小的互助组,能掀起多大浪!这样我留在蛤蟆滩,几十年以后,我就是一个该抱孙子的老太婆了。我还是奔城里的社会主义吧。”于是,改霞决定离开梁生宝去考工厂,她不能只做一个给丈夫做饭、缝补衣服、生孩子的家庭主妇。在她看来,一个人——尤其是作为新社会的女性,其价值不仅是为了家庭,而是更应该体现在工作事业上。“对于改霞,搞对象既不是为了吃穿有人管,更不是为了生理上的需要。她是为了一种崭新的愿望——两口子共同创造社会主义”。在她看来,离开生宝去考工厂是正确的,“她觉得她的决定是爱国的、前进的和积极的。”[2]
其实,“奔城里的社会主义”与“奔农村的社会主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美好未来的两种不同的现代性方案。但是,改霞作出的这种选择无疑等于放弃了曾经与梁生宝共同搞互助合作的最初理想,或者说她“背叛”了自己的初衷。而改霞与梁生宝的分道扬镳完全是合作化时期两条路线分歧与斗争所使然。而透过这样的情爱叙事模式,不难看出,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于作者柳青的创作立场以及《创业史》中的情爱叙事的强力规约的痕迹。尽管小说在梁生宝与改霞的情爱叙事中将这一叙事话语隐蔽的很深,可是,经过仔细的分析仍能够从中发现问题的所在。
二、“志同道合”的情爱模式
合作化小说的情爱叙事中带有一定的“才子佳人”传统模式的因子,不过与古典小说的情爱模式有所不同:“才子”和“佳人”在合作化小说中已分别被置换为了“新人英雄”与“积极分子”。可以说,“十七年”合作化小说中这种“女爱男”的情爱模式乃是对“才子佳人”传统模式进行的一种现代性转换,并且在诸多小说文本中普遍地存在。如范灵芝与王玉生(《三里湾》)、盛淑君与陈大春(《山乡巨变》)、刘淑良与梁生宝(《创业史》第二部)、芸芸与王树红(《夏夜》)、贞妮子与吴小正(《在田野上,前进!》)、万春芳与祝永康(《风雷》)、白云英与石林(《太行志》)……等男女主人公形象之间的情爱皆属此种模式。
这些女积极分子皆是思想进步、热爱劳动、积极投身合作化事业的典型代表,她们中有的是合作社的女劳动模范,如刘淑良;有的则是动员宣传合作化的“干将”,如盛淑君、焦淑红;有的则是文化水平较高的回乡女知青,如范灵芝在中学毕业后选择回乡担任民校教师,以减少农村中的文盲的比例……这些女性群体都是农村合作化运动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与此同时,在“新人英雄”形象中,他们大都富有常人所不具备的敏锐的阶级斗争眼光(如梁生宝、刘雨生、萧长春等),勇于与那些反动破坏分子做斗争;要么则是具备一定文化知识或掌握某种专业技术的“农民精英”(如王玉生、任为群、吴小正、石林等)。
“新人英雄”与社会主义新女性的情爱叙事清晰地表明:他们无论是在阶级身份、政治信仰还是革命立场方面都有着一致性,在合作化事业上更是“志同道合”。要而言之,政治立场与道德品质往往是他们爱情选择的最根本的标准。瓦西列夫认为,“爱情(选择)必然受到人置身其中的道德环境的影响:思想、感情、理想、乐趣、价值等等都不同程度上参与生活的这一最隐私的领域的构成。”[3]113-114的确,瓦西列夫的观点为“十七年”合作化小说的情爱叙事特质作出了很好的概括。然而,这种社会主义新女性与“新人英雄”的“志同道合”式的情爱模式,很大程度上乃是意识形态化的产物,他(她)们“……的爱情选择,往往也意味着是一种政治文化选择。”“新人英雄”与积极分子的相爱“通常寄托着作家强烈的政治文化心理与道德理想。”[4]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保尔在身体瘫痪、双目失明后与达雅结为夫妻,不过,保尔并不感到自己对于达雅是一种拖累或者负担,他反而觉得自己与她的结合尤其是对她的思想改造乃是出于一种神圣的革命道义感/使命感,在他看来,帮助达雅提高阶级觉悟并使其成为党的一员便是他的人生价值所在。保尔认为是自己将“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他所参加的革命斗争是“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而这种道德理想主义、殉道精神以及对革命的虔诚狂热的信念在中国的“保尔”们——梁生宝、萧长春等农民“新人英雄”形象的身上其实也都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即便是他们最终接受了进步女性的爱,但却将其视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并没有因为爱情的到来而沉迷于现状或者放弃革命理想,反而是更加坚定了其献身革命事业的信念。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大胆追求中国的“保尔”们的那些社会主义新女性(如盛淑君、焦淑红)也并“不是以一个美貌姑娘身份(来与其)谈恋爱,也不是用自己的娇柔微笑来得到(新人英雄)的爱情;而是以一个同志,一个革命事业的助手,……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同时,让爱情的果实自然而然地生长何成熟……”[5]显然,在他(她)们看来:恋爱绝对不同于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那种庸俗的恋爱,而是一种志同道合的“崇高的恋爱。”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十七年”合作化小说的情爱叙事伦理在于阐明:他们的恋爱完全是建立在政治、革命基础上的,其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发展合作化事业以及与反动破坏分子作斗争的正义之举。爱情与婚姻关系的建立完全是同双方的革命立场、阶级出身、政治信仰等意识形态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这些“志同道合”的情爱叙事中,“新人英雄”梁生宝、刘雨生的情爱叙事是最为复杂且同时也最能体现出政治意识形态对男女情爱婚姻选择的强力干预。应该说,梁生宝与刘淑良彼此之间的爱情选择实乃二人的理想志向的投合所使然。梁生宝第一次与刘淑良见面时,“女方给他的印象既不是简单的‘满意’,又不能说‘不满意’”。他也没有太明确的想法;而刘淑良对梁生宝的印象颇好,只是由于梁生宝的不够热情尤其是一直忙于工作,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任何进展。然而,梁生宝去县里开会时偶遇刘淑良,这一次的偶遇使得梁生宝对刘淑良有了全新而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当他得知刘淑良已经是范村的互助合作代表时,梁生宝“开始从心底里热爱刘淑良了”。那个“机智沉着”“大方正经”“又有心胸”的刘淑良也在梁生宝的眼中开始变得“美丽”了,甚至“连(粗大的)手和脚(此时)都是美的,不仅和她的高身材相调和,而更主要的,和她的内心也相调和着哩”[6]。应该说,梁生宝与徐改霞之间的爱情是属于“情投意合”式的爱情,而与刘淑良的爱情纯粹是“志同道合”式的爱情。前者在一定程度上还带有些许的含情脉脉的意味,而后者则是完全由于二人志愿“奔农村的社会主义”而结合到一起的。而小说之所以设置刘淑良这一女性形象,恐怕其主要意图就是要告诉(更是教育)读者——只有热爱劳动、甘心扎根农村并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一生的女性才能够与梁生宝结相爱并为夫妻。
小说《山乡巨变》中的张桂贞因为模样娇美被人们称为“一枝花”,起初,夫妻感情还算不错,但是对于丈夫刘雨生整天忙于“革命事业”、疏于照顾家庭,她越发不满于生活的困窘,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也因此而逐渐产生了危机,最终她离开了刘雨生。然而,后进妇女盛佳秀在刘雨生的帮助引导下,不仅参加了互助合作化,并与刘雨生组成了新的家庭,还成为了一名劳动能手。张桂贞与刘雨生的离异及盛佳秀与刘雨生的结合,其实同样暗含有主流政治话语的因素在内,当然这也是作者周立波对主流意识形态迎合的一种体现。张桂贞尽管有着苗条纤细的腰和娇美的容貌,但是身材瘦小且好逸恶劳、爱慕虚荣。所以,她与刘雨生的离异实属必然;而相貌平平,但思想经过改造之后而变得进步、能干的盛佳秀似乎更适合刘雨生。瓦西列夫认为:“对选择爱情对象首先发生影响的是对方的社会地位(阶级、阶层、等级)属性。这方面的差异往往会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爱情的障碍。”[3]399的确,《三里湾》中的范灵芝之所以选择王玉生而没有选择马有翼,主要原因就在于马有翼的思想立场不坚定(或许“有翼”成了“右翼”、保守的代名词?),在父母的压力下总是动摇不定,而且连劳动也做不好……经过对王玉生和马有翼二人的“思想行动”以及“家庭”环境等进行全方面的比较衡量后,范灵芝一改对于王玉生文化知识上较为欠缺的顾忌、嫌弃而决定嫁给玉生。另外,小说《山乡巨变》中的积极分子盛淑君拒绝了花言巧语、不务正业、心怀不轨的二流子符贱庚;《艳阳天》中的焦淑红断然拒绝了心术不正、贪图享受并且与反动破坏分子有染的马立本的无理纠缠……看以看出,那些道德败坏、品行不端、思想反动落后的人是不会被女积极分子所认可与接受的。而梁生宝、萧长春、祝永康对于赵素芳、孙桂英以及羊秀英的示好甚至挑逗的严厉拒斥,除了说明“新人英雄”的品行正直外,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这些好逸恶劳、思想落后、道德堕落的女性及其“出身的不洁”使得她们没有“资格”去爱“新人英雄”。
“十七年”合作化小说的情爱叙事无形中传达出了这样的声音:即革命与爱情之间的冲突只能是要么如梁生宝与徐改霞那样因为“志同道不合”而“有花无果”,以分手告终;要么则是如焦淑红与萧长春那样因为“志同道合”而“在革命中产生了恋爱”,爱情与革命一道前行,合二为一……由此可见:“新人英雄”与社会主义新女性之间的爱情是让位于政治和从属于革命事业的,建立在扎根农村、献身合作化事业这一共同的理想志向的爱情与婚姻才具有“合法性”。
三、结 语
需要补充强调的是,有人认为“不管是梁生宝还是萧长春,这些农民英雄人物的性格皆保持‘完整’的状态。所谓‘完整’的状态,便是指革命对萧长春或梁生宝内心世界的‘冲击’,从未导致他们对革命信念的人和疑虑、惶惑或恐慌。”[7]其实,这个判断不够客观而略显有些武断。“新人英雄”们的内心中并不是没有革命与爱情之间的两难选择的性格心理冲突,尽管它无法与苏联的同时期“红色小说”中人物性格心理冲突的深刻程度相提并论,但是,我们要看到,合作化小说叙事中,导致刘雨生、梁生宝的内心矛盾冲突的条件都是足够充分的,而且在他们的意识中,也都曾有过爱情婚姻与革命事业的冲突所带来的焦虑和烦恼,只不过,故事的最后无不是以主人公的“舍小家为大家”而宣告结束,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当时的意识形态话语对于文学创作的干预。
一个易被忽略的问题是:“新人英雄”的情爱、婚姻的“大团圆”结局严重地遮蔽了主人公的性格心理冲突以及由于爱情/婚姻危机所带来的烦恼和不完满。然而,如果从另一角度来看的话,如此的情爱叙事的结局恐怕也是在有意暗示:只要一心一意地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任劳任怨,最终肯定会有所“回报”①革命以及政治意识形态对人的强制与规约往往是与它对革命者的“回报”相辅相成, 当然这种“回报”更多的是指一种精神、荣誉层面的回报.。而这也极大地迎合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民众的普遍心理期待。完全有理由说:“志同道合”式的情爱结构模式与“大团圆”的结局暗含着一种“劝说机制”在内,同时也表明了:思想进步、大公无私而又热爱农村、志愿扎根农村的男女青年才是确保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性这一美好蓝图化为现实的关键所在。
[1] 金宏宇.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300-304.
[2] 柳青. 创业史: 第一部[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0: 242-243.
[3] 基·瓦西列夫. 情爱论[M]. 赵永穆, 范国恩, 陈行慧,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4] 何言宏. 中国书写: 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研究[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210.
[5] 浩然. 艳阳天: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410.
[6] 柳青. 创业史: 第二部[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7: 308.
[7] 余岱宗. 被规训的激情: 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4: 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