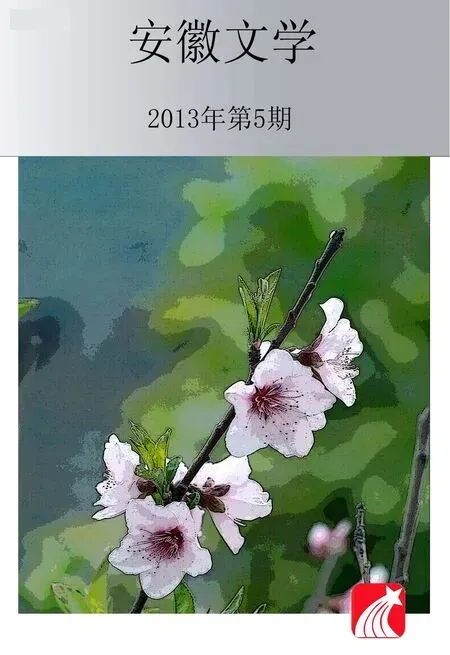奥尔罕·帕穆克的后现代维度
曹培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穆克凭借 《我的名字叫做红》获得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在颁奖公告中说,授予帕慕克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Who in the quest for the melancholic soul of his native city has discovered new symbols for the clash and interlacing of cultures.”( “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这位出生在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作家,正如东西文化激荡的城市一样,在问鼎文学荣耀的时候,同时面临了各种批评、争议,甚至威胁和攻击。
帕慕克是不是一个后现代作家?这更像是一个哲学命题。因为到目前为止,对后现代主义概念本身就存在很多争论。维基百科也注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一个从理论上难以精准下定论的一种概念,因为后现代主要理论家,均反对以各种约定俗成的形式,来界定或者规范其主义。正因为后现代这个术语过于模糊,所以有些文学批评家、哲学家并不喜欢使用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纵使很难有统一的定义概念,但也没有人站出来否认当下的后现代主义时代境况,均承认后现代广泛存在于在艺术创造、文学批评、心理分析、法律、教育、社会、政治、建筑等诸多领域。西方有学者指出:“后现代主义并非一种特有的风格,而是旨在超越现代主义所进行的一系列尝试。在这种情境中,这意味着复活那被现代主义摒弃的艺术风格,而在另一种情境中,它又意味着反对客体艺术或包括你自己内在的东西。”[1]国内学者王岳川、高宣扬、黄进兴等均在后现代艺术研究上进行了深入探索,得出了很有价值的结论。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后工业理论和后现代主义哲学,但在文艺思想及写作技巧上来说,可以看做是现代主义文学的继续发展。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后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并驾齐驱。汉斯·伯顿斯所著《后现代主义及其与现代主义的关系》、詹姆逊所著《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等书都作了较为深入的研讨。
一、“人权大于主权”的价值取向
“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现在已经成为西方主流自由主义的一个公认原则。同时,这也为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者所信奉和坚持。虽然,在人们眼里,后现代主义结构“历史、意义、价值”,摒弃传统,嘲弄精英写作,反对固定模式,崇尚所谓“零度写作”,但无一例外,以独特的个性,又都坚守了“自由”、“人性”、“人权”这些普世价值。可以这么说,后现代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国家、民族、宗教对个体的束缚和限制。[2]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就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无权躲在国家主权后面侵犯人权”。这句话,也代表了后现代主义的价值取向。
帕慕克的作品很多,但题材永远都是一样——土耳其。帕慕克同其他后现代主义者一样,重视个人权利,坚守个人自由,勇敢捍卫人权,怀疑并抵制任何高于个人的集体范畴如民族与国家,他作品中呈现的历史观和对土耳其政府的批判,多次引起国内外的哗然,尤其是他有关土耳其境内库尔德人处境以及20世纪初期亚美尼亚人遭杀戮的谈话,让他成为土耳其保守派的眼中钉。2005年2月,帕穆克在接受瑞士一家周刊的采访时说:“三万库尔德人和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被杀害,可除我之外,无人胆敢谈论此事。”可以想见,土耳其“爱国”人士该会有怎样的反应,批评、诉讼、甚至人身威胁接踵而至,在“爱国”人士的眼里,他分明就是国人嘴里的“汉奸”。而在世界更宽泛的范围,人们对其昭示的人性光芒而充满敬意。
土耳其的人权问题始终是被欧盟指责最多、最激烈的,并将其能否有效解决人权问题与入盟挂钩。历史记录昭示,在1984年到2008年,土耳其当局为了一己之私,对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进行残酷的镇压,十五年来,在土耳其当局的镇压下,共有3.2万多名库尔德工人党成员命丧黄泉。为打击库尔德势力,土耳其在对库尔德势力进行血腥镇压的同时,还对本国东部和东南部13个省长期以紧急状态治理,严重限制了13个省市的集会、言论、甚至是居民的人身自由。在1998年,土耳其还利用外交手段迫使叙利亚把库尔德工人党领袖奥贾南驱逐出境,并派特工在肯尼亚将其抓获。这一事件当时在国际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反响。帕慕克《纯真博物馆》中凯末尔追随着少女芙颂的影子和幽灵,深入另一个伊斯坦布尔,穿行于穷困的后街陋巷,流连于露天影院。在被民族主义分子的炸弹破坏的街道上,在被油轮相撞的大火照亮的海峡边,在军事政变后的宵禁里,他努力向芙颂靠近,但最终没有成功。帕慕克用他的文学之笔,生动展现了土耳其人权的恶劣现状,同时也宣告了作者对人性自由的向往。
二、产自穆斯林文化的“异类”
后现代主义既彻底否定过去,也不寄希望于未来。他们认为崇高的事物、伟大的信念皆为虚妄,所谓“真诚”、“严肃”的态度只能是一场自欺欺人的笑话。他们反对人为造神的乌托邦,不承认终极价值,也拒绝超验神学,绝对的形而上学诉求、权力中心话语、主体性都是毫无道理,需要解构并彻底消解清算。然而,解构只是硬币的一面,硬币的另一面则是建构。后现代虽然否定了神的存在与价值,但没有否定信仰的存在与价值。在现代性的霸权下发轫,浴火重生之后,又另辟蹊径,寻找新的价值。美国新教神学家科布(John B.Cobb)研究指出了当代新神学的变迁,“神学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下不是消亡,而是积极适应回应了这一调整,最终实现由破坏到建设、否定到肯定、悲观到乐观的飞跃,最终成了其实现自我的内在动力”。新教神学家在新形势和新挑战下,反而推动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转变。[3]
在土耳其,99%民众信仰伊斯兰教。在帕慕克作品里,随处可见西方基督教信仰的入侵给土耳其人带来的信仰危机和观念改变,导致了穆斯林信仰的混乱和迷惑,甚至是自相残杀。但他又明确地告诉人们,“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来自于穆斯林文化的人。无论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我是个把历史和文化身份同该宗教联系起来的穆斯林。我不信仰能与上帝亲自接触,在那儿就是变得超出人类经验的”。在《我的名字叫红》一书中,有很多探讨阿拉伯世界细密画传统的内容,以致有读者以为帕慕克是伊斯兰教教徒,在宣扬传播伊斯兰传统。许多人以为作者无比热爱细密画这种传统的艺术,而事实恰恰是否定的,帕慕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直接表明了这一态度。
三、独树一帜的后现代叙事
受解构主义思潮的直接影响,叙事学从 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进入后现代叙事理论阶段。这一转变的标志是叙事理论的多样化(叙事无处不在)、解构化(叙事结构的数量和性质是可变化的)和政治化(叙事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从此,叙事批评坚持标准化(批评有理论可依)和多样化(理论绝非一家之言)并重的原则。主体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关注,承认叙事结构和叙事意义建构和解构的一切参与者,或者将自己的身份属性深嵌其中,或者从中识别到自己的身份属性。[4]马克·柯里的《后现代叙事理论》被看成是应用后现代理论对叙事学进行改造和转化的代表作品,作者在这本书的引论中说:“叙事学中的某种东西可能确已死亡,某种内在的东西……但总的来说,叙事学不过经历了一次转折而已,而且是一种积极的转折。”[5]
奥尔汗·帕慕克在小说创作中一直致力于艺术形式的突破和创新,后现代风格十分明显。代表作品《我的名字叫红》里,叙事手法多样,实验性文体特征、多声交错、隐晦暗示等交织出现,读者诠释空间大大增强,同美国作家唐纳德·巴塞尔姆《白雪公主后传》一样,成为后现代文学经典。《白色城堡》貌似“历史小说”,其实是写作为个体人的挣扎,作为个体的我们很需要从一个与自己相似的灵魂身上得到慰藉,当这个人真的存在你的身边时,我们又会心生恐惧与厌倦。后现代叙事价值和精髓也恰恰如此,在我们开始厌倦了别人絮叨的时候,想打断对方,可当我们自己坐在演讲台上,看看下面脸色各异的听众,却已无从开口。
[1]柯勒.后现代主义:概念史的考察[J].美国研究,1977(22):13.
[2]刘北成.后现代主义、现代性和史学[J].史学理论研究,2004(02).
[3]王岳川.后现代:科学、宗教与文化反思[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2(03).
[4]索宇环.后现代叙事理论的新视野[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05).
[5](英)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M].宁一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