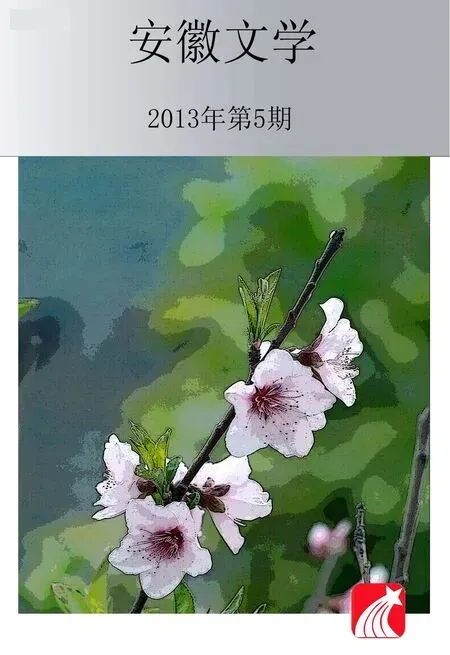天问:从黑格尔悲剧论看电影《莫扎特》
孙 昉 余高峰
一、引言
电影 《莫扎特》(《Amadeus》), 脱胎于英国戏剧《上帝的宠儿》,放映后好评如潮。影片以倒叙手法,表现了宫廷乐队指挥萨列里杀害莫扎特的故事。通常,萨列里被认为是庸才的化身,而笔者认为:萨列里并非一个简单的庸才,他和莫扎特是不同意义上的两种“天才”,莫扎特是音乐奇才,具有来自天堂的纯洁品质;而萨列里是“发掘命运”的“天问”之才,他对莫扎特的陷害,并非出于庸人对有才者的嫉妒,更多由于对上帝造物的不满。因而,影片中两位主人公的矛盾,并非正邪之争,而是两种不同的力量彼此冲突。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理论中的悲剧冲突,不是以“善恶”为基础,而是在伦理意义上,两种处于同等的而又是对立的善与善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的起因是它们各自的片面性。影片中的萨列里和莫扎特,就处于“拷问上帝之善”和“上帝之善”的矛盾中,奠定了这个故事不同寻常意义的悲剧色彩。
二、黑格尔悲剧理论
黑格尔眼里的冲突,是指人物性格在某种具体情境中所遭受到的两种普遍力量(人生理想)的分裂和对立。普遍力量是抽象的,在具体化过程中,它才“现出本质上的差异面,而且与另一方面相对立,因而导致冲突”(黑格尔,1979:260)。黑格尔把冲突分为三类:第一种是物理的或自然的情况所产生的冲突,如索福克勒斯的悲剧《斐罗克特》,该剧的冲突是由于主人公的脚被毒蛇咬伤而引起的。第二种是由自然条件产生的冲突,如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斯》,冲突起于主人公的出身不能继承王位,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罪行。第三种是由心灵性的差异产生的分裂。黑格尔认为前两种冲突是不合理或不公平的,理想的冲突必须起于“人所特有的行动”(黑格尔,1979:260),而电影《莫扎特》正是符合这种冲突的典型。
在黑格尔理论中,悲剧人物去追求目的的出发点如下:“在人类意志领域中具有实体性的本身就有理由的一系列的力量。”(黑格尔,1981:284)真正悲剧人物的性格需要有一种实现这些实体性伦理力量的积极性和活力,“他们完全是按照原则所应该做到而且能做到的那样人物”(黑格尔,1981:284)。冲突的悲剧性在于:“对立的双方各有辩护的理由,而同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和内容却只能是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黑格尔,1981:286),从而达到永恒的和解。
三、电影《莫扎特》中的悲剧冲突
(一)萨列里的正义性和片面性
电影开篇,当神父说“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时候,年迈憔悴的萨列里露出轻蔑的微笑:“是吗?”无疑,萨列里以他的人生经历否定了上帝的公平。在父亲生意兴隆,本可以衣食无忧时,4岁的男孩跪在耶稣像前祈祷:“主啊,让我成为一个伟大的音乐家,让我用音乐赞美你。”他甚至为父亲之死感到喜悦,因为这是通往他音乐之路不可缺少的一步。他凭借不懈的努力,成为了宫廷指挥,仅仅为了献给莫扎特一首欢迎的小曲,他呕心沥血。而同样4岁时,从没接触过钢琴的莫扎特一上琴凳就能弹奏,4岁写出第一首协奏曲,7岁写出第一首交响曲,12岁写出第一部歌剧。听萨列里的曲子,他粗粗听过一遍就完全记住,并且即兴改写,不绞一点脑汁,不费一点时间,作品就迥然不同。当观众跟萨列里一起,看到莫扎特没有草稿的完美乐谱时,只有自然而然地同意萨列里的看法:莫扎特是被上帝宠爱的,他的音乐是上帝早就写好放在他头脑之中的,他只需将其如实展现在世人面前。米开朗琪罗说他的天才是由于家乡“飘逸的空气”所致,那么莫扎特展现奇才时真如呼吸一般自然顺畅。人与人的情况截然不同到如此地步,除了“不公”,又有什么可以解释呢?
在萨列里看来,上帝的不公不仅在于差异性,而且在于它选择的荒谬性:“你选择了一个自吹自擂、下流无耻的小子做你的化身,却只给了我识别你化身的能力。”
萨列里是个什么样的人?影片里的很多乐师都喜欢他,皇帝信任他:“这是我们杰出的指挥家。”从侧面反映出他勤于事业,尊重权威,维护制度,具有主流社会要求的美德。在感情上,他虽然出身平民,却看上一个高雅的唱歌剧的姑娘,这和莫扎特选择的有貌无才、懒惰浅薄的小妻子,形成了鲜明对比,从中可见他们不同的口味和性格。
如果萨列里是多数评论者眼里的“嫉贤妒能”,那么,他从小听说过莫扎特,理应从小嫉恨。可是我们看到,在萨列里听说莫扎特同来宫廷时,一开始非但不失落,反而急切跑去观摩,神情尊敬而带笑。谁料想,他遇到的竟然是个满地乱滚的顽童,弧形腿,蓬头的白色假发,黑鞋,在地上一遍遍教女孩说“倒着放屁”、“吃我的屎”。萨列里发出了对上帝的第一声质问:“上帝为什么选择一个讨厌鬼作为他的工具?”
在此可以看见,萨列里对莫扎特的愤恨,并非由于世俗名利,他是被一种说不清的力量驱使。在影片中,我们可以多次听到这样的声音: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对上帝歌唱,上帝给了我这种渴望却让我失声。如果它不给我天资,为什么又给了我这么强烈的渴望?”
“从今以后我们就是敌人,你和我……因为你不公平,不公正,不仁慈。我要阻拦你,我发誓,我要竭尽全力破坏和伤害你在地上的宠儿,我要毁灭他,莫扎特。”
“笑吧,嘲笑吧!笑着的不是莫扎特,是上帝借着他下流的笑声在笑我。我也要嘲笑你,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要嘲笑你。”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都是独白,不可能有虚伪的成分。足以证明:萨列里对莫扎特的陷害,是凡人对上帝的反抗。如果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作战,注定是悲剧,因为后者是无法战胜的。这就让我们看到了萨列里身上体现的黑格尔口里的“高尚”。
然而,萨列里的所谓“高尚”,其实是片面之极。因为,他控诉上帝没有让他成为音乐天才这个举动,本身就暴露了他不具备一个音乐天才该具备的心灵——纯粹、无邪。而这,恰恰是与他相对的另一种更为高尚的力量——莫扎特的力量。
(二)莫扎特的正义性和片面性
在萨列里眼里,莫扎特是个被宠坏的孩子:不会打理生活;待人接物一团糟;傲慢无礼:“我是最好的作曲家”;不知理财,却在人前死撑面子;不分场合地嬉闹;毫无理由地批评他的同行:“你们都是音乐白痴”,“那不是爱情,那是垃圾”。那么,何以这样一个人,却成了“上帝之善”的化身呢?
影片中,笔者印象最深的就是莫扎特的笑声,如此尖锐,而他也始终如这笑声一般,纯真无比。他不会理财,是因为他把整个灵魂投入了音乐;他待人接物糟糕,是因为他不留心眼;他批评人,说下流话,是因为他根本没意识到这是批评和下流。在他看来,“你们是音乐白痴”,这是事实,而他是如此诚实,认为既是事实就不会触怒到人;那些话也并不下流,是听话者思想不纯,才会觉得下流,莫扎特本人,即使在和妻子进行鱼水之欢时,也是好奇的。正如罗曼·罗兰所说:莫扎特歌咏的爱情没有一点狂热气息,甚至不浪漫,只有甜蜜。当他说那些话时根本没有想到肉欲的粗暴,他太清澈,所以才能写出通往上天的音乐。
电影里随处可见莫扎特的善良:他虽然嘲笑萨列里的平庸,却认真帮助他修改乐章;对蒙面人,他明知对方来者不善却一步步受其摆弄;他始终热烈地爱着不理解他、不懂音乐的小妻子,屡次在人前为她辩护;他爱父亲,以至于把父亲之死当做是自己谋害,才会在写《安魂曲》时崩溃,中了萨列里的圈套。直到临终,连他的小妻子都怀疑萨列里的用心,他却拉着对方的手,一遍遍地道歉、感激。是的,上帝之善当是如此。
至于他的嬉闹,只见幼稚,不见肮脏,正如他的音乐,轻松轻快轻盈,而毫无轻浮轻浅轻佻。在他眼里,那些小丑、佣人,就和上流人一样平等、可爱,所以他歌剧的人物都是市井市民,各有缺陷。如果说贝多芬有升华性,只对人类最严肃、最重大、最深沉的领域感兴趣(唯一的一部歌剧就是如此),那么,莫扎特的音乐,有包容和超越性,他有能力化为一切不同的人,卑微的、不起眼的、坏的。贝多芬用高视角俯瞰人生,莫扎特则是平视加全方位的透视,与这样的音乐对称的,与其说是人生的悲欢离合,毋宁说是自然的芬芳美丽:这就是上帝之美。
影片一开始就围绕着一个问题:怎样接近上帝?萨列里靠的是祈祷,但当一切都没有结果时,原来虔诚的行为往往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诅咒和亵渎。相反,莫扎特轻而易举就能触到上帝之手,那是因为他敢于突破一切,永远向上帝伸出手:保持赤子之心。
然而,莫扎特身上,也具有片面性,因为他注定是不切实际的。黑白颠倒、压抑天性是社会的状态,高于常人的成了罪恶。他的父亲意识到这一点,费尽心思想让他走上正路,莫扎特却毫不领情,反而不断用言语和行为去伤害那些“好人”。在影片中,他先是被故主解聘,然后被同道排挤,被皇帝厌恶,歌剧停演,岳母训斥他“自私”,父亲因其而亡,妻子离他而去,贫病交加,才让萨列里有了陷害的基础。正如萨列里的独白:“我可以人间为所欲为地给他设置障碍。这人间是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欺世者发财,盗名者成功。”在莫扎特周围,除了害死他的萨列里,皇帝、音乐家们、民众们,甚至他的亲人们,都不知道他的价值。古人云:“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早于时代而生,必死无疑;晚于时代而生,必死无疑。莫扎特的领先于众人,清新自然,竟成了他的片面性。风雨之中,他从租来的棺木里滑入满是尸体的泥坑。
(三)萨列里和莫扎特结局中的和解性
黑格尔认为,片面的、相对的高尚力量,都不能带来永恒正义。而这种两难之境的解决,就是代表片面力量的人物遭受痛苦或毁灭。个体虽然被消灭了,但他们所代表的伦理实体并不因此而毁灭,而是在此基础之上出现新的和谐与平衡,也即是“永恒正义”的胜利(黑格尔,1981:288)。让我们来看看,莫扎特和萨列里是如何结局的:
当萨列里兴奋地刺出最后一剑的时候,35岁的莫扎特死去,上天不让人间继续糟蹋他的宠儿了,上帝的宠儿要回家了。
萨列里名声鼎沸,烜赫一时。多年后,他询问年轻的神父,可记得他的音乐,神父摇头。“上帝毁了他的宠儿,却让我活活受折磨。32年的折磨,32年我看着自己慢慢地消亡,看着我的音乐暗淡。”影片尾声,萨列里挥动着枯干的双手,听着莫扎特的音乐在世间永远流唱。
四、结语
黑格尔悲剧理论的独特性在于:都有辩护理由的双方在冲突中由毁灭达到和解。在电影《莫扎特》中,萨列里的行动有其辩护的理由,莫扎特也是美与善的化身。以一种伦理力量去反对另一种,这种行为的正义性、片面性与毁灭的必然性便形成了悲剧性的实质。结合黑格尔理论,观众不仅可以把这部影片看做电影史上的佳作,更可以当做研究悲剧的范本,展开深深的思索。
[1]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北 京:商 务印书馆,1979.
[2]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