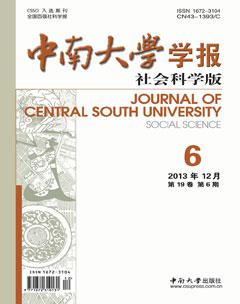论斯宾诺莎自然法思想的基本构成
摘要:斯宾诺莎的自然法思想强调自然法、自然权利、自然权力之间的等同关系。从表面看,三者之间的等同关系似乎失之独断,令人费解。但如果从其全部哲学的基底概念“实体”出发,将其自然法思想分殊为两层语境,即实体语境与个体语境,那么,通过分析“实体”概念统筹下的语境论述,就会使这种等同关系的合理性和意义显明起来。实体语境中的等同关系表明一种理想的观念学,个体语境中的等同关系则表明一种现实的政治学。阐明两种语境的过渡与转换,也便阐明了其自然法思想的基本构成。
关键词:斯宾诺莎;实体;理性;自由;自然法;自然权利
中图分类号:B5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6?0016?05
斯宾诺莎的自然法思想是近代理性主义自然法思想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具备了诸多革新性质。作为一名典型的欧洲大陆唯理主义者,较之英国经验主义者,斯宾诺莎更注重对自然法形而上学的建构。这或许使其思想理论更具深度,但从中延展出具体政治建构时就显得多有繁复而不够从容。本文试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将其自然法思想分理为两个层次,以期做出一种更清晰的展示。
一、作为背景的“实体”概念
“实体”概念是斯宾诺莎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因此,在具体探讨其任一思想样式之先,重新展示一番“实体”概念的基本内涵就显得极为必要。斯宾诺莎在论及哲学目的的时候并未给出实体概念,他鼓励人们摆脱“财富、荣誉、肉体快乐”这三种东西,追求探寻“永恒无限的东西”并遵循“自然永恒的秩序”——他的论述中出现的只是“无限”和“自然”。斯宾诺莎似乎在一开始便遵循了斯多葛派教导的原则,依靠自然理性寻求自然的神圣秩序。当然,就“培养我们的心灵”并“获取内心的平静”而言,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要旨与斯多葛派并无不同,但区别于古典学者的是,斯宾诺莎拒绝断言人的完善本性。古典学者对人完善本性的断言依从于对外在完善自然的断言。人向其本性的回复过程与人脱离世俗社会生活是同一个过程,也是相对于自然的被动过程;而斯宾诺莎认为“没有东西,就其本性来看,可以称为完善或不完善”[1](249),作为个体的人自身并无“至善”可藉回复,人若要获得至善就需要对社会生活的参与,是相对于自然的主动过程。
那么,为人的社会活动提供可能性范畴的“实体”如何被叙述出来?尽管实体自身包含“存在着”要素,并因为自身的“必然性”而存在着,但这些具有绝对意义的性质并不构成斯宾诺莎论说的重心,毋宁说它们只是充当了其论说的技术性前提。显然,斯宾诺莎不但继承了笛卡尔的认识论,而且对其进行了新的彻底的发挥,“在他那里,灵魂与肉体、思维与存在不再是特殊的东西,不再是任何一种自为存在着的事 物”[2](50)。“实体”充当了改进知性认识的坐标,它本身是自明自洽的,也是自发的,我们对它无法“审视”,只能“直观”,而这种直观显示的初始性与明晰性直接照亮了其它认识推论。附源于同一实体的各种属性在其本源上达到内在统一,“神具有广延属性,从而万物才具有形体,才有所谓的物质世界;神具有思想属性,从而万物才赋有心灵,才有所谓的精神世界”[3],这便克服了笛卡尔心灵实体与物质实体的二元对立。在论神(实体)的界说之初,他给出的三个概念和范畴——实体、属性与样式,构成了覆盖其整个哲学论说的基本框架,自然也构成了我们探讨其自然法思想所需的基本背景。实体存在于自身并通过自身被认识,属性构成实体本质,样式则是实体的分殊。按照斯宾诺
莎哲学的论说理路,实体为“一”,也为“万全”,其属性与样式则有“无限”,皆由实体“分有”。人作为实体样式之一,分有实体的两种属性,即思维和广延。
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分别论说了人的情感力量和理智力量,既然人分有思维属性,理智自然是思维的题中之义,理智力量必可谈,但情感何来,情感力量作何谈?“情感”的出现似乎显得突兀,但斯宾诺莎的处理是顺理成章的。一般我们对“情感”一词最先想到的是感觉和印象,但在他的论说中,“情感”总是伴随“情感观念”。他把情感理解为身体的感触,“这些感触使身体活动的力量增进或减退,顺畅或阻碍,而这些情感或感触的观念同时亦随之增进或减退,顺畅或阻碍”[4](84)。在此之前,斯宾诺莎对心灵起源和性质的论说其实就是对人的思维属性的论说,“心灵是能思的东西”,但“能思”只是一种潜能,单纯的潜能并不能生成现实性,“所以构成人的心灵的现实存在的最初成分是一个现实存在的个体事物的观念”[4](47)。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斯宾诺莎的整个伦理学就是一部观念学说。情感反映为情感观念,便也成为思想的各别样式,于是,心灵与情感也便产生了直接而紧密的联系。心灵作为能思的心灵,它处理任何东西依靠的都是清晰明确的观念,或者说,它所处理的东西只是观念。于是,情感不再是不可捉摸或者模糊不定的感觉,而是作为思想的样式有待于被心灵还原为清晰明确的观念,进而被把握和征服,“我们在哪里限囿于情感,就在哪里用理智解除这种限囿”[5](48)。
情感是对某一目的的追寻和实现,而这一追寻和实现的过程往往使人将目的形式化和绝对化。当人僵持在某一目的框定的场域时,占据心灵的情感观念便极有可能陷入错误的“目的论”境地。而目的论与实体观念是不相容的,斯宾诺莎特别指出,“自然的运动并不依照目的,因为那个永恒无限的本质即我们所称为神或自然,他的动作都是基于它所赖以存在的必然性”[4](142)。情感向人传达的第一个信念是“自我保存”,它不仅在最初的意义上要求人的“存在”,而且在最一般的意义上界定了“善”与“恶”。当情感滑落为情欲并为情欲所激动时,人们便陷入各自癫狂和彼此敌对状态。单纯任由情感而为最终会蒙蔽心灵,从而陷入对财富、荣誉和感官快乐的固执追求之中。这样以来,人便陷入奴役状态,斯宾诺莎将奴役定义为“人在控制和克制情感上的软弱无力”。但是,情感之于心灵的纷扰只是情感观念的冲击,也就是说,情感最终化作某种知识或者某种知识类型驻居在能思的心灵。心灵对情感观念的控制和引导表现出人的理智力量,能动性和自主性。正是通过理智力量对情感力量的消融和化解,使人走出奴役状态走向自由状态。从情感到理智,从奴役到自由,斯宾诺莎哲学中的自由观念强烈依赖人的理性能力,自由被归结为理性的自觉。这种理性的自由既标示了人之于实体的“天命”,也标示了人的真实利益所在。
二、两种语境的划分
具体到斯宾诺莎的自然法思想则包含这样一组基本概念,自然状态、自然法、自然权利和自然权力。他直接将自然权利等同于自然法,“我把自然权利视为据以产生万物的自然法则或自然规律,亦即自然力本身”[6](10)——这也明确了自然权利与自然权力的等同。然而,其文本给人的直接阅读印象,似乎存在一组显而易见的矛盾:自然法是理性主义的自然法,具体说就是,理性自觉明示的“知识”对人达成的要求即自然法,理性标示了自然法;自然权利则源出于“自我保存”观念,为自我保存采取的行动都可划入自然权利范围,而“自我保存”观念为情感本能所源出,可见,情感标示了自然权利。这样来看,似乎自然权利与自然法的等同就显得不合理了,理性怎能等同于情感?但是,斯宾诺莎的论说首先和直接针对的并不是“个体”,而是“实体”。这种“等同”关系之间存在一个简要的推论。自然法与自然权利首先被指归于“整个自然的法与权利”,这即表明,无论是自然法还是自然权利,其首要承载者和析出者只能是整个自然,即实体,其次才是作为实体样式之一的人,即个体。而对于完备实体来说,其“完备性”必然要求自然权利与自然法统一到其所具备的自然力(权力)中去。实体既若此,那么这种统一并存的观念自然要进阶到人,进阶到个体。从个体方面来看,符合其本性的活动不外乎指向两个方向,即实体表现于人的两种属性,其一是维持肉体之存在(“广延”属性),另一则是维持思想之纯正(“思维”属性)。事实上,斯宾诺莎在很多地方提及的自然法观念可以分殊为两个层面:第一,实体按照其内在必然性的生发和运转——实体的自然法;第二,个体为谋取真实利益所汲取的理性知识——个体的自然法。
这两个层面的自然法根本目的并无歧异,并且将自然权利与任一层面的自然法等同都无错误。显然,当斯宾诺莎论说自然法的时候,他也在同样的意义上论说了自然权利。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在双层的叙述情境和人类状态之中被表达——实体的自然法对人而言,就是尽其可能发挥力量以维持其存在;当斯宾诺莎转而论说理性的教导(个体的自然法)时,则更多地将自然法的效能指向人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标示了人的真实利益所在。尽管人并不能享有绝对的自由,但“自由”的自然法使人达到对“必然性”的认识。洪汉鼎先生在《斯宾诺莎哲学研究》中将人的必然性分解为外在必然性和内在必然性,将内在必然性归为人的“努力”,否者谈论人的自由就有失合理。[7](609?613)但从认识论来说,无论外在必然性还是内在必然性都是实体自由使然,人的思想能力认识到实体的自由便相应地具备了思想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同时标示了存在的自由,即人的自由。而这一认识的最终成果便是对“上帝”(实体)更进一步也更为深刻的了解。“我们的最高的善和最高的幸福,其目的就在于此,也就是爱上帝和了解上帝。”[6](68)当然,个体的自然法与实体的自然法最终必须是重合的,对人而言,这种重合的现实表现就是内在的和谐宁静与外在的安全和平。相应于此,斯宾诺莎自然法思想的基本结构便可分解为两个基本的论说域:实体语境中谈论的自然法与个体语境中谈论的自然法。
当然,这两个论说域绝非分裂不相关,相反,在斯宾诺莎的文本叙述中它们总是以相互交织的形式呈现出来。与霍布斯不同,斯宾诺莎所设想的自然状态中,实体概念是一个先行参与的前提性要素。这一点更类似于洛克,洛克的自然状态中“自然法”已然发挥着规约力量。区别在于,洛克的自然法观念为理性所天然启示,斯宾诺莎的实体观念则逻辑在先地启示了理性:这也使斯宾诺莎的自然法思想显示出对古典的回复。但是,这一形式上的回复在其政治学中所显露的实质却与古典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
三、实体语境中的自然法
实体概念作为斯宾诺莎哲学的思维起点,充当了其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第一要素。具体反映到其自然法思想中就是,实体概念的完备性(实体的力量或权力)直接明示了自然法观念与自然权利观念,及其等同关系。整个自然界的事物所展示的现实状况无非实体自身因其自因所作的自由展示,出于实体的一切并无所谓道德言语的指称和道德色彩的涂染。实体分化和衍行的自然秩序是舍此别无他途的,世俗所谓的善与恶在实体的自然状态中没有地位,也不会得到实体的理会。如果要为实体拟取名称,那么,从出于实体的一切都可称作“至善”。善与恶真实有效的意义来自个体人对自己主观偏好的考虑,且只有当人处于联合的社会状态(国家状态)时,通过理性检验的情感之善最终成为理性之善,此时的理性之善因为对实体(至善)的了解和向往才与至善产生关联。于是,理性之善便以
至善的名义申明了人的共同本性。斯宾诺莎说,“人类的本性就在于,没有一个共同的法律体系,人就不能活。”[6](6)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人类的本性就在于人类的联合,而谋求安全、和平与方便正是联合的题中之意,因而,从更进一步的意义上来说,确保安全、和平与方便的理性之善表达了人类的本性。
“存在属于实体的本性”,实体表现出来的一切秩序无不在于其存在本性的表达。同时,实体自身也具备表达其存在的力量,而这力量就表现为自然权力,即自然权利,也即自然法。这样一来,自然秩序则正在于权力、权利与法的表达,而权力、权利与法所表现的正是自然秩序。对人而言,实体表现于人的属性只是广延和思维;在自然状态中,对独立的个体人而言,实体的自然秩序直接表现于人的就是“自我保存之维系”。于是,自我保存成为人遵从自然秩序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此处自然法与自然权利存在一个显著的区别,具体表现于人的自然法不可量化,它已然完整继承了实体表现的自然法,而具体表现于人的自然权利却是可以量化的,它因人而异——在此意义上,自然法并不等于自然权利。实体赋予个人力量的大小也直接标示了个人自然权利所及范围。因为实体的限定,直接引用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然权利,说自然状态下每个人享有对一切的权利,在斯宾诺莎这里就显得模糊和不必要了。而自我保存首先诉诸于情感,情感便也在斯宾诺莎的自然法思想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维护,虽然情感需克制,但不必否弃。斯宾诺莎在做政治学论述的时候,也特别在先地强调了这一点,“既然这里讨论的只是万物工具的自然力量或自然权利,我们可以暂不区别我们心中有理性根据的欲望和那些由其他原因产生的欲望,因为这两者同样是自然的产物,都是人借以努力保全自己的自然力量的表现。”[6](11?12)
概括来说,就实体而言,自然权力、自然权利与自然法这三个观念的重合完全基于实体概念本身的内涵,是不证自明不言而喻的;而至于自然状态中的人,简而言之,作为实体之样式的人直接分有了自然权力、自然权利与自然法以及这三个观念之间的等同关系。
但显然,斯宾诺莎论说切身于人的政治学和自然法思想的时候,他选择的是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的论说,“这是一个显著的实践过程,不但要求对自然法的哲学化理解,更要求将其运用于个别境况的天 分。”[8](133)与古典学者相对,斯宾诺莎在《政治论》开篇不久就指出,“实际上,他们没有按照人们本来的面目来看待人,而是按照他们所希望的样子来想象人。”[6](4)古典学者鉴于理想人所设想的只能是理想社会,而斯宾诺莎则迫不及待地强调了人的现实性和不
完善,从而为世俗社会建构留下余地。那么,“人们本来的面目”对斯宾诺莎又意味着什么呢?斯宾诺莎直接从人的现实状况出发,自觉且充分地重视了人的经验,而鉴于经验的考虑首先将人带入“实际存在的人性”,这就是人的现实——“他”并不能天然地把情感纳入理性的轨道,从“情感之善”到“理性之善”并非坦途,人的现实存在首先是人的经验性的情感存在。已经清楚的是,人分有实体的广延属性和思想属性,所谓思想也即“能思”。情感的触动将相应的情感观念带入能思的心灵之中,情感观念可能胁迫人的心灵,心灵则更可能收服情感观念。无论如何,作为思想样式之一的情感观念既可能陷入消极被动,亦可使人富发积极主动,正如斯宾诺莎所言,“我们的心灵有时主动,但有时也被动;只要具有正确的观念,它必然主动,只要具有不正确的观念,它必然被动。”[4](84)而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便时常陷入被动,被过度的情感所操纵,最终把人带入奴役状态。
出于能思心灵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可分殊为两种,出于情感的能动和出于理性的能动。显然,在自然状态中,即便在一般性的世俗社会中,人类经验显示给我们的事实是,人更多地出于情感的能动而非理性的能动。实体语境中无论出于何种情感的“自我保存”都是与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观念相称的。但事实上,与自然权利等同的自然法于此层面只保证了个体人形式上的“自我保存”,与个体人实际上的“自我保存”并无切实的正相关。个体人反而会因为力量的不同使一人处于另一人权利之下,这种负相关性斯宾诺莎在《政治论》中有着细致说明。就个体人而言,形式上的“自我保存”带来的后果往往并非自我保存的达成,反而更其可能走向个体的毁灭。斯宾诺莎对自然状态到国家状态的过渡实际上从两方面给予了论说:一方面按照清晰明确的推理来论证这一过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则属于经验论断。在此,斯宾诺莎与古典学者又一个形式上的重合显露无疑——他几乎是以戏谑的语气表示了对“人天生是社会政治动物”命题的赞同。人与人之间广泛的联合使每一个人和这一群体掌握更为强大的力量和更多的权利,斯宾诺莎用简短独立的一节对此进行了概括:“如果两个人通力合作,那么,他们合作在一起产生更大的力量,从而比任何一个单独的人对自然事物有更多的权利;以这种方式联合起来的人愈多,他们共同拥有的权利也就愈多。”[6](17)至此,当人类进入社会状态(国家)之后,因为彼此之间是联合的状态,联合的目的在于享有更多真实的权利;那么,由人的理性自觉所得的个体自然法就必须为这一联合的稳固有所贡献。
四、个体语境中的自然法
斯宾诺莎曾言,“所谓天然的权力与法令,我是指一些自然律,因为有这些律,我们认为每个个体都为自然所限,在某种方式中生活与活动。”[9](212)这等于说,没有实体这一概念作为前提,就无法谈论人的思维和存在:这是一种逻辑上的依存关系;而人的联合状态则不啻于“在某种方式中”的生活与活动,就“在某种方式中”的个体人而言,实体自然法之后,个体自然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个体自然法把国家、理性和自由视为其所着重的几个概念。理性正确引导人的情感之后,社会生活中人的自由和真实利益最终是通过理性得到标示的。正如斯宾诺莎所言,“人的理性的诸法则只是以谋求人的真正利益与保全自身为目的的。”[6](14)在此之前,在自然状态中,情感与权利的等同关系无需赘言,那么社会状态下理性与权利的关系如何呢?事实上,当斯宾诺莎的论说进入具体政治学情景中时,由于“自由”观念描摹了人的真实利益,权利观念就直接趋同于自由观念。理性在斯宾诺莎自然法思想中的地位是超脱于国家观念的,国家并不是霍布斯意义上的利维坦。尽管国家是人类整体从奴役状态解放出来所必需的中介,但对个体人来说,国家从始至终所充当的只是工具角色。“自我保存”在斯宾诺莎这里的彻底贯彻终使无所谓道德称谓的“自我保存”获取了正当的道德称谓;相较于此,“自我保存”在霍布斯那里的彻底贯彻,尽管是鉴于理性的参与和协调才告完成,但人的情感本性到底是为“主权者”所遏止。斯宾诺莎认为,即使在成型的社会状态中,大部分人依然被情感所主导。只是鉴于理性对情感涂染的道德色彩使人认识到其真实利益和权利所在,国家所充当的无非这一过程的中介而已。显而易见,在斯宾诺莎的自然法思想体系中,最为合适的国家形式就是民有民享民主的“共和”式建制,而非享有绝对统治权的“利维坦”式专制实体。这种从霍布斯思想的偏离也表明,“斯宾诺莎从关于自我保存的一般理解走向了对自我保存概念的深入细致的理解。”[10](553)
那么,社会状态下,人与国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必须为人的真实利益服务,而自由正是其真实利益所在。在这种政治关系中,自由与权利显示出强烈的合并倾向,即“自由权利”。 显然,自由权利在洛克的自然状态中已被申明,而在斯宾诺莎这里,自由权利这一观念却是从具体的政治社会中达成的。说到底,理性在于维护人的自由,国家的目的亦在于此。根据斯宾诺莎的论说,无论自然状态还是国家状态,一个受理性指导的人总是能够掌握最充分的权利,以此类推,以理性为根据并且受理性指导的国家是最有力量和最充分掌握自己权利的国家。一般来说,情感只是确定了权利形式上的分属,而对权利的实际掌握则有赖于理性的指导。一个相对完善的国家及其政权形式应该处处为理性所设想,尽力使自身体现为一个理性和自由的组织。这样一来,即便社会生活中大部分人的具体行为里埋伏了情感因素,但因为国家的理性组织而能够使这些情感因素得到安全和平地发挥,也使个人达到彼此之间的理性对待——因此,一个国家的理性便保有了一个人的理性,一个国家的自由也便保有了一个人的自由。
理性之于个人,标示了其所能达到的自由和所能掌握的权利;理性之于国家,则标示了其作为中介系统为理性的发挥所能提供的指引和便利。理性的能动性也即思维的能动性,这这种能动性最显著地表现为自由与权利的合取,而这种合取只有在社会状态和政治关系中发生并达成。反过来说,国家状态除了维持生活的稳定,更其关键的目的则在每一个体的权利与自由的获取和扩展。个体语境中的自然法之于国家最切实的要求便是“一个最大程度的理性国家”,而这样的一个国家最终目的是保证个体“思想的自由”。这样,斯宾诺莎的自然法思想便证成了其内部的完整转化,即从哲学的观念学到现实的政治学,再从现实的政治学回复到哲学的观念学。
作为近代理性主义自然法思想的样式之一,较之霍布斯与洛克,斯宾诺莎自然法思想的基本观念与诉求并无根本差异。但鉴于其唯理主义,斯宾诺莎自然要求一种形而上学的合理性。其整个自然法思想出于形而上学又回复到形而上学,但这并不构成其思想论说的关键和重点。尽管斯宾诺莎预设了不可违逆的实体原则和自然秩序,但是,单纯对实体自然法的遵从只是个体人的情感盲从。理性自主才能确立个体自由。他的论说揭示了自然法与自然权利在两个层级的等同关系,而第二个层级的等同则完全有赖于个体理性的发挥,这种理性的积极发挥确证了人的真实利益,这一真实利益也指明了人的权利与自由所在。古典学者提及理性时往往一并提及自然的启示,斯宾诺莎论及自然(实体)却将自然的启示搁置不理。如果理性的生活必须是顺从自然秩序的生活,那么对斯宾诺莎来说,对自然秩序消极适从的后果只会是无所适从,而对自然秩序的积极适应则在于从这一过程中寻取和探讨国家、权利、自由等政治概念。斯宾诺莎的自然法思想之所以极富现代性色彩,就在于其对政治社会基础的探讨并不依托完满的自然理性,而是从不完满的个体理性中析出权利和自由概念加以探讨。理性通过权利观念显著且牢固地标注了“自由”,“这种自由就是每个人应该从法律上得到保障的选择信仰的自主权,言论自主权,思辨自主权,把握个人命运的自主权。”[11]
然而,正因为先行引入了实体概念,从而使理性的自然法在个体内部无法彻底表达。个体的能动性和自主性虽然能够在具体的政治形式下取得卓有成效的成果,但无所不在的“实体”始终充当着个体思想与行为的坐标。如果个体所思所为偏离或失却了这一坐标,那么个体的存在及存在意义都将成为谵妄或空谈。正如黑格尔就斯宾诺莎哲学所指明的,“世界并没有真正的实在性,而是一切都被投进了唯一的同一性这个深渊。所以并没有什么东西具有着有限的实在性,有限的实在性是没有真理性的。”[2](129)那么,对斯宾诺莎来说,无论人处于怎样的生活状态,如果想要生活真正地有所起色就只能依靠自身的理解力,将自身付诸思辨的激情。“他还特别向我们强调,如果失去对思辨的热爱,就不可能保持自由。”[10](561)而这种思辨的激情也正体现了整个近代自然法思想的精神,即一切指导政治体系建构的自然法思想都出于自主理性的沉思,“于是,伦理与法律的整个体系就由那些被一种真正的思辨激情所驱使的学者细致入微地予以阐明 了。”[12](70)
参考文献:
斯宾诺莎. 知性改进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
姚大志. 观念与观念对象[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4(6): 1?7.
斯宾诺莎. 伦理学[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Moira Gatens, Genevieve Lloyd. Collective Imaginings: Spinoza, Past and Present [M]. London: Routledge, 1999.
斯宾诺莎. 政治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洪汉鼎. 斯宾诺莎哲学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
Susan James. Democracy and the good life in Spinozas philosophy [C]// Charlie Huenemann. Interpreting Spinoza: Critical Essay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斯宾诺莎. 神学政治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
列奥·斯特劳斯, 约瑟夫·克罗波西编. 政治哲学史[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3.
李登贵. 论斯宾诺莎自由观的四重机构[J]. 哲学研究, 1993(12): 61?69.
海因里希·罗门. 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7.
收稿日期:2013?04?23;修回日期:2013?10?27
作者简介:张卫(1986?),男,河南开封人,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2011级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道德哲学与现代西方政治哲学.
On the basic structure of Spinozas theory of natural law
ZHANG Wei
(Center for Fundamentals Philosophy and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et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Spinozas theory of natural law emphasizes the equivalent relationship among natural law, natural right and natural power. Outuardly, the equivalent relationship seems to be arbitrary and puzzling. However, we can start with the base concept of substance, and divide the theory of natural law into two parts of contexts, that is, the context of substance and the context of individuality. And with an analysis of discourses under different contexts, the equivalent relationship will be intelligible and significant. One kind of ideal ideology is indicated by the equivalent relationship of substance context, while one kind of realistic politics is indicated by the equivalent relationship of individual context. To clarify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 theory of natural law, it is nessary to clarify the trans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two contexts.
Key Words: Spinoza; substance; rationality; freedom; natural law; natural right
[编辑: 颜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