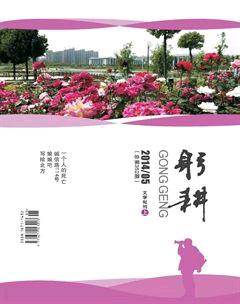远逝的乡村技艺
◆ 司葆华
远逝的乡村技艺
◆ 司葆华

木匠
那个时候,在村子里能养家糊口的手艺中木匠要算上一个。被请到谁家干活,除了好吃好喝伺候着以外,完工了还有一定的酬劳。做一个木匠虽说不上高人一等,甚至还比一般人要吃苦受累,但用村里人的话说,“到底是一个吃饭的门道”。
村里有好几个木匠,他们各有师承,自然各干各的。所谓各师傅各传统,几个木匠自然也互不服气。那句文人相轻的说法,改成匠人相轻也同样适用。三爷是村里年纪最长,手艺最精的木匠。祖辈都以此为业,到了三爷这辈要上溯多少代似乎也没人能够说清。由于手艺家传既久且不断发扬光大,对他应该坐上第一交椅大家倒是可以达成共识,没哪个提出异议。那时做一名凭手艺吃饭的木匠应该是还算不错的选择,因此总有人想拜在三爷门下。三爷择徒甚严,不仅要求勤快有眼色,还要肯吃苦,标准上绝不降格以求。从拉大锯,打墨线,开榫眼等一系列基本功,三爷有自己一套学成出师的标准,严格要求,绝不通融。和学演戏一样,三爷认为基本功不扎实,干一辈子都出不了好活,习业不精的直接后果是木匠这碗饭就吃不好,甚至吃不饱。这样的徒弟出去干活,背后人家能把当师父的脊梁骨戳出个洞来。
三爷对木工活的讲究,让他的产品在村里理所当然成为免检。他只在家里接活,哪怕你顿顿酒肉伺候,他都规矩不改。他做的最多的是板车。在没有机动车的时代,拉粪肥庄稼粮食,甚至赶集上店走亲戚,都离不开板车。拥有一架板车,对庄稼人家来说意义真是大到无法估量。他做板车都要求材质密实坚硬的槐木做框架,至于其他部件选材用料,则根据各家情况,悉听尊便。三爷做的板车扎实而漂亮,拉着出门一眼就能看出那活儿非他莫属,日晒雨淋好几年都不变形不走样,品质和它的制造者一样过硬。
他接活多的还有嫁妆。所谓嫁妆就是闺女出门时娘家陪送木制家具。在刚刚吃饱肚子的当时,准备一套嫁妆应该说是举全家多年之力,一家老小省吃俭用以几件嫁妆撑门面,也算有粉搽在脸上。三爷做嫁妆的时候,一锯一斧,一凿一刨都拿出看家本领,每道工序精细如同刻字绣花,他想让每一件嫁妆成为自己的金字招牌。如此好了再好,精益求精,除了对自己这份祖传手艺的敬重,还有来自他内心对庄稼人日子不易的体谅。有三爷的活儿在那里摆着,村里别的木匠就永远猴子称不了大王,龙头老大的地位因此多少年来一直无人撼动。
到三爷的孩子这代,木匠这一行竟然再也做不下去。尽管孩子们在木匠活上青出于蓝,但最终英雄没有了用武之地。几乎没有人再需要那种手工制作的家具,即使请木匠做也是买来合成版,嘭嘭嚓嚓打一通气钉,或者嗤嗤啦啦喷一阵粘胶,整个工序一个榫眼不用打,一个墨线不用拉,做的简单快捷,而且新潮有型。再过硬的基本功,再好的手艺,在新材料新工艺面前都让你无所作为,甚至一无是处。三爷有些悲愤莫名,他觉得那样干活不是一个匠人该走的正道。三爷的义愤填膺却没有赢得多少共鸣,新材料新工艺生命力大到让大家无视他的唏嘘感叹和捶足顿胸。更有意味的是三爷的孙子辈干脆中断木匠手艺的承传接续,摸惯锯子的手开始操起建筑的瓦刀,木工作为一种手艺在村里薪尽火灭。
编织
曾经有些年,村子周边沟渠河岸上长满了一簇簇条子状的植物,村里人把这种一株生出几十根的植物叫做紫树槐条子。说它是槐,只有叶子相似,却没有槐树扎人的刺。称作条子呢,大概是因为年年都发出一丛指头般粗细的长条。这种长条子大多用来编粮食囤。东亚哥手把快,技术好,是村里编条子公认的好手。每年秋天收割了槐条子,东亚哥便开始足不出户地忙紧了。他好像总有编不完的粮食囤。他对大伙所有的请求总缺少那份拒绝的狠心。不管哪个拎着一捆条子找上门来,他一般都来者不拒,只要几句夸奖话,他就把人家的要求照单全收,而且从来不计报酬,还要他白天黑夜的搭上一整个冬天。
那时候对一个家庭来说,粮食囤既是一种摆设,又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关系到一个家庭的脸面甚至实力。有无粮食囤,有几个粮食囤,往往成为相亲时决定取舍的重要参考。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家庭无论家底子厚薄,日子过得穷富,在粮食囤的拥有上却丝毫不能含糊,哪怕一只粮食囤空空如也,至少也把过日子的架势撑在那里了。东亚哥自然明了粮食囤对于一个家庭的意义,为了成人之美,干起活来不遗余力。东亚哥到底编了多少粮食囤,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他一双关节粗大的糙手,摆弄起条子来却灵巧至极,那些指头粗细的条子在他手中像可以任意揉搓的泥条,编织起来轻松自如,随心所欲。除了那些粗笨的粮食囤,他还用条子编织盛粪肥的筐子,编割草挎着的扠子,编放在板车前后的拦笆。他还无师自通地编织一种像板凳一样的坐具,这种东西两头稍高,中间微凹,像一只镂空的雕花工艺品,坐上去稳当又舒服,曾在村子里流行一时。用柔韧纤细的柳条编织东亚哥也同样得心应手。柳条编织的多是日常家用的小东西,比如装饰简洁的馍馍筐子,小巧精致的筷子笼子,赶集上店走亲戚提的篮子等。东亚哥用柳条编织同样用心巧妙,手法精细,编出来的玩意耐看又耐用,成为村里的抢手货。
在编织手艺上,村里的女人可以说不让须眉。那时候沟沿河岸生长支树槐条子,河汊水沟里则是清一色的芦苇。芦花飘飞的时节,也该场光地净农闲了。妇女们除了聚在一起飞针走线,就是在家里编织苇席了,野外一望无际的芦苇几乎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原料。大椿嫂子娘家在微山湖里,那里盛产芦苇,织席曾是不少人家赖以糊口的门道。当闺女时大椿嫂就凭着一手家传的编织功夫让人称道。嫁过来以后经过数年的习练,在村里更是技高一筹,无人可比。她和几个妯娌整个农闲时节就是大门不出整天编席子。整个工序繁琐而辛苦,苇子收割下来,先用刀子削,再用石磙碾,最后放到池塘里浸泡,然后才成了编织用的苇眉子。大椿嫂那裂出血口子的指头像苇眉子一样柔韧灵巧,编织的时候随着苇眉子在她指间跳荡抖动,身子底下不一会就结出来一片云朵般的席子。她的手艺之好和东亚哥一样在村里不庸置疑令人刮目,各种来料加工的活也让她和妯娌们应接不暇。只要你有等待的耐心,她从来不把人拒之门外。手艺精加上热心肠,使她和东亚哥一样在村里很有口碑。特别是要娶媳妇人家编织婚床上的席子更是非她莫属。村子里一年要娶多少新媳妇,就会有多少张席子要她亲自织成。她工艺上创意不断,时常别出心裁,席子中间用红秫秸眉子穿插着织成双喜字样和连心图案,四角织出抽象对称的花纹,为当时布置简单的婚房平添了吉祥喜兴。大椿嫂还能用苇子编织大小各异的篓子,用秫秸梢作材料编织花样翻新的箱子。
现在槐条子早已被斩草除根,根本见不到踪迹;残存在河沟里的芦苇,也没有早先的一望无际,年复一年地任其荣枯,自生自灭。使用粮囤和苇席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东亚哥和大椿嫂那手编织绝活恐怕也像乡村里的不少手艺一样,已经失传,后继无人。
撒鱼
曾经在村子里谁能拥有一张捕鱼的撒网就足以叫人羡慕眼热,若再能将那张网像玩折扇一样用起来挥洒自如,便有十足资格牛气哄哄了。
满月大爷是绝对有资格牛气哄哄的人。村子人把用撒网捕鱼叫做撒鱼,他是远近几个庄子撒鱼的顶尖好手,是大伙一致公认的撒鱼王。凭着从小练就的过硬功夫,多少年来这个龙头老大的地位一直无人撼动。据说他穿开裆裤就跟着父亲到河里捞鱼摸虾,就像学武一样练得可是童子功。其实对所有捕鱼的方法他都不隔行。比如傍晚时分在水流湍急的涵洞前面安装“跳箔”,或者在平稳的河道放上“扳罾”,通常他在旁边草庵子里一躺,抽着旱烟单等着天亮拾鱼了。他还会在小溪上放置一种叫做“蓄笼”的东西,自己则该干嘛干嘛去,等把蓄笼捞上来,里面的蚂虾、黄鳝甚至老鳖活蹦乱跳。他会使用鱼叉。手执明晃晃鱼叉的满月大爷显得雄姿英发,虎虎生威。只要他手提鱼叉往沟沟渠渠边走上一圈,一般不会空手而返,多多少少都有斩获。
满月大爷的拿手绝活是撒网。他家里各种各样的渔网有七八张之多,网眼稠的,网眼稀的,铁角子多的,铁角子少的,颜色深的,颜色浅的,用来撒鱼的,用来围鱼的,种类之多,花样之繁,在村子里绝对无人可比。平日里把这些网收拾的干干净净,修补的停停当当,挂在盛放杂物的东屋墙上,如同精心保养以备战事的武器。满月大爷平时在生产队照看场屋,那是个出力不多又时间富足的闲差,但他却没闲过一时半刻,在场屋他似乎永远都有织不完的网。织网的活大都是受人之托,能托得动他是一种值得显摆的面子。特别是农闲时节,满月大爷差不多一天到晚都在场屋里竹梭翻飞,银线游走。他不轻易答应哪个,一旦答应就绝不糊弄,活儿细了再细,工艺好了再好,因此他精于织网和惯于撒网一样名震乡里。
村东大河夏天涨水时节是满月大爷最长脸的日子。一连多日暴雨倾盆,沟满壕平,大河一下子变得宽阔浩荡,泛黄的河水打着旋儿一路滚滚流淌,来自上游湖里的鱼群也集结着顺流而下。“大河里来鱼啦”的消息一下子让全村人兴奋空前,大家装备停当齐集在河筒子里。几乎人人身上套着打足气的车胎,以便在湍急的河水里漂流。通常两人合伙,手扯网纲顺水流漂游把鱼网住,这种大伙称作“拉鱼”的方式,是一种费力气、耗时长,又没有技术含量的捕捞。那些从来没有捕捞经验的纷纷赤裸上阵,类似于从来没有摸过枪的在战场上临时征调,很为以满月大爷为代表的技术派所不屑。
满月大爷在满河筒子激动的人群里表情平静,面对开锅一样的吵吵嚷嚷,他一言不发,一板一眼地收拾渔网,时不时卷上一根纸烟,吱吱吸得青烟盘旋缭绕。然后眯着眼睛瞅瞅泛花打旋的河水,选定一个并不显眼的地方,一般是两河交汇或者回水区域。然后再一次整理渔网,好像临战验查武器,然后双手操起整理好的渔网,就像拿起一把待开的折扇。他带着草帽的头微微向后仰起,接着身子猛然前倾,双手次第起落,渔网像张开翅膀的大鸟,又像被风撑开的云朵,网纲发出清脆的撞击声,在满月大爷目光所及的地方,水面上发出同样清脆的声音。满月大爷的双手扯住沉甸甸的网纲,心里涌起沉甸甸的喜悦,凭着他的感觉和经验,这一网绝对收获多多。随着渔网一点点浮出水面,网内鱼头攒动,泼辣有声,密匝匝的鱼儿用尾巴甩出同样密匝匝的水花。满月儿大爷表情还是一样平静,他不像别人那样一惊一乍,更不大呼小叫,每一网再怎么收获不菲他都表情如常,波澜不惊。仿佛这样的结果早就在他意料之中。在整理好渔网之前他绝不心急火燎撒第二网,像吟诗作赋一样慢条斯理,仔细清除网上面哪怕再细小的草屑树叶,一遍遍将渔网汰洗干净,那般笃定沉着,胸有成竹,就好似主持一场庄重盛大的仪式。
每次鱼汛满月大爷都满载而归,成为村子里最大的赢家。他在河里有了比地里面更丰盈的收成,牢固了他撒网技术上东方不败的永久神话。现如今捕鱼的方式叫满月大爷感叹世道变了,除了河道里遍布着那种密似针眼的绝户网,甚至有的还用电瓶电,炸药炸。撒网作为一种捕捞工具已经难得一见,他那手撒鱼的绝活,在村里更无人习得,早已绝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