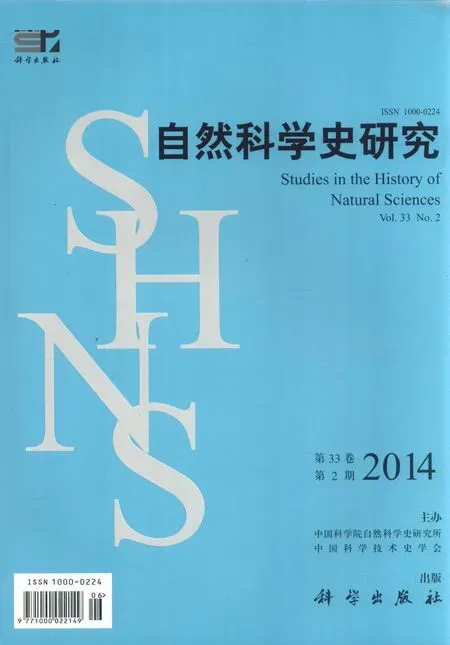女性病者与男性医家
——清代礼教文化中的女性隐疾应对
张田生
(渭南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中国性别史研究是当今学界的热门,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关研究成果逐渐增多。时至今日,这一研究领域逐渐趋于成熟[1]。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关于女性隐疾应对的研究成果甚少①管见所及,目前学界,仅有陈秀芬的《在梦寐之间——中国古典医学对于“梦与鬼交”与女性情欲的构想》(《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1本,第4分,第701~736页)一文。作者对古代隐疾之一——女性情欲病,做了深入的研究。对古代医学对“梦与鬼交”与女性情欲之间关系认识及其演变进行了梳理,呈现了医学认识与社会条件及主流价值之间的相互形塑和渗透的过程。。然而,女性隐疾及其应对可以为我们了解古代关于性别关系的礼教实践②“‘实践’是新文化史的口号之一,也就是说,他们应当研究宗教实践的历史而不是神学的历史,应当研究说的历史而不是语言的历史,应当研究科学实验的历史而不是科学理论的历史。”(彼得·伯克《什么是新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7页)根据新文化史中实践研究的视角,我们应当研究礼教实践的历史,而非礼教理论的历史。中国古代性别史研究可以将礼教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即从礼教理论的历史到礼教实践的历史。提供一个新的窗口。因为,女性隐疾涉及女性的身体隐私,病家不得不延请男性医家治疗,这必然与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产生矛盾。当时的病家、病家中的女性病者、男性医家是如何认识隐疾的?他们如何解决隐疾应对的性别文化矛盾?在女性隐疾应对过程中,病家与男性医家各自应对隐疾的策略对对方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不同社会阶层的病家和医家在隐疾应对中,对礼教文化的认识有何不同?这些问题无疑对于从性别角度研究女性史具有重要的价值,对于疾病史和医病关系史研究也大有裨益。为了便于问题的讨论,我们选择清代女性隐疾的应对,作为文本的论题。之所以选择清代,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这一时期的史料比较丰富,便于微观考察;其二,清代礼教更加严格,对女性隐疾应对中的两性关系影响更大。
1 清代礼教的加强与民众的日常生活
一般认为,在整个传统社会,礼教的发展趋势是严格化。到清代,礼教发展至顶峰。作为礼教的核心问题,男女有别的性别思想制度,也是如此。清代的男女有别观念以及节妇观念的强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政府加大对节妇的旌表力度,以维护当时的性别制度。顺治时期,清廷就开始旌表节妇,并将旌表制度推广到八旗女性之中。康熙帝延续了这一政策,雍正帝做了进一步推广,旌表节妇数量因之激增。到乾隆朝,旌表之风愈刮愈烈,国家有不胜招架之势。有清一代,旌表的节妇有百万之多。在正面表彰的同时,国家还通过法律等措施,对再嫁寡妇进行贬低和丑化,地方政府将贞节政策作为乡约教化的重点,向民众宣讲[2]。政府对节妇的旌表,有力地强化了当时的性别隔离制度。
其二是民间节妇堂的发展。据梁其姿统计,有清一代,以救助节妇和维护其名声的清节类善堂,全国共计216个,大多数府县都有,其中江南地区最多[3]。清节类善堂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尤其是“清节堂真是罕见的壮丽设施。在那里,投入了较恤嫠会用于一名女性十几倍、二十几倍甚至更多的费用。”[4]民间士绅投入巨额资金,建设壮丽的清节堂,对维护寡妇的名节,严格两性区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三是士大夫女性观的保守。“在女性观上,与晚明诸多学者开放的心态与意识迥然不同,清初学者的女性观转而趋于保守,随之而来的则是男尊女卑的观念在清初重新甚嚣尘上。”[5]被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王夫之,其性别观念也十分保守,他说:“不可拂者,大经也;不可违者,常道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妇道之正也。”[6]曾对君权有过反思的王夫之尚且如此,清代主流社会的性别观念就可想而知了①当然,清代亦有人对礼教性别关系质疑,提出自己的看法,袁枚就是其中的代表(蔡尚思《中国礼教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5~115页)。。
清代礼教的发展对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对此影响不宜估计过大。传统的中国女性史研究忽视了社会思想制度在生活层面上予人的实际影响及具体成效,因而对女性地位以及男女有别的性别制度估计过于严重。清代一些社会上层女性并没有局限在家里,而是通过跟随丈夫宦游、与女伴出游、外出谋生游、卧游等方式,寻找家庭之外的活动空间,闺房并不是她们生活的唯一空间[7]。尽管这类女性应该是社会上层女性中的一部分,但这部分女性足以说明了当时礼教对社会生活影响的局限。李伯重对礼教的局限也有过反思,他说:“正是当时绝大多数丧偶女性不愿守节,因此朝廷也才会如此积极地旌表节烈。”“官方和道学家鼓吹‘男女大防’和女性贞节最积极的时代,往往也是人欲横流、色情泛滥的时代。”清代出版物中销售最广的是艳情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并非四书五经。[8]可见,清代的性别关系是多面相的,受礼教熏陶较深的女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将自己与丈夫和儿子之外的男性隔离开来;崇尚自由的女性寻找多元的活动空间,追求爱情,对与男性交往并不排斥。
2 清代女性隐疾及其应对
清代医学发达,医家众多,但受过医学训练的医家绝大多数是男性。至于女性医家,数量不少,但其中受过医学训练的医家少之又少,大多数是没有经过医学训练的以接生和卖药为职业的稳婆和药婆。因此,女性病者延医治病,就得面对男性医家,这使得医病之间多了一层性别关系。尽管在日常生活层面,男女之别没有礼教宣传的那样严格,但性别之间的关系肯定会受到礼教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男性医家与女性病者及其家属之间的交流,以及医家的施治,都面临着一些难题。要是女性病者患隐疾,医病之间的关系处理就更为棘手。
2.1 清代的女性隐疾
在了解清代女性隐疾应对之前,我们首先考察清人对女性隐疾的认识。
“隐疾”一词,始见于春秋战国时期。鲁桓公六年,桓公向申纟需询问命名的礼仪,申纟需正面说明了命名的几种方式,从反面论述了命名应该注意的几种避讳:“不以国,不以日月,不以隐疾,不以山川”。古人郑玄、周寿昌等人认为,这里的“隐疾”,指衣服下面的疾病①今人杨伯峻以为,这里的隐疾意为是所有疾病,而非某一类。他说:“《庄子外物篇·释文》引李颐云:‘隐,病患也。’此隐字当此义,隐疾为同义词连用,犹言疾病。旧解隐疾为衣中之疾(初见于《礼记·曲礼》郑玄注),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一且谓:‘隐疾当如秦公孙痤(疖也,痈也)、汉郦疥(《史记·陆贾传》)、温疥(《汉书·功臣表》)之类。’疾病,人所不免,口难以避讳,故不以为名。”(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5~116页)。《礼记正义》对此解释做了补充,“隐疾”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衣服下面的疾病,即不为外人所看到的“黑臀”、“黑肱”等疾病,二是指身体幽隐之处的疾病。同时,它指出了隐疾不易治疗的特点,即隐疾令医家很难为,不容易诊治②《礼记正义》原文的说法是:“此在常语之中,为后难讳也。《春秋传》曰:名终将讳之。隐疾,衣中之疾也。谓若‘黑臀’、‘黑肱’矣。疾在外者,虽不得言,尚可指摘。此则无时可辟,俗语云:‘隐疾难为医。’……‘不以隐疾者,谓不以体上幽隐之处疾病为名。’”(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上、中、下)》,卷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5页)。
在内涵上,医书中的隐疾与《礼记》中的隐疾有些不同。管见所及,在医书中,《外台秘要》首先转引了《素女经》关于隐疾的说法,“《素女经》论:妇人八瘕积聚,无子,断绝不产,令有子受胎养法。……及阴闭生息肉,阴痒生疮,阴痒 疮,带下阴,子脏不正,阴门挺出,阴肿坚隐疾方。”[9]在这里,隐疾主要指女性身体幽隐之处的诸多疾病,即生殖器方面的疾病。这也是清代狭义的隐疾概念。医家程国彭就说:“妇人隐疾,前阴诸疾也。有阴肿、阴痒、阴疮、阴挺、下脱诸症。”[10]广义的隐疾指妇科疾病。医家王士雄说:“带下女子生而即有,津津常润,天赋之恒,或至太多是病也。然古以妇人隐疾统名带下,今人但知白带、赤带等名耳,病因非止一端。”[11]王士雄认为,时人对隐疾的认识并不全面,古代对隐疾的认识比较准确。总之,在医学层面,清代女性隐疾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隐疾指性器官方面的疾病,广义上的指妇科疾病。
在礼教层面,女性隐疾的含义在范围上更广,除了医学层面的隐疾外,还包括乳房等一些身体敏感部位的疾病,如乳痈、乳漏等。清代礼教对男女之别十分重视,这类隐疾病者及其家属在延请男性医家治病的过程中,同样存在与其他隐疾类似的不便和尴尬①在清代,情欲不遂和狐臭也被看作隐疾。王士雄曾治疗过王杞庭姐姐情欲不遂的疾病。参见王士雄《王孟英医案》,卷2“损”,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年,第166页。龙光妻子因为狐臭的隐疾不受丈夫的喜爱(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一百四回“良夫人毒打亲家母,承舅爷巧赚朱博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93页)。这两种疾病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2.2 清代女性隐疾应对中的性别关系
陈东原认为,宋元以后女性盛行有病讳医[12]。明清时期,随着礼教的加强,的确有些女性患隐疾后,羞于延医治病。但大多数女性并非如此,正如李贞德所说:“历史上大多数的女性既非才高八斗,也未曾割耳自誓,只是过着生儿育女的生活。”[13]清代大多数女性还是以生活为主,积极应对隐疾,延请男性医家治疗。
清代女性隐疾的应对,相关文献记载主要有两类——医书和笔记小说。前者主要是男性医家书写的,后者是文人士大夫书写的。对于女性隐疾的应对,两类文献书写者的立场不同,书写内容有较大的差异,两类书写者各自面向的读者也不同,两类书写的阅读群体亦有差别。为此,我们从书写的角度,分别剖析两种文献所呈现的女性隐疾应对中的性别关系。
2.2.1 男性医家视野中的女性隐疾应对
在严格礼教文化中,女性隐疾病者及其家属,在延请男性医家治疗的过程中,往往羞于说明疾病的详细症状。男性医家不得不设法开导,以消除性别关系中的尴尬。明代医家孙一奎就书写了这样一则案例。“吴氏妇有隐疾,其夫访于予,三造门而三不言,忸怩而去。后又至,未言而面先赧。”孙一奎从人情、事理和医学三个方面,对病者丈夫进行了开导。随后,“其夫乃俯首徐应曰:‘言之无任主臣,先生长者,即言之,谅无哂。山妇子户中突生一物,初长可三寸,今则五寸许矣。状如坚筋,色赤,大可拱把,胀而且痛,不便起止,憎寒壮热,寝食俱减。羞涩于言,每求自尽。闻先生能为人决疑疗怪,不啻扁、华,特相访而祈一决。”孙一奎询问患病日期后,诊断为阴挺,分析了病理,认为不影响生育。“其夫合手顶礼于地曰:愿如药王言,敢徼一料。”孙氏根据病情,开方抓药,给了病者丈夫。三月之后,病者康复,而且怀孕[14]。在此案中,吴氏妇因为患隐疾,即使给自己的丈夫,也羞于表述,更不用说延请男性医家诊治了。因此,这位女性经常想自杀。而病者的丈夫,同样羞于向医家说明妻子的症状,三次登门延医,未启齿而面红耳赤。第四次在医家的开导下,才羞涩地描述了隐疾的症状,同时要求医家不要笑话。在得知疾病可以治疗后,又给孙氏顶礼膜拜。可见,当时病家受到的礼教压力很大。然而,病者的顾虑和压力,在医家孙一奎看来,似乎大可不必。从孙氏对自己的书写来看,他好像没有男女有别观念的压力。这则病案发生在明代,但也符合清代的情况②清代医家魏之琇就在《续名医类案》中转录了此则验案,以供世人参考(魏之秀编著《续名医类案》,卷19“前阴”,名医类案(正续编),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年,第613页)。。
医家与病家的友谊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淡化性别关系的尴尬,减缓病家表述病情的压力。医家尚某“昔在粤东,与郡司李某交善,后李没,某妻售濠畔街宅,与尚仍分院而居,两家往来如亲串然。一日李妻私语尚夫人,有女及笄而病,病且甚异,欲求尚诊之而难于言。夫人告尚曰:‘与李君夙交好,言之何伤?’李妻乃言:‘女初患腹痛,久之溲溺甚艰,溲内有物能游泳,或二或三,似有鳞鬣者。’取视之,乃比目鱼半体也,身微黑,止具一目,其背白,置水中果如所云。”尚某诊断为肝气久郁所致,继而治愈了病者。[15]病者系刚到出嫁年龄的少女,身患隐疾,寡居的母亲延请与其夫关系甚笃的医家尚某治疗,但顾忌两性之间在表述隐疾过程中的尴尬。尚氏医家的妻子以两家的友谊关系进行开导,病者的母亲才消除顾虑,向尚氏详细描述了病情。在重视女性名节的清代,一个黄花闺女患隐疾,病者母亲又在寡居,在此情况下,延请男性医家治疗,向其说明病情,病家所承受的礼教压力可想而知。然而,医病两个家庭之间的友谊关系,悄然化解了性别之间的尴尬以及礼教的压力。
上述病家借助一定的条件,说明了病情。但有些病家则难以突破礼教障碍,不得已歪曲病情,或者不言病情。王士雄书写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倡女蔼金,年二十七,患时疫颇危,余为治痊矣。忽又求诊,云患急痧。及察其脉甚细,而按之数紧,神极委顿,吁吁而喘,眉锁春山,泪含秋水……似房劳太过,寒袭奇经之男劳复也。……知其性情通脱,因微询曰:‘夜来勿过劳乎?’渠谓:‘以君善治隐曲,敢尔乞怜。既得其情,但求援手。’余闻而矜之”,很快治愈了病者。[16]这位妓女大病初愈,就接待客人,因之患男劳复。但她身份特殊,没有家庭,无法借助家庭中的男性成员,转述隐疾病情,只能自己说明。面对男性医家,她无法直接表述自己的身体隐私,不得已歪曲病情。所幸,王士雄医术高超,一眼看穿。鉴于病者性情通脱,王氏委婉询问了病情真相,以证实自己的诊断。病者也吐诉了衷肠,得到了医家的怜悯。这个相对特殊的案例,为我们提供了医病两性之间的一些重要的信息。其一,即使是妓女,也囿于当时礼教的压力,羞于向男性医家当面讲述自己的隐疾。可见,礼教所影响的群体很广。其二,从“眉锁春山,泪含秋水”这个文学化的描写可以看出,在男性医家王士雄眼中,这位病者非常漂亮。病者漂亮的外表引起了男性医家的怜悯之情。其三,在王士雄医案中,对女性病者相貌文学化的描写只有这一次。王士雄之所以做出这种描写,一方面因为这位女性病者的相貌引发了王氏作为男人的心理反应,另一方面是病者特殊的身份——妓女,要是其他身份的女性病者,王士雄就未必如此了,否则他会受到道学家的挞伐。其四,疾病的压力可以冲破医病两性之间交流的障碍。这位病者没有男性家庭成员可依赖,在疾病的压力下,尽管羞于启齿,但不得不直面男性医家。
医家郑重光经历了一个患隐疾的女性病者,病家受困于礼教,不说明病情,仅让其诊脉。“瓜镇胡宅之内眷,隔幕诊脉,两尺弦数,左关单弦,独异他部,默不言病,似欲考医者。余因脉言病,谓两尺弦数,定为下部之痛,数则为热,必有血证,但不知为何病。彼家然后直告,谓一月前小便淋秘而痛,因其夫常宿青楼,疑为梅毒。”疡医诊治无效,病家也“因亵病不能直陈耳”。郑重光以脉辩证,“因属隐疾,不便明言”,直接拟方。病者服用两剂后,痛苦减缓。第二天病家再次延请,郑氏“遂以阴疮证书封问其夫,合病则治,否则当别延医也。”病者丈夫认为诊断符合病情,病者继续服药,服用多剂后痊愈。[17]从“瓜镇胡宅”一语判断,病家属于社会上层,受到礼教的影响应该较大。因此,病家对有辱家门的“亵病”三缄其口,郑重光还以为病家在考察其医术。病家后来坦白,主要是出于对医家的信任。可见,首先不言病情是病家保护病者隐私的一种策略。郑氏也顺从病家的心理,第一次治疗时,没有继续了解病情,直接拟方;第二次以书信的形式,向病者的丈夫证实自己对病证的判断。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受礼教影响较大的上层病家中,尽管患病的是女性,但在医病互动中,女性的直接参与甚少,在家人的监督下,病者隔着帘幕,仅伸出手腕供医家诊脉①在诊脉的过程中,病者的手或许还是被手帕之类的织物盖着。在《红楼梦》中,晴雯受了风寒,大夫受邀诊脉,晴雯就隔着帘幕,伸出手腕,手用手帕盖着。(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695~698页)可见,在清代上层社会,医家给女性病者隔着帘幕诊脉,病者的手也是被掩盖的,医家只能看见手腕。。
不过,并非所有的病家不敢直言隐疾病情,孙一奎在医案中就记述了一位直言隐疾的病家。“迪老之子凤林,见予起乃翁疾,乘间语曰:‘内子包有隐疾,每月汛行,子户傍辍生一肿毒,胀而不痛,过三五日,以银簪烧红,针破出白脓盏余而消,不必帖膏药,而生肉无疤痕。初间用针刺,近只以指掐之,脓即出。但汛行即发,或上下左右而无定所,第不离子户也。于今八年,内外科历治不效,且致不孕,先生学博而思超,幸为筹之。”孙一奎沉思两日后,认为此病由中焦痰湿所致,随后治愈病者([14],21~22页)。马凤林见于医家孙一奎治愈了父亲的病患,因而十分信任孙氏,直接对其讲述了妻子的隐疾。从表面上看,马氏似乎所受到的礼教影响较小,没有过多的男女身体隐私方面的忌讳。不过,从整个故事情节来看,事实并非如此。病者患病八年,且不孕不育,病家延医无数,但治疗全部失败。在此情况下,疾病和求子的压力代替了男女有别的礼教压力,因此,在见证孙氏的高超医术后,马氏毫无顾忌,直接向孙氏说明了妻子的病情。可见,在病家心里,与礼教相比,治愈疾病更重要。
上述医家为了减少性别之间的尴尬,在脉诊或问诊之后,直接治疗。然而,一旦疾病需要望诊,医病间的两性关系就更加突出,礼教的障碍则难以逾越。医家通常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借助其他女性的眼睛来观察。如此一来,医病间两性关系的不便就消除了。医家郭志邃就是如此。“一妇人患血崩,其家人曰:‘痧也。’引他妇阅之,果有痧筋,放之。用养血和中之剂,治之而愈。”[18]血崩属于妇科病,如果系痧证,需要通过观察阴户的痧筋,才能确诊。郭志邃不便直接望诊,所以找其他女性替代其观察②相比中国此种观念,宽政时期的日本就比较开放,当时的医家片仓元周曾亲眼望诊了一位佛具匠妻子阴户赘物,且用手触摸,以确诊病证(片仓元周《产科发蒙》,卷5治验(三十四道),见陈存仁编辑《皇汉医学丛书》,第9册,上海:上海中医学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30~131页)。。
要是女性的隐疾需要外科手术,医家需要直接接触病者身体的隐私部位,医病间无法做出避讳,问题将如何处理呢?医家余景和医案中的一则案例为我们提供了答案。“有上海世家某姓女,受湿阴门溃烂。外科敷以生肌药,后俱长合,仅余一小孔,惟能溲溺,生育无望矣。又请医剖开,仍敷以止血生肌药,长合如故。连剖数次而俱长合,痛苦万状,闻者惨然。”病者哥哥携其妹求诊于孟河医家奚大,奚氏听闻病情后,说:“甚易,一月可完璧归赵,奈其事实难,不能治也。”病者哥哥问其故,奚氏回答:“此症非父子、母女、夫妇不避嫌疑,不可施治。若欲吾治,当拜吾为义父。”兄妹允诺。数日后,奚氏将病者带入内室,先给病者服用了一些手术前的药物,之后将白蜡和生肌药融合,涂于油纸,把纸剪成方形,做夹纸膏百张,再将病者前阴用刀切开,敷上止血药,以夹纸双叠折好,要求病者正卧,夹入前阴缝中,溲则取开,溲后拭尽再夹,一日三四次。药纸用了七八十张后,前阴两旁长好,病者痊愈。[19]病者出身世家,社会地位较高,受礼教的影响应该较大。然而,迫于疾病的压力,病者对男女有别的观念已无所顾忌,因此,她连续数次接受了男性外科医家的手术治疗。这说明当时一些外科医家对于这种隐疾手术,并不因礼教而拒绝。相比同行,孟河奚氏注重礼教,认为这种手术只有在父子、母女、夫妻等家庭成员之间进行。为此,他通过与病者结成准父女关系,从而跨越了普通男女有别的礼教障碍。可见,将医病间普通的男女关系转化为家庭血缘关系,是当时受到礼教影响较大的男性医家,为女性病者进行外科手术的有效途径。
应该说明的是,社会阶层对女性病者与男性医家的两性关系的处理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上述病家大多数属于社会中上层,受到礼教的影响较大,女性病者有条件与男性医家做适当的避讳。如果女性病者属于社会下层,她们患隐疾后,与男性医家的避讳就十分模糊。二十四岁的苏氏妇,“患乳肿如悬瓠,溃处日流水,医治二百余日,略不见效。”病者向王士雄求诊,王氏见于病者为温补之剂所误,于是用焦饭末和橘皮做成的假药,治愈了病者。在医案中,王氏详细描写了自己哄骗病者服用假药的情景,以表现其高超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唯独没有提及他与病者之间的性别避讳。[20]在此案中,这位女性病者患病的部位乳房,明显属于身体隐私部位,王氏做了望诊,对症状做了细微的描述。他们之间为何不避讳?我们认为,关键在于病家出身社会下层,没有条件避讳。病情比较严重,而病者没有任何家人陪同,自个寻找医家就诊。由此可知,病者的家庭很贫困,既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又缺乏必要的人力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治愈疾病是病者所关心的,至于男女之间的避讳,不在病者考虑的范围。前文向王士雄求诊的妓女蔼金,尽管经济条件可能较好,但在社会地位上亦属于社会下层,与苏氏妇一样,她也是自个向王士雄求诊,尽管男劳复的隐疾令她更加难以启齿。可见,社会阶层对女性隐疾应对中的性别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避讳主要是病家考虑的问题,多数医家顺从病家对避讳的要求。
由上可知,在医家的视野中,在患隐疾后,大多数女性病者及其家人迫于男女有别的礼教压力,对治疗中的性别关系比较敏感。他们往往羞于讲述病情,或者歪曲病情,或不言病情。社会中层病家的表现比较明显,社会上层病家更甚。不过,一旦信任医家技术,他们则坦言相告。可见,首先隐讳病情是病家保护女性身体隐私的一种策略。至于社会下层病家,因病情的不同,其表现有所差异,但总体来说,他们对礼教考虑较少。与病家相比较,大多数医家受到的礼教影响甚微。在医案中,他们通过书写病家的羞愧和无措,以及自己对病家的开导,来反衬自己的理性和通达。似乎,对于他们,礼教是可有可无的。当然,有些医家对礼教比较重视,通过与病者结成准血缘关系的方式,适应礼教的性别规则。医家通过此类书写,一方面为同行处理医病间的两性关系提供一种规范和参考,另一方面树立自己在业界及后世的职业形象。由于医书的阅读群体并不限于医家,还有文人士大夫,因此,这类书写提高了医家的社会形象。作为社会中人,医家为何很少顾及礼教?我们的解释是,经济利益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严格按照礼教,医家就无法给女性病者治病,更不用说治疗女性隐疾了。这必然损害其经济利益。在礼教与经济利益之间,医家选择了后者。
2.2.2 女性病家视野中的隐疾应对
对于女性隐疾应对的书写,除了医家之外,还有文人士大夫。这些文人士大夫未必是女性病家,但是,在笔记小说中,作者往往表现和突出女性病者及其家人的感受和内心活动,间接反映了女性病者及其家人的立场。因此,这类书写者可以看作是女性病家,或者说,二者的立场是一致的。
受礼教的影响,女性患隐疾后,首先感受到的是羞耻和担心。“一妇病阴中奇痒,苦甚而不敢告人。平日虔奉观世音,见一尼持药一函至,曰:‘煎汤洗之,即愈矣。’尼忽不见。启视之,乃蛇床子、吴茱萸、苦参也。”①这则故事虽出于前朝,但清人将其转述,这反映了他们对此故事所包含的思想观念的认同(褚人获《坚瓠秘集》,卷2“神药愈疾”,见《笔记小说大观》,15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第468页)。这位患阴痒女性,因为观念保守,虽然十分痛苦,但不敢告诉他人。所幸,平日受其信奉的观世音,化作尼姑,为其送来治疗的药物。这本是一则信佛得善报的故事,但故事也透露了观念保守的女性,在患隐疾后所面临的困境。她们觉得,阴痒属于隐疾,必须绝对保密,否则会污损其名节,所以,尽管痛苦,也不敢告人。
不过,大多数女性患隐疾后,对于延医,病家尽管很纠结,但还得设法延医治疗。对他们来说,如果能找到一种既不泄漏女性身体隐私,损害病者名节,还能治愈疾病的办法,那就是最理想的了。十七岁富家小姐宜春,患了阴疮。病家的女仆在延医的途中,巧遇出身世医、赴京城赶考的霍筠。霍氏尽管出身世医,但不屑医家职业,又不善营生,因此生计颇为艰难,尚未娶妻。此时日近黄昏,霍氏行至无人之处,正在苦于无处投宿,听说有人延医治病,便自称是医家,可以治病。霍氏到病家后,主人告知其心意:“尝与小女商量,必访得医生貌美年少者,乃请疗病,病愈即以小女相配。”霍氏爽快答应了此事。霍氏观察了疮口,配置了药物,亲自敷药施治,治愈了病者。期间,病者羞怯,但因如意郎君施治而窃喜。之后,宜春与霍氏结为伉俪,生活幸福美满。宜春及其家人并非世间凡人,一日,宜春以缘分已尽为由,与家人离开了霍氏。[21]这则爱情神话故事尽管在情节上是虚构的,但故事所反映的隐疾女性病者及其家人延请男性医家治病的观念是真实的。故事主人公的家庭属于社会上层,受到礼教的熏陶较深,对男女有别的观念十分重视。病者系未婚的少女,其所染之疾又在生殖器上,且属于外科疾病,服药等内治法不能完全治愈。在这种情况下,既治愈疾病,又不影响少女名声的两全其美的办法显然是病家最想要的。经济拮据、出身疡医世家的霍氏正好符合这个条件,他也以此脱贫致富,由社会下层一步跨入社会上层。在这个故事中,女性病者与男性医家结婚,双方获得双赢,将坏事变成了好事。这种方式太完美,或许大多只能出现在神话故事中。
女性隐疾应对的难题,关键在于礼教对普通男女之间的严格区隔,如果医病间的两性关系放在家庭之中,这个难题的破解变得相对容易。“有依表兄嫂同居者,室三楹,虚其中,对室居焉,三人皆略知医。一夜漏将阑,嫂忽大呼表弟,弟至中室,候启门。嫂以兄危急,不能离身,离恐无救,令由牖入。弟悟表兄必阳脱,稔知艾灸可治。乃取艾,破窗入。然尚交股,未便启衾。遂剪被径之寸许,以艾灸尾闾骨。不意嫂伏其上,误灸其臀,一惊呼而火气度入茎中,兄亦顿苏。”[22]哥哥和嫂子夜晚同房,不意哥哥发生阳脱,即休克。按照当时的医学知识,此时女性不能离开男性,否则男性就会死亡。因此,嫂子只能在被窝里光着身子喊表弟救命,弟弟从嫂子的言行中判断出真情,通过艾灸治愈了哥哥。期间,弟弟误判,以为哥哥在嫂子上面,故而将艾灸在嫂子臀部上。尽管这个情节比较令人尴尬,但家庭关系还是跨越了普通男女之间的礼教区隔。当然,这种情况的发生有一个前提,就是家庭成员中的施救者必须是医家,至少掌握一定医学技能。
当然,家庭中最为方便的还是夫妻之间的隐疾救治,夫妻关系不受礼教男女有别规则的限制。“有少年未娶时,好狎邪游,体尪弱。新婚之夕,畅极阳脱。新人偎抱,以口度气而救之。郎苏后,询何以知此救法,女曰:‘在室时,闻隔窗兄与表兄放谈秽亵,曾论及脱阳不可离身,必以口度气乃可活。昨郎下部热出屡屡,色变气闭,恐是此症。姑试之,不意竟验。’”([22],364页。)妻子婚前听说了救治阳脱的方法,在新婚之夜的夫妻合欢过程中,及时救治了阳脱的丈夫。医者与病者是夫妻关系,这使得隐疾救治不存在任何礼教观念的障碍。
由上可知,女性病家视野中的隐疾应对书写,主要强调女性病者患隐疾后,病家承受的礼教压力以及有苦说不出的痛苦感受,他们既想治愈疾病,又想保护病者的身体隐私和名节,但两者很难周全。因此,当时文人士大夫往往通过神话故事,建构两全其美的场景。同时,他们对家庭之内隐疾应对的书写,实际上间接反映了时人希望在隐疾应对中跨越礼教障碍的心理。因为,只有在家庭中,男女之间的距离可以拉近,在诸如隐疾应对的此类紧急事件中,避开礼教的障碍。故事夸张而搞笑的情节,实际上是在淡化家庭异性成员在救治隐疾过程中因身体隐私而产生的尴尬,缓冲他们之间的紧张心理。当然,书写者通过有趣的故事情节,也是在吸引更多的读者。笔记小说的读者群体十分广泛,他们通过小说对私密空间的描写,以及对隐疾病家心理的想象,获得了隐疾应对的一些医学知识,隐疾应对通过广泛的读者群体而成为公开的事件,从而突破了礼教的限制。
3 清代女性隐疾应对与礼教文化
由上可知,在清代女性隐疾应对中,病家的压力和痛苦,以及医家的不便,与当时社会的礼教文化有直接的关联。在此,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
3.1 隐疾的不可抗拒与礼教设计的缺陷
如前文所述,清代女性隐疾,不仅包括医学层面的妇科疾病,还包含乳房等身体敏感部位的疾病。这些疾病是每个女性不可抗拒的,上至后宫的嫔妃,下至村姑村妇。因此,隐疾关乎每一个家庭,隐疾应对是清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疾病应对本来不易,礼教的设计增加了疾病应对的困难,这在女性隐疾应对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礼教提倡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甚至主张男女分开走路。两性之间的正常交流因之出现人为的障碍,随着礼教的严格化,到了清代,这种障碍更加突出,对民众的日常生活影响更大。然而,医疗职业的男性化与女性疾病的不可抗拒性,悬置了礼教对性别的规范。清代受过医学训练的医家绝大多数是男性,此类女医甚少①管见所及,清代受过医学训练的女医有丹徒县鲍之镛的妻子、平江陈瑞珠、吴县顾德华,在这三位医家中,只有顾氏留下著述《花韵楼医案》(吕耀斗等《丹徒县志》,卷37“方伎”,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29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27页;淮阴百一居士《壶天录》,见《笔记小说大观》,22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第136页;邱庆元辑《珍本医书集成》,第4册,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年,第255~272页)。,绝大多数女医是产婆,不能治病。女性医家患病,就不得不延请男性医家治疗。一些观念保守的女性,患隐疾后,选择遵从礼教,有病讳医,拒绝治疗。但大多数女性患隐疾后,还是选择延请男性医家治疗。尽管受礼教观念浓厚的病家,采取诸如隔幕诊脉等措施,做适当的避讳。即使如此,医家为女性病者诊脉,也是一种零距离的身体接触。因此,在女性隐疾应对上,礼教的性别区隔所发挥的实际效果不大,在某种程度上被悬空了。如果礼教设计者注意到女性隐疾应对的特殊性②礼教的设计者对女性疾病应对之外的一些特殊情况做出了规定,孟子就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蔡尚思认为,这里的“权”是权宜、例外的意思(蔡尚思《中国礼教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7页)。可见,孟子将生命的救助看成是男女之别的例外情况。,对男性医家与女性病者之间的互动制定出适当的规范,那么,医病间两性关系的处理也就有章可循了,病家也就不会有礼教的压力,男性医家则获得了治疗的方便,疾病的治疗就消除了人为的障碍,仅是技术的问题了。
3.2 难言与困医——医病之间因礼教而产生的误解
礼教在女性隐疾应对上存在的缺陷,给男性医家与女性病家之间的交往造成了误解。有些女性病家为了保护女性的身体隐私,隔着帘幕,让医家诊脉,这使得医家无法做到采用望、闻、问、切四诊法,全面诊断病情。有的病家甚至不言病情,或者歪曲病情,仅医家通过脉诊,判断病证。病家的难言和保护隐私的做法,被医家理解为病家以病困医。为此,他们在医书中直言批评这类病家。医家黄庭镜就说:“有隐疾莫告,有故隐疾,试医工拙”[23]。黄氏虽然没有直接批评,但言语间透露出的是对此类病家的不满。医家杨乘六则批评更为直接:“近来迎医服药者,不惟不先言其所苦,甚至再三询叩,终于默默。而隐疾以困医者,讵知医而果可为人所困者,则其病亦未有不为医所困者也,不亦愚昧之甚耶!”[24]杨乘六认为,不言病情而困医的现象比较普遍,病家困住了医家,其实也困住了疾病治疗,因此,这类病家十分愚昧。可以看出,杨氏对困医的病家很愤怒。
医病之间产生的这种误解,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由礼教造成的。
3.3 医学身体与社会身体——医病双方不同的身体观
在女性隐疾应对中,医病双方的分歧和误解,其实也表现了双方不同的身体观。病家认为,身体不仅是生物躯体,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着社会的意义。尤其是女性的身体,以其与男性身体之间严格的区隔,维护着当时的礼教制度。从这个角度看,女性患隐疾后,病家千方百计保护身体隐私,这在情理之中。
然而,从医家对女性隐疾应对的书写来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似乎并不关心身体的社会意义,以疾病治疗为主,将男女有别的礼教置于次要地位。这反映了当时医家的身体观,即他们认为身体是医学意义上的。问题是,医家也是社会的人,也应该受当时礼教文化的影响。为何他们对身体的社会意义视而不见?如前文所述,经济利益是问题的关键,医家对利益的看重或许与当时社会的商业风气有一定的关系①“明中后期开始,伴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士好言利’的社会氛围和‘弃农从商’及士人‘弃儒从贾’的社会现象”(张海英《明清商业思想发展及其转型困境》,《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148页)。可见,当时有重利的社会风气。。
4 结语:医疗视野中的清代礼教
隐疾本来是一种疾病,是生物性的,但因出现在身体的隐私部位,而具有了文化的意义。在不同时代,隐疾的内涵有所不同。在倡导“男女之大防”的清代,隐疾含义具有浓厚的性别色彩。易言之,尽管男性性器官方面的疾病也被称为隐疾②清代医家王士雄和罗越峰认为,羊外肾可以治疗阳痿、遗精等男性隐疾。参见王士雄《随息居饮食谱》“毛羽类”(盛增秀主编《王孟英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236页)及罗越峰《疑难急症简方》卷3“男妇阴中诸症”(《珍本医书集成》,第3册方书类,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778页),但在隐疾应对中,面对同性医家,一般情况下,病者不会产生害羞之情③在王士雄治疗吴云阁和徐大椿治疗沈维德的两则医案中,医病之间的交流都不存在障碍(王士雄《王孟英医案》,卷2“阴虚”,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年,第159页;徐大椿《洄溪医案》“下疳”,见刘洋主编《徐灵胎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399页)。不过,要是患了与同性恋有关的性病,男性病者也会隐匿病情,保护隐私。丹徒县名医王九峰在治疗孟河一位富翁的龙阳毒时,这位富翁就隐瞒了自己的病情,即使王氏识破真相,富翁也不愿自述病源(余景和《诊余集》“龙阳毒”,见刘更生主编《医案医话医论名著集成》,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年,第431~432页)。。在同性之间,身体的隐私没有多大的意义。相反,隐疾出现在女性身体上,在应对的过程中,面对男性医家,女性病者及其家人就面临很大的思想压力,设法保护病者的身体隐疾。同时,女性病者对隐疾的认识以及对身体隐私的保护,会因社会阶层而有较大的不同,一般来说,社会上层和礼教影响较大的女性病家,对身体隐私的保护更为看重,而社会下层和礼教影响较小的女性病家,更看重疾病的治疗,身体隐私的保护则是其次。
在女性隐疾应对的过程中,面对礼教,医病双方的策略不同。为了保护隐私,病家采取的策略主要有:(1)不让医家当面给病者诊断,而是给其表述病情。(2)延请医家诊治,首先不言病情,仅让医家诊脉。要是诊断与病情相符,病家才坦言相告。(3)面对医家,如果实在无法启齿,就歪曲病情。(4)病者如系未婚少女,病家则寻找未婚貌美的男性医家,先与病者结成夫妻关系,然而施治。这是一种理想的选择。(5)家庭成员之间救治隐疾。(6)如若没有做出上述策略的条件,则直接面对医家。为了满足病家保护隐私的心理和方便治疗,医家选择的策略有:(1)顺从病家的要求,不诊视病者,或不当面询问病情,若非得望诊,则要其他女性代替。(2)通过说理或医病两家的友情,开导病家,化解其压力,以便说明病情。(3)要是需要手术,则与病者结成准血缘关系。总体而言,病家保护隐疾的策略,容易使医家误以为困医,或考医,由此心中产生不满。医家的策略部分缓解了病家的礼教压力,满足了病家保护隐私的需要。
与饮食男女④“饮食男女”一词指食欲和性欲的意思(宋永培、端木黎明主编《汉语成语词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956页)。一样,医疗也是人们生存的一种基本需求,对大多数人来说,与这种基本需求相比,礼教是次要的。同时,女性隐疾应对,从根本上讲,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包含着女性病者与男性医家之间的性别关系。从逻辑上来讲,前者是第一位的,后者是第二位的。在隐疾应对中,根本的问题是医家和病家一同战胜疾病,而非男性医家与女性病者之间关系的处理。此外,礼教没有对女性隐疾应对中的性别关系做出相应的规范。受上述三种因素的影响,在大多数病家积极应对的过程中,主流社会所提倡的男女之大防的意识形态,尽管发挥作用,但其作用不是实质性的。因此,在女性隐疾应对中,礼教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了。从这个礼教实践的视角看,清代礼教有一个新的面相。从理论层面看,清代礼教相对前代来说,更加严格,似乎对社会的影响很大;但从实践层面看,当时的礼教对社会的影响是有限的,尤其是在社会下层,异性之间交往有较大的空间。即使是在中上层社会,异性之间的交往也有一定的空间,尽管这种空间的大小往往因当事人及其家庭的观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同时,本文的研究显示,从疾病史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社会,我们会得到一些新的认识。
致谢 在本文修改的过程中,业师余新忠教授和审稿专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笔者在此一并致谢。
1 杜芳琴.中国女性/性别史研究六十年评述:理论与方法[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9,(5):13~20.
2 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86~405.
3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368~376.
4 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403.
5 陈宝良.清初礼教秩序的重建与士大夫精神史的波折[J].浙江学刊,2013,(2):39.
6 王夫之.宋论[M].卷4“仁宗”.北京:中华书局,2003.76.
7 高颜颐.“空间”与“家”——论明末清初女性的生活空间[M].∥邓小南,王政,游鉴明.中国女性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74~199.
8 李伯重.问题与希望:有感于中国女性史研究现状[J].历史研究,2002,(6):157.
9 王焘.外台秘要[M].卷34“八瘕方一十二首”∥张登本.王焘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868~869.
10 程国彭.医学心悟[M].卷5“妇人隐疾”∥曹炳章.中国医学大成.第46册.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47.
11 王士雄.鸡鸣录[M].“女科第一”∥盛增秀.王孟英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581.
12 陈东原.中国女性生活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177.
13 李贞德.中国女性史研究中的医疗照顾问题[J].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2):86~87.
14 孙一奎.孙文垣医案[M].卷2“三吴治验·吴氏妇隐疾”∥曹炳章.中国医学大成.第36册.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50~51.
15 魏之秀.续名医类案[M].卷19“前阴”∥裘沛然.中国医学大成三编.长沙:岳麓书社,1994.1035.
16 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M].医案第三梦影∥盛增秀.王孟英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168.
17 郑重光.素圃医案[M].卷4“女病治效”//珍本医书集成.第4册医案杂著类.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638~639.
18 郭志邃.痧胀玉衡[M].后卷“妇人隐疾痧”∥曹洪欣.温病大成.第4部.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83.
19 余景和.诊余集[M].“龙阳毒”∥刘更生.医案医话医论名著集成.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447.
20 王士雄.归砚录[M].卷3∥盛增秀.王孟英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443~444.
21 袁枚.子不语[M].卷23“疡医”∥笔记小说大观.第20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157.
22 采蘅子.虫鸣漫录[M].卷2∥笔记小说大观.第22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363.
23 黄庭镜.目经大成[M].卷1下“人情论”∥傅景华.珍本医籍丛刊.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7.81.
24 高鼓峰.四明心法·诊法[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