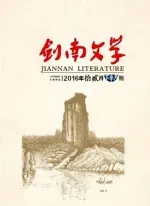城市生活
■戴 岱

夏日黄昏。五彩斑斓的人群像漂浮物一样,在燠热的街筒里淌过来,淌过去。
佳佳从大院里出来时,看见老廖在门廊里修自行车。
佳佳的印象中,老廖总是自己修车。佳佳的车从来都是送去修车店里。先前是自行车,最近是 “木兰”。把车往修车师傅面前一放,双手抱在胸前,佳佳居高临下看修车。
老廖好象从来就没有进过修车店,车也一直是那辆颇有陈旧感的“永久”牌。修车的家什倒是添置得越来越齐整了。
老廖蹲着,佳佳立着,立着的佳佳就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佳佳推出门廊里的“木兰”,坤包里拈出钥匙,姿势幽雅地一捅,一拧,“木兰”就突突着火了。排烟筒里喷出淡兰色的烟雾,搅起灰尘一起扑向老廖。佳佳和她的“木兰”梭鱼一样,轻飘地游出了大门。
佳佳总是在黄昏出门。唇红眉弯乳沟现,花枝招展一步三摇。佳佳一出门,夜生活就开始了。
老廖心里一阵莫名的冲动和烦躁。
老廖没正眼看佳佳,却眼角余光烙铁一样一直觑着。佳佳出来时,老廖正向里蹲着修车,拧一颗螺丝。只一眼,就在心底印上了佳佳白嫩的乳沟和短裙下的大白腿。佳佳走近时,老廖探身去工具箱里找工具,就势换了个蹲姿,面向了大门外。瞟佳佳的屁股。佳佳抬腿上车时,短裙下白腿一闪也没逃脱老廖鹰隼一样犀利着的视线。
老廖自己也觉得,自己虚伪。
老齐也是。那天,老廖一步跨进办公室,老齐正鹅一样伸着个长颈子,瞅窗外。老廖透过半掩的窗,就正好看见了佳佳远去的背影。听到背后动静,老齐急忙缩回头,一脸尴尬。
“嘿嘿,”老齐笑着,说:“今天又是大太阳哦。”说了,又去瞅窗户外的天。
“就是,就是。”老廖说,也去瞅窗户外的天。
老廖就觉得老齐也虚伪。其实,他们这辈人,都放不开的。
人生四十不惑。老廖和老齐,都是四十好几的人了,什么不懂?老廖感觉里,他们这辈人活得累。那话怎么说?胀死眼睛饿死球?有贼心没贼胆?
“佳女子现在,”到底还是由老廖拾起了话题,“越来越……”老廖笑着,去拾掇办公桌上的茶杯和文件,下半截话没出口,却是此处无声胜有声地更加意味深长了。
“球,”老齐缓过劲来了,立刻雄起,愤愤地说,“球,啥女子哦?早已是千人骑万人压的婆娘了!”老齐说,佳佳经常在宾馆里出入,陪那些有钱的老板睡觉。那些老板和她父亲年龄差不多的。
其实,这些都已经不是新闻,但却是常说常新的话题。
老廖就在心里痛快地笑了,笑老齐的酸葡萄情结。
“骚货!”老廖心里骂一句。
“狗日的骚货!”老廖望着佳佳的背影骂,心里骂。
老廖使劲拧螺丝,心里还骂,“又出去卖了,骚货!”
老廖心里一阵莫名的冲动和烦躁。
老廖不知道,他会跟佳佳这个骚货遭遇。现在他不知道。
佳佳是个骚货,地球人都知道。大院里男、女背了她都骂骚货,当了面却谁也不提说。好象从来就没有这回事情。甚至女人些见了佳佳新奇搞怪的衣服,还总要围上去,摸摸捏捏,问个价钱,打探在哪里买的。往往,佳佳的衣服都是价钱高得出奇,听了的莫不象被蛇咬了一样,喔唷一声,惊跳了开去,连声说,买不起买不起,我们这些人肯定买不起的。“我们这些人”几个字咬的特别重,仿佛在特别申明她们之间的不同类。佳佳也并不多意,只是笑着就昂了头走人。
老廖把螺丝拧得死紧后才发现,后护泥罩的半边支架还没上。
“日他妈!”老廖骂一句。
“日他妈,”老廖笑一笑,说,“早晨起来眼皮跳,搞了头道搞二道。”
佳佳是本单位老吕的独女。先前是在县丝厂上班。
佳佳长相一般。脸上几粒雀斑,集中在鼻翼处昭人。皮肤白,却少血色。素打扮时,“丝妹儿”中间她也就中等的份儿。耍了两个男朋友,刮了两次宫,都没成。
那时在院里进出时,见了老廖总是谦和地笑,叫一声:“廖叔。”
老廖是副科,老吕才是主办科员。那时老廖心态好,听了招呼,总是响亮地应一声“哎”,还总要回一句问候:“小佳,上班去了?”或者是“下班了小佳?”也是居高临下,叔叔辈的感觉。
后来,丝厂破产了,佳佳成了失业的下岗女工。四处去找工作,找了一个多月都无着落。后来去了宾馆,去了不久就变了样子,一日日花枝招展起来。
老廖重新上好后轮,倾斜了车身,支上脚架,握住踏板转轱辘,转得呼呼风响。总算是弄好了。拍拍手,老廖把地上的工具、零件一一拣进工具箱里。
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才有钱。日他妈,这二年就这理儿。
现在的佳佳,哪还有一点以前的影子?到宾馆上班不久,就变了。先是化妆,脸上画得红是红,白是白,眉毛象柳叶儿。眼圈一画,一对原本平凡的眼珠子就猫眼一样黑亮了,波光闪闪。鼻翼的雀斑,也变了妩媚和柔情。一对辫子盘成髻,在脑后巍峨、玲珑。后是衣服,上衣变得短和小,下装紧又贴,变魔法似的一下就显得凹突有致、韵味无穷了。
这不,才初夏,胸脯和后背就都露了一片肉出来。窄短的裙,包得两腿只能迈出小米粒儿似的碎步,却屁股左扭右扭,第一眼就能粘住了男人的眼睛。
看着佳佳一日一个样,大院里人就都有了一种老鸹变白鹤的沧桑感。
佳佳先还躲闪,后来就坦然了,昂着头进出。神情里明白地昭示着“你知道不知道都是那么回事。”
自惭形秽的,倒是老廖们。这些年,企业不景气,一个接一个破产,工人日子难过。就是老廖他们这些吃财政饭的事业单位,也是日渐一日地捉襟见肘。开始是奖金没得拿,后来就工资滞后发。月月如此。
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也是这二年的理儿。
大院里陆续有人松闲着出来,松闲着游进街筒里。
夏日的小屋子,和西双版纳一样留不住爸爸,也留不住妈妈。
小贾和他的女友,也出来了。小伙子名牌体恤、西装裤、皮鞋铮亮,女友也是分外妖娆。
小贾分到科里才一年,工作懒懒散散,却是搞女朋友勤奋有加。不断有新面孔的女孩子在他的身边出现,而且又都是极其缠绵的样子,以为要地老天荒的。又都每次都还没到让人眼睛腻烦的程度就换了。换了,又每个都是那么地花枝招展着,好象世上的漂亮女孩儿都被他吸引过来了。又好象,天下所有的女子都在一夜之间变漂亮了。
小贾的老爸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做老总。衣是人的脸,钱是人的胆,小贾有脸也有胆,满世界谁都不在他眼里。老廖这个科头儿,在新职员小贾面前,常有心虚气短的时候。老廖也早就习惯了。
“廖科,走,OK一盘去!”小贾说,小贾一脸的嘻皮。
“走哇。”老廖说。
“跟你们年轻人去操一盘,起码年轻十岁。”老廖说。老廖用抹布擦着手。
小贾就伸了手去拉老廖,老廖嫌自己两手脏,该出手时没出手,就被小贾拉了个趔趄。
“你们快去哦。那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老廖嘿嘿地笑着,笑却是谦卑的笑,谦卑是不自觉流露出来的。老廖用眼角瞟一眼小贾的女朋友。小贾的女朋友真好看。
小贾搂了女朋友,潇洒地笑着,也游进街筒子里去了。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一个人流泪到天亮……”走远的小贾甩下一路断断续续的嘶吼。
老廖把擦车布塞进座垫下,拍拍车座,完工。
老廖自己修车多年,已成了一名熟练的修车师傅。老婆的车也是他修。旧车毛病多,一月总有好几次修。送去修车店一整几块,一整几块,一月算帐下来,就心疼了。敝帚自珍,在老廖还是小廖的年代,是高尚的情操;现在却是窘迫的无奈了。老廖的指甲缝里,常有洗之不尽的污垢。
拎着工具箱上楼,屋里传来电视声。果然,儿子在看电视。
老廖混了二十几年,才弄了个两室一厅,且房屋的产权还只有一半跟自己姓。沙发破旧了,电视也跟不上趟。此刻的儿子,正蜷在旧的沙发上,两眼死死盯着屏幕。脸上的光斑,忽明忽暗着,象机器人一样怪异的样子。
老廖心里有些恼火。现在的孩子太不懂事了,除了吃喝拉撒,啥都要大人耳提面命。读初一的孩子了,做作业还要家长时刻提醒。简直没一点点的自觉性。
老廖常说,我们小时候,哪里有现在一半的条件好啊?早晨天不亮就起床煮饭,匆匆吃了赶十多里山路去上学;放学回家了,不是背了背篼去打青草,就是拎着竹筐拾粪。做作业都是点煤油灯,熏得鼻孔黑糊糊的。还得抓紧啊,不能多浪费灯油。但是,这样的话老廖已不能再说了。他一开口,儿子准说,现在是啥子年代口罗?跟你那时比,我们这个社会都莫法进步了!呛得老廖半天回不过来神。再开口就怵,不敢再提“那二年。”
“作业作业!日你个先人板板哦!再看老子把电视砸球了!”
“给老子把电视关了,做作业。”老廖气呼呼地吼着。
没想到,被吼起来的儿子却给老廖找麻烦。儿子问老子要钱。
“我们有个同学,明天的生。”儿子说。
老廖楞楞地望着儿子,老廖不明白。
“他生他的,关你啥子事?”老廖说。
“又不是你过生。有你屁事。”老廖说。
“全班同学都要去的。她是我们班长。”儿子说。儿子的小眼睛鼓起来也是蛮精神的。
“你给我拿钱,我要给她买礼品。”儿子说。
“给我拿钱!”儿子说。
老廖明白了。老廖瞪着儿子。儿子也瞪着他。儿子的眼睛象老廖,小而聚光。精光暴射时很有威慑力的。可惜,儿子跟他一样,只在家里显示小眼睛的威力,极其缺少在外面展示的机会和能源。
老廖扛不住了。老廖从裤包里抠半天,摸出一张十元的票子,皱巴巴的。老廖恶狠狠地把钱扔到斑驳的木茶几上。
“拿去嘛!孽债!老子前辈子欠你龟儿子的孽债!老子晓得,你是来收债的!”老廖说。像终于卸下些什么,老廖拎了工具箱去往床下塞。
“不够!眼屎巴一点钱,买屁啊!”儿子说,儿子的声音突然大了好几倍。
“钱不够,老汉儿!”儿子说。
“要好多?老子把银行给你搬回来,要得不?”老廖气哼哼的。气是气,还是又从口袋里抠出一张10元的票子,没好气地摔给了儿子。
“老子前辈子欠你龟儿子的!”老廖气呼呼地说。一边就把工具箱塞去卧室床下。
老婆在卧室清帐。零钞摆一床。和客厅一样,卧室的角落里也都码着袜子、凉鞋等百货,显得凌乱不堪。
“廖斌看电视,你也不管?”老廖瞥一眼老婆,抱怨说。
“咋管?”老婆头也不抬,继续清理她一天的账务。“他要看,老子把电视机背身上?”
“你啥都依了他,学习咋办?将来考不上大学,哭都晚了!”老廖说。面对满床皱巴巴的零钞,提不起他丝毫兴趣。
“学不学值狗球!”老婆也没好气了。“学不学值狗球!”
老婆说,你那二年学习该用心嘛,现在如何?还不如一个留级生混得好!
老婆一句话就把老廖打哑了。老廖有几个读书不怎么样的同学,他曾经把他们在学校的丑事当笑话讲给老婆听,同时炫耀自己的正经、好学。那时,老婆还不是老婆,是对象。没想到时过境迁,曾经调皮捣蛋的差生同学,现在却一个个都是腰缠万贯的大款了。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成小城里举足轻重的人物,跟书记、县长称兄道弟。哪里像老廖,有他不多无他不少的个小角色。
被老婆抢白,老廖心里更加憋闷,很是悻悻然。
老婆下岗后,老廖没能帮她找到一份好工作。老婆自己厚了脸皮去大街摆摊,老廖一家之主的地位日益衰落。
一直到了大街上,老廖还气结在胸。
街上人真多。熙来攘往,花花绿绿,不绝如缕。老廖随意走去。
夏日的傍晚,街筒子里一派松闲气氛。行人身上的饰物都轻薄,几乎无了负荷。步履也是软着,仿佛可走可不走地迈着,踱着,很是优雅的样子。其实,内心里也都是欲望四射着。一双双暗里烁烁偷窥的眼,少了白日的岸然,多了些本色的流露。
老廖走着,心里的气慢慢消了些。此起彼伏的灯,闪闪烁烁亮起来。亮起来,小城的夜就地道了。多姿多彩地诱人,和温馨了。
一家家商店,灯火通明。老板眼巴巴地望着街上的行人,期冀着上门的顾客。这二年,下岗的人多了,人们都纷纷涌到大街上来讨生活,这生意就愈是艰难了,买的没有卖的多。生意人坐冷板凳,就成了家常便饭的事。转到小吃一条街,却是另一种景象。街的两边,摆满了小吃摊。散啤酒,麻辣烫,烧烤,串串香,小火锅,火爆田螺,冰粉,乐山飘汤,云南米线,宜宾燃面……应有尽有,琳琅满目。几把沙滩椅围一张小桌,就成一处生意。光着膀子的男人,袒胸露背的女人,喝酒划拳,热闹非凡。小城是穷县,却是出了名的好吃好玩。白天,大街小巷里摆满了卖薄饼儿的小摊。一个背篼扣地上,上面放个小簸箕,平底锅里摊出比铜钱大不了多少的熟面皮,瓷钵里装了莴笋或土豆切成的细丝儿,旁边一溜儿盛了调料的小塑料盒。来了食客,围了小簸箕坐一圈,一个面皮包了小撮拌了熟油辣子的菜丝,吃得嘴里咝咝直嘘气,却津津有味得很。有一次,来了个省城的记者,在大街小巷里转悠时,发现穿戴时髦的女孩,却围着街边的小簸箕人人吃个红嘴圈。像是发现新大陆一般,拍下照片在报上发表了,让小城里人很是自豪了一阵子。
“一个人用在吃上面的花销越大,就说明他越贫困。”老廖记得在报纸上看过这样一句话。当时不太明白,后来才理解了。这话是真理。一个城市也是这样,越是贫穷越吃喝风盛行。
“老廖,一个人单操哇?”突然有人招呼。“噢,啊,”老廖吃了一惊。他正暗里盯着一个女人的身影。
是熟人,一家三口。
“一个人单操,安逸噻。”老廖说。老廖尽力做出潇洒的样子。
但老廖脸上却忍不住有些发烧。其实,中年男人一个人单溜是可悲的。有钱的男人,呼朋唤伴喝酒唱歌寻热闹;没钱的男人带着妻儿压马路图个家庭和睦。一个大男人在街上无所事事地蹓跶,算怎么一回事呀?
和熟人道别后,老廖走出好长一截街筒子心里还尴尬着。
“一个人走,其实没意思。”老廖想。
“没球意思,一个人。”老廖心里想。
“要是包里有钞票,一个人就有意思了。”老廖想。“男人有了钱,好玩的地方就多了。”但老廖没有钱。主要是没有玩的闲钱,或者说,钱不宽裕。
老廖也想和老婆和儿子一起散步,那样才有意思。他们原来就是那样。每个黄昏,吃完饭的他,都会和老婆、儿子牵着手,在大街上悠闲地走。感觉里,全是城市人的自豪和自得。老廖还不是城市人的时候在乡下。天一黑人就只能龟缩在屋子里,外面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也没什么好玩的。无聊极了。所以,他极是喜欢在城市里灯火通明的街道上散步,给儿子讲他在乡村的过去。可现在不行了。儿子大了,作业多了,也有他自己的伴了。老婆起早贪晚守摊,没时间也没精力。就此告别了一家三人行的黄昏。
老廖也怕和朋友一起 “群操”。男人在一起,吃吃喝喝太耗钱,老廖手长衣袖短。
衣是人的脸,钱是人的胆。老廖没胆又少脸,日子就孤单和凄惶。
要是老婆的企业不垮就好了。那样,即使儿子不能来,作为上下班有序的老婆也可以陪自己一起散步的。那些企业,好好的,几十年都过来了,咋就一下子垮了呢?老廖想不透。以后会怎么样,老廖也很茫然。
街上千娇百媚的女人,千姿百态地走着,一个比一个花俏,或丰腴,或窈窕,阿娜多姿,成就夏日里街筒子里一道靓丽的风景。老廖心里一阵莫名的冲动和烦躁。
在满街女人裸露的胸脯和短裙下光滑大腿纷呈的景观中,老廖感到了一种缺陷,那就是女人普遍的低胸。在女人努力展示体态的时代,作为女人重要部位的胸的不丰满,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老廖少小时,在乡村见过无数胸脯饱满而拼命遮掩的女人。现在丰乳、挺乳的药物、器械广告满天飞,却女人不约而同的都小乳。这真是怪事。老廖每每想起,就会诞生不可思议的困惑,觉出冥冥之中不可抗拒的神秘,和上天的捉弄。
前面围了一堆人,有吵嚷声从中传出来。老廖立刻生了兴趣,趋步上前去看。却是坐车的和拉车的吵。坐车的是个年轻人,挺横地骂骂咧咧:“妈妈的X,老子给你脸不要脸哈?”拉车的也年轻,却怯懦,声气和神情都嗫嚅着:“你……一块钱咋行吗?从东关外到五马寺哟,别人都给三块的,你再咋也给我两块嘛!”老廖一听,也觉得坐车人确实过分了。坐车人恼羞成怒,手一扬,啪地就给了拉车人一个耳光。拉车人鼻血淌出来,立刻噤了声。围观人中不乏愤愤不平者,却谁也不愿站出来说句公道话。现在的人,都怕血溅了自家身。老廖也赶紧走开。
当漫无目的老廖看见熟悉的圆柱灯箱时,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又来到了“睡美人”这里。
“睡美人”是一家发廊。近些年,受了外地影响,小城里的理发行业也日益神秘起来了。门脸儿生辉,里面的名堂也兀自多了不少,美容、按摩,和浴足。常见一些流光溢彩的妙龄女郎进进出出,妖艳而招摇,让男人的心都驿动不已。
有一次,老廖和老齐,骑车路过 “睡美人”。 老廖正盯了那不断涌动的圆柱形灯箱看,老齐突然神秘地对他说,这是一家“猫店”。“你不信哪天去试一下,里头的小姐保证给你洗舒服!”老齐说。说时,老齐还怪怪地笑。
老廖一下就明白了老齐的言下之意。当时老廖一笑置之,装出一点也不在乎的样子。暗里,却上了心。记了这叫“睡美人”的地方。路过时,有意无意,总要往里瞅一眼。
圆柱的灯箱,一道道的光带无止无休地盘旋而上,看得老廖头晕。一时想不明白,那一道道的光带,来自何处,又去向了哪里。无休无止,无穷无尽。门楣上的大灯箱,是一女郎千娇百媚的卧姿,和“睡美人”三个血红欲滴的大字。美人却没睡,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样子。老廖瞅一眼,心里咯噔一下。又瞅一眼,又咯噔一下。
迟疑着,老廖走过去了。老廖侧目望望,街上行人熙来攘往,却都是各行其是,没谁注意他。就又走回来。走回来,却还是犹豫。之前也有好几次,老廖走过“睡美人”想进没进。没进,又后悔。
再次转回到“睡美人”门前,老廖心一横,鼓起勇气跨进去了。进门的一刹那,五彩的灯光让老廖感到有些晕眩。
一位胸脯饱满的小姐迎上来,笑意盈盈。
“先生做个按摩?”小姐说。
老廖紧张得手心都冒汗了,腿也有些软。妈的,以前进理发店,老廖从来都是昂首挺胸,哪里这样拘束过?
“洗个头。”老廖说。
老廖说:“洗个头就行,不按摩。”
老廖在小姐指点的皮椅上坐下来时,恢复了些镇定。左侧洗头的小姐也有几分姿色。左侧的顾客却是个一脸横肉的大胖子,感觉不是熟人。老廖就收回了视线。
老廖发现外间洗头的堂子很窄,通往里间的门帘也窄。可他能够感觉到帘后的幽深,和鬼祟。不断有戚戚的低语和压抑不住的浪笑挤出布帘的缝隙,昭示着里面的繁华。
这时,通往里间的门帘一掀,出来一个高挑的小姐。长裙飘然,裸露的胸脯上一条金项链闪烁耀眼。高挑小姐老练而老辣的样子,看起来像老板。
像老板的小姐像对老熟人一样热情地对老廖笑。
“洗头哇?”老板说。
老廖觉得她的声音很好听。像成都人那样温和,和绵软。
“小李,你进去给二号上面膜。”老板说,“我来给这位大哥洗头。”老板把老廖身后的小姐支走了。
“这位大哥第一次来,我亲自给他服务哈。”老板说,一边麻利地给老廖围上了白布单。一股好闻的香水味钻进了老廖的鼻孔。
叫小李的小姐应一声,就撩开帘子进去了。老廖从前面的镜子里看到小李丰满的屁股一扭,就消失在布帘后面去了,心里约略地泛起一丝憾意。身体干瘦的老廖却喜欢丰满的女人,偏偏老婆又是一个骨瘦如柴的女人。
老廖从镜子里瞟一眼老板,虽然面容也姣好,却不够丰满。遗珠之憾再次升腾在心里。又瞟一眼布帘。
“大哥贵姓?”老板一边麻利地在老廖头上倒上洗发液抓挠着,一边和他攀谈。
“我,姓廖。”老廖说。老廖感到自己的声音因为兴奋而有些变调。
“哦,廖哥。”老板说。
老板说:“廖哥在哪里发财啊?”
老廖就有些尴尬,“发啥财哦,”犹豫了一下,说:“在一个破单位上班。”
老板似乎毫不在乎,仍是热情的声音:“一回生,二会熟,廖哥以后可要多照顾小妹的生意呀!”
“要得要得。”老廖竟然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一口就答应了。老廖觉得这女老板挺招人爱的,也很会做生意。心里一高兴,人就活泛些了。攀谈的愿望像蜗牛的触角,一点一点冒出来。
“老板是成都人?”老廖问。
“不是。”老板眉毛一扬,很有兴趣的样子,“廖哥咋说我是成都人喃?”
老廖笑着,“我听你口音像成都那个方向的呀。”
“嘿嘿。”老板也笑了。
“我在成都学的理发和美容,在那里呆了几个月。”老板说。
“哦,”老廖恍然大悟的样子,“怪不得哟。”
里间的低语和波浪一样,愈加汹涌。老廖细了心捕捉,心里一阵莫名的冲动,和躁热。
“王哥,再进去洗个面哈?”左侧的胖子洗完头,身后的洗头小姐立刻不失时机地问。
胖子哼哈着,就跟在小姐的屁股后进到帘子里面去了。老廖一阵心动。老廖不明白洗面是怎么回事,但觉得与那些不可告人的事有关。或者,洗面就是个幌子。心里,就像微风荡漾的湖面,涟漪不断,动荡不已。
当老廖的头洗完,老板轻声问:“廖哥,你也洗个面哈?”
老廖不自然地咧嘴一笑,掩饰说:“我啊,都老头子了,还洗啥面嘛?”
但冰雪聪明的老板已经看透了老廖的心思,莞尔一笑,“到我这里洗一次面,包大哥你年轻十岁哈。”老板一边说,一边就往里间引老廖。
老廖兴奋而羞涩地跟在老板身后,撩开布帘时竟有些手忙脚乱。
里面光线暗淡,刚进去的老廖感觉云烟缭绕,香风扑面,仿若仙境,看什么都若隐若现。老廖努力睁大两眼,迅速而贪婪地搜视着里面的一切。
其实,里面并没有想象中的深不可测。只有被层板和布帘隔出的四个小间。里面的三个小间都有了客人。老廖被引进最靠外面的一间。和外面的堂子仅一板之隔。外面的说笑声,和里间的窃窃私语,老廖都能听个满耳。
隔间实在窄小。靠边摆张按摩床,剩下的空间就只够按摩小姐行走。床也极窄。老廖躺上去,两只手还得抱胸前,不然得吊床沿下去。
老板让老廖躺下,老廖有些迟疑。在一个陌生的年轻女子面前躺下,老廖有些不习惯。老廖还是躺下了。
老板拿来盛了热水的小盆,毛巾,和一堆高矮不一的瓶子。玻璃的,陶瓷的,塑料的,形状各异。老板用毛巾沾了水,在老廖的脸上擦拭着。然后拿起一个小瓶往老廖脸上倒出乳白的液体,用手掌反复抹,抹。还打开一台呼呼喷气的机器,对着老廖的脸喷蒸汽。老板走动时,老廖的手就擦着她的腿,或者腹。老廖心里痒痒的。老廖的手几次想有些动作,但却犹豫着始终不敢。紧张、兴奋。老廖的背上出汗了,濡湿了衣服。老廖没说。
外面又来客人了,高声大嗓要找老板。老板听了,就停下了手里的活。她喊了声小李,就有个胖乎乎的小姐出来接替了她的工作。李小姐有着饱满的身体,圆润的脸潮红带笑,让老廖心里感到熨帖。却很快看出,李小姐的笑,不是因为他。他想,李小姐来之前,定是和其他客人调笑过。老廖心里一阵骚动。他想瞟一眼李小姐的屁股,却不敢侧脸。脸上正有蠕动的液体。
李小姐接着给老廖洗,用了好几种香味各异的洗料,慢慢地洗。李小姐胖乎乎的手指在他脸上柔柔地抹,柔柔地搓。侍弄得老廖很舒服。给了钱的服务就是享受,在家里洗脸三两下就完事,哪有这么舒服啊?老廖的手,几次想动作,却最终都没有。老廖想找些话来说,也找不出。老廖觉得有些无趣。
老廖总是心怯。老廖恨自己的没出息。
洗完后,上面膜。除了眼睛,老廖的整个面部都被涂上了凉悠悠的面膜。老廖闻出一股石膏味儿。上完面膜,李小姐就空闲了。空闲了的李小姐在老廖的身边坐下来。她随意地拉起老廖的一只手,抚摸着。老廖立刻就有了醉酒的感觉。
李小姐柔声说:“大哥,你以后经常来我们这里洗面嘛。”
“经常洗面,皮肤就会好得多。”李小姐说。
老廖突然想起自己的指甲缝里有着洗不尽的油垢,就有些难为情。要是在明亮处,是一眼就可看清楚的。刚刚感受到的幸福感也立刻像潮水一样退去了。
后来,老廖回想起这一幕,就后悔。那个李小姐明明是在暗示他,可他却糊里糊涂地忽略了,白白放过了一个机会。老廖很气自己的怯懦。老廖自己也瞧不起自己。
李小姐要老廖经常来,老廖嘴里连连答应着,却心里苦笑:来他妈个脚!老子哪里有这个闲钱呢?老廖希望李小姐有进一步的动作。他想,如果李小姐能有进一步的动作,他也就动作。决不犹豫。李小姐却放下他的手,掀开布帘出去应付别的客人了。
老廖立刻怅然若失。老廖一动不动地躺着。脸上的面膜开始干,皮肤有些发紧。老廖有些无聊,就盯着墙上的一幅美女图看。美女赤裸着身体,一缕红纱绕过关键部位,留些想象空间。老廖看得心潮起伏。里间传出幽幽的嗤笑。有女声压抑着,说了句讨厌。有男人的坏笑。老廖喉咙有些发干。老廖想起李小姐丰腴的身体,心里一阵莫名的烦躁。
这些男人都他妈的色狼。他们哪里是来理发、洗面,分明就是冲小姐来的。跟逐臭的苍蝇一样。对,就是一群苍蝇!老廖愤愤地想。自己呢?自己是什么?老廖突然就惭愧地笑一笑。又细了心去捕捉里间的动静。
外面有新进来的男人,在大声地说话。他嫌老板安排的小姐不如意。老板就娇了声口,说,你罗二哥要哪个嘛?我马上给你喊来。叫罗二哥的男人就说,还是要上次的三儿。老板说,哎呀,我还以为你要七仙女哩。三儿,好说。你手机给我嘛。就传来一阵叽叽的拨号声。电话通了,让呼那个叫三儿的快点过来。老廖心里一阵堵闷。那个男人居然看不起这些小姐。不知那个叫三儿的小姐又是什么天仙的模样?
但老廖却是无缘得见了。清除面膜,洗完脸,老廖从里面出来时,还见一个男人大咧咧地歪在厅里的沙发上候着。两只脚脱了鞋,蜷缩在座位上,一边玩着手里的大哥大,一边哼着:“你总是枪太软,枪太软,一晚上坚持不到天亮……”老廖听了,觉得和小贾唱的差不多,都是不正经的调调。
老廖理理后背粘湿的衣服,摸摸洗过的脸,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对着镜子瞄一眼,似乎皮肤真的白了些。老廖想,有钱真是他妈的好啊!老廖的这种好感觉很快就被中止了。
“好多钱?”老廖一边把手伸进裤兜,一边问老板。
“收钱,老板。”老廖说。老廖尽量让自己说得豪爽些。根据老廖的经验,一般的理发店洗头三元。这里档次高,洗头恐怕得翻一番。洗面呢,恐怕就得十元吧。两项加起来,应该得三十元。却老板轻启朱唇,柔柔一句就把老廖惊了个目瞪口呆。
“廖哥头一回来我这里,给你算个优惠价,就给五十嘛。”老板美目顾盼,微笑盈盈。
“就给五十嘛。”老板说。老板小姐很是难为情的样子,站在老廖面前,像个娇小的女儿,在等着父亲给零花钱。
老廖像被一下扔进了冰窖,脸上的笑还僵着,心里却乱成了一团麻。他怎么也没想到,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就要五十元,还是优惠价!他记得从家里出来之前,儿子曾向他要钱,他兜里一共就50元,给了儿子二十元,就只剩下了三十元。这可怎么办?要现洋相啦!老廖急出一身冷汗。
老廖心里叫苦连天:“糟了糟了!今天要丢人了!”。
“死狗日的,要是不给啥子鬼礼钱就好了!”老廖在心里把儿子恨得要死。
老廖在裤兜里掏一阵,摸出了早就清楚的三十元,却做出很意外的样子:“哦,对不起,晚上出来,没想到要洗头……嘿嘿,钱没带够……真是不好意思……”老廖口吃起来,他抹下了手腕上的表:“我把表,放你这里,明天带钱来取……”
老板见多识广,脸上依然笑着,大度地说:“没关系,没关系。”
老板微笑着,把钱收了,也收了老廖的表。
“你明天来取就是了。”老板说。
老廖眼角的余光看见那个叫罗二哥的男人明显的睥睨眼神。老廖想钻地。老廖讪笑着,脸上的肌肉横七竖八地牵扯出些笑来。老廖急忙转身往外走,逃似的。
老廖万没想到,他会在此时与佳佳相遇。佳佳与老廖,差点撞个满怀。一个进,一个出。
两个人都同时吃了一惊。老廖做梦都没想到会在这里与佳佳遭遇。老廖像被人捉了奸一样狼狈,和心慌。还是佳佳先醒悟过来。佳佳在一刹那的愣怔后,理解平静了脸色,没事人一样,闪身进去了,仿佛根本就不认识老廖。老廖舒了一口气,快步走出去。
背后传来男人喜兴的叫声:“哎呀,三儿,你好难请啰!”
佳佳的声音:“哎呀罗哥,我可是一接到你的传呼,气都跑断了哟!”
佳佳就是三儿?匆匆逃离的老廖想,原来佳佳在这些地方叫三儿。果然,老廖在门口看到了佳佳的那辆女摩 “木兰”,老廖一眼就认出来了。看来佳佳不止在一处“上班”,而是同时在几个地方赶场子。
听不到背后的声音了,老廖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哎,这个鬼地方,真不是穷人能来的!”老廖愤愤地想。
走出老远了,老廖才回头去望了一眼,又一眼。突然明白,里面的事情,并不是在外面想象的那样。至少,不全是。
昏黄的街灯依旧昏黄。闪烁的霓虹灯,也依旧闪烁。却行人变得稀少了,大街开始冷清,和幽凉。老廖不由加快了脚步。
看着人前那么妖娆的佳佳,却在背后曲意逢迎,讨好那些下作的男人,也是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辛酸和苦楚。再一想,那些衣冠楚楚的新贵,体面的背后定然也有着自己的难处和艰辛。老廖心里突然释然了。像被寒霜打了的菜叶,春风一吹就舒展开了,简直就是舒展透了。
老廖觉得,这小城现在更像个城市了。当初,他从学校出来被分配到县城工作,农村娃变了城里崽,心里美极了。那时,就觉得这个城市真是美啊!笔直的街道,下雨天也不用担心打湿鞋。晚上大街上亮着灯,人们可以赶场——当然,城里人不叫赶场。赶场那是乡下的说法。多美气啊!可现在想想,当初那街道,那商场,哪里有现在这样明丽,这样气派,这样繁华啊?这个城市里虽然还有那么多的不如意,可生活却是一日一日地好起来了。
起风了,骤然起的,所以一下子就感觉到了凉爽。如果一直就这样吹着,可能就感觉不到了,甚至还是会觉得热的。其实,这生活也是这样。有热就有凉;有暖就有冻。有乐也就有苦,有笑也就有哭。有好也有坏。全在于你的感觉。这样一想,就觉得生活里还是好的多。不是吗?
既然生活好起来了,干吗还这不满足,那不如意呢?好好活着吧,知足吧,生活实在是太美好了呀!依稀忆起少年时乡村的生活,就觉得这城里生活真的不错了!
老廖正海阔天空胡思乱想着,肩头突然被人一拍,吓一跳。是老齐。
老齐一把抓了老廖的胳膊,说:“咦,你狗日的又跑哪里去潇洒了?”
老廖有些慌乱,说自己只是蹓跶了一下。老廖非常担心老齐发现自己去了 “睡美人”,但老齐的心思不在这里。老齐拉着老廖说了一件新闻。
老齐说:“王大昌糟了!”
“王大昌那狗日的糟了!”老齐的声音里透着明显的兴奋。
“王大昌,糟了?”老廖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老齐一脸严肃:“那还有假?昨天市纪委来人带走的!”
老廖就信了。信了的老廖立刻喜形于色。
王大昌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副局长兼下属单位一把手。劣迹斑斑,却因手眼通天而难以撼动。小城里让人又怕又恨的“不倒翁”。没想到,这个不倒翁也有这一天!老廖感到喝了冰水一样的畅快。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老齐说。同样喜形于色的老齐显得很可爱,老廖觉得。
“就是就是。”老廖应和着,脚底也轻飘了许多。
两个人慨叹不已。老廖摸出烟,两人都点上,舒舒服服吸一口,高高兴兴往回走。
前面有年轻的男女过来。男的搂了女的腰,手在腰上不规矩。女的就如蛇一样扭,嗤嗤地笑。老廖和老齐都看他们亲昵,一直把他们目送出好远,好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