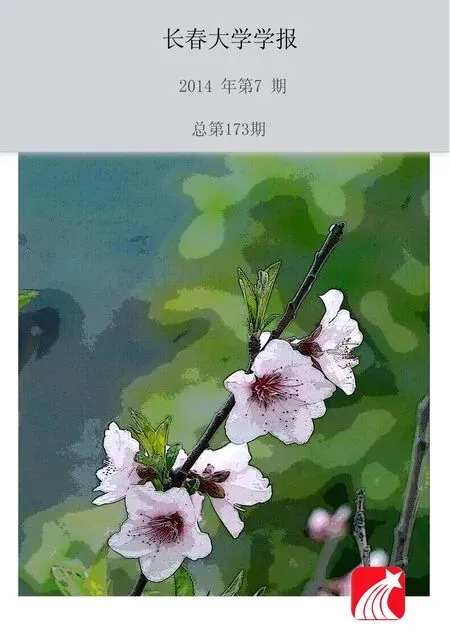小红帽女性形象重建
——结构主义视角下的《与狼为伴》
江妍,孙妮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芜湖 241003)
小红帽女性形象重建
——结构主义视角下的《与狼为伴》
江妍,孙妮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芜湖 241003)
《与狼为伴》是安吉拉·卡特对童话《小红帽》的戏仿之作。文章运用结构主义批评策略,分析小说中存在的三组二元对立项——男性与女性、天真与经验、感性与理性,揭示作者通过改写小红帽与狼人对立的结局建构了一个独立自主、成熟理性的新女性形象。
安吉拉·卡特;《与狼为伴》;二元对立;新女性形象
安吉拉·卡特是20世纪英国最具独创性的女性作家之一,她的作品体裁多样,文风繁杂。魔幻现实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各领域的批评家,都可以其作品作为研究资料。她早年翻译过法国17世纪著名作家夏尔·佩罗的童话集,其中包括经典童话故事《小红帽》。深受童话影响的卡特创作了《梵舟记》短篇小说集,这些短篇小说多以童话故事、民间传说、文学经典为蓝本,再经改写而成。《与狼为伴》就是卡特对经典童话《小红帽》的改写杰作。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她把崭新的当代思想注入了古老的童话”[1]228。在旧瓶装新酒中带给读者新的童话意义。
无论是经典童话《小红帽》还是《与狼为伴》,故事都围绕着一个不变的中心,即狼与小红帽的对立。在这样不变的中心对立中,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又衍生出多组对立,这些对立项组成了文本的结构意义。结构主义学建立在整体性和系统性之上,其基本运作方式是二元对立。“将文化现象进行分解,按二元对立结构框架重新组合,得出本质意义和价值,即文化现象的深层结构。”[2]271通过细读文本,可以发现在狼与小红帽的表层对立下隐藏着男性与女性、天真与经验、感性与理性这三组深层二元对立项。本文将从结构主义视角分析《与狼为伴》中的三组二元对立项,来探讨作者改写童话的目的,揭示新童话中建构的新女性形象。
1 男性与女性的对立
故事中最明显的对立就是狼与人的对立。狼在童话的开头就被描写成强大凶残的恶魔形象,出没在幽深的森林,随时准备吞噬弱小的生命。在新版小红帽的童话正式开始前,卡特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详细描绘狼与狼人因其嗜血欲望而与村民发生的激烈冲突。这些冲突其实是作者用隐喻来预设男女两性对立的一个大背景,为改写小红帽的经典故事埋下了伏笔。
狼与人的多次冲突中,最具男女对立隐喻意义的有3次。“曾经有一个妇女在她自己的厨房里搅拌意大利面时被狼咬伤。”①本文中所引用的《与狼为伴》以及外文文献皆为本文作者翻译。[3]2327还有一次,一个女孩在照看羊群时被狼突袭。在激烈的挣扎和大声的呼喊中,猎人及时赶到并用枪吓跑了狼。最后一次冲突,是狼化为狼人与当地村落中一位年轻姑娘结婚后发生的家庭冲突。狼人在新婚之夜突然消失不见,新娘的兄弟们寻觅了许久也不见其丈夫踪影。“这位理性的姑娘擦干了眼泪,为自己找到另一位丈夫。她为他生了两个健康的宝宝,他们的生活就像三脚架一样稳定安详。”[3]2328就在生活迈向了幸福的轨道时,她的第一任丈夫狼人在冬至的夜晚出现了。狼人进门的第一反应就是以命令的口吻让妻子给自己盛菜。当另一个男人走进房间时,他觉得妻子背叛了自己,气急败坏地吼叫道:“我希望能再次变成狼来给你这个贱人一点教训。”[3]2329话音刚落,他立马变成狼咬断了少妇大儿子的左脚。随后,狼人被孩子的父母用斧头砍死。仔细对比,卡特在小红帽故事开始前特意加入的这3次狼与人的冲突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狼或狼人攻击的对象都是天真柔弱的女性;其次,狼与人冲突的事发情境都是女性正在履行家庭责任;最后,遭到狼攻击的女性凭自己的力量无法解救自己,都要寻求男性的帮助。
狼与人的冲突发生在女性的活动范围之内,狼嗜肉的欲望直指女性,狼幻化为狼人(男人)诱惑的对象也是女性。不难发现,童话中狼与人的浅层对立之下暗藏的是男女两性的对立。故事中,一个有关狼人由来的传说间接暗示了狼人作为男性的隐喻和女性之间的冲突。“山谷那边有个女巫曾将所有前来参加婚礼的人变成了狼,因为新郎娶了别人为妻。”[3]2328在这个传说中,狼就是男女两性对立的产物。在格林版和夏尔·佩罗版的《小红帽》中,小红帽与祖母都摆脱不了被狼吞噬的命运,只不过格林兄弟设置了猎人的角色来拯救小红帽。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观点来看,童话故事所反映的是适应男性社会的道德观,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男性社会价值观的烙印。从这个角度讲,“《小红帽》警戒的对象不仅仅是孩子们,还可以包括其他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4]24。老版的《小红帽》旨在警示女性不要离经叛道(森林小路),否则就会随时丧命。小红帽去祖母家必经的那条森林小路,是男权社会对女性强制施加的道德规约。男性作家创作的童话传达的是对女性的道德警示,由此意味着女性在男女两性上的对立中处于劣势的地位。卡特用象征的手法将两性对立置于一个新的结构中从而改写女性的命运,重塑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形象与角色。由小红帽与狼人的对立引申至男女两性的对立,再由男女两性的对立引申至天真/经验的对立和感性/理性的对立,卡特理想中的新女性形象逐渐被建构起来,跃然纸上。
2 天真与经验的对立
小红帽在之前的版本中是天真的典型代表,她不谙世事,缺乏主见。她在母亲的命令下出门看望祖母,途中轻易被狼人的花言巧语迷惑后就离开了那条象征女性道德规范的安全小径,最后被狼无情地吞噬。虽然小红帽答应母亲不会离开小径,但是面对狼人的狡猾,天真无邪的小红帽还是被狼人当作牵线木偶一样随意摆动。小红帽也为自己的天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食肉动物的化身,只有洁净的肉体才能吸引他。”[3]2334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是成为像圣母玛利亚式的“家庭天使”,以纯洁天真作为衡量女性道德观的标准。然而,这样的天真反而是小红帽丧命的导火索。老版《小红帽》中刻画的纯真克己、被动顺从的女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男权思想的传播工具。童话作为影响儿童的教育媒介之一,无形中宣传了男权思想中对女性的道德规范。女性在这种文化媒介的影响下,会渐渐默许社会对自己的形象定位。而卡特版《与狼为伴》中的小红帽一改往日天真的形象,成了经验的化身,而狼人成了被欲望蒙蔽心智的天真野兽。卡特用了这样的形象颠覆来刻画她心中的理想女性形象。
大多数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都被父权意识形态洗了脑,从而造成了男性优势和女性弱势的既定形象[5]129。卡特的改写打破了这种既定形象,重建新时代的女性形象。她将小红帽的年龄由小女孩设置成青春期的少女阶段,“她身体内的时钟每月都会敲响一次”[3]2330。小红帽与狼人的对立也随之变成了男女两性之间真正的较量。故事的开端,小红帽不是在母亲的要求下去看望祖母,而是坚持自己独自进入森林。“尽管被警告有危险,她确信野生动物无法伤害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她带着刀,不惧任何事物。”[3]2329-2330新版的小红帽有自己的主见,而且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在接下来她与狼人的对立中,她的经验战胜了狼人的天真。狼人伪装成猎人在森林小径上与小红帽相遇,他试图用帅气的外表诱惑小红帽离开那条小径。虽然小红帽开始相信了狼人并将装有小刀的篮子递给他,但她仍然坚持走小径。随后他用打赌的游戏继续诱惑小红帽,他告诉小红帽如果他不走小径先到祖母家,小红帽就要给他一个吻。自认为经验丰富的狼人以为凭借自己的“猎人”魅力可以轻易征服小红帽,殊不知小红帽才是这场赌注的幕后操控者。“她想在路上慢慢走来确保这位帅气的小伙能赢得她的赌注”[3]2331。她故意输给狼人是为了满足青春期少女对爱情的幻想。但当小女孩终于到达祖母家,敏感的她立即发觉了屋中的异常气氛。“女孩环绕房间一周,看见枕头光滑的表面一点头部的卧痕都没有,并且她生平第一次发现圣经是关闭着放在桌子上的。”[3]2332-2333此时她意识到祖母已经遇害,而自己正身处险境。“因为害怕对她毫无帮助,所以她不再恐惧。”[3]2333冷静下来的小红帽假装顺从狼人的欲望,并且在屋外狼嚎的氛围中和他举行了世上最野蛮的婚礼仪式。小红帽通过牺牲对当时女性而言最重要的贞操征服了狼人。故事以狼人变回狼,温顺地睡在小红帽怀里结束。
卡特版的小红帽失去了先前童话版本中宣扬的女性特质——天真。男权意识影响下的社会要求女性成为天真纯洁的家庭天使,她们因为有男性(猎人)的保护无需拥有经验。新版本中,小红帽以经验(性)为武器征服狼人,而狼人却天真地相信了小红帽,失去了主导地位。在天真与经验的对立项中,卡特赋予了小红帽新的女性魅力和女性形象。
3 感性与理性的对立
《与狼为伴》中以祖母为代表的感性家庭主妇,都免不了被狼(狼人)吞噬的结局,而理性独立的小红帽却征服了狼人。卡特在《与狼为伴》中巧妙地颠覆了社会对男女两性的刻板认知。狼(狼人)作为男性的隐喻,嗜血为性,“一旦觉察到肉的气息,那么什么都无法阻止他”[3]2326。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甚至会因为无法补救的欲望而哀嚎。“狼或狼人在欲望的驱使下伤害弱小无辜的生命,他们比鬼怪、食婴巫师还要凶残。有时,这些野兽看上去好像他们内心有一半是欢迎那些驱赶自己的致命武器的。”[3]2327—2328狼在幻化为人后,因出众的外貌成功找到深爱自己的伴侣,却还是逃离不了欲望的枷锁,最终会伤害唯一接纳自己的女性。所以,狼人的婚礼总是伴随着群狼的哀嚎,“狼的嚎叫声中总有一种辽阔的伤感,而这无尽的伤感就像森林和漫漫冬夜一样没有尽头。”[3]2328卡特用狼人理性的丧失颠覆了男性是理性的思维模式。这种狭隘的思维模式不仅在男性心中根深蒂固,在女性心中也举足轻重。
诚如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指出的,“男性对女性的内在殖民比任何形式的隔离更加稳固,比阶级划分更加严格,更加统一,当然也更加持久”[6]199。卡特的改写不仅要打破男性比女性更加理性的社会成见,更重要的是改变女性对自身的认知。在女性主义运动兴起以前,男权意识影响下的女性普遍认为男人是理性的代名词,而她们自己容易情绪化,适合在家相夫教子。卡特在《与狼为伴》中着力刻画了两类女性形象来启发女性读者对感性与理性的新认知。一类是以小红帽祖母为代表的传统女性形象,她们崇敬上帝,相信直觉。另一类是以小红帽为代表的新女性形象,她们聪明睿智,相信自己的理性判断。这两类女性在面对狼或狼人的攻击时采取的态度分别是感性与理性二元项中的一项。感性的守旧派妇女认为只要恪守家庭妇女的职责,并且经常阅读圣经,那么遇到危险时就会得到救赎。“村子周遭岁数较大的主妇认为向狼人扔围裙就能保护自己。”[3]2329小红帽的祖母就是这样典型的家庭主妇形象。自丈夫死去,她一个人生活在远离村子的森林里,“她有圣经作伴,她是一位虔诚的老妇人”[3]2331。她特意为自己心爱的孙女缝制了一条鲜红色的围裙来抵御狼的袭击。这位祖母相信遇到狼(狼人)时应该立即将手边的圣经和围裙扔向他们,可是这两样象征宗教和家庭职责的武器并没有使她得到拯救。与祖母感性的抵御措施不同,小红帽面对狼人时清楚地意识到,“现在召唤上帝和他的母亲以及天上所有的天使来保护你都对你毫无帮助”[3]2332。理性的小红帽用智慧与狼人周旋。“这个聪明的孩子从没有退缩,甚至当狼人告诉她要吃了自己时,女孩却意想不到地笑了。因为她知道自己不是任何人的食物。”[3]2334她嘲笑着狼人的威胁,她脱掉自己与狼人的衣服并扔进壁炉的火焰里。此时的她智勇双全,用理性的思考与狼人较量。而凶恶的狼人却被小红帽的行为打动,在这场野蛮的狼人婚礼中失去了主动权。狼人因为欲望丧失了理性,在小红帽的温柔抚慰下变成了感性温顺的小狼,最后在小红帽的怀中甜甜地睡去。小红帽理性征服狼人的方式显然不会被传统女性观所接纳。所以当小红帽失去贞洁时,她能感觉到祖母的“老骨头在床下发出一阵恐怖的撞击声”,像是在咆哮小红帽制服狼人的方式。两类女性形象在与狼人的冲突中采取的不同态度,造成了她们截然不同的命运。卡特的改写不仅颠覆了男人与理性对应而女性与感性对应的思维定式,而且将一个理性智慧的新小红帽形象刻画得深植人心。
4 结语
在《与狼为伴》发表之前,男性作家塑造的小红帽是一个天真感性的家庭女性形象。她一旦脱离了象征传统女性道德规范的那条森林小径,就会随时有生命危险,而能够拯救自己的只有男性(猎人)。而《与狼为伴》围绕着以狼人为代表的天真感性的男性形象与以小红帽为代表的经验理性的女性形象之间的对立,成功颠覆了男性眼中的理想女性形象,重新构建了作者心目中的新女性形象——独立自主,理性成熟。卡特的改写不仅拓宽了童话故事的叙事范围,而且还为女性读者对于自身的认知带来启发。
[1]张中载.狼·童话·男人和女人:评安杰拉·卡特的《与狼做伴》[C].张中载.当代英国文学论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
[2]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Angela Carter.The Company of Wolves[M]∥Sandra M Gilbert,Susan Gubar.The Norton Anthology of Literature by Women:The Tradition in England[M].New York:W.W.Norton&Company Ltd.,1985.
[4]王虹.隐喻、道德与童话新编:评安吉拉·卡特与新编童话《与狼为伴》[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0(2):24-27.
[5]Raman Selden.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
[6]Wilfred L Guerin,et al.A Handbook of C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
责任编辑:柳克
Reconstruction of Little Red Riding Hood’s Female Image —The Company of Wolves from the Structuralism Perspective
JIANG Yan,SUN N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3,China)
The Company of Wolves is Angela Carter’s parody of Little Red Riding Hood.By implying structuralism criticism,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ree binary oppositions existing in the novel:male vs female,innocence vs experience and sense vs sensibility in order to expose the author’s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an independent,experienced and rational new female image by rewriting the end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Little Red and the Werewolf.
Angela Carter;The Company of Wolves;binary opposition;new female image
I561.074
A
1009-3907(2014)07-0924-04
2014-02-24
安徽省高等教育质量工程项目(20100234)
江妍(1990-),女,安徽黄山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孙妮(1958-),女,安徽芜湖人,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