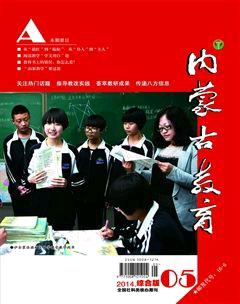专题资讯
编者按:
教材出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仅是语文教材,数学、物理、化学等教材屡屡被人挑出错误,一些出版社几乎成了犯错的“老油条”。对此,人大新闻学院副教授翁昌寿建议,建立完善的追惩制度。设立黑名单,如果教材出现知识性错误,就将出版社列入黑名单,几年内不能进入教材招投标目录。对教材出版者来说,出错后如果付出代价不大,就不具有任何威慑作用。
案例一:文字错误实例
据媒体报道,郑州一位彭老师在新版课本中发现一些错误。其中有“硬伤”,例如将“沐浴”写成“沭浴”;“常识性”错误,例如“【重阳日】九月九日重阳节”,他认为,此处应当清楚地标注农历的九月初九,因为阳历九月九日并不一定是重阳节,这样标注会误导读者;争议性问题,例如彭老师认为在词典中只能查到“温故知新”这个词语,而没有“温故而知新”这个词语。“但是人教版初中七年级上册新版课本第53页第10课《〈论语〉十二章》的课后练习第三题将温故而知新归类为词语。”所以,他认为“温故而知新”是否归类为词语有待商榷。
经过总结,彭老师在课本上共找到常识性错误2处、知识性错误1处、与课标规定不符的5处、争议性话题2处、语法错误3处、系统不严密4处、未按照课标要求编写3处和其他低级错误11处,共31处错误。
但人教社在其官网上发布的《关于人教版语文教材的致歉信》,只承认了6处错误。
案例二:配图错误摘录
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多处配图出现史实性错误。六年级下册《语文》中的《七步诗》背景图中,魏文帝曹丕是垂足坐在有靠背的椅子上。而椅源于魏晋和隋朝,直至唐明皇时期开始才形成有靠背的椅子。
四年级下册《语文》中的《手不释卷》插图中,三国时期吴国大将吕蒙据桌读书,其坐势是垂足坐,而且画中出现的桌子是唐代以后才有的。
吕蒙手中拿着一本册页书,将两汉三国时期的书籍画作简策为最佳,其次为卷轴,而册页书则是错误的。
三年级下册《语文》中的《西门豹》插图中,一位年轻女性手捧托盘,盘中放着一串葡萄。西门豹治邺的故事发生在战国初年,而葡萄是300年后西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后才传入内地。
三年级上册《语文》中的《盘古开天地》插图中,左上方画着一个火红的太阳,太阳之中绘有一只两条腿的彩色小鸟。而在中国的神话传说和民俗中,三条腿的乌鸦才是太阳的象征。
案例三: 印度一中学教科书错误百出
英国《每日邮报》2014年2月25日报道称,印度古吉拉特邦的一部供5万学生使用的中学教科书因错误百出遭到各界批评。
这部“雷人教材”是一部供八年级学生使用的社会科学教材,内容涉及历史、地理以及自然科学知识。据粗略统计,这本124页的教材中共有150多处事实、语法以及拼写错误。其中,事实性错误59处,拼写错误100多处。如书中将甘地遇刺的日期“延后”了9个月,称甘地死于1948年10月30日,而事实上这位印度“圣雄”的死亡日期是1948年1月30日。另一处让人大跌眼镜的错误是“二战期间,日本向美国本土投放了一枚原子弹”,实际上是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原子弹。此外,该书还将二氧化碳(CO2)和硝酸根(CO3)弄混。
案例四:日本教科书的错误
日本初中生的新版教科书竟出现了208处错误。错误是日本文部省审查时被发现的。而且,日语、英语、数学等课本里都出现了不同的错误。在日本语文课本中,目标的“目”,日语应该念me,教材上却写着ma。平假名hiragana也变成hiranaga。数学课本也是错误百出,一个算式中赫然写着20X-20X+16=0。不过最离谱的算是英语课本,something这个简单的单词竟然被丢了一个“h”。
其他案例:教材出错并非个案。北京十五中一位高一历史老师发现,人教社2008年再版的《历史选修2: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里有误,即“1660年,他们同意流亡海外的詹姆士一世之子带领保王分子返回伦敦,登上王位,称为查理二世”中有严重错误,“查理二世”为“查理一世”之子,并非“詹姆士一世”之子。还发现,课本第45页写着英国第一任内阁首相名字为“沃波尔”,而紧随其后的下一页同一个人的名字变成了“华尔波尔”。
北京二中的一位高三历史老师也指出,岳麓书社《历史必修II:经济成长历程》(2007年5月第2版)第3页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一件“骨耜”,被错标为“石耒”;《历史必修III:文化发展历程》(2008年5月第2版)第16页《三教图》的作者“丁云鹏”实为明代人,却错标为“清”。
2013年年初,张作霖之孙指称2007年前人教社高中历史教材中,张作霖的照片并非其本人,而是湖南督军何海清。此外,教科书的插图中,屈原、祖冲之的衣襟被穿反;荀子坐凳子读那个时代不可能有的纸质书;秦始皇、汉光武帝、诸葛亮、唐玄宗、颜真卿等多位古人的画像相似度极高,只是有胡子和没胡子的区别;2010年,在人教社高中语文教材中,有一名高一学生在鲁迅的《祝福》中找出10个明显的错别字。
从现代知识传播的角度观察,教科书是人类获取完整、系统、准确知识的基本载体,也就是说,在人类知识的传播中,教科书的地位为一般其他传授知识的方法难以取代。在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方面,争议相对较少,而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传播方面,对教科书的争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人们熟悉的一个例子是日本修改教科书事件,常常受到中国政府的抗议,因为他们歪曲了历史事实。
教科书的编纂,一般来说有强制特征,在涉及有关国家历史和文化制度方面,国家会对教科书的编纂有强制性要求,这是教科书编纂的通则,因为它可以保证知识传播的国家意志。教科书的一个伟大作用是它与一个国家的基本教育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在一个人的成长阶段,他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必定是教科书,它保证了一些基本知识和价值的稳定性与系统性。人类判断知识的自由程度,只有到了成年以后才成为基本事实,而在成长阶段这种自由程度很难真正实现,这决定了我们知识的主要来源是教科书。
教科书的编纂有人类共同遵循的基本规则,但也有相当多的特殊国情。国家越是依靠意识形态管理,相对来说,对教科书的编纂,越有制约,越少自由。因为意识形态提供全部社会生活的价值和目标,中国教科书的编纂意识形态色彩最浓。
历史通常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教科书更是如此。在一般的历史研究中有这样的规律:“自来成功者之记载,必流于文饰,而失败者之记载,又每至于淹没无传。凡一种势力之失败,其文献必为胜利者摧毁压抑。”这是瞿兑之上世纪40年代为《一士类稿》所写序言中的看法,他的判断,我以为是一般读历史的人都认可的。
陈寅恪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中也说过:“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陈寅恪、瞿兑之都是对历史有卓见的学者,他们的判断应当是历史研究中的深刻经验。
用陈寅恪的说法,官修之书中,一定包括教科书,而它的特点就是易于“讳饰”。要求教科书完全符合历史真相的冲动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事实上我们很难做到,现在我们的教科书问题,常常还不是因为历史观念出现差异,而是在事实上远离了历史真相,这样不但传播了虚假的历史知识,也影响了人们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思维。
教科书不能造假,这是教科书编纂的底线,可我们总是突破这个底线。没有绝对的历史真相,历史一旦发生,就存在解释和判断的问题,我们不可能返回历史现场,而解释历史的知识方法有无数。
一般说来,判断历史真相的标准还是存在,它包括自由、完整使用史料的权利,自由理解历史的意识,具有自由、公开、平等讨论历史问题的平台,以及建立在合理知识体系基础上对历史的自由判断。
(摘自作者博客)
对出版物作差错率的要求,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按道理说,不能有错。尤其是小学教材,错误的影响是深远的,儿时学错一个字的读法,有时会终生改不过来。如果教材上的错误都容忍,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中小学教材出错,问题出在哪儿?
急功近利、浮躁之风的侵袭是重要原因。问题出在目前教材出版也很“着急”,编书和出书的速度都太快。出版社每年对出版图书有品种数量的要求,上世纪80年代编辑的发稿定额是一年几十万字,现在要求一年发几百万字,有的人甚至可以发到上千万字,并因此受到奖励。我曾听到不止一个出版社的领导说,利润和码洋每年都要实现两位数增长。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教材出版周期短,专家审校环节相应较短或者缺失,质量难以保证。
应建立完善的教材编辑出版流程。教材主管部门一定要组织高水平的专家队伍承担教材审读工作,从源头上保证不出知识性错误。在编校质量上提出比一般图书更严格的标准。
(摘自《光明日报》)
教材出错,表面上看是因为编者和出版者责任心缺失导致,但长期以来无法避免的现实,则映射出教材的出版发行存在制度缺陷的本质。
一直以来,我国的教材出版市场都被行政高度垄断着,现实中,只有极少数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出版社才有资格进入教材市场,而且贯穿了编撰、审订、出版、发行的全过程,从中赚取高额的利润。垄断导致了暴利,也滋生腐败,加上有行政背景的出版社尤其缺乏必要的监督管理,最终出现低质量产品。其实,国务院曾牵头对教材出版进行调查,也曾着手对教材出版及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但由于长期以来垄断者的强势局面难以在短期内打破,既得利益者的消极应对以及暗箱操作的腐败现象屡禁不止,教材出版体制仍未能“伤筋动骨”,最终还是逃不过“指定”和“垄断”者独大的局面。
可以说,每一本教科书都是孩子们成长道路中必须经过的阶梯,“教科”二字意味着权威、标准和正规,理论上应经过数位专家学者的反复论证、校对,即便对其差错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也不为过。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当前教材屡出差错的乱象,为孩子们提供优质的教材,必须对教材出版体制进行真正、彻底的改革,用竞争机制把市场做好做活。
(摘自东方圣城网)
教材出错问责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应开放教材编写机制。教材出错的消息屡次出现,正反映了我国中小学教材编写的机制存在问题,说明教材编写缺乏开放的竞争机制,在行政主导的制度下,专家只对行政部门负责,学生家长没有真正参与进去致使教材屡屡出错。
我国中小学教材的编写,目前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教材经审定、出版后,当地学校统一使用,这种教材编写、采用机制,导致教材的编写质量总是遭遇质疑、存在争议,学校和老师被动使用教材,同时,也被指存在教材利益链。
与之对比,国外中小学教材,却是由社会专业机构编写,社区教育委员会、学校、家长委员会共同参与选择。不存在“统编教材”之说。这种教材编写、选用机制,既通过市场竞争促使教材编写质量的提高,同时也避免教材发行出现潜规则,更重要的是,通过学校自主选择教材(或自编教材),保证了学校办学的自主性和个性。
所以,行政色彩过于浓厚,是目前中小学教材编写、出版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减少行政干预,建立公正、透明、民主、科学的教材选用机制,充分尊重学校、老师和学生的选用权利,真正实现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保护教材编写者和团队的利益和积极性,才能充分保证优秀教材脱颖而出,也才能不断完善提高教材质量。同时,应该进一步反思我国教材的编写机制,应把公众参与、选择作为提高教材编写质量,让教材更符合教育教学需要的重要途径。毕竟,靠少数教育部门官员和专家的智慧,解决不了那么多的教育问题。应该建立教材编写开放机制,打破行政部门的垄断,由专业机构组织编写,公开出版,出版后再由教师或者家长共同参与选择。假如是这样的开放式编写过程,编写机构自然会听大家的意见,也会重视编写的质量。
(摘自作者博客)
2013年,与语文有关的新闻可谓层出不穷,引发诸多专家和网友的热议。但是几乎每一个对语文教育提出建议和意见的人,都忽略了最基本的问题。语文是什么?语文教什么?语文怎样教?而《语文课改调查报告》的出炉,则明确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如今的语文,早已经被我们边缘化。
为何“热议”的总是语文
语文其实是社会性很强的学科,和每个人的生活关系密切,谁都能批评,插得上嘴,数学、物理、化学、英语等其他科目,专业性强,大家想说,也未必能说出什么来。语文天生就会受到社会格外的关注。这些年每隔两三个月,就可以看到一些与语文教育有关的热议甚至炒作,实在有些“过于关切”。
有人爆料某版本初中语文教材发现30多个错误,爆料者声称要把出版社告上法庭,各大媒体网站都在热议,甚至中央台都跟着报道了,成了新闻事件。我很好奇,找来材料仔细看,发现所谓30多个错误,绝大多数是夸大,或者是爆料者自己弄错了的,真正错的只有五六处,而且只是编校的过失,比如标点不完整、个别错字等,没有校对出来。出版社当然应吸取教训,加以改正。爆料者本可以通过学术讨论的途径,给出版社指正,但弄到媒体上,广为炒作,给人印象就是教材一发不可收拾了。这不符合实际,对教材编写的改进其实会有负面影响。对语文的“过度关注”,并不是好事。
语文有社会性,它还是一门学科,有学理性。语文的社会关注度应当降降温,媒体不要去炒作,大家少争论,让一线教师和专家安静下来,认真做些调查研究,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提有建设性可行性的意见,而不只是在印象的、情绪的层面没完没了地争论下去。
语文教材编写出现了变味的竞争
其实新中国建国后三四十年,中小学教材是全国统一编纂的。原来全国的语文教材都由国家组织专家统一编纂。最近十多年变成了“一标多本”,由教育部颁布课标,然后各地各个出版社组织编写,经过审查即可发行。目前全国小学有11套语文教材,初中8套,高中5套。
本来“一标多本”这个政策是个进步,是为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让教材也有竞争,广大师生可以选择使用。可是十多年下来,这种竞争变味了,不再是质量上的竞争,只是营销上的竞争。由于经济利益推动,出版社用各种手段极力扩大发行量,加上地方上的保护,行政干预,使得语文教材编写发行出现了很多问题。所以从2012年开始,国家尝试着收回语文、历史以及思想品德等教材的编纂权,虽然遭到许多抵制,但是目前国家统一的示范性教材编写工作正在进行。
民国语文作为标杆大可不必
说起语文教材,前几年一直流行民国热,尤其是民国语文课本。其实民国语文作为标杆大可不必。民国时期有它的特殊性,那时候现代的教育体制刚建立,有较多的办学自由,办学上容易形成各自的个性,也培养出不少“国学”大师。那时的语文教材大都是个人编写,如《国文八百课》等,自主性很强,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很有特色,值得借鉴。
另外,民国时期语文教育刚脱胎于传统,学生的所谓“国学”底子自然比较厚实。而且民国时期能上学的人极少,国民大多数都是文盲,那时主要是精英教育,当然要比现在的语文教育水准高。
目前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所有人都能上学,是公民普及教育。如果从“普及”的角度看,现在的教育包括语文教育的成就又远远大于民国时期。更为重要的是,现在学生要学的东西比民国时期增加了很多,英文、计算机等占用相当多的时间,他们不可能像民国时期学生那样专注地学语文。
因此,借鉴民国时期的语文教育经验是应当的,但拿民国语文作为标杆大可不必,语文教育的改革还得适应现有的社会需要,面向未来。
(摘自《山东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