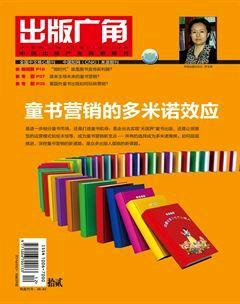巨头开战 出版业围观
李爽
传统出版业的概念里,出版和销售起实是各自分工合作的,而新经济的浪潮下,这样的分工合作势必被打破,像所有其他的行业一样,重新洗牌在制造业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但出版业一直以文化产品而做最后的盾牌以求保护。文化产品该如何面对新经济浪潮呢?
2014年5月,也许会作为出版业的一个历史时刻被记录:控制美国图书市场销售额多达1/3的世界最大电子商务公司美国亚马逊开始对法国桦榭出版集团进行市场控制:从5月初不鼓励读者购买桦榭出版的图书,因为“亚马逊无法或者推迟邮寄”,到5月27日正式宣布因为“价格问题”不再进桦榭出版的图书,这意味着现有图书销售完毕以后,亚马逊不再销售桦榭的图书;而且“看来很难找到解决的办法”,起码近期无望解决。
这场战争当然不是起自于2014年,最早可以追溯到2010年,当时以桦榭出版为首的5大出版集团集体要求亚马逊开放售价上的出版社自主权;而亚马逊的决定也不仅仅涉及桦榭出版一家,按照参加5月美国出口书展一位出版商的说法,所有的出版社其实都是“桦榭”。
Forrester预测2014年美国的电子图书销售额将达到87亿美元,而纸本图书继续下降只有195亿美元(2010年的数字是260亿美元)。在电子图书大行其道的今天,分析此次争执,也许可以为出版业的未来预测提供一些有效的参考。
争执起于青萍之末
亚马逊曾经在2010年2月宣布麦克米伦出版社可以自行对电子书定价,将亚马逊一直执行的精装本价格从9. 99美元涨到14. 99美元,并与桦榭出版、兰登书屋、哈泼柯林斯、企鹅出版社等五大集团重新签订合约。当时被认为是传统出版业对新型电子出版销售上的一大胜利。而涨价消息直接导致亚马逊在美国当日股价的下跌,被评论为 “以量制量”或者说“批发模式”的一种失败。此后,2012年,与亚马逊同样在图书销售上占举足轻重位置的苹果公司在加拿大遭到联合诉讼,因为与五大出版公司联手“操纵电子书价格”。而2013年7月10日,苹果被美国司法部判定与五大出版商联合操纵电子书的最终定价,也有业界声音称是美国政府对亚马逊的变相保护。
可见,在过去的四年里,随着图书数字化势不可挡,但因为更多的读者是通过购买亚马逊或者苹果的阅读器来阅读和购买电子书,所以传统出版巨头到底如何才能拿到数字化后最大的销售利润,一直是他们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出版业因此在亚马逊和苹果之间游移、谈判,包括做自己的网络销售等。电子书的定价之争直接反映的是出版商和销售者之间的利益之争,而这次亚马逊和桦榭把这个争执再次明晃晃地摆到光天化日之下。
但是,到底谁能代表读者的利益呢?或者说,在这个商业模型里,谁更能代表最重要的消费者的位置呢?
并非一个人的战斗
媒体在报道桦榭和亚马逊之争时,把眼光聚焦在了一个人的身上——Michael Pietsch——现任桦榭出版集团的执行总裁。他拥有多达数十年的出版经验,而因为保密的协定,外界无法得知到底桦榭和亚马逊的争执具体在哪些方面,仅可以猜测是,在亚马逊希望得到的桦榭图书折扣上,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传统出版业都视Michael Pistsch为英雄,具有代表性的说法来自原亚马逊的执行官、现任职某出版社的Laurence J. Kirshbaum:“他像独力反击入侵者而试图拯救罗马的传奇英雄,他背负的是整个出版业的希望。”
在媒体前曝光的Michael Pietsch被形容成“即是球员又是教练”,因为他从1979年就开始其出版编辑的职业生涯,从小布朗出版社的畅销书编辑走到桦榭出版集团执行总裁的位置,也因此,传统出版业视其为最合适与亚马逊对抗(谈判)的人选:即是编辑,又是商人。
按照评论,传统书业都在暗地里欢呼,默默地为Michael Pietsch鼓掌,而不能直接站出来参与对抗,因为他们并不想被置于与亚马逊敌对的尴尬境地,特别是在亚马逊明确表示会处罚“不合作者”的时候。
Michael Pietsch被推到了这样一个浪潮前,而他的表态似乎可以代表更多传统出版者的心声:“亚马逊想控制出版业的销售、购买甚至出版,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传统出版业的概念里,出版和销售其实是各自分工合作的,而新经济浪潮下,这样的分工合作势必被打破,像所有其他的行业一样,重新洗牌在制造业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但出版业一直以文化产品做最后的盾牌以求保护。文化产品该如何面对新经济浪潮呢?
到底是大灰狼还是恶霸?
为亚马逊辩护的文章当然层出不穷,而着眼点都放在亚马逊代表的是新经济概念,以及消费者即读者的真正利益。
在成立之初,贯穿亚马逊的理念就是“用户至上的哲学”,甚至拿出股东的利润去满足消费者,给予其最低的价格和最快的服务,因此亚马逊解释,对桦榭的谈判是为读者进行利益最大化之争,而如果桦榭不能满足读者的利益,那想继续购买桦榭图书的读者只能另辟蹊径,去其他网站甚至对手网站购书,而亚马逊不再成为桦榭的推广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在与法国桦榭出版开战,亚马逊与德国第三大传媒集团Bannier出版的谈判从2013年底起至今都没有达成。而在德国,因为二战的历史原因,出版定价是有法律保障的,特别是保障那些小的独立出版社,因为图书是多元社会、自由思考的一个大众且流行的途径,保障图书出版的多元化是保障社会多元文化的有效途径之一。
所以对亚马逊的质问之一,是不是亚马逊过于扩张而遭遇现金流的压力,比如购买HBO的版权但免费提供给消费者之类的市场策略。
根据亚马逊自己宣布的数字,全世界有多达上千家出版社与其合作,而即使桦榭出版的图书不再通过亚马逊销售,读者也不过只失去了2‰的选择,还可以选择其他998本图书。从这种表态而言,如果图书作为一种商品没有其不可替代性,那读者是不会在乎失去某种或者某本图书的。
对图书这种特殊的文化产品而言,除价格的比重到底在购买行动中应占有多大比例外,是否便捷也是重要的问题:便宜和方便是决定读者购买的主要因素吗?如果亚马逊拥有的忠实读者认为“价格和便利”是最主要的促使他们购书的因素,那么桦榭出版的忠实读者与亚马逊的忠实读者之间有多大的重合度,也许将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走向。
谁能对付亚马逊?
从今年5月与桦榭出版开始谈判起,亚马逊先后通过论坛、网站申明等采取一系列方式“不鼓励”消费者购买桦榭出版的图书,而且声明是站在读者的立场上。这一点让桦榭出版集团有些狼狈。虽然桦榭出版的新闻发言人严正指出“亚马逊故意延迟对桦榭图书的发货”“而且在网页上频繁出现‘无货等字样”,严重影响了桦榭图书的销量。对此,亚马逊公司不置可否。
信息不对称和不公开也许让读者和业界永远无法判断这场战役谁做了小动作,或者说谁是真正考虑了读者利益而不仅仅着眼于市场利润,但对于整个出版业来说,分析来龙去脉甚至吸取有益的经验才是看客得益之处。
彭博网站的作家兼评论员Ben Th-ompson写道:在出版社把图书交给亚马逊的那天起,实际上就放弃了对读者的了解和读者数据库,现在才会僵在谈判桌前。出版商其实从来就没有真正明白新经济的概念,所以与亚马逊的交易一直是一种“浮士德”的交易,现在应该借机重新考虑了。他提出的思路是,亚马逊主要靠Kindle来销售图书,而这一阅读终端是使读者方便地成为亚马逊的忠实用户。如果读者不仅只有一个阅读器,第二或者第三个阅读器能直接接到其他销售渠道,包括出版社甚至作者的直接渠道,从而购买他们需要的书籍,那么亚马逊如何操控市场呢?而在此基础上,他的建议是作者去寻求有能力的出版社代理,图书定价由固定的前期费用和销售数量的百分比构成,由作者控制市场。这个模式无疑是作者市场化的模式,但在目前也很难有普遍意义。
《纽约时报》则提出2010年亚马逊与麦克米伦的例子,暗示最后和解的可能性,并认为传统出版业会占上风。但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亚马逊已经有强大的Kindle销售数量为后备,而且对消费者数据库的建立也今非昔比,所以乐观地站在传统出版业一边,估计已经没有那么简单了。
不管桦榭与亚马逊之争如何结束,出版业借这个机会需要审视的是,到底对新经济了解多少,顺应多少,或者借势多少。至于他们把利润和读者如何摆位而求生存,市场自然会给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