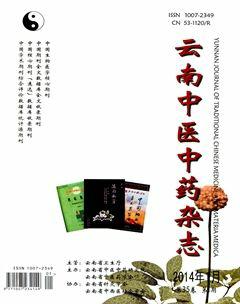林佩琴治疗喘证的学术思想初探
王智星
摘要: 通过对林佩琴《类证治裁》中喘证之辨证立法、处方用药加以分析,发现林氏治疗喘证的学术思想独具特色,将健脾化湿与纳气归元有机结合,健脾化湿药与收涩补肾药同用,共奏陪土生金、收摄真元之功,同时强调时间医学在喘证辨证施治和服药中的运用。
关键词: 林佩琴;类证治裁;喘证
中图分类号: R256.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2349(2014)01-0009-03
林佩琴,丹阳后松卜村人,生活在清·乾隆至道光(公元1771-1839年)间。《类证治裁》为其据就医病愈者所交还的处方,择要写成医案,并加论证,总结数十年学医心得和临床经验的著作,其中对于喘证治疗的学术思想,倾向于李东垣的脾胃学说,注重将健脾化湿与纳气归元有机结合,同时强调时间医学在喘证辨证施治和服药中的运用。
1 健脾化湿法在喘证中的运用
林氏认为:“痰生于脾,湿胜则精微不运,从而凝结,或壅肺窍,或流经隧;饮聚于胃,寒留则水液不行,从而泛滥,或停心下,或渍肠间。”李东垣认为,脾胃是心、肝、肺、肾四脏的“升降浮沉”及其“四时”等运动的枢纽,故胃气一虚,五脏受邪,就会产生“元气下陷,阴火上乘”的病理状态。对于“元气下陷,阴火上乘”,治疗上东垣认为应当“升阳益气”,火与元气不两立,元气不足与阴火上僭的矛盾,根源在于脾胃受损,枢纽亏虚,故以甘温健脾化湿和升阳益气治之,但是,林氏更侧重与将健脾化湿和纳气归元结合在一起治疗。
如林氏治疗喘证之寒痰阻肺案,“族某 七旬以来,冒寒奔驰,咳呕喘急,脉弦滑,时嗳冷气。”(《类证治裁》·卷二·喘症论治)本案中“咳呕喘急”,即林氏认为的痰饮“在肺则咳,在胃则呕”。方用“淡干姜、五味、桑皮(炙)、茯苓、潞党参、甜杏仁、橘红、制半夏、款冬花、紫衣胡桃”,取半夏辛苦温燥之性,善能燥湿化痰,且又降逆和胃而止呕;橘红理气燥湿祛痰,燥湿以助半夏化痰之力,庞安时云:“人身无倒上之痰,天下无逆流之水,故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顺矣”,故治痰大法以顺气为先,理气可使气顺则痰消;痰由湿生,湿自脾来,“若出纳升降失常,斯喘作焉。”提示四脏“升降浮沉”的枢纽脾脏失常,故佐以茯苓、潞党参健脾渗湿,脾湿去脾旺,痰无由生;淡干姜归脾、胃、心、肺经,以其燥湿消痰,温肺化饮,助半夏、橘红行气消痰,和胃止呕;复用少许五味子收敛肺气,与淡干姜、半夏相伍,散中有收,使祛痰而不伤正,并有欲劫之而先聚之之意。桑皮性甘寒性降,主入肺经,能清泻肺火兼泻肺中水气而平喘,制半夏之温燥,甜杏仁、款冬花助其宣降肺气,润燥止咳,与半夏相伍,升中有降;《脾胃论》曰“肾水反来侮土,所胜者妄行也。作涎及清涕,唾多,溺多,而恶寒者是也”,所以症见“时嗳冷气”,且“老人元海根微”,紫衣胡桃味甘热而润,入肺、肝、肾三经。温肺补肾,而通命门,使下焦得温而寒去,则膀胱之气复常,约束有权,并助五味纳气平喘,收摄真元。[HJ3.4mm]
2 纳气归元法在喘证中的运用
《类证治裁》曰:“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肺主出气,肾主纳气,阴阳相交,呼吸乃和。若出纳升降失常,斯喘作焉。”肺主肃降,肺气肃降顺利,能顺利地吸入清气,呼出浊气,完成吐故纳新;通过肺气的下降,肺所敷布的津液、水谷精微也运行有序,最终精微归肾之所藏元气,余浊归膀胱、大肠,完成清浊之运;肺失肃降,水谷精微到达不了肾脏,则肾不纳气。
如林氏治疗喘证之肾虚不纳案,“某肾不纳气则喘息上奔,脾不输精则痰气凝滞。”(《类证治裁》·卷二·喘症论治)脾胃升降失和,元气不充不畅,谷气下流,郁滞化火,使下焦阴火上僭而致发热,即“虚中夹温”。肾水在下,需要相火的蒸腾、推动和脾气之升清,才能上济于心,使心中君火不至于燥烈于上,现在下焦阴火上僭,脾胃受损,则清阳下陷,阳气不升,无力推动肾水上济于心,故心火独盛。相火郁于下焦,加之下陷之清阳,下焦火势太过而成阴火,消耗元气,肾水和心火失去平衡,不能相济,就会产生“忽神烦不寐,语谵舌灰”的症候。“急用纳气归原,冀根蒂渐固”后,此处“元气下陷,阴火上乘”,根源在于脾胃受损,枢纽亏虚,林氏将纳气归元和健脾化湿结合在一起治疗。清·何梦瑶《医碥·杂症·气》云:“气根于肾,亦归于肾,故曰肾纳气,其息深深;肺司呼吸,气之出人,于是乎主之。”可见肺失肃降会影响到呼吸运动的节律,导致“喘息上奔”,“呼吸颇促”和“喘息乃粗,脉见虚促”等喘证症候。急用纳气归原,方用高丽参大补元气,茯神宁心安神,远志安神定志,且通肾水上达于心,如此心肾相交。莲子补脾止泻,益肾涩精,养心安神,五味子酸收,配伍莲子固肾生津,不使津液下流,收纳下焦散越之气;牡蛎微寒而质重,能益阴潜阳,镇惊安神,助莲子、五味子纳气平喘,收摄真元;牛膝炭苦泄下降,能引血下行,导热下泄,并制莲子、五味子酸收之性。
3 时间医学在喘证中的运用
《灵枢》有“一日分为四时,朝则为春,日中为夏,日入为秋,夜半为冬。”在此基础上,林氏认为:“气血所周,子时注胆,丑时注肝,寅时注膀胱、卯时注大肠、辰时注胃、巳时注脾、午时注心、未时注小肠、申时注膀胱、酉时注肾、戌时注心包、亥时注三焦,其更迭有如此者。”
如林氏治疗喘证之痰热郁肺案,“赵 衰年喘嗽痰红,舌焦咽燥,背寒,耳鸣颊赤,脉左弦疾,右浮洪而尺搏指。”(《类证治裁》·卷二·喘症论治)“午时注心”即中午11至13时到达心脏,对应“日中为夏”和“去杏仁、牡蛎、阿胶,加生地、竹茹、丹皮、元参、羚羊角午服”。“酉时注肾”即晚上17至19时到达肾脏,对应“夜半为冬”和“用熟地、五味、茯神、秋石、龟板、牛膝、青铅晚服,以镇纳下焦散越之气,脉症渐平。”午服“去杏仁、牡蛎、阿胶,加生地、竹茹、丹皮、元参、羚羊角”,《脾胃论》曰“心火旺则肺金受邪,金虚则以酸补之,次以甘温及甘寒之剂,于脾胃中泻心火之亢盛,是治其本也。所胜妄行者,言心火旺能令母实,母者,肝木也,肝木旺则挟火势,无所畏惧而妄行也,故脾胃先受之。”可见清上中浮游之火,即清心肝之火,与“午服”对应“午时注心”。《脾胃论》中“心火亢盛,乘于脾胃之位,亦至而不至,是为不及也”。方中羚羊角咸寒,入肝、心经,最擅长清肝热、熄肝风、止痉定搐;丹皮辛苦而凉,归心、肝、肾经,泻阴中之伏火,清热凉血,消瘀散结,竹茹助丹皮清热化痰;元参即玄参,苦咸而凉,滋阴润燥,壮水制火,启肾水以滋肠燥,张元素曰“治空中氤氲之气,无根之火,以玄参为圣药”;生地甘苦而寒,清热养阴,壮水生津,以增玄参滋阴润燥之力;又肺与大肠相表里,故用甘寒之麦冬,滋养肺胃阴津以润肠燥。晚服“熟地、五味、茯神、秋石、龟板、牛膝、青铅”,镇纳下焦散越之气,对应“酉时注肾”。
4 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见林氏治疗治疗喘证的学术思想是以李东垣的脾胃学说为借鉴的,尤其是其中的阴火学说,但不同于东垣的健脾化湿和升阳益气以治之,而是辨证论治,将健脾化湿与纳气归元有机结合,肺脾、肺肾同用,运用到喘证的辨证立法、处方用药中,将健脾化湿药与收涩补肾药同用,共奏陪土生金、收摄真元之功,同时在内经的指导下,发展了时间医学,并将其运用到喘证辨证施治和服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