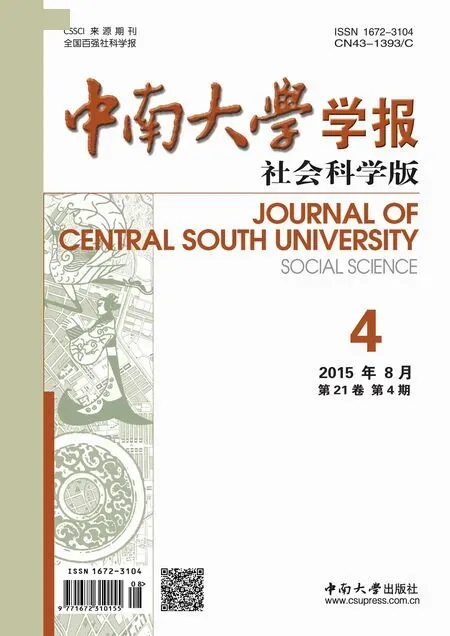中国经济发展与国家自主性关系考察
——基于改革开放前后的比较视角
陈霞,王彩波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中国经济发展与国家自主性关系考察
——基于改革开放前后的比较视角
陈霞,王彩波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国家自主性理论为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分析视角。以改革开放为历史分界点,国家由绝对自主向有限自主的转变推动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家社会关系从同构到分离催生了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中央地方关系从封闭到开放塑造了以创新和发展为特征的地方自主性。但经济发展的背后,国家自主性面临失衡困境,需要思考如何重塑国家自主性的均衡性。一方面,塑造有限政府,构建协同共治体系。另一方面,塑造有效政府,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国家自主性;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国家;社会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中国发展奇迹”,我们经常使用“改革开放”这一概念作为一个历史分界点来描述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一分界点不仅仅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点和中国经济起飞的起点①,它的背后隐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变化和中国社会变革的方向转变。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基于自主性的国家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和分权让利的结果,中国依靠自主性的国家形态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那么,是何种变化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背后中国面临何种困境?本文以国家自主性理论为分析视角,对改革开放前后的国家自主性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比较考察。
一、国家自主性:理论来源与分析概念
(一)理论来源:回归国家学派与国家自主性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回归国家学派②及其国家自主性理论成为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新范式。回归国家学派的核心代表人物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最先提出了国家潜在自主性的概念,她指出:“作为一种对特定领土和人民主张其控制权的组织,国家可能会确立并追求一些并非仅仅是反映社会集团、阶级或社团之需求或利益的目标,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1](10)之后,诸多学者以国家自主性为分析概念考察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发展等问题,并逐渐形成了以“国家自主性”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
回归国家学派把国家研究看作是一种研究路径和范式,构建了一种新的国家理论。这种构建突破了近代以来国家中心主义偏重规范性探讨的基本特征,实现了从概念推理到历史现象研究的转变。它突出强调“不能把国家简单看作利益竞争的公共舞台、竞争力量的裁判或支配阶级的工具,国家具有追求自己的偏好和利益的性质,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依照自己的偏好,按照自己的行为方式来贯彻自己的意志”[2](IX)。国家自主性理论在强调国家自主性偏好和特征的同时,同样强调社会政治结构的差异性对国家自主性的影响。因此,只有把抽象的整体性国家分解成为特定历史、政治社会背景下可以观测、考察的具体要素(国家机构、官僚体系、政策制度),才能展开对国家具体行为实践的分析。
国家与经济的关系是国家自主性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回归国家学派发展的“镶嵌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理论主张经济的发展不能只是依赖于国家或市场其中的一方,国家只有在官僚体制的基础上实现与社会的镶嵌才能真正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维斯(Linda Weiss)和霍布森(John M. Hobson)运用这一理论具体分析了东亚的崛起,他们认为东亚的经济发展案例实际上超越了国家主义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东亚的成功发展在于在有效干预的基础上,实现了国家与市场的结合。国家自主性理论为解释东亚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分析视角和解释概念。借鉴国家自主性理论及其核心概念来分析、理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自主性,特别是比较分析改革开放前后国家自主性的变化,有望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困境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二)分析概念:国家自主性的核心要素
运用一种理论分析现实,我们首先需要界定基本的分析概念和确立基本的分析框架。对国家自主性的概念界定我们可以从解构的角度入手,分解为以下两个基本问题。即国家自主性概念主要包含哪些构成要素?国家如何实现其自主性偏好?这两个基本问题包含了国家自主性的基本内涵及概念外延。国家自主性的基本构成要素由自主性主体(国家)、自主性动力(偏好、利益)和自主性行为(政策、制度)三部分构成。国家自主性的概念外延是国家能力,因为“将一个国家产生的大量自我偏好视为自主性是没有多大意义的,除非它能够实践这些偏好”[3](13),所以,考察国家自主性必须把国家能力纳入进来才有意义。
以国家自主性理论为视角的分析框架的确立,我们从整体性(横向)和解构性(纵向)两个角度出发。一方面,整体性分析视角以国家社会关系为基础,涉及国家偏好的变化以及如何通过自身拥有的资源将其意志、偏好贯穿到整个社会之中,并且这种意志观念可以作为社会的引擎和规范。另一方面,解构性分析视角以中央地方关系为基础,涉及体制内中央—地方关系的变化和互动,特别是重点关注其中变化的部分和环节,能更好地在比较的视角下考察中国经济发展与国家自主性的关系。因此,以国家偏好、国家行为和国家能力为基本分析概念,以国家社会关系、中央地方关系为分析角度,比较改革开放前后国家自主性的变化是文章的基本分析框架。
二、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自主性比较
市场化、放权让利、改革开放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核心关键词,但理解这三个关键词的前提是需要重点考察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因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在国家主导和推动下进行的,这是大家能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如果说中国经济的发展缘于国家自主性的推动,那么,为何改革开放前的国家自主性没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自主性的限度问题,对比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国家自主性形态,我们可以用“有限自主”③(bounded-autonomy)这一概念来解释。在国家社会关系层面,有限自主主要体现为国家社会关系从同构到分离塑造了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在中央地方关系层面,有限自主主要体现为分权驱动发展,分权化改革提升了地方自主性。
(一)从绝对自主到有限自主:改革开放前后国家自主性的转变
改革开放前,国家的自主性主要体现为一种绝对性特征的全能主义政治。国家以权力高度集中为特征实现对社会的渗透和对地方的控制,这禁锢了个人、企业、地方政府的活力。国家不仅垄断着绝大部分的资源,而且掌握着决策制定权,决策的集中、信息资源的封闭都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建立在意识形态激励基础之上,虽然国家有能力将全国的人力物力调动起来发展经济,但基于全能主义国家理念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后,有限国家自主性形成了有效的经济发展体制。以市场化为基础的分权化改革一方面重塑了国家社会关系、中央地方关系。从政治权力结构中释放了流动资源,同时也释放了创造力,分权使地方政府和社会成为制度创新的源泉,而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成为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加之中央对物质利益追求的认可以及由此形成的激励结构,均刺激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形成了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伴随分权化改革而来的是国家自主性形态的转变,即有限国家自主性。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经济绩效合法性形成的依赖,以及在分权基础上形成的新型中央—地方关系、国家—社会关系使得市场经济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不以个人意志而改变的道路选择,这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对国家权力的制约。
(二)从同构到分离: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国家自主性比较
分权驱动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的理念就是要释放出公民个体和下级机构的活力,以刺激其创造性和灵活性。这一释放的过程是国家向社会和地方分权的过程,也是重塑国家—社会关系、中央—地方关系的过程。在国家—社会关系层面,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主要体现为以“国家本位”为核心的国家社会同构到以“国退民进”为特征的国家社会分离。
改革开放前,以“国家本位”为观念形成了国家社会同构的局面。国家社会同构主要体现为国家对资源的垄断和对个体的束缚。首先,以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和控制禁锢了社会自主性。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垄断着绝大部分的资源和信息,社会处于国家的全面控制之下而形成了一种“总体性社会”(Totalitarian Society)。以企业为例,国家决定着企业产品的数量、价格和方向,产权和政权的二合一使得企业的身份不是经济发展中以盈利为目标的经济主体,而变成国家行政力量的一个环节。具有政治性角色并没有决定权的企业不可能有动力和意愿去创新。其次,以国家单位为基础对社会个体的控制束缚了个体自主性。改革开放前国家行政权力以国家单位为中心实现了对社会的政治整合和控制,在城市主要是单位体制,在农村主要是人民公社。国家单位集政治职能与经济职能于一体,通过控制资源分配冻结人口流动,个体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依附于国家单位,从而对国家形成了全面依赖的状态。国家与社会的同构以牺牲社会的自主性为代价,国家呈现出一种绝对自主性特征,这种国家自主性形态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因为无竞争机制、无社会自主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
改革开放后,以“国退民进”为特征形成了国家社会分离的局面。由于国家社会同构阻碍经济发展的原因在于对资源的垄断和个体的束缚,那么改革的起点自然是释放资源和个体自由。首先,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提升了社会自主性。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改变了传统国家全权的局面,催生了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社会成为与国家并列、提供资源和机会的主体,也成为制度创新的源泉。仍然以企业为例,随着放权让利改革的推进,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自主支配的资源。企业不再是行政力量的一个环节,而演变为积极主动的经济活动主体,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为社会带来活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对第三产业的鼓励和倡导更是刺激了企业的发展活力。其次,中国社会的利益单元的转换激发了个体自主性。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利益单元实现了以集体为中心向以个人/家庭为中心的转换。特别是在农村,产权制度激发了社会的活力。家庭联产承包制不仅让农民获得自主经营土地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劳动力自主使用、自主支配激发了个体自主性。在中国农业环节引发的“边缘革命”④带动中国进入现代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不仅释放了流动性资源,同时也释放了个人,职业封闭性的打破使得个人对国家的依附性减弱。中国现代政治的一大标志性成果,就是建立在职业分化与平等基础之上的成就与功绩取向。
(三)从封闭到开放:中央地方关系视角下国家自主性比较
以央地关系为视角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是很多学者⑤的切入点,如果以国家自主性为分析框架,从地方政府角度而言,中国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自主性的增强有直接的关联性。分权过程中形成的以创新和发展为特征的地方自主性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强了国家对经济绩效的依赖。在中央地方关系层面,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由封闭到开放、地方政府自主性逐步增强的一个过程。
改革开放之前,地方政府形成的是以“块块”为主、单向服从型的“蜂窝状”封闭体系。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分权导致中国市场的碎块化。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经济发展,都尽力不让本地区的资源和信息外流,地区封锁导致资源配置率低下和重复性建设。分权化赋予了地方政府的权力和动机使得地方保护主义凸显。结果是两次分权都以失败终结,地方政府以“块块”为主的自给型体制的形成,所谓的“诸侯经济”导致中国市场的碎块化。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分权导致中国市场的封闭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命令−服从型,权力下放保持了纵向的中央控权,但割断了横向层面各个地方之间的经济联系、打破了信息的平衡分布,加上地方政府保护主义倾向使得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追求“小而全”的封闭经济体系。结果是地方政府自给自足“蜂窝状”⑥(honeycomb-structure)封闭体系的形成。而高效率经济体制需要建立在信息和资源流通开放的基础之上,封闭的地方政府阻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地方政府封闭性被打破,地方自主性逐步增强。一方面,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对外开放的实行打破了地方政府的横向封闭性。在中国原有的官僚体制的结构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是中国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秘籍之一。“行政管理的分权化和地方官员激励的市场化,这是中国行政体制的灵活性、动员能力的重要来源。”[4](23)市场机制的引入不仅打破了地方政府的封闭性,而且实现了信息和资源的流通,为高效经济体制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从政策执行者逐渐发展为一个拥有独立性权力、独立性利益的主体。分权化改革赋予地方政府获得自主性的条件和能力,分税制改革赋予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权,人事制度改革赋予地方政府人事自主权,而且“在政治的维度上,中央政府将相当部分的决策权力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使地方政府享有一定的自主性,从而形成一个类似于联邦制的框架。该框架对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5](139)。分权化改革在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调动着地方政府的发展积极性,事权和财权加上以政治晋升为目标的竞争,驱使地方政府在自主权基础上扩大其自主性空间,增强其自主性能力。
三、过度与不足并存: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家自主性的失衡
国家在向社会和地方分权的过程中形成了有限自主国家形态,并有效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但以经济绩效为中心的中国面临一个悖论: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发展脱节,社会发展的滞后使得很多人不能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另一方面经济若不发展,很多人会因为经济的不发展而受害。在国家层面就体现为国家自主性呈现出过度与不足的失衡局面。
(一)警惕掠夺性政府:国家专制性权力的过度
国家自主性权力可以划分为两种:一是国家专制性权力(despotic power),即国家可以不与公民社会进行制度化协商而开展活动的范围;二是国家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即国家在其统治领域内渗透公民社会并有效实施其政治决策的能力。[6](5−8)关于目前的中国政府能力,有两种声音,一种是认为政府权限过多,限制了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一种认为政府能力太弱,对很多问题力不从心。两种声音的差异性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建设面临的困境。经济单兵前行导致的收入差距、经济非均衡发展引发的社会不公、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的失衡与断裂⑦等问题,都对政府能力带来新的挑战。王绍光称之为“中国政治怪象”(the paradox of Chinese politics)。
国家自主性的过度主要是国家专制性权力过度限制了社会和市场充分发挥作用,主要体现在社会自主性不足和市场作用发挥不足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自主性不足。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国家社会的分离改变了国家的“全权性”,确实塑造了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但中国政府仍然承担着许多社会自身能自我管理的职能,社会自主性仍然具有提升的空间。二是市场基础性作用发挥不足。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走向成熟,政府减少对经济发展过程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是21世纪政府改革的目标取向。但目前仍然存在政府错位、越位的现象,不利于有序竞争市场机制的发展。
(二)警惕俘获型政府:国家基础性权力的不足
国家自主性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国家基础性权力为基础的公共服务产品供给方面和利益集团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方面。首先,公共服务产品供给呈现不足性和非均衡性。国家渗透力的强弱是判断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标准,国家渗透力弱的表现一是不能直接从社会中抽取资源,二是抽取的资源分配不均衡。中国国家基础性权力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和分配方面。国家在涉及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产品供给方面体现出国家能力的“不足”。在社会阶层分化加剧、贫富差距拉大的背景下,市场化改革对住房、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冲击导致弱势群体的基本社会保障利益受损,但国家力量在这方面显得比较薄弱。
其次,利益集团的形成增加了国家偏离公共利益的概率。中国改革开放始于“放权让利”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念,这必然导致社会利益格局的分化和分层。中国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导致利益集团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不在于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存在,而在于国家能否不受利益集团的影响而保持中立性,制定符合公共利益方向的国家政策。若国家政策被利益集团影响或者绑架就意味着国家自主性会异化为利益集团的自主性而偏离社会公平的轨道。从而增加损害弱势群体利益的几率。例如房地产领域,改革房地产领域的目标是实现公平,但现实情况是如果国家受到相关利益群体的影响,改革的真正含义就存在异化扭曲的可能,也代表着权力和腐败的结合。
四、国家自主性的重塑:国家有限−有效自主形态的建构
我们的理论如何指导我们对国家自主性作出客观的评价?国家自主性应该被强化还是被弱化,答案取决于一国的实际历史背景,因为国家自主性概念具有中立性特征。对国家自主性的分析要根据具体国境而言,国家回归学派的国家自主性概念的应用范围最主要是西方国家,而西方国家是“强社会,弱国家”,所以,国家自主性是需要强化而不是弱化的一方。但在中国一方面不能回避国家自主性限度问题,因为中国仍然处于“弱社会,强国家”状态。另一方面不能回避国家建设问题。“市场自身依靠一套从属性的社会制度网络,其运行则通常由国家来建构并维系。”[7](297)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都需要国家有效引导,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治理秩序必须配以有效的国家管理模式。我们需要思索如何实现国家自主性的均衡性以及如何建构一个良治政府。
(一)塑造有限政府,构建协同共治体系
中国有限政府的塑造意味着国家权力控制范围的适度缩小,重新调整国家市场关系、国家社会关系,让市场和社会发挥更多的治理功能,“建构一个由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共同构成的多中心治理体系”[8](306),形成三种治理主体相对平衡的协同共治体系。
首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指明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界限分明的国家权力清单有利于现代市场体系的发展,只有国家与市场各司其职,才能推进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其次,提升社会自主性。强国家—强社会才是中国未来的国家自主性状态,强社会的塑造意味着个体和社会活动空间的不断扩大和自治能力的不断提升。从中国的社会治理结构而言,国家要放权社会,“寻求社会通过民主参与、社会运动、自治结社以及舆论影响而对国家政治决策进行参与和影响”[9](277)。
(二)塑造有效政府,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中国有效政府的塑造意味着提升国家基础性权力,国家建设的重心由建设型向服务型转变。首先,以社会公正为导向,增强公共服务产品供给能力。公平制度的建构、贫富差距悬殊的消解、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应该遵守“差异化原则”,依法逐步完善以机会平等、分配公平、权利平等为内容的普惠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和民生福利体系。其次,以公共利益为目标,保障公共政策公共性。“建立一个保护基本权利、限制政府对其公民劫掠的法律体系是全球公认的对一个合理的人权社会制度的要求。”[10](315)国家决策要以公共性为原则而不受利益集团影响和绑架。只有当一个国家能行使更多的社会管理职能而能成功防止被少数权贵俘获时,才能实现经济的公正增长和社会的有效治理,民族国家建设的普适性经验是增强国家的自主性,减少国家的依附性。[11](31−44)有限性与有效性是中国政府实现良治的基本方向。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塑造有限政府并不代表对“最小政府”的追求,不代表无限度的弱化政府行为,政府和国家建设要先于民主化进程,非洲和拉丁美洲已经用事实告诉我们脆弱的政府不能促进国家的民主发展。正如福山提出的强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构成了良治政府的三个要素,而强政府是第一位的。“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12](1)中国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自主性社会的塑造必须以有效的国家管理为前提。
注释:
① 这并不代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经济是不增长的,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计划经济虽然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的动荡和混乱,但根据世界银行预测,1950—1975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是4.2个百分点,而且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② 1982年,斯考切波的文章“使国家回归”及其国家自主性概念引起非常大的反响,对于这些重新重视国家问题研究的学者,被大家称为“回归国家”学派。回归国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埃里克·诺德林格(Eric A. Nordlinger)、乔尔 S.米格代尔(Joel S. Migdal)、彼得·埃文斯(Peter B. Evans)、维斯(Linda Weiss)和霍布森(John M. Hobson)、艾尔弗雷德·斯特潘 (Alfred Stepan)、艾伦·凯·特里姆伯格(Ellen Kay Trimberger)、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迪特里希·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艾丽丝·阿姆斯登(Alice H. Amsden)、彼得·卡岑斯坦(Peter Katzenstein)、贾恩弗朗哥·波齐(Gianfranco Poggi))、斯科·罗尼克(S. Skow ronek)等学者。
③ 这里的有限自主(受约束性自主)基于国家的绩效合法性。赵鼎新教授把国家的合法性类型界定为:法律选举型、绩效型和意识形态型,详见The Dingxin Zhao.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④ 家庭联产承包和乡镇企业,两者加上个体经济、经济特区,有学者称它们为来自民间的“边缘革命”。具体参见[英]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M].徐尧,李哲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213−219.
⑤ 从政府体制视角阐释中国经济发展较有影响力的是钱颖一、Weingast等人提出的“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federalism,Chinese style),在中国的M型层级制下实行分权化制度安排有效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从官员激励理论阐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学者周黎安分析和总结了中国政府治理的两个基本特征,即行政的分权化和官员激励的市场化,财政分成、晋升竞争、属地管理和行政逐级发包构成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概念。也有学者从法团主义理论、委托代理理论、财政制度变迁理论角度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现象。
⑥ “蜂窝状”由许文慧提出,主要解释了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体制和中央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的相对独立性带来的是中国社会的分割状态。具体参见:Vivienne Shue.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⑦ 失衡社会是指在一个社会中,一个利益集团或阶层拥有的各类社会资源占社会总资源的比例远高于他们占总人口的比例,另一个利益集团或阶层拥有的各类社会资源占社会总资源的比例远低于他们占人口的比例。所谓断裂社会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几大板块(利益集团和阶层)并存,彼此之间不仅缺乏有机联系,又不能互换、交易、妥协。具体参见王绍光.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参考文献:
[1] 彼得·埃文斯, 迪特里希·鲁施迈耶, 西达·斯考克波.找回国家[M]. 方力维, 莫宜端, 黄琪轩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2] 斯考切波. 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M]. 何俊志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3] 埃里克·A·诺德林格. 民主国家的自主性[M]. 孙荣飞, 朱慧涛, 郭继光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4] 周黎安. 转型中的地方政府: 官员激励与治理[M].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08.
[5] 郑永年. 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0.
[6] Michael Mann. states: war and capitalism. Oxford, Cambridge: Blackwell, 1988.
[7] Hall P, Governing Economy: The Politics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8] 郁建兴. 马克思国家理论与现时代[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7.
[9] 张静主编. 国家与社会[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10] 李侃如. 治理中国: 从革命到改革[M]. 胡国成, 赵梅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社, 2010.
[11] 杨光斌, 郑伟铭. 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苏联—俄罗斯转型经验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07(4): 31−44.
[12] 赛缪尔·P.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tate autonomy: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CHEN Xia, WANG Caibo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State autonomy theory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economy as its core content, provides an analytical perspective to expla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s the historical dividing point, the country transformed itself from absolute autonomy to bounded-autonomy, which promotes China’s econom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from mutual construction to separation produced a relative autonomy socie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 from the closed to the open created local autonomy characterized b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But behi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s state autonomy presents an unbalanced predicament, wee need to figure out how to reshape a balanced state autonomy. On the one hand, we need to build a limited government and form a multiple governance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we need to build an effective government and improve the capacity of public services.
state autonomy; economic development; local government; state; society
D6
A
1672-3104(2015)04−0151−06
[编辑: 胡兴华]
2015−01−22;
2015−06−2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研究” (12&ZD058); 吉林大学种子基金项目(2015BS001)
陈霞(1983−),女,山东新泰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家理论;王彩波(1950−),女,吉林长春人,法学博士,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