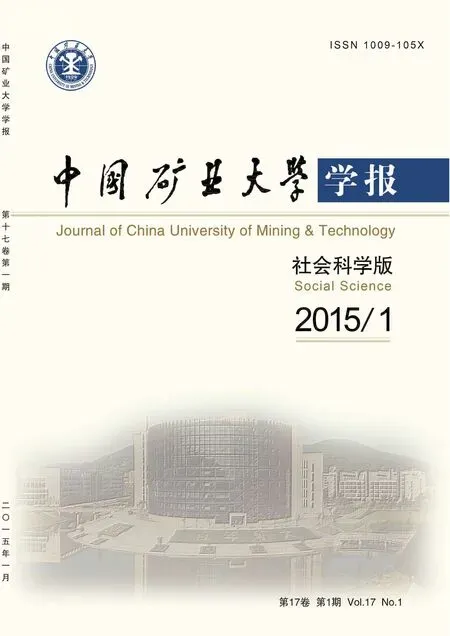左拉与劳伦斯小说中的煤矿书写
张慧捷,史修永
(中国矿业大学1. 文学与法政学院 2. 中国煤矿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江苏 徐州 221116)
左拉与劳伦斯小说中的煤矿书写
张慧捷1,史修永2
(中国矿业大学1. 文学与法政学院 2. 中国煤矿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江苏 徐州221116)
摘要:左拉和劳伦斯是两位伟大的欧洲作家,他们都对煤矿工业进行审美观照和书写,反映了当时英法乃至欧洲的工业社会现实和人的灵魂世界。前者注重对煤矿区的自然写实,后者则倾向对煤矿区的生态批判;前者直观再现矿工悲惨生活,后者偏向表现矿区人们的畸形心理。两人都对疾病和死亡进行隐喻表达,控诉和批判西方工业文明的罪恶,表现出他们对西方社会、自然人性的关怀。左拉和劳伦斯的小说就像镜子一样,折射出煤矿区丰富、复杂而沉重的社会现实,为我们理解现代西方社会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也为我们客观地理解和阐释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左拉;劳伦斯;煤矿;生态;疾病;死亡
在西方现代文学中,许多作家都以文学的形式表达对工业文明的关注和沉思,从不同侧面和不同层次叙述现代工业发展背景下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冲突,以及不同阶层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取向。在众多杰出的作家中,法国作家左拉和英国作家劳伦斯堪称代表,他们对煤矿工业的审美观照和书写,反映了当时英法乃至欧洲的工业社会现实及人的灵魂世界。《萌芽》、《儿子与情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恋爱中的女人》等小说都对煤矿区、矿工阶层生活状况以及社会冲突等问题进行了成功的叙述和表达,这些小说极富有行业特征和时代文化内涵。然而,由于左拉和劳伦斯创作风格的不同。前者擅长自然主义的写法,后者倾向于批判现实的手法,因此,在对煤矿区和矿工的书写上,展现出了各自独特的审美风格,这造成了他们对煤矿工业文明的不同审视和理解,进而为人们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彩的煤矿世界。今天,读解他们的作品能够帮助人们重新回到当时西方社会的场域,透过他们所再现、塑造和想象的世界,可以揭示西方工业社会和文化的某些症候,对于考察和探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中国工业题材文学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矿区的自然写实和生态批判
煤炭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能源动力,大量煤矿区是现代工业文明的象征。它们带给了人类大量的物质财富,推动了现代文明的发展,同时因煤而生的煤矿产业工人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过着被奴役的生活,无法获得劳动的尊严。左拉通过细致入微的描写试图让人们看清楚19世纪末西方原生态的矿区环境,而劳伦斯则是通过煤矿区和自然环境的对比来表达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及忧思。
在左拉的《萌芽》中,矿区这个到处压迫人的空间形象逼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给人一种强烈直观的感受。“这个矿井蜷缩在洼地的深处,和那些低矮的建筑物汇成一片,其中有座高耸的烟囱突兀出来活像一只吓人的犄角。在他看来,这个矿井更像是一头贪得无厌的猛兽,伏在那里随时等着吃人”[1]3,“排气管不停地呼呼作响,就像是一头堵住了嗓子眼的怪兽在喘息”,“气泵依然在喘着那种长长的粗气,这仿佛是永远吃不够的妖魔在呼唤”[1]8。从这里看出,左拉运用丰富的修辞手法和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将矿区机械化生产的工具比作给人以压迫感的“猛兽”、“怪兽”、“妖魔”。这不仅仅能够表现出矿区环境的恶劣,矿井内部设施的不完善,器械的陈旧、原始,而且这修辞的背后“包含对生活的理解、对生命的感知,而这些都具体化为外观,形成个体化的世界”[2]22,让矿区生活的原始情感呈现出来,强烈地渲染了矿井中恐怖、神秘的气氛,进一步说,通过对这些器械“吃人”的叙述,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深刻感受到这些“妖魔”对人的压迫和残害,从而表现出左拉对资产阶级的仇视和对工人阶级的同情。
作为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领袖,左拉试图细致地描绘现实,给人以一种实录生活的印象。因此,在创作《萌芽》这部作品之前,左拉展开了丰富而艰难的调查。他不仅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还亲自深入到矿区,与矿工们一起生活、工作,并且将自己亲历过的感受记录下来,转化为文学创作的素材。所以,在左拉的作品中,对矿区和矿井的描绘显得相当自然写实和生动形象,一些细节描写给读者带来不寒而栗之感。左拉这样描写主人公艾迪安第一次下井时的情形:
突然,罐笼动了,是他的身子晃动了一下,不一会儿一切都变得黑糊糊的,周围的东西好像在向天上飞驰,这种下坠让他感到头晕目眩,似乎五脏六腑都要倒出来似的。罐笼在井上,在盘旋而过的井楼中经过两层收煤处的时候,他就有这种感觉。不一会,他到达漆黑的矿井后,依然有点神志不清,就再没有这种清晰的感觉了。……大家又继续往前走,走了一会儿,来到一个三岔口,又看见两条新的巷道。工人们在这里再次分散,大家逐渐分别前往煤矿的各个掌子面。这里的巷道装有木头框架,一些橡木立柱支撑着巷道的顶,这些立柱俨然是为了防止岩石的坍塌,从框架向后看去,可以看到一层层的页岩,还有闪闪发光的云母,以及大量凹凸不平、灰暗的砂岩[1]22。
显然,左拉用写实的手法描述了艾迪安、马厄一行人是怎样从井口乘坐罐笼下到井底五百五十四米的罐笼大厅,再步行大约两公里到达马厄负责的掌子面——纪尧姆矿脉。作为沟通地面与矿井底部的工具,罐笼的安全性是保障矿工生命安全的重要因素。然而,左拉在此处将罐笼描写成为一个“夜间的怪兽”,虽然罐笼上面装有安全伞,还有一些铁质的挂钩,一旦连接罐笼的钢索断了它们就会伸进控制器。但是,罐笼周围却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只安装着几块条形铁皮和一张小孔铁丝网。在下坠过程中,罐笼还会受到水线中渗出的水的侵袭,使里面的矿工被淋成落汤鸡。此处写到的矿井坑道存在着的安全隐患也为小说最后苏瓦林破坏防水设备,矿工们惨死井下的结局做了铺垫。
另外,小说中有许多文献资料式的描述,如数字,给读者以一种严谨而精确的印象。作者用诸如“五百五十四米”、“直径四米”、“五十厘米”、“35度”等数字,使得关于罐笼和井下恶劣环境的描写更加清晰明了,读者对此的认知也变得更清楚直观。如果没有自己的亲身体验和经历,是难以将细节描绘得如此真实和自然,这也体现出自然主义创作手法的魅力。
然而,劳伦斯却不同,他的作品中关于矿区的描写并不密集,甚至把它作为一个若隐若现的空间存在,但是正是这个象征工业文明的空间场域,却从不同层面显现出劳伦斯对矿区环境和对整个工业文明社会的审美感受。在他的笔下,矿区并不仅仅是一个阴森恐怖的地狱,而且是具有丑恶之美的另一个世界。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开头就写到康妮来到勒格贝老家附近煤矿的情形,“她用年轻的忍耐精神,把这无灵魂、丑恶的煤铁区的米德兰游览了一遍,便撇开不顾了。那是令人难信的可怕的环境”[3]12。同样在《恋爱中的女人》第一章中对女主人公戈珍和厄秀拉所居住的贝多弗矿区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写:
姐妹俩穿过一片黑黑魆魆、肮脏不堪的田野。左边是散落着一座座煤矿的谷地,谷地对面的山坡上是小麦田和森林,远远的一片黢黑,就像罩着一层黑纱一样。白烟柱黑烟柱拔地而起,像在黑沉沉的天空上变魔术[4]6。
在短短的一段话中,与“黑”相关的词就出现了5次,由此可见,劳伦斯与左拉相同,对矿区环境最直接最重要的感受就是“黑”,这不仅仅源于煤炭本身的颜色,更因为黑色这种偏消极的色彩会给人一种厚重的、恐怖的、死亡的、严肃的感觉。的确,劳伦斯认为被工业文明侵占了的矿区是一个黑暗、粗鄙、生态恶化的世界,他也曾在自己的散文随笔《诺丁汉矿乡杂记》中多次用“丑恶”一词来形容矿区和矿工生活。但是,劳伦斯却不是完全厌恶这里。《恋爱中的女人》写道:
姑娘们下到矿区街上,街两边的房屋铺着石板瓦顶,墙是用黑砖砌的。浓重的金色夕阳辉映着矿区,丑恶的矿区上涂抹着一层美丽的夕阳,很令人陶醉。洒满黑煤灰的路上,阳光显得越发温暖、凝重,给这乌七八糟、肮脏不堪的矿区笼罩上一层神秘色彩。
“这里有一种丑恶的美。”戈珍很显然被这景色迷住了,又为这肮脏感到痛苦。“你是否觉得这景色很迷人?它雄浑,火热。我可以感觉出来这一点。这真令我吃惊。”[4]109
通过这样的描写,劳伦斯让人们看到,这脏乱的矿区街道也有美的一面。它的雄浑,它的火热,正是自然人性的特点。在发现煤矿区黑暗肮脏背后蕴藏着美的同时,劳伦斯从更深层的美学理念考虑,把煤矿区作为一个审美参照物,采用理想与现实相对比的方式,以想象的姿态在这片黑暗的矿区旁边设置另一片美的天地,构建一种与黑暗的矿区完全不同却符合人性自然的生态世界。
她们离开了矿区,翻过山,进入了山后宁静的乡村,朝威利格林学校走去。田野上仍然笼罩着一层浅浅的黑煤灰,林木覆盖的山丘也是这样,看上去似乎泛着黑色的光芒。这是春天,春寒料峭,但尚有几许阳光。篱笆下冒出些黄色的地黄花儿来,威利格林村舍的园子里,一丛丛的黑豆果已经长出了叶子,伏种在石墙上的香雪球,灰叶中已经绽出些小白花[4]7。
劳伦斯笔下的矿区是黑暗的,令人感到压抑的,这种黑色蕴含着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和反思,对自然美好社会的憧憬和向往。正如林语堂在评价《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时所说:“劳伦斯此书是骂英人,骂工业骂机器文明,骂黄金主义,骂理智的。他要人归返于自然的、艺术的、情感的生活。”[5]3的确,劳伦斯往往把煤矿区作为一个否定性的空间存在,通过对宁静淳朴的自然和纯净闲适的田园生活的描写,勾画出一幅与矿区形成鲜明对比的自然田园图景,以此来表达自己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对复归自然人性的推崇。在《白孔雀》和《儿子与情人》等作品中,劳伦斯把矿区当做大自然的对立面,展现工业文明与自然的对立,同时以诗意的笔触描绘出一个个生机盎然的自然世界。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左拉对矿区的细致描写和修辞渲染,试图激起煤矿产业工人的对抗性意识。黑暗和吃人的矿区是工人阶级要砸碎的世界,这昭示着工人阶级承担着解放全人类事业的历史使命,因此,左拉笔下的煤矿是一个汇集阶级使命、呼唤民众、指引革命的空间。而劳伦斯深刻认识到工业文明对人心灵的摧残以及所造成的违背自然人性发展的困境,让人们看到他对工业文明的生态性思考和指引人们如何走出精神困境的出路,即对原始自然的崇尚。因此,他的作品没有过多地凸现和强调浓重的阶级对立观念,而是充分展现工业文明与人、自然的冲突和对立,以及人性和自然的复归,以此来拯救现代人的精神迷失。
二、 矿工的物质匮乏与矿区人的心理畸形
由于个人经历和创作角度的差异,左拉对矿工生活的描写主要集中在工业文明对其身体的损害,再现物质匮乏的矿工生活。他善于运用对比的手法,将贫苦的矿工生活与奢侈的资本家的生活作对比,从而将矿工生活的悲惨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而劳伦斯则更注重工业文明对矿工心理方面的摧残,因此对主人公畸形心理的成功描绘是其小说的闪光点。
马厄是《萌芽》这部作品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苦矿工的代表。像马厄一样的矿工,用微薄的工资来维持一大家子的生计,唯有等儿女们长大之后继续到煤矿工作,才能减轻家里的负担。由于贫困,他们缺乏最基本的文明意识和道德观念。马厄一大家子睡在紧挨着的四张床上,平时脱衣服、穿衣服、大小便、洗澡都互不避讳。女性在给孩子喂奶时也丝毫不会顾及身边是否有男性。矿工的性生活非常开放,尚未成年的马厄之子查夏里就已经与情人菲勒梅有了孩子,就连年幼的让兰也学着做那些“隔壁或者通过门缝听到和看见的事情”。这样一来,矿工们的孩子越来越多,孩子一多就更加重了家庭的贫困,成为一个恶性循环。
与矿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坐享其成的煤矿资本家。克雷古瓦是蒙尔苏煤矿的股东,他平时不需要工作,一年就有四万法郎的收入。马厄一家十口人住在一个简陋的小房子里,但仅有一女的克雷古瓦夫妇却与佣人一起住在奢华宽敞的彼奥莱纳庄园。马厄的儿女们生活在完全没有屏障的屋子里,家里也没有像样的家具,而克雷古瓦的女儿塞尔西的闺房却布置得相当阔气,《萌芽》写道:
里面张挂着蓝色的绸帷幔,白底蓝格的家具油光锃亮,父母很溺爱她,尽量满足她。依稀的晨光从窗帘的缝隙中射了进来,光线不明亮,在洁白的床上,年轻的姑娘将半边脸枕在赤裸的胳膊上,睡得正香。
她(塞尔西)的肌肤相当好,又嫩又白像牛奶一般,栗色的头发,圆圆的脸蛋上“栽”了个任性的小鼻子,陷在两颊中间。被子已经滑落,她均匀地呼吸着,以致她那已经变得沉甸甸的胸脯都看不出在上下起伏[1]52。
相反,再看左拉对矿工马厄15岁的女儿凯特琳的描写:
终于,凯特琳挣扎着起床,她伸了个懒腰,又用双手拢了拢额前和项背上乱蓬蓬的红棕色头发。十五岁的她身体显得很瘦弱,从紧裹着身子的内衣中伸出的,是那像被煤刺过花纹似的发青的双脚和细细的胳膊。她胳膊的颜色是乳白色的,和她那苍白的脸完全不同,因为经常使用劣质肥皂洗脸,她的脸色已经损害了。她打最后一个哈欠的时候稍稍张大了点嘴巴,露出两排漂亮的嵌在患萎黄病的苍白的牙龈间的牙齿,她那双战胜瞌睡后的灰色眼睛在流着泪水,神情疲惫痛苦而劳累,累得她那赤裸着的肌肤仿佛全都是浮肿的[1]10。
这种强烈的对比,让人们看清楚矿工生活与资本家生活之间的巨大差距,煤矿工人真实而悲惨的生活也就充分体现出来了。劳伦斯的小说直接描写矿工生活的内容并不多,并不像左拉一样从不同生活角度来展现矿工悲惨的生活状态。但是,劳伦斯善于对矿区家庭成员畸形心理进行描写。《儿子与情人》可以说是劳伦斯的一部自传性作品。整个家庭故事是在矿区里展开的。主人公保罗的父亲莫瑞尔是一位矿工,由于长期井下沉重的劳作和不断经历井下事故,让他变得脾气暴躁,酗酒成瘾。母亲却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文化程度较高、对生活有追求的富家女。两个不同阶级不同性格的人的结合造就了不和谐的婚姻,夫妻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冲突。这种特殊的矿工家庭最终导致儿子保罗的畸形心理。保罗的母亲是整个家庭的核心,而父亲却被排斥在外,没有任何地位。由于母亲莫瑞尔太太对丈夫彻底绝望,她把所有的感情寄托在保罗身上,致使母子之间产生异乎寻常的感情,在“恋母情结”的支配下,保罗个人的爱情与婚姻受到了强烈的影响。他在与初恋女友米丽亚姆的交往中,处处受到母亲的影响和牵制。他在与其他女性的交往过程中也难以摆脱母亲的影子,因此他不能在精神上依赖米丽亚姆,却在肉体上占有她。此外,莫瑞尔太太对保罗过度的占有欲使得她排斥保罗真正爱的女性。对于克莱拉,她与保罗仅仅是肉体上的关系,而无精神之爱,因此莫瑞尔太太可以与她和平相处,一起在背后辱骂米丽亚姆。但米丽亚姆与保罗是真心相爱的,他们的感情不是建立在肉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因此,莫瑞尔太太百般阻挠,对米丽亚姆痛恨至极。这样畸形的母子关系造成了保罗心理的扭曲。“他喜欢跟她一起走过田野,到村里去,到海边去。她害怕过那些木桥,他笑她像个小孩儿。总之,他和她形影不离,好像他是她的男人一样。”[6]189小说中多处写到保罗对母亲独一无二的爱,在他的意识里,母亲就是全部。他甚至将自己的父亲看作是情敌,在父亲受伤时不闻不问,当父亲殴打母亲时,在心里祈祷他被砸死在井下。
然而,劳伦斯的高明之处并不仅限于此,保罗的畸形心理并不仅仅是“恋母情结”,还有他在恋母基础上的残暴本性和变态性格,这是一种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下的反抗和爆发。按照常理,保罗深深地爱着自己的母亲,他可以为她做任何事情,付出一切,他是不会做出伤害母亲的事情的。然而,在莫瑞尔太太生命垂危之时,他却亲手了结了母亲的生命。身患癌症的莫瑞尔太太受着病痛的折磨,保罗却将母亲止痛用的吗啡全部拿出来,将药片碾成粉末。当安妮问他在干什么的时候,他竟然说要将它们全部放到母亲喝的牛奶里,二人还像“在策划什么阴谋的小孩子一样笑了起来”。当母亲发现牛奶异常的时候,保罗也丝毫没有悔改之心,而是骗母亲说这是一种新药。最终,服用过量吗啡的莫瑞尔太太病情急转直下,于第二天上午死去。口口声声说深爱着母亲的保罗最后亲手夺走了母亲的生命。更让人感到震撼的是,在母亲去世后,保罗竟然可以若无其事地擦靴子、打牌,这与之前保罗强烈的恋母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因而也将保罗的变态心理描绘得淋漓尽致。
除了塑造具有非理性、畸形心理特征的矿工家庭形象外,劳伦斯还刻画了一系列有偏激行为、畸形心理的富人形象。如《恋爱中的女人》中的赫麦妮和杰拉德。赫麦妮是一个占有欲极强的女人,她的外表光鲜亮丽、安富尊荣、自信傲慢,但内心却“有一个可怕的空白,缺乏生命的底蕴”,只有当伯金在她身边的时候,她才感到自己是完整的,而在其它时间里,她都会感到自己就像建在沙子上的房屋一样摇摇欲坠。她敌视一切与伯金亲近的女人,看起来很爱他,却常常与伯金对着干,甚至想要杀死他。当她兴奋地用青金石砸烂伯金头的时候,她感到“情欲的狂喜与美妙的快感”。而杰拉德同样是一个权力欲非常强的人,他从父亲那里接管煤矿后激动不已,把煤矿作为他实现权力意识的工具。他要用最高效率采最多煤,把煤控制在自己的意识之下。小说第九章“煤灰”中,写杰拉德在火车的岔道口制服烈马,他让马朝向轰隆的运煤火车,面带微笑地驾驭惊恐着、嘶叫着、前后蹄飞扬着、身体不停地打转的枣红色马,充分表现出他残忍的权力意识。
因此,左拉擅长把矿工底层的生活场景再现出来,让人们看清楚当时法国矿工真实的生活状态,从而造成一种凄惨和悲剧的审美气息,让人产生怜悯、同情之感和对资产阶级的痛恨之情。而劳伦斯则是通过揭秘矿工家庭成员的畸形心理和富人变态的权力欲望,探索人的无意识心理和原始的欲望本能,从而反思传统文化和批判工业理性主义、资本主义工业文明。
三、 疾病与死亡的审美意义
煤矿从发展之初就是一个高危、高污产业,疾病和死亡每时每刻都在威胁着矿区的人们。不可避免,矿工的疾病和死亡也是左拉和劳伦斯煤矿书写的对象。左拉笔下的疾病描写表现为各种职业病对矿工身体的折磨。《萌芽》第四部第七章中写道:“艾迪安研究过矿工的职业病,他把它们一一列举出来:贫血、淋巴腺结核、矽肺、窒息性哮喘和会引起瘫痪的关节炎,详细至极,令人吃惊。”[1]202疾病似乎伴随着所有的矿工,马厄一家人都患有贫血症,马厄老婆和孩子们患有遗传性淋巴腺结核,善终患有风湿病,马厄患有气喘病和关节炎。这些仅仅是矿工职业病中的一部分,他们的一生都将伴随着这些职业病,甚至最终因为这些疾病而死亡。
小说中职业病最突出、最严重的矿工代表是善终老人。他由于自幼在矿井工作,肺部吸入了大量的煤灰,即使不再下井也还是不断地咳出“黑痰”。“是煤……在我身体里有的是煤呢,够我烧到临终了。不过我已经有五年没到井下了,看来这东西我还有不少存货,这事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楚。嘿!那就让它放着吧!”[1]6善终老人的黑痰几乎伴随着整部小说情节的发展。自他的祖父开始,他们全家人就为蒙尔苏煤矿公司工作,他的父亲、两个叔叔和三个哥哥全都葬身井下,他自己也落下一身疾病。即使在小说结尾,矿工罢工失败,他的儿子马厄牺牲之后,已经没有意识的善终老人仍旧无法摆脱“黑痰”的折磨。
然而当这些患有严重职业病的可怜矿工向矿区的医生求助时,那些医生却总是喊着“别烦我了”,就匆匆离开,从未真正认真地为矿工们看过一次病。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资本家,他们养尊处优,身体健康壮实,一旦有病就会有专门的私人医生贴身为其诊治。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完全对立的生存状态,更加凸显出左拉想要表达的思想:“可怜的穷人们被当做草料扔进粉碎机里,像牲畜一样被圈在矿工村里,各大公司给他们规定了奴隶般的劳役,把他们的血一点一点吸干,还扬言说把劳动者全都网罗过来,让百万只胳膊给一千个懒汉创造财富。”[1]202这表现出他对工人阶级的深切同情,对资产阶级的无比痛恨,以及希望工人阶级能够联合起来积极反抗的愿望。
与左拉相似,劳伦斯作品中的许多人物都有“肺结核体质”。这类病症与矿区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烟囱”城市的环境污染息息相关。在《儿子与情人》中保罗的哥哥威廉就是死于肺病,随后保罗也得了一场严重到足以致命的肺炎。学界猜测,劳伦斯本人也患有肺结核,与其作品中的人物相似,劳伦斯的身体常常受到肺病的影响和威胁,表现为“情绪容易失控、暴怒,在与两性关系的另一方发生剧烈冲突之后,又会很快恢复平静。”[7]30这类疾病产生于工业文明覆盖下的现代社会。可怕的疾病不仅仅摧残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的身体,更成为一种潜伏在人们心中的对生命的惶恐和对死亡的畏惧。
比疾病更残忍的死亡,让左拉和劳伦斯的小说折射出更深层的审美意义。“死亡促使人沉思,为他的一切思考提供了一个原生点,这就有了哲学。死亡促使人超越生命的边界,臻求趋向无限的精神价值,这就有了伦理学。当人揭开了死亡的奥秘,洞烛了它的幽微,人类波澜壮阔的历史和理想便平添了一种崇高的美,这也就有了死亡的审美意义。”[8]4在小说中,死亡并不仅仅意味着生命的终结,预示着一种神秘力量的完结和崩塌,它还昭示着一种生命的新生。马厄是左拉《萌芽》中觉醒矿工的代表,而杰拉德是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中利欲熏心的资本家代表。他们的死亡直接与煤矿生活有关,前者与煤矿内的阶级斗争有关,后者与工业文明的异化相联。因而他们的死亡在各自小说中都有着特殊的美学意义。马厄是《萌芽》中的主人公之一,艾迪安正是通过与马厄一家的交往才逐渐接触矿工、矿井,可以说,马厄一家的命运是贯穿整部小说的主线。左拉通过对马厄这个人物的描写,展现了在工业文明重压下的煤矿工人从愚昧无知、一味顺从到逐渐觉悟、开始反抗的过程。马厄原本是一名普通的矿工,他的身上却承担着一个九口之家的沉重负担。他是一个勤劳正直的人,然而,资本家残酷的剥削和压榨逼得这样一个老实的工人也无法忍受了。他在艾迪安的启发和引导下开始觉醒,开始想要用实际行动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善全家人的生活现状。在罢工过程中,马厄始终与艾迪安并肩作战、积极抗争:在罢工开始的时候,他作为工人代表同资本家谈判;当罢工的群众与警察对峙的时候,他奋不顾身,“解开上衣,扒开衬衫,露出毛茸茸的、满是煤痕的胸膛”,“对着刺刀冲过去”,最后壮烈牺牲在资本家雇来的警察的枪口之下。此时的马厄已经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这个人物的身上体现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底层劳动人民从不觉悟到觉悟、从一味顺从到积极抗争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整个无产阶级的成长历程。然而,这样一个开始觉醒的工人却死了,他的死亡与罢工的失败有着直接的联系。一方面,他的死表明受苦受难的工人阶级已经开始觉醒,开始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为了改善自己的命运和生活、为了打破现有的不公平的社会状态而斗争,斗争中他们英勇无比,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马厄最终还是死了,这是一个悲剧的结局。他的死亡预示着艾迪安领导下的工人罢工的失败。究其原因有四,其一是艾迪安个人日益膨胀的权力欲望和盲目的领导;其二是工人阶级力量的弱小与资产阶级的强力镇压;其三是缺乏正确的领导思想与物质方面的支持;其四是工人阶级内部不团结,导致罢工的工人受到了内外双重夹击。正是这四个原因导致了罢工的失败,同时也导致马厄的死亡。虽然罢工失败和马厄死亡容易给读者带来阅读的阻碍,但是矿工的死并不是无价值的牺牲,而是充满生命力的萌芽,它告诉人们这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和开始。小说的结尾给读者以希望的曙光,这也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新的生机出现。
杰拉德是《恋爱中的女人》中的一个主要人物,他是一个极具管理头脑的煤矿工业巨子。在他接替父亲的职位掌管了煤矿之后,很快就找到了煤矿运转困难的症结所在:是因为他父亲过于念旧,从而把煤矿办成了“慈善机构”。于是,他立志要改变这种情况,要抛弃“民主、平等”的思想,于是他大张旗鼓地进行了重大改革。他在各方面压缩开支,把原本免费送给寡妇的煤收费,还建立了发电厂,引进了新的机器,使矿工们沦为单纯的生产工具。
杰拉德冷血无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物质主义者。他痛恨矿工,甚至从小渴望枪杀矿工。他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没有丝毫同情心。但是,他确实是一个成功的改革家,在他的改革下,企业的管理变得正规化、程序化,收入也大幅度增加。然而当矿工完全沦为机械的附庸的时候,资本对人的异化已经扩展到它的主人身上,杰拉德也变成了一个精神空虚、缺乏生命气息、感情枯竭的人。他声称自己“活着就是为了工作,就是为了生产东西”。能够使他感到幸福的就只有毒品的麻醉、伯金的安慰和对女人的陶醉。杰拉德身上令人窒息的死亡气息最终使得戈珍离他而去,他也在被抛弃之后变得精神错乱,死在了冰天雪地的山谷中。因此,杰拉德的死亡一方面在批判工业文明对人性的异化,工业文明的顽疾不仅仅影响到矿工,还侵扰着处在社会上层的资本家,这充分表现出被工业文明侵袭的现代社会中出现的严重的精神危机和社会危机,突出作者创作的主要思想;另一方面,工业文明的代表杰拉德最终魂归冰冷宁静的雪山,这象征着工业文明的消逝以及原始的、纯净的大自然的复归,流露出劳伦斯个人对工业社会的批判态度和对大自然的崇尚之情。
左拉和劳伦斯小说中对疾病的隐喻表达,意味着对工业文明的控诉和对西方现代社会冲突根源的探索,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畸形发展的恶果昭然若揭。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层级两端的两个人物马厄和杰拉德,在小说结尾都走向“死亡”,这样的设置表现出左拉与劳伦斯一个共同的思想,那就是已经觉醒的社会底层劳动者将用自己的反抗来推翻现有的不平等的和扭曲人性的社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工业社会必然走向衰落和灭亡,合乎人性的理想社会必然会建立。虽然这是作家的美好想象,但也充分表现出他们对西方社会、自然人性的关怀和为人类寻找新生之路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四、 结语
煤矿为左拉和劳伦斯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和写作资源。左拉主要从煤矿细微的外观形式,着眼于自然的写实,让本来幽暗、阴森、凝固的煤矿涌动着斗争、冲突、反抗和革命的生命力,同时通过修辞艺术来渲染和集聚政治意识形态,完成对煤矿产业工人悲惨生活的确认和表达,彰显出煤矿世界中充满挣扎和反抗的苦难之美,具有沉重的历史感和使命感。而劳伦斯更多地是从宏观的视角,一方面展示煤矿世界丑恶;另一面将丑恶和异化的煤矿作为审美参照物,利用强烈的反衬来折射工业文明的痼疾,从更深层和更隐秘的心理层面来窥视和显现被现代工业文明压抑下的人的原始欲望和自然人性,以此唤醒沉睡的生命,建构更加生态自然的世界。左拉和劳伦斯的小说就像镜子一样,折射出煤矿区丰富、复杂而沉重的社会现实,为我们理解现代西方社会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也为我们客观地理解和阐释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1]左拉.萌芽[M].刘征,译.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9.
[2]谭善明,等.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变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3]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M].饶述一,译.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95.
[4]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M].黑马,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5]林语堂.谈劳伦斯[M]//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M].饶述一,译.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95.
[6]劳伦斯.儿子与情人[M].王巧俐,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7]刘洪涛.荒原与拯救:现代主义语境中的劳伦斯小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8]陆扬.死亡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史修永 (1977-),男,文学博士,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中国煤矿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中文系主任,硕士生导师。
Description of Coal Mines In Novels by Zola and Lawrence
ZHANG Hui-jie1,SHI Xiu-yong2
(1.School of Literature,Law and Politics,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2.Research Center of China Colliery Literature and Culture ,Xuzhou 221116,China)
Abstract:Zola and Lawrence are two great European writers, who write about the coal industry from aesthetic perspectives and reflect the social reality of the then European (as British and French)industries and the world of the human soul. Zola pays attention to natural realism of the coal mines while Lawrence tends to wri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riticism. Zola gives a direct descrip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the miners’ miserable life while Lawrence has the propensity to show the abnormal psyche of the coal mining community. In denouncing and criticizing the evils of the west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hey all use metaphors to write about disease and death to show their concern for the western society and the human nature. Like a mirror, their works reflect the colorful, complex and heavy social reality of the coal mines, thus providing a unique perspective as well as beneficial references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modern western society, and to objectively appreciate and explain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Zola;Lawrence;coal mines;ecology;disease;death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2015)01-0106-07
作者简介:张慧捷(1991-),女,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3RC23).
收稿日期:2014 - 10 -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