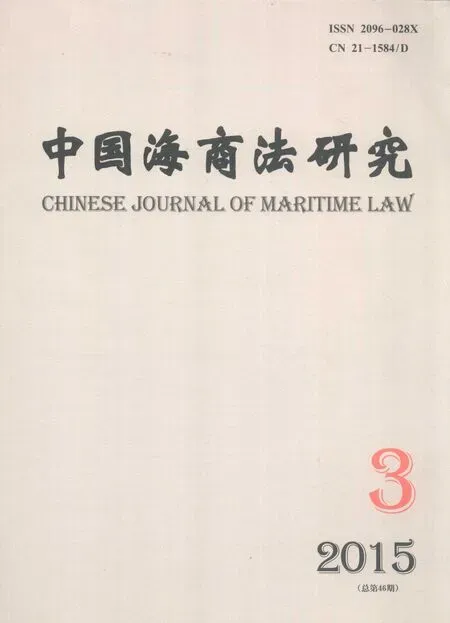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概念及其展开
安晨曦,王 琦
(1.海南省南海法律研究中心,海南海口 570228;2.海南大学法学院,海南海口 570228)
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概念及其展开
安晨曦1,2,王 琦2
(1.海南省南海法律研究中心,海南海口 570228;2.海南大学法学院,海南海口 570228)
存在主权国家,则必有其管辖权力。当今国际海洋事务正经历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各国在行使海上管辖权的过程中,争议与冲突日渐增多。在中国维护海洋权益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已初见端倪。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系定位于国际法层面、主权意义上的管辖,更多地表征着维护国家海洋主权与海洋权益的独特品性。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是国家作为特殊的民事主体,根据权力指向对象为标准而分类之产物,其着眼于权力指向对象的主权归属问题,包括但非限于主权国家对以自然形态客观存在的海洋系统的管控;对各管辖海域的海域活动、涉海事务、涉海行为等管控权力,具有宣示国家海洋主权的时代品格。
国家管辖权;国家海上管辖权;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海洋权益
“从全世界范围来说,海洋新世纪应当是多数国家全面认识、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世纪。”[1]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关系中涉海因素的日益增多,国际海洋事务正经历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近年来,中国与海上邻国在渔业、环境、科研等方面的利益争夺日趋激烈,如何有效地运用和行使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提高中国对海洋的实际管控能力、化解涉海事件之能力,进而维护海洋主权与海洋权益将是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然而,中国学界对于国家海上管辖权的学理研究也仅属初级阶段,作为理论创新的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概念的提倡,更是鲜为人知。在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之背景下,虽然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作为一个“异样”的法律概念尚未被正式界定和使用,但官方与民间已在不知不觉地探讨与之相关的问题。如海洋环境污染管辖、海洋渔业资源开发管辖、油气资源开发利用管辖等等。可见,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在中国已初见端倪。任何一个概念均是在特定时代中人们意识的反映,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这一概念也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同时,一个科学的概念,既要具有“一种理论性的品格”,又要具有一种“客观的品性”。[2]于此,尝试性地对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及其核心概念予以界定,是其理论体系构建乃至指引管辖实践的前提与基础。
一、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的由来
“不明白某学术上之用语者,亦不明白该学术。”[3]概念系任何理论之基石,若概念不明晰,则判断难以确立,推理难于立足,进而体系无法确立。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理论体系之建构,亦应以支撑该理论的相关概念之准确厘定为前提。国家管辖权、国家海上管辖权、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三个逐级递进的概念是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理论中的关键词,需要从三类管辖权的多元递进关系中考究海上民事管辖权之生成背景及根源。
(一)源于主权与国际法的海上民事管辖权:研究思维定位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公约》)将海洋划分为法律地位不同的若干海域,法律地位的差异决定了国家行使海上民事管辖权有着不同的权力来源或基础:领海内的民事管辖权系源于国家主权;领海外的海域则主要依据《公约》的授权①当然,国家在领海外行使海上民事管辖权的依据除《公约》外,还包括国家制定的符合《公约》和其他国际法规则的相关国内法。。
1.派生于国家主权的国家管辖权与国家海上管辖权
一般认为,现代国家主权有四种具体权能,即平等权、独立权、自卫权与管辖权。[4]125可见,国家管辖权派生于国家主权,是国家主权的基本属性,有其源流的发展脉络可资溯源。根据《国家权利与义务宣言草案》第2条之规定:“各国对其领土以及境内之一切人与物,除国际公法豁免者外,有行使管辖之权。”[5]111它表征着各个国家基于领土主权享有对其领土及域内一切人的行为、客观存在物、事件等进行管理的权力。世界的海陆二分法已众所周知,国家管辖权从空间维度可分为陆上管辖权与海上管辖权。海上管辖权是以陆域管辖权为参照系,是在世界各国把开发海洋、利用海洋列为国家发展战略之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国家海上管辖权派生于国家管辖权理论,是国家主权在海域时空的具体表现,如国家基于属地管辖权对其领海拥有管辖权;前者虽遵循了后者的基本理论,但二者并非同日而生,前者基本是伴随人类活动由陆地向海洋的发展而出现;因海洋系统及海域活动有异于陆地资源与事务,所以前者更多地展现了自身的特有属性,更多地承载了维护国家海洋主权与海洋权益的时代使命。
2.定位于国际法管辖语境的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②此处所言的“国际法”主要指称《公约》,当然还包括中国参加的有关海上民事管辖权的其他公约。诸如船舶碰撞方面的《1910年统一船舶碰撞某些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1952年船舶碰撞中民事管辖权方面某些规定的国际公约》《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公约》,海难救助方面的《1979年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船舶污染方面的《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1972年防止倾倒废物和其他物质污染海洋公约》《经1978年议定书修订的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1990年国际油污防备、反应和合作公约》《2001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等。
“管辖”一语,在词源解释学中注解为“管理或统辖”,且“管”与“辖”也都有“管理”的含义。而言及管辖权,必然会涉及法律,因为“依法治和民主的观点来分析,权力不仅在历史而且在现实中都是由法律所赋予给特定组织的职责或义务。”[4]9但无论是国内法抑或国际法范畴内的“管辖”、还是陆域与海域时空内的“管辖”,均属性质不同,功能各异,在各自范畴内涵义极其丰富、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传统上,国内法上的管辖主要解决国家在事实上行使其管辖权的范围和方式问题,因而更侧重于司法诉讼管辖与行政管理程序中的行政管辖。如国家主体对“案件”的管辖(民事诉讼案件管辖、刑事诉讼案件管辖、行政诉讼案件管辖、其他非诉讼案件管辖等)、行政或公共事务领域的管辖(行政主体的执法管辖)等;而且在学理研究中,一般以陆域时空内的民间事务管理权或社会治理的主体权限配置为研究视野。而国际法上的管辖,国际法学者对其认识多以国家和国家主权的观念为前提,一般多用“国家”加以修饰管辖,即国际法上的“国家管辖权”主要宣示了一国的主权,划定了某一特定国家对某类事务、某些行为等而相对于他国的有效权力范围,反映的是一种主权意义上的权力归属。于此可以看出,国际法与国内法范畴内的管辖表征着不同的意蕴,国内法上的管辖基本是在国家主权所及的领土范围内来具体分配微观意义上的管辖主体之权限;而国际法层面的管辖是在宏观主体——各个国家的平台领域,根据适当的原则、国际法规范等手段来解决某类事务、特定行为等归属哪个具体的国家来行使权力,几乎不涉及具体国家域内微观主体的权力界分问题。因此,这也正如国际法学者所言,国际法上的管辖决定国家可以采取各种形式的管辖权的可允许限度。[6]
因国家基于主权而对其领海拥有当然的民事管辖权,故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研究的定位侧重于国际法层面的管辖,如国家在领海外的其他海域基于《公约》、关涉海上民事管辖权的其他公约等行使管辖权的问题。至于某类涉海事务归属中国管辖无争议之后,如何再行分配微观的管辖主体问题则属于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研究的侧面,这一点是研究海上民事管辖权的首要思维定位。
(二)陆域到海域及案件到事务的民事管辖权:研究视野拓展
社会科学研究中,学者历来有着对其研究的概念进行分类之偏好,国家管辖权理论的研究亦不例外。理论研究中对于管辖权的不同分类或者诸学者对管辖权分类的各异见解中,虽也有“民事管辖权”这一学理称谓的提倡,但无论在国内法抑或国际法领域均主要指称的是民事诉讼(司法)管辖权,即仅指某种“案件”的管辖。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章关于国内民事诉讼管辖的规定,这种管辖不仅仅属案件管辖,而且属于微观层面法院主体间权力的配置,不涉及国家主权问题;《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章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的管辖,这种管辖虽涉及到国家主权意义上司法权在不同国家间的归属问题,但也是一种案件的管辖。再转向分析号称“海洋宪法”的《公约》,《公约》第28条规定了“对外国船舶的民事管辖权”,但这实质上也是一种民事案件的管辖①《公约》第28条规定:“对外国船舶的民事管辖权:1.沿海国不应为对通过领海的外国船舶上某人行使民事管辖权的目的而停止其航行或改变其航向。2.沿海国不得为任何民事诉讼的目的而对船舶从事执行或加以逮捕,但涉及该船舶本身在通过沿海国水域的航行中或为该航行的目的而承担的义务或因而负担的责任,则不在此限。3.第2款不妨害沿海国按照其法律为任何民事诉讼的目的而对在领海内停泊或驶离内水后通过领海的外国船舶从事执行或加以逮捕的权利。”。又如《1952年船舶碰撞民事管辖权某些规定的国际公约》所规定的船舶碰撞事件中的民事管辖权亦属于案件的管辖。同时,民事管辖权的既有理论或观点的抽象与形塑主要是以陆域的管辖经验为视野,虽也有海域管辖权的探讨,但成果甚少,基本是在传统的领土管辖——“陆地”框架内进行的局限性研究,因此仅属于“海上民事管辖权”研究的一个侧面,所以不能与笔者的研究重点同日而语,进而也就不易从前人对陆域管辖的研究中得到太多借鉴。即便在国家陆域管辖的学理与实践中,也很少提及民事管辖权的概念,或者诸学者先前研究的仅仅是民事“案件”的管辖权。笔者所提倡的海上民事管辖权,突破了既有理论的局限,一则将行使管辖权的范围从陆域延伸至海域;另则将管辖权的对象由案件或事件的管辖拓展到对于海上非争讼性民间事务的管辖。
(三)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之源:研究背景剖析
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这一概念是个新生事物,因源于实践,则需从实践探求其根源,笔者认为主要有四层背景。
1.国家海洋战略层面
作为发展中的海洋大国,中国在海洋有着广泛的战略利益。“每一个国家都有采取适合于自己情况的手段,对本国资源及其开发实行有效控制的权利,包括有权实行国有化或把所有权转移给自己的国民,这种权利是国家充分行使主权的一种表现②参见1974年5月1日联合国大会第2 229次会议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是国家作为特殊的民事主体,对其全部海洋生态、海洋资源与海洋民商事活动等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的表达。提倡这种管辖权之根本目的在于落实“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等战略目标,并针对当前海上民商事活动乃至海权争夺等现实问题做出学理上的回应。
2.国家民事赔偿请求权层面
在涉海事务、涉海活动中,国家作为海上刑事犯罪、海上行政管理的(追诉)主体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如果仅有目前的两种管辖权限或处罚手段,那么对于损害国家海洋资源、环境等而尚不构成犯罪、行政处罚标准或即便已构成犯罪或需要承担行政责任的行为,将不能依据国家所有权请求民事赔偿,国家海洋利益将受到极大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3条规定:“海域属于国家所有”。因而,国家作为海洋天然资源的所有权主体,对此些国有财产享有所有权,同时也对因生态、资源等开发利用而引起的事件(如海洋生态损害)拥有处理权限,这也是国家参与民事法律关系最重要的类型。因此,依据逐步得到众多学者承认的“国家作为民事主体”之观点,当海上事务、活动中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行为给海洋生态、资源等造成重大损失时,国家主体的意志执行机关①关于何种组织能够代表国家请求赔偿,有学者曾撰文建议:“国家主体意志的产生,必须通过一定机关的活动来实现。从法律上说,国家主体的意志执行机关只是那些能够以国库的财产为基础、代表国家从事民事活动的国家机构。”将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而这种“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基于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而产生的②如国家海洋局于2014年10月制定了《海洋生态损害国家损失索赔办法》。。[7]当然,这里强调因海上民事管辖权的行使而提起损害赔偿请求,并不排除另两种管辖权限同时行使之情境下,三种责任形式的一并承担。而且,上述主要是基于行为人侵害国家利益的情形而言,在此并未否定行为人单纯侵害私权的行为,如船舶内发生的民事争议,也未否认行为人之行为同时侵害了公权与私权,如海洋污染事件中不仅对国家所属的生态资源造成损害,也对渔民培殖的非自然鱼等个人财产造成侵害。
3.国家领土管辖认识转型层面
整个世界的“陆地与海洋二分法”、“中国约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国土非等于国家所辖的陆地”等观念意识的逐步清晰化,使得陆域管辖的理论与管辖实践逐步有甄别地向海域延伸,而在海域管控领域也必须有独立的、自成体系的理论架构——国家海上管辖权理论。这套理论是主权国家之间,尤其是沿海国与非沿海国、海洋强国与弱国之间在海洋权益维护与争夺中的法理依据。其中,维护海洋生态资源主权与涉海事务中相关主体权益意识的日益增强,客观上呼唤国家海上管辖权理论之分支——海上民事管辖权理论体系之形塑与培植,这也将有助于完善国家海上管辖权的理论体系。
4.国家立法规范层面
虽然《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等成文规范中有关于“民事管辖权”的少量显性术语以及虽未直接言明“民事管辖权”,但有属于民事管辖权范畴的相关规定,但这些规定的内容不足以涵涉最广义海上民事管辖权的涵义,亦与海上管辖权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时代语境不相契合。因而,海域视野下的民事管辖权概念以及相关理论需要在成文规范已有涉及的情境下,进一步以此为依托而不断丰富与拓展,不仅使其具有理念革新的意义,同时也为涉海事务的管辖实践提供可予操作的规范指引。
二、国家管辖权与海上管辖权类型解构
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这一概念本身是个有争议的概念。虽然国家管辖权、国家海上管辖权的概念与内涵较为清晰,但不必然推论出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的概念。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国家海上管辖权理论分类的多元性以及学界对多元类型的百家争鸣。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概念与内涵的准确界定,除了依托对海洋实践活动、海洋管辖现状等经验事实的归纳、提炼与抽象等工具手段外,更依赖于对国家海上管辖权类型的清晰认识,若厘不清这层分类,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概念甚者由其引出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只能在争鸣的夹缝中生存。于此,需要以分析国家海上管辖权的分类为突破口,在各类型的辨析中推论出海上民事管辖权之概念。
(一)国家管辖权类型的学术梳理与评析
如前所述,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派生于国家管辖权理论,其概念与内涵的界定依赖于对国家管辖权及国家海上管辖权类型的研究。何谓国家海上管辖权,借鉴已有成果,“国家海上管辖权是国家依据主权和国际公约、国际惯例,对各种海域中的人、事、物进行管理和处置的权利,是国家管辖权的重要组成部分。”[8]这一概念虽有一定的不周延性,但能够为我们界定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提供理论指引。这一概念其实只是将国家管辖权概念的理论具体化到海域空间,其余要素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因而,国家海上管辖权的类型化,可以先行考察国家管辖权的分类。目前学界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将国家管辖权分为不同的种类,笔者择其要点略论。
1.立法管辖权与执(法)行管辖权
持该观点的学者主要有美国学者路易斯·亨金、日本学者松井芳郎等。[9]332,[10]但他们对于执法管辖权又有不同的解释,路易斯·亨金认为:“在牵涉国家适用法律的权力时,国际法将国家的立法管辖权与执法管辖权加以区分,并且,通常将后者称为‘审判管辖权’”。[9]367松井芳郎则认为:“采取征税、搜查、没收、逮捕等的强制措施的权限称为执行管辖权。将事件依法审理、判决或决定的权限称为司法管辖权。执行管辖权和司法管辖权也被统称为强制管辖权或执行管辖权。”中国大多数学者也持这种观点,如学者张乃根认为:“一国在其领土内拥有立法、司法和行政管辖的绝对权力,通常称为立法管辖、司法管辖和执法管辖。”[5]113
2.立法管辖权、行政管辖权、司法管辖权
英国学者希利尔认为“有必要对立法管辖权和执行管辖权进行区分,也有必要对立法管辖权、行政管辖权和司法管辖权进行区分。”[11]136从他的论述来看,执行管辖权与司法管辖权是不同,执行制定规则的权力是执行管辖权,而司法管辖权是国内法院审理具有外国因素的案件的权力。[11]119英国学者马尔科姆·N·肖认为,管辖权可以通过立法、行政或司法行为得以实现,也将管辖权分为立法管辖权、行政管辖权、司法管辖权三类。司法管辖权又包括民事管辖权与刑事管辖权。[12]505,508,510,511中国学者粟烟涛也认为:“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国家管辖权……包括立法管辖权、裁判管辖权和执法管辖权。”[13]
除以上两个主要分类外,学者饶戈平从实施管辖的范围,将国家管辖权分为域内与域外管辖;从进行管辖的对象来分,分为对人与对物的管辖;从行使管辖时采用的程序性质来分,分为刑事程序管辖、民事程序管辖与行政程序管辖;从管辖适用法律的性质来分,分为公法与私法管辖;从国家管辖权的内容与形式分,分为属地管辖权、属人管辖权、保护性管辖权与普遍性管辖权。[14]
经分析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笔者认为,国家管辖权的不同分类虽然在形式上不尽相同,但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基本都是以国家权力为中轴而向不同的社会关系领域的辐射,大致可概括为立法管辖权与执行管辖权,其中执行管辖权包括行政行为与司法行为。但是较多的美国学者在此两种管辖之间增加了裁判管辖,原因是司法行为并不经常表现为执行行为,而是维护权益。至于民事管辖权,基本属于司法管辖的一个分支,而学者饶戈平按管辖的对象将管辖权分为对人与对物的管辖这一分类,将有助于拓宽我们研究海上管辖权类型之视野,并从中逐步认识何为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
(二)国家海上管辖权的学理类型
借鉴国家管辖权的理论分类,笔者尝试将国家海上管辖权作如下划分:(1)根据不同类型国家权力在海域管理中的延伸,分为海上立法管辖权、海上行政管辖权与海上司法管辖权;(2)基于广义执法包括司法(审判权)与狭义的执法(权)——行政之标准,分为海上立法管辖权与海上执法管辖权两类,海上执法管辖权是司法管辖与行政管辖的统称;(3)根据权力指向对象的自然属性不同,分为海上民事管辖权、海上刑事管辖权。第一种与第三种分类,对于界定海上民事管辖权的概念与内涵具有价值导向功能,笔者予以重点详述。
从人类海洋实践活动与涉海事务的社会管理角度审视,行使海上管辖权的基础是国家权力,因而微观意义上的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等均不同程度地运用其不同属性的国家权力分担着对海洋活动的管理。
国家海上立法管辖权,表明国家运用立法权从宪法、海洋基本法、各部门法(不同立法权主体/效力层级)、批准国际条约或公约等层面,对管辖海域本身及海洋实践活动等拥有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权能。这种国内立法是与《公约》或其他有关海上管辖权的公约之规定或理念相契合的,从多数国家的立法内容来看,基本属于将相关公约内容进行国内适用的转化。国家海上立法管辖权是行使其他执行管辖权的前提,因其与海上民事管辖权关涉甚少,我们不再赘述。但有两个有待研究的问题需明确,一是立法权对海洋实践活动管辖权的配置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是海洋基本法抑或是单行的部门法予以规定?二是某一海洋实践活动的管辖权配置于某一主体的考量因素?比如将海洋环境污染的管辖权授予海洋行政主体行使,为何?当然,这里不仅涉及到国家主权与立法权的关系,也涉及到微观层面的海上司法非裁判权与行政权的合理配置问题。
国家海上司法管辖权,主要指海上诉讼案件与非争讼事件的管辖。包括海上民事司法管辖权(包括海上民事诉讼裁判权和海上民事非讼事件裁判权,前者主要指海事诉讼裁判权)、海上刑事司法管辖权以及海上行政案件管辖权。其中,国家海上刑事管辖权是国家主权在惩罚海上犯罪领域的具体表现。此概念的界定比较清晰,并无学理上的分歧。海上行政案件管辖权是国家在维护海上行政相对人权益、监督行政权运行中的司法权配置。
国家海上行政管辖权,仅指基于海上行政(管理)法律关系而生成的,海上行政主体与其相对人形成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此种管辖权指向的对象是从事海上实践活动的“人的行为”,当然犯罪行为是除外的;其性质与陆域或海上行政程序中的管辖权等同,即行政管辖权是行政主体之间就某一行政事务的首次处置所作的权限划分。[15]其内涵也基本等同于目前学界对“海事行政法(学)”研究中各海上行政行为管辖的范畴。从这种管辖权的本质而言,国家海上行政管辖权主要解决的是海域中某一特定民商事活动由中国的哪一行政主体来主管的问题,实质上是一种国内的海上行政管理权,是陆域各种资源开发行业主管部门管理职能向海洋延伸时的职权划分,因而我们建议称其为海上行政管理权更为妥当。有学者认为,“我国海事行政管理机构在海上对外国民用船舶的管辖,即行政管辖权。”[16]笔者认为这种界定有商榷之处,这里所描述的应当是管辖的实施,即管理而非行政管辖。因为行政管辖是静态的,是对权力的分配,是管理的前提;具体的行政执法应当是一种动态的管理行为。此问题应当是目前学界与实践中关于“管理与管辖”混为一谈,彼此混用的结果,也因此造成海上民事管辖权与行政管辖权界限不清,海上民事管辖权被视为“异样概念”之结果。同时,笼统地将对海上船舶的管理均纳入行政管理的范围也是有失偏颇的①如《公安机关海上执法工作规定》第4条规定:“对发生在我国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违反公安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违法行为或者涉嫌犯罪的行为,由公安边防海警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行使管辖权。”该条表明“立法”将违反公安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违法行为或者涉嫌犯罪的行为的管辖权配置于公安边防海警行使。。
三、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的概念诠释
(一)从与海上行政管辖权辨析中认知海上民事管辖权
一般而言,海域活动、海域事务、涉海行为等的管辖,除涉嫌犯罪的行为可能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刑事案件管辖外,其余均属于民间涉海事务或活动等非刑事管辖②关于涉海事务,有研究表明,主要是一种国内外自然人、法人在国家管辖海域的上覆水域至底土范围内以获取自然资源或利用海水水体为目的的活动,本质上是海洋权益的实现。。[17]但非刑事管辖是否均属于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的范围则不无争议。即争议的焦点在于非刑事管辖中是否有海上民事管辖权与海上行政管辖权共存的客观事实?换言之,海上行政管辖权在海上民事管辖权概念及其理论提出之前,是确属客观存在的。如《公约》第94条第1款与第2款(b)、第219条③参见《公约》第94条第1款:“每个国家应对悬挂该国旗帜的船舶有效地行使行政、技术及社会事项上的管辖和控制。”第2款(b):“根据其国内法,就有关每艘悬挂该国旗帜的船舶的行政、技术和社会事项,对该船及其船长、高级船员和船员行使管辖权。”第219条:“在第七节限制下,各国如经请求或出于自己主动,已查明在港口或岸外设施的船只违反关于船只适航条件的可适用的国际规则和标准从而有损害海洋环境的威胁,应在实际可行范围内采取行政措施以阻止该船航行。这种国家可准许该船仅驶往最近的适当修船厂,并应于违反行为的原因消除后,准许该船立即继续航行。”,虽未明确使用“行政管辖权”之表述,但实为蕴含着此种管辖权。在海上民事管辖权理论生成之后,又如何厘清二者的界限呢?二者是并存?属于包含关系?抑或是其他的关系?笔者认为,在前述分类中,根据不同国家权力的分类中,并无民事管辖权这一类;而根据权力指向的对象分类中并无行政管辖权这一类。那么,处于两种不同分类标准中的民事管辖权与行政管辖权究竟是何种关系呢?其实,二者的关系还是比较明确的,我们认为属于各自独立且并存的格局。广义而言的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包括海上民事司法管辖权与非司法管辖权。前者属于国家权力分类的产物,后者即狭义的海上民事管辖权,是根据权力指向对象为标准分类的产物,其着眼于权力指向对象的主权归属问题,如以争议海域渔业资源所有权归属为例,海上民事管辖权主要解决渔业资源所有权归属于何国,此时的国家自然系属民事法律关系中的物权主体;而海上行政管辖权是以国家权力类型为标准分成的产物,它着眼于权力指向对象之主权归属(或所有权归属)无争议之后,按照什么标准或考虑何种因素来配置权限的问题。如前例中,争议海域渔业资源所有权归属中国后,由哪个海上行政主体进行渔业资源开发、利用等的管理权限分配属于行政管辖权解决的问题。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传统国际法理论将国家民事管辖权等同或视为民事案件的管辖,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具有时代的局限性,现代国际法包括海洋法理论应当对此有所突破。经以上分析,笔者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海上民事司法管辖权,主要是海事诉讼的管辖以及法院作为某一海洋实践活动的管辖主体的非裁判管辖的情形,这类管辖是国内法意义上微观管辖主体的权限分配问题,几乎不涉及国家主权问题;而海上民事非司法管辖权,通俗地讲,也可称为非法院主体的、国家主权语境中的海上民事管辖权,主要是指正当的主权国家参与海上民事法律关系,对以自然形态客观存在的海洋系统的管控,属于对“物”的管辖,这种管辖权称之为狭义的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具有国家主权的品格。
这里要着重区别国家海上行政管辖权。正如前文所述,某一海域的特定物或涉海事务在确属划归中国管辖之后,才涉及到国家海上行政管辖权的行使问题。因为“国家是互相独立的,并且享有领土主权,因此,(在没有得到东道国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国家官员一般不可以在外国领土上执行公务,也不可以在外国领土上执行他们国家的法律。”[12]509此时,这些涉海事务具体的管理操作虽然多数由中国的海洋行政主体客观行使,但此种管理权的行使几乎不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而重点在于各个海洋执法主体如何划分在海域的执法权限的问题。我们并不能将国家海上行政管辖权扩大到国家主权意义上理解,更不能因为某一海域的特定物或涉海事务是由海洋行政执法主体在具体执行,而将其笼统地、不加以具体分析直接认定为国家海上行政管辖权。国家海上行政管辖权基本可以用国内海上行政执法权配置或国内海上行政管理权配置注解,如海上行政处罚权、海上行政强制权等,它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国内行政执法(管理)事权。总之,各海域的海域活动、海域事务、涉海行为等管控问题或所有权之争在未明确确定归属于何国具体行使之前,不涉及国家海上行政管辖权的问题;而确定各海域的海域活动、海域事务、涉海行为等管控权力或所有权究竟归属于何国具体行使的过程,即为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力之归属定位,它是在国家主权之语境中生成与发展的产物。
(二)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的多维视角考究
关于“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的概念,笔者主要选取了三个不同的角度予以理解。
1.词源学考察
许多法律概念虽耳熟能详,但其内涵却鲜有人考究,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中“民事”便是如此,即何为“民事”?对此,目前学界鲜有人研究。“民事”一词似乎从其生成起便于法有着紧密的联系。从现有语言学工具书来看,《中华辞海》把“民事”一语作了这样的解释:“民”注解为人民、劳动大众的、非官方的;“事”注解为事情;[18]“民事”一词则注解为“有关民法的”,[19]《现代汉语词典》把“民”解释为人民、民间的、非军事的;[20]950“事”解释为事情、关系或责任;[20]1246“民事”注解为有关民法的。[20]951与“民事”组合的新词一般为“民事案件”、“民事法庭”、“民事权利”、“民事诉讼”、“民事责任”、“民事行为”等。[20]951
从中国古籍中记载使用的“民事”一词略作考察,《周礼》一书尤为值得研究。《周礼》多处使用了“民事”这个语词,内涵极其丰富。如《周礼·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一日听政役以比居,二曰听师田以简稽,三日听闾里以版图,四日听称责以傅别,五日听禄位以礼命,六曰听取予以书契,七日听买卖以质剂,八日听出入以要会。”按照《周礼》之注解,此八项事务均为“民事”。涵盖了案件管辖问题、实体权利问题,包括军、政、赋、役、财物出入、借贷、买卖众多方面。于此,中国古代“民事”一词,即已遍布了行政法、财政法、经济法、民法等法律领域,几乎涉及到了市民社会、民商事关系的方方面面。[21]
从“民事”与刑事、行政的交叉关系来看,可以说非刑事即属民事的范畴,“民事”旨在强调一个对象范畴,“民事”与“管辖权力”二者是相互结合来表达各自的内涵,因为并不存在一个“民事权力”;而“行政”旨在强调执行民事事务的主体及其权力,行政的执行指向实质也是民间事务的范畴,民事管辖权力的实现依赖于行政权的执行;从法律责任的角度而言,海上民事管辖权中一般仅有民事赔偿等责任的承担,而海上行政管辖权除代表国家实现民事赔偿请求权外,还需课予行为人以行政法律责任;至于海上刑事与行政管辖权的分野,二者的行使在于划分海上行为人之行为违法与犯罪的执行权限。总之,海上民事管辖权的实施需要确定行政管辖权后才可行使具体的执行权能。基本可以将海上管辖中的“民事管辖”范围界定为涉海的民间事务,即非政治、非官方、非军事的事务。
2.管辖权主体考察
根据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权力主体的归属和实际有效行使,可以把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权力主体分为归属主体和行使主体两类。其中,归属主体或称宏观主体即是海上民事管辖权力归谁所有,何种主体是权力的所有者。在现代国家管辖权理论中,国家属于当然的管辖权权力主体,而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的抽象主体也应是国家。国家基于统治与有效的社会管理之需要,理应拥有各种类型的财产,当然对海域的“物”享有物权。因而,对于各海域的海域活动、海域事务、涉海行为等而言,国家属于特殊的物权主体。
从微观层面而言,海上民事管辖权的实际行使主体相对于归属主体而言处于意志的执行主体,是归属主体实现其海域治理宗旨的手段之一。从海洋活动的实践考察,主权意义上的海上民事管辖权必须依附于公共权力机关。就中国而言,海上民事管辖权的行使主体主要包括海上行政主体、法院等组织,其中海上行政主体是最重要的权力行使主体。于此,便存在海上民事管辖权执行主体与行政管辖权主体的重合,因为后者是前者抽象主体意志的实际执行者,主体的一致并不影响二者各自的功能定位,因而并不矛盾。另外,有待研究的问题是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能否成为中国海上民事管辖权的微观主体?
3.管辖权对象考察
国家海上管辖权理论实质上配置着微观意义上管辖权主体的具体管辖权能。如前所述,国家海上管辖权的宏观对象包括海上活动中人的行为、事件、案件、物等。然而,海上民事管辖权只分担着对部分对象的管辖权能,依据上述各类海上管辖权的内涵及其功能范围,笔者认为,海上民事管辖权的对象包括但非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作为自然物客观存在的海洋本身。海洋作为一种客观现实存在,本身即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域自然生态系统对人类生存发展的有用性或者海洋能满足人类需要的多元属性——海洋价值,催生了国家及其人民对海洋本身进行管辖的主权意识。诚如有学者指出,“中国对于南沙群岛的管辖意味着主要是对渔业、海洋资源等相关事务的管辖。”[22]从海域生态系统的静态属性而言,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主体主要对中国管辖海域内的如下对象之所有权、用益物权的享有和行使具有民事管辖权能:一是海洋物质资源。诸如海水资源、矿产资源(如油气资源、固体矿物资源等)等非生物物质资源;由海洋藻类资源、海洋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资源组成的海洋生物物质资源(如渔业资源等)。二是海洋能量资源。此类资源基本属于非物质性产品,对人类的价值在于其服务功能。鉴于当前科技与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性,海洋能量资源主要包括海洋波浪能、海水温差能、海水盐度能、海洋潮汐能等。三是海洋空间资源。主要包括用于工业、农业、旅游等的海岸与海岛空间资源;用于海运、可建设海上人工岛、海上工业等的海面空间资源;用于海底隧道、海底通信电缆等的海底空间资源、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和海洋特别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等。
国家基于主权而对海洋本身行使的民事管辖权能与国家作为特殊的民事主体对海洋本身享有的所有权具有一定的共性,包括权利主体、具体内容、权利的流变等方面。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主权、管辖权与所有权均带有支配性,主权特别是领土主权以及领土主权延伸而来的自然资源主权,都有排他支配的一面。这也印证了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的主权品性。但国家所有权与海上民事管辖权也存在差别,管辖权虽宣示着主权,但更强调管理、控制;所有权则强调归属问题,其实现依赖于管辖权的有效行使。
第二是海上活动中人的行为。海洋价值的发挥和体现最终还依赖于人的行为。海洋实践活动中,人的行为主要体现在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层面。海洋活动中行为人的行为均具有其主观目的性,目的的不同决定了行为的多元化。除涉嫌一般违法、涉嫌犯罪依法由海上管辖权主体分别行使行政管辖权、刑事管辖权外,行为人在中国管辖海域对海洋本身及其附属物等所实施的诸如开发、利用、保护、科研等(如海洋油气勘探开发、海砂开采、海上风电工程、海洋盐业、电力业、船舶工业等)积极行为以及诸如对海洋水体及资源造成污染、对自主或他主船舶等洋面财物造成损害等消极行为均属于海上民事管辖权主体行使管辖权能的范畴。当然,行为人的行为有些属于可能对沿海国权益造成影响的行为,还有些行为虽不关涉沿海国的权益,属于行为人间意思表示的行为,但也属民事管辖权的范畴。此外,行为人之间在涉海事务中的民事行为,依属地或船旗国管辖原则当属民事管辖权之范畴。
第三是涉海事件与案件。涉海事件一般是不依行为人意志所产生的客观事实,如海上环境污染等;而涉海案件一般是可能启动诉讼程序或其他违法追诉程序予以处理的事件,如船舶碰撞案件等。这类非刑事事件或案件的处理也应强调国家主权原则,同时也应遵循属人管辖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实际控制管辖原则等行使管辖权。
(References):
[1]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6:1.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China ocean agenda in the 21st century[M].Beijing:China Ocean Press,1996:1.(in Chinese)
[2]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M].高湘泽,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26. ALBROW M.The global times:transcending modernity beyond the state and society[M].translated by GAO Xiang-ze,et al.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2001:126.(in Chinese)
[3]郑玉波.法彦(一)[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6. ZHENG Yu-bo.Legal maxims(I)[M].Beijing:Law Press,2007:16.(in Chinese)
[4]江河.人类主权的萌芽:现代国际法的启示与回应[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JIANG He.The buds of human sovereignty:the modern enlightenment and respond to international law[M].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2011.(in Chinese)
[5]张乃根.国际法原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ZHANG Nai-gen.The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M].Shanghai:Fudan University Press,2012.(in Chinese)
[6]奥本海.奥本海国际法[M].王铁崖,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327. OPPENHEIM.Oppenheim international law[M].translated by WANG Tie-ya,et al.Beijing: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1995:327.(in Chinese)
[7]王利明.论国家作为民事主体[J].法学研究,1991(1):59-66. WANG Li-ming.Country as a civil subject[J].Legal Research,1991(1):59-66.(in Chinese)
[8]宋云霞.国家海上管辖权理论与实践[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4. SONG Yun-xia.National maritime jurisdiction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M].Beijing:China Ocean Press,2009:4.(in Chinese)
[9]路易斯·亨金.国际法:政治与价值[M].张乃根,等,译.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HENKIN L.International law:political and value[M].translated by ZHANG Nai-gen,et al.Changchun: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05.(in Chinese)
[10]松井芳郎.国际法[M].辛崇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86. YOSHIRO M.International law[M].translated by XIN Chong-yang.Beijing: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2004:86.(in Chinese)
[11]希利尔.国际公法原理[M].曲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HILLYER.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principle[M].translated by QU Bo.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06.(in Chinese)
[12]马尔科姆·N·肖.国际法(下)[M].白桂梅,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SHAW M N.International law(Vol. II)[M].translated by BAI Gui-mei,et al.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1.(in Chinese)
[13]粟烟涛.冲突法上的法律规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4. SU Yan-tao.Evasion of law on the conflict of laws[M].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8:24.(in Chinese)
[14]饶戈平.国际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3. RAO Ge-ping.International law[M].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1999:103.(in Chinese)
[15]章剑生.行政管辖制度探索[J].法学,2002(7):28-32. ZHANG Jian-sheng.Explo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jurisdiction system[J].Law,2002(7):28-32.(in Chinese)
[16]李倩,邹立刚.中国海事对外国船舶的海上行政管辖权[J].新东方,2013(3):59-62. LI Qian,ZOU Li-gang.Maritime administrative jurisdiction over foreign vessels in China[J].New Oriental,2013(3):59-62.(in Chinese)
[17]安应民.南海安全战略与强化海洋行政管理[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129. AN Ying-min.The South China Sea security strategy and strengthen the marine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M].Beijing: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2012:129.(in Chinese)
[18]冷玉龙.中华辞海[M].北京:中华书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26. LENG Yu-long.The Chinese lexicon[M].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China Friendship Publishing Company,1994:26.(in Chinese)
[19]现代汉语大词典编委会.现代汉语大词典[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2420.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Editorial Board.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M].Shanghai:Century Publishing Group,Chinese Dictionary Publishing House,2000:2420.(in Chinese)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Language Dictionary Newsroom.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M].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2005.(in Chinese)
[21]李志敏.中国古代民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2. LI Zhi-min.Civil law in ancient China[M].Beijing:Law Press,1988:2.(in Chinese)
[22]李智,李天生.有效管辖视角下中国南海海权的维护[J].中国海商法研究,2013(4):82-86. LI Zhi,LI Tian-sheng.The safeguard of China’s righ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in the perspective of effective administration[J].Chinese Journal of Maritime Law,2013(4):82-86.(in Chinese)
National maritime civil jurisdiction:the concept and its expansion
AN Chen-xi1,2,WANG Qi2
(1.Hainan Province Law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outh China Sea,Haikou 570228,China;
2.School of Law,Hainan University,Haikou 570228,China)
Where there is a sovereign state, there must exist its jurisdiction. International maritime affairs are undergoing complex and profound changes, controversies and conflicts are increasing in number in the process of exercising jurisdiction at sea by the sovereign states. Agaist the background of safeguarding marine rights and interests by P.R.China, the issue of national maritime civil jurisdiction has emerged. National maritime civil jurisdiction is a special kind of jurisdiction operating in the leve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 the sense of sovereignty, characterized by the unique character of safeguarding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maritim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ocean. National maritime civil jurisdiction takes the state as a special civil subject, it is classified by the subject the power points to, and focused on the question of sovereignty of the subject the power points to,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control by the sovereign state over the marine system in its natural objective existence state, the power of control over the maritime activities in the sea within its jurisdiction, sea-related affairs and conducts, and i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declaration of national marine sovereignty.
national jurisdiction;national maritime jurisdiction;national maritime civil jurisdiction;maritime rights and interests
2015-07-10
司法部2013年度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一般项目“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研究”(13SFB2026)
安晨曦(1982-),男,河北张家口人,海南省南海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海南大学法学院民事诉讼法专业博士研究生,E-mail:anchenxi2010@sohu.com;王琦(1967-),男,海南澄迈人,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wangqi9199@163.com。
DF961.9
A
2096-028X(2015)03-0073-10
安晨曦,王琦.国家海上民事管辖权:概念及其展开[J].中国海商法研究,2015,26(3):73-82
——民事二审不开庭审理的失范与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