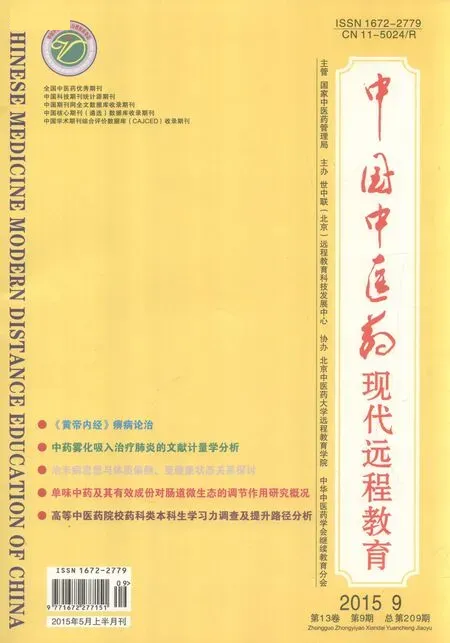耶稣会士与新教传教士对中医之评介与影响※
郭强
(广州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中医文献教研室,广州510006)
耶稣会士与新教传教士对中医之评介与影响※
郭强
(广州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中医文献教研室,广州510006)
17、18世纪耶稣会士来华时期,中西医发展水平大致相当,耶稣会士以文化交流的心态来审视中医,他们所翻译的西医书籍主要以性学的面貌出现,在中国影响有限。而19世纪新教传教士来华时期,西方医学已经完成了向现代医学的转变,他们以现代医学的标尺来衡量中医的科学性,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甚至提出在中国建立西方医学体系。他们在中国传播西方医学,对中医造成了巨大冲击,推动了近代中国医学的发展,促就了近代中西医汇通思想的形成。
中医文化;耶稣会士;新教传教士
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文化交流上一直都是相互的,不仅有西学东渐,也有东学西渐。在这个双向过程中,无论是明代来华传教之耶稣会士,还是近代之新教传教士,在推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哲学与科学于一体,是西方教士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然而由于耶稣会士和新教传教士来华之社会背景、自身知识体系和传教方式等的不同,他们对于中医的评价态度亦有所差异,其对中国本土医学产生的影响亦不同,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作初步探讨。
1 耶稣会士的中医观及明清之际西医在华传播
16世纪以降,欧洲的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为了能站稳脚跟,他们积极地结交中国上层阶级精英,学习中国文化。其中中国医学所展示的技术和魅力给耶稣会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他们潜心观察和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尤其是脉诊、针灸、人痘术三个方面。明万历年间来华的传教士曾德昭曾赞叹:“(中医)摸脉后马上开方子,治病常常十分成功”[1]。清代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李明认为:“中国人获得了有关脉搏方面的特殊知识,这使他们闻名世界”。[2]巴多明观察了中国太医院的针灸铜人模型,通过铜人身上经脉循行路线与欧洲所知的血液循环路线的对比,指出:“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已经认识了血液循环,但不知道运行机制”[3]。另一位耶稣会士殷弘绪则对中国的人痘术大加赞赏,他说:“这种(在中国)施行了一百年的方法直到17世纪才在君士坦丁堡流行起来,应该承认它的历史悠久”。接着便开始“毫无遗漏地收集这方面的知识”,想尽办法从中国宫廷医生那里获取了3个人痘接种的方法[4]。
应该说耶稣会士对中国医学大都是持肯定态度的,而且不吝赞美之词,但也有个别18世纪中后期来华的耶稣会士,在将中国医学与欧洲医学比较及亲身实践之后,对其理论性、科学性和效用性有所怀疑。如韩国英曾经阅读过《医宗金鉴》里的“痘疹心法要诀”,认为“中国的接种方法并不有效”,因为他亲身经历了北京1767年的天花流行,目睹了“几个月内有十万个小孩丧命”,他认为中医缺乏解剖基础,难以理解,且认为中医“在占星术、迷信和偶像崇拜的控制之下,非常愚蠢”[3]116-117。
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也将一些当时的西医著作译介到中国,不过并非为了医学争鸣,而是为了填补中国的格物理学,因此数量不多,仅有明末邓玉涵的《人身说概》,罗雅谷等编写的《人身图说》,白晋、张诚、巴多明翻译的《钦定格体全录》,以及石铎录的《本草补》等几部专著。而且这些著作多是“以性学的面貌传入中国,其具体的内容以解剖生理学为主,也包括西医理论、疾病观念等”,目的是用它来解释形、神与天主之间的关系,因而涉及的理论和概念都相对简单。“由于当时的中国人是以格物的角度来审视这些书籍的,因此传教士和中国士人均未将这些知识与治疗疾病联系在一起”[5]。还应注意的是,这些著作在当时的刻印数量非常少,流传范围相当有限,像《人身图说》从未正式出版过,仅存抄本数种,而《钦定格体全录》则因康熙皇帝以“此乃特异之书,故不可与普通文籍等量观之,亦不可任一般不学无术之辈滥读此书”[6]为由未加推广。不过性学书籍却种类繁多,对中国医学精英产生了一定影响,比如清代王宏翰的《医学原始》就受到了《性学觕述》、《空际格致》、《主治群征》、《形神实义》等性学著作的影响,有研究者认为其是“中国最早尝试汇通中西医的医学家”[7]。可以说,耶稣会士对中医的认识与其传播西医知识并无多大关联,也没有激发其通过西方医学来提高中国医学技术水平或是替代中医的想法。
2 新教传教士的中医观及近代西医在华传播
1807年,英国伦敦会派遣马礼逊来华,开启了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时代。马礼逊是第一位研究中国医学的新教传教士,为此他“购买了800多卷中医书籍”,并于1820年与东印度公司的医生李文斯顿在澳门开办一间诊所,还专门聘请了一位李姓中医和一位药剂员相助应诊并为他们讲解中医药知识[8]。之后李文斯顿在《印中搜闻》季刊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中国医史、医理、治疗原则、脉学、疾病治疗、中草药等内容的文章。但是他们对于中医基本上还处于初步认识阶段,马礼逊[9]自认为“还没能够掌握这些书中的内容,以达到精通或者精益求精的程度。”李文斯顿[10]的想法则是看看“中国的药物和疗法是否可以对现今西方所掌握的、能减轻人类痛苦的手段再做点补充”。
1830年代后,来华的传教士对中国医学的态度有所转变,他们开始以西方现代医学的尺度来量度中医的理论和实践。1831年来到澳门的郭实腊曾三次游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凭借略懂医术在民众中行医传教,他认为:“相对于更高级更普及的欧洲医学知识而言,中国医学的实践知识是非常贫乏的,且不能满足人们控制疾病的需求,他们似乎一点都不懂血液循环的内容,从来都不知道化学,在他们的语言里找不到一个与之相关的词汇,他们反对用任何外科手术,这使他们在外科疾病治疗中受到约束,总是使用并不有效的内科疗法”[11]。1835年来华的首位医学传教士伯驾则认为:“虽然中国可能很早就有了外科知识,但现在他却不值得拥有这个称号,……以中国目前这样的医疗水平,人们更易于赞赏和欢迎欧洲先进的医学”[12]。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随着不平等条约制度的实行,在华的新教传教士在描述中国医学的状况时,毫不掩饰西医的先进性和自身的优越感,开始以殖民者心态来看待中医。比如1839年来华的英国伦敦会医学传教士合信,就极端地批评中国医学缺乏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他认为:“(中国医学)没有动静脉之分,不知道心脏的正确功能,也不知道血液在肺脏和毛细血管中流动的变化;不知道神经系统和它的功能以及相关疾病的治疗;不知道内脏的正确位置、功能和作用。反而把一切甚至是神秘莫测的东西都用阴阳来解释,几乎每个症状都是个病,一个处方对应一个想象中的症状,这说明他们对疾病的本质和原因知之甚少”[13]。
合信是近代来华医学传教士的先驱之一,且对中国医学有深入的研究,他曾在欧洲的《Medical Times and Gazette》杂志上连续发表了5篇关于中国医学历史和现状的论文,因而他对中医的看法被之后来华的医学传教士广泛认同。比如1860年到上海接替合信管理仁济医院的伦敦会医学传教士韩雅各就非常认同合信的观点,他甚至指出:“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医学都比现在19世纪的中国医学更加闻名更加具有实践性,原因是中国医学的从业者从来没有像希波克拉底及其西方的追随者那样去追求真理。”[14]广州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也是合信的拥护者,他在1877年上海传教士大会批评中国医学“完全不知道解剖学和生理学,而且还用荒谬的理论来替代真正的知识”[15]。
对传教医师而言,其最终任务是传教,行医只是他们传播基督福音的手段之一,合信认为中国人只有理解了现代医学及其他西方科学的真谛,掌握了科学的思维方法,才能理解并接受基督,因此在中国建立西方现代的医学体系显得与传播基督教同样重要[16]。基于这样的想法,他在中国首次出版了一批现代西医书籍——《全体新论》、《博物新编》、《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和《妇婴新说》,这些书籍对中国医学精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开始重新审视以往对于脏腑解剖及生理方面的认识,并尝试利用西医的知识来解释中医的理论。比如罗定昌、唐宗海、朱沛文就曾运用解剖观察、实证等方法解读经络的客观形态,尝试用动静脉血管解释经络形质[17]。正是由于西方医学对中国医学造成的巨大冲击,推动了近代中国医学的发展,促就了近代中西医汇通思想的形成。
3 耶稣会士和新教传教士对中医认识差异之原因分析
由上可知,耶稣会士与新教传教士对中医的态度以及传播西医的目的是截然不同的,因而对中国医学产生影响的程度亦不同。原因在于二者的知识体系不同,他们所处的社会背景、传教方式等也存在差异。
首先,二者的知识体系不同。17~18世纪是欧洲医学由传统向现代发展的时期,尽管当时已出现了解剖学、血液循环、化学方面的知识和理论(如1543年维萨里出版了《人体的构造》,1628年哈维发现了人体血液循环运动的规律),但是这段时期西方医学仍然是以希波克拉底的四行四液学说为基础,它与中国医学的五行学说有非常相似的哲学基础,利玛窦就认为“中国的全部医术都包含在我们自己使用的草药所遵循的规则里面”[18],因此他们并不认为中国医学比欧洲医学先进或落后,而是处在大致相等的水平上,他们只是对中国的脉诊、针灸、人痘术等先进技术感兴趣并积极向欧洲介绍,而对中医学的其他理论的反应则比较平淡。1830年代以后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他们已知晓或熟悉现代医学知识,尤其是以解剖和生理学为基础的外科,在他们眼里,中国医学如同已被欧洲所摒弃的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医学,当中充斥着荒谬和错误甚至是迷信,极不具专业性和科学性,因此他们便言辞激烈地提出了批评,甚至产生了取代中医的想法。
其次,二者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尽管二者来华的目的都是为了传教,但新教传教士能够大批来华居留和传教得益于中国与西方列强所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因此他们往往以优胜者或殖民者的心态来看待中国医学乃至中国文化。而耶稣会士则不同,他们并没有条约制度保障,因而从一开始便积极结交中国上层阶级以站稳脚跟,在评价中国文化及中医时,也往往抱着文化交流和学习的心态来审视。
第三,二者的传教方式不同。由上文可知,批评中医的大多是新教传教医师,他们在华传教的方式主要是借医传教,医学是其传教的工具,因此他们总是刻意地拿西医和中医作比较,试图以西医的先进性,加上基督普世仁爱的人性关怀和语言暗示,以使民众皈依基督。其另一个目的是“通过否定中医的价值,来证明传教士在中国行医的合理性,求得教会内部的支持。”[19]而耶稣会士时期,西方医学与中医理论体系差异不大,而且自康熙禁教之后他们便不采用借医传教这种手段,主要是通过传播西方性学(内含医学)来与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即用天主神学加医学知识来契合中国传统的儒医结合的文化,以使中国民众尤其是上层精英从文化层面上更容易接受天主教。
[1]曾德昭.大中国志[M].何高济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69.
[2]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M].郭强,龙云,李伟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195.
[3]韩琦.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121.
[4]杜赫德.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212.
[5]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13.
[6]白晋.康熙皇帝[M].赵晨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40.
[7]董少新.从艾儒略《性学觕述》看明末清初西医入华与影响模式[J].自然科学史研究,2007,26(1):64-76.
[8]马礼逊夫人.马礼逊回忆录[M].顾长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58-160.
[9]John Livingstone.The History of Medicine in China[J].Indo-Chinese Gleaner,1820,(14):424.
[10]王吉民,伍连德.中国医史[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307.
[11]The editor.College of Physicians[J].London Medical Gazette.1838:776.
[12]No author.Meeting in Behalf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Held in Exeter Hall Building[M].London,1841:10-11.
[13]William Lockhart.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a Narrative Twenty Years’Experience in China[M].London:Hust and Blakett Publishers,1861:155.
[14]James Henderson.The Medicine and Medical Practice of the Chinese[J].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1864,(1):23.
[15]Matthew Tyson Yates.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Held at Shanghai,1877[M].Shanghai: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78:116-118.
[16]Benjamin Hobson.An Appeal to the Religious and Benevolent Public on Behalf of a Proposal to Establish a Medical School for the Natives of China,in Connection with the Chinese Medical Mission at Hongkong[M].Welford,1846:3.
[17]李素云.明清西医东渐背景下经络理论的解读[J].中国针灸,2010,06:517-519.
[18]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34.
[19]陶飞亚.传教士中医观的变迁[J].历史研究,2010:68.
The Jesuits and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Comments on TCM and Their Influence
GUO Qi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Medical Literature,Basic Medicine College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Guangzhou510006,China)
In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y when the jesuits came to China,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and Western medicine were roughly at the same level.The Jesuits looked at the TCM in culture exchanges,the Western medical books they translated occurring mainly in the sexology outlook had limited impact on Chinese.During the period of nineteenth century when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came to China,the Western medicine had completed the transition to modern medicine,they tooked the ruler of modern medical science to measure the TCM,and severely criticized it,even proposed to establish the Western medical system in China.They spreaded the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caused a huge impact on the TCM,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in modern China,and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idea of the integrated medicin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Jesuit;Protestant Missionaries
10.3969/j.issn.1672-2779.2015.09.002
1672-2779(2015)-09-0003-03
:杨杰本文校对:李计筹
2015-04-13)
广东省中医药局科研项目(No:2012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