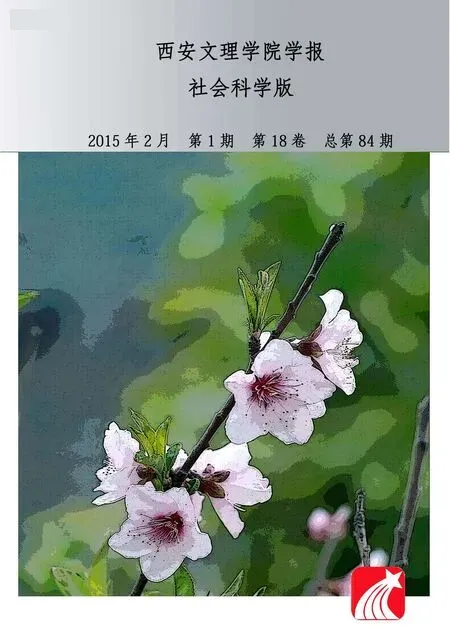第十二种孤独——从《复活节游行》解读理查德·耶茨“孤独的女性”主题
【文学艺术研究】
第十二种孤独——从《复活节游行》解读理查德·耶茨“孤独的女性”主题
张晗
(兰州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兰州730050)
摘要:发表于1976年的《复活节游行》是美国现代作家理查德·耶茨的“女性小说”。在作品中,耶茨从一个男性作家的视角,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上世纪70年代美国都市普通家庭两姐妹,用犀利但满含怜悯的笔触展示了以主人公艾米莉一家为代表的孤独的女性群体,是作家在其短篇小说集《十一种孤独》之后所描述的“第十二种孤独”——女性孤独。从孤独的女性主题着手,以《复活节游行》的分析为突破口,结合存在主义探讨作家对女性孤独的理解,并试图找到破解现代人孤独的钥匙。
关键词:《复活节游行》;理查德·耶茨;女性; 孤独;存在主义
收稿日期:2014-11-08
作者简介:张晗(1980—),女,陕西汉中人,兰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712.47
文章编号:1008-777X(2015)01-0047-05
理查德·耶茨(1926—1992)曾经被英国《泰晤士报》称为“美国文学史上被遗忘的最优秀的美国作家”。[1]他的叙述手法独特,关注现代人的焦虑,在艺术思想上水平很高。耶茨对普通人的关怀中,尤其对女性倾注了特别的笔触。正如耶茨的知音库尔特· 冯古内特称:“福楼拜以来,鲜少有人对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妇女表达出那么深切的同情”。[1]3冯内古特的评价是相当精准的,作为“焦虑时代(the Age of Anxiety)”的代言人,无论他得到国家图书奖提名的《革命之路》,还是被誉为“纽约的《都柏林人》”的短篇小说集《十一种孤独》,无不透露出耶茨写作的两大主题——孤独和女性。
美国小说家斯图尔特·奥南(Stewart O’Nan, 1961— )曾在《波士顿评论》上发表文章为耶茨长期遭受读者及出版界的忽视而鸣不平,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也在他的小长篇《女人男人在一起》(Women With Men)中的谢辞部分中惋惜地承认:明白这位作家价值的人太少了。[1]3国内对耶茨的研究较多地关注了他的处女作《革命之路》,由李奥纳多和温斯莱特主演的同名电影让国人认识到了耶茨这位对孤独和女性主题探讨的美国作家,而对于他的其他作品则研究得很少。《复活节游行》是理查德·耶茨的代表作,也可以称之为作家的“女性小说”,出版当年即在美国获得如潮好评。本文通过《复活节游行》这部小说的分析,展示了艾米丽一家在男权社会中被置于“他者”地位所经历的生活的压抑与困顿以及女主角艾米丽追寻理想之爱的心路历程,进而探究耶茨本人对孤独和女性问题的理解。作者并不仅仅是写一部关于女性的作品,更是想从广泛意义上观照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因此可以说《复活节游行》并不仅仅是一部揭示女性生存状态和精神困惑的小说,而是作者倾注了全身心的同情在孤独中寻找自我的写照,某种程度上说,艾米莉的孤独作者感同身受,是作者对存在及生存意义的一次探索。
一、女性:孤独的存在
叔本华说,人生来就是孤独的,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一个孤独的存在。孤独作为一种情绪体验,一方面是个体无法与外部世界沟通而产生的疏离,另一方面也是个体探寻自我存在意义的过程。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孤”是古代帝王对自己的称呼,是王者;“独”是与众不同,孤独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可能与物质的满足无关,但又与物质紧密相连;孤独特别指精神上的空虚寂寞,思想上的独一无二。《复活节游行》所描写的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社会,正处在一个交通和科技迅猛发展的年代,按理说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比过去更加广泛和紧密,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在现代化理性进程中,在现代社会对利润的追逐中,作为个体的人很容易利用别人,利用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人本身真正生存的意义变得支离破碎,虽然每一个人都想紧紧地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但是内心很容易产生不安全感,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不可避免。黑格尔认为,孤独和异化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状态;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也指出:我们被抛到一个充满偶然性的世界,世界的冷漠使每个人都充满了异化。[2]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生活对于普通人来讲,物质上尚且可以满足,可是精神对于女性来讲,经过一波又一波女权主义运动的洗礼,大部分女性的女性意识已然觉醒并不断加强,她们对独立自由的渴望愈加强烈,特别是1976年波伏娃《第二性》的出版,让整个社会重新审视女性所处的位置。源于内心深处的焦虑彷徨和源于社会的疏离隔膜难免让女性更容易感受到孤独。难能可贵的是,作为社会两极中的另一极,作为一个男性作家,理查德·耶茨敏锐地感受到了女性的孤独,意识到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他通过自己的笔端表现在了《复活节游行》中。艾米莉一家的三位女性就是这样孤独存在:艾米莉的母亲和父亲离婚,母亲和两姐妹生活在一起。母亲和两姐妹、父亲和两姐妹、两姐妹之间都有着无法逾越的疏离感,他们总是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造成艾米莉一家三位女性孤独的因素中,无法沟通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两姐妹的母亲艾斯特格兰姆斯,或者被人称为普奇,爱面子讲派头,离婚以后她需要独自抚养孩子,每到一个地方生活不了几天就因为种种原因搬家,每搬一次家就让姐妹俩失去刚刚认识的朋友,再次陷入孤独。普奇与丈夫无法沟通,唯一一次让姐妹俩感到温馨的父母的谈话仅发生在他们离婚以后。普奇与女儿们没有办法沟通,她的虚荣总是让两姐妹伤痕累累。两个姐妹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性格敏感且缺乏安全感,自孩提时代起就与常人截然不同,长大后更是选择了不同的道路。理智的姐姐萨拉总是高高在上,她有着顺从和乐观一点的性格,长相较好,好像人生更多一些亮色。按常理来论,萨拉有三个儿子,有丈夫的陪伴,生活应该不孤独。可实际上,为了维持表面上的美满婚姻,萨拉把自己隔绝在一个美好的童话中,甚至与妹妹写信也要故意用那种少女般快乐的字体,以掩饰自己长期酗酒、忍受丈夫家庭暴力的事实。
小说的主人公妹妹艾米莉没有令人注目的身材和长相,从小就缺少父母亲的关爱,她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和姐姐不同的道路,那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追求自我独立。她获得了全额奖学金,上了大学,成为父亲唯一的骄傲。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后,她从事过记者、文案工作。结过一次婚,两年后离婚,先后与多个男友同居,可是,所有的生活都无法满足她孤独的灵魂,总是感觉游离在生活以外。最后为了一点尊严而辞去文案工作,后半生的生活孤苦伶仃,潦倒失意。虽然两姐妹之间一直有联系,可是她们之间的距离却是越来越远。两姐妹与母亲普奇的关系也很疏离,甚至在母亲住进养老院之后都很少去看望她。
艾米莉的孤独正是她女性意识觉醒的体现。她不想像姐姐一样依附男人,决意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人。与姐姐萨拉及母亲普奇相比,作为知识女性,艾米莉的身上有着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那个年代的女性女权意识不断增强的显著特征,她试探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姐姐和母亲的老路,可是结果却很惨淡。经济上的拮据也许不是她生活中最大的挑战,感情上,身边也不乏爱慕者,精神世界的孤独空虚才是她最难以忍受的。在这里,耶茨充分表达了他的存在主义观点,他用大量的笔触描写了艾米莉非理性没有逻辑的情绪体验,总是感觉昏昏噩噩,生活没有目标,生存没有价值。她时常觉得工作索然无味,内心没有着落,与母亲和姐姐也说不上话。孤独感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对生活一种理性的思考和坚守。她也曾与这种孤独斗争,从一个男人换到另外一个男人,从一个工作换到另外一个工作,可内心的孤独和寂寞还是让她的生活越过越糟。
艾米莉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周围男人们对待她的态度之间的分裂造成了孤独的另外一个要素。艾米丽身边的男人们对她的态度模棱两可,与其说是艾米丽与几个男人的爱情,不如看成觉醒的女人与男人的遭遇。因为这些男性们从来没有把艾米莉看成独立自由的人,没有打心底里关心过她,为她着想和考虑过;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欲望,偶有疼惜,但看不到真心。说穿了,这些男人从没有试图理解过艾米莉的处境和心态,只是把她当做一个杯子或一部汽车一样的物品来对待。在理查德·耶茨的笔下,男性们基本都麻木不仁,没有灵魂,即使有灵魂,也不过是为满足自己欲望的一个想法,男性只是艾米莉生命中的外来客。
HE Jing-wen, WEI Yan-yan, SU Tong, PAN Xiao, CUI Yi, LI Zi-qiang, TANG Yun-xiang
二、探寻:生命存在的意义
由于受到现代哲学和存在主义的影响,耶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视角讲述着对女性、对孤独的理解。他的行文简朴直白,他笔下都是芸芸众生普通平凡的生活,写得是普通人的孤独,失落与绝望,真正是“孤独的人写孤独的书”。[3]261-262耶茨自己的经历及周围女性的经历与《复活节游行》中描写的情形非常相似。耶茨本身父母离异,自己又和妻子分开,两个女儿的抚养权未能归他。孤独的生命体验使耶茨一直对命运感到茫然,对现实生存感到无奈。因此,耶茨在自己的作品中总是选择普通人的孤独作为主题。耶茨的原话有助于对这一点的理解:“如果说我的作品有一个主题,我怀疑这个主题并不复杂,那就是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一种无法逃脱的孤独中,他们的悲剧也在于此。”[3]261-262
耶茨通过对主人公艾米莉孤独苦闷内心世界的刻画,表现出对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疏离的精神世界的重新思考,探寻生命存在的意义。存在主义认为,人的存在总牵涉到意义,个体在不断为建构理想自我而努力。耶茨在《复活节游行》中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向我们展示了美国中下层阶级普通人生活的不如意,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人物内心的孤独,同时他也选择艾米莉为突破口,探寻生命存在的意义。作为人类存在的基本处境之一,孤独具有丰富、复杂的特定内涵。一方面,它是人类在隔绝或陌生环境下油然而生的一种感性情绪的宣泄;另一方面,它更是一种理性认知的人生姿态,暗含着一种自我选择。存在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自由选择”,想要改变生活就要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当主人公爱米莉长大到她能够审视这个家庭所遭受的挫折并从中吸取教训以后,她终于从母亲反像中看到了勇敢和坚强,从姐姐的反像中她看到了理性和独立,爱米莉决意走上了一条勇敢、坚强、理性和独立的道路。她勇敢地坚守自己的这个理念,凭借努力拿到奖学金,成为这个家庭唯一一个真正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正如波伏娃所说的那样:“一个女人要选择,实现她所愿干的事情,并取得成功。”[4]21耶茨小说中,女性形象的自由选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力图摆脱现代社会疏离冷酷的现实和逃避精神空虚的一次有益尝试。
三、彼岸:难以超越的生存困惑
耶茨在小说中的第一句话就为全篇定下孤独的旋律:“格兰姆斯家的两姐妹都不会过上幸福生活,回过头看,总是让人觉得问题始自她们父母的离婚,那是一九三零年,当时萨拉九岁,艾米莉五岁。”[5]父爱的缺失使艾米丽敏感、害怕孤独、渴慕抚爱,总是把爱情摆在第一位,一旦生活中没有爱情就会觉得窒息。艾米丽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丈夫是有点变态的中年男人。生活的艰辛让她不得不坚强富有理性,独立面对生活的一切。性格的两面使她既有女性的特点又有点男人的气概,在耶茨的笔触下,她算不上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只有她的外甥称她为“女性解放主义者”。也许艾米丽根本就不想当个女性解放主义者,她只是想让自己的生活好过一点,有个好男人疼她和她结婚。而这也恰恰言说出女性在现代社会存在的尴尬地位。一方面,随着现代女性自我意识的不断提高,她们更加意识到“我自己的存在”,存在先于本质,更加倾向于“自由地”选择“自我”以何种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艾米莉就是这样一个“我在的化身”,希望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我存在方式。[6]22-24然而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对“我在”的最大和最经常的威胁就是“他人”,“自我”可以通过意识到自己而存在,却不能掌握“他人”的自我意识,“他在”就称为“我在”的最大威胁,进而成为自我的束缚和限制,“他人即地狱”。[6]22-24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冷冰冰的结果。另一方面,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提出的:“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逐渐形成的”。[4]77女性的解放,更是一个社会和制度的问题,单凭女性的觉醒还远远不够。正如在《复活节游行》中耶茨所描写的那样,在艾米莉的前半生,她努力选择自己存在的方式,上大学拿奖学金,精神和经济都达到独立,不依附于任何人。看到这里,也许你会想到灰姑娘,想到简· 爱。在那些小说中,充满理想和努力奋斗的女性,无论她在生活中受到了什么磨难,最终仍然会有比较幸福的结局,灰姑娘的故事一直存在于每个女性的内心深处,即使灰姑娘到故事的结尾还没有得到王子的吻,但在读者的心中也会得到。而本书却要让你失望了,在本书中爱米莉的生活却是越走越差,随着父亲、母亲的去世,姐姐酗酒发疯直至离去,身边的至亲一个一个离她而去,身边的男人们更是一个一个抛弃她,直至她为了尊严愤而辞掉工作,作为对生活的愤然一击,生活总该有点起色吧!然而可悲的是,艾米莉辞职后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社会也一点点地将她抛弃,直至老年更是孤苦无依到要靠别人的救济生活。最可悲的是,读者还会发现,假如让艾米莉重新来到世间,她仍然有可能再这么活一遍!何至于此呢?艾米莉不是坚守自己的理想,选择了与妈妈、姐姐不同的道路,她不是内心觉醒,决意不依附于男人想独自寻找自己的幸福吗?她为什么还摆脱不了命运的桎梏?耶茨用他既辛辣又饱含怜悯的笔触,把命运的残忍一点一点描绘了出来,一遍一遍地逼问着自己,同时也逼问着读者。体现了他对女性内心世界的深入了解以及温情态度,同时也表达出他对女性所遭遇到的现实问题的拷问,对生命意义的拷问。
小说取名为《复活节游行》其实是深有含义的。只有在复活节游行中,艾米丽和姐姐萨拉才感受到真正的幸福,这次游行让姐妹俩回味终身,可见她们的生活和经历是多么悲惨。小说主要是以艾米丽的感情经历为主线的,这些爱情也就构成了爱米莉生活的全部内容。读者期盼着艾米莉能遇到罗切斯特一样的男人能拯救她,或者如简爱一样通过自强自立解救自己。可现实是艾米莉身边的男性们要么不成熟,只需要实用可靠这样最基本的功能;要么成熟的过了头,把女性当成一个不屑一顾的物品或者游戏的玩具。在作者的笔下,艾米莉总是遇到这些可悲的男人,与他们在一起也只能是过一天算一天。艾米莉自己虽坚守理想,努力挣扎,也如身陷泥潭,越挣扎只会陷得越深,最后只有孤独地等待生命悄无声息消失在这个世界,这就是艾米莉一生的生活历程。当这种生命的轨迹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只会让人感受到可怕,直至绝望。
《复活节游行》中所有人物的经历其实都很平淡,说不上波澜跌宕,但读者读完无不得不同情几位女性,感受到她们的孤独。耶茨从最为平凡的普通女性入手,通过描写她们最普通的生活,向读者展示了美国社会20世纪70年代女性的困顿。那个时候的美国女性,在政治上几乎都获得了相对平等的权利。然而政治上的男女平等,或者说表面上的平等并不一定能改变甚至消除世人对女性的偏见,女性的自我精神和自我价值并未得到完全的体现和彻底的改变。作为一个关注女性的男性作家,耶茨尽力在《复活节游行中》将女性的这种挣扎和争取权利的行为社会化,生活化,但父权制的残骸仍余烬未了,在艾米莉一家身上仍有彰显。姐姐萨拉循规蹈矩,逆来顺受,虽然遭受家庭暴力,仍然需要忍气吞声,维持表面上的美满。妹妹艾米莉的形象虽然被耶茨赋予了话语权,勇敢的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仍然碰得头破血流。波伏娃认为:在社会历史中,男性居于主导地位,女性处于被主导地位,女性的这种现状就是由男性的利益和地位决定的。[4]88波伏娃用存在主义来解释女性的文化身份和地位,显然耶茨很受这些思想的影响,把造成两姐妹的人生描述为“永远深陷于两难困境中,她感受到体内自为的冲动,但却被固定在自在的位置”。[7]因此耶茨把两姐妹不幸福人生的原因更多地归结为命运和社会,特别是父爱的缺失。从理查德耶茨笔下两姐妹的形象塑造中,一方面读者可以读出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对现代女性身份地位及价值的判断;另一方面,他也以艾米莉为媒介隐蔽地传递出作家对自我、社会的判断及期望。正如拉康的“镜像理论”所阐述的那样,艾米莉形象的塑造,也是“男性作家创作的一个策略,即男性作家把自我人格的一个侧面转化为女性,以求更为自由和隐蔽书写自己内心的情感世界。”[8]
四、破解的钥匙——真正的爱
孤独的生命体验使耶茨对孤独和女性不断地追索和探问,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寻求着意义,也寻找着自己最后的归宿。而文学的目的就在于为人类寻找精神的家园,探求灵魂救赎的钥匙。如何从生存的困惑中走出,建构女性精神的家园呢?这是先哲们孜孜以求的问题,也是作家书写探寻的意义。好在耶茨并没有放弃希望,在《复活节游行》的最后,艾米莉试着与萨拉的儿子、自己的外甥对话沟通,虽然是争吵,可是她试图讲出对姐姐死因的疑惑,试图和亲人们和解,走出自己生活和灵魂孤独的困顿。
如何克服孤独,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在他的著作《爱的艺术》中为现代人克服孤独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在分析孤独的根源时,认为孤独源于疏离感,所以要克服孤独就要消除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而要消除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真正的成熟的爱是真正的钥匙; 弗洛姆把爱分为成熟形式的爱和不成熟形式的爱,成熟形式的爱是创造性的,是在保持一个人完满性和一个人个性的条件下的结合,是一种积极的力量。[9]爱的缺失造成了个体和外部世界沟通的障碍,真正成熟的爱才能给予人力量打破这一障碍;成熟的爱会打破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是对生命个体真正的关心、尊敬和人性关照。[10]艾米莉悲剧的产生,就是因为缺乏身边的人对她生命和成长的积极的关爱,虽然有爱,却是表面的肤浅的爱。成熟的爱也要求个体本身充满爱,有力量鼓励和推动周围的人前进,才能培养成熟的充满创造性的爱,进而关心自己,关心别人,克服真正的孤独。因此,对现代女性来讲,成熟具有创造性爱的培养,不仅要有独立的经济和物质基础,还需要超越狭隘的思想,建立起成熟的人格,作为独立成熟的个体面对外界社会,这样才能搭建起跨越生存困惑到信念彼岸的桥梁。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 耶茨. 序言·复活节游行[M].孙仲旭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2]陈海峰.孤独与异化——汤姆斯·沃尔夫的《天使望故乡》主体探析[J].外国文学,2010,(6):114-115.
[3][美]理查德· 耶茨.序言·十一种孤独[M].陈新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4][法] 西蒙娜· 德· 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5][美]理查德· 耶茨.复活节游行[M].孙仲旭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3.
[6]齐彦芬.西蒙娜· 德· 波伏娃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所反映的存在主义观点[J]. 国外文学,1984,(2).
[7]方钰.波伏娃存在主义的女性主义哲学思想渊源探析[J]. 山东社会科学,2008,(12):36-41.
[8]魏丽明.男性作家的写作策略——论介男德尔·古马尔笔下的女性形象 [J]. 外国文学研究,2005,(1):141-146.
[9][美]埃·弗洛姆.爱的艺术[M].康革尔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10]梁若冰.现代人的孤独及其克服——浅谈弗洛姆爱的力量[J].学术交流,2011,(1):17-19.
[责任编辑石晓博]
The Twelfth Kind of Loneliness: Interpretation of Richard Yates’ Viewpointsabout the Theme of Lonely Women fromTheEasterParade
ZHANG Han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LanzhouUniversityofTechnology,Lanzhou730050,China)
Abstract:Published in 1976, The Easter Parade is one of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American modern writer Richard Yates and is called his “Female Novel”. In this novel, Yates described the miserable life and experiences of three female characters from the lower strata, U.S.A., especially sister Amily in 1970s sharply yet sympathetic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male writer, meanwhile this novel contains Yates’ viewpoints about women and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twelfth kind of loneliness beside his other book the Eleven Kinds of Loneli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woman and loneliness, the paper intends to probe Yeats’ understanding of life and fate with the theory of existentialism and tries to find the key to loneliness in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TheEasterParade; Richard Yates; women; loneliness; existenti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