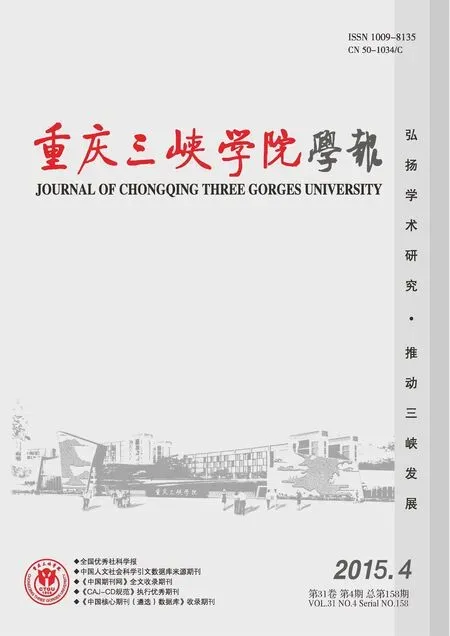鲁迅小说的言语主体与抒情的话语及语用修辞
许祖华
鲁迅小说的言语主体与抒情的话语及语用修辞
许祖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湖北武汉 430079)
鲁迅小说的言语主体主要有三类,一类是文外叙述者,一类是文内叙述者,一类是小说中的人物。这些言语主体的抒情的话语,虽然由于言语主体的身份不同,在小说中所担任的角色也不同,因此,这些抒情话语,不仅意味各不相同,而且,采用的修辞手段也各异,但无论是哪一类言语主体的抒情话语,从小说来看,都符合作为言语主体的身份及所扮演的角色,也都具有话语修辞与语用修辞的匠心,并包含了众多可资分析的内容。当然,在鲁迅的小说中,言语主体的设置,有时又是较为灵活和较为复杂的,而言语主体设置的这种状况,从一定意义上讲,是鲁迅小说的艺术匠心的一个方面。
鲁迅小说;言语主体;抒情话语;修辞
李长之在论鲁迅的创作时曾经指出:“鲁迅的笔根本是长于抒情的,虽然他不专在这方面运用它”[1]90。如果说,抒情就是指文字浸泡在情绪里的话,那么,李长之的这一判断是很有道理的。仅就鲁迅创作的小说来看,不仅各篇小说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的情感表露力透纸背,各类浸泡在情绪里的文字、话语比比皆是,而且,有的小说甚至全篇都是“纯粹的抒情文字”[1]83,如《伤逝》,所以,李长之认为:“广泛的讲,鲁迅的作品可说都是抒情的。别人尽管以为他的东西泼辣,刻毒,但我以为这正是浓重的人道主义的别一面,和热泪的一涌而出,只不过隔一层纸。”[1]76李长之的观点,实际上揭示了鲁迅作品两个方面的特色,一个方面是人们较为公认的“泼辣”、“刻毒”的特点,一个方面是他自己坚定认可的“抒情”的特点,而对鲁迅作品抒情特点的认可,也正是李长之在鲁迅研究方面的创意,因为,在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成果问世的20世纪30年代之前,还没有人如此明快地认为“鲁迅的作品可说都是抒情的”。到了20世纪40年代,另一位研究鲁迅小说的学者也如是说:“鲁迅的小说,一般地说来是散记体的形态,它的结构是直述的散记,它的风格是叙述的诗,含有情感的色彩,跃动着生命的呼吸”[2]465,更干脆地将鲁迅小说的风格与“叙述的诗”画了等号。
一般说来,小说中的抒情有各自形式,既有直接抒情,也有间接抒情,但不管是什么形式的抒情,在小说中都主要是由三类言语主体的话语来体现和完成的,一类是文外叙述者的话语,即作者的话语;一类是小说中人物的话语;一类是文内叙述者的话语,如,小说中的特殊人物“我”或其他事件的见证者、其他人物故事的讲述者等的话语。鲁迅小说的抒情也主要由这三类言语主体的话语所体现和完成。这三类言语主体,由于其身份或所担任的角色不同,对小说艺术世界构成的作用也不同,因此,其抒情话语的修辞,甚至构成抒情话语的语用修辞也泾渭分明,它们不仅以其深邃、隽永、生动的审美性存在,直接体现了“鲁迅的笔根本是长于抒情”的特点,而且也充分地彰显了自身话语及语用修辞的特点与魅力。
一、文外与文内叙述者的抒情话语及语用修辞
这里列举的是鲁迅小说中的几段文外与文内叙述者的抒情话语:
看哪,他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阿Q正传》)
舜爷的百姓,倒并不都挤在露出水面的上顶上,有的捆在树顶,有的坐着木排,有些木排上还搭有小小的板棚,从岸上看起来,很富于诗意。(《理水》)
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故乡》)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一件小事》)
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轻松了,身体也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社戏》)
五段抒情话语,分别由两类言语主体承担,第一例和第二例的言语主体是文外叙述者;第三例至第五例的言语主体是文内叙述者。这两类言语主体的话语虽然都具有抒情性,但意味与修辞却有不同的情趣,而这些不同的情趣就导源于言语主体的身份及在小说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者说,鲁迅就是按照这些言语主体的身份及在小说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意识地采用的不同的修辞手法,从而赋予这些言说主体的抒情话语以不同意味的。
就文外叙述者的话语来看,这些话语虽然也具有抒情性,但这种抒情性却明显地具有一种“矫情”的意味,即,在不该抒情的地方,偏偏写下了一段抒情话语,而这些抒情话语,不仅不怎么符合情理,而且也与这些抒情话语生成的语境十分地不协调。如第一例的抒情话语就是如此。这段抒情话语是直接针对阿Q欺负小尼姑“胜利”后的行为与心态展开的,而阿Q的这种向更弱者施暴的行为及所表现出的“得意”的神态,无论是从情理上还是从鲁迅的思想与情感倾向上来讲,都是应该批判与否定的,而且,在事实上鲁迅已经在这段抒情性话语出现之前的一段议论性话语中给予了讽刺与否定,认为阿Q的这种“得意”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种国民病态心理的反映,而不应该、也不值得来一段抒情的,可是作为文外的叙述者的鲁迅却偏偏来了一句抒情;同样,第二例的抒情话语的出现,也是如此。面对滔滔洪水及挣扎在洪水中艰难地生活着的大众所构成的民不聊生的所谓“风景”,即使不表达一下同情、哀叹,至少不应该用“很富于诗意”来抒情,可文外叙事者却也偏偏来了这么一句抒情。所以说,这些文外叙述者的抒情话语充满了“矫情”的意味。但也正是这种“矫揉造作”的抒情,在彻底而有效地消解了这两段抒情话语的所有赞赏性意味的同时,也消解了这两段抒情话语中词语所指的赞赏性意义,而让浓厚、尖锐的讽刺性意味力透纸背地发散出来,并且,这种讽刺性意味的发散还表现出这样一种倾向,即,越是用赞赏性词语修饰的抒情话语,其讽刺意味越浓厚、越尖刻,如“很富于诗意”这段抒情话语就是如此。这是因为,这两篇小说中的文外叙述者,即作者,扮演的本来就是一个批判者的角色,一个力图要“改造国民性”的角色,这两段话语的抒情性并不是在文外叙述者“真诚”赞赏的基础上诞生的,而是基于“真诚”的批判与否定的意识,即“改造国民性”的意识生成的,所以,这两段抒情性的话语采用的修辞手段,虽然表面上似乎是“直抒胸臆”的修辞手段,而在实际上所采用的则是反讽的修辞手段,而且这种反讽还具有明确的针对性:第一例的反讽针对阿Q,第二例的反讽针对即将出场的那些聚集在“文化山”上看“风景”的文人,这种反讽的修辞手段正是文外叙述者作为一个批判者鲜明的角色意识的体现。
就文内叙述者的抒情话语来看,《故乡》与《一件小事》中的抒情话语,充满了质疑和反省的意味,所采用的修辞手法一为“提问”的修辞手法,一为对比的修辞手法。而这些充满了质疑与反省意味的抒情话语及所采用的修辞手法也符合成年的“我”,这种接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身份及“我”在小说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故乡》中的“我”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见证者”的角色,即见证了故乡的变化和人的变化的角色。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从小说的整体来看,对现象的思考是“我”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特点(小说后面“我”对闰土叫“我”“老爷”现象的议论正说明了这一点),更何况“我此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所以,面对“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的故乡,“我”质疑“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自在情理之中。作为一个“见证者”,在“我”的记忆中,“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眼见的现在的故乡却一派死气沉沉,所以,这段抒情性的话语采用“提问”的修辞手法也与“我”作为一个“见证者”的角色相吻合。《一件小事》中的“我”虽然也是一位现代知识分子,“我”所扮演的角色虽然也是一个“见证者”的角色,但“我”扮演的更为重要的角色则是“对比”的角色,即“我”与车夫的对比的角色,所以,这段抒情性话语也就主要采用了对比的修辞手法,用车夫的“大”来对比“我”的“小”。从语用修辞的角度看,这里所使用的打引号的“小”,固然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解读,但最为切近的解读,则是“对比”修辞的角度,因为,无论将这个打引号的“小”的所指解读为是什么,如“我”的“小心眼”、“我”的“小九九”等,但在客观效果上都具有“对比”的效果,都指向“我”的人品、精神的“小”与车夫的人品、精神的“大”的对比。《社戏》中的抒情话语,充满了快乐的意味,采用的修辞手法则是“直陈”胸臆的手法。这也是符合“我”的身份及所扮演的角色的。就“我”的身份来看,“我”不过是一个“十一二岁”少不更事的少年,就“我”的角色来看,就是一个喜欢看戏的角色。作为一个少年,“我”既没有什么城府,也不善于压抑自己想看戏的情感倾向,“我”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并表现在行动上,作为一个“喜欢看戏”的角色,“我”“现在”的所有追求都集中在一个事情上,就是想看戏,而由于不能去看戏,“这一天我不钓虾,东西也少吃。”以至于“母亲很为难”。所以,这段抒发“我”在得知“我”看戏的愿望可以实现时的情感的话语,也就主要采用了直陈的修辞手法。从语用修辞上看,这里使用了一个“大”来形容“我”的心情,也正与“我”作为一个少年对于词语的直观理解相吻合,也与“我”扮演的一个喜欢看戏的少年的角色相吻合,因为,“我在那里所第一盼望的,却在到赵庄去看戏。”也就是说,“看戏”不仅是“我”这个时候的最“大”愿望,而且也是“我”来这里做客“所第一盼望”的,当“我”的这个最“大”和“第一盼望”的愿望就要实现的时候,用“我”的“身体也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来形容,不仅形象、生动、新颖、有趣,而且也符合“我”所扮演的角色。苏雪林当年在评鲁迅小说的用语时曾经指出“鲁迅文字新颖独创的优点,正在这‘于词必己出,’‘重加铸造一样言语’上。”[3]141这自是中肯之言,而鲁迅文字新颖独创之所以能成功,并非是凭借天马行空似的灵感偶然获得的成功,而是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培育的结果,这种坚实的基础就是小说人物外在与内在的规定性和语境的合理性,正是由于有如此坚实基础的保障,才使鲁迅小说中使用的任何“必己出”的词语和“重加铸造一样言语”,都能经受得起哪怕是最严格的检验,也就当然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二、人物的抒情话语及语用修辞
在展开论述之前,请先看例子:
“我真傻,真的。”(《祝福》)
“我是赌气。你想,‘小畜生’姘上了小寡妇,就不要我,事情有这么容易的?‘老畜生’只知道帮儿子,也不要我,好容易呀!七大人怎样?难道和知县大老爷换帖,就不说人话了么?”(《离婚》)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伤逝》)
这些抒情话语,虽然由于言语主体的身份不同,在小说中所担任的角色也不同,因此,不仅意味各不相同,而且采用的修辞手段也各异,但都符合作为言语主体的人物的身份及所扮演的角色,也都包含了众多可资分析的内容。
祥林嫂的这段抒情话语充满了悲剧的意味,所采用的修辞手法则是将抒情渗透于叙事里的手法。这种悲剧的意味及所采用的修辞手法,也是符合祥林嫂的身份及在小说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从身份来看,祥林嫂应该是一个质朴而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下层劳动者,因为,从小说的叙述来看,没有任何地方交代过她曾上过学,也没有任何描写话语或其它话语暗示过她懂“子曰诗云”,再加上她本来就少言寡语,即使开口也是“别人问了才回答,答的也不多”,所以,她的抒情话语完全采用的是下层人的口语,语用修辞上也基本以口语词汇为主,句式基本都是陈述句,且“句子短、语调急促、节奏强烈”[4]251;从她所扮演的角色来看,她是小说的主角,而且是一个苦难集于一身的主角,是一个“只有痛苦是家产,别的么,是一无所有的”[1]83不幸遭遇的集合体,而她最大的痛苦和最痛苦的遭遇就是失去了最重要也是最后依靠的儿子这件最悲惨的事件,让她最无法忘却而刻骨铭心的事件也是这一事件,她最想向人讲述的事件,也是这一事件,她的人生和情感所遭受的最重的打击与伤害,也是这一事件,让她最为悔恨的事件,还是这一事件,所以,小说采用将抒情渗透于她的叙事之中的修辞手法,自然也是符合她的身份以及在作品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因为,不仅祥林嫂所叙述的这个事件,包含了祥林嫂最直接、最深厚、最悲痛的情感内容,是最能体现她作为一个苦难集于一身的角色的事件,而且,祥林嫂饱含血泪地讲述这个事件,也完全符合她作为一个目不识丁的下层劳动者不善于“直抒胸臆”而只会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尤其是自己亲历的故事来表情达意的身份与特点。
与祥林嫂相比,爱姑虽然也是一个普通农家的女子,但其抒情性话语的意味却充满了“火药”味,所采用的修辞手法既有借代,也有移就,而话语这种意味及所采用的这些修辞手法也同样符合她的身份及所扮演的角色。没有疑问,爱姑在小说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像祥林嫂那么单纯,她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角色,从她的言语行为来看,她最初出现在小说中时,她是一个具有抗争性,而且是无所顾忌的抗争性的角色,尽管她的抗争所依据的只是传统婚姻赋予她的名分:“我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抗争的勇气来自于传统文化赋予她的虚幻的“合法性”,但毕竟表现出了维护自己“名分”的抗争性。而这里引用的她激愤地抒发情感的一段话语,正反映了她作为一个抗争角色的特点,而所采用的修辞手法,又正切合了她作为一个农家女子和复杂的抗争角色的特点。从身份来看,她虽然是一个农家女子,恪守着封建礼教的种种规范,自从嫁到婆家“真是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可丈夫和公公却“一个个都像个‘气杀钟馗’”一样虐待她,从而使她对自己的丈夫与公公又恨之入骨,而小说采用借代的修辞手法,让她用“小畜生”来借指她的丈夫,用“老畜生”来借指她的公公,则正切合了她要表达强烈憎恨的情感需要和她作为一个“没有现代性知识话语”[5]611的农家女子的经验知识素养与身份;从她在整个小说中所扮演的角色来看,一方面,她固然是一个具有抗争性的角色,另一方面,她的抗争又主要是针对自己的丈夫与公公的,却不敢挑战乡村的大人物“七大人”的权威,再加上这个时候,即她与父亲一起到慰老爷家“会亲”的时候,她又不知道“七大人”在“会亲”的过程中对她的事会如何判决而又要表现出自己的“抗争”是“理直气壮”的,所以,在涉及到“七大人”的时候,尤其是涉及到对“七大人”评价这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时,小说没有采用如爱姑对自己的丈夫和公公的评价一样的借代的修辞手法或者其它的修辞手法,而是采用了“移就”的修辞手法,将爱姑前面所指称的“七大人”中的“人”“移就”到了后面“就不说人话了么”之中,从而满足了她这个复杂的抗争角色表达“复杂”情感的需要,因为,“移就”的修辞手法中使用的“人”,不具有挑战性,更不具有显在的谩骂性,只具有“寓情于物物不变”[6]251的特征,但又显示了爱姑的“理直气壮”和爱姑对“七大人”的复杂心态。同时,人物抒情话语的这种十分讲究的修辞,不仅合乎情理,也十分精巧地为后面爱姑面对“七大人”的权威的最终妥协的结局埋下了伏笔,正是这种修辞手法的艺术匠心。
与祥林嫂和爱姑相比,《伤逝》中的主要人物子君的抒情话语则是另外一种意味,这就是“自信”而决绝的意味。这种意味所透射出的是对“个性解放”决绝追求的勇气,有学者甚至认为,子君这段抒情性话语本来就是从“个性解放”的思想意识中生发出来的,也是她追求个性解放的行动“宣言”。使用的修辞手法是直抒胸臆的“感叹”手法。这段抒情话语的意味及所采用的修辞手法,不仅同样符合子君这个人物的身份及在小说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且审美意味更为丰富。子君作为一个经常与“我”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的女性,很显然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且是一个深受新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因为,“我”与子君谈的这些话题,都是新思潮的话题,所以,在争取自己幸福的过程中子君用如此自信、决绝而充满个性解放意味的话语来抒发情感,完全符合她的身份及其知识背景。从子君在小说中所扮演的角色来看,她无疑是一个悲剧性角色,不仅是一个承担着生活悲剧的角色,更是一个承担着精神悲剧的角色,而使她成为这样一个“双重”悲剧角色的思想依据,不是别的,正是由“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都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段抒情性话语所表达的“个性解放”的思想。因为,这段抒情话语固然昭示了子君决绝、自信的精神风采,但这种似乎具有昂扬特征的精神风采却无法掩盖子君思想的幼稚性。其幼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她自己与“他们”关系的认识太天真,她只知道或者说只认识到了她是她自己的,将自己从“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孤立了出来,也只在主观上认为“他们”没有权利干涉她,但却没有认识到即使她的亲朋好友不干涉她,可是,人(包括子君她自己)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虽然人(包括子君)不一定能干涉社会,但是,社会却是一定会干涉人的,对于像子君这样的人来说,社会不仅要干涉她,而且对于她的“个性解放”还要予以扼杀,这是因为“旧社会旧势力并不是这样好心肠和大气度的,能容许这对爱人安享他们的幸福。这里还有第二道关口——比第一道关口更困难的、家庭以外的社会旧势力的关口。不用说,当时的封建旧家庭和社会旧势力是一个整体;但社会旧势力究竟比封建旧家庭更复杂,更不容易冲破。”正是因为子君和涓生没有认识到社会的如此强力,也当然没有任何的思想与行为的准备,所以,“就在这第二道关口面前,子君却悲惨地失败了,屈服了。”[7]108二是她和涓生一样,对“个性解放”的理解太肤浅,仅仅只将“个性解放”的要义狭隘地理解为“爱”,而子君这段自信十足地表现了她的勇敢与无畏的抒情话语,就正是建立在这种“爱”之上的言说,也就是涓生后来的反省所指出的:“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而涓生所指出的:“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正揭示了她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肤浅性。正因为“她当时所追求的只是爱,超出爱以外的东西,例如打破旧习惯,实现男女平等,彻底解放妇女,以至于完全推翻封建制度等等,她并不十分理解”,这也就决定了“子君的悲剧并不因为她信奉了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的思想,并不因为她信奉了民主主义,恰恰相反,是因为她缺乏充分的、坚定的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的思想,缺乏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8]327由此看来,子君这段抒情话语的“感叹”不仅符合子君的身份及在小说中所扮演的“双重”悲剧角色,而且,将这段抒情话语及所采用的修辞手法从审美效果上分析我们还会发现,这段抒情话语的抒情性越强烈、越凸显了子君的身份,子君所扮演的悲剧角色的意义也越鲜明;话语所具有的个性解放的意味越浓厚,则越显示了个性解放的弊端及在当时中国社会的虚幻性。对虚幻性的揭示,正是鲁迅深刻的思想之一,也是支撑鲁迅《伤逝》这篇小说的坚实思想基础之一,也是这段抒情性话语的意义和价值。
陈鸣树先生曾经指出:在鲁迅小说中,作者赋予抒情语言的主要有两类人物,“一类是农民或农村劳动妇女,另一类是当时进步或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显然,对这两类人物所赋予的抒情语言,不但要表现他们不同的阶级地位的特点,而且要表现他们在阶级性制约下的个性化的特点,这还不够,还必须表现他们这种阶级性与个性辩证统一的思想情感如何在特定的情势支配下的抒情方式。正是他们这种抒情方式,决定了他们的抒情语言的特色。”[4]250这种观点虽然是从一般现实主义塑造人物的规范中总结出来的,并带有十分鲜明的阶级论的色彩,也没有从言说主体的角度来分析人物抒情话语与人物在小说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关系,但所揭示的人物的“抒情方式”与人物“抒情语言”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人物的抒情话语与人物自身的质的规定性——一定阶级与一定倾向的代表和人物自身个性之间的艺术关系,还是十分中肯与精当的,而这也正是鲁迅小说中人物抒情话语合理、生动并经受得起生活逻辑与艺术逻辑检验的内在原因。
三、鲁迅小说言语主体设置的复杂性一瞥
上面虽然分析了鲁迅小说三类言语主体及其抒情话语的修辞特点及语用修辞的特点,但,我们也要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即,鲁迅小说中的言语主体的设置是十分灵活,也十分复杂的。有时,小说中的言语主体的设置十分规范,如,在《孔乙己》这篇小说中,文外叙述者、文内叙述者(即咸亨酒店中的小伙计“我”)和人物孔乙己,三类言语主体设置齐备,有时又常会发生一些变化,尤其是文外叙述者与文内叙述者这两个言语主体,不仅设置灵活,常常忽隐忽现,而且还常常角色混淆,无法界定,如《明天》这篇小说,言说的主体是文外叙述者与人物,文内叙述者本来是隐身的,但在情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这个本来隐身的文内叙述者却突然现身来了一句“我早经说过:他是粗笨女人”;还有《阿Q正传》中的第一章的言说主体是文内叙述者“我”,而之后各章中这个文内叙述者“我”又隐蔽起来了,将叙述与描写的任务转交给了文外叙事者。还有《出关》这篇小说,全篇本只有文外叙述者与人物这两个言说主体,可在情节发展的中间,却突然出现了这样两句话:“无奈这时鲁般和墨翟还都没有出世”和“那时眼镜还没有发明”,这两句话究竟是属于文外叙述者的话语呢,还是属于文内叙述者的话语呢?实在不好界定。
如何理解或解说鲁迅小说中的言语主体如此设置的现象呢?在我看来,鲁迅小说中的这些言语主体设置的变化甚至复杂状况,也是鲁迅小说艺术匠心的一个方面。有学者在研究《明天》这篇小说中文内叙述者突然现身的现象时就曾指出,这是鲁迅采用的一种强行介入小说叙事的修辞方法,其目的是为了提醒读者注意人物的身份;也有学者认为,无论文外叙事者和文内叙述者是现身还是隐蔽,甚至是混淆,这都是鲁迅反传统小说的范式和突破“文学概论”一类小说理论框框的创新性实践,而且是很新颖、独特的创新性实践等等。这些观点虽然只是见仁见智的论述,但也的确触及到了鲁迅在小说中如此做法的艺术匠心。但也正是由于鲁迅在自己所创作的小说中采用了这样一些独运的匠心,从而也带来了小说抒情话语依附的一个明显现象,这就是,在鲁迅小说中,抒情话语的言语主体,主要不是文外叙述者,也不是小说中有名有姓的人物,而是小说中的“我”这个既是小说中一个独立的人物形象,又常常是小说中典型的文内叙述者,鲁迅小说中的抒情话语,也常常由这个特殊的角色承担,而这个特殊角色的抒情性话语,不仅意味深长,而且话语修辞与语用修辞的手段也丰富多彩美不胜收。所以,分析鲁迅小说抒情的话语修辞及语用修辞,最好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是分析“我”的抒情话语。更何况,在鲁迅的小说中,这些“我”的抒情话语所负载的情感内容,虽然不等于就是鲁迅自己的情感内容,两者之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但两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有学者就曾指出:“鲁迅主要是个主观作家,他写的东西大抵都跟自己有很深感受的事情有关,感情色彩很重的《伤逝》自然不能例外”[9]664。这虽然是一家之言,其判断也可以商榷,但这种一家之言中所下的两个判断,即,鲁迅的小说创作与鲁迅自己“有很深感受的事情”的关系以及鲁迅小说的“感情色彩”与鲁迅这个“主观作家”的密切联系,还是较为中肯和经受得起推敲的。如果基于这种密切的联系对这些“我”的抒情话语展开分析,在我看来,不仅能更好地寻索鲁迅采用各种修辞手段书写这种抒情话语的艺术匠心,也不仅能从这样一个特殊的角度来研究鲁迅小说的审美性,而且,也能更清晰地透视鲁迅丰富的情感世界。
[1]李长之.鲁迅批判[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2]吕荧.鲁迅的艺术方法[C]//李宗英,张梦阳.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集: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3]苏雪林.《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C]//李宗英,张梦阳.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集: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4]陈鸣树.鲁迅小说论稿[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5]罗宗宇.“她”言说的虚妄——关于《离婚》中爱姑突变的一种解读[C].谭桂林,朱晓进,杨洪承.文化经典和精神象征——“鲁迅与20世纪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6]袁晖.论修辞中的“移就”辞[C].修辞学研究:第1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7]王西彦.第一块基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8]陈安湖.鲁迅研究三十年集[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9]张钊贻.《伤逝》是悼念弟兄丧失之作?——周作人强解的真意揣测[C]//谭桂林,朱晓进,杨洪承.文化经典和精神象征——“鲁迅与20世纪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郑宗荣)
Speech Subjects, Lyric Words and Pragmatic Rhetoric in Lu Xun's Novels
XU Zuhua
(School of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Hubei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Research Centre, Wuhan, Hubei 430079)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speech subjects in Lu Xun's novel: the outer narrator, the narrators and the characters. The lyric words vary with different speech subjects and characters in the novels. Likewise, the implications vary with the lyric words and rhetoric in the novel. In spite of these differences, the lyric words of any type of speech subject are compatible with the status and roles of the speech subjects and thus sophisticated in speech and pragmatic rhetoric and are rich in contents to be analyzed. Yet in Lu Xun's novel, there is sometimes some flexibility and complexity in setting the speech subjects, which is a partial reflection of the artistry of Lu Xun’s novel.
Lu Xun's novel; speech subject; lyric discourse; rhetoric
I210.6
A
1009-8135(2015)04-0047-06
2015-04-07
许祖华(1955-),男,湖北仙桃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教育部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鲁迅小说修辞的三维透视与现代阐释”(项目批准号:13YJA75105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