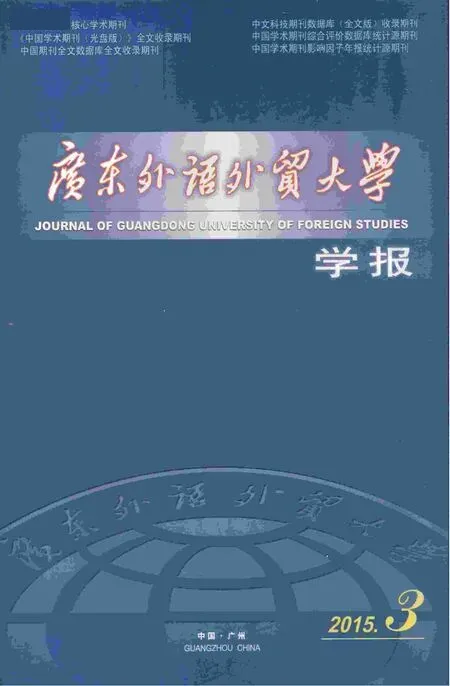散文翻译: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以丰子恺散文《渐》的两个英译本为例
李 娜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外语系,广州 510635)
一、引言
《渐》是现代散文作家丰子恺先生的经典名篇。说其经典,首先因其一再被选入我国现代散文的权威读本,更因其被选入我国中学语文课本,给无数的莘莘学子以人生的启蒙和启迪。其次,因其一再被译为英文,被编入汉英对照散文集,更有诸多学者撰文研究其译文,以此来探讨散文的翻译问题。
张培基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2009:147-150),语言流畅,意义清晰。多年来,该译著一直受到读者的喜爱和追捧。然而,“老虎亦有打盹时”。在参照《渐》的原文,逐字逐句细读其译文后,笔者发觉,张培基为了追求神似而肆意删减原文,为了形似而使译文佶屈聱牙,误读原文而使译文貌合神离等。本文结合欧阳利锋在《悠闲生活絮语》 (2013:8-16)中对同一散文的英译,拟从“形似”与“神似”、“直译”与“意译”的视角,对两位译者的译文进行一些粗浅的对比研究,以就教于译界同仁。
二、先“形似”而后“神似”
鲍川运在给《悠闲生活絮语》所作的《序言》中说,“译事难,译入外语更难,将文学作品译入外语更是难上加难。”(欧阳利锋,2013:1)。一般翻译,只要译出原文的意思,语言通顺,即大致可以。但是,散文的翻译,除要译得忠实原文之外,还要求传达原文的风格,表现出原文的美感,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文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受到与原作相应的艺术感染。
不少人曾经主张,散文翻译但求传神,不必求其形似。他们甚至认为,为了传神,形的方面甚至可以完全牺牲。在他们看来,“形”和“神”总是那么格格不入,似乎永远彼此排斥,存在着矛盾。请问,舍形是否真可以传神?在通常情况下,答案是否定的。须知,神以形存,得形方可传神。脱离形似而谈神似,无异于天方夜谭。依笔者愚见,散文翻译应该首先强调形似,然后才是神似。唯有这样,译作才有可能同原作如影随形,浑然一体。
“神形皆似”是散文翻译追求的理想,然而,却并非处处行得通。在神形确实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就应该像傅雷所言:“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傅雷,1984:1)。罗新璋在《翻译论集》的序中指出,“所谓‘重神似而不重形似’,是指‘神似’、‘形似’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倚重倚轻,孰取孰弃的问题。这个提法,意在强调神似,不是说可以置形似于不顾,更不是主张不要形似”(罗新璋,1984:1)。
在文学翻译中,“形”与“神”的独特关系构成了“忠诚”与“叛逆”的悖论。忠其形,求貌之相似,容易得其形而忘其神。译者如何才能既忠其形,又得其神,做到神形皆似呢?孙致礼 (1998:531)认为,“一般说来,‘神形皆似’的译文通常都是直译的结果”。他认为,“直译尽管可以达到“神形皆似”的效果,但在确实性不通的情况下,也勉强不得,否则,弄巧成拙,反而会令人啼笑皆非”(孙致礼,1998:532)。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不能将直译等同于求形似,将意译等同于求神似,不要以为直译只能传形,凡意译必能传神,从而,将直译与意译,形似与神似完全对立起来。在散文翻译中,我们不但要译出言内之意,还译出言外之味,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神似”。
散文是以形传神的语言艺术。为了更忠实地再现原作之神,译者在意义方面要力求忠于原文,尽量存真。同时,要力求形式上的移植,原作中的每一个实词在译作中都应该各有恰当的归宿,原作的结构和修辞手段要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如果直译无法做到“神形皆似”,译者就要转而进行意译,进行适度的创造。不过,“译者的创造,不是拜倒在原作前,无所作为,也不是甩开原作,随意挥洒,而是在两种语言交汇的有限空间里自由驰骋。”(罗新璋,1998:224)因为过度的创造会歪曲原作的内容,破坏原作的意境。如果以“创造”为名,行“背叛”之实,翻译时不细读原作,随心所欲加以处理,尤其是涉及到形象比喻、语言表达形式独特的文字,往往添油加醋或大而化之。这些问题的存在,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三、散文《渐》两个译文的赏析
17世纪法国著名的翻译家于埃说过,翻译的最好方式就是“在两种语言所具有的表达力允许的情况下,译者首先不要违背原作者的意思,其次要忠实于原文的遣词造句,最后要尽可能地展现原作者的风采和个性,一分不增,一分不减。” (Douglas Robinson,1997:169)他提倡的翻译观,归根结底,就是要先形似而后神似。在散文翻译中,追求形神兼备确实是个理想的高标准。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张培基所译散文《渐》中所表现出来的局限,然后,结合欧阳利锋的译文,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1.误读原文显凝滞
朱光潜说,“翻译的第一要领是吃透原文。只有尚不理解的,不存在无法表达的。然而每个字都认识不一定能理解,字面上理解也不等于真理解,只有全面地理解了作者,才能吃准他的一个词、一句话所包含的潜在意义。”(艾珉,1998:189)开始翻译前,译者务必先要读懂原作,弄懂每句话每个词的含义,吃透原作的风格,千万不能不懂装懂,连猜带蒙,遇上难点便故意绕过。请看《渐》的开首第一句:
①使人生圆滑进行的微妙要素,莫如“渐”;造物主骗人的手段,也莫如“渐”。
The subtle factor that makes life endurable is“gradualness”.It is by this“gradualness”that the Creator deceives all humans.
这是典型的字对字句对句所谓“字比句次”的翻译。张培基的译文同原文貌合神离,形似而神不似。这主要在于译者对原文理解不透所致。译者将“使人生圆滑进行”理解为“使人生可以忍受”,大谬也!通读全文,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根本没有这样的表述。整句话的意思:人的一生不知不觉地溜走,因为它行进的步伐极其缓慢;造物主骗人而让人无法觉察,也同样由于其手段使得悄无声息。顺带提一句,丰子恺师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笃信佛教。张培基用基督教的术语 the Creator来翻译佛教徒所谓的“造物主”,是否妥当?作者以为不妥。既然直译行不通,欧阳利锋采用意译,透过字面,传达原文的精神,表达字里行间的意蕴,请看:
Life advances on the quiet,so does Nature’ s trick on men.
可见,理解是翻译的前提。不吃透原文,不弄清楚文本在具体语境中的确切涵义,千篇一律硬译,只能牵强附会,曲解原意。
②儿女渐渐长大起来,在朝夕相见的父母全不觉得,难得见面的远亲就相见不相识了。
While parents living together with their children all the time never perceive their gradual growth,they may fail to recognize,however,a distant relative whom they have not seen for quite some time.
这是典型的硬译,主要因为译者没有吃透原文,没弄清楚文本在具体语境中的确切涵义。我们不妨先将译文回译为中文,即为:“一直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的父母永远没法察觉他们的逐渐成长,可是,这些孩子可能没法认识他们很长时间没有见面的远方亲戚。”对照原文,我们不难看出,译者牵强附会,完全曲解了作者的意思。作者想表达的意思是:“儿女渐渐长大成人。父母由于和小孩朝夕相处而没法觉察他们的变化。然而,住在远方的亲戚,由于常年难得见上这些孩子。一见面,他们就会觉得简直认不出这些小孩而感慨唏嘘不已。”欧阳利锋在正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适度地进行了创造性叛逆,充分做到了译文和原文的形神皆似,请看:
Children gradually grow into adulthood,but their parents,who see them all the time,are unaware of the changes they have gone through.On the other hand,their distant relatives,who rarely see them,may be amazed that they have changed beyond recognition.
由此看出,正确理解永远是散文翻译求形似或神似的基础。欧阳利锋逐字逐句的对译,保留了与内容和风格都密切相关的结构和原作的语言形象,又有一定的创造与变通,从而在更本质的意义上达到了形神皆似。
2.亦步亦趋缺变通
在《水无定性随物赋形——谈翻译家的语言观》一文中,方平提出了“亦步亦趋”与“灵活再现”相结合的观点。他指出:“高度重视艺术形式和内容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亦步亦趋,自然很好;但无论如何不能摒弃语言处理上的变通和灵活性” (1998:320)。为使读者得到美的享受,受到与原作相应的艺术感染,译者就不能千篇一律硬译,而是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进行适度地创造。碰到“形”和“神”的关系不易处理时,“舍形求神”该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③渐
Gradualness
这是该散文的标题。对于标题的翻译,译者必须高度重视。翻译时绝对不可掉以轻心,因为标题通常是作品主题思想的集中体现,对读者具有导向性作用。从张培基翻译的标题Gradualness,读者能从中了解到什么?恐怕什么也没有。此外,根据笔者的统计,gradualness在文中共出现十一次之多。同一抽象名词在散文中反复出现,是否有点太刺目、太单调?欧阳利锋另辟蹊径,将标题译为:The Gradual Advance,这样,可以更多向读者传递作者的意图和文本的信息,同时可以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④由萌芽的春“渐渐”变成绿荫的夏,由凋零的秋“渐渐”变成枯寂的冬。
Budding spring“gradually”changes into verdant summer;withered autumn“gradually”changes into bleak winter.
散文翻译不只是简单的解码和编码过程,因此,译者不能拘泥于原文的表面形式,一味跟在原作后面亦步亦趋,而是要努力吃透原文,摆脱中文句型的束缚,按照英语规律和习惯,适当利用转换词类等技巧,然后用通顺流畅的英文忠实加以表达。此外,我们必须注意到,英文是科学语言,而中文是艺术语言。“萌芽的春”、“绿荫的夏”、“凋零的秋”和“枯寂的冬”,都是富有诗意的中国特色的语言。由于张培基没有考虑中英文表达上的差异,也没有顾及到译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期待视野,因此,译文有些诘屈聱牙。欧阳利锋在透彻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了原文的神,忠实再现了原作的内容,又兼顾了原作的文笔及风格。请看:
The buds of spring gradually turn into the green leaves of summer,then wither and fall,and finally give way to winter’s desolate silence.
可见,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译者在语言运用上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愚笨的忠诚可能会导向‘叛逆’,而巧妙的‘叛逆’可能会显出忠诚,这也许是‘相似处犹显贫乏,不似处倒见魅力’的翻译辩证法吧。” (许钧,2003:6-11)
3.删减原文太随意
文学翻译确如戴着手铐脚镣跳舞一样,译者面对两种文化、两种语言间的种种“天然限制”,要在语言运用上充分发挥创造性,将地道的原文转换成地道的译文。可以说,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创造性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不可或缺的。然而,创造性不是任意的,必须忠实于原文,不能肆意删减、篡改原文,损伤原文意境。同时,译者还必须考虑接受者 (读者)的接受心理、文化特征等因素,在尽可能保留原文意境的前提下,对无法用本族语表示之处,进行适当的叛逆。一个好的译者不仅要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而且要尽量地译出原文的形象语言,甚至体现出原文的优美形式。
⑤假使人生的进行不像山陂而像风琴的键板,由do忽然移到re,即如昨夜的孩子今朝忽然变成青年;或者像旋律的“接离进行”地由do忽然跳到mi,即如朝为青年而夕暮忽成老人,人一定要惊讶、感慨、悲伤、或痛感人生的无常,而不乐为人了。
Suppose a kid suddenly became a young man overnight,or a young man suddenly became an old man in a matter of hour from dawn till dusk,you would definitely feel astonished,emotionally stirred and sad,or lose any interest in life due to its transience.
不难看出,原文中的形象如“山坡”、“风琴的键板”、“由do忽然移到re”、“像旋律的“接离进行”地由do忽然跳到mi”,在张培基的译文中,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译文就失去了原作的韵味。这样随意地舍弃,恐怕有点让人难以接受。请看欧阳利锋的译文:
If the journey of life could be described as the keyboard of a parlor organ rather than a gentle slope,the sudden move from do to re is like the unexpected growth from yesterday's children to today's youths,and the big jump from do to mi is like the shocking decline from this morning's youths to tonight's old people.If we grew or declined like this,we would be amazed,shocked,or even consumed with grief.Some might be overcome with the realization of our impermanence and might no longer wish to go on.
可见,对原作削鼻剜眼,不值得提倡,甚至应该极力反对。张培基的译文读起来很顺口,且有几分的“雅”,却没能保留原汁原味。这样做,虽然可以逃过读者的眼睛,但对原作来说却是个巨大的遗憾。
⑥“渐”的本质是“时间”。时间我觉得比空间更为不可思议,犹之时间艺术的音乐比空间艺术的绘画更为神秘。因为空间姑且不追究它如何广大或无限,我们总可以把握其一端,认定其一点。时间则全然无从把握,不可挽留,只有过去与未来在渺茫之中不绝地相追逐而已。性质上既已渺茫不可思议,分量上在人生也似乎太多。
“Time”is the essence of“gradualness”.
原文共有五句话,而在张培基的译文里,却只剩下一句话,而且,有些不明不白,没能将原作者的意思表达出来,“形似”与“神似”都无从谈起。严格意义上来说,原作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是有其用意的,译者应该一字不漏、一句不少地译出来。当然,因为源语和目标语之间存在差异,译者有时才不得不舍其形,求其神。请看欧阳利锋的译文:
Gradual advances are,in essence,a matter of time.To me,time is even more difficult to grasp than the concept of space.Indeed,the art of time in music is more mysterious than the art of space in painting.No matter how huge or infinite a space is,we can always hold one corner of it.Yet time is completely different.It is beyond our grasp,and we can never stop its passage.We can only watch helplessly as the past chases the future into the void.Time is in essence vague and inconceivable,and too much of it seems to be rationed to each individual.
不难看出,译者终坚持“忠实”和“通顺”的翻译标准,其译文既再现了原作之形,又传达了原作之神,可谓“神形皆似”。
⑦ 然人类中也有几个能胜任百年的或千古的寿命的人。那是“大人格”,“大人生”。他们能不为“渐”所迷,不为造物所欺,而收缩无限的时间并空间于方寸的心中。故佛家能纳须弥于芥子。中国古诗人 (白居易)说:“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英国诗人 (Blake)也说:“一粒沙里见世界,一朵花里见天国;手掌里盛住无限,一刹那便是永劫。”
张译:However,we do have among us a few who know how to correctly view life.They are great,indeed!They refuse to be fooled by“gradualness”or the Creator.
原文共有六句,其中夹杂着唐诗和外国名人的名言,颇有禅意。张培基只用三句综合地译出了这段文字的大概内容,而将白居易和布莱克的诗一概略去不译。译文读起来虽然流畅,但却失去了原作的禅意和韵味。这不能不说是对原作者的一种“背叛”。作为译者,要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分析,在理解原作的神韵风格上精益求精,同时要忠实传达原作者的意思。请看欧阳利锋的译文: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only a very few have managed to live life to its fullest.This takes greatness to achieve.These people were not deceived by the slow advances of time or misled by Nature.Instead,they grabbed hold of infinite time and space and made a place for it in their hearts.In this way,a Buddhist can see a pagoda in a mustard seed.Bai Juyi,the famed poet of the Tang Dynasty,wrote,“For what matters do we fight,on the horns of a snail?We live our life in a flash struck off a stone.”William Blake,the well-known British Poet,challenged readers“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上述译文质朴清丽,明快流畅,细腻传神。译者忠实地传达了原文的深层意思,又不露生硬牵强的痕迹,可以说是翻译中的上乘之作!
四、结语
通过对比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欧阳利锋的译文基本上做到了形神皆似,而张培基的译文或因过分忠于原文而貌合神离,或因肆意删减而形神皆异。尽管张培基在这篇译文中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是,瑕不掩瑜,丝毫不会减损他作为中国一流翻译家的声誉。
成方圆于规矩之内,出神韵于法度之中。形神兼备,应该是散文翻译的一种追求。“这是由于人类总是通过有形把握无形的,也正因为这一规律,翻译散文而为求形神皆似,就应该首先力求形似。”(江枫,1998:420-421)为求“神似”,译者既要钻进去以求理解,又要跳出来以求表达。齐白石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冯颖钦,1998:306)散文翻译又何尝不是如此?译作不可“不似”原作,但又不可“太似”原作。一流的译者都应该尽量保持原汁原味,达到“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艺术高度。
艾珉.1998.切勿损害大师形象[M]∥许钧.翻译思考录.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鲍川运.2013.序言[M]∥欧阳利锋.悠闲生活絮语 (Essays on Easy Life).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傅雷.1984.《高老头》重译本序[C]∥罗新璋.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方平.1998.水无定性随物赋形——谈翻译家的语言观[M]∥许钧.翻译思考录.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冯颖钦.1998.妙在似与不似之间[M]∥许钧.翻译思考录.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江枫.1998.形似而后神似[M]∥许钧.翻译思考录.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罗新璋.1984.序言[C]∥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罗新璋.1998.释“译作”[M]∥许钧.翻译思考录.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欧阳利锋.2013.悠闲生活絮语(Essays on Easy Life)[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孙致礼.1998.关于我国翻译理论建设的几点思考[M]∥许钧.翻译思考录.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许钧.2003.“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定[J].中国翻译(1):6-11.
张培基.2009.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Selected Modern Chinese Essays 2)[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Robinson D.1997.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M].St.Jerome Publishing Ho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