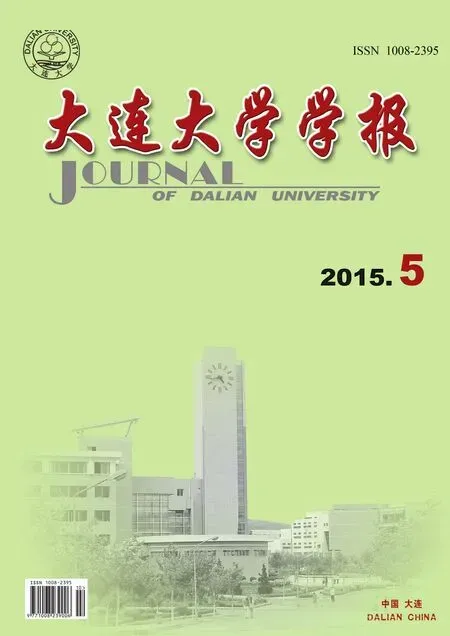我国《婚姻法》中离婚条款历史变迁的社会学意蕴
徐祥运,鞠孝严,丁丽兰
(东北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我国《婚姻法》中离婚条款历史变迁的社会学意蕴
徐祥运,鞠孝严,丁丽兰
(东北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我国共出台了三部《婚姻法》,三个阶段《婚姻法》中有关离婚条款的历史变迁,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学意蕴:1950年的《婚姻法》作为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其离婚条款以离婚自由、倾斜性保护女性为特点,由此产生了我国首次离婚高峰、妇女大规模从事生产劳动的社会影响;1980年《婚姻法》是在文革终结和社会开始转型的社会背景下诞生的,其离婚条款的特点是充分尊重个体情感意愿,由此导致第二次离婚高潮及“第三者”问题的浮现;2001年《婚姻法》中离婚条款是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个人财富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其最大的特点是确立了多样的财产制度,重视离婚赔偿保护弱势群体。我国《婚姻法》中的离婚条款,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变迁,在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个体自由与利益之间,基本上维持了二者之间的社会平衡,彰显了法律的社会控制功能。
婚姻法;离婚;历史变迁;社会控制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学者们对《婚姻法》中的离婚条款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定离婚理由、离婚自由度与离婚事由、解除军婚的特殊保护、登记离婚与协议离婚、父母离婚后未成子女利益保护、夫妻财产分割、婚姻债务、离婚救济、离婚程序等十个方面[1]。劳伦斯·M·弗里德曼在《法律制度——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观察》一书中指出,法律的真实现象有三种:一是“哪些以某种方法挤进来制定法律的社会和法律势力”,即法律的输入方面,实际涉及的是法律产生的社会背景;二是“法律”本身——机构和规则,即法律的输出方面;三是法律对外部世界行为的影响[2]。依劳伦斯·M·弗里德曼的观点,上述主要研究方面都是关于第二个现象,而忽略了第一和第三现象。然而离婚——婚姻关系终止的同时也意味着作为个体社会化的初级群体、社会基本组织单位和社会维系凝聚整合重要纽带与桥梁的家庭关系的终结,由于婚姻关系的特殊性,我们在研究我国《婚姻法》中有关的离婚条款时应区别于其它一般法律,应更多的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分析我国各个历史阶段《婚姻法》中离婚条款的发展脉络、涉及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关系、具有的社会特征和社会影响等等。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建国以来三个阶段的《婚姻法》中的离婚条款,主要包括1950年、1980年和200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的离婚条款,相应阶段关于离婚的政策文件以及《婚姻法司法解释》中与离婚相关的条款。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法律社会学中法律多元化视角下,法律分为国家法和民间法(习惯法)。习惯法是指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用以调节人们社会关系、约束人们社会行为的一套行为准则,包括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舆论等[3]。日本社会学家青井和夫曾经指出:“法律社会学从社会控制的观点,不仅把国家法律而且也把习惯法、传统、惯例、习俗、习惯这一系列的社会规范作为研究对象。而且在与社会控制相关的意义上把研究延伸到道德规范,延伸到更加普遍化和绝对化的伦理问题,甚至对立法、行政、司法的具体程序也进行了研究。”[4]从法律社会学对于法律的宽泛的理解,再考虑到法律学者对我国现阶段司法解释价值的肯定,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的运用上,司法解释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略,因此本文将司法解释中与离婚相关的内容作为《婚姻法》的组成部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的离婚条款一起,共同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本文将通过搜集各个阶段历史数据资料,包括报刊、统计年鉴、历史文献等,分析与其相对应阶段《婚姻法》中离婚条款的关系,解读其出台的社背景、社会原因,以及具备的特点和产生的社会影响。通过各阶段的历史分析比较,探索我国《婚姻法》中离婚条款历史变迁的社会学意蕴。
二、1950年《婚姻法》离婚条款:离婚自由、倾斜性保护女性
(一)倾斜性保护女性及其正义性
1950年的《婚姻法》作为我国建国以来的第一部《婚姻法》,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担负着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责任,其中离婚条款的最大特点是实行离婚自由、保护女性。对于1950年《婚姻法》中对于离婚自由、保护女性的规定,可以从正义的角度进行分析。正义是一个十分抽象的词语,其内容也难以界定,古往今来的贤哲们对于正义的探索和讨论也难以统一。总的来讲,正义分为个人正义和制度正义,制度正义包括国家政治正义、法律正义等。对于《婚姻法》中离婚条款的分析基本可归类为制度正义中的法律正义。有学者认为,在探索法律正义的路上,有四种道路,即社会契约论、自然法理论、人权理论、价值理论[5]。社会契约论认为只有通过约定和法律把权利与义务结合起来,才能使正义具有现实性。因此,其代表人物卢梭的观点是,正义来自于、体现于人们的约定和法律在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形成一个共同体之后,这一共同体的全体人民对全体人民作出的规定就是法律这种规定体现着人民的协议,依据着人民的公意,由于公意永远是公正的。所以,这种体现着人民的公义的法律本身就是公正的、正义的[6]。自然法的代表人物普芬道夫主张法律都要受到自然法原则的限制;人权理论的代表人物马里旦将人权分为人类个人权利、市民个人权利和社会个人权利,认为人的权利是人自然地享有的。价值理论不同于前几面的理论,它是通过说明一些特定价值来阐明法律正义的内在意义,关于法律正义,各思想家有的认为其追求的是平等,有的认为是自由,有的认为是安全,有的则综合之前的各种思想和观点认为是自由与平等的结合。上述四种探索法律正义的道路各有侧重也各有利弊,但总体来说有一个共同点,即对于个人权利和社会秩序的维护。1950年《婚姻法》中离婚条款关于离婚自由的规定是对婚姻中的男女尤其是妇女追求自由的权利的保护,而女性作为社会中的相对弱势群体,法律在社会控制层面上进行保护有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体现法律正义。
(二)社会背景:发展社会生产需要与文化动力具备
1949年我从半殖民半封建主义社会进入到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社会组成部分的旧婚姻制度在新中国成立时成了新生的社会机体上已经衰败的细胞,必须把男男女女尤其妇女从婚姻制度的锁链下也解放出来,并建立一个崭新的合乎新社会发展的婚姻制度[7]。按照作为社会学家的卡尔·马克思的观点,法的关系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8],“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二每一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哲学的和其他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9]我国 1950年《婚姻法》的出台从根本上是由经济发展的需要所决定的。
另一方面,当时具备了推翻传统婚姻家庭制度的文化动力。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提出了“男女同受教育、男女社交公开和婚姻自由,改造家庭、改善妇女地位”的要求以及具体措施,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作为封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冲击。另外,建国之前我国就与苏联等东欧国家关系友好,相互间的文化交流和碰撞多。起草小组主要的参考资料是中华苏维埃政府1931年12月1日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婚姻法》作为法律的一部分属于文化的范畴,传递性作为文化的特性之一在1950年《婚姻法》上体现的十分明显[10]。
(三)社会影响:离婚高峰出现与妇女大规模从事社会生产
1950年《婚姻法》施行后,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出现了我国的第一次离婚高峰。成千上万饱受封建婚姻痛苦的男女,特别是妇女,纷纷提出解除包办婚姻和买卖婚姻[11]。建国初期为了改变我国落后的经济状况,实现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53年我国实行了“一化三改”,在此大背景下,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积极地投入到了社会生产中,尤其是妇女,由于受到婚姻法中关于保护女性的条款以及提高女性地位措施的鼓舞,逐步改变观念,参与生产的积极性大大增强。中国的广大妇女,无论身处城市或者农村,都加入到了社会劳动的队伍里,妇女群众的“半边天”作用不断突出显现出来。无论是妇女从事农业生产的数量,还是妇女从事行业的种类和跨度,以及妇女在各个行业的表现,都足以体现妇女所产生的积极而且十分重大的影响。1950年全国工农兵模范中妇女代表有22名,占到了代表总数的1/9。1958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有844人来自农业战线广大妇女群众[12]。妇女群众生产劳动的范围从辅助性劳动及一般的田间生产转变到掌握各种农业生产技术和从事林、牧、副、渔各业生产中来,有相当多的妇女掌握了生产技术,成为农业生产的技术骨干。到1955年底,全国女性农业技术人员达到2540多人[13]。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的过程中,到1956年,全国约有一亿两千余万户农村妇女,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从事农业、牧业、副业生产[14]。妇女从家庭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从事大规模集体社会生产劳动状况可略见一斑。
三、1980年《婚姻法》离婚条款:重申离婚自由、尊重个体情感
(一)对于个体情感自由的尊重与满足
与1950年《婚姻法》对离婚的规定条款相比,1980年《婚姻法》中的离婚条款只是对于在上一部《婚姻法》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偏离甚至严重问题的相关条款进行了补充或者强调,在内容上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鉴于“文革”时期对法治的破坏以及改革开放后人们对于婚姻中情感的追求,1980年《婚姻法》再次重申离婚自由这一条,并且明确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准予离婚的法律原则。这一条款体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婚姻法对于人们在婚姻中追求爱情、追求感情至上的肯定。在马斯洛看来,大多数人的需要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自身到他人、由个人到社会,是一个逐渐上升的体系。他按其高低与优先次序将人的需求划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从马斯洛需求层次上看,情感自由属于第三个层次——爱和归属的需要。当生理和安全的需要都能满足时,对归属和爱的需要就会支配人的行为,开始成为人们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1980年《婚姻法》中的离婚条款对于人们爱和归属需要在法律上的保障,说明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的生理和安全需要是基本能够得到满足,而且已经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
(二)社会背景:文革的终结和社会的转型
1966年,我国进入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此期间,政治因素成为影响男女结婚的重要甚至首要因素,正常的婚姻家庭关系被扭曲,人民的婚恋权利受到严重侵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面临社会转型。在生物学中,“转型”是指生物物种间的变异。这个概念被西方社会学家借用以描述社会结构具有进化意义的转换和质变。西方较早使用“社会转型”一词的,是社会学者D·哈利生。关于社会转型这一概念的界定,各学者观点不一,具有代表性且得到较多认同的是陆学艺和景天魁的观点,他们认为“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15]。社会转型的基础是生产力的发展,正是由于生产力的变革,带动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变革。在建国后的30年,我国初步建立起了现代工业体系,初步奠定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为之后中国社会的转型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将“以阶级斗争为纲”定位为中心任务,实施计划经济体制而排斥市场经济,而且盲目轻视现代知识,所以就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社会呈现出停滞甚至落后的局面。改革开放后,随着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基调的逐渐确立,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形成,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为整个社会的变革提供了很好的经济基础,我国社会面临着继新中国建立结束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这一社会转型后的又一次大的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是包含着经济、政治体制、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变化,思想文化的转型受到经济政治转型的影响,同时也具有自身特有的特点。这一时期由于改革开放,西方思想的涌入对我国人民长久以来形成的传统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感情的追求成为人们建立婚姻的目标。这一心理及行为的转变过程可以从这30年来法院受理的离婚类型中看出一些端倪。50年代受理的离婚案件多以反抗封建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由为主;60年代多以反抗夫权至上,争取夫妻平等为主;70年代多以性格不合、经济纠纷政治原因为主[16]。
(三)社会影响:第二次离婚高潮及“第三者”问题浮现
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贯彻了世界上比较先进的“破裂主义”的离婚原则,使不少当事人解脱了不幸婚姻的枷锁,并造成了离婚率的急剧攀升。但是到六七十年代极左思潮盛行的时期,离婚者常遭到舆论的谴责和歧视,离婚自由的法律条款实际上已被限制离婚的现实所代替。1978年,全国离婚总数下降到28.5万件,离婚率为0.35‟[17]。但是,随着1980年《婚姻法》以“感情确已破裂”取代1950年《婚姻法》中的以“婚姻破裂”作为离婚的条件,加上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在婚姻家庭领域里出现的不少新情况,一方面催生了新的婚姻理念,人们获得了更多的婚姻自由,为寻求婚姻幸福提供了空前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出现了大量的婚姻问题,困扰着人们的生活。就后者而言,最显著的特征是,离婚率节节攀升。据统计,1978年的离婚率为0.35‟,1986年上升为0.94‟,1990年为1.38‟,1995年甚至飙升到1.75‟[18],[22]。
随着情感破裂论在《婚姻法》中的确立,人们在婚姻中追求情感的目标越来越强烈,然而当婚姻中的爱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变淡时,人们便在婚姻之外追寻情感的寄托,“第三者”的社会问题渐渐浮现出来[19]。在婚外恋案件中,尤以走在全国经济前列的上海、广东为甚,就婚外恋中的“包二奶”现象看,单广东省妇联接受这方面投诉的,1996年为219件,1997年为235件,1998年多达348件[20]。
四、2001年《婚姻法》离婚条款:重视离婚赔偿保护弱势群体
(一)夫妻财产制度形式多样重视离婚赔偿
2001年《婚姻法》离婚赔偿中财产分割的条款增多、范围更广、内容更细。另外,在随后的司法解释中对于不动产、无形资产的规定也出现并且细化。司法解释二中关于无形资产的解释有2条,关于公司财产分割的规定有3条,关于房屋的规定有2条,司法解释三中,对于财产的解释多达10条,其中涉及不动产的有4条。
可见,2001年新《婚姻法》中的离婚条款及其随后颁布的三部司法解释中很大的特点是重视财产的分割和离婚赔偿,这是由我国社会转型后财产纠纷在离婚案件中越来越突出的现状决定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但是,在财产分割的规定中过度强调个人财产,忽略了婚姻家庭的特殊性,由财产的独占性而带来的个体的独立感不符合婚姻家庭作为一个整体的本质及其所具有的功能。
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婚姻作为个人活动结果的生活实体,定义可概括为持续的性关系和共同生活体;而家庭作为生活实体,可定义为实体婚姻、孩子以及共同生活体;作为社会设置,强调的是血缘、供养和继承关系[10]170。根据其中的内涵我们不难看出婚姻和家庭的共同点即本质——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关系而存在,而且这一社会关系是成员间亲密程度最高的初级群体。另外,就家庭而言,其具备的情感交流、成员社会化和抚养赡养等功能也只有当家庭中的成员归属感、凝聚力强的时候才能更好的发挥。有学者采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调查了我国 304个城市家庭的家庭功能状况和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家庭功能与家庭成员的亲密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21]。
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对于房产的多处规定过度强调了个人财产,而忽略了成员处在家庭这个特殊整体的事实。例如司法解释三第七条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以利益为驱动的市场经济所形成的价值观,片面强调了作为经济主体的男女双方对于财产的占有,这种以利益为主导的价值观将处于家庭中的社会人与经济学中假设的完全理性经济人混淆,过度强调了财产的独占性,由此带来的个体的独立感削弱了婚姻家庭的核心价值观——爱、责任和奉献,削弱了在家庭中原本应该有的温情、呵护和关爱,进而削弱了家庭在情感交流、成员社会化等方面的功能。
(二)社会背景:个人财富权利意识增强和家庭暴力突显
改革开放后的20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经济的发展带来社会的巨大进步,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日渐丰富,个人财富不断积累,人们财产权利意识日渐增强。在不同的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中,人们拥有财富的形式也逐渐多样化[22]。在财产的构成方面,除了住房、汽车、高档家具、家用电器等实物财产外,还出现了股票、债券、彩票、外币、邮品、著作权和知识产权等无形财产形式,而个体工商户、承包经营户、私营企业等老板还拥有相当数量的生产资料和债权、资本收入等,其价值往往远远高于通常概念的夫妻财产。与此伴随而生的,是夫妻离婚时发生财产纠纷也呈上升的趋势。据统计,夫妻离婚财产纠纷案件在离婚案件中所占比例 1980年是0.7‟,1990年上升到1.4‟[23]。1999年、2000年夫妻财产协议公证件数分别为85285件和94428件,占民事法律关系公证比重分别为1.38%和1.69%[24]752。
上文谈到,新《婚姻法》明确提出反对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社会问题。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侵害家庭成员的合法利益,受害人都往往不知道如何得到救济,有的因此导致家庭矛盾激化并走上犯罪道路,严重影响了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安定。家庭暴力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受害的对象主要是生理条件处于劣势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全国妇联1997年对15个省市的信访统计,因家庭暴力引起的信访量已占婚姻家庭信访量的34.5%;1999年广东省妇联在广州等11个市组织了1589个家庭入户抽样调查,有29.2%的家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现象,因家庭暴力导致离婚和人身伤害案件增多,毁容、残肢、烧妻、杀夫等恶性案件也时有发生[24]。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反对家庭暴力被明确提出,体现出法律对社会问题进行社会控制的时代性和强制性。
(三)社会影响:弱势群体受到保护彰显社会正义
首先明确提出反对家庭暴力。1950年《婚姻法》中只规定了“父母子女之间均不得虐待或遗弃”,1980年《婚姻法》规定“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随着上述问题的日趋严峻,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将反对家庭暴力写进了法律,《婚姻法》第3条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第43条规定“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劝阻: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的成员,受害者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行政处罚”,第45条规定“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在第32条中家庭暴力也被作为离婚的条件之一,第46条中规定家庭暴力也是离婚时受害方请求损害赔偿的依据之一。根据之前的背景描述中已经知道,家庭暴力的对象普遍是妇女儿童以及老人等弱势群体,因此新《婚姻法》中对于惩治家庭暴力的明确规定是保护弱势群体的体现。
其次是对家务劳动的认可。根据2000年全国第二期妇女地位调查显示的结论显示,85%以上的家务劳动主要由妻子承担,已婚男性每天家务劳动时间1.45小时,女性每天4.08小时,女性平均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比男性多近2.7小时[25]。由于家务劳动不可量化,更无法用货币来计量,在这中情况下,无论采用何种财产制度,都会使得女性利益受损,存在男女实质不平等的状况。为此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第40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这样至少在法律的高度认可了女性抚养子女、照顾老人等家务劳动的价值,体现了对家务劳动的法律承认。这是对整个社会观念在方向上的一个引导,表现出很多的人文关怀。
最后在社会伦理上维护了夫妻的忠实。在学术界,学者对夫妻忠实义务的含义多有不同表述,我国多部《婚姻法》都没有明确夫妻忠实义务的内涵和外延,但结合2001年《婚姻法》第4条和第46条的规定来看,我国《婚姻法》中规定的忠实义务是指夫妻之间的贞操义务,夫妻双方的性权利应合理地限制在合法的婚姻之内,即夫妻之间不得有婚外性行为、在性生活上保持专一的义务。这既维护了无过错方的利益,又伸张了社会正义。
五、结 语
法律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之一,《婚姻法》中的离婚条款作为调整婚姻家庭领域社会关系的重要条款,在整个变迁过程中充分体现了法律的社会控制功能。社会控制的功能和意义体现在两个层面,在微观上它规定了社会成员的价值规范、行为方式,并强化与之相适应的权利、义务体系,调整成员的利益格局与关系;在宏观上它使得社会运行系统的各部分功能耦合,结构协调,子系统之间信息和能量充分自由地交换流动[3]198。从微观层面上来看,《婚姻法》离婚条款的变迁,引导人们婚恋观的转变,很好地调整了家庭成员的利益关系。1950年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在离婚方面确立了离婚自由、保护女性的原则,不幸的婚姻对于人们尤其是女性而言不再是一生的枷锁和牢笼,鼓励人们追求自由和幸福。1980年继十年“文革“动乱和改革开放之初的《婚姻法》重申离婚自由,确立情感破裂论原则,对于“文革”期间遭到破坏的法治进行重构和调整,修正阶级、政治因素在婚姻家庭中的起主要作用的价值取向,尊重个体意愿。2001年伴随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发展、人民财产增加且构成多样而出台的《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以及离婚赔偿等做了详细的规定,调整了家庭成员在家庭中的利益关系和格局,对于妇女、儿童和老人这些弱势群体的保护措施宣示了社会对正义的追求。从宏观层面上看,《婚姻法》离婚条款的变迁,保证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的相互耦合以推动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这一功能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第一部《婚姻法》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总体而言,我国建国以来三个阶段的《婚姻法》中的离婚条款,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具有与当时社会相应的不同特点,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影响。《婚姻法》中的离婚条款,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变迁过程,在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个体的自由和利益之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各有侧重,但基本维持了二者之间的平衡,并给弱势群体以应有的社会关怀,越来越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意蕴。
[1]蒋月.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离婚法研究回顾与展望[J].法学家,2009(1):63-87.
[2]李瑜青.法律社会学经典论著评述[M].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89.
[3]郭星华.法社会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8.
[4]青井和夫.社会学原理[M].华夏出版社,2002:22.
[5]张恒山.论正义与法律正义[J].法治与社会发展,2001(1):28-38.
[6][法]卢梭.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5.
[7]徐安琪.新婚姻法修改:社会转型的晴雨表[N].中国青年报,2001-06-01.
[8]杨善华,谢立中.西方社会学理论(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78.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39.
[10]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68.
[11]当代中国从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审判工作(下)[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3-5.
[12]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32.
[13]武舟.中国妓女文化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89.
[14]伊庆春,陈玉华.华人妇女家庭地位:台湾、天津、上海、香港之比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75.
[15]陆学艺,景天魁.转型中的中国社会[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15.
[16]丁文,徐泰玲.当代中国家庭巨变[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31.
[17]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人口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395.
[18]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9[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895.
[19]艾米莉•韩尼格,盖尔•贺肖.美国女学者眼里的中国女性[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185-188.
[20]段京连.包“二奶”、婚外恋与重婚[J].人民公安,2000 (8):7-9.
[21]龙翼飞.我国物权法对家庭财产关系的影响[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8( 6):18-21.
[22]国家统计局.2001年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304.
[23]国家统计局.2000年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768.
[24]杨学明,曲直.新婚姻法热点聚焦[M].沈阳:辽宁画报出版社,2001:218-220.
[25]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课题组.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报告[J].妇女研究论丛,2001 (5):4-12.
The Evolution of Divorce Terms in Marriage law of China--A Sociological Implication
XU Xiang-yun, JU Xiao-yan, DING Li-la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China has issued three marriage laws so far.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divorce terms contain rich sociological connotations.In 1950, China issued the first marriage law keeping the freedom of divorce and the protection of women resulting in the first divorce peak and women’s engagement in large-scale production.The 1980 marriage law was passed at the end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respecting individual emotion leading to the second peak divorce and problem arose thereafter.The 2001 marriage law was passed with the economy developing rapidly and the awareness of wealth and rights increasing establishing various property system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protecting the vulnerable from the divorce.Terms of divorce in the marriage law are changing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times, maintain a balance between social order and individual freedom highlighting the function of social control.
marriage law; divorce; historical change; social control
C913.13
:A
:1008-2395(2015)10-0063-07
2015-04-05
徐祥运(1963-),男,教授,主要从事应用社会学,社会问题与社会发展;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鞠孝严(1991-),女,研究生,主要从事法律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研究。丁丽兰(1991-),女,本科生,主要从事法律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