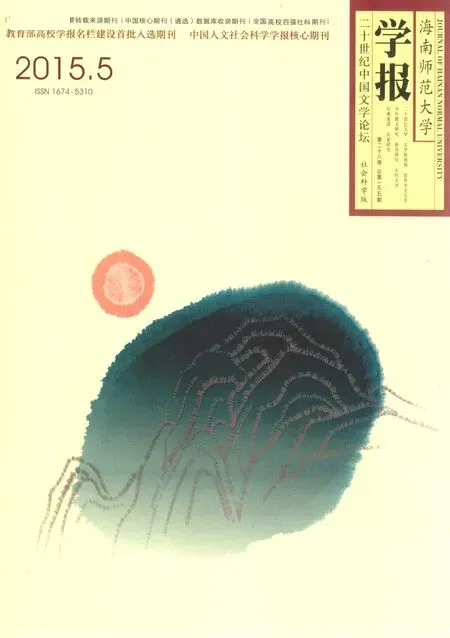神圣的消解与自我的迷失——从黎族文身诸说看文身女性角色演变
黄淑瑶
(海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海南 海口571158)
一、问题的提出
黎族文身,作为传统黎族女性的特有文化标志,向来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对于文身何以存在,黎族传说和历史文献中提供了多种解释。欧阳洁、孙绍先曾统计出14 类文身解释,其中有些类别还有变体。在这些文身解释中,历史上较具代表性的有“成年礼”(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逃避外族掠夺”(周去非《岭外代答》)、“祖先识辨说”(顾岕《海槎余录》)和“守节说”(张庆长《黎歧纪闻》)。其中“逃避外族掠夺”在后世演变成“部落争斗说”(刘咸《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逃避恶霸说”(王国全《黎族风情》);“祖先识辨说”中的祖先又与“纳加西拉鸟”传说(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兄妹婚配”(王国全《黎族风情》)、“母子婚配”(刘咸《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发生联系。如此多的说法,让研究者陷入了对文身起源、功能的认识迷沼。如何看待这些关于文身的歧出认知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
有些研究者试图穿过历史迷雾,从众多说法中寻找最初的本源,如早期有彭华认为,越人文身是对龙(蛇)的崇拜,而后衍生出生殖、婚姻和审美意识。[1]焦勇勤、孙海兰详细对比和剖析黎族文身的图案与黎锦花纹后,认为文身实为青蛙的抽象化,可视为对青蛙的崇拜。[2]欧阳洁、孙绍先则对黎族文身举凡14 种说法进行了一一辨析,最终将黎族文身归为生殖崇拜。[3]而郑小枚从乱伦禁忌角度主张认为,黎族文身是乱伦禁忌的现实设计,统一了黎族的伦理秩序,保障了黎族的生息繁衍。[4]对本源的寻求,虽然某种程度上能让研究者在文身迷雾中确定一个明确方向,但却让其他文身说法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另有研究者试图将文身与社会变迁和族群差异联系起来,给予文身诸说以各自的合理性。如赵全鹏认为黎族文身的众多说法反映了黎族不同时代的历史和社会生活。[5]王献军通过对汉文古籍记载的黎族文身史料进行梳理,指出诸多说法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6]他还特别指出汉黎之间在文身观点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影响了文身变迁。[7]将文身与所处的时代联系起来的做法,无疑给文身诸说赋予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客观性。但该角度有待进一步深入的地方,也是文身研究待拓展之处,即对文身现象的基本要素和文身活动的核心主体——黎族女性的关注。作为被刻画在黎族女性身上的“敦煌壁画”,文身与女性密不可分。但在众多文身研究中,鲜见对文身女性的关注,即使有,也只是作为文身的附属品出现。
对于文身研究中的这类现象,从女性人类学角度,笔者认为这是长期男性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所造成的。亨瑞塔·摩尔曾指出,“女性在人类社会中是‘缄默’的一群,在人类文化中女性处于缄默状态”。[8]白志红也认为:“人类学对人的研究原来是对‘男人’的研究……他们对妇女的关注往往是由于研究课题涉及妇女,而不是以妇女为中心,也没有意识到这个必要性。那些对女性的观察和记录是研究内容本身的需要,如婚姻家庭、亲属称谓、性生活、社会制度、人类心智等‘重大’命题的研究,而不是出于研究者自觉公正的反思。”[9]女性人类学正是要求从女性视角来重新考察人类文化现象,以获得对人类历史文化发展更深的认识:“通过对女性历史与现实的考察,来探讨女性文化在人类文化中的历史命运,来描述女性文化在人类文化中失落的真实过程,并重新讨论女性文化在人类文化中的价值和对人类文化重建的意义。”[10]6
沿着女性人类学的研究思路,重新审视文身与女性,我们会发现,歧出的文身诸说牵涉黎族族源、发展及内部社会关系演化,尤其是女性身份历史演化等诸多重大问题。故笔者拟以黎族女性角色地位变化为主线,综合神话史诗、传世文献、口述历史资料和田野调查报告,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具有代表性的文身诸说①因文身说法众多,记载时间不一,故可能出现今人搜集的资料其内容所反映的时间早于前人所记载。为统一资料来源,笔者以汉古文籍的记载为依托,根据其对黎族女性影响的程度选择了“祖先识辨说”、“成年礼说”、“外族掳掠说”、“守节说”、“爱美说”五说,根据所反映的信息,对照黎族的神话传说,来确定诸说可能的发生顺序。(“祖先识辨说”、“成年礼说”、“外族掳掠说”、“守节说”、“爱美说”)进行梳理,探讨其背后反映的两性权力和地位更迭的状况,并籍此反思文身女性角色变化对以文身为代表的黎族母系文化残余的最终影响。
二、“祖先识辨说”与“成年礼说”中的神圣女性
在文身诸说当中,“不文身不归宗”的“祖先识辨说”②“祖先识辨说”的记录时间虽然晚于“成年礼说”,但笔者认为,不能根据资料搜集的时间来判断二者的发生时间。从“祖先识辨说”所包含的信息,以及对黎族女性的影响来看,远非“成年礼说”所能比拟。故笔者认为“成年礼说”的发生时间应晚于“祖先识辨说”,且有可能是在“祖先识辨说”的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说法。是目前现存文身解释中发生时间相对较早,影响最广,留存最久的说法。虽然对其确切的文献资料记载较晚,最早见于顾岕的《海槎余录》:“黎俗:男女周岁,即文其身,不然,则上世祖宗不认其为子孙也。”但其所隐含的祖先崇拜、氏族标识的信息在黎族的《吞德剖》、《三月三》、《纳加西拉鸟》等众多关于文身的史诗、神话、传说中都能找到最早的踪迹。而对于黎族女子来说,“祖先识辨说”也是对其最具有威慑作用的说法。如冈田谦、尾高邦雄的《黎族三峒调查》中记录:“嫁到其它方言的女子,死后回娘家时,祖先要以其文身作为识别的标志。”[11]王国全在《黎族风情》中对“祖先”与女性文身的联系有更详细的描述:“未受文女性,死后祖宗不认,成为无家可归的‘鬼妇’……因此,死去时,必须在尸体的受纹部位用木炭划身后才入棺下葬,违者不得在公墓埋葬。”[12]46在女性文身的过程中,始终都有祖先鬼③黎族认为,人死后,其灵魂会变为“鬼”,并对血缘子孙的荣辱祸福,生死康健产生影响。因此黎族人遇事必祭拜各自隶属的“祖先鬼”。(王国全《黎族风情》,广东民族研究所1985年印,第117 页)的身影。文身前,“先由主文婆举行仪式,杀鸡摆酒设祭品,向祖先鬼报告受纹者的名字,求保佑平安”,文身后,“受纹者父母要摆宴请酒,庆祝祖先赐予受纹者美丽的容貌”。[12]51那么黎族的始祖是谁?与文身有何关系?又何以对女性的文身如此看重?这些问题一直缺少确切的材料,且牵涉广泛,杳渺难踪。但笔者从黎族的创世史诗《吞德剖》中却挖掘出一些可以侧面窥测个中因缘消息的黎族文化人类学材料。
“吞德剖”为黎语,意为“祖先歌”,“吞”为“歌”,“德剖”为“祖先”④黎族语言多数采用倒装句,翻成汉语时需倒过来翻译。《吞德剖》目前已被列入海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孙有康、李和弟在20 世纪80年代曾对其搜集整理,并以《五指山传》之名翻译出版。,是一代代黎族人口耳相传的诗歌,广泛流传在黎族地区。众多黎族神话传说如“三月三”、“纳加西拉鸟”等都能在《吞德剖》中找到最初的原型,是了解黎族历史的重要的材料。《吞德剖》全长1,544 行,共分“序歌”、“天狗下凡”、“五指参天”、“布谷传种”、“雷公传情”、“海边相遇”、“成家立业”、“男大当婚”、“分姓分支”和“尾歌”10 个部分。在《吞德剖》中,对黎族祖先和文身的介绍主要集中在前五部分,其主要情节如下:看守天庭厅阶的天狗①《吞德剖》的“天狗”和“婺女星”存在语义符号置换的可能,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另著文研究。爱上了天帝的女儿婺女星,在南蛇和蜂王的帮助下,与婺女星结为夫妻。二人下凡后,住在海南岛黎母山上,二人生了一男一女,儿子叫扎哈,女儿叫姆拉。有一天,天狗因年老体衰未变回人形被儿子扎哈误杀。之后,天崩地裂,天狗的身躯化成了海南的山川河流。婺女叫儿女寻求天帝的帮助。天帝命天人为姆拉绣面文身,并告诉扎哈,去人间找一绣面文身的姑娘,娶她为妻。由于天人的失误,将扎哈的母亲绣面文身。而姆拉贪恋天上美景,与哥哥错过,扎哈遇上绣面文身的母亲,并娶她为妻,生下阿寒阿弹姐弟俩。后天帝出面,令婺女星上天复归星位,并让绣面文身的妹妹姆拉替代了婺女星与扎哈在一起。姆拉不喜阿寒阿弹姐弟俩,总是折磨二人,后被毒蛇咬死。时天上有两个太阳,酷热难耐,姆拉叫扎哈射日。扎哈箭射日月后,日月破碎,惹怒天帝。天帝下令放天河之水淹没下界以示惩罚。婺女星得知化作一只天鸟飞临黎母山,告诉她的孩子阿寒和阿弹,洪水将要到来,只有躲进密封的葫芦里才能得救。阿寒阿弹与众多动物躲在密封的葫芦,躲过了洪水的劫难。大洪水之后,人间只剩下阿寒阿弹姐弟俩。这时,雷公出场,劝说阿寒阿弹姐弟俩结为夫妻,遭到拒绝,姐弟俩为此分开居住。于是雷公分别告诉他俩,在海边种田比在山里打猎要好过一些,并为阿寒纹了面。雷公叮嘱阿弹,海边有穿裙子的绣面女在等着他。姐弟俩离开黎母山南下到了海边,三月三那天,他们见面了,对歌之后,他们结为了夫妻,生下四个儿子,后分家立业,成为后世黎族四个支系。
剔去诗歌中的神话色彩,我们可以从《吞德剖》前五部分总结以下信息。
第一,文身是族外婚的标志。从《吞德剖》中,涉及两个氏族,一个是具有强大实力,被后人神话为“天人”的氏族,这里我们暂且称之为“天族”;另一支是天狗所代表的较弱的氏族,我们姑且称之为“天狗族”,天狗与婺女的结合可视为两个氏族的交融汇合。在两次文身事件中,黎族祖先看似借助文身达成了“母子”、“姐弟”的血缘婚姻,实际上,代表着黎族人对血缘婚的否定和族外婚的确立。在第一次文身事件中,“天人”对文身图案进行了解释:“细纹绣上脸,天云与飞烟,手上刺花草,刺痕蓝水填。花纹一片片,赫族的符签,天帝认得赫,绣成更志诚。天帝的令签,绣在姆拉面,配给琶扎哈,子女世代连。”[13]47从这段诗歌可见:首先,文身是“天族”的氏族标记,“天族”人凭此标记辨识族人;其次,文身还是氏族之间男女辨识是否可通婚的依据,不同氏族男女通过辨识诸如“天帝的令签”等可婚配的特殊符号,来确定对方是否可进行通婚。在《吞德剖》的叙事中,姆顿、姆拉、阿寒三人凭借这些符号完成了身份转换,使她们与扎哈、阿弹之间的关系由血缘亲人转变为外人,创造了可婚配的条件。而“吞德剖”第六部分“成家立业”中明确警示了血缘婚对后代繁衍的严重影响:“原是姐与弟,阿弹娶做妻,纵使不相识,毕竟不适宜。不知年与日,两人没儿女,前人劝后世,勿娶亲姊妹。”[13]121这段话进一步确立了文身作为非血缘氏族通婚的标记。
第二,文身只在女性世系中传递。无论是《吞德剖》的记载还是后世的调查,都显示,文身只在女性世系中传递,男性被排斥在外。从婺女到姆拉再到阿弹,三人均是直系血亲女性。而为她们文身的人也均是来自母族——“天族”的“天人”、“雷公”。这传统在后世的黎族调查资料得到印证:“文身的工作都由上了年纪的有经验的妇女担任。多是被文者的亲戚,如祖母、母亲、姐姐、姑母、姨母等担任。”[15]“妇女纹身是本族女性的内事,男性不得参与,更不许偷看。”[12]52这条信息大致可推定,文身产生之时的海南氏族,无论是“天族”还是“天狗族”,有可能处于母系社会时期。摩尔根认为,当“一个处于原始阶段的氏族,包括一位假定的女性始祖、她的子女、她的女儿的子女、以及世世代代由女性下传的一切女性后裔的子女。至于这位女性始祖的儿子的子女以及由男性下传的一切男性后裔的子女,则均被摈斥在本氏族之外”时,该氏族属于母系氏族。[16]作为只在女性世系中传递的族外婚制度,文身所保证的氏族血缘之链,显然是以女性为主线而发展传递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天帝”、“天狗”或许是后世对身份不明的父系祖先的神话想象。而“婺女”的身份和地位不仅是母族力量的彰显,也代表当时女性在氏族中的地位。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假设,文身是母系时期由黎族祖先创设并主宰的一种族外婚制度。涂尔干认为这是母系氏族的普遍特征,“只要家庭与氏族相混融,特别是和母系氏族相混融,那么,性禁忌就会完全地或者是基本上用在母系亲属身上”[17]。但对于黎族女性而言,文身对她们的意义并不只意味着性禁忌。当黎族女子文身后,意味着其生死都与出生氏族紧密相连:“黎族已婚女子得病或难产,必须由母家杀牲以祀,请本氏族的‘鬼公’出面‘做鬼’求恕,祈求娘家血缘的‘祖先鬼’念起骨肉之情,领受贡品,接受子孙祭奠,解恶除邪,使其转危为安。若病危或亡故,必须抬回娘家,葬在娘家公共墓地,并将其作为娘家家族的‘祖先鬼’加以崇拜。”[18]这意味着,黎族女子婚后可以不必“从夫”,享有一定的自主权,尤其是经济上的自主权,如婚后可以拥有自己的私人财产,夫亡返落娘家或改嫁随身带走。[18]而对氏族来说,文身的女性不仅保证了后代的质量,也扩大了氏族的外援力量。泰勒认为:“外婚制凭借氏族间不断的结合,促使一个成长扩展的部落保持自身的巩固,使它能够胜过任何孤立无援的小型内婚群体。”[19]在《吞德剖》的叙事中,文身将黎族与“天族”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关系使得“天族”在黎族面临危机之时一次次伸出援手,助其渡过危机,使黎族得以幸存、发展和壮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身的承载者——女性是氏族之间最牢固的联盟。
文身对氏族的重要意义使得黎族对女性格外重视。不仅将其发展成“不文身不归宗”的铁律,并将文身视为黎族女性“成年”的标记,“绣面乃其吉礼。女年将及笄,置酒会亲属女伴,自施针笔,涅为极细虫蛾花卉,而以淡粟纹遍其余地,谓之绣面女”(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相反,男性则没有如此隆重的成年礼,即使某些支系有男性文身,也未见有为男性举行文身仪式的记载。这些举措无疑给文身添上宗教式的色彩。黎族女性通过这些仪式,完成神圣转变,成为氏族的守护者,也获得了在族中令人钦敬的地位和实权。后世的记载和调查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如宋代有些地区峒首就由女性担当,“王二娘者,黎之酋也,夫之名不闻,家饶于财,善用其众力,能制服群黎,朝廷赐封宜人。琼管有令于黎峒,王宜人,无不帖然。二娘死,女亦能继其业”(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到清代,女性在族中依然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峒溪织记》、《琼崖黎岐风俗图》都曾记载,当黎族内部发生纠纷时,只要当女性出面干涉调解时,即可偃旗息鼓:“(黎人)恒兴兵报先世之仇,敌人若令其妻车前谢过,即曰:‘彼贤如此,可解此围’。或避之曰:‘彼惧我,可凯旋矣’。”(陆次云《峒溪纤记》)“黎人习气彪悍,与其同类一言不合,持弓矢标枪相向,有不可遏抑之势,若得妇人从中一间,则怡然而解。”(《琼黎一览·琼崖黎岐风俗图》)甚至在20 世纪50年代,保亭县“翁统打”地区毛枝峒和毛道峒发生械斗,械斗前和械斗和解时,仍然需要械斗双方的女性出面下战牒和主持和解仪式。[20]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母系社会的一种族外婚制度的设计,当文身被文到女性脸上时,意味着女性承担起保障氏族血统纯洁和繁衍生息的艰巨任务。黎族女性虽然为此付出了痛苦的代价,但也在族中获得了神圣地位。从这意义上来讲,文身成为黎族女性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文身与女性成年挂钩的做法、禁止男性在文身现场的规矩、以及女性“不文身不归宗”的铁律等,某种程度上都是为了保障女性对文身的独占权,并最终保障黎族女性在族中的地位。当进入父系社会后,尤其是中原儒家文化进入海南岛后,文身开始在父权(夫权)话语的侵蚀下,被解构和重新诠释,而黎族女性的角色形象和地位也在悄然改变。这种改变可以从“逃避外族掳掠”和“守节说”中折射出来。
三、“逃避外族掳掠说”和“守节说”中的贞节女性
对于文身的功能,另一种流行说法是“逃避外族掳掠”。此说最早见于周去非《岭外代答》(卷10):“海南黎女,以绣面为饰。盖黎女多美,昔尝为外人所窃,黎女有节者,涅面以砺俗,至今慕而效之。”刘咸①刘咸所搜集到的“部落争斗说”时间虽然指向上古,但该说法在黎族的神话、史诗中均未找到最初的痕迹。而赵全鹏认为,从该说法所反映的两性地位来看,这说法的出现应是黎族进入父系社会后所产生的(《黎族文身传说的发生与史学价值》,《海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5 期)。结合以上两点,笔者认为该说法应是进入父系社会后,文身女性地位下降后的一种现实阐释。铺说得更具体:“上古之时,族类相残,每俘掠妇女,载之俱归,为战利品。因此各族妇女,于将成年时,均黥面文身。族各有图识,所以免族类混淆,易于辨识,及去女子之美妍,藉免为俘虏,意盖两善。”[21]类似的变体还有“逃避官兵说”、“逃避皇帝说”、“逃避财主说”等。
由于文身赋予了黎族女性以神圣角色,以致黎族部落之间的争斗一般不牵扯女性,史载:“黎人善射好斗,积世之仇必报……其俗云:男子仇,只结于男子面上;若及妇女,则于其父母家更添仇怨矣。”(顾岕《海槎余录》)因此,“逃避外族掳掠”掠夺女性的“外族”更可能是黎族以外的民族。而一些文人的记载直接将矛头指向汉族。如三国时的薛综认为,罢弃珠崖郡的直接原因与当时官吏掠夺黎女的头发有关,他说:“汉时法宽,多自放恣,故数反违法。珠崖之废,起于长吏睹其好发,髡取为髲。”(陈寿《三国志》卷53)《林邑记》也记载说:“朱崖人多长发,汉时郡守贪残,缚妇女割头取发,由是叛乱,不复宾服。”(李昉《太平御览》卷373)汉人掠夺行为让黎族感受到的不仅是强大的武力,还有对女性尊严的践踏。这些都激起了黎族女性对汉人的恐惧。这种恐惧也反映到文身功能诠释中,如有文献记载:“或云不文面恐为汉人所娶。即汉人各居黎村者,欲娶黎女,女必以不出外地为要求。”(陈铭枢《海南岛志·人民·黎苗侾伎》)文身成为黎族女性忠于氏族、誓不离开本族的一种方式,女性的神圣性开始消解。
如果说汉人的武力掠夺行为只是让文身一举两用,尚未实质影响到文身女性角色形象,那么,中原统治者在海南岛长期实行的潜移默化的“兴文教、以化蛮俗”的教化举措,则显然进一步瓦解了黎族女性的神圣角色。
黎文化与汉文化最大的不同,就是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与汉族女性在婚姻中以夫为中心的被动角色不同,黎族女性则享有相当大的性自由和择偶权利。《三国志·吴书·薛综传》(卷53)载:“自臣昔客始自之时,珠崖除州县嫁娶,皆须八月引户,人民集会之时,男女自相可适,乃为夫妻,父母不能止。”又如《古今图书集成·广东黎人岐人部·旧志·岐人考》也有记载:“男女未配者,随意所适,交唱黎歌,既为婚姻。”另据方志载,婚后无子前,女方可选择“不落夫家”,“新妇至次日,始归宁,候有野胎方返夫家,或有不谐者,男女自由脱离”(《民国感恩县志》卷13《黎防志·黎情》)。这些习俗在中原统治者眼里均为需教化的“蛮俗”。明海南籍名臣丘濬曾为此专门制定了一套《家礼仪节》,强调了婚姻中的“六礼”,并被当地乡贤大力推广,成为当地所遵循的礼仪标准:“(琼山)俗敦礼仪,尚文公家礼。冠丧祭礼多用之,始自进士吴琦。及邱深庵著《家礼仪节》,故家士族益多化之,远及邻邑。”(《正德琼台志》卷7《风俗》)此外,官方也采取诸多措施推行中原婚俗礼仪,如明正德年间,徐琦知崖州,“教以婚丧礼。在崖九年,俗为之变”(周广《广东考古辑要·名宦》)。再如,明隆庆年间万州吏目陈宗圣“以山僻小民多沿黎俗,失夫妇之道。乃编立户口册,注写年岁,使皆以年齿相配……同时捐俸助之,人比之东汉任延”(《道光琼州府志》卷30《官师志二·宦绩中》)。在官方和民间的大力推广下,儒家礼仪开始在全岛普及,如:北部琼山县“冠婚丧祭遵文公家礼及邱文庄公濬仪节”(《康熙琼山县志》卷1《疆域志·风俗》);会同县“仪节,惟士大夫家尚,仿文公家礼”(《嘉庆会同县志》卷2《风俗》);定安地区婚俗也“仿六礼行之”(《光绪定安县志》卷1《风俗》)。在此大环境下,黎族婚俗也受到影响。
宋代,黎人并无繁缛的婚仪,只需“折箭而定”(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而至明清时期,婚俗开始有了变化。婚前,黎人男女虽仍可“自相谐偶”,但当关系确定后,男方必须通过一定的仪式向女方正式求婚,“若婚姻,仍用讲求,不以此也”,“至于议婚姻,不用年帖,只送槟榔而已”(顾岕《海槎余录》)。类似记载在张庆长《黎岐纪闻》里也有出现:黎族男女私订终身后,须“各回家告知父母,男家始请媒议婚”,议婚时“用牛为聘,或数头或数十头,随贫富议之”。婚后,尤其是落夫家后,对男女交往有着严格的禁忌,“既婚即不容有私,有则群黎杀之”。黎人婚俗的变化说明了以夫权为中心的婚姻制度在海南岛的确立,也意味着以父权、夫权为中心的氏族传承的建立和加强,文身女性的守护角色开始可有可无。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身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守节说”应运而生,“女将嫁,面上刺花纹,涅以靛,其花或宜或曲,各随其俗。盖夫家以花样予之,照样刺面上以为记,以示有配而不二也”(张庆长《黎歧纪闻》)。“又先受聘则绣手,临嫁先一夕乃绣面。其花样皆男家所与,以为记号,使之不得再嫁”(李调元《南越笔记》)。这两则记载明显看出文身的夫权转向,文身由母系世袭变成夫家、男家“赐予”,而文身的功能从血缘标识变成“不事二夫”的忠贞决心。这些都表明,文身女性身上的神圣光环已褪去,痛苦的成年礼仪式不再是其成为有担当的成年女性的独立宣言,而仅仅是作为夫家给予的已婚女性的标记,女性的神圣性和独立性受到侵蚀,成为依附于氏族和男性的卑属者。
另外,我们从“祖先识辨”说依然流传至今的事实可以看出,文身“守节”功能应主要发生在沿海一带如文昌、琼山、定安等汉化较深的“熟黎”①“生黎”“熟黎”之分始于明朝,当时统治者根据其汉化程度,是否服从管辖、愿意供赋役对黎族进行的划分,“黎有生、熟二种。生黎有名无姓,不受约束;熟黎慕化,服役稍同编民”(田汝成《炎缴纪闻.蛮夷》卷四)。因“生黎”多在山腹中,故屈大均也按居住地区来区分“生黎”“熟黎”:“黎有两种,五指山前居者为熟黎,山后为生黎。”(屈大均《广东新语·人语》),而山腹之地,如五指山、鹦歌岭等地的“生黎”仍坚守文身的本质,文身女性依然保持较高地位,上文索引的一些史料也显示了这一点。随着汉文化的影响和扩大,“熟黎”逐渐融入汉族,“悉输赋听役,与吾治百姓无异”(海瑞《海忠介公集》卷1《平黎疏》)。清道光年间,一些地区已黎汉不分,如澄迈县“虽有黎都之名,实无黎人之实”,文昌县出现“无黎”之说。连开发较晚的崖州黎也“饮食衣服与民人同。唯束发于顶,其俗未改。日往来城市中,有无相易,言语相通,间有读书识字者”(《道光琼州府志·村峒》)。在这种趋势之下,即使在深山中的“生黎”区,“祖先识辨说”也日益式微,而另一种符合现实背景的解释——“爱美说”悄然兴起。
四、美或不美:“爱美”背后迷失自我的女性
文身作为一种美的装饰,在文身诞生之初就已作为一种基本动机隐藏在文身图案的设计当中。刘咸曾如此描述过文身的美饰功用:“文身为装饰之动机,人类爱美,出于天性,女子尤甚。曾询黎女何以忍痛刺面,请求美观。试观各种文身图谱,多为几何图案,无不美观可取之处,吾人虽认定文身非为求美之动机但有美之元素存其中,则似无疑问。”[21]但文身的美饰作用在早先并未被大家所关注,早先的一些记载甚至认为黎女文面起初是为了遮美,如上文索引周去非《岭外代答》中的材料,同样的记载在陈铭枢的《海南岛志·人民·黎苗侾伎》也有出现:“文面之初,或起于惧为异族所得,故毁其颜,今则率以为美观矣。”(陈铭枢《海南岛志·人民·黎苗侾伎》)。屈大均则直接否认文身的美饰功能:“其绣面非以为美……世以为黎女以绣面为绝色。又以多绣为贵,良家之女方绣,婢媵不得绣,皆非也。”(屈大均《广东新语·人语》)这些说法,显示了早先文身作为一种美饰的功用,并不是黎族女性文身的主要目的。随着氏族父系传承的确立,文身女性作为氏族守护者角色逐渐减弱,文身与婚姻的联系日益凸显和加强时,作为一种美的装饰,尤其是作为一种能缔结好婚姻的象征,逐渐成为黎族女性忍受着这痛楚的针刺手术的主要动机。现代研究者的田野考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姚丽娟在田野考察时,当她问起黎族文身妇女为什么要文身时,多答“为了美”、“好看”[22]。苏丽萍则更详细地记录了黎族女子对于文身的渴望:“那些珠子、花、漂亮的服装,都要文脸后才能穿戴,不画脸没得佩戴这些美丽的饰物,所以我想:‘快点让我文脸吧,文了我就好看了’。”[23]20这些话充分显示了黎族女性将文身作为一种美的象征的想法。但经姚丽娟、苏丽萍她们进一步调查爱美的背后,发现“要美”,“要文身”是因为“不文身没有人要”[22],“文了可获得男子的追求,不文就嫁不出去”[23]20。当“不文没人要,不文嫁不出去”的想法成为一种共识时,意味着文身已彻底世俗化,成为一种女性取悦男性,获取男性喜爱的工具。下面这首民歌形象地反映了文身的这种功用:
情人啊,情人!
你为何不跟我对歌?
你是不是嫌我难看?
你是不是选中了那个脸蛋大大、头发长长的姑娘?
你是不是选中了那个文有机柕花纹的姑娘?
你是不是选中了那个文着象蛤蚧一样花纹的姑娘?
你是不是选中了那个腿上文有西瓜皮一样花纹的姑娘?
你是不是选中了那个耳后文着“龙凤花”的姑娘?
天旱时,你是否给她寄出做好的鱼茶?
五月时,你是否把打到的山猪肉做成喃杀寄给她?
砍黄藤时,你是否要把嫩嫩的一节送给她?
她要挖山薯时,你就寄出长长的铲子给她用。
她要吹笛时,你就把砍回的竹子做成竹笛送给她。
她要文身时,你就把墨条寄给她。[23]28
从这段民歌中,我们可以看出,文身与否以及文身的图案成为黎族女子受男性欢迎程度的关键因素。当文身成为取悦男性的行为时,文身女性对自己的认同也开始随着男性而摇摆,这种摇摆在黎区与外界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越发明显,苏丽萍的调查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当苏丽萍在调查现今黎人对文身的看法时,得到了截然相反的答案。有些人为文身感到自豪,认为是文了身才是女人,也会得到大家关注:“我一直以来都认为画脸好看,女的如果没有画脸,那就像男人一样了,怎么会好看?”,“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文身好看,你瞧我去北京,一上飞机,就很多人嚼里啪啦为我拍照”,“以前大家都抢着文,也都没人说文身不好看啊!我很喜欢文脸”。但更多的人开始认为文身不美,尤其是文身对婚姻有负面影响:“我老公以前在海口灵山那边当兵,我去部队探望他,很多士兵跑来看我,别的军嫂也问我干嘛要画脸,她们说我这样不好看。老公1960年从部队回到乡政府当干部后,他便嫌我有文脸,就对我不好了,但那时己不能离婚。现在我很后悔文了身,因为出门去哪里都会被人说不好看。”甚至连黎族男性也开始转变想法:“我不赞成文脸,本来白白净净的脸,文了黑乎乎的,不好看。”一个黎族男性如是说。[23]28-29
在这样的大趋势下,文身女性开始迷失。原先被当成神圣戒律、成年象征的文身,成为人们所评头论足的对象。美或不美,完全取决于社会,尤其是男性的眼光。当社会,尤其是男性普遍否定文身的价值时,她们也开始否定文身,甚至为了获得好的姻缘,选择以惨烈的方式去掉文身。苏丽萍的调查中有这么一位黎族女性,当她要嫁汉族人时,汉人以“可惜你是文脸的黎族”理由拒绝了她。为达成嫁汉族人意愿,她用一种极痛苦的方式去掉脸纹。苏丽萍详细记载了该种方式的具体过程:“先用米汤把脸上的纹线画好,后用白藤沿着米汤纹路打刺,直至流血,再用尖锐的小刀刮纹线。”[23]58从该过程我们充分感受到这位黎族女性对于去除文身的决心。当文身女性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宣告其对文身的决绝时,也决定了文身最终消亡的命运。
至此,纵观文身诸说发生轨迹,以女性角色形象变化为主线,我们发现,从“祖先识辨”到“逃避外族掳掠”、“守节”至“爱美说”,文身女性的角色形象不断在发生改变,这改变是与黎族社会父权不断加强、母权不断削弱有关。在“祖先鬼”说中,文身作为一种母系时期产生并延续下来的保障氏族血缘和生存的制度设计,给予了文身女子以神圣的角色和地位,使其在族中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但随着中原儒家文化的北风南进,其文化中父(夫)权为中心的思想冲击和影响着黎族社会,使黎族社会的父权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文身开始被父系话语重新诠释和解读,“逃避外族掳掠说”和“守节说”就此产生。在重新诠释的过程中,文身的宗教性和神圣性不断被削弱,文身女子也不断被世俗化,由氏族守护者变成需要氏族和男性守护的卑属者,最终文身成为黎族女性取悦于男性的一种装饰。随着黎族与外界交流的增多,作为一种装饰的文身,被社会尤其是男性世界否定时,黎族女性也开始否定文身,甚至否定文身后的自己。这种否定标志着以文身为代表的维系黎族女性地位的母系文化残余在父权(夫权)为中心的大背景下,将消解、退散,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1]彭华.百越文身习俗新探[J].宜宾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1).
[2]焦勇勤,孙海兰.略论黎族妇女文身的起源[J].中州大学学报,2006(4).
[3]欧阳洁,孙绍先.黎族文身诸说析疑[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
[4]郑小枚.论黎族文身的伦理隐喻[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
[5]赵全鹏.黎族文身传说的发生与史学价值[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5).
[6]王献军.汉文古籍中的黎族文身史料分析[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2).
[7]王献军.黎汉文化的冲撞——黎族文身的“被禁止”与“被终止”[J].贵州民族研究,2011(6).
[8]Henrietta L.Moore.Feminism and Anthropology[M].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8.
[9]白志红.早期人类学研究中女性的在场与缺席[J].云南社会科学,2005(6).
[10]禹燕.女性人类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11]〔日〕冈田谦,尾高邦雄.黎族三峒调查[M].金山,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38.
[12]王国全.黎族风情[M].广州:广东省民族研究所,1985.
[13]孙有康,李和弟,搜集整理.黎族创世史诗——五指山传[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80.
[14]郝思德,王大新.海南考古的回顾与展望[J].考古,2003(4).
[15]王学萍.中国黎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246.
[16]〔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下)[M].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41-342.
[17]爱弥尔·涂尔干.乱伦禁忌及其起源[M].汲吉吉,付德根,渠东,译.梅非,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61.
[18]符和积.黎族“不落夫家”婚俗浅析[J].社会科学战线,1988(2).
[19]R·M·基辛.文化·社会·个人.[M].甘华鸣,陈芳,甘黎明,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267.
[20]《黎族简史》编写组.黎族简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23.
[21]刘咸.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C]∥詹慈,编.黎族研究参考资料选集:第一辑.广州: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编印,1983:233.
[22]姚丽娟.海南岛黎族妇女文身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23]苏丽萍.独特的历史遗痕——海南省昌江县黎族文身口述史研究[D].海口:海南师范大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