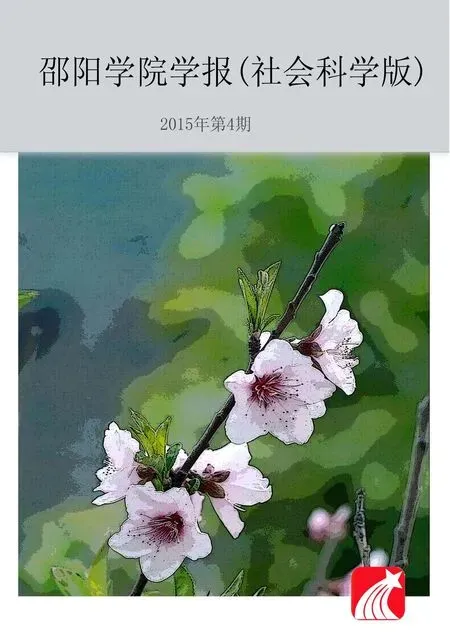对革命的中性艺术叙事
——试论巴别尔的《骑兵军》
○曾思艺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387)
对革命的中性艺术叙事
——试论巴别尔的《骑兵军》
○曾思艺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387)
巴别尔的《骑兵军》主要从六个方面客观真实地描写了革命军人形象,既写出了他们的骁勇善战,也写出了他们的缺点与不足,并隐隐表达了自己矛盾复杂的心绪,从而在俄罗斯文学史上较早地真实塑造了革命军人的形象,是对革命的一种中性艺术叙事。
巴别尔; 《骑兵军》; 中性叙事
巴别尔的代表作《骑兵军》是俄国现代文学的著名经典作品,在世界各国享有颇高的声誉。但这部经典作品却曾波澜突起,其成书也有一个过程。
1924年,《红色处女地》、《列夫》、《俄罗斯现代人》等莫斯科杂志相继发表了巴别尔一系列描写骑兵军的小说,共30多篇,这些作品使他一举成名。1924年10月,《真理报》发表评论,称巴别尔为苏联文学“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就连一向态度粗暴的“拉普”评论家也对《骑兵军》青眼有加,列列维奇在《在岗位上》杂志1924年第1期发表文章,宣称在巴别尔之前,“还没有人在文艺作品里如此描绘过布琼尼的战士们的那种英雄主义,天生的革命性,以及哥萨克放荡不羁的游击习气”,称赞巴别尔的艺术才能,认为他“具有惊人的简洁,善于三言两语勾出完整的形象,新颖独特,内容与形式完全一致,语言无与伦比,生动形象,表现力强”,并且断言:“《骑兵军》将永远是真实的而非臆造的革命性的典范。”[1](P249-250)1926年,这些作品结集出版,定名为《骑兵军》。不过,《骑兵军》得到的不光是赞扬,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就是20世纪20年代苏联文坛上波澜突起且轰动一时的“元帅与文豪之争”,即骑兵军统帅布琼尼与大文豪高尔基之间的公开争论。
布琼尼在《十月》杂志1924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指责巴别尔描写的不是骑兵军,而是真正的马赫诺匪帮,巴别尔诬蔑和诽谤骑兵军,这样写红军的人只可能是白卫军和明显的阶级敌人,他还指出:“小说作者使用‘骑兵军’这样响亮的名字,目的显然是要唬人,使读者相信过时的谎言,即我们的革命是由一小撮匪徒和无耻的篡权者搞出来的。”这当即遭到沃隆斯基等一批有声望的评论家的反驳,高尔基更是多年来一直维护巴别尔、反驳布琼尼。他在1924—1928年这五年里与许多作家通信,热情地称赞巴别尔的《骑兵军》,坚决驳斥布琼尼的指责,认为像《骑兵军》这样的作品是不能“站在马的高度”来批评的。1928年9月30日,高尔基在《真理报》和《消息报》发表了《向工农通讯员和军队通讯员谈谈我是怎样学习写作的》,其中谈到:“布琼尼同志已经攻击了巴别尔的《骑兵军》,而我不觉得他该这么干,因为布琼尼自己不但喜欢装饰他的战士们的外貌,而且也喜欢打扮他的马匹的外表。而巴别尔则美化了他的战士们的内心……人在很多方面还是野兽,而且在文化上,他还是一个少年,因此去赞美和美化他往往对他很有益。”布琼尼不服,在同年10月26日《真理报》上发表了《致马·高尔基的公开信》,首先承认在文学问题上自己无法与高尔基争辩,但自己攻击巴别尔的《骑兵军》是有道理的,因为巴别尔对骑兵军的描述,“只是发挥了老女人们的闲话,翻掘了老女人们的垃圾堆,然后带着恐惧散布什么红色战士拿人家的面包和鸡的谣言,他发明了从没发生过的事情,朝我们最优秀的共产党指挥员身上栽赃,听任自己肆无忌惮地瞎编烂造,简直就是扯谎”,更为重要的是,“巴别尔小说的主题被这个有色情狂的作者的主观感觉扭曲了。他讲的故事从一个疯子犹太人的胡言乱语,到对天主教堂的打砸抢,到骑兵军鞭打自己的步兵,到一个有梅毒的红军战士的肖像,而以展现作者的科学好奇心结束,此时的他想看看一个被十名马赫诺的人强奸过的犹太女人是什么样的。正像他把生活当成有女人和马匹在那儿走动的五月的牧场,他也这样看待骑兵军的行动,而且,他是通过色情的棱镜看的”。高尔基在11月27日的《真理报》发表《答谢·布琼尼》,一方面坚决抗议布琼尼的不公正评价,一方面回答了他涉及的问题:“你谈到巴别尔是色情狂。我刚重读完巴别尔的书,我却没能在书中找到此病的症状,不过,当然了,我不想去否认他故事中某些情色细节的存在。而这是原本应当如此的。战争总是唤醒一种勃发的情欲。……我倾向于认为它是一种天然的,尽管也是反常的,对偷生保种的本能的强化,这种本能在面临死亡的人群中是常见的。”“我是一个细心的读者,但我没能在巴别尔的书中找到任何看上去像‘挖苦’的东西。相反,他的书把红色骑兵军战士们展示成真正的英雄——他们无所畏惧,并且深切地体会到他们事业的伟大,这唤醒了我对他们的爱和尊重。我不知道还有比这更多彩、更生动的对各具特色的战士的塑造,我也想不出,还有谁对红军整体心理的描绘更能让我懂得那完成非凡战斗的力量,这在俄罗斯文学里真是无与伦比的。……巴别尔以这样的高才深化了我对一支军队的英雄主义的理解,这支军队是有史以来第一支知道它现在以及将来为何而战的军队。”而布琼尼批评中“粗鲁而有失公正的口吻”使一个年轻作家蒙受了“不白之冤”。高尔基呼吁在这转折时期,更应该爱护像巴别尔这样本来就少的有才华的青年作家,“更不能践踏这些有才华而有益的人”。[2](P295-300)
这场突起的波澜——布琼尼的指责使巴别尔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创作热情受到了很大的抑制,《骑兵军》他原计划写50篇,但被迫中止,此后,他也只是出版了此前创作的短篇小说集《敖德萨的故事》(1931),创作了几个零星的短篇小说(如《但丁街》、《格拉苏》)、未完成的小说《巨井》以及两个剧本《霞》(亦译《日落》,1928)、《玛丽亚》(1938)。
《骑兵军》最初的版本包括34篇作品,作家生前再版时又增加了补写的《千里马》,死后再版时再增入补写的《吻》和此前写的《格里休克》、《他们曾经九个》。因此,我国出版的《骑兵军》,由于所据版本不同,收入篇目也有所不同:戴骢所译共35篇,孙越、傅仲选所译则是36篇,现把篇名罗列如下(前面为戴译,括号中是孙译、傅译,相同者不重复):《泅渡兹勃鲁契河》(《渡过兹布鲁齐河》、《横渡兹布鲁奇河》)、《诺沃格拉德的天主教堂》(《诺沃格拉德的天主教堂》、《新城的天主教堂》)、《家书》(《一封家信》、《家信》)、《战马后备处主任》(《军需主任》、《军马储备局局长》)、《潘·阿波廖克》(《阿波廖克先生》、《阿波列克先生》)、《意大利的太阳》(《意大利的太阳》)、《基大利》(《格达利》)、《我的第一只鹅》(《我的第一只鹅》)、《拉比》(《经师》、《拉比》)、《通往布罗德之路》(《通往勃罗德的道路》、《通往布罗德之路》)、《机枪车学》(《话说敞篷马车》、《闲话敞篷马车》)、《多尔古绍夫之死》(《多尔古绍夫之死》)、《二旅旅长》(《第二旅旅长》)、《萨什卡·基督》(《萨什卡·耶稣》、《萨什卡基督》)、《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科传略》(《帕弗利钦科,马特韦依·罗焦内奇的一生》、《帕夫利琴科,马特维·罗季奥内奇传》)、《科齐纳的墓葬地》(《科济纳的墓地》、《科津墓地》)、《普里绍帕》(《普利谢巴》、《普里谢帕》)、《一匹马的故事》(《一匹马的故事》)、《政委康金》(《康金休息地》、《休息地》)、《小城别列斯捷奇科》(《别列斯坚科》、《别列斯捷奇科》)、《盐》(《盐》)、《夜》(《夜晚》、《傍晚》)、《阿弗尼卡·比达》(《阿丰卡·比达》)、《在圣瓦伦廷教堂》(《在圣·瓦连特教堂》、《在圣徒瓦连特圣骨匣旁》)、《骑兵连长特隆诺夫》(《骑兵连长特龙诺夫》、《骑兵连长特鲁诺夫》)、《两个叫伊凡的人》(《两个叫伊万的人》、《两个伊万》)、《一匹马的故事续篇》(《一匹马的故事(续篇)》、《续一匹马的故事》)、《寡妇》(《寡妇》)、《札莫希奇市》(《扎莫希奇》)、《叛变》(《叛变》)、《契斯尼基村》(《切斯尼基村》)、《战斗之后》(《战斗之后》)、《歌谣》(《歌声》、《歌曲》)、《拉比之子》(《经师之子》、《拉比之子》)、《千里马》(《骏马》、《阿尔加马克》),孙越和傅仲选译本多了一篇《吻》。王若行翻译的《骑兵军日记》在《骑兵军》补遗里则补足了遗漏的三篇,并且说明:“《格里休克》和《他们曾经九个》写于一九二三年之前,前者曾发表于敖德萨当地报刊,后者似乎未在作者生前发表,手稿亦为М.Я.奥弗鲁茨卡娅所保存;《吻》则刊载于《红色处女地》杂志一九三七年第七期。以上三篇增补进作家身后再版的《骑兵军》里。现有的三种中译《骑兵军》,孙越、傅仲选译本均未收《格里休克》和《他们曾经九个》,戴骢译本则三篇皆无。此次特为译出,以飨热爱《骑兵军》的中国读者。”[3](P223)至此,《骑兵军》全部38篇作品都翻译成了中文。
在苏联文学史上,曾经把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1923)、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1924)、法捷耶夫的《毁灭》(1927)称为三大国内战争史诗。与这三部作品完全从正面歌颂革命,塑造正面的革命英雄形象不同,巴别尔更客观真实地描写了革命军人形象,既写出了他们的骁勇善战,也写出了他们的缺点与不足,并隐隐表达了自己矛盾复杂的心绪,从而在俄罗斯文学史上较早地真实塑造了革命军人的形象,也使他对革命的叙事成为一种中性的艺术叙事。
纵观《骑兵军》38篇,这些作品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是描写骑兵军的机智英勇。《机枪车学》写骑兵军把普通的无蓬轻便马车巧妙地改造成威力无穷的机枪车;《二旅旅长》写新提拔的二旅旅长科列斯尼科夫在战场上英勇杀敌;《政委康金》写康金仅仅两人,却勇战八个敌人,并且获得了胜利。
二是描写知识分子在骑兵军中的改变。《骑兵军》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写“我”——彼得堡大学法学副博士,“一位在俄国寂寞无名的年轻作家基里尔·柳托夫,遵照政治部的派遣从敖德萨赶来”,[3](P3)参加骑兵军对波兰的战事——在骑兵军中的改变,不止一次地采取趋同于战士们的行为。《我的第一只鹅》中,“我”架着眼镜,到骑兵军后受到战士们的蔑视与嘲笑,于是“我”利用向女房东——一位老太婆要吃的的机会,向他们表示“我”向他们的趋同:当老太婆说没有吃的时,“我”当胸给了她一拳,并且操起一把别人的马刀,一个箭步把在院子里踱着方步的鹅踩在脚下,然后用马刀拨弄着鹅,喝令女房东“把这鹅给我烤一烤”,从而赢得了战士们的好感,“这小子跟咱们还合得来”。在《札莫希奇市》中,“我”甚至放火烧另一位女房东的房子。《多尔古绍夫之死》写“我”不愿答应身负重伤、又深陷敌人重围中的战友多尔古绍夫开枪打死自己的请求,而排长阿弗尼卡在斥骂“你们这些四眼狗,可怜我们兄弟就像猫可怜耗子”后,开枪打死了他。“我”因此而深受教育,知道了在特殊情况下,什么是真正的仁慈。《千里马》中,“我”驾驭不了千里马,也无法与千里马的主人——红军战士吉洪莫洛夫达成和解,但“千里马教会了我吉洪莫洛夫的骑式”,这使“哥萨克们不再在我身后不以为然地望着我和我的马”。因此,马克·斯洛宁指出:“这个敏感的知识分子同凶暴的骑兵之间的冲突以及最后取得和解的情节构成了《红色骑兵》(即《骑兵军》——引者)中的两个主题之一。”[4](P68-69)
三是描写骑兵军存在的问题。《战马后备处主任》写骑兵军强要去庄稼汉的好马,而把累坏了的、不能做事的马交换给他们;《意大利的太阳》中西多罗夫不愿打战,只想脱离军队去意大利享受那里的太阳;《一匹马的故事》写师长萨维茨基仗势夺取了骑兵连连长赫列勃尼科夫心爱的坐骑——一匹白色的公马,致使他一怒之下复员退伍;《在圣瓦伦廷教堂》描写了骑兵军战士对当地民众宗教信仰的不尊重;《骑兵连长特隆诺夫》既描写了特隆诺夫的英勇,也写了他残杀俘虏的事情;《他们曾经九个》也描写工人出身的排长格罗夫残杀了九个俘虏;《契斯尼基村》则描写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伏罗希洛夫不等配合部队到来,便下令向敌人进攻,结果导致失败。马克·斯洛宁指出,《骑兵军》的“另一个主题是残酷无情的‘革命士兵’和他们的尽管含糊不清却是理想主义的愿望之间的矛盾。巴别尔以精炼的,常常近似心理自然主义的手法讲述人们身上那种非人的因素。他那些狂暴好斗的伙伴不仅蔑视他的温顺,还认为他们自己是平等和美好的生活的热情倡导者。他们的刀剑随着战斗口号‘乌拉,世界革命’而左右飞舞。他们愿为这个口号而死,但在临死时还满口秽语或低级的戏谑语。杀人对他们说来只不过是家常便饭。在白俄罗斯一个遭到洗劫的村庄里,在一堆堆被波兰人在撤退时剖开肚子的老人和孕妇的尸体中……一位哥萨克红军,在割断一个被指控为间谍的犹太老人的喉管……一个年轻哥萨克阿方基·毕达(即阿丰卡·比达——引者)为了替他一匹在战斗中死去的爱马报仇,他纵火烧毁了波兰人的村庄,枪杀老人,抢劫农民。中尉特鲁诺夫(即骑兵连长特隆诺夫——引者)把他的马刀戳进战俘的咽喉,或者用冲锋枪把他们的脑壳打开花……”[4](P69)
四是写革命与反革命间的斗争。这里有不同阶级间的斗争,如《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科传略》写牧童出身的将军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科用脚活活踩死了地主老爷尼基京斯基而走上革命道路;还有亲人之间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而激烈搏杀,如《家书》写父子之间因在不同阵营而相互残杀:父亲是白军连长,凶残地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红军战士费奥多尔,他的另一位红军儿子谢苗为替兄弟报仇,拼命追捕父亲,抓住父亲以后,杀死了他。
五是写骑兵军战士的人性欲望和独特个性。《夜》、《寡妇》等写了骑兵军战士对女性的正常欲望;《阿弗尼卡·比达》的主人公阿弗尼卡在战斗中痛失爱马,离开部队,四处找马,甚至穷凶极恶地打家劫舍,最后找到了一匹魁梧雄伟的公马;《歌谣》既写了“我”为了吃的对女房东——一位很穷的寡妇进行恫吓,又写了民间歌谣的巨大力量,还写了萨什卡对女房东的情欲;《千里马》则表现了吉洪莫洛夫等骑兵军战士对战马的深挚感情——竟然因为“我”没有善待战马而准备揍扁“我”,甚至要杀死“我”。
六是描写了骑兵军各宿营地的民众困境和地方风情。这部分作品主要描写民众生活的穷困与苦难,如《泅渡兹勃鲁契河》,描写了诺沃格拉德市犹太人的生活:怀孕的女人由于战乱和贫穷,用“两条骨瘦如柴的腿,支着她的大肚子”,她的父亲被波兰人活活杀死,家里“几个柜子全给兜底翻过,好几件女式皮袄撕成了破布片,撂得一地都是,地上还有人粪和瓷器的碎片,这都是犹太人视为至宝的瓷器,每年过逾越节才拿出来用一次”;[5](P2)《基大利》则写了当地犹太人基大利发现革命和反革命同样朝他们开枪,人们只能“就着火药吞食”共产国际,“用最新鲜的血当佐料”,因此深感困惑:“谁又能告诉基大利,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别何在?”[5](P28-29)《札莫希奇市》既写了波兰人屠杀犹太人,又写了骑兵军战士用放火的方式逼迫当地农村老太婆拿出仅有的牛奶和面包。与此同时,小说也介绍了当地的风俗民情乃至艺术,这类作品有《诺沃格拉德的天主教堂》、《科齐纳的墓葬地》、《小城别列斯捷奇科》、《潘·阿波廖克》、《拉比之子》等。
综上所述,《骑兵军》既歌颂革命赞扬红军战士,描写他们的英勇作战,机智勇敢,不怕牺牲,也写他们正常的人性欲望和独特的个性,也写骑兵军存在的问题、红军战士的缺点及过火的行动,从而写出了真实可信、栩栩如生的鲜活的骑兵军形象,也充分体现了对革命的中性叙事。
[1]李明滨主编.俄罗斯二十世纪非主潮文学[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
[2]王天兵.哥萨克的末日[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
[3](俄)巴别尔.骑兵军日记[M].王若行,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4](美)马克·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1917—1977)[M].浦立民,刘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5](俄)巴别尔.骑兵军[M].戴骢,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A Neutral Narrative Art on Revolution——An Analysis on Babel’s The Red Cavalry
ZENG Si-y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Babel’sTheRedCavalrydescribes objectively and authentically the images of revolutionary soldiers from six aspects. He not only portrays their bravery and fierceness, but also their shortcomings and deficiencies. At the same time he faintly expresses his complex and contracted feelings. Through his writing, the images of revolutionary soldiers were early established authentically in the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It is a neutral narrative art on revolution.
Babel;TheRedCavalry; Neutral Narrative
2015-06-20
曾思艺(1962— ),男,湖南邵阳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
I106.4
A
1672—1012(2015)04—0116—05
——献给第一线的交警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