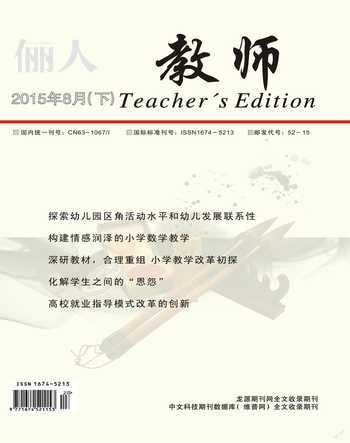无罪的孽子
张逸龙
【摘要】在世界范围内一段时间以来,同性恋现象不仅在宗教上被“定罪”,同时在法律上被“定罪”,甚至在医学上也被“定性”。然而回溯过去,我们发现同性恋现象在人类历史中早已存在,同性恋现象从自然现象到变成一种罪恶和一种疾病,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梳理同性恋现象的污化及其正常化的过程,将使我们以一种更加理性的态度来对待这一人类社会现象及人类群体。
【关键词】同性恋 建构 制度
1943年,海因里希·希莱姆向集中营发出通知:集中营里的同性恋者,凡是愿意接受阉割手术者,可以回家。……在集中营里,大批同性恋者犯人主动接受手术。不过,手术做过之后,他们就被送往俄国前线战场去了。
——《不该被遗忘的人们——“二战”时期欧洲的同性恋者》
一
这是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街头,无所归依的孩子们。他们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他们疑惑,他们迷惘,他们四周寻找着自己的同类,依偎在一起,黑夜里寂寞得发狂。同性恋者,他们自然的一切,在异性恋者眼里成为异常、扭曲与变态,甚至被贴上罪恶的标签。事实上,性在被证实无罪之前总是被假定有罪。
二
罪孽,同性之爱为何罪孽深重,罪孽来自于何方?
基督教认为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罪恶,只有在婚内以生殖为目的的性和不追求快感的性,才有可能赎罪。在伊斯兰教中,《古兰经》亦多次苛责这种同性之爱。不同于西方禁忌,中国古代对同性恋持着一种宽松的态度,且不说古大夫有娈童之癖,喜慕男风更是多有史书记载,其中西汉更有汉哀帝为男宠董贤断袖之谈。直到1903年大清刑律修订之时,中国法律才对同性恋摆脱暧昧状态,有了明确条文:“至于鸡奸一项,自唐至明迄无明文,既揆诸泰西各国刑法……故本案采其意,赅于猥亵行为之内,而不与妇女并论。”随后,民国法律斥之有伤风化,新中国成立后,文革期间鸡奸者一律按强奸犯处理直接枪毙,待到1973年流氓罪对同性恋者模糊入法,1997年刑法废除流氓罪才标志着中国同性恋者的非罪化。
性的本质主义认为,性是自然的力量、先于社会而存在并造就制度。然而,当一遍又一遍既定的观点写入我们的大脑,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是否就是真实的认知?抑或是我们本身就是一张空白的磁盘,在被一遍一遍地写入写满最后只剩读取却没了思考的空间?
相反,在福柯提出的建构论中,“欲望并不是一种先验存在的生理实体,而是在特殊的社会实践中被历史地构建起来的”,肛交本来只是一种宗教禁忌和违禁行为,但我们并未规定违规主体的身份,然而在历史的演变中,同性恋者慢慢地从一种宗教批判对象,发展成违法罪犯,再变成神经或生理错乱者,最后成为一种角色、一种案例和一种历史。 从喜好男风,到同性恋入法,到处死同性恋者,再到模糊入法和废除刑罚,无疑,中国同性恋也经历了一个建构的过程。
神性的道德,制度的大厦啊。荒谬的是,人创造了制度,制度却压迫着人。
三
宗教罪孽论、法律犯罪论和医学病态论常作为反对同性恋的三大观点。 作为一种存在了几千年的文化,同性恋未影响到人类的繁衍生存,并不反自然(反同性恋者用反自然一说攻击同性恋者,事实上,自然界动物亦存在同性行为);作为一种平等自愿的恋爱关系,同性之爱不对第三方造成任何伤害,同性恋者不存在任何道德的瑕疵;作为一种天生的性心理倾向(1973年美国心理协会、美国精神医学会将同性恋行为自疾病系统分类去除;2001年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把“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单中删除),同性恋者和你我一样是一个正常的人。
法国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在《乱伦禁忌其起源》一书中,意外地发现乱伦禁忌源于部落氏族的外婚制,而外婚制的源头又在于对血的恐惧和对氏族图腾的敬畏,“我们现在禁止乱伦的名义是其为道德所不容,但是,这种与道德的不相容性本身却是这种禁忌的一个后果。”
多么悲哀的事情,我们把后天的习性当做天生的本能,我们把人为的构建当做是先知的预判。在我们的认知中,性与社会性别相等同,女性与男性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这异性恋的社会统治着同性恋者,并多少有些阴险地把他们引向死亡之地。”(萨特)一旦我们发现了男性的躯体里有女性化的灵魂或女性的躯体里有了男性化的灵魂,我们感到惊恐,单一的思维无法容纳多元的性——这破坏者、越轨者、异常者,我们向所谓“罪人”高高举起的磐石,最终砸向的是我们自己,砸向“人”自己。
主的话语仿若还在耳边:“你们当中谁是无罪的,谁就可以砸她。”
四
1870年,德国法律175条释法同性行为将被判刑 ,而到了1934年臭名昭著的175条例中的“将被判刑”则更是被纳粹改为“剥夺公民权”,此后的11年里,十多万的欧洲同性恋者成为纳粹的牺牲品。二战后,美国受麦卡锡主义影响,右翼意识形态将非常态性活动与共产主义及政治软弱性相关联,政府和军队中大批同性恋者被辞退。
无疑,劳动生产物质资料,两性结合使人类得以再生产,这两种生产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先决条件和真正起点。 异性恋(并且也理应作为)作为社会的性霸权,从维持物种生存繁衍生存的本能出发,由异性恋主体构成的社会会自觉不自觉地排挤甚至于想要消灭同性恋,物尽天择的自然残暴从未消失过。但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在残暴面前仍可坚守良知,在苦难之中仍能怀抱希望。
1990年,德国废除反同性恋法,议会正式向当初的同性恋受害者道歉并赔偿。2012年,美国已有九个州正式承认同性恋婚姻。
五
斷背山上的青年终会离开,会试图融入常人的生活,会拥有家室。但彼此最为怀念的,仍是断背山。多年过去,恩尼斯收到杰克的噩耗,他的脑海里立马闪过同性恋者被虐杀的画面。影片结束时,恩尼斯把杰克的衬衫包在自己衬衫的里面就像是怀抱,说了句:我发誓……他的眼里已噙满了泪水,画面里干净的琶音响起。那时,似乎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
他们曾被唾弃、他们曾被判刑、他们曾遭虐杀甚至毁灭,他们曾是政客转移社会不满的替罪羔羊曾是道德激愤的泄洪口,或许迫于压力他们也会结婚生子,然后缄默,一辈子。
“我们为何不忠于自己最真的情感呢?”
当我问起上课的教授对同性恋的看法时,教授引用了一位女学生对她说过的话。
时代可以宣判他们有罪,但爱本无罪。
参考文献
[1]艾小娥《同性恋在中国法律规制缺位之思考》,《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17期
[2]葛尔·罗宾《酷儿理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