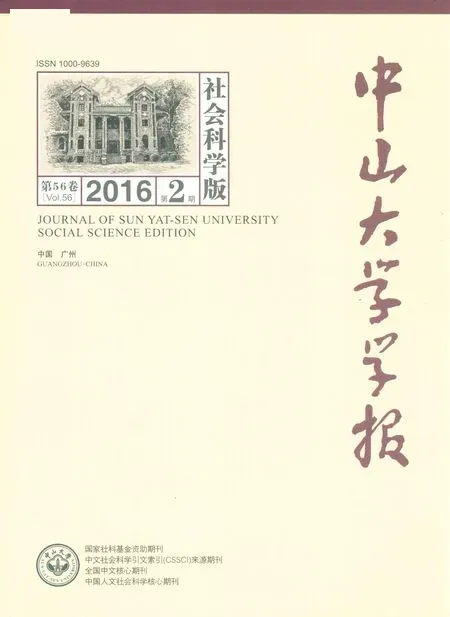向先圣祈祷*——比较宗教学视域下的朱熹“祝告先圣”
张 清 江
向先圣祈祷*
——比较宗教学视域下的朱熹“祝告先圣”
张 清 江
摘要:向先圣祈祷是朱熹生活中的重要行为,朱子文集中保留了很多朱熹在祭孔仪式上向先圣祈祷的祝文。在朱熹看来,祈祷是个体情感的恰当表达,也是通过“悔过迁善”走向生命改变的切实行动。他将先圣看作自身生命效法的原型和指引,在祝告时不断祈求与先圣之灵的感通和交流,以此通过遭遇“先圣”回向自身。对朱熹来说,祝告先圣的精神性意义在于,它是自身默想圣贤人格并向着圣人方向前进的重要方式。从比较宗教学的视角来看,朱熹这一行为真正体现着宗教祈祷的本真性意义,因为祈祷的本质在于祈祷者在跟神圣对象的相遇和交谈中实现心灵的改变和转化。朱熹从“祝告先圣”中获得的是一种与“神圣”遭遇的价值体验。对这种经验的揭示,有助于拓展对儒者生活神圣向度的认知,从而丰富和深化对儒学宗教性的理解和把握。
关键词:朱熹; 先圣; 祈祷; 转化
在中国哲学这一学科门类下,传统儒学研究深受西方哲学研究范式影响,偏重对概念、范畴的解读和辨析。因而,一提到朱熹,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理、气、心、性等概念,是朱熹对“存天理,去人欲”这个命题的极力主张,是对于“格物致知”的分疏和强调。这种理解进路当然无可厚非,也非常重要,但是,片面强调概念的重要性,可能忽略古人的实际生活本身。从根本上说,思想言说的形成,首先来源于思想家的生活经验,因为一个人所处的“生活形式”,构成了其思考与言说的“深层语法”。忽视儒者实际生活经验带来的结果之一,是可能片面强调思想的体系性和内在一致性;而忽略儒者生命实践本身所具有的神圣向度,会将儒者所具有的神圣态度和神圣情感化约为其他类型的感受,将儒学单纯划定为伦理道德学。众所周知,儒学与宗教的关系,是已经争论很久却无法得出定论的问题。不过,由于宗教学研究视野的扩展,学者们已经越来越多地同意宗教信仰的核心是人与神圣相遇的经验,它体现在活生生的人类行为、经验和情感中,而不是教义的理论思辨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暂时悬搁对于儒学理解的种种先入之见,把目光转向这个传统之下的信仰个体,以“同情”的态度去理解儒者生活中的情感体验,有助于更好地看清儒学传统中与宗教相关的内容。
基于这种理解,本文试图讨论南宋大儒朱熹向先圣孔子进行祈祷的经验,并希望站在比较宗教学的视角,对于这种经验的独特意义结构做出深度反思,借此更好地呈现传统儒者的精神世界,展现儒家生活经验中的神圣向度,而不是用其他层面的研究去认识它。下文的论述,首先从朱熹对于祈祷的看法入手,继而呈现其在向先圣祈祷时的独特表现,然后从比较宗教学对于祈祷本质和意义的分析,说明朱熹“祝告先圣”过程中所蕴含的情感经验和精神性活动,从而展现出这一行为所体现的精神世界。
一、朱熹的祈祷观
“祷”是一种普遍的宗教行为,信仰者通过祈祷与超越者交流,表达自身的诉求或愿望。在中国,“祷”字的本义是“告事求福”(《说文解字》),是“祈神之佑”,是人祈望获取外在力量帮助的行动。落实在儒家礼仪中,祈祷表现在祭祀的“祝”这个环节。在最初的意义上,祝与祷、诅、呪等词一样,都表示以言辞向神灵祈求,要实现自身的某种愿望。这种行为的信仰前提是,相信鬼神能介入现实的人类活动,并施加影响。不过,随着周初人文精神的兴起,以神灵为中心的祭祀转为以人为中心,祭祀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的情感需求,而不是出于对鬼神本身的信仰和敬畏*关于周初宗教中人文精神的兴起及春秋时代的宗教人文化,参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39页。。在这种转变中,鬼神在人的生活中不再具有绝对的支配力量,“祝祷”应验的思想基础已经不复存在。
秉承这种人文化的态度,汉唐很多儒者对祈祷行为抱有很大的不信任,认为人的吉凶福祸与行为、德义密切相关,祈祷、占卜虽然有助于知晓天命,却只能补救生命过失的细微之处,并不足以应对大的祸福遭遇,因而,人不能通过突然的祈祷获得渴求的福祉,也不能通过“临时抱佛脚”的行为规避自身所犯的恶行*比如《潜夫论·巫列》明确说到:“凡人吉凶,以行为主,以命为决。行者,己之质也,命者,天之制也。在于己者,固可为也;在于天者,不可知也。巫觋祝请,亦其助也,然非德不行。巫史祝祈者,盖所以交鬼神而救细微尔,至于大命,末如之何。”([东汉]王符撰、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01—302页)。对于《论语》中直接涉及祈祷的“子路请祷”一章,汉唐儒者基本认为,孔子的回答表明了对祈祷行为的拒绝,因而,子路的做法是错误的。平日的“修身正行”,才是天地鬼神护佑的依据。对于儒者来说,不需通过特别的祈祷而求得福祉,重要的是平时要“履信思顺”,实现一己的“全德”,这成为儒家对于“祝祷”的主流态度。不过,过分强调德行,贬低祈祝的作用,可能带给人的印象是儒家不赞同祈祷。然而,祷是正礼,“祭有祈”“祈福祥”都明载儒家礼典之中,如果片面强调祝祷的无用,等于是质疑礼制的合法性。在这个方面,宋儒做了更精细的阐发,方式是将“祷”作为应对生活中非常处境时“修身”的一种行为。
宋儒对“祷”的基本理解是:“祷者,悔过迁善,以祈神之佑也。”*[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1页。很明显,相比《说文》“告事求福”的解释,宋儒所强调的“悔过”,内在道德意识的味道更浓。朱熹尤其为《论语》“子路请祷”进行了辩护,认为“请祷”行为本身并没有很大问题,并专门举出《士丧礼》“疾病行祷五祀”的经典依据来为子路撑腰。郑玄注“行祷五祀”云:“尽孝子之情。”贾公彦疏:“云‘尽孝子之情’者,死期已至,必不可求生,但尽孝子之情,故乃行祷五祀,望祐助病者,使之不死也。”*[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王文锦审定:《仪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67页。按照这种理解,“行祷”的目的并非一定为了令疾病好转,只是身为人子,无法接受眼睁睁看着亲人因病痛离世而自己却无所作为,故而无论何种方法,只要希望尚存,都要一试。按朱熹的说法,“请祷”反映着臣子“至情迫切之所为”,是作为学生的子路“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1页。。因而,“祷”的主要目的正是为了回应孝子的这种情感,而这种情感依据正是祈祷得以进行之“理”。因为有这种“理”,所以孔子也并不认为子路的做法是错误的,只是认为自己不必祷而已:“圣人也知有此理,故但言我不用祷,而亦不责子路之非也。”*[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34,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03页。
当然,朱熹也认为子路的做法有不足,即不应该“请”,“病而祷,古亦有此理,但子路不当请之于夫子”*[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34,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03页。。原因在于:“非病者之所与闻也。病而与闻于祷,则是不安其死而谄于鬼神,以苟须臾之生。君子岂为是哉?”*[宋]朱熹:《论语或问》,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54页。如果是病者知道了请祷行为并且应允,那性质就变为病者谄媚鬼神以求自己福祉的自私行为。朱熹认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才会对子路做出那样的回答,但这回答绝非对于祈祷行为本身的否定。在朱熹眼里,《仪礼》很好地表明了祈祷行为的动机和意义,因而,“祷是正礼”,是圣人所作,“盖祈祷卜筮之属,皆圣人之所作”*[宋]朱熹:《论语或问》,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54页。。
作为“正礼”的祈祷,是个体在非常处境下安顿自身情感的一种方式。通过祈祷行为,个人“不能自已”的情感得到安顿,从而平稳度过非常处境。而要获得这种情感的安顿,需要反省自己的内心,使自己问心无愧。于是,祈祷的最重要内容,成了“悔过迁善”这个具体行动:在虔诚的祈祷中承认自己的过错和不足,以祈求神灵的护佑。由此,祈祷不是真的因为相信神灵能够降福而祈求自己的福祉,而是对自身至诚之心的外在表达,因而,必须在“礼”的范围内进行。儒家士人自觉地将作为“正礼”的“祷”与世俗“追寻一己之福”的祈求区别开来,作为“礼”的一部分,儒者只应依照自己的身份,“各祷于其所当祭”,世俗那种“靡神不祷、靡祀不修”的做法,朱熹当然不会赞同。虽然宋儒对“祷”的界定是“悔过迁善,以祈神之佑”,但这两部分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神佑”显然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并非基于前面行为的必然结果。
因而,无论“告事求福”还是“祈神之佑”,在儒家的精神价值中所占的地位都不高。相比汉儒由于对世俗信仰的戒心而表现出的对祈祷的警惕,朱熹对“祷”的态度更加积极。对朱熹来说,“祷”的意义在于它是臣子“不能自已之情”的恰当表达,并且能够在“至诚”的祈告中完成生命状态的转化,“悔过迁善”成为一种生命的超越和更新。在这个意义上,祈祷重又跟个体的切己情境关联起来,成为跟儒者生命切身相关的生存行动,甚至成为儒者维护神圣价值的内在动力和切实表达。正是在这种对于祈祷的理解下,朱熹在自身的生活中,向先圣孔子进行了虔诚的祈祷。
二、向先圣祈祷
作为新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祝告孔子非常频繁,如陈荣捷先生所说:“朱子即非告先圣之最勤者,亦少见矣。”*陈荣捷:《朱子之宗教实践》,氏著:《朱学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第183页。表现在文字上,就是收入《朱文公文集》卷86的众多“告先圣文”,它们代表着朱熹在每次祭祀仪式上对先圣孔子进行的祈祷。那么,朱熹向先圣祈祷了些什么?
宋代儒者大多写过“告先圣文”,但对很多人来说,这只是出于仪式的需要。他们并不重视这类文字的写作,只是按照官方规定的通常格式来写,内容一般是赞美孔子的伟大和功绩。但朱熹“告先圣文”的基本关注点,在于自己精神上的不足和道德修养。明显的表现之一,是《南康谒先圣文》表达了希望能够尽早“归田”的心愿。“归田”的目的不是退休养老,逍遥自在,而是因为朱熹更大的志愿在于讲学和悟道。祝文提到“以终故业”,“故业”即是“伏读先圣先师之遗书,夜思昼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第4036—4037,4050—4051,4036,4045页。。晚年的《沧州精舍告先圣文》更明确表达了要与同道深入体究道之根原的愿望,“逮兹退老,同好鼎来,落此一丘,群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以此祈求先圣之灵“陟降庭止,惠我光明”*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第4036—4037,4050—4051,4036,4045页。。
着眼于自身的道德生命,朱熹的祈祷文一再表达着对自己生命历程的剖析和回顾。《南康谒先圣文》说:“熹早以诸生,推择为吏,中遭疾病,即退丘园。乃得其耕耨之余日,伏读先圣先师之遗书,夜思昼行,不敢以昧陋自弃者,二十余年于此矣。”*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第4036—4037,4050—4051,4036,4045页。《漳州谒先圣文》说:“熹总发闻道,白首无成。”*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第4036—4037,4050—4051,4036,4045页。《沧州精舍告先圣文》说:“熹以凡陋,少蒙义方,中靡常师,晚逢有道,载钻载仰,虽未有闻,赖天之灵,幸无失坠。”*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第4050,4036—4037页。这种回顾是对自身生命的反省,是面对一个高于自己的生命时内心的自然反应。在这种生命的开敞中,在先圣生命的典范指引下,祈祷者会从一个不同的视角审视自己的生命,剖析自己的不足,以此达到“悔过迁善”、提升生命的目的。
与这种生命的敞开相关联,朱熹在祝文中表现出强烈的负疚和焦虑意识,用词极为谦卑。“熹总发闻道,白首无成”“永念平生,怛焉内疚”(《漳州谒先圣文》),这样的说法在朱熹的祝告文中频繁出现。《南康谒先圣文》首先回顾了自己的生命历程,然后说明受皇命恩典得以受任这个官职,但是自己已经年老力衰,“已深不梦之叹”,很怕任期内会有辱先圣先师的教诲,“大惧弗称,以辱君师”,因而要告知先圣,祈求先圣之灵保佑,使自己能够顺利完成使命,“惟先圣先师之灵实诱其衷,使幸不获罪于其民,而早遂归田,以终故业”*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第4050,4036—4037页。。这篇言辞恳切的告文没有像一般官员谒见先圣的祝文那样,表达一种要按照儒家教导治理地方的决心(当然其中蕴含着这层含义),而相反自始至终在表达对自家生命修养的关切、对自己使命的担忧。
相比于形式化的“先圣祝文”,朱熹向先圣的祈祷凸显出他与先圣之间的本己性关联。先圣不是与自家生命无关的过往历史人物,而是与自己的生命成长密切相关。在朱熹所表现出的谦卑感和懊悔感背后,是更为急迫的对于先圣的向往感。这些情感交织在一起,类似于宗教上对于神圣的“敬畏感”。这种感受的基础,是朱熹对于先圣的独特理解。
毫无疑问,先圣孔子是儒者心目中最重要的圣人,但孔子的形象在不同儒者那里却并不相同。王阳明有个“精金比喻”提到“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犹九千镒”*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第119页。,引起朱子学者的强烈不满,原因就在于它不符合朱熹心目中孔子的地位。在朱熹眼中,先圣孔子的地位是任何其他圣人不可比拟的。按余英时先生的说法,朱熹有意将“道统”与“道学”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自“上古圣神”到周公“内圣外王合而为一”的“道统”时代;孔子开创的“道学”时代,内圣与外王分裂为二*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7—15页。。对后世儒者来说,三代文教政治合一的理想秩序无法复现,要在现实处境中发扬儒家教训,在“无道”的现实世界努力延续“道”的传承,并活出不一样的道德生命,需要效法的“原型”只能取自孔子。在这个意义上,孔子的出现作为一个事件,已经不再具有历史性,而是具有了“原初性”的意义。
对朱熹来说,孔子作为后世儒者效法的“原型”,其一言一行毫无过失,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在这一点上,朱熹也不会同意陆王一系学者关于“圣人有过”的论断。由于认为“圣人有过”,心学认为圣人的言行并无神圣之处,神圣的是“道”本身。就序列而言,圣人、经典的地位比不上“道”,由“尊道”可以“离经”,甚至可以否定圣人的说法。但朱熹则坚定强调,圣人无过,所以先圣的一言一行,皆有深意在焉,皆是天道落实到事上的具体表现。由此,朱熹强调,修身就是要模仿圣人。他用“熟”与“不熟”区分学者与圣贤,“圣人与庸凡之分,只是个熟与不熟”*[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413,825,3117页。,“圣贤是已熟底学者,学者是未熟底圣贤”*[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413,825,3117页。,因而,“学道便是学圣人,学圣人便是学道”*[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413,825,3117页。。
对朱熹来说,先圣孔子是始终需要效法并赋予行为以意义的“神圣原型”。“先圣”这个名称所代表的,是儒家追求的神圣价值世界,它传达了儒者面对世界所应当采取的恰当态度,并激励着儒者经由在此世界的行为走向神圣。这种形象不是历史的真实,它更近乎 “神话”,但对儒者(信仰者)来说,它是“真实的神话”*对于“真实的神话”的界说,参见[英]约翰·希克著,王志成、思竹译:《第五维度:灵性领域的探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12—314页。。对朱熹来说,先圣的样式就是自己生命努力的方向,无论为学或者为政,都是在践履先圣所教导和实践的内容。因而,跟先圣的交流,正是遭遇自身生命的另一种可能向度。在这种遭遇中,朱熹不仅会从心底赞扬先圣的功绩,更会触及自己生命的现状。与先圣的伟大相比,自己的生命总是在努力通向超越的路途中,总是充满着各种不足和缺陷。正是出于这样一种信仰态度,朱熹在向先圣祈祷时才会全然敞开自身的生命处境,更倾向于将祝告先圣视为审视、提升自身生命的时机。先圣所代表的神圣价值不只是提供伦理道德上的规范举止,而是规定着儒者的整个存在的“基本模式”。因而,对朱熹来说,祝告先圣的精神性意义在于,它是自身默想圣贤人格并向着圣人方向前进的重要方式,是实现自我根本性转换的重要方式。这个过程的实现,只有放到“祈祷”这个行为的本质中才能更好理解。
三、祈愿的心灵
按宗教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的看法,广义的祈祷是指“内心所有不同的感通,与自己认可的神圣力量交感或交谈”,而这构成了宗教的灵魂和精髓。詹姆斯说:祈祷是实践的宗教,是真实的宗教,正是“祈祷”显现出个体心灵救度并改变自己生命的全部努力*[美]威廉·詹姆斯著、尚新建译:《宗教经验种种》,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337页。。宗教史学家海勒在其代表作《祈祷》(Prayer:AStudyintheHistoryandPsychologyofReligion)中详细描述了祈祷的历史和类型,指出祈祷的动机是“追求一种更高、更丰盛、更深刻的生活”,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生命*F.Heiler, Prayer:A Study in the History and Psychology of Relig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2, p.355,357、361,356。。因而,“祈祷意味着人转向另一个存在(Being),他的心灵内在地向此一存在开放,祈祷是‘我’(I)与‘你’(Thou)的交谈”,“不只是一种兴奋的感受,不仅是感到神圣的心情,也不只是屈服于一个超越的善,毋宁说,它是神与人的现实交流,是有限心灵与无限(Infinite)的真切交往”*F.Heiler,Prayer: A Study in the History and Psychology of Relig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2,p. 355,357、 361,356。。俄国神学家谢尔盖·布尔加科夫指出:就其先验组成来说,祈祷“是人的全部精神努力和全部个性对超验的追求:一切祈祷(当然,是真诚热烈的祈祷而不是徒有其表的祈祷)都在实现着一种旨意:超越自我”*[俄]布尔加科夫著、王志耕等译:《亘古不灭之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页。。一句话,祈祷意味着向神说话,并与神交流,是向一个超越的“你”的呼唤,并期待着“你”的干预。对宗教人来说,这种交流不是假想出来的,而是真实发生在其经验之中。由此,海勒指出,有三个因素构成了祈祷的内在结构:对一位活生生的位格上帝的信念;相信祂真实、当下的临在;在神的临在中,人进入与神的真实交往*F.Heiler, Prayer:A Study in the History and Psychology of Relig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2, p.355,357、361,356。。这里最核心的因素即是位格上帝(God)的存在,但不应该只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理解这样一位位格上帝,因为那样的话,很多宗教中的祈祷就要被排除在“祈祷”之外。
祈祷是发生在祈祷者与神“两者之间”的交谈。祈祷者相信,神倾听祈祷者的祈祷,并且会做出回应。这种交谈(talking)不是对谈(conversation),不同于人与人之间的交谈*D.Z. Phillips, The Concept of Prayer,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imited, 1965, pp.49—50。,因为它建立在一种不对称的关系上,祈祷者的祈祷总是意味着对祈祷对象的依赖*[意大利]达瓦马尼著、高秉江译:《宗教现象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8页。。不过,在祈祷中,神与人之间的界限得以消除,两者在祈祷中“相遇”,人在祈祷中接近神,“超验作为内在被祈祷获得”*[俄]布尔加科夫著、王志耕等译:《亘古不灭之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页。。因而,祈祷不仅仅是言语,而是“人的存在运动——一种在‘两者之间’进行的运动。祈祷不是毫无用处的对空之言,它是在人的存在的深层,在人的‘心’的深层发生的某种事件,这种事件在祈祷中形成言语,又用言语表达出来”*[瑞士]海因利希·奥特著,朱雁冰、冯亚琳译:《上帝》,香港:社会理论出版社,1990年,第93页。。对于这种运动,奥特(Heinrich Ott)有精彩的表述:
存在的深层和心的底层却并非人最终完全退隐独处的所在,而是他面对上帝(Coram Deo)而存在的地方。因为人在“两者之间”存在于上帝面前,同时他的自身完全得自上帝,最终因为上帝在倾听着并满足着请求,所以,人的内心最底层的运动——它在渴望得到一颗警觉的、高尚的、正直的、坚定的和自由的心的祈祷之中用语言表达了出来——是人自身通往上帝的道路和达到与上帝在一起的途径。一个如此祈祷的人——他不仅用口说出祈祷,而且在自己的内心经历着祈祷——在接受着他所渴求得到的那颗真正的心。与上帝一起,就是说在上帝的帮助和“休戚与共”之下,他走向经请求而被许诺给他的未来,他走向上帝将恩赐给他的那颗新的心。他的祈祷是他向着他所祈求的东西迈出的一步,这将在未来生活的某个时刻得到证实。任何鲁莽思想都不会使他远离上帝,任何激情都不会左右他……他的祈祷、他的内心深层的运动将在他的一生之中一步一步地得到验证,包容着他的一生,与之溶为一体。*[瑞士]海因利希·奥特著,朱雁冰、冯亚琳译:《上帝》,第93—94页。
奥特虽然是从基督教位格主义出发来解释上帝在人的祈祷中的地位,但他无疑揭示了祈祷的本真意涵,即,作为“人的内心最底层的运动”,祈祷使人得以超越自身,走向与神圣的合一。詹姆斯表达了类似的主张:“祈祷并非空洞的语言习念,或者仅仅复诵某段神圣的经文,而是指灵魂的运动本身,灵魂使自己进入一种个人关系,与它感觉就在面前的神秘力量相接触——即便还没有名号称呼这种灵魂的运动也可以发生。”*[美]威廉·詹姆斯著、尚新建译:《宗教经验种种》,第337页。神圣者启示了人可以成为的样式,人在内心的运动中努力提升自己达到那种要求。因而,祈祷者总是把自身所处的“窘境”向神圣者告白(confession),而渴望获得“警觉的、高尚的、正直的、坚定的和自由的心”,以此通向“未来的我”*最典型的例子,是托马斯·阿奎那的祷文,见[瑞士]海因利希·奥特著,朱雁冰、冯亚琳译:《上帝》,第91—92页。其实,很多伟大心灵的祈祷都是典型的例证,可参唐佑之编译:《伟大心灵的祷告》,香港:证道出版社,1977年。。祈祷不同于人与人之间的交谈,是因为它所面对的是无限的“你”,在此人所交托的也并非自身的某个部分,而是整个位格。这之间的差别,举个例子来说,是“不要对我做那样的事”(Don’t do that to me)与“不要让我成为那样的人”(Don’t let me become that)之间的不同*这是借用D.Z. Phillips的说法,参The Concept of Prayer, p.51。。换句话说,祈祷者祈求上帝改变的是整个自己,真诚地做出这个祈祷即是改变的开始,因而,祈祷不是把责任都推给一个全然相异的存在,而是在与祂的交谈和相遇中获得改变自身的力量。
对于祈祷者而言,祈祷对象是神圣的位格存在。按海勒的说法,这个存在是活生生的(living)。这意味着祂不是与信仰者的生活毫无关系的“冷漠的他者”,而是始终与信仰者“同在”,并真实影响着信仰者生命的存在者。同时,信仰者在祂面前不会隐藏自己,而是全然地开放自己,因为这种隐藏毫无意义。因而,祈祷的前提是对于祈祷对象的真诚信仰,并在跟这个神圣对象的相遇和交谈中实现心灵的改变和转化。那么,对于朱熹来说,“祝告先圣”是否是这样一种精神性的运动过程?
四、祈祷应验与生命转化
显然,对于朱熹来说,先圣孔子是他真诚的信仰对象,但“祝告先圣”是否拥有海勒所说那种祈祷的内在结构?如前所述,朱熹眼中的先圣,是代表神圣价值的位格象征,是神圣之“道”的完全体现,是自己要效法、并努力达到的生命向度。于是,重要的是,朱熹在“祝告先圣”时,是否相信先圣真实、当下的临在?两者之间是否有真实的交往?
确实,儒家主流传统对祭祀有高度人文化的理解。以《荀子》和《礼记》为代表,它们认为祭祀不再是为了与神灵沟通,而是祭祀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76页。。但是,朱熹仍然坚持祭祀在与鬼神沟通上的真实性和重要性,最显著的表现是他对于《论语》“祭如在”的重新诠释。“如在”在大多数儒者的理解中,只是当作鬼神好像存在,以此来表达和培养诚敬之心。不得不说,这种理解在传统上占据主流地位,影响至今。但细观朱熹对此的解释,他实际上并不认同这种流行的理解,而是有意识地回到《论语》的原初语境,指出“祭如在”并非孔子亲口之语,而只是“门人记孔子祭祀之诚意”*[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64页。。这样一来,“祭如在”就成了旁观者对孔子祭祀状态的观察和描述,而不应成为祭祀者应当遵行的行为规范。由此,“如在”并不是祭祀主体“设想”鬼神存在,这就为祭祀中鬼神的真实临在留下了空间。相反,朱熹始终强调,祭祀就是要实现与祭祀对象的“感格”,这种感格的发生,是因为祭祀者与祭祀对象之间的“气”具有共通性。儒者“行圣贤之道,传圣贤之心”,“气”自然与圣贤相通*[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3,第46页。。通过生者与死者的“神气交感”,祭祀能够成就出双方当下“共在”的世界,就像用手指抚奏丝桐能够再现消失的琴声一样*这是朱熹弟子黄干的比喻。详细分析,参见李继祥:《孔庙的形上学议题》,氏著:《宋明理学与东亚儒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2—155页。。可见,朱熹始终认为:祭祀可以实现与祭祀对象的感通与交流。他的极力坚持和解释让人有理由认为:他真诚地相信,在祭祀过程中,“先圣之灵”会真实地临在,并在祭祀者的“极其诚敬”中实现感通和交流。在这个意义上,朱熹的“祝告先圣”正是宗教意义上的祈祷。只有在这个性质界定的前提下,才能真正理解这个行为带给朱熹的精神意涵。
祈祷当然希望应验,但什么是祈祷得应?祈祷是一种真实的交流,在祈祷中个体与超越者之间建立起真实的关系。借着这种行为,祈祷者泯除了与神圣者之间的隔阂,使个人生命与神圣世界连结起来。经由仪式中的这种体验,行为主体会获得精神上真实的转变,从而获得跟此前生命状态不相同的触发和效验,这种效验就是宗教上所讲的祈祷的应验。祈祷的本质意义并非祈求神灵以超自然的能力改变祈祷者现实的困境,而在于通过祈祷进入与神圣的交感,从而获得真实的力量。詹姆斯在列举了很多祈祷应验的文献材料后指出:“在祈祷生活的所有阶段,我们都发现一种信念,即进入交感过程,有上方的能量流入,以应付需求,并在现象世界发生作用”,这种“能量流入”或许只是激发了祈祷者“原来潜伏的精神能力”,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能力“现在成为活跃的,而且,某种精神的运作发生实在的效应”*[美]威廉·詹姆斯著、尚新建译:《宗教经验种种》,第347页。。换言之,祷告所带来的效果,是让祈求者能够以一种全然不同的心态和动力去面对生存中的困境。在这种理解前提下,可以尝试描述朱熹在向先圣祈祷过程中所产生的精神体验。
朱熹相信,祈祷的意义在于,它是人类在面临某种无助情境时情感的真切表达。在这些情境中,人类自身的能力往往显得非常渺小,只有通过与更高存在的交流,人类才能从这种无助中解脱。从本质上说,朱熹眼中的“道学事业”正属于这种情境,无论是自身的修养(对“圣人难为”的感叹,临终前“坚苦”的感受),还是通过“教”施行教化,都不是单靠个人的力量可以轻易达到的。朱熹一再祈求圣人之灵“陟降庭止,惠我光明”,恰好表达了祈祷的真谛。
对朱熹来说,先圣不是历史上那个“恓惶”“无奈”甚至如“丧家狗”一般的无家可归之人,而是充满无限智慧的圣人,是儒家神圣价值在世的典范,并为后世儒者提供了效法的“原型”,需要后人不断地回溯和体认。与先圣对话,不是和历史上某个过往的人物进行交谈,而是与儒家神圣价值的真正“遭遇”,其中蕴含着关于意义和真理的观念,也塑造着儒者在世的生命态度与价值意向。在这个意义上,孔子的存在成为了朱熹生命的“指引”,与朱熹自身生命的超越紧紧关联在了一起。在“至诚”的祝告中,祈祷者内心会重新获得力量。作为感通,它是祭祀者与先圣的真实沟通,但这种沟通不是面对面的共同参与,而主要是祭祀者对先圣之圣性的体验,是对神圣价值人格的体验与再次内化。朱熹所说祭祀中与“先圣之灵”的“感通”,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够获得合理的解释。在这种仪式行为中,朱熹将仪式与自家生命密切关联在了一起,并从这种极具开敞性的交往行为中获得了重要的精神力量。
作为祈祷,祝告先圣带给朱熹的,是不同于其他祝告行为的经验,这种不同源于孔子在朱熹心目中的地位及其所代表的神圣价值。作为“感通”的意向对象,“先圣”不是其他祖先,因而在感受结构上,对先圣的体验完全不同于先祖。对朱熹来说,“先圣”的意涵不只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一个人物,而是儒家神圣价值世界的象征,规定着后世儒者的“在世生存模式”。这种价值规定了儒者在世生存的基本样态与努力的方向,因而,在圣化的孔子观中,“无过”的先圣成为儒者生命的标杆与典范,成为他们反思和面对自己的参照。重要的不是“历史之中”的先圣,而是“历史之上”的先圣,在后代的历史中,先圣始终作为“道”的象征而存在,并且能够在祭祀者的“极其诚敬”中与其发生感通。在祈祷这种“交感”中,面对先圣这样的完美人格,朱熹深刻体认到了自身生命的缺失与不足,这从他祝文中对自己生命境况的认识即可看出。而由这种体认和开敞,朱熹也会开启自身生命的转化和超越之途。
祝告先圣带来超越历史的体验。在这种体验中,朱熹感受到的不是与历史上孔子的“相遇”,也不是与经典中透显的圣人行为相遇,而是与先圣之灵直接当下的遭遇。在这种遭遇体验中,作为信仰者的朱熹再次体认到儒家价值的神圣性,并借着向先圣的告白与祈祷,获得改变的真实力量。通过与自己眼中这位“无限者”的感通和交流,朱熹不仅再次确证了生命努力的方向,而且实现了“内心最底层的运动”。用朱熹自己的话说,这种运动就是作为“祷”的“悔过迁善”。
五、结语
由上分疏可见,在朱熹的信仰观念之下,礼制要求的祭祀先圣所具有的意义并不仅仅只是形式上的,而是跟朱熹自己的生命有着紧密的关联。对朱熹来说,祭祀孔子发生在他生命中的每一次重大活动中,而他本身也在仪式中倾注了更多的生命关注。仪式与朱熹的生命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朱熹在祝告仪式中通过遭遇“先圣”回向自身,从而使这种行为具有了类似神秘主义的表现。通过这种仪式上的遭遇,朱熹能够不断地进入与“神圣”的同在,从而在“世俗”的世界中获得自我肯定的“勇气”,产生不断继续下去的动力,并开启生命转化的精神运动。这种意涵真正体现着宗教祈祷的本真性意义。对这种生命经验的揭示,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朱熹对很多观念的论说和坚持,也有利于更深入理解传统的生活世界。
过往的儒学研究并不重视儒者的生活经验,这可能导致对儒者生命本身所具神圣向度的忽视。本文希望说明,对儒学研究来说,宗教学所关注的神圣向度也是不可缺少的研究内容,需要更深入的开拓和挖掘。因而,比较宗教学的视域(尤其是宗教现象学的态度和方法)可以为儒学研究提供更为宽广的视野,值得更多的关注和研究;站在宗教学视域深入开掘儒者的生活经验,对于更进一步理解和诠释儒家的历史形态和精神意义,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宗教问题的研究绝不限于断定儒学传统的宗教(或非宗教)性质,更是要通过现代学术视角的阐发,凸显儒家传统所蕴含的对于人类精神的深刻意义,这种意义彰显在儒者真实的生活过程中,尽管不同儒者的表现并不相同。
【责任编辑:杨海文;责任校对:杨海文,许玉兰】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2.016
作者简介:张清江,中山大学哲学系(广州510275)。
*收稿日期:2015—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