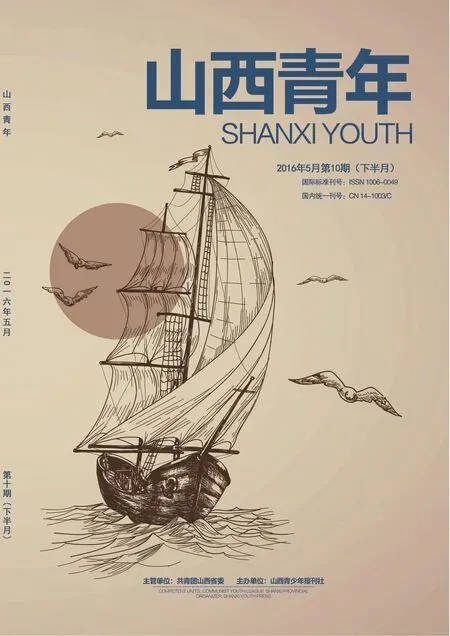论《离骚》人物性别的转变及其寓意
朱碧菲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580
论《离骚》人物性别的转变及其寓意
朱碧菲*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山东青岛266580
摘要:《离骚》中抒情主人公的外在形貌是不统一的,“他”的性别在全诗中出现了多次转变。主人公从出场时的贵族男子,变成遭众女嫉妒的美人,又从美人变成了“求女”的君子。这种人物性别上的不统一,是因为屈原在写作的时候采取了“以男女喻君臣”的比兴手法,并且在比喻中以楚王作为喻体中心来改变自己的性别。然而屈原一片忠心却遭佞臣毁谤,楚王厌弃,他感情上对君王是从期望到失望的,因此最后他以“自我”男性的身份“求女”,并表明了从彭咸之所居的心愿。
关键词:屈原;《离骚》;性别变化
一、绪论
要讨论《离骚》中人物性别的问题,就不得不涉及到“以男女喻君臣”之说和“求女”的寓意这两个问题。自南宋朱熹提出《离骚》中的“以男女喻君臣”这一现象后,附议者颇丰。建国早期,以游国恩为代表的屈骚大家,在研究中也延续了这一观点。但是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也一直存在,有学者认为,《离骚》中不存在“以男女喻君臣”的现象。尤其是在90年代前后,有许多专家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证。有部分人支持“以男女喻君臣”之说,如潘啸龙的《论<离骚>的男女君臣之喻》,也有赵奎夫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屈骚中的主人公自始至终都是男性,提出“以男女喻君臣”之说的看法是误论等。
针对“求女”的解说也是层出不穷。“求女”不是真的寻求美女,是另有所寓,这一观点已经广为认同。“求女”论证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的“女”的寓意上面,有人认为“求女”是在寻求贤君,也有人认为“求女”是在寻求同朝贤臣。
虽然论证颇多,但是年代久远,也无法确定屈原作《离骚》时的确切用意,因此这两个问题尚未形成定论。笔者较为赞同“以男女喻君臣”之说和“求女”是求贤君的解释。
二、人物性别的多次转换
纵观《离骚》全诗,抒情主人公的性别出现了多次转变。前半篇主人公出场的时候,从其字号“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来判断,他是一位身份高贵、承载厚望的贵族公子。但是到了“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一处,主人公却摇身一变,成了遭众女嫉妒的绝色佳人。而在《离骚》前半篇结尾“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处,主人公又成为了男性。直至全文的后半篇,主人公各种“求女”的举动都表明,他是一位谦谦君子。
(一)从“正则”到“蛾眉”的转变
在《离骚》的前半篇,诗人的“自我”形象,经历了从男性转换到女性,又从女性转换到男性的一个过程。开篇诗人写道: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从主人公的字号上判断,可以确定此时人物的性别不是女性,而是男性。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女性命名取字的方式与男性不同,一是女性的名讳必须带上自己的姓,二是女性的名、字之间没有意义上的联系:
先秦女性的名、字、号由母家国名、夫家国名、母家姓、母家氏、夫家氏、排行、夫谧、自谧等八种材料组成,能反映出籍贯、家庭背景、血缘关系、婚姻状况、德行善恶,如同一个个履历标签,具有标识身份的功用。①
关于《离骚》主人公的名字,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是这样解释的:“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故父伯庸名我为平以法天,字我为原以法地。言己上能安君,下能养民也。”说的是其长辈观察他出生的年月,合天地中正,因此而赐予他的嘉名,都是对这个人从品行上给的美好希冀,名字中并没有任何像女性名字一样拘泥于血缘集团的标志。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在开篇的时候,主人公的身份还是一名男性贵族。
然而到了“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琢谓余以善淫”一处,主人公突然变成了一位女子,并因其美好的容貌遭致了众多世俗女子的嫉妒和毁谏。这名女子也是屈原在文中“自我”形象的比喻,因为品行美好中正,而遭到了众多奸佞之臣的嫉妒和恶意中伤。王逸对此句的注解是:众女嫉妒蛾眉美好的人,谏而毁之,谓之美而淫,不可信也;犹众臣嫉妒中正,言己淫邪不可任也。此处明显是以众女比喻众臣,以美人比喻品行中正的“正则”。虽然只是一种比喻的手法,但是也清晰的体现了人物性别从男性到女性的转变。
(二)“蛾眉”却戴“高冠”
从“正则”到“蛾眉”的转变,是诗中主人公性别的第一次明显变化,到了《离骚》前半篇的结尾处,遭受了“众女”嫉妒的主人公,其外在形貌再一次发生了变化。从一名因为蛾眉美好而遭受嫉妒的美人,变成一位整理衣冠的男士“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并且因为无法接受“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而打算“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了。文中主人公戴上的“岌岌”的高冠,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一种典型的男性饰物,又表明他此时的身份是男士。到这里为止,文中人物性别的变化就已经停止了,在《离骚》后半篇中,主人公都始终保持着男性的身份,主要进行了“求女”和为了“求女”顺利而进行的“问卜”活动。
《离骚》中人物性别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频繁的变化,而且主要是集中在前半篇,许多学者都对此提出了疑问。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指出,《离骚》里这种人物性别上的多次变化实在是“扑朔迷离,自违失照。”他认为屈原这样来塑造抒情主人公是非常违背常理、难以理解的,并且从全文的结构上来说存在情节上不连贯的问题“文中之情节不贯,犹思辨之堕自相矛盾”。但是《离骚》作为浪漫主义诗人屈原最杰出的长篇抒情诗,是经过作者精心构思,内涵丰富的诗作。文中人物性别的多次变化,并不仅仅是随意的比喻,也不可能是屈原在写作时因为构思不严谨而出现的自相矛盾。
在总结国内外建筑防火设计经验和消防科研成果以及开展大量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公安部组织编制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以下简称《建规》),新增了对建筑保温系统的防火要求,于2015年5月1日实施,并于2018年进行了局部修订。《建规》第6.7节建筑保温和外墙装饰对外墙保温作了具体规定,整体上体现了“材料防火”与“构造防火”的理念,以条文规定的形式将这两个理念予以明确,可以认为该规范可用于解决外保温使用阶段的火灾问题。
三、人物性别转变的原因
屈原之所以在《离骚》中采取了这样的写作手法,原因有二,其一是他采取自《周易》、《诗经》以来,流传下来的“以男女喻君臣的”比兴方法,他除了用香草比喻美好的事物之外,也惯用男女之情以喻君臣。早在《周易》中,“以男女喻君臣”的思维方式、表达模式,就已基本形成。又在《诗经》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和体现,屈原在创作《离骚》的时候,其思想和写作模式就明显受到了这种比兴方式的影响。
其二是他本着“君动而臣随”的原则,屈原在除了固定的用美人比喻美好的人事物之外(如用美人指代怀王),在文中涉及到楚王与自己君臣关系的时候,就会将自己写成处于随从地位的女性。然而在没有涉及到楚王的部分,或者是在他被楚王彻底厌弃之后,无君主可辅佐的时候,他就恢复了自己本来的男子面目。主人公在后文的“求女”中,因为一直也没有求得明君,无君可随,所以他的性别也没再发生过改变。
(一)以男女喻君臣
从《离骚》的构思整体来看,有两条主线。第一条在其前半篇,是贯串其中的比兴主线,就是“以男女喻君臣”,由此分化出贤臣“自我”与佞臣“众女”的对立和斗争,与之相对应的是香草众芳之喻,以揭示“自我”和“众女”品行、好恶的不同。第二条主线是后半篇中以主人公锲而不舍的“求女”行为为线索的。
最初诗人的“自我”作为“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的“余”,怀抱着美好的理想,希望能辅助君王“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却遭到了“众女”的谗毁、中伤和君王的遗弃。诗人的“自我”因此在内心激发起极大的情感冲突,表述了深切的悲愤和不平,并以“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之句,宣告了誓不变节、决不随从与众女同流合污的决心。
楚怀王第一次在文中出现的时候,屈原为了歌颂楚王的美好,用美人来比喻楚王“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对此,王逸和洪兴祖都进行了注解。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很明确的指出,美人就是指代怀王:
美人,谓怀王也。人君服饰美好,固言美人也。言天时转运,春生秋杀,草木零落,岁复尽矣。君不建立道德,举贤用能,则年老耄晚暮,而功不成,事不遂也。
而到了“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一处,王逸说:“女,阴也,无专擅之意,犹君动而臣随也,故以喻臣。”③此处,已经比较明白的写出了楚王与包括屈原在内的众臣的君臣关系,因此包括屈原在内的众臣就变为了处于随从地位的女性。然而屈原这样一位身怀报国之志,希望“来吾道夫先路也”的贤臣,却被“反信馋而齌怒”的楚王厌弃,并且始终“非世俗之所服”,甚至“謇朝谇而夕替”。他的心中是十分苦闷的,在感情上的落差也十分巨大。
(二)君动而臣随
主人公一心报国,却怀才不遇,深陷谗毁,心中之愤懑抑郁难以言喻。文中有许多屈原强烈表达自身不满和想要自裁于世的句子:“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些句子都很明显的体现了作者在遭遇到众臣陷害、楚王厌弃的经历之后,虽然坚持“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保持了自己的美好品质,但是也感受到了不为世所容纳接受的孤独悲痛,因而产生了不如归去,自绝以谢天下的情感。
此时的屈原,由于被楚王厌弃放逐,对于楚王和自己的君臣关系,已经不抱希望了,于是他就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貌,“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准备去四方荒远之地游览,也为下文寻求贤君做了铺垫。
有一些学者认为,像屈原这样极其忠君爱国的人,不可能背离楚王去寻求别的明君。但是他们忽视了一点,就是屈原当时的心理状况是宁死不流俗,他在文中两次提到将从彭咸之所,并且他最后也是自投汨罗,可见他对目标的执着,已经超越了生死,又怎会拘泥于早就岌岌可危的君臣之义。屈原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并不是楚王一人安好,而是希望整个楚国强大昌盛,人们美好的品质得以保存发扬。所以当他被楚王厌弃,并且尝试了多次,确定无法在楚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时,他的内心出于对美好的追求,对楚王一人的忠诚可能是有所动摇的。也就衍生出了下文“求女”的情节,并且在“求女”的过程中,屈原始终保持了“自我”形象的男性化。
四、终从彭咸之所居
在“求女”过程中,诗人运用浪漫主义神游的幻想方式,展现了“自我”上天下地求“宓妃”、求“有娀女”、求“二姚”的漫漫历程,结果均以不遇、失败而告终。求女的喻意究竟为何,古今注家有很多种说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五种,即求贤君、求贤臣、求隐士、求同志、以及能通君侧之人。
以王逸为代表的大家,认为“求女”是求贤臣和隐士。然而古时大家不敢直言求贤君,未尝不是受到当时忠君思想的影响。后世有些研究《离骚》的儒家学者,因为屈原表现出的苦闷幽怨之情,而批评他对君王不够忠心,现在看来,未免有些不妥。毕竟非屈原之背弃楚王,乃楚王听信谗言,不用忠臣而已。屈原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去寻求贤臣也好,隐士也好,都无法改变楚王剥夺他政治权利的现状。他只有去寻求明君,才能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他兴国利民的美好愿望才能得到实现。
然而求“宓妃”,她却美而无礼,想求“有娀氏”之女,却又没有好媒人,“二姚”待字闺中,却无法传达自己的心意。屈原始终没有“求女”成功,也始终没有完成自己寻得贤君实现抱负的心愿,只能怀着对故国和人世的不舍,追随彭咸投水而去。
[注释]
①焦杰.从中国古代女性名字的演变看社会性别文化的建构[J].郑州大学学报,2006(6).
②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③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参考文献]
[1]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林家骊.楚辞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焦杰.从中国古代女性名字的演变看社会性别文化的建构[J].郑州大学学报,2006.
[4]田恒金.从《春秋》《左传》看先秦时期女性的名字及其文化内涵[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8.
[5]潘啸龙.论《离骚》的男女君臣之喻[J].文学遗产,1987.
[6]杨成孚.《离骚》“求女”解新论[J].南开学报,1995.
[7]赵奎夫.《离骚》的比喻和抒情主人公的形貌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92.
[8]梅琼林.《离骚》:男女君臣之喻及其原型追索[J].中南民族学院院报,1994.
[9]陈莹莹.《离骚》“求女”研究回顾与思考[D].山东大学,2013.
** 作者简介:朱碧菲(1991-),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049-(2016)10-006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