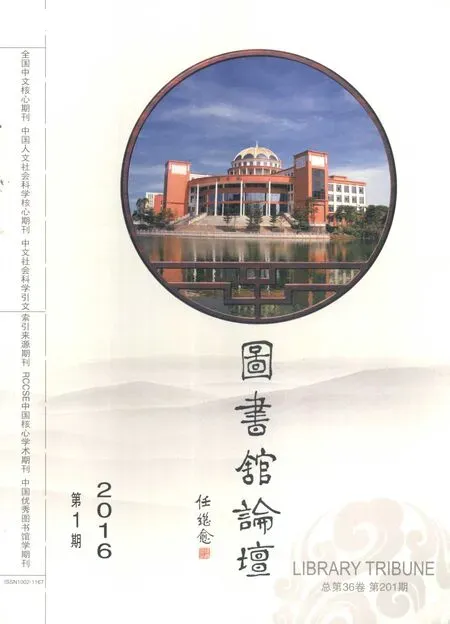后现代语境下基于Library2.0的图书馆学五定律追问与反思
许正兴
后现代语境下基于Library2.0的图书馆学五定律追问与反思
许正兴
文章以后现代主义为视角,通过Library2.0与后现代主义的关联,对阮氏五定律进行全面反思,并在逐条解构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追问,为信息时代图书馆的转型提供理论支持。
图书馆学五定律 后现代主义 Library2.0
0 引言
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学五定律(以下简称“五定律”)因精准概括“服务”这个图书馆永恒的主题而一直被学界奉为经典。然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尤其是W eb2.0的诞生,不仅深刻地改变了图书馆的服务模式,还极大地丰富了五定律的思想内涵。PaulM iller指出:“与其说W eb2.0是一种新技术,倒不如说是一种新理念。”这种理念的溯源与后现代主义紧密相联——作为后工业虚拟经济的文化逻辑回应,后现代思潮以反本质主义、解构统一性、提倡价值多元化为根本特征;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柯的考古学、德国的哲学解释学等[1]为基本学说。其中,基于情境认知(Situated cognition)、涉身认知(Em bodied cognition)的后现代认识论扬弃了传统静止、单向的客观主义知识观[2],凸显了人在知识生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彰显了人作为“实践主体”的智慧创新价值。正是在此背景下,Web2.0与后现代思想交融,开创了Library2.0的图书馆新范式。
被“2.0化”了的图书馆具备后现代性特征[3],但作为传统图书馆的延伸与发展,其所遵循的五定律“服务”宗旨并没有改变。这不仅引起学界关注,还激发了业内以W eb2.0阐发五定律的热潮。然而笔者调查发现,相关研究往往注重以Web2.0术语对五定律进行替换、诠释和重构,鲜有以W eb2.0与后现代主义的关联对其进行解构、追问和反思——而众所周知,后现代的本质就是对体系化元叙事(M eta narration)的拒斥和消解!作为理论体系的五定律无疑难免解构(Deconstruct)的冲击。同时,作为对现代性存在的质疑,后现代的最大特点是表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强调“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问题就是口号”[4]。这为人的思维模式乃至整个社会意识的重新认定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5]。因此,伴随着后现代主义引发的图书馆意识形态的变迁,未来图书情报学应该成为一门后现代科学——不完全了解外在世界的运作,而是以问题为导向[6]。鉴于此,笔者以后现代主义为视角,通过Library2.0对五定律进行审视和反思,并在逐条解构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追问。
1 第一定律:书是为了怎样去用?
第一定律“书是为了用的”实际上引申出一个哲学上认识与实践关系的命题——“基于知识的认识世界是为了通过实践来改造世界”无疑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但运用知识的具体方式和目的在不同时代却有不同的解读:在以客观生产力为经济基础的传统工业社会,知识被客观主义定义为“通用常量”,“输入”到公式化的生产实践中。相应于这种知识“应用”导入型的工业制造“线性方程”,图书馆也在传统分析性思维模式下将知与行相互隔离,使学与用分割为两个独立的环节——先知后行的“机械加工”式知识使用流程。然而,在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7]的后现代社会,原来固定、线性、独立的文献被动态、基于内容和内容间的关系所解构[8];知识价值的形成也并非遵循工业社会的理性主义原则,而表现为社会主观意识决定的短暂性价值和动态性特征[9]——这种“知识流动质态”决定了研究者必内在于这一系统之中[10],在分析性思维的基础上重建整体性思维,以整体性和过程性的思维引导分析性思维[11]。因此,将知识和知识使用者割裂的传统客观主义虽然适用于工业时代个体对静态“书”的历时性传承,却无法适应后现代社会对动态知识的共时性创生。于是在后现代经济“产消合一”的趋势下,知识创新的过程取代应用知识的结果,创造性运用知识取代应用性制造产品[12]。相应地,后现代图书馆也应从传统的学、用二分的维持性知识应用转向知、行合一的发展性智慧创新,即知识在应用中创新、在创新中应用的“创新双螺旋”,从而使学与用能动地统一于认识与实践的共时性转化过程中。而以“并行生产”为特征的Library2.0无疑充分契合了后现代“社会协商隐喻”的知识生发理念——它不仅以扁平化开放知识网络提升了知识的可获得性和易用性,还通过“参与和分享”推动了人与书、人与人的主体间交互(Interaction),从而使读者从信息的消费者转为了知识的产消者(Prosum er),实现了知识读取与应用的时时同步,学习与创造的辩证统一。借用经济学术语,如果说传统图书馆的知识运用是主从模式下的应用型计划生产方式,那么Library2.0就是后现代主体间模式下的创新型并行生产方式。
2 第二定律:读者要有什么样的书?
把获取知识与掌握知识等同的第二定律“读者有其书”无疑建基于传统客观主义知识论之上[13],其实质就是把外在于人的抽象知识当做永恒的“绝对精神”主体,使人成为知识灌输的客体对象。而在此关照下的图书馆也成了一个以普遍客观知识同化特殊个体知识的社会“教化机制”。因此,读者在这种图书馆里“有”的书都是一种“教化-控制”话语逻辑[14]下绝对化甚至神圣化的“物化之书”,而代表着个体话语权的“人化之书”却被剥夺于这一教化过程之中——这哪里是彰显读者个性自由的“人读书”?分明是阅读教化论下的“书读人”!它只能使读者在获取客观知识的同时丧失其主体智慧创造力,导致本源于人实践的知识作为人的对立面去禁锢人!因此,这种重物轻人的“无身认知观”(Disem bodied)下的“读者有其书”只能有外在“抽象的书”,而没有内在“自为的书”;这种有知无智的“为人找书”也仅能找到读者拥有“他人书”的形式,却无法收获创生“自己书”的内容。
后现代主义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有赖于人的历史、语言而“共在”于“生活世界”(The life w orld)中:其形式以情景化的涉身认知表现出来,其内容通过不同个体认知的整合和转化不断拓展。因此,知识的进化离不开读者的多元知识结构,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个体的自主实践参与。而个体“自我”(Ego)的觉醒正是W eb2.0文化所倡导和提供给后现代教育的新动力。作为一个自组织学习系统,Library2.0为后现代个性化、多样化和差异性的教育理念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15]。在这个平台上,不同读者通过交流,不断将客观知识“内化”为主体智慧,将社会经验转换为个人意识,从而不断生成着表征其生命价值和确证其生命存在的“涉身认知”的“自我的书”。
因此,后现代图书馆的特征在于借助W eb2.0技术形式对用户知识结构建构过程的介入[16],使读者和作者自由建构自己的知识[17]——它不仅是“读取别人”既成客观知识的单向、静止“获有结果”,也是“实现自我”主观个体知识的交互、动态“创生过程”。它激扬生命的本真意蕴,凸显图书馆的人文关怀,使读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主体。而正是这种基于“涉身认知”的个体话语的兴起,意味着“教化-控制”被祛魅(Disenchanted),标志着现代图书馆学向后现代图书馆学的转型[18]。
3 第三定律:书要有什么样的读者?
基于传统“主客二分”认识论下的第三定律“书有其读者”,无疑将“书”与“读者”割裂对立,造成对象化的“读者”以一种“局外人”的眼光“静观”知识。而后现代主义强调认知是定域(Located)和参与的(Participate),即读者与环境的交互及其反馈对知识建构有决定性作用。因此,知识并不是传统“主从对立”下的总结性(Summ ative)独断,而是“主体间交互”中的生成性(Enactive)过程;读者也不应以“知识旁观者”(Spectator of know ledge)的身份单向遵循地“听”,而是要以参与者的身份双向探讨地“说”——正所谓“学问”同时包含着“学”与“问”两层含义,研究学问也不应仅“读”取统一“真理”,而还要“问”以不同“意见”。这正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也不是完全相信知识,而是要在认知的基础上独立思考,有所创新。因此,后现代语境下的“书”所需要的不应是“尽信书”而被动接受的“读”者,而是有批判精神、主动质疑的“问”者和有主见、能够提出不同见解的“思”者。
由此看出,后现代视野下的图书馆、文献信息与人实质上是一种价值互动的对话关系[19]。作为读者的人是一个基于“我问”“我思”的主体间存在:他唯有主动地建构意义,才能获得自我的意义;他唯有通过与社会的关联,才能反观其价值的存在。然而,以书籍阅读来进行单线知识传播的传统图书馆并不能实现多重网状的反馈回路(Comm unication circuit)[20]。而Library2.0不但以“对话”作为交往逻辑,而且以共识作为对话目的:它不仅在空间上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知识间的转化提供了理想的情景域(Field),还通过“可写”的弹性网络阅读促进了读者对知识的自由反馈和充分反思,从而使互动、分享和评价成为学习的维度[21]。因此,Library2.0的读者不再是被动“下载和阅读”的知识接收者,而是主动“上传和分享”的知识建构者。
4 第四定律:“节约时间”是手段亦或目的?
当今图书馆在技术崇拜论的喧嚣中不断高扬着Library2.0、云计算等满足第四定律“节约读者时间”的便捷信息工具。然而“手段的完善和目标的混乱,似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22],在技术时时更新,知识刻刻变化的后现代社会,我们在重视获取既有知识效率的同时,却忽视了新生知识更替的频率;我们踏着传统客观主义的足迹,执着于减少静态知识获取时间的量变,却没有跟上后现代动态认知理念质变的步伐。如上所述,后现代知识已经不是一个静止获取的结果,而是一个读者融入其中的持续性学习过程,我们唯有不断地学习,才能避免被时代淘汰的命运。然而,“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正如杜威提出的“教育即生活”,人毕生都应在学习中成长。因此,强化终身学习的教育职能,有效组织读者学习活动才是后现代图书馆的本质所在[23]。
由此看来,Library2.0不仅是一种对象化信息技术,更是一种创生性学习理念。它不仅以泛在、共享作为节约时间的实体之器(手段),更是以突破时空限制的自由精神彰显人“自我超越”类本质、以“读者参与”凸显人自为本性的“探究式”学习之道(目标)——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盖阴阳亦器也,而所以阴阳者道也”[24]。同理,后现代图书馆也要实现从以技术“锋芒”切斩知识获取时间的有形“剑器”,向以智慧“光芒”透穿时空的无形“知识场域”之“剑气”,即后现代图书馆学所具有的精神气质[25]的功能转换,从而将图书馆传统信息职能之器与后现代教育职能之道辩证统一于Library2.0“网络社会化和个性化”的创造性学习实践之中。
因此,我们不仅需要节约外在知识获取时间的Library2.0信息泛在图书馆,更需要以其“参与和共享”精神提升内在知识转化时间的后现代“泛在教育”(Ubiquitous education)即“泛学”图书馆。借用福柯语言哲学的概念,后现代图书馆不仅是一个“陈述”背景下向读者提供文献的泛在信息中心,还是一个“话语”背景下交互认知与终身学习的“泛学”学习中心[26]——在这里,事事都是学问,时时都是学习。它以“反求自识”的内省精神超越了“理在心外”的时空境域,践行着后现代图书馆服务的至高境界。
5 第五定律:图书馆的本体存在吗?
第五定律将图书馆视为一个“不断生长的有机体”,具有概括性的本体论意义,然而“解构”是后现代的根本性理论,它终止了一切诗意唤醒的本性,放逐了一切具有深度的确定性[27]。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营垒都难免被解构的命运[28]。这对于带有本体论色彩的第五定律当然也不例外。那么,后现代语境下的图书馆本体究竟是否存在?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所有哲学史上的“本体论情结”都是传统基础主义追求“超验本体”终极存在的逻辑使然。然而,“上帝是诗人,不是数学家”,任何所谓“价值中立”的客观绝对性背后都实则是“人在场”的“价值负载”。因此海德格尔指出,虽然“本体”一直被视作最高的理性“存在”范畴,但“存在”一直被误读为感性的“存在者”。这种作为存在者的存在总是以“在相应的科学探索中专题化为对象”的形式表现出来:我国图书馆学界诸如“第三世界论”“知识组织说”等本体论的实质都是不同“视界”下“人”建构的本体形式展现,是图书馆本体的“存在者”。而图书馆本质这种永远不可确定的东西,与其说它客观存在,不如说它“没有”[29]!
然而,后现代主义却并不是“贵无论”——它不仅是对现代性的解构,还是对现代性的重写;它不仅要“以无为本”,还要“以无为用”——而用的主体则必然离不开人:后现代性作为现代性对人性压抑的反动,其全部旨趣就在于实现人对建构世界及其意义的主导地位。因此,以不断解构去建构的本体作为超越性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人类的成长论、人性的伸张论和心灵的拓展论[30]。由此,笔者认为,后现代图书馆学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再通过将图书馆存在专题化为对象来追求其“实在”的本体“是什么”(W hat),而是通过追问其存在何以可能(How)来不断揭示、领悟图书馆存在的价值,进而凸显人的意义。因此,本体不是已成之识,而是未竟之事[31]。我们以界定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方式不断追问图书馆学的本质并不是在寻找本质,而是在制造本质[32]。同样,Library2.0的魅力亦在于它的发展无穷无尽:网络文化所赋予人们的学习弹性是无法估量的,它亦将带给人们更多的批判冲动与反思空间[33]。因此,以持续生发着人追寻生命本真(Leben)的新意义为旨归的后现代图书馆就是要通过Library2.0,使“人与书”从主客“我-他”的“独白”下解放出来,重塑主体间“我-你”的“对话”,从而引领读者从自在到自为,学习从自发到自省,并在此基础上自主地生成、建构一种内在的文化世界,这也是后现代图书馆文化意识建构性品性的应有之举[34]。
6 结语
后现代语境下的五定律是一个永恒发展的生成性理论。作为一个带有强烈后现代情结的作者,笔者并无意于构建一个新的五定律“客观逻辑体系”以为读者所“读”,而是以“隐喻”最大化表达“隐性”的后现代理念对五定律进行了无回复的“问”,以期待为读者所“思”——正如前所述,“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比答案更有意义”[35]!在互联网不断升级、Library2.0不断演进的后现代,我们理应在追寻和探索图书馆服务转型的过程中不断提出新问题,引发新思考,为作为信息时代“知识产消者”的读者开辟更多的想象空间,从而激发其主动参与知识建构的能动性,发扬其个体认知的主观创造力,进而在以后现代“超越精神”不断“解构与重写”图书馆服务准则的基础上持续推动五定律的“返本与开新”。
[1][25]邱景华.后现代理论与中国图书馆学[J].图书馆杂志,2011(9):11,8.
[2]袁维新.从授受到建构——论知识观的转变与科学教学范式的重建[J].全球教育展望,2005(2):19.
[3][16]梁灿兴.不可或缺的黯淡蓝点——图书馆后现代浪潮中的现代性[J].图书馆,2009(4):3-4.
[4]杨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在当代的相遇[J].学术界,2000(2):14.
[5]黎莉.后现代知识观与图书馆的变化和发展[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8(33):24.
[6]W ersig G.Concep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history,empiricaland the theoreticalperspective[M].London:Taylor Graham Publishing,1992:205-208.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4.
[8]张晓林.重新定位研究图书馆的形态、功能和职责[J].图书情报工作,2006(12):5-10.
[9]王蓉光.后现代社会与图书馆知识服务[J].兰台世界,2009(18):79.
[10]朱伟珏.信息社会学理论概述[J].国外社会科学,2005(5):7-14.
[11]韩震.全球化与后现代哲学语境中的高等教育改革[J].新华文摘,2005(22):137-143.
[12]崔新建.从创造性应用到应用性创造[J].哲学动态,2004(08):6.
[13]许正兴.智慧服务背景下的图书馆学五定律推演与重构——以后现代构建主义知识观为视角[J].图书馆论坛,2015(1):25-29.
[14][18][29]蒋永福.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理论品格[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9(4):26-27,25.
[15][33]江卫华.W eb2.0网络文化的后现代教育现象[J].现代远距离教育,2006(6):74-75.
[17]Radford GP.Flaubert,Foucault and the bibliotheque fantastique:Toward a postmodern epistemology for library science.Library Trends,1998(4):616-634.
[19]吴慰慈.图书馆学概论[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143.
[20]R.Darnton.W 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J].Daedalus(Summer):65-83.
[21]Ruth Craw ley:CSCLW hat’s in a Name?[DB/OL] http://www.bton.ac.uk/cscl/jtap/whatis.htm.
[22]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M].许良英,李宝恒,赵中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541. [23]颜务林.后现代图书馆的职能定位——对“图书馆是学习中心”这一命题的学理分析[J].新世纪图书馆,2013(3):9.
[24]朱熹.朱熹集:第四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255.
[26]Hubbard TE.Bibliographic instruction and postmodern pedagogy[J].Library Trends,1995,44(2):439-452.
[27]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44-145.
[28]蒋永福.不再追问本质:图书馆学理论的后现代走向[J].图书情报工作,2010(1):6.
[30][31]王岳川.艺术本体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75,367
[32]陈立华.论现代图书馆学的实践论与后现代主义理论范式的冲突及延续[J].图书馆,2011(2):41.
[34]万进.信息技术语境下高校图书馆文化自觉价值取向的主体间性诉求:一种后现代的检视[J].图书馆,2009(2):42.
[3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489.
Inquiry and Reflection of the 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 in the Library2.0 under the Postmodernism Context
XU Zheng-xing
From the aspect of postmodernism,this paper has a comprehensive reflection of the 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 through theassociation between postmodernism and Library2.0.Then it raisesappropriatequestions on the basis of the deconstruction.This article aims to trigger readers’thoughts about postmodern library service and to providea theoreticalsupport for libraries’transform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Five Lawsof Library Science;postmodernism;Library2.0
格式许正兴.后现代语境下基于Library2.0的图书馆学五定律追问与反思[J].图书馆论坛,2016(1):26-30.
许正兴,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任职于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2015-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