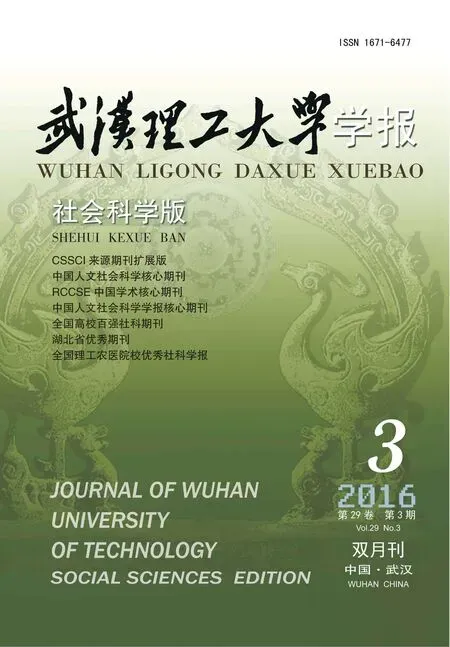本真性·有死性·自由
——李贽美学思想的存在主义维度审视*
潘海军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本真性·有死性·自由
——李贽美学思想的存在主义维度审视*
潘海军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对李贽美学思想的研究,学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外学者讨论最多的是其理论渊源,但总的来讲,均不能超越儒道释的逻辑范畴。在当今学界,从存在主义维度来研究李贽美学思想的尚存阙如。在借鉴前辈学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论析了李贽美学思想所内含的本真性、有死性及自由三个价值范畴,并系统探讨了其背后的哲学本体论基础。
李贽;本真性;有死性;自由;存在主义
在中国明代的学者中,能够一生以求生死大学问为自己的使命,且勇于解剖自己灵魂深处问题的人除了王阳明之外,则当推李贽。他的美学思想是以对人的自然本性的肯定为核心来展开的,将人性提升为最高本体,是中国近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中国知网以“李贽美学”为主题词以检索中国期刊论文,在1980—2012年间共有133篇研究论文,且相互重复现象较为严重。总体而言,学界对李贽美学思想的研究大致呈现出如下几种理路:首先是心学传统研究。如日本学者岛田在《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一书中总结的那样:“童心说”是心学的逻辑终点,也是中国近代思维的一个顶点。李贽虽是王学左派的代表人物,但受泰州学派“心学”的影响较深,对心学也有较大的超越。潘运告认为:“李贽吸取并充分发挥王阳明的心学思想,阐发人的主体精神,阐发个体的独立人格和人生价值。”[1]79李泽厚等人的观点也与此大致相同,学界遵循此理路予以研究的较为普遍。对李贽的美学思想基本上从精神资源的吸纳角度来分析,比如心学的个体受用、佛禅的自我解脱、老庄的自我关注等等,大都重视其心学传统的挖掘与整理。以蔡仲德为代表的很多学者提出李贽美学思想的反儒教本质,具有师法道家的自然浪漫精神传承。这样理解有其合理性,但是忽略了问题的复杂性和深刻性,由于没有注意到“由乎自然”的原发性真实与生命觉醒的关系,故对李贽美学思想的解读有其片面性和局限性。还有的学者从社会历史角度来思考其美学思想产生的必然性,其从明代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层的开始扩大、旧的观念和意识发生动摇等方面出发,强调李贽的美学思想是这种社会变化的要求和反映。另外从启蒙角度来探讨现代价值观点的文章和著作也相当丰富。李贽的美学思想表面看来较为驳杂,不易概括,但是其内部隐含着深刻的逻辑结构。由于受到机械社会学的影响,许多学者皆从进步意识来解读李贽的美学思想,而没有从生命语境和哲学语境的高度来探讨其深刻的心灵诉求。解读李贽的美学思想要还原其原生态面目,研究者要充分重视“体验”的有效应用。笔者在吸纳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存在主义视角来解读李贽的美学思想,并大致勾勒出其美学思想三个价值范畴,期望能为学界提供一种更具个人化的解读视角,敬祈方家指正。
一、李贽美学思想的本真性
李贽的本真性美学思想,主要是一种揭橥自然人性的本体论。他倡导的“自然”、“童心”等学说,实际上强调内部情感的原发性真实,这种价值理想极大地强调了自我接触的重要性。艺术美感与个体道德性的有无都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动”[2]80,“自然之我”意味着守护自己的原发性真实,而道德力量则蕴涵于这种本真性的诉求之中。在他看来,成就自我乃至于实现自我皆有赖于此。李贽本真性美学思想发端于道德重音的移位,在充斥“代圣人立言”的文化氛围中,他强调内部声音的重要性,“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3]273一个人要始终与自己的道德感受保持接触,坚守本真成为完整的人不可移易的内在本质。而文艺贵在表达“童心自出”的真实与自然,他主张“童心者之自文”,各人应从自己独特的情性出发作赋为诗,只要就此境域把本真之性情自然发出去,不矫作而求真,不执己而求同,则“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扬,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性自然之谓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然则所谓自然者,非有意为自然遂以为自然也。若有意为自然,则与矫强何异?”[2]67正如学者于浴贤所言,“摆脱了儒学孔教的桎梏,抛开世俗欲利羁绊的人生,何等轻松自由,何等率性真诚。李贽所描述宣扬的人生,是回归人性本真、自由淳朴的人生,是李贽所追求的以真心、真事、立真言的真实人生。”[4]
李贽倾心于洒落清真的精神,赞叹“不蹈故袭,不践往迹”的狂狷之士,痛斥那些畏缩自我心性的怯懦之徒。他批判“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道学先生,皆是“欺世盗名,不宜信用”的功利之徒,并嘲讽儒士乃“依仿陈言,规迹往事,不敢出半步”[2]227的保守者,是“操一己之绳墨,持前王之规矩,以方枘欲入圆凿”[2]15的僵化主义者。李贽带着巨大热情致力于扭曲人性的非人文化的匡正,竭力张扬自我的真实情思,反对一尊思想“强而齐之”。他自喻“如凤凰翔于千仞之上”,坚决推崇自我生命的独一性,“宁使天下以我为恶,而终不肯借人之力以为重”,主张“性非一种,道非一途”,对思想规训造就的僵化局面尤为愤懑不平,认为只有“顺其性不拂其能”,才能展现生命的真实与精神的活力。李贽指出“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2]16,思想定为一尊必然异化本真精神:“儒先臆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朦聋而听之”,正因为思想盲从才导致了“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的恶果,导致了“至今日,虽有目,无所用矣”[2]318的偏枯本质。李贽崇本真、倡狂狷、尚真率,他认为文艺创作皆来源于情感的自发性,来源于情至、情深、情真,倡导文艺当追求“为情而造文”“志思蓄发”的“化工”境界:“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2]245这一文艺观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和推崇,开启了一代文学的新风尚。
李贽倡导文艺创作的“本真性”,来自于他思想中“道自我出,天不足言”[2]235的哲学认知。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提出的原则之一则是“存在先于本质”。萨特认为人的“存在”在先,“本质”在后。所谓“存在”,首先是人的存在、露面、出场,是自我感觉到的存在。我不存在,则一切都不存在。所谓“存在先于本质”,即是“自我”先于本质,也即是人的“自我”决定自己的本质。在萨特看来,人偶然地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本质可言,人的本质皆是行动的结果。而李贽对世界的永恒本体也如萨特一般,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李贽否认了有所谓“道”先于生命的依据存在,他说:“见得未生前,则佛道、外道、邪道、魔道总无有,何必怕落外道乎?”[3]1在生命未存在之前,统摄生命本质的“道”皆虚妄,故生命之“道”应该与生命同时存在。虽然李贽谈的是生命之道,但是也是宇宙之道和真理之道,其思想的主旨则是反对先于存在的“本质”,主张“道自我出”的本真显露与敞开。他评价俞伯牙之所以能够获得很高的艺术造诣,就是来源于对本真自我的守护:“唯至于绝海之滨、空洞之野,渺无人迹……故乃自得之也。”[3]133生命个体都具有不可移易的独特性和殊异性,“成连有成连之音,伯牙有伯牙之音”,自然之本心的维护来源于道德本体的觉醒,扎根在自我精神的“苏醒”之中。本真性自我的真实坦露作为一种美学精神,源于与自己内部本性的接触。“学人者不至,舍己者未尽”,而儒生由于外部压力而采取工具态度,从而失去了这种倾听内部声音的能力。他认为“真信本心,勿顾影,勿疑形,则道力固自在也,法力固自在也,神力固自在也”。本真性美学思想是从存在的维度出发自上而下对美学所作的本体论规定,乃是实现自身、肯定自身的重要领域。这种自觉意识,实际上是近代美学的逻辑起点。
他倡导文学创作的本真性追求,实质上是超功利、重想象、尚虚灵的创作心境,唯有此才可能产生真言、真文。倘若一位作家创作之际还心存戒律,未达空明自如的状态,则思理不畅动笔有碍,又何来生花妙笔之文?李贽在远行前其母曾与之书,深沉地表达了对李贽的牵挂,读后不禁令其痛哭:“言出至情,自然刺心,自然动人,自然令人痛哭,想若无必然与我同也,未有闻母此言而不痛哭者也。”真感真情,必然产生出感动心灵的艺术力量。他从内心里仰慕陶渊明:“夫陶公,清风被千古,余何人而敢云庶几焉?然其一念真实,不欲受世间管束,则偶与之同也。”(参见彭际青《居士传》卷43《李卓吾传》)故原发性的自然坦露乃创作之源,它使得创作主体能够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激发创作主体的创作能量,由此构建的本真性品质乃文艺之本体。
二、李贽美学思想之有死性
本真性追求意味着被抛入生存论的责任之中,在存在者的层次上,良知的声音发现自己陷入自己的存在深渊之中。海德格尔认为,良知的召唤在存在论上是可能的,仅仅因为此在存在的真正基础是操心。李贽不断探讨追问“生命”的意义,反映了作为被抛于“此在”的生存所具有的基础存在论结构。他究诘“道”的结果落在了自然之道的本源上。“道”所具有的自然本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不长的时间内,李贽家中接连七位亲人相继去世,死亡的阴影萦绕在他的心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惧和参透生死难题的强烈愿望。对死亡的现象学领会,促使他对此在予以生存论意义上的把握和分析。李贽经历了“大衰欲死”,突然“于生死之原窥见斑点”,实际上是从最彻底最原始的意义上把自我的生命看作是终有一死的生命,生存的纯粹偶然性昭示了建构完整性、本真性的生活,并在其可能性中开放自己。
随着“知天命”之年的到来,李贽对自己“生死根因和性命下落”的内在操心与日俱增,他对死亡的焦虑无法消解。他言及自己一生“到处为客,无定生处”,只能借助佛学来消解自己无根性的存在焦虑。嘉靖四十五年,李贽安葬好父、祖三代,婚嫁毕弟妹,完成伦理责任卸去家庭重担后,他潜心于对人生终极问题的解惑:“唯志在闻道,故其视富贵若浮云,弃天下如破屣然也”。万历八年他为了能够释然对人生之谜的困扰,矢志参透生死之玄学,竟然有官不做,有家不归,只身赴异地湖北黄安,日夜“闭门下键”读书,以闻道为最终的使命。万历二十七年,他曾在所居禅房贴一副对联,上联为:“无事常如有事时提防”。一位后学之士不解问之,李贽答曰:“凡事也要提防。如出路人不论晴雨,必先备了雨伞;未上船,就要来米买柴,这都是提防。吾人为生死事大,也是这等提防。”
存在主义哲学认为,只有对死亡现象及其此在角色获得更加彻底的了解,才能揭示出它的生存论意义。而欲从生存论的意义理解死亡,则必须作为此在存在的一种可能性来理解。海德格尔认为:“死亡是此在绝对的不可能性的可能性,因此死亡把自己作为某人最本己、非关系性的、不可捉摸的那种可能性揭示出来。就其本质而言,死亡是以与众不同的方式正在悬临的东西。”[5]294正因为死亡是悬临着的可能性,面对这种纯粹的威胁,海德格尔把生存主体与自己的终结关系称之为“向死而在”。生存主体在此向度上建构起了真实生存的可能性。李贽多次谈到人的生命注定要被死亡剥夺,要被死亡抽空或变成虚无,他为此操心焦虑,甚至“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万历二十一年与友人共游龙湖,伯修对其问道:“学道遂不怕生死否?”李贽回答说:“别人怕不怕不可知,我却怕。”他曾对好友梅澹然谈及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尤甚:“且湖上僧虽能守戒行,然其贪生怕死,远出亡僧之下,有何力量,可以资送此僧?若我则又贪生怕死之尤者。”畏、焦虑、苦恼、形而上恐惧暗示了未来将临的灾难,印证了存在主义者具有的本质情绪。直面“畏”意味着从日常生活的“不诚”之中超拔出来,回归本真存在,并呈现出敞开自我的现身情态。
李赞认为艺术创作来自于心灵的觉醒,任何人不能超越生理上的衰老以及死亡的定数,故要“发念苟真”。 这种“发念苟真”所引出自我揭示的具体形式,就是一种缄默的自我筹划,朝向自己最本己的终极存在,存在主义哲学里称之为“决断状态”。“决断状态”并没有与世界完全分离开来,而是涉及到在何等范畴中筹划自己,并最终被赋予生存论上的规定以及自己的活动背景:“学道人大抵要跟脚真耳,若始初以怕死为跟脚,则必以解脱生死、离苦海,免恐怕为究竟。虽迟速不同,决无有不证涅槃到彼岸者”[3]1、“生死原是超的,你要出生死,便入生死了。言已,复且弹扇,且申语曰:生死原是超的,要出生死,便入生死。只是此处也要晓得,所以又不可不学。”[3]1对终极意义的惶惑与焦虑使李贽不得不进行形而上的思索与观照,他思考儒道释对此的阐释:“‘咔地一声’,道家教人参学之话头也,‘未生之前’,释家教人参学之话头也,‘未发之中’,吾儒家教人参学之话头也,同乎,不同乎?唯真实为己性命者默默自知之,此三教圣人所以同为性命之所宗也”[3]113。在所拥有的文化资源之中,他不断地“穷究自己生死根因,探讨自家性命下落”,其彻底性在于自我的生命不是从外面获得规定的,而是以生命个体对其存在的承担方式而规定。这种担荷赋予生活一种整体性,而文艺的功能则正在于舒缓或解脱“有死性”之“沉重”。
李贽认为:“读书伊何?会我者多。一与心会,自笑自歌;歌吟不已,继以呼呵。恸哭呼呵,涕泗滂沱。歌匪无因,书中有人;我观其人,实获我心。哭匪无因,空潭无人,未见其人,实劳我心。弃置莫读,束之高屋,怡性养神,辍歌送哭。何必读书,然后为乐?乍闻此言,若悯不谷。束书不观,我何以欢?怡性养神,正在此间。世界何窄,方策何宽!……歌苦相从,其乐无穷,寸阴可惜,曷敢从容!”[3]228“有死性”的形而上“迫压”决定了在世存在以及所关注的问题,悲欣交集的心灵则欲求“歌哭相从,其乐无穷”、“歌咏弹琴,乐而忘死”的至高境界。他认为:“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焚书·忠义水浒传序》)在文艺创作上他倡导“愤”而为文,这种“愤”既指个人之忧愤,也指人类公共之忧愤,内含有焦虑、惶惑、忧郁、烦、畏等情感。他要求作者“蓄极积久,势不能遏”的情感孕育,一旦发而为文,纵然“予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这种“忧愤”之情感显然是“非理性”的表达,是对传统儒学提倡的“致中和”“温柔敦厚”等美学传统的冲击。因其来自生命体验的非理性情感抒发,是生命沉醉中释放出的本真创造,具有震撼心灵的艺术效果。
李贽弟子汪本钶在评论李赞的创作时说:“盖言语真切至到,文辞惊天动地,能令聋者聪、聩者明、梦者觉、醒者醒、病者起、死者活、躁者静、聒者结、肠冰者热、心炎者冷、柴栅其中者自拔、倔强不降者亦无不意頫而心折焉。”[6]李贽认为欲通达文艺则识、才、胆是最重要的。而识是第一位的,“才与胆皆因识见而后充”。要想达到“出词为径,落笔惊人”,须有“二十分识,二十分才二十分胆”。(《焚书·杂述》)这种“识”意味着写作主体处于旷世般的孤独,正如其诗所言:“独雁虽无依,群飞尚有伴。可怜何处翁,兀坐生忧患”。孤独与“操心”皆与有死性及终极虚无有关。存在主义哲学谈到“自由的眩目”,意味着深渊现身,大地根基的缺失。“识”还意味着写作主体拥有的“深渊意识”和“悲剧体验”,个体存在从公共世界之中抽离出来,只能做“淹留客”,“躯壳终是个宅子”。正因为虚无是“世界之为世界”的本质,故“多一日在世,则多沉苦海一日,诚不见其好也”,又言及“所喜多一日则近死一日,虽恶俗亦无能长苦吾也”(《答友人书》)。一个将世界视为“监牢”并退守其内在自我的人,必然反叛社会所固有的习惯、意见和品味,李贽以自我精神的彻底性和一贯性践履了追求“自由意志”的生命理念。
三、李贽美学思想的自由精神
存在主义的核心是自由,萨特认为,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不可让渡的自由,面对各种环境,采取何种行动,如何采取行动,都可以作出自由的选择。自由选择是存在主义的精义。李贽推崇自由选择,他认为“夫天下至大也,万民至众也,物之不齐,又物之情也。或欲经世,或欲出世,或欲隐,或欲见,或刚或弱,或可或不可,固皆吾人不齐之物情,圣人且任之矣。”[7]115决定论是没有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意志作出“自由选择”,“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每个人都当“各从所好,各骋所长”,“道者,路也,不止一途;性者,心所生也,亦非止一种已也”,唯有自由的人生才能实现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李贽曾言:“凡人作文皆从外面攻进去,我为文只就里面攻打出来”,他倡导“以自然为美”、要求艺术家自由地书写,而不应以群体伦理意志为艺术定性,以个人自由情感的抒发来为艺术立法。有学者认为,“李贽把自由的生命追求视为其人生的无上追求一样,他也把自由的情感追求视为其人生的最高追求。同理,正如李贽可以为自由的生命追求而宁死不屈一样,在自由的情感追求上,他也是那样的执着。”[8]
对自由精神的渴望是李贽人生追求的真谛所在,他提出“古之立言者,皆卓然有所自见,不苟同于人,而惟道之合,故能成一家言,而有所托以不朽”。李贽主张人是自治自律的主体,凡是不尊重道德主体的自由意志皆是“伐”,是所谓“以彼柯易此柯”。他认为“人即道也,道即人也,人外无道,而道外也无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人从根本上说就是自由的。学者傅小凡认为,“尊重个体之人,必然会尊重个性,崇尚自由。人即道,道即人,人天性好自由,所以自由也是合乎道的。因此,在李贽心目中,求道与追求自由是一致的。所以李贽主张,信仰自由,学术自由,个性自由。”[9]正如法国先贤卢梭所言:“人生来是自由的,却无时不处在枷锁之中。”李贽处处感到“枷锁”的存在,他自言“平生不爱属人管”,追求自我生命的自主性,但现实的禁锢却无时不在:“夫人生出世,此身便属人管了。幼时不必言;从训蒙师时又不必言;既长而学,即属师父与提学宗师管矣。入官,即为官管矣。弃官为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其为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管束得更苦矣”。(《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但是,“卓尔不群的李贽坚持以‘真’为武器,以人的本真生存状态为出发点,高举人的自然本性的伟大旗帜,向着以人的个性自由和人的主体性目标迈进。”[10]
李贽追求的自由首先是一种审美的境界,学界对此认识大抵相同。许苏民认为,“在李贽的思想中,‘自然’与‘自由’是同等程度的概念,即本质上相通的概念。所谓‘自然之为美’,实即‘自由之为美’。因为美的精髓在于自由,美的领域中的活动是灵魂和精神的一种解放,是摆脱一切压抑和限制的过程。美向人们展示什么是真正美好的生活和应当如此的生活,美的本性要求人的精神插上自由的翅膀。”[11]李贽认为“学至游艺,至矣,不可以有加矣。”艺术的真谛是“顺其性”,是“率性之真”,“凡艺之极精者,皆神人也”,因为艺术能够让“人我俱泯则生死两忘,生死两忘则寂灭现前,真乐不假言也。……此乐现前,则当下大解脱,大解脱则大自在,大自在则大快活。世出世入,无拘无碍,资深逢源”,最终成就“一己快活之心”[7]5。这里的“大解脱”、“大自在”皆是自由精神的体现,把人的感性存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一次把个体的心灵自由和个体的感性自由统一起来,给美学注入了新的人生内涵。张少康先生认为[12],李贽的自由追求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没有一点虚假的成分,是最纯洁最真实的,没有受过社会上多少带有某种偏见的流行观念和传统观念的影响”。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讲,自由是相对于两种约束而言的。一种是“社会理性”,另一种是“自然暴力”。 李贽敢于破解权威,追求自由,始终尊奉“见从己出”,是对社会理性规训心灵的个体反抗。同时,他敏锐的心灵以及现实的悲怆困境让他时刻感受到天地之间实乃大的囚笼,即使以“大地为墨,难尽写也”。苦难意识促使人觉醒心灵的深刻诉求,“知此极苦,故寻极乐”。而“极乐”则是对苦难之境的超越,存在的意义在“探讨性命下落”,其基点就奠定在对终极自由的追求上。
李贽认为,只有“深愁痛苦”才能达道“生知”,而自己对于虚无则浸淫于心。自称“无时不梦,无刻不梦。天以春夏秋冬梦,地以山川土石梦,人以六根、六尘、十二处、十八界梦,梦死梦生,梦苦梦乐,飞者梦于林,跃者梦于渊。梦固梦也,醒亦梦也,盖无时不是梦矣,谁能知其因乎”[7]113在茫茫的宇宙之中,人类实质上是“既无所来,则无所去,在古在今,镇然一我而已”[7]5。他听闻可能遭到迫害时大义凛然地说:“史道欲以法治我则可,欲以此赫我他去则不可。”“我若告饶,即不成李卓吾矣。”“故我可杀不可去,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是为的论。”(《续焚书·三教归儒说》)他刚烈决绝,不肯移易内在的持守。所谓“随其资性,一任进道”,是李贽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他明知自己的著述必然遭致杀身之祸,但依然故我,以致身陷囹圄,未等定罪“遂持刀自割其喉”。以颈就刃,“气不绝者两日”,侍者问其因何自刭,其书曰:“七十老翁何所求”。李贽以生命和鲜血来捍卫自己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意志。轰轰烈烈的崇高来自于悲壮激越的生命体验,极端苦闷悲愤的胸膛,燃烧成反叛传统的火光。李贽在狱中曾言:“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他的自杀不仅仅体现了反叛者对世俗的抗议,佐证了存在主义者在终极奴役与形而上反抗之间践履自由的命题考验。李贽堪称东方的“苏格拉底”,是中国文化人格中极其罕见的“哲学烈士”,他带着睥睨一切的自尊与献身真理的激情,树立起了一座自由精神的丰碑。
总而言之,李贽丰富的美学思想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在不同时期积累、演变而来的。他剥伪见真、追求自由思想的一生,造就了一部心灵的传奇。他创造性地融会伊斯兰教义、阳明心学、老庄之学、佛教经典,但“又创特解,一扫而空之”,使他的美学思想具有“存在主义”的哲学魅力。
[1]潘运告.冲决名教的羁络[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2]李贽.李贽文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3]李贽.李贽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于浴贤.童心说:李贽思想和生命的底色[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94-99.
[5]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2002:294.
[6]孙长军,杨德贵.李贽、龚自珍童心思想的多向辨析[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1):84-91.
[7]李贽.李贽文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8]张再林.作为情圣的李贽[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45-56.
[9]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91.
[10]魏中银,马树芳.狂狷童心与自然之子:李贽与卢梭诗学比较初探[J].江淮论坛,2011(4):81-84.
[11]许苏民.论李贽文艺思想的新理性主义特征[J].文学评论,2007(4):49-55.
[12]张少康.古典文艺美学论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49.
(责任编辑文格)
Genuineness, Fatality and Freedom: An Existentialism Perspective of Li Zhi's Aesthetic Thoughts
PAN Hai-jun
(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Culture,ZhejiangYuexiuForeignLanguageUniversity,Shaoxing312000,Zhejiang,China)
Academic circle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on the study of Li Zhi aesthetics ideology. The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mostly discussed the theory origin, but generally they can't go beyond the discussion of the logic category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None has studied Li Zhi's aesthetic thoughts from existentialism perspective until now.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es, focuses on Li Zhi's three value categories of aesthetic thoughts, including genuineness, fatality and freedom,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philosophic ontological foundation behind them.
Li Zhi;genuineness;fatality;freedom;existentialism
2015-11-22
潘海军(1973-),男,山西省应县人,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Y201534671)
I106.4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6.03.0004
——以黄麻士绅纠葛为中心的讨论
——《李贽学谱(附焦竑学谱)》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