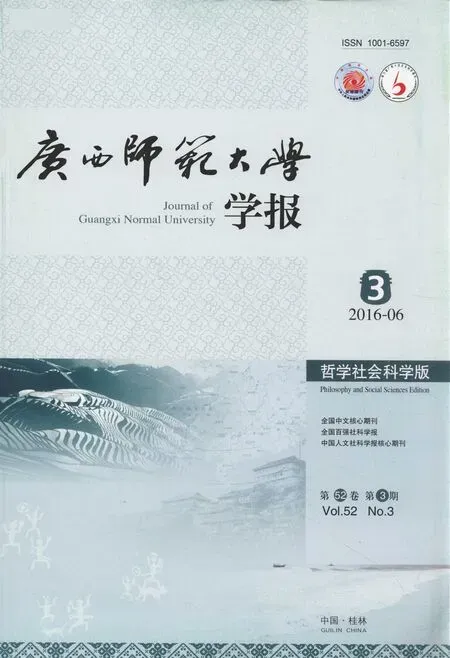论民间信仰在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中的功能
——基于那坡县黑衣壮聚居区的田野调查
李何春,包丽红
(广西师范学院,广西南宁530001)
论民间信仰在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中的功能
——基于那坡县黑衣壮聚居区的田野调查
李何春,包丽红
(广西师范学院,广西南宁530001)
[摘要]乡村治理是“学术下沉”、关注乡村社会自我管理和发展的实践探索,其逻辑依据是打破传统国家“自上而下”操控乡村社会的管理方式,并逐渐认识到乡村社会和国家统治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乡村社会早已形成一种可供内部自行运作的秩序。显然,这样一种产生于当地社会,对乡村社会的历史、演变和发展有重要影响意义的内在秩序,包含了民间信仰所发挥的正向功能,其在很长时间内伴随人类社会的演变和发展,对人类历史有重要影响。应辩证看待民间信仰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影响,吸收民间信仰对乡村治理的积极因素,有利于整合社会资源,强化民族认同,维护边疆稳定和团结。
[关键词]民间信仰;乡村治理;壮族;功能
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术界重新认识到乡村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从“村民自治”到“乡村治理”理论的不断探索和发展,表明乡村社会在整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与此同时也表明乡村在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以致需要重新定位和思考有利于乡村发展的治理模式。但是,在对乡村治理模式进行实践和探索时,显然不是一味地否定乡村社会内部早已形成的运作秩序,例如民间信仰的教化功能,而是要吸收民间传统文化中包含的治理因子,使之能有效服务现代乡村治理,这样才能有效避免政策强制执行所带来的非必要的文化冲突和公共事务管理成本的支出。
总体看来,学者将乡村治理的研究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理解乡村治理发生的背景、历史条件及其现实处境;中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理解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度和法律在农村实践的过程、机制及后果,并为理解农村政策的实践提供理论解释;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理解乡村社会内在的运作机制及农民的生活逻辑”[1]。显然,宏观层面的研究是认识乡村社会历史和现实的重要基础,只有掌握乡村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把握正确方向,才能提出相应的合理治理方案;中观层面的研究考察的是现代国家的政策和制度在乡村社会实施的进展,是要发现政策执行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微观层面的分析则是有效认识乡村社会本质的一把钥匙,有利于理解非均质化的乡村社会,以此提出多元治理的模式。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乡村治理不仅需要考察国家正统对乡村社会的影响,而且也要考虑乡村社会自有的秩序逻辑对国家政策的接受或回应。与此同时,微观视角的乡村治理是“学术下沉”、关注乡村社会自我管理和发展的实践探索,其逻辑依据打破了传统的正统政治制度“自上而下”对乡村社会的统治,认识到乡村社会和国家统治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乡村社会早已存在一种内部可以自行运作的社会秩序,这就需要显微镜式的观察。这样一种产生于当地社会,对乡村社会的历史、演变和发展有重要影响意义的内在秩序,包括了民间信仰——在很长时间始终伴随人类,对人类历史有着重要影响。正如学者所言,“在传统乡村社会,存在着丰富的治理元素,嵌在杜赞奇所说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中”[2],而民间信仰是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正是学者所提出的观点——在治理理论中,管理主体并非只有一个,可以存在诸如政府、公民团体甚至个人参与的多个管理主体。[2]笔者通过实地调查,考察广西那坡县黑衣壮聚居区的社会治理情况,从民间信仰以及族群认同面对外来宗教传播起到的阻隔作用来分析民间信仰的功能,认为辩证地看待民间信仰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乡村社会运作的影响,吸收民间信仰对乡村治理的积极因素,有利于整合社会资源,强化民族认同,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
一、民间信仰的社会控制功能
当下,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诸多学科都在关注民间信仰的相关议题,这表明民间信仰在现代社会进程中仍然是一个亟需进一步探索的领域。民间信仰总体上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神灵崇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不同的学科研究视角亦不相同,但是围绕民间信仰与国家、社会、民族等相关议题和相互关系展开研究,以及讨论民间信仰在这些互动关系中的功能是学界的一大共性。杨庆堃在论述中国宗教问题时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的宗教属于分散性宗教*杨氏将宗教分为制度性宗教和分散性宗教。制度性宗教主要以西方的基督教为代表,分散性宗教包括中国的儒教、道教、佛教及民间信仰,杨氏并没有将民间信仰分离出来。杨氏所说的宗教,很大程度上指的是民间信仰。,而且“在发散性的形式中,宗教发挥着多种功能,以组织的方式出现在中国社会生活中”[3]35,他还指出“低估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实际上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3]25。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研究”课题组经过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内信仰“民间俗神”的人数达11.5%,而信仰“祖先保佑”的人数达15.1%,两项合计人数达26.6%,这是很高的一个比例。[4]“根据2007年中国零点研究咨询公司“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所提供的数据,杨凤岗的研究团队认为“16岁及以上人口中,85%的中国人有某些宗教信仰或宗教实践,只有15%的中国人是真正的无神论者”[5]。两组数据表明,民间信仰在中国民间社会地位十分重要,毫无疑问,中国的百姓在生产生活中均离不开民间信仰。
应该说,民间信仰在乡村社会所发挥的功能,既有显性的,也有隐形的,既有正功能,也有负功能。而且在乡村社会中,民间信仰的隐形功能要比显性的功能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对于民间信仰功能的论述,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从民间信仰具有社会整合,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起到慰藉、教化、精神寄托,维护地方秩序等功能来看,具有一定的正功能。而将民间信仰当作一种迷信时,人们更多地批评民间信仰的消极性。围绕乡村建设和治理,人们的关注点显然是考察民间信仰与乡村治理的关联性,反思民间信仰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何种积极作用。毕竟“在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中,国家公共权力并没有深度渗入乡村社会,乡村治理所依托的更多地是建立在地位、财富和功名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公共权力”[2]。也存在这样的历史事实,即“民间信仰自古以来就不为政府所承认,经常处于被官方压制、打击、甚至被禁止的境地”[6]。但是,民间信仰是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呢?显然需要对民间信仰进行客观分析。
第一,尽管民间信仰很难被传统国家意识所认可,但是民间信仰始终伴随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种中国文化的“小传统”,甚至和以都市为中心的、以乡绅阶层和政府为发明者和支撑力量的文化(大传统)之间存在相当密切的关系。[7]141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民间信仰是一片汪洋大海。千百年间,极其庞大而又不断扩充的神灵队伍驻守在遍布村镇城乡的各色神庙,深入到各行各业、千家万户,普通百姓时时与‘有形’的神灵同在,也与‘无形’的神秘力量同在,对它们的崇信渗透到风俗、习惯、礼仪、禁忌当中,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8]显然,民间信仰始终在民间社会发挥着社会控制作用,是民间社会控制的一种力量,也是维持民间秩序的一种工具。[9]197这种民间秩序是以文化的传承为基础约定俗成的规范,成为限制人们从事各项活动时所遵循的准则。“民间信仰的规范作用在于它通过教义、教规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实质上是要告诫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评判人类行为、目标、理想、观念,甚至社会道德本身的标杆,起着凝聚人心、整合社会、稳定社会的作用”[10]。
第二,民间信仰的认识和研究应该放在一种历史观的逻辑关照中,即从历史演变来看,和国家统治意识渗入到乡村社会来比较,民间信仰在地方社会早已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起到慰藉、教化、精神寄托、整合、维护地方秩序等功能。学者指出:“除了自上而下的政策在农村社会实践产生后果以外,乡村社会内部也会自发地内生秩序,这种内生秩序构成了乡村治理的另一部分内容。乡村治理的内生基础研究,重在研究乡村治理得以发生的微观基础,而不是研究乡村治理本身。”[1]但是,不得不承认,从不同角度去看待民间信仰的功能时,因为衡量的标准存在差异,导致对民间信仰的看法发生偏离,肯定和否定的情况都会存在,甚至否定的声音比肯定的声音高,这是违背历史和现实状况的,也是不客观的。从现有的研究来看,人们对信仰的认识逐渐提升理论高度,扩大视野,最重要的是认识到国家统治和民间信仰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而不是二者相脱离。“研究表明,在民间信仰和仪式的传统形式外表之内,已经融合或渗透进了当代的国家治理技术和权力关系”[11]。应该说,民间信仰在乡村秩序中的控制作用,不同于国家制度化下所采用的强制手段,而是一种较为柔性的教化。但是这种柔性的控制力,弥补了单靠行政手段和法律约束难以深入基层社会的缺憾,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民间信仰能发挥更加有效的作用。在地方社会,特别是民族地区的乡村社会,民间信仰已经构成了一个体系,长期发挥着教化的作用。这是因为,“信仰的主旨仍是教化百姓和谐向善,其通过各类感性生动的民间故事的叙述将忠孝节义、和睦助人、积德行善、善恶报应、安分守己、无量度人等优秀传统道德观念渗透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世界并以此构成了底层民众最基本的道德‘知识储备’,为其人性向善与品德修养奠定了文化地基”[12]。
民间信仰之所以能在乡村社会发挥社会控制的功能,一定程度上维护当地的稳定和团结,避免乡民之间冲突的发生,这涉及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也是一个人情社会,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社会。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论述乡土中国的时候,提出了“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成为理解中国乡土社会的一把钥匙。熟人社会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典例,这在长期封闭、依靠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村庄更为突出。用当地人的话来说,“村里任何时候来了陌生人,大家都能知道”;“一个人走在路上,只要听到他(她)脚步声或咳嗽声,就能知道是村里的哪个人”。因此,在乡村社会一旦出现任何风吹草动,大家都能马上知道。而一旦村民的行为违反了乡约民规或风俗禁忌,作为村里的乡绅和精英将对其加以惩罚,这正是“民间信仰能够通过其自身所具有的并不成文的程式化规矩属性,对其信众群体的行为和意识起到一定程度的约束作用,并通过对社会各种关系和行为、意识等进行规范,进而实现其对特定信仰流行区域内民众群体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效应”[13]。有学者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分析了乡村社会通过民间信仰能促进乡民之间的信任,这为社会资本积累奠定了基础。从历史来看,“在信仰过程中,村民相互的信任逐渐滋长,人们超越了血亲范围建立起信任。宗祠与寺庙相结合,祖先崇拜和神灵祭祀相结合,反映出宗法制度与民间信仰的互动关系,把信任扩大,从家庭、社区扩大到全村、全县、全国,并在社会上形成规范,这个时候群体走向高信任,社会资本就增加和扩展”[10]。二是民间信仰起到整合的功能,容易建立起信任的支撑性社会网络。在乡村社会,一个村或寨都会有属于这个区域的一个或多个庙宇,这些庙宇中有些仅属于供某个区域内的人们定期或不定期从事相关仪式活动,有些庙宇则可以在特定的时间内接纳所有愿意祭拜的人。不管是何种情况,通过庙宇自身被赋予的功能,例如保护该地方人畜平安、风调雨顺、获得丰收等功能,或是一个庙宇能有多种功能,例如求子、求财、求平安等,都将一个区域内的人们整合在一起。有些庙宇只能在特定的时间去祭拜,其他时间不能去。有些则是本村人可以随时去,本村之外的人则不能。不管如何,在一定的仪式活动中,可以将不同的群体在特定的时间集中起来,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完成整个信仰仪式,体现仪式的规模和仪式组织者的权威,另一方面可以让大家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有沟通的机会。因此,由血缘、地缘和业缘所形成的信仰圈,其地方精英或民间信仰仪式中的长者都具有地方权威性,能博得大家的信任。
二、民间信仰强化族群(民族)认同,利于乡村稳定和团结
广西是少数民族分布较多的省份,除汉族之外,有壮、瑶、苗、侗等在内的11个少数民族。其中,壮族在整个广西少数民族中占到80%以上,主要分布在南宁、百色、河池、柳州4个地市。那坡县地处广西西南部,西北靠近云南省富宁县,南部与越南接壤,东临靖西县。那坡县下辖9个乡镇,130个行政村(社区),聚居着壮、汉、苗、瑶、彝五个民族,总人口20多万。全县是以壮族为主的县份,总人口中,壮族人口占90%以上。壮族按自称和语言划分有12个族群,分别是布壮、布央、布垌、布农、布税、布依、布嗷、布省、布决、布拥、隆安、左州等。其中布壮因自古以来穿着自制的黑衣服,又称为黑衣壮,总人口5万多人,占当地壮族人口数的33%,遍及9个乡镇,130个行政村(社区)。*《那坡县黑衣壮文化保护措施情况》,那坡县妇联提供。
黑衣壮以服饰为黑色而著称,这成为该族群的一大特点。笔者深入那坡县城厢镇调查之后,发现这里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十二三岁的孩子,都能说出黑衣壮的来历,并与壮族英雄人物侬智高有着密切联系。调查表明祖先(英雄)崇拜在当地民间具有强化族群认同的功能:
像以前,我们这边的壮族头领是侬智高,他以前要逃去云南的时候,因为打了败仗,又有很多伤亡,就路过我们这里,后边一直有追兵在追杀,到我们这边有个山洞,就在这里躲起来。这些伤者都伤得比较严重,然后他们就会拿蓝靛,这种草是一种很好的止血药。然后他们就用蓝靛治好了士兵的伤,好了以后他们想到的是如何反击。发现这种草你要是用牙齿嚼的话,它会出现很黑的汁,然后他就想到用它把衣服染成黑色。然后晚上去偷袭对方,后来果真偷袭成功了。他(侬智高)为了纪念这场战争的胜利,他就把所有的、什么的都染成黑色。这一过程把枪都染成黑色了。然后这个族群在壮族中就被称为黑衣壮了。*2014年8月那坡县吞力屯田野访谈资料,访谈对象:黄慧莲。
黑色成了黑衣壮族群的一个象征性符号,形成了该族群的强烈认同感。族群认同是基于英雄人物的崇拜和信仰,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区别“我者”和“他者”的作用,以此建构起一道族群的边界。从工具论的视角看,具有较强的功利性。这一功利性的出现,不仅建构了黑衣壮英雄祖先的传说,而且在生产落后、经济意识落后之时,表现出通过历史记忆和强化自觉而维持族群在特定时空下的生存状况。在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今天,那坡县龙华村吞力屯的黑衣壮自旅游开发以来,这种认同立即转化为大家通过一起表演节目(即便不参与表演者,也要穿上黑衣壮服饰在旁边观看)来获得均等的经济收入。当地一位黑衣壮女孩甚至放弃了中专毕业后留在省城工作的机会,回到当地当一名导游,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喜欢这个民族给她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黑衣壮族群认同同样表现在利益面前集体行为的一致性,也可以在另一种文化(外来宗教)侵入的时候,发挥其保护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功能。在当地问及是否有人进来传教时,村民说道:“前几年有人进来传教,但是我们特别不欢迎。我觉得自己特别反感这种的。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自己不太信这个(外来宗教)。最近几年也有人进来(传教),那坡信的人很少。主要是有钱人比较多。我们每家都有灵堂,我们不信佛,主要信死去的亲人。”其实,壮族的文化系统中还吸收了佛教或道教的文化元素。如学者所言:“壮族长期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孝悌观念与汉族并无二致,而壮族的祖先崇拜与图腾崇拜观念远比汉族要深。壮族人民虽然认为万物有神灵,但诸物中总有一种与本氏族关系密切,能够保佑本氏族繁荣……壮族人民认为祖宗在天之灵是神圣的,不容亵渎。”[14]尽管壮族的民间信仰吸收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但是在某些文化因子上依然能保持它的独立性。
在黑衣壮的村头、房屋或菜园附近,我们很容易发现用瓦片盖起来的坟墓。它的构造如同黑衣壮人家的小屋,“小屋”仅露出顶部。这就是黑衣壮独有的平棺葬。此种葬法采用二次葬,人死之后定在村子周围选择坟地,一般整个村子都集中在某一块区域,离村子不会太远。先是平整一小块地,直接将棺木平放在土上,然后以棺木为圆心,四周用石头垒起来,顶部用瓦盖成人字形屋顶。下葬后四到五年,再请道公选择吉日,撤掉坟墓,子女捡起尸骨,重新选择风水宝地下葬。第二次葬时,开始立碑。从请道公做法事来看,第一次比较隆重。关于这一过程,当地的村民解释,黑衣壮认为人死后有两魂,一个魂要升天,另一个魂则回归祖宗故地,因此这一个魂要留下来同子孙后代一同生活。因此坟地不能远离村子,离得近才能保护当地人畜平安。此种死人和活人空间上的相连,不存在明显的界限,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同,将生活圈和坟地的空间整合起来,形成边界。此外,每个黑衣壮村落(屯)都拥有一道石门,均体现出黑衣壮始终在建构自己的一个生活圈。
通过上述有关黑衣壮英雄祖先的传说,壮族能吸纳儒家和道家文化,反对外来宗教,以及通过空间的建构,形成边界,达到强化族群认同的情况,可以看出以民间信仰为基础的认同功能,具有乡村社会的整合功能。
三、民间信仰在外来宗教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阻隔的作用
外来宗教传入中国,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了碰撞。自19世纪以来,外来宗教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很大,而且伴随的是侵略和战争,因此蒋梦麟在其自传中对西风东渐的过程形象地比喻道:“如来是骑着白马来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着炮弹飞过来的。”[15]当然,有学者提出外来宗教引发的教案和冲突,主要表现受当时中国上层社会——绅士阶层的影响,而在下层社会教徒和百姓之间的关系没那么紧张,即便有冲突,其原因和宗教无关。[16]笔者认为,这一结论,似乎在弱化乡村社会民间信仰所建构起来的传统秩序机制发挥的功能。分析广西基督教传播的历史和影响,不难看出,基督教渗透到边远的民族地区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传播的地点主要限于县一级以上的城镇中心。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和西方侵略者之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各种教会组织伺机展开传教活动,基督教广泛传入广西,并采用了自东向西、自上而下的传播策略。1886年之后基督教开始向西传播,教会先后在贵县和南宁设立总部,1887年设立南宁总教区,在此建学校,招收学生,设8个传教点。这一阶段英国的圣公会在1899年传入广西,并向桂林和湖南等地传教;英国的宣道会、美国的复临安息日会,不断发展势力,到1923年,广西有基督教会143个,教徒19 717人。[17]至此,国外宗教势力已经发展到广西多数地方,中部、东部、北部和南部均有分布。“桂西的百色、隆林、扶绥、上思、田阳等广大壮族地区,在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下,各地都有部分壮族群众信仰基督”[14]。国外宗教势力不断深入广西民族地区传教,巴黎外方传教会甚至希望广西能成为基督教福音的第二故乡。[18]50然而,基督教在向广西各地传播的过程中,无不引发多起教案,例如1856年12月,马赖因再次潜回西林非法传教被杀,发生震惊朝野的“西林教案”;1883 年秋天,清政府在贵县招兵抗法,当地青年踊跃参加,由于之前积累了怨恨,于是几十名青年夜袭教堂,不想教堂的李神父开枪警告,更加让青年们愤怒,最后一拥而上,逮住神父,火烧教堂,史称“三板桥教案”。1896年之后又发生乐里教案和永安(今蒙山县)教案。
从基督教自东向西传入南宁、百色、河池等壮族地区来看,其传播地点主要集中在乡镇以上的区域,难以深入到民族地区核心地带,这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千百年来形成了传统的文化体系具有自我保护的防御功能不无关系。新中国成立,国家制定了相应的宗教管理政策后,民族地区的基督教进入了有序发展的阶段,广西也不例外。这一时期,政府要求国内的外籍传教士、神职人员回国。国内的外来宗教发展进入了本土化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现象是重要的神职人员几乎全是中国籍的。
自建国以来,国内宗教逐渐走向自由发展的本土化过程。随着整个社会的变迁、生产力的发展,当地基督教的传播形式也从传统的在外国神职人员的动员和组织下发放宣传资料和《圣经》、治病或以小恩小惠吸引民众,然后逐渐使其加入教会,走向了基于家族或同村关系来发展信徒。但是,外来宗教和民间信仰之间的矛盾和隔阂并未消除。据2014年8月的调查资料显示,靖西县有7个宗教场所,有神职人员5人,教徒1 000多人,仅占当地人口的1.6‰;那坡县无固定宗教场所,教徒30余人。1949年基督教传入德保县,现有基督教堂点20个,信徒2 000余人,并已经深入到农村。对三者进行比较,靖西和那坡基督教传入的时间比德保要早,但是目前靖西和那坡信教人数明显小于第三者。尽管基督教进入了本土化传播阶段,但从那坡县的情况来看,其传播受到一定阻碍,笔者认为和那坡县特有的族群认同(黑衣壮)有很大的关系。
那坡县龙华村吞力屯村离县城仅14公里,三四年前有人进屯传播基督教,带神职人员进屯的是本屯外出务工人员。务工人员在广州和东莞等地打工,在这些地方受到信教者影响,渐渐熟悉之后,开始接受基督教,回到家乡后便主动寻找当地的堂点。他们将基督教带入了吞力屯,并向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发展。先后有五六家开始信仰基督教。一年之后,由于文化上的冲突,造成信教家庭和村中其他村民之间较深的隔阂,最终放弃信仰基督教。究其原因,以族群认同为基础的村落传统文化通过排他性,放缓了基督教在当地的传播速度。那坡尽管离靖西较近,但是并没有教堂,礼拜和其他活动在一位信徒家中进行,这是临时的宗教活动点,因此外来宗教的传教成效甚微。
壮族是广西的土著民,早在儒、道未传入之前,当地已经形成了原始宗教信仰,这种原始信仰主要是自然崇拜,有天体崇拜、动物崇拜,也有植物崇拜。在接受外来文化上,的确有其包容其他宗教文化的一面,能够在原始宗教信仰的基础上融合佛教和道教等宗教文化。而且一旦这种文化融合之后,形成了稳定的基础,并对一个民族产生长久的影响。
那坡县壮族民间信仰在融合了道教的思想后,对当地的影响无不体现在生活、祭祀及其他仪式中。那坡有几个重要的传统节日很隆重,各种祭祀互动很多。“元宵前后以大稷酒肴祭土神,杂坐土祠前共饮,唱土歌,以祝平安,正月底采白头翁艾草和米为粢,益以鱼虾祭畜栏,名曰收鸭魂”。“三月三染五色饭,割牲煮酒,男妇咸出墓,以石灰涂冢,以纸钱挂墓前饮食而归”。*靖西民族宗教事务局编《靖西县壮民族古籍》,2009年版,第35页。六月六和七月十四是重要的节日。六月六是当地壮族拜祭山神的节日,这个时候各家各户都要买一些贡品如水果之类,到各屯的山神庙去祭拜。中元节是当地壮族第二个重要的节日,那坡县村民告诉我:“过中元节一定要杀鸭的。说是鬼节,不能不杀鸭。以前大家都不会杀鸡的,现在生活水平好了,基本上都要杀鸭和杀鸡。鬼节还要剪衣服,十四那天摆在神台上,十五的烧,衣服上还要写上谁的名字,不然到了阴间是收不到的。”
在那坡很多重要场合和仪式都离不开道公和女巫。当地居民赋予了这些人神秘的色彩,言语中还持肯定的口吻,特别相信道公和女巫的法力,对其身份和地位毫不怀疑,如受访人所述:
道长不是每个村都有的,命出了(注定)才能做,命的八字对了才能做。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每个道长在收了一个徒弟之后,都会看他们的八字,看命中有没有做道公的可能。有的道长过世以后,按照农村的说法,死后会还魂,寻找适合的接替他衣钵的那个人。如果那个人不做的话,就会浑身不舒服。即使你住院,你也不会治好,治不了的。等你回来以后,只能找已经达到一定级别的那些人(道公)来给你搞一个仪式,你出去以后就能继承衣钵了,从事这个行业……
不管你信不信,我们家那边有个女的,就说大家都在一个屯里边,很正常的一个人,有段时间就是见她精神恍惚,然后经常说:“你看,你看有人来找我了。”其实大家是看不到什么人(出现)。有段时间,就像疯了一样,去拔别人家的菜,这样后来家里边的人觉得很奇怪,就去找巫婆,说是有人来找她啦。要让她去当道士了,你们愿不愿意让她去做。让她做的话,只要走个程序就好了。后来她清醒的时候,家里人问她愿不愿意,她说太麻烦了。礼仪和讲究太多了,太麻烦了,就不想做。后来她又隔三差五地病,实在顶不住了,只能接受做了。然后她那个还魂的师父在云南那边呢,竟然,她原来都没有出过远门,她能告诉家里的人往哪个方向走,走到云南那家人,跟那家人说明情况,那家人就把原来(巫师)生前留下来的衣服、道具全部拿给她,她回来做了仪式之后,马上好了。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我们屯,你说奇不奇怪。然后村里有人生病,然后拿生病那人的衣服来给她,她就能帮你算出什么原因生病的。*2014年8月,那坡田野调查,访谈地点:那坡县吞力屯。
在当地的黑衣壮中,大家都愿意请道公或女巫来做法事。道公所做的事情是帮忙看日子,如下葬的时间、捡骨的时间、迁坟都要请道公来。以前经济条件不好的时候,大家的生活水平不高,道公做完法事后都是给半只鸡、半边猪头。后来发展到给红包,开始的时候两块、五块,现在到五十元左右。但是道公在当地的文化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甚至能凝聚和团结当地村民。基督教传入吞力屯之后,两种不同的文化,处理丧葬事务亦不相同。基督教简单,以牧师念诵圣经为主;而信仰民间宗教者,则请道公来做法事。最后到了下葬地点,大家自觉分成两边,一边是基督教徒,一边是信道公的村民。信基督教的教徒本来人就少,村民不时对其说三道四,另眼相看,道公也时不时谴责他们背叛祖宗,而他们自己总是觉得到哪里都有人在盯着他们,久而久之,大家不愿意信基督教了。
结论
民族地区以本民族特有的族群认同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体系,其中民间信仰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非均质化的特殊情况下,民间信仰在基层社会即村落的社会秩序中行使着重要的控制和调节职能,并在长期以来形成的族群认同、国家和民族认同之下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民族地区的社会和谐稳定,并通过特有的文化现象开发旅游资源,以此获得经济补偿。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在宗教传播过程中起到自我防御的功能,以此消解各种社会矛盾。民间信仰体系在另一层面上能提高民族的凝聚力,这将利于在新时期探讨乡村治理如何利用乡村早已形成的文化功能来推进乡村发展,具有积极效应。正确引导民间信仰,对推动我国民族地区朝着和谐、稳定、健康的方向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贺雪峰,董磊明,陈柏峰. 乡村治理研究的现状与前瞻[J]. 学习与实践,2007(8).
[2]蒋永甫. 乡村治理:回顾与前瞻——农村改革三十年来乡村治理的学术史研究[J].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3]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孙轶炜.当代中国人宗教信仰调查[N].瞭望东方周刊.2007-02-06.
[5]宁二.中国人的信仰与伦理道德重建[N].南方都市报,2010-08-08.
[6]林国平.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几个问题[J].民俗研究,2007(1).
[7]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8]辛之声. 中国民间信仰事象随想[N].中国民族报,2006-05-23.
[9]陈旭霞.中国民间信仰[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
[10]徐姗娜.民间信仰与乡村治理——一个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J].东南学术,2009(5).
[11]覃琮.人类学语境中的“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J].民俗研究,2012(5).
[12]王四小.论民间信仰的乡村治理功能[J].求索,2013(1).
[13]王存奎. 民间信仰与社会和谐:民俗学视角下的社会控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9(6).
[14]刘祥学. 论基督教在广西壮族地区的传播及文化冲突[J].宗教学研究,2012(2).
[15]蒋梦麟.西潮[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16][美]史维东.中国乡村社会的基督教:1860—1900年江西省的冲突和适应[M].吴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17]谢铭.近代广西基督教势力述论[J].河池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3).
[18]庚裕良,陈仁华,吴国强.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M].南京: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阳欣]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16.03.006
[收稿日期]2016-02-10
[基金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东盟多元宗教渗透与我国西南地区意识形态安全研究”(11BKS005);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研究中心项目“西南边疆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会风险防范机制研究”(2014YB005);广西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民族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开发课题“民俗信仰的社会治理功能研究”(2014MSB017)
[作者简介]李何春(1984—),男,白族,云南大理人,广西师范学院讲师,人类学博士,研究方向:藏学、盐文化、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包丽红(1984—),女,江西南丰人,广西师范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研究。
[中图分类号]C9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16)03-0032-07
On the Function of Folk Beliefs in Rural Governance Theory in the Ethnic Areas:A Research Based on the Fieldwork of the Heiyi Zhuang Areas
LI He-chun, BAO Li-hong
(Guangxi Teachers Education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1, China)
Abstract:Rural governance is the “academic sinking”, focusing on the practice of the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ety. Its logical basis is to break the management method of “top-down” manipulation of the rural society by traditional country. And to gradually realize the close interaction between rural society and the rule of national relationship,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rural society has formed a kind of order access to internally operation. Obviously, the internal order, produced in local society, exerting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history,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ety, includes folk beliefs played the positive function. For a long time with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t has important impact on human histor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dialectical view of folk belief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and the effect of absorption of folk beliefs about rural governance play the positive roles, beneficial to integrate social resources, to strengthen the national identity, and to maintain frontier stability and solidarity.
Key words:folk beliefs; rural governance; function; Heiyi Zhu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