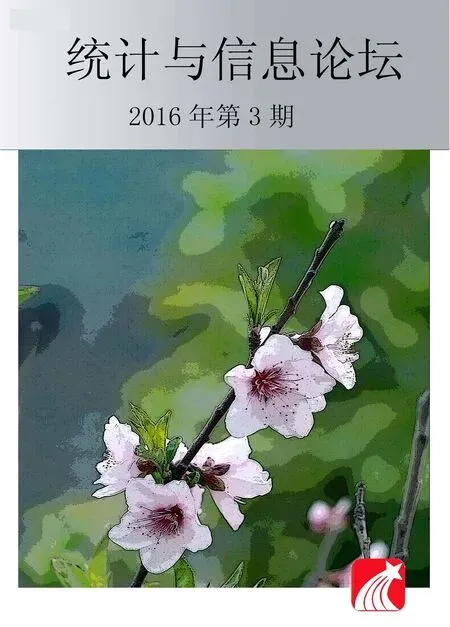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分解与失衡分析
尹伟华
(国家信息中心 经济预测部,北京,100045)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分解与失衡分析
尹伟华
(国家信息中心 经济预测部,北京,100045)
摘要:利用WIOD数据库,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对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进行了分解与对比分析。研究表明:中美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比例呈现不同程度下降趋势,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在不断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获益能力低于美国,且处于全球价值链相对下游位置;相对美国而言,中国制造业出口中隐含大量的国外增加值,中间产品的国外增加值比例在不断上升;中美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环节越来越多,但国内价值链构建和发展却相对薄弱;技术类别越高的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相对越高,但却明显低于美国;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大幅缩小了中美贸易失衡,且技术类别越高贸易失衡缩小幅度越大。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双边贸易;世界投入产出表;贸易失衡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进入全球价值链(GVC)时代。面对GVC主导的国际贸易新格局,由于大量中间产品贸易的存在,传统的以贸易总额为基础的官方统计数据无法区分贸易增加值的真正创造者,产生了大量重复统计等问题,进而经常会造成贸易扭曲并误导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对实际贸易格局的判断。世界第一和第二贸易大国的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中,中间产品贸易表现得更为活跃,其发展速度均显著高于最终产品贸易,使得上述问题在中美制造业中更为严重和突出。资料显示*根据《世界投入产出表1995-2011》相关数据计算而得。,1995—2011年中美两国制造业的双边贸易规模发展迅速,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4.94%,其中中国向美国出口贸易中中间产品比重由1995年的26.01%上升到2011年的41.41%,最终产品由1995年的73.99%下降到2011年的58.59%;美国向中国出口贸易中中间产品比重由1995年的63.17%上升到2011年的70.78%,而最终产品由1995年的36.83%下降到29.22%,这与GVC国际分工发展趋势相一致,即中美两国制造业越来越依赖进口的中间产品。基于此,如何在GVC视角下正确判断中美制造业的双边贸易结构变化,重新审视中美双边贸易失衡问题等,对中国制造业制定发展政策和实现产业优化升级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自从Gereffiet等(2005)提出GVC这一概念后,迅速显示出强劲的理论张力和实用价值,并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推广。Hummels最早构建垂直专业化指数测算一国(或地区)出口贸易中所蕴含的国外增加值,进而实现衡量一国(或地区)参与GVC国际分工程度[1]。Yi证明了GVC的发展所带来的垂直化分工是造成近年来全球贸易总量增长远远高于GDP 增长的最重要原因[2]。Lau基于区分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较为准确地测算了中国出口贸易中所隐含的国内增加值部分[3]。Grossman等提出了“任务贸易”的概念和理论模型,并为后续研究开创了全新的视角[4]。Antras等将中间品贸易引入传统贸易模型,并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视角对价值链上的生产组织结构进行了探讨[5-6]。Koopman等从“增加值贸易”(Trade in Value-added)视角出发,在双边、行业等细分层面,构建了统一的测度GVC统计分析框架,重塑了学术界对基本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格局的认知[7-9]。冯志坚基于联合国进出口数据和中国投入产出表测算了中国工业行业参与GVC的程度,并据此分析了相应的影响因素[10]。童伟伟等在放松进口中间产品价值构成的假设下考察了中国对美出口贸易情况,结果发现中国出口中,国内增加值比例总体下降,国外增加值却表现出更加多元化的趋势[11]。王岚利用GVC分析框架考察了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程度和地位,并据此剖析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路径[12]。马风涛等基于WIOD对中国制造业产品GVC进行解构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正积极融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中,国内增加值比例有回升趋势[13]。尹伟华从出口和进口两个方面构建了相应的后向和前向垂直专业化率指标,并据此测算了中国参与GVC的程度与方式,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主要是以后向方式参与GVC,处于GVC中相对下游的位置[14-15]。
纵观上述文献,大部分只是基于简单理论框架下对GVC贸易增加值的不完全或不彻底分解,而关于中美两国不同技术类别制造业的双边贸易分解则鲜有涉及。因此,本文基于欧盟最新公布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采用的完全分解的GVC统计分析框架,较全面地剖析中美两国制造业双边贸易增加值结构及变动情况,以期为现有文献提供有益的补充。
三、双边贸易的分解方法
运用国家间投入产出表(ICIO)模型框架对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的全球价值链进行分解分析。假设全球共有G个国家(或地区)(s,r=1,2,…,G),每个国家(或地区)有N个产业部门(i,j=1,2,…,N)。

表1 国家间投入产出表(ICIO)
注:ROW表示世界其他国家。
ICIO模型能够较为详尽地刻画各国(或地区)间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投入和使用情况。Zsr是N×N阶的中间投入(或使用)矩阵,表示r国(或地区)使用s国(地区)生产的中间产品;Ysr是N×1阶的最终使用矩阵,表示r国(或地区)使用s国(或地区)生产的最终产品;Xs是N×1阶的总产出矩阵,表示s国(或地区)的总产出;VAs是1×N阶的增加值矩阵,表示s国(或地区)的增加值。由于基本的列昂惕夫方法只能从整体上测算出某国(或地区)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并不能将隐含于出口中其他部分的价值进行分解,使得结果的政策应用受到一定的限制。基于此,Wang等提出了完整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其主要是根据出口产品最终吸收地及吸收渠道的不同,将一国出口分解为16个增加值和重复计算部分,实现了对中间产品贸易的完全或彻底地分解[8]。假设s国(或地区)向r国(或地区)出口贸易的具体分解过程如下式。Esr=Zsr+Ysr=AsrXr+Ysr





=DVA+RDV+FVA+PDC


本文基于上述分解过程以及研究目的,将s国(或地区)向r国(或地区)出口贸易分解的16个部分进行相应的归纳合并,如表2所示。

表2 双边贸易出口总额分解
四、样本和数据说明
目前国际上常用的ICIO数据主要有经合组织(OECD)的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美国普渡大学的GTAP数据库、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IDE-JETRO)的亚洲国家投入产出表(AIIOT)等,但由于这些数据库存在数据资源获取受限,或存在假设条件过于严格、涵盖国家(或地区)较少等问题,使得应用具有局限性。基于此,本文使用的ICIO数据来源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由于WIOD数据库中40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5%以上,故能够很好地反映全球主要的经济和贸易活动。。最新的WIOD数据库是涵盖了1995—2011年40个国家或地区(27个欧盟成员国和13个其他主要贸易国)、35个产业部门和59种产品的时序数据,其中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s)被广泛应用于研究GVC或贸易增加值。WIOTs中记录的制造业涉及14个产业部门,同时本文根据欧盟统计局(Eurostat)对制造业技术层次的划分方法,将制造业划分为四大类:髙技术制造业(包括: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中高技术制造业(包括: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中低技术制造业(包括: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橡胶及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制品业)和低技术制造业(包括:食品、饮料制造及烟草业,纺织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鞋类制品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业,其他制造业及废弃资源和旧材料回收加工)。本文使用的1995—2011年中美两国制造业投入产出数据均来自WIOD中的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s)。
五、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的分解分析
基于WIOTs数据,根据双边贸易总值的完全分解公式,可测算出1995—2011年中美两国制造业双边贸易中隐含的各部分增加值及其所占比重,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的分解结果 单位:%
注:(1)=(1a)+(1b)+(1c)表示DVA,其中1a表示DVA_FIN,1b表示DVA_INT,1c表示DVA_INTrex;(2)表示RDV;(3)=(3a)+(3c)表示FVA,其中3a表示FVA_FIN,3c表示FVA_INT;(4)=(4a)+(4b)表示PDC,其中4a表示FDC,4b表示DDC。
表3结果总体来看,1995—2011年中美两国制造业出口有着非常不同的增加值结构,中美两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参与程度和所处位置存在显著差异。报告期内,中美两国制造业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DVA)比例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其值分别由1995年的81.83%和82.11%下降到2011年的74.65%和77.35%,下降了7.18和4.76个百分点,表明中美两国制造业参与GVC的程度都在不断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DVA)比例相对低于美国,且主要以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内增加值(DVA_FIN)为主,而美国制造业主要以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内增加值(DVA_INT 和DVA_INTrex)为主,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出口附加值率或获益能力是相对较低的,处于GVC的相对下游位置,而美国制造业出口附加值率或获益能力是较强的,处于GVC的相对上游位置。2009年中美两国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DVA)比例都表现出跳跃性地上升,这主要是由于受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
考察期内,中美两国制造业出口中返回增加值(RDV)比例均相对较小,但美国的返回增加值(RDV)比例要显著高于中国,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制造业处于GVC的相对上游位置,其重点专注的是创新、产品研发、设计和出口关键性零部件的生产,有很大一部分美国出口增加值通过从其他地区的进口再次返回到国内,并被美国消费者使用。中国处于GVC的相对下游位置,很少有出口增加值通过其他地区的中间产品进口再次返回到国内。近年来美国制造业出口中返回增加值(RDV)比例呈现出一定幅度下降趋势,这可能是由于美国积极推行的“制造业回流”和“再工业化”发展战略引发制造业出现“逆转移”现象。中国制造业出口中返回增加值(RDV)比例不断上升,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参与GVC程度和所处位置都在不断攀升。
中美两国制造业出口中国外增加值(FVA)比例都呈现出显著地上升趋势,其值分别由1995年的17.18%和10.58%上升到2011年的21.86%和13.11%,上升了4.68和2.53个百分点。相对美国而言,中国制造业出口中国外增加值(FVA)比例较高,表明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中隐含着大量的国外增加值(FVA)。同时,中国制造业出口中隐含的国外增加值(FVA)主要体现在最终产品上(FVA_FIN),这表明中国制造业主要从事的是最终产品的加工、组装生产活动,只是参与GVC中较为低端的国际分工。中国制造业出口中中间产品的国外增加值(FVA_INT)比例不断上升,意味着中国制造业正在进行产业优化升级,由GVC的低端向中高端环节攀升。
中美两国制造业出口中纯重复计算部分(PDC)比例呈现出不断上升趋势,但中国的同期比例要显著低于美国,其值分别由1995年的0.90%和2.84%上升到2011年的2.81%和4.72%,表明中美两国制造业产品被用于最终产品生产之前,跨越海关的次数在不断地增加。也就是说,伴随着国际生产分工程度的不断深化,GVC的环节变得越来越多,价值链条变得越来越长。同时,中美两国制造业出口中来自于国外账户的纯重复计算部分(FDC)要显著高于来自于国内账户的纯重复计算部分(DDC),意味着中美两国制造业切入GVC的倾向和程度要高于国内价值链(NVC),其NVC的切入和构建程度并不高,这与张少军(2009)的结论相一致的。
(二)不同技术类别制造业
同时,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不同技术类别制造业出口产品GVC的分解情况,本文对2001年中美两国制造业中低技术制造业(LL)、中低技术制造业(LM)、中高技术制造业(MH)和高技术制造业(HH)的双边贸易进行分解和相应的对比分析,结果见表4。

表4 2011年中美不同技术类别制造业双边贸易的分解结果 单位:%
注:各列含义同表3。
表4结果显示,2011年中国低技术制造业的国内增加值(DVA)比例高于同期美国,而高技术制造业的国内增加值(DVA)比例显著低于同期美国,表明中国低技术制造业出口获益能力相对较强,而美国高技术制造业的出口获益能力相对较强。考察期内,中国低技术、中高技术、高技术制造业出口中以最终产品的国内增加值(DVA_FIN)比例显著高于以中间产品的国内增加值(DVA_INT 和DVA_INTrex),而美国却表现出相反的特征,这意味着中国这三类技术类别制造业在GVC中所处位置要明显低于美国。特别地,中国中低技术制造业的国内增加值(DVA)比例高于美国,且主要是以最终产品的国内增加值(DVA_FIN)为主,表明中国中低技术制造业在GVC中具有一定的优势。具体说,2011年中国低技术、中低技术、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DVA)比例分别为85.43%、73.81%、75.68%和69.63%;与此相对应的美国四类技术类别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比例(DVA)分别为82.18%、73.07%、75.01%和80.76%。相对于其他技术类别制造业而言,中国低技术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DVA)比例最高,这主要是由于低技术制造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中国凭借丰富廉价的劳动力实现该产业部门出口中绝大部分的增加值(王岚,2014)。
相对美国而言,2011年中国四类技术类别制造业出口中返回增加值(RDV)比例微不足道。其中,2011年中国低技术、中低技术、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出口中返回增加值(RDV)比例分别为0.22%、1.04%、0.90%、0.73%,这意味着中国低技术制造业在GVC中地位相对最低,中间产品出口的增加值很少通过进口再次返回到国内。与此相对应,美国四类技术类别制造业出口中返回增加值(RDV)比例分别为3.93%、5.13%、3.15%、7.04%,这意味着美国高技术制造业在GVC中所处位置相对最高,很大一部分中间产品出口的增加值通过进口再次返回到国内,用于出口产品的生产。
2011年中国四类技术类别制造业出口中国外增加值比例分别为13.79%、21.07%、20.11%和26.28%,显著高于同期美国。其中,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的国外增加值比例虽然最大,但其以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比例却明显低于以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这意味着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参与GVC程度虽然相对最高,但仍是以最终产品加工、组装的生产活动为主,参与GVC中较低端的生产分工,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高技术(郎咸平,2009);中国低技术制造业的国外增加值比例相对最低,且以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比例显著高于以中间产品的国外增加值,这意味着中国低技术制造业在GVC中的参与程度和位置都相对较低。特别地,中国中低技术制造业中以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比例低于以中间产品的国外增加值,再次表明中国中低技术制造业在GVC中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较为成功地融入到全球性生产网络中。
2011年中国低技术、中低技术、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出口中纯重复计算部分(PDC)比例分别为0.55%、4.07%、3.32%和3.36%,显著低于同期美国,表明技术类别越高的中国制造业跨地区生产分工深化程度相对越高,但却明显低于美国。同时,在这四类技术类别制造业中,中美两国出口中来自于外账户的纯重复计算部分(FDC)要显著高于来自于国国内账户的纯重复计算部分(DDC),意味着这四类技术类别制造业都更倾向于融入GVC,而缺乏搭建和延长以本土市场需求为基础的NVC。
(三)中美制造业贸易失衡
以总额为基础的传统贸易统计方法存在大量重复计算问题,存在夸大和扭曲贸易失衡现象。基于GVC的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是以“价值增值”为统计口径,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贸易失衡水平。

表5 2011年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失衡测算结果 单位:亿美元
注:MF表示制造业整体;占比表示增加值方法的贸易差额占传统方法的贸易差额的比重。
无论是制造业整体还是四类技术类别制造业,增加值贸易差额规模都显著小于总额贸易规模,即传统贸易统计方法均夸大和扭曲了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的失衡程度,而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贸易统计方法进行纠正。从表5结果可看到利用传统贸易统计方法测算的2011年中美制造业贸易差额为2 483.06亿美元,而利用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测算的2011年中美制造业贸易差额仅为1 824.09亿美元,贸易差额缩小了26.54%,这与张咏华(2013)、王岚等(2014)的结论基本一致。本文所测算的贸易差额缩小幅度相对较小,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测算方法和统计口径的不同,另一方面是由于没有将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进行区分,进而导致了贸易差额被高估。具体来看,在四类技术类别制造业中,低技术制造业的中美贸易差额程度缩小幅度相对最小,2011年中美增加值贸易差额占总额贸易差额的比重为86.05%,即贸易差额缩小了13.95%;高技术制造业的中美贸易差额最大,2011年中美增加值贸易差额占总额贸易差额的比重为66.88%,即贸易差额缩小程度高达33.12%。这些表明技术类别越高的制造业,其贸易失衡程度缩小幅度也就相应的越大,这主要是由于技术类别高的制造业参与GVC国际分工程度相应越高,在生产过程中中间产品在跨国(或地区)次数越多,进而导致总额贸易重复计算问题更为严重(王岚等,2014)。
六、结论
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从GVC视角对1995—2011年中美两国制造业双边贸易进行分解与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995—2011年中美两国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比例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表明其参与GVC程度都在不断地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比例相对低于同期美国,且主要是以最终产品为主,意味着中国制造业出口获益能力低于美国,且处于GVC相对下游位置;中美两国制造业出口中返回增加值比例都相对较小,表明中国出口增加值很少通过从其他地区进口返回到国内,而美国却相对较多;相对美国而言,中国制造业出口中隐含着大量的国外增加值,且中间产品的国外增加值比例不断上升,意味着中国制造业正由GVC的低端向中高端环节攀升;中美两国制造业出口中纯重复计算部分比例不断上升,其来自于国外账户的纯重复计算部分要显著高于来自于国内账户的纯重复计算部分,表明国际生产链的环节变得越来越多,但融入GVC的倾向和程度高于NVC;2011年中国低技术制造业出口获益能力较强,而美国高技术制造业出口获益能力较强;技术类别越高的中国制造业跨国(或地区)生产分工深化程度相对越高,但却明显低于美国。
参考文献:
[1]Hummels D,Ishii J,Yi K M.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1, 54(1).
[2]Yi K M. Can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Explain the Growth of World Trade?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3(1).
[3]Lau L J, Cheng L K,等.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及其应用——中美贸易顺差透视[J].中国社会科学,2007(5).
[4]Grossman G M, Rossi-Hansberg E. Trading tasks: a simple theory of offshoring[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8, 98(5).
[5]Antràs P, Costinot A. Intermediated Trade[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1, 126(3).
[6]Antras P, Chor D. Organizing the Global Value Chain. Econometrica[J].2013, 81(6).
[7]Koopman R, Wang Z, Wei S. 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Tracing Value A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R].NBER Working Paper No. 16426,2010.
[8]Wang Z, Wei S, Zhu K. Quantify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haring at the Bilateral and Sector Level[R].NBER Working Pape,2013.
[9]Koopman R, Wang Z, Wei S.Tracing Value-Added and Double Counting in Gross Export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4,104(2).
[10]冯志坚.垂直专业化的决定因素与国际贸易——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检验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2,27(12).
[11]童伟伟,张建民.中国对美出口的国内外增加值含量分解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3,31(5).
[12]王岚.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J].统计研究,2014,31(5).
[13]马风涛,李俊.中国制造业产品全球价值链的解构分析——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研究[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4,195(1).
[14]尹伟华.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与方式——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36(8).
[15]尹伟华.中国与APEC主要成员贸易的特点和政策建议——基于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J].中国投资,2015(10).
(责任编辑:张爱婷)
Decomposition and Imbalance of Sino-U.S. Bilateral Trad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based on Global Value Chain
YIN Wei-hua
(Economic Forecasting Department, State Information Center, Beijing 100045,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GVC), Sino-U.S. bilateral trades of manufactured industries are decomposed using 1995-2011 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s. Our studies indicate the following: (1) The domestic value-added (DVA) share in Sino-U.S. bilateral trades presents a downward trend from 1995-2011. It means that the level of participation in GVC is rising for Sino-U.S. bilateral traders. (2) Chinese manufactured goods which are the downstream of GVC are lower value-added rate. (3) Large share of foreign value-added (FVA) in final goods exports indicate that China mainly engages in final assembling activities. (4) The increase of pure double counted terms (PDC) suggests the GVC of Sino-U.S. is getting longer, but national value chain (NVC) is shorter. (5)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which are the higher level of technology, are the higher integration into GVC, but are lower than America. (6) The method of trade in value-added leads to a reduction in Sino-U.S. trade imbalance.
Key words:global value chain; bilateral trade; world input-output tables; trade imbalance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3116(2016)03-0021-07
作者简介:尹伟华,男,安徽合肥人,经济学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预测与决策,全球价值链分析,宏观经济统计分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国进出口贸易分解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15CTJ002)
收稿日期:2015-10-30;修复日期:2015-10-26
【统计应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