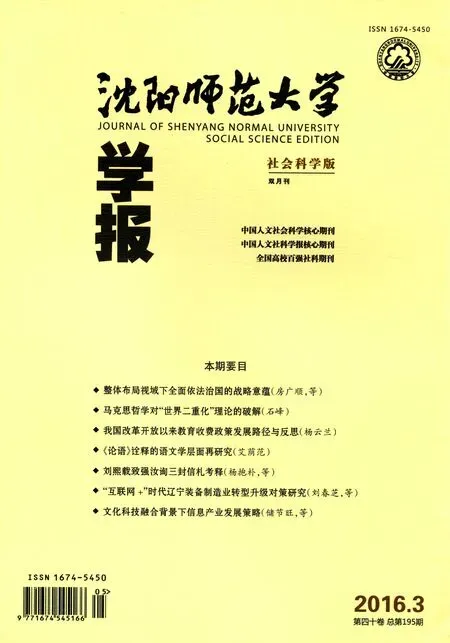《三国演义》嘉靖本与毛本之比较——以毛本语言特色为中心
华云松
(沈阳大学师范学院,辽宁沈阳110004)
《三国演义》嘉靖本与毛本之比较——以毛本语言特色为中心
华云松
(沈阳大学师范学院,辽宁沈阳110004)
嘉靖本与毛批本是《三国演义》的两个重要版本。二者的语言有较大差异,对其优劣高下的评论历来见仁见智。嘉靖本与毛批本在叙事语言上有所不同,晚出的毛批本叙事语言具有俗中见雅、情中见理、韵味悠长的特点,三者浑然统一于对艺术语言典雅美的审美追求之中,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毛本对嘉靖本语言的修改,虽也有因过于追求简洁造成的偏颇之处,但无伤大雅。
《三国演义》;嘉靖本;毛本;语言特色
一
目前学术界虽然对《三国演义》版本存在诸多争论,但不可否认,明嘉靖壬午年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为较早版本,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评点修改的《三国演义》是“后来最流行的本子”[1]。早在本世纪初,黄霖即指出:“嘉靖本与毛本孰优孰劣是《三国演义》版本研究中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2]。关于两个版本语言特色的比较,更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追溯起来,该研究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清代至1949年建国,研究模糊不明,评价不一。清人黄叔瑛认为,《三国演义》行文“不无支蔓,字句间亦或瑕瑜不掩”,毛本“领挈纲提,针藏线伏,波澜意度,万窍玲珑”[3]。虽未明言嘉靖本,“行文支蔓”评语当包括之;虽未明言毛本语言特色,而“万窍玲珑”中亦当含有此方面评价。胡适则持不同意见,他指出:“《三国演义》的作者、修改者、最后写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学家”,并以诸葛亮舌战群儒、三气周瑜为例,言其最精彩的部分尚且如此,其余自不必说[4]。在其对作者、修改者与最后写定者的评价中,自当包括对嘉靖本与毛本的评价;而对最精彩情节的贬斥中,亦当有对两本的语言评价。当然,两位学者评价不一,且对嘉靖本与毛本的语言关注是模糊的。
第二阶段:从建国初至上世纪80年代末,研究目的明确,争论热烈。建国初,郑振铎指出:毛宗岗在嘉靖本基础上作了删改[5],虽无大成就,但“他将原书行文拖沓、不大清楚之处,大加整饰,而使之成为简洁流畅的文字”,不能不说较嘉靖本有些进步[5]217。在此基础上,上世纪80年代,学术界就嘉靖本与毛本优劣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剑锋指出,毛本通过修改,使全书文辞整洁流畅;傅隆基则认为:毛本在语言上未必比嘉靖本精警洗炼[6];宁希元对毛本批评尤甚,指出由于清初文字狱及毛氏不明元人语汇,造成毛本在词语上“有意窜改”,甚至“随意乱改,多有改错之处”[7]。
第三阶段:上世纪90年代至今,研究意见趋同,关注淡化。上世纪90年代,嘉靖本与毛本优劣比较意见逐渐趋同,即肯定毛本的艺术价值。在语言研究方面,许振东指出:“嘉靖本有些人物的某些语言能与性格紧密结合,但也有一些语言与人物性格相悖”,毛本的修改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步[8]。刘永良认为:“尽管毛宗岗在对小说语言的加工润色中也有一些不足,但是他的贡献是巨大的,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9]至此,嘉靖本与毛本的语言比较研究在学界逐渐淡化。
如此,再作两个版本的语言比较是否还有价值?此问题当从三方面考虑:
首先,从上文所述的研究历程来看,对两个版本尤其是毛本语言特色的研究只是经历了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虽然总结出了毛本语言比嘉靖本更简洁、合理、通畅、有文采、感情更强[9]等特点,但仍是流于表象,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其次,从新世纪的《三国演义》语言研究来看,存在着范围较广而不注重版本的问题。该方面研究涉及《三国演义》语言的类型(如骂语、敬语)、审美性(如凝重之美、辞约意丰、音乐性、个性化)、修辞性(如修辞语法、修辞类型、修辞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民族性(如韵散兼行)等多个方面,但很多研究在参考文献中并不列出所依据的《三国演义》是何种版本,列出版本的也是嘉靖本与毛本不一,论述中则不作说明,统称为“《三国演义》的语言特点”。如此研究,至少是不全面的。因此,从版本比较的角度对《三国演义》的语言加以研究,仍然具有时代意义。
第三,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关于中国古代小说民族性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在90年代形成浩大的声势,并延续至今而不衰。其研究涉及古代小说民族性的性质、内容、艺术表现、创作者、接受者、影响等诸多方面,尤以在艺术性的研究方面着力最大,包括结构、人物塑造、辨体、审美特性、艺术表达方式等各个方面,而专门对语言民族性加以研究的则相对较少。此方面的研究包括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如《〈三国演义〉语言的民族特色》,也包括对古代小说总体的阐释,如《试论中国古代小说语言的雅俗共赏》。但总的说来,该方面研究数量少,并有待于进一步拓展。
二
毛宗岗对《三国演义》语言的评改非常关注,他在《三国志演义凡例》中指出:“俗本之乎者也等字,大半龃龉不通,又词语冗长,每多复沓处。今悉依古本改正,颇觉直捷痛快。”其后,又表现了对《文选》中有关三国时期佳文的喜爱与录入,对回目对偶精工的要求,对小说韵散兼行的肯定,对周静轩诗俚鄙的嘲讽[3]240-241。虽然毛宗岗并未指出他是据嘉靖本进行文辞修改的,但对词语不通、冗长与重复的改正,对《文选》佳文的关注,对古本诗词、回目的删改,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对文辞典雅的重视,“直捷痛快”一词更是这种重视的最佳阐释。据此,本文试通过对嘉靖本与毛本语言的分析,从三个方面研究毛氏对文辞典雅的关注。
首先,毛本语言的修改具有“俗中见雅”的特点。
在毛本之前,很多学者对《三国演义》的语言加以评价,蒋大器称之为“文不甚深,言不甚俗”[10];张尚德称之为“俗近语”[10]137;谢肇言其“俚而无味”[10]288;胡应麟鄙之“浅陋可嗤”[10]170。虽褒贬不一,但皆言到其语言通俗的特点。如何在俗中见雅,人物语言较难,尤以在尖锐矛盾冲突中的人物语言为最难。毛评本则往往通过字、词的删、改、增,使矛盾冲突尖端的人物语言更生动、精准,体现出对文辞典雅的审美追求。
如在“吕布辕门射戟”情节中,写吕布为排解袁术与刘备的矛盾,以自己箭法是否精准为标准,其中两本对吕布射箭时语言的陈述各有不同:
嘉靖本:酒毕,布挽起袍袖,搭上箭,拽满弓,口呼:“箭中!”[11]
毛本:只见吕布挽起袍袖,搭上箭,扯满弓,叫一声:“着!”[12]
从吕布语言来看,射箭用力处,“着”字比“箭中”一词更精准,因其更能突出箭法的力度,也更符合人物的语言表达习惯——即人物专注于射箭的紧要关头,语言表达自然要简而又简,并以有助于力量的运用为佳。而且,“着”字比“箭中”一词更直白、更质朴,也更口语化。故而“着”字比“箭中”一词更能体现毛本俗中见雅的语言特色。《宋元语言词典》引《水浒传》三十三回:“搭上箭,拽满弓,只一箭,喝声道‘着!'正射中门神骨朵头。”[13]若引毛本此段之“着”,岂不更见“着”字来处?
再以“王允献貂蝉”为例。吕布责备王允背信弃义、将本许与自己的貂蝉又改送董卓,王允为挑起吕布与董卓的矛盾,巧言辩之,王允向吕布的辩辞中有一句:
嘉靖本:“老夫见太师自到,安敢少违,随引貂蝉拜了董公太师。”[11]55
毛本:“老夫不敢有违,随引貂蝉出拜公公。”[12]42
王允在此是向吕布剖白自己不知董卓欲强占貂蝉之心,毛本对董卓的称呼改为“公公”,何为“公公”?《宋元语言词典》列四个义项,分别为:对老人的尊称;称家翁;称祖父;称太监[13]168。此处当为第二义,因为从吕布的角度看,董卓本来就应该是貂蝉的公公。毛本此改,比嘉靖本的“董公太师”更有利于王允表现自己的无辜,也更有利于他激起吕布对董卓强占貂蝉的不满。而且,“公公”一词何其通俗直白。毛本评语中对此也颇为得意,批之曰:“‘公公'二字搠心,妙。”[12]42何止妙在“搠心”,更妙在直白地“搠心”。
有学者指出:“语言节奏的急和缓,语言格调的高和低,语言距离的远和近,语言层次的深和浅,都被高明的作家们用力暗示那些为语言的指代性形式所无法传达的人生感受,以唤起读者的情绪反应。”[14]以上两例,毛氏即通过加快语言的节奏和拉近语言的距离,高明地传达出无法传达的人生感受,达到了俗中见雅的审美效果。
其次,毛本语言的修改具有“情中见理”的特点。
对毛本语言逻辑性的研究由来已久。刘永良曾指出毛本对嘉靖本“长坂坡赵云救主”情节的四处修改更具合理性[9]59-60。刘洪强以嘉靖本姜维之母的结局与冯习死两次的情节为例,指出毛本对嘉靖本逻辑错误的合理修改。以上两例研究颇具代表性,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着重体现了对毛本语言修改合理性的关注,但对毛本语言情感性的分析不足。毛本语言修改的合理性是与情感性相伴随的,在作品中体现为“情中见理”的典雅风貌。
《三国演义》写刘、关、张的友情最为感人。在“关云长挂印封金”这一情节中,嘉靖本与毛本语言处理不同,艺术效果则完全不同。仅以刘备给关羽的书信为例:
嘉靖本:备尝谓古之人,恐独身不能行其道,故结天下之士,以友辅仁。得其友,则益;失其友,则损。备与足下,自桃园共结刎颈之交,虽不同生,誓以同死。今何中道割恩断义?君必欲取功名、图富贵,愿献备级以成全功。书不尽言,死待来命[11]183。
毛本:备与足下自桃园缔盟,誓以同死,今何中道相违,割恩断义?君必欲取功名,图富贵,愿献备首级,以成全功。书不尽言,死待来命[12]152。
当时刘备在袁绍处寄居,关羽在曹操处受重用,袁绍与曹操势同水火,关羽为报曹操重用之恩,为之杀颜良、诛文丑,袁绍因关羽之故两次欲杀刘备,刘备巧言辩解,虽有惊无险,怎不心有余悸?在这种心情下,哪顾得圣贤之论?且刘备临终之时对孔明表明:“朕不读书,粗知大略”[11]589[12]507,其语言表述两本皆同,可见,刘备在文墨素养上与一般儒生不同,这是两个版本的共识。这样一个粗通文墨的人在生死关头向情同手足又误会重重的义弟大谈圣人之道,何其怪诞!故毛本在语言上直接删去了圣人之言,保留了原文刘备对桃园缔盟的追忆与对关羽以死相报的决心,使刘备的情感抒发更显得合理而重情。
在“孙策之死”的情节中,毛本的删、加更见功力。孙策临终嘱托孙权勿忘父兄创业之艰难,要尽心以保江东,后写孙权受命:
嘉靖本:权拜受印绶[11]204。
毛本:权大哭,拜受印绶[12]172。
毛本之“大哭”突出了孙氏兄弟的情深,比嘉靖本具有一种感情的合理性。
后写吴国太,两本皆写其担心孙权不能立事之忧,并以其忧告弥留之际的孙策,嘉靖本曰:“母乃嚎哭曰”[11]205,毛评本曰:“母哭曰”[12]172。吴国太是问国事,若嚎哭而问,则当如何表达?毛本用一“哭”字,虽含混,却减弱了嘉靖本“嚎哭”的强度,更有利于表现一位母亲在儿子临终前虽伤心又不得不以国事为重的特殊心情。孙权的“大哭”与其母的“哭”,显示了亲人生离死别时在不同情境下不同人物的不同心态,毛本之增删,合于情,更合于理。
以上两例从英雄人物刻画的角度体现了毛本语言修改“情中见理”的特点,下一例则把重点放在一般人物身上。在“左慈戏曹操”一节中,写左慈被操兵追赶,遁入羊群,操兵杀尽群羊,牧羊童守羊而哭,忽见羊头在地上作人言,令牧羊童将羊头放在死羊腔子上。两本后文写道:
嘉靖本:都凑了,左慈忽然跳起,将群羊百余只尽凑活。左慈拂袖而去[11]476。
毛本:小童大惊,掩面而走。忽闻有人在后呼曰:“不须惊走,还汝活羊。”小童回顾,见左慈已将地上死羊凑活,赶将来了。小童急欲问时,左慈已拂袖而去,其行如飞,倏忽不见[12]413。
嘉靖本仍将叙述的重点放在神仙左慈身上,毛本的修改则明显体现了叙述重点的转移,以更多笔墨写牧羊小童。由“大惊”“掩面而走”“回顾”“急欲问”等动作、情态的加入,合理地刻画了小孩子在巨大变故面前必然的惊慌失措与疑虑。若依嘉靖本的叙述,小童对羊作人言毫无反应,且敢自己将百余只羊头放在死羊腔子上,又对羊之死而复生亦无反应,真是无情亦无理之极了。
再次,毛本语言的修改具有“韵味悠长”的特点。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毛本在字里行间留下了很多的空白点,使文本结构对读者更具有召唤性,从中国的传统美学来看,毛本更多味外之味,韵外之致,现从局部与整体两个角度展开论述。
从局部来看,毛本中很多情节的表述均耐人寻味,现举两例析之:
一例写赤壁之战孔明七星坛借东风成功后,周瑜与鲁肃关于孔明的对话:
嘉靖本:周瑜大惊曰:“此人如此,使吾晓夜不安矣!为今之计,不若且与曹操连和,先擒刘备、诸葛亮,以绝后患也。”……鲁肃闻而谏曰:“都督岂可以小失而废大事!曹操甚于刘备十倍,若不破曹,丧无日矣。曹破之后,攻刘未迟。”[11]340-341
毛本:周瑜大惊曰:“此人如此多谋,使吾晓夜不安矣。”鲁肃曰:“且待破曹之后,却再图之。”[12]295
两个版本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嘉靖本完全可以作为毛本的注解,但其失之太露,把一切能讲的都讲尽了,没有给读者留下任何可供想象的空间。若无嘉靖本而只看毛本,读者就会有更多的联想:周瑜不安到什么程度?他要对孔明作什么?鲁肃为何要在破曹之后再图之?毛本两句话,可供寻味的空间颇大。
另一例是曹操大胜黄巾军后的行为陈述:
嘉靖本:操来见皇甫嵩、朱隽。赏劳了毕,便教曹操引兵追袭。操欣然去了[11]7。
毛本:操见过皇甫嵩、朱隽,随即引兵追袭张梁、张宝去了[12]5。
嘉靖本对曹操的行动刻画较详细,从其行文来看,曹操处于被动受命的状态,并对这种状态欣然受之。毛本则只写了曹操见过皇甫嵩、朱隽并再去追击敌兵的简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表现出曹操抗敌的主动与否,也没有刻画曹操的情绪如何,只给读者一种人物出场又转瞬即逝的感觉,这种简略的行文,能使读者对曹操的性格、才干等内容作丰富的联想。
除了局部表述之外,毛本语言的韵味性在作品整体内涵上体现的也较充分。杨义认为,《三国演义》虚实相生的叙事机制中,“虚”发展到极致就是“无”[15]。并以刘备三顾茅庐为例,指出虽然诸葛亮未出现,但其充盈的精神已弥漫于作者笔下的山水之间了。由此作者得出结论:“这种聚焦于‘无',达到了比聚焦于‘有'更高级的审美层面,从而在独具神采地创造一个充满诗化灵气的文化人格世界上,成为我国叙事文学史的一大奇观。”[15]289杨义对《三国演义》“无”的审美观照同样适用于毛本语言韵味性的描述,其最佳处,在于开篇词的增入与结尾诗的修改上。毛本开篇词曰: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此词乃明代杨慎所作,有学者指出:杨慎在词作中表现的是自怜身世、感慨兴亡的文人腔调,毛氏则以此词表现了“道德对历史有无作用”的悲怆追问[16]。这是当前学术界很多学者的共识。我倒以为,这种解读无论是对杨慎还是对毛氏,都是偏颇的。词作上阕着一“空”字,下阕着一“笑”字,“空”非悲悼之“空”,而是“笑谈”之“空”,而且是饱经沧桑的白发渔樵的“笑谈”之“空”,个中体现的是勘破世事的豁达,而非自怜之叹或悲怆之问,否则,何“笑”之有?
再看结尾诗,仅以结尾四句为例:
嘉靖本: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一统乾坤归晋朝[11]839。
毛评本: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12]721。
两个版本对历史如梦、天数难逃的看法是一致的,不过嘉靖本尾句重在史实陈述,毛评本尾句重在演说空幻。这一后人徒然凭吊之“空”与开篇词是非成败的历史之“空”交相呼应,形成了作品整体表述上关于“空”的历史循环。那么,何为“空”?“空”原为佛教用语[17],“与‘有'‘实'相对”,“指现象为因缘所生,无有不变之‘自性';或谓世俗认识的对象,虚幻不实;或称心性、理体之空寂明净;或说离污染,无谬误等”[18]。与《三国演义》的内容相联系,此处当指世俗之“有”的虚幻不实。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毛本在宏观上构筑了一个“空”的理念,在这一理念中,是三国纷争的惨烈与执着,是无数关于功名、政治、道德、富贵等追逐的实实在在的“有”,于是,“空”与“有”在文本中形成了矛盾的统一,在毛氏以“空”构筑出的大框架之中,读者的审美想象拥有了广阔的施展空间,毛本的文辞修改也具有了最高层次的典雅之美。
辩证地讲,毛本对嘉靖本的文辞修改,无论是俗中见雅、情中见理还是韵味悠长,彼此都不是割裂的。俗中见雅、情中见理之处自然颇耐寻味,韵味悠长中自有其俗中见雅或情中见理的表象,只不过在具体行文中各有侧重而已。
三
毛本语言修改也存在悖理、偏颇之处,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对文辞简洁的过度追求上,现试举例以论之。
如果说毛本主题在哲学层面体现为历史之空的话,在政治层面则明显表现为对贤明政治的渴慕,塑造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以歌颂仁义、反对暴政,便是为这一主题服务的。但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毛本存在着一些失误。先看正面形象的代表刘备。两本叙述刘、关、张桃园结义后:
嘉靖本:刘、关、张“祭罢天地,同拜玄德老母;将祭福物聚乡中英雄之人,得三百有余,就桃园中痛饮一醉。”[11]4
毛评本:刘、关、张“祭罢天地,复宰牛设酒,聚乡中勇士得三百余人,就桃园中痛饮一醉。”[12]3
毛评本删去“同拜玄德老母”六字,抹杀了嘉靖本对刘备奉行孝道的表述,不符合刘备的仁义形象,又与其前文玄德“事母至孝”[12]3的表达不能形成呼应,自不利于歌颂仁义的主题,只是在语言上更为简洁罢了。
再看反面形象董卓。董卓在长安恣意横行、残暴凶狠,两本皆写其宴百官而杀张温,其后对董卓解释的语言则有不同:
嘉靖本:卓笑曰:“诸公勿惊。张温结连袁术,欲图害我。因使人寄书来,错下在吾儿奉先处。故斩之,以夷其三族。汝等于吾孝顺,吾不害之。吾天佑之人,害吾者必败。”[11]52
毛本:卓笑曰:“诸公勿惊。张温结连袁术,欲图害我,因使人寄书来,错下在吾儿奉先处,故斩之。公等无故,不必惊畏。”[12]40
毛本略去董卓“汝等于吾孝顺”、“吾天佑之人,害吾者必败”等语,不利于塑造董卓恣意张狂的形象,也不利于突出董卓天命观掩映下自以为是的性格特点,更不利于反对暴政的主题表达,仍然只是在语言上更简洁罢了。
毛本对语言简洁的偏颇追求不仅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体现在对语言形式的修改上,有时甚至能达到偏执的程度,其对刘备、关羽的身高刻画可见一斑:
嘉靖本:刘备“身长七尺五寸”[11]3,关羽身长九尺三寸、髯长一尺八寸[11]4。
毛评本:刘备“身长八尺”[12]3,关羽“身长九尺,髯长二尺”[12]3。
虽然两个版本均属于艺术创作,但毛本为了追求语言表达上的简洁,而使刘备、关羽身高或髯长的数字过于整齐,反不如嘉靖本具有一种艺术的真实性。
不过,总的来看,毛本对于语言简洁的追求过当无伤大雅,作品整体的语言修订仍是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对艺术语言典雅美的审美追求。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26.
[2]黄霖.中国小说研究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288.
[3]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77:490.
[4]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M].实业印书馆,1934:390.
[5]郑振铎.郑振铎全集第四卷[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207.
[6]沈伯俊,谭良啸.三国演义辞典[M].成都:巴蜀书社,1989:670.
[7]宁希元.毛本《三国演义》指谬[J].社会科学研究, 1983(4):45.
[8]许振东.评两种版本《三国演义》人物塑造的异同.[J].明清小说研究,1996(2):48-49.
[9]刘永良.毛宗岗对三国演义语言的加工润色[J].明清小说研究,1998(3):64.
[10]黄霖.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131.
[11]罗贯中.二十四卷嘉靖壬午本《三国演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12.
[12]罗贯中.三国演义[M].北京:中华书局,2013:89.
[13]龙潜庵.宋元语言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860.
[14]唐跃,谭学纯.小说语言美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28-29.
[15]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87.
[16]李子广.道德何为——说《三国演义》开篇词[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3):54:57.
[17]胡孚琛.中华道教大辞典[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437.
[18]任继愈.佛教大辞典[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866.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Jiajing's and Mao Zonggang's Editions of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Focusing on Mao Zonggang's Language Features
Hua Yunsong
(College of Teachers,Shenyang University,Shenyang Liaoning110044)
As two important editions of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Jiajing's and Mao's editions differ obviously in languages,which have brought about diversiform comments of the two.Mao's edition is different from Jiajing's edition in the narrative language.Mao's edition,which was published later,was characterized by elegance in uncouth,rationality in affections and long lasting charm,which harmoniously united in the aesthetic pursuit of the elegance in artistic language,forming a conspicuous ethnic feature.Although there are several inappropriate revises on the languages in Jiajing's edition caused by over pursuing of conciseness,they would not affect the excellence of the Mao's editio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Jiajng's edition;Mao's edition;language features
I207.413
A
1674-5450(2016)03-0061-05
2016-01-08
华云松,女,辽宁沈阳人,沈阳大学讲师,辽宁大学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杨抱朴责任校对:张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