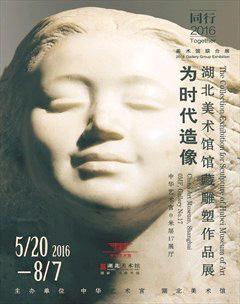德语舞台上的华文戏剧
罗妙兰
中西戏剧的交流历史很早,汉代时便由罗马来华杂技艺人的表演开始。中华戏剧传至西方的情况,则可溯到18世纪上叶。通过回溯历史,或可借此瞻望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下,德中戏剧文化交流的去向。
18世纪的改编剧本《中国人,或命运的公义,悲剧》
在西方,最早有关东方的写作,可回溯至14世纪记叙马可·波罗(Marco Polo) 在中国所见所闻的《马可·波罗游记》。除了商人、旅行家、探险家和外交使者外,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也通过书信输入不少中华文化到欧洲大陆。其中,由马若瑟传教士在1731年所翻译的《赵氏孤儿》法文版本便是首个将中华戏曲带入欧洲的故事。该法译本名为Tchao-chi-cou-eulh, ou LOrphelin de la Maison de Tchao, tragédie chinoise,收录在由杜赫德神父所编的《中华帝国全志》内,并在1735年出版。杜赫德的译介里指出马若瑟译本中没有翻译原剧曲词,而只翻译了宾白 ,但保留了剧情和结构。在17和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chinoiserie)文化艺术和思想风尚下,除了《中华帝国全志》很快被转译成英、德和俄文版本外,《赵氏孤儿》的法文删译本也被改编成英、俄、意和德文的戏剧文本或演出。其中的佼佼者,便是伏尔泰所著《中国孤儿》。它对1774年德语舞台上出现改编的德文本《中国人,或命运的公义,悲剧》有一定的影响。
该德文改编剧本是匿名发表的。剧本上的献辞是致当时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Mecklenburg—Strelitz) 大公国的王子卡尔,内文道出希望展示王子一些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在前言里,作者引译伏尔泰对中国文明的推崇和对《赵氏孤儿》剧本审美的评论。可是,他反对伏尔泰的一些审美观点,并引译原著戏曲译本中有关程婴被韩厥审问的一小节,说明该作品也有对理性和感情的表达。再者,作者认为作品像大多数东方国家的故事一样,透过神奇的命运赞赏美德,又或惩罚罪恶。事实上,他将东方(无论近东或远东)的故事典型化,也把东方国家的道德价值一般化了。作者也同意作品的结构违反了亚里士多德的悲剧法则,但是,他认为亚氏可能会对情节和一些角色满意。前言的最后部分,作者道出他不会完全遵从原著,但仍会呈现中国的特性,尤其是保留东方专制主义的礼仪习俗。 总之,作者改编该剧的目的是为了介绍外来文化给本地的王亲贵族,隐含地批评伏尔泰对中国文明的褒扬和东方式的君主专制。
改编本共有五幕二十八场,用在巴洛克时期普遍流行的六步抑扬格诗句(Alexandriner)写成。其主要人物角色缩减至五个: 韩同(Hantong) 代替了屠岸贾,为国家的一级武官和部长;赵盾和赵朔改为兰福(Lanfu),为国家的一级文官和部长;坎布尔(Rambul) 是成人了的赵氏孤儿,但也是韩同的养子;苏伦(Sulem)代替程婴,成为坎布尔的生父;并新增韩同女儿一角,名为莉莉花(Lilifa) 。戏内的场景地点不变。故事情节叙述韩同想排除当时受皇帝宠爱的兰福,所以要求早已与莉莉花情投意合的坎布尔除掉兰福,并承诺让他与莉莉花成婚作为奖赏。虽然坎布尔因道德善恶考虑而犹豫不决,但在莉莉花再三说服下,他还是呈文给皇帝诬告陷害兰福。皇帝听信诬陷,派人来圣旨和三件物品:绳索、匕首和毒酒 ,命兰福选取一样用以自尽。兰福饮鸩自尽后,坎布尔接替了他的官位 ,但受到良心的责备。这时,快将去世的苏伦向坎布尔道出他的真实身世:说坎布尔原来是赵氏孤儿,韩同是他的杀父仇人。坎布尔前往向韩同复仇,并在韩同面前揭发自己原身世时,用匕首杀了他。莉莉花扺达后,在报仇和爱情的伤感之间挣扎,最后把自己——作为杀人者坎布尔的未婚妻,杀死,以为父报仇。
德语改编版本保留了原有的复仇主题,并新加入莉莉花和坎布尔的爱情故事。虽然剧中透过朝拜皇帝的描写表现了朝拜君主的中国严格礼仪,但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描写,却只轻述皇帝听信诬陷便判臣子死刑的事,而没有深入描写暴君专制行为,所以没有足够说服力,无法达到作者改编的原意。剧本因题材、语言格式和文化热潮等不同的原因而未被赏识,它的影响也无从稽考。然而,《赵氏孤儿》还是通过其他途径,如德文译本或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影响了当时德语系的剧作家。类似的题材如政权和美德的冲突,都可以在戈特霍尔德·莱辛(Gotthold Lessing)的《智者纳坦》、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在陶里斯的依菲格湼亚 》,又或《额尔彭诺》中找到。
20世纪的美学概念“‘陌生化效果”
19世纪初,在德语剧场里上演了由弗里德里希·冯·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 翻译卡洛·戈齐(Carlo Gozzi)所著的悲喜剧《图兰朵》,展现了剧作家们对中国朝廷的想象。然而,德中戏剧文化交流在十九世纪时出现了低谷,当时被引进德语舞台的中华戏剧寥寥可数。其一例子是由剧作家沃海姆·德·丰塞萨(Wolheim de Foncesa)翻译的元杂剧《灰阑记》德文本,它是据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所翻译的法译本,再转译至德语而成的。到了20世纪初,情况有所改变。在欧洲剧场“再戏剧化(Retheatricalization)”趋势下,德语舞台上前卫的戏剧家又再次向欧洲呈现远东的中华戏剧文化。再戏剧化目的在于反击自然主义剧场,想要代替一种写实心理的、被文学所支配的幻觉剧场。当时的戏剧家将过往传统的剧目用新的美学风格重新搬上舞台,如马克斯·赖因哈特(Max Reinhardt)在柏林的德意志剧院据弋齐的剧本,运用了象征主义导演《图兰朵》一剧。也有些戏剧家提议不模仿现实,而是去创造属于戏剧本身现实的剧场, 如欧文·皮斯卡托(Erwin Piscator)在柏林他的第三剧院里、以政治剧场样式实验《太阳,觉醒》的演出。还有些戏剧家寻找一种舞台和观众没有被第四堵墙隔离的新的沟通形式,而布莱希特在莫斯科看到梅兰芳时,便遇上了这契机。
1935年,已流亡丹麦的布莱希特,在莫斯科观看了梅兰芳的演出后,于中国戏曲表演中发现了支持他戏剧改革的表演范例。他认为中国古典戏曲运用了 “陌生化”艺术手法。其实,布莱希特通过他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和作家谢尔盖·特列季亚夫(Sergej Tretakov)讨论关于中国和尼古拉·奥旋洛夫(Nikolai Ochlopkow) 的戏剧时,接触了“陌生化”这个术语。特列季亚夫介绍了形式主义作家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klovskij)文章内的‘ostranenije (意即“陌生化”) 。 1937年, 布莱希特完成《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陌生化”效果》论述他的戏曲观感,尤其比较戏曲表演和欧洲演剧方法的区别。在演员和角色关系上,布氏认为戏曲演员与角色保持一定距离,并观察、审视自己的动作,处于冷静的状态中,但仍有感情的表现。而西方演员则想变成角色,在神志恍惚的状态中表演,此外,戏曲演员不像西方演员,没有被第四堵墙与观众隔离的问题。戏曲演员的表演是让观众观看的,观众需从一个理性的观察者来感受,在感情上不一定要和舞台表演的事件融为一体。西方演员则想让观众和自己所表现人物的感情融为一体,让观众堕入舞台上的幻觉里。布氏在文中也道出他看到戏曲虚拟象征手法的特征,又发现戏曲运用程序化动作,如“咬发”和“以桨代船,驾舟”等外部手段去达到“陌生化”效果。不过,布莱希特也间接道出自己对中国戏曲中“陌生化”效果的观察认识,是建基于西方的现实主义和革命戏剧,脱离了中国戏曲的艺术观念。他的重点在于从戏曲中寻求可应用于欧洲戏剧的特点:即在欧洲戏剧艺术的基础上,借鉴东方戏剧艺术,创造新的戏剧流派。
布莱希特的“陌生化”定义是“首先意味着取去这事或人物角色最自然的、熟悉的和显而易见的东西,从而制造出对它的惊讶和新奇感”。“陌生化”具有一种辩证的思谁:理解—不理解—理解、否定之否定的认识事物的辩证过程。它不只是在于制造间离,而是在惊异或反对中达到另一水平上:消除所表演的东西和观众的隔离,而赋予观众的一种探讨批判的态度来对待舞台上的表演。 “陌生化”效果在德国的新史诗戏剧中是独立自主地通过实践发展着,其目的是使被表现的事物历史化,有着一种对社会批评和改造历史记录的任务。它的手段是艺术的,不但可通过演员,也能通过音乐(合唱队和歌曲) 或布景(标语牌和电影)等而产生。 特别从表演方法上看,演员要与角色保持距离,可用面具观察注视角色的手势动作、可用惊异者或反对者的态度理解角色的特殊性,也可通过采用第三人称、过去式或兼读表演指示和说明等等,去达到“陌生化”效果。在观众审美方面上,演员在没有第四堵墙的情况下,不让观众进入舞台上的幻觉,而是要观众观察和理性地批判表演的事物,从而改造社会和历史。
事实上,“陌生化”这一美学概念和布莱希特的史诗叙事戏剧不可分割,不只呈现在表演和观众审美方面,也呈现在舞台美学、音乐和剧作方面。尤其是在布莱希特后期的剧作中,运用了“陌生化”效果作为创作原则;如《四川好人》中的寓意所反映的生活典型,或以其比喻性的双层次布局来实现被表现事物的“陌生化”; 又或在《高加索灰阑记》以歌唱叙述剧情,突破剧作的传统结构形式和时空限制,因而达致的“陌生化”效果。 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中的表演手法,冲破了西方在自然主义风格影响下的表演方法,发展了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Konstantin Stanislavskij)现实主义体验派不同的“间离”的表演方法。史诗剧中“陌生化”效果的间情——即理智地认识和改造社会历史——的观众审美概念,打破了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洗涤”之说。布莱希特的“陌生化”对同时代和60年代的德语系剧场有相当大的影响。当代剧作家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的《中国长城 》,便是一出追随布莱希特的叙事剧,运用了历史和现代虚构统治者形象的人物角色、叙述者与观众直接对白、角色们自我介绍等“陌生化”手段,展现一个从古代中国到20世纪西方的故事。60年代的德语系剧场也可找到布莱希特“陌生化”的痕迹,如彼德·魏斯(Peter Weiss)的 《马拉/萨德》、彼德·汉德克(Peter Handke) 的 《冒犯观众》,也呈现了“陌生化”效果。
21世纪德中合作演出的《晚风酋长》
20世纪60年代,由西欧和北美所提倡的生活及工作社群(Lebens- und Arbeitsgemeinschaft)思想和西方的剧场生态,对戏剧文化交流有一定的影响。有别于各大城市的国家剧院或商业表演团体,由独立的戏剧团体、剧院和个别的戏剧工作者们发起的“自由剧场 ”标志着一种新的剧场模式。这涉及内容、美学形式、戏剧的社会政治功能和剧院机制结构等各方面。慕尼黑的“红甜菜集团”、“柏林戏剧工厂”、巴伐利亚的“普林臣泰戏剧农庄”和法兰克福的“史力拾剧团”可被视为自70年代在德国自由剧场的先行者团体。自由剧场发展迅速,德国的剧团数目从70年代约为40个,增长至21世纪初的超于1200个。 它的创作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工作方式通常会是没有等级划分并共同决定的团队合作;对不同的题材和美学风格持开放态度,制作出实验性、社会政治性,或跨文化的剧场,甚至有社群娱乐、参与、互动或包容的戏剧。西方不少自由剧场的剧团,通过本地跨文化的制作和在国际戏剧节演出,建立与外地戏剧的联系。德语系自由剧场中的代表之一,正是史力拾剧团的延伸、在80年代末成立的法兰克福无为剧团 (以下简称无为剧团)。
早在80年代中,史力拾剧团已演出再现中国文化元素的戏剧,如达里奥·福(Dario Fo) 的《母老虎的故事》。而无为剧团在1989-1994年间的史诗式试验演出系列包括了《四川好人》和《另一只狗》。《另一只狗》是据布莱希特的逃亡诗《有关道德经起源于老子在流亡道上的传说》和无为剧团中国之旅的经验为题材改编的跨文化创作。史诗式试验的一些演出系列也在中国客席演出,其中奥地利戏剧家约翰·内斯特罗伊 (Johann Nestroy)的趣剧《必要的和多余的》,便通过翻译员俞唯洁的中介在上海戏剧学院上演。从此,无为剧团与上海戏剧学院建立了戏剧交流的友谊关系。2000年,无为剧团邀请上海戏剧学院到德国四个不同地方演出中文古装剧《庄周戏妻》。作为戏剧文化交流的延续,一出在2001年联合制作演出的闹剧《晚风酋长》应运而生。
据无为剧团主干成员安吉莉卡·西堡(Angelika Sieburg)透露,上海戏剧学院让无为剧团构思这次合作概念和方法。无为剧团选用了内斯特罗伊的另一闹剧《晚风酋长》作为参考文本。剧本描述当时欧洲维也纳和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两个对立世界的相遇;而这次的演出以欧洲维也纳、巴伐利亚和中国上海为背景。无为剧团让三位在维也纳市内翻译公司的华人把剧本翻译成中文。中译本忠于维也纳方言,因此在和上海戏剧学院剧人共同研读剧本时,对方言产生了不少理解和沟通的问题。通过用普通话排练后,才把这些问题解决。 表演方面,由德中演员同台演出,包括无为剧团的两位主干成员, 西堡及安德烈亚斯·为兰路(Andreas Wellano)和当时的上海戏剧学院讲师和学生,有安振吉、钱正和马良。虽然欧洲演员们用德语演出,但说话时强调演说他们出生成长地,即维也纳市和巴伐利亚省的口音。中国演员们虽用普通话演出,但是说话时也会带有他们成长地的方言口音。此外,在演出中增加了两个口头翻译的角色,来传译酋长们的会议。这两个角色分别由汉学学生西蒙娜·基士迈亚(Simone Griessmayer)和钱正饰演。经过约六个星期的排练,《晚风酋长》在2001年上海戏剧学院举办的第二届国际小剧场实验戏剧节内首演。2002年,它被邀请到德国的第二十六届杜伊斯堡文化节,在玛利亚大门剧院(Theater am Marientor)演出。2003年,合作演出应邀到德国的法兰克福、柏林、德莱艾希(Dreieich) 、沃尔夫斯堡(Wolfsburg) 、明登(Minden)和路德维希港(Ludwigshafen)六个城市作巡回演出和交流。这次的巡回演出,由当时旅居柏林研读戏剧的笔者在制作排练中担任口头翻译,并在剧中演出口译员一角。
无为剧团的成员不谙中文,他们接收中国戏剧文化的方式,突出反映了两国文化差异。笔者在口译过程中也有心得。其一:提出口译员个人见解。演出期间,中德戏剧工作者们的视野都集中在双方文化的差异上。例如在筹备上海演出时,无为剧团曾建议使用一个堆满破烂轮胎垃圾的肮脏岛屿作为舞台布景,却遭到中方舞台设计师的强烈反对。笔者解释道,中华文化中个人在公众面前尽量表现出得体正面的模样,艺术表演也如此。此外,中方演员询问观看柏林演出观众不多的原因,笔者向他比较柏林和上海市居民数量的差别、并指出观众理解跨文化戏剧演出中外语的困难;其二:以自身作为双方的沟通媒介,翻译并传递讯息。笔者在面对未能以个人识见即时解答的问题时,会以自身的语言能力作媒介,为一方向另一方作出询问而解答一方的问题。例如,德方细问了气功练习如何作为中方演员进入角色的方法,笔者询问中方,用他们的角度来看有关中华戏剧文化的问题以回答德方。又中方想认识德国不同类型剧院和剧团(即市政剧院、巡演剧团和自由剧场)的分别,笔者询问德方,用德方角度来看德语戏剧文化问题以回答中方。通过传译双方的问题和解答,笔者让双方跨越自身,认识了解对方的戏剧文化。
从两国观众的笑声中,可知《晚风酋长》颇受观众认可。上海的观众们有感这场演出高度的娱乐性。在德国的巡回演出中,四个剧院(除了柏林和德莱艾希)的座位都几乎售罄。观众们不只是德国人,也有中国或亚裔血统。前者倾向不大展露其感情,而后者时常笑得前仰后合。此后,无为剧团希望进一步和中国戏剧艺术家合作,已开始倾谈演出流亡到上海的德国艺术家的故事。虽然合作计划还未实现,无为剧团对中国文化的演绎仍然乐此不疲,持续演出他们首部呈现中国文化元素的《老虎的故事》。直至现今,在德语地区的演出已超出了500场。《晚风酋长》中的德中演员通过翻译同台表演的合作方式、多语(也包括口译)的演出形式和在两地的演出,在二十一世纪初开启德中戏剧文化交流先河。其后,在德语系剧场里,也可找到德中表演者的同台合作演出,如由葛斯娜·丹克瓦特(Gesine Danckwart)执导的,在柏林和北京演出的《评弹故事》,又或德中语系艺术工作者的共同合作,如由马梓·史德达(Mats Staub)和曹克飞联合编导,在伯尔尼屠宰场剧院(Schlachthaus Theater Bern)上演的纪录戏剧《嫦娥》。
总结与前瞻
本文从以上三个不同年代的事例,描绘德中戏剧文化交流的历史过程。由18世纪下叶中国风热潮末的文化介绍、想象与偏见;20世纪上叶,德语剧场在再戏剧化下寻找改革西方戏剧的形式和美学;以至21世初自由剧场界增生下所创建的跨文化戏剧。三者都呈现了德语系戏剧工作者们在不同的背景下,对中华戏剧文化产生兴趣,并有其自身内在的需要和目的,有着实用工具性。他们主动接受外来文化,接收方式变化多样,分别出现在不同的戏剧创作范围内。从剧本的删减、转译与改编,观看真实中华戏剧表演、书写观后感及实践,到通过翻译中介的交流演出与同台表演合作,都不是照搬抄袭中华戏剧,而以自身戏剧文化历史为基础创作发展的。这些戏剧文化交流的事例,尤以后两者,其结果都颇为正面,发展了新的美学形式、概念或戏剧类型,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后的德语系、西方、甚至中国戏剧的发展,使双方都能有所获益。
从德中戏剧文化交流的历史观看,德语系戏剧工作者自主地接收中华戏剧文化,与其探索实践创新或共同建构演出,和在文化全球化下的商业戏剧大相径庭。在德中戏剧文化交流下所产生的跨文化戏剧,因从自身文化出发和外来文化接轨,本地色彩未被冲淡,但又能呈现世界在地化的特色。近年来,德语系戏剧与中华戏剧的文化交流呈现一片繁盛景象,如中国众多的剧院或剧团在德国演出和中国当代戏剧德译本的出版。 但是这些交流还是呈基本和单向性的。事实上,以《晚风酋长》的事例为证,在21世纪初、德中戏剧文化交流已走进平等合作的基础,通过翻译认识彼此的戏剧文化和双向性地在两地演出。在德国,已有文化机构,如在柏林的世界文化中心(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提供资源平台,在文化合作沟通方面寻找新的可能性。德语戏剧能否通过与中华戏剧文化的交流再创新犹,又或中华戏剧能否在文化交流中成为德语戏剧重要的组成部分,姑且让时间告诉大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