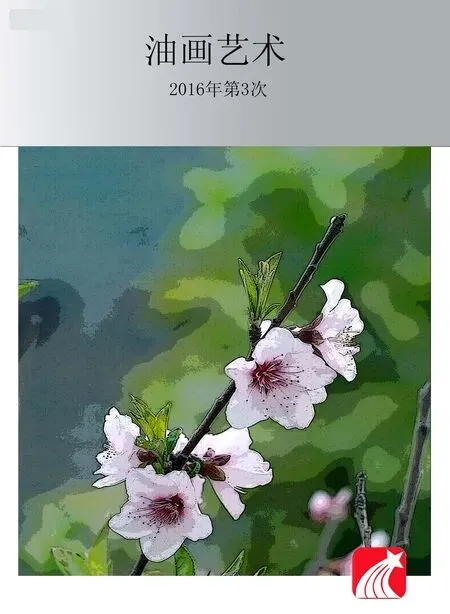中国油画的写意精神
文
写意精神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古代汉语“写”的原义为“摹画”“书写”“倾泻”“抒发”。后来中国传统绘画“写意”的“写”多取“抒发”的意义,文人画也强调“写”的“书写”意义。古代汉语“意”的原义为“心意”“意图”,在中国古典诗歌与绘画理论中多指“诗意”“意境”。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主要是指抒发情感、营造意境。
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精神,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崇尚自然的老庄哲学。老庄哲学的根本宗旨是“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道”(way)是指宇宙的终极本体和普遍规律,“自然”(nature)是指自然的朴素状态和纯真本性。“道法自然”是说“道”效法、顺应自然的本性,而不违背自然的本性。既然自然主要是指自然的本性,那么表现自然的艺术就不应停留于模仿自然的外在形态,而应该深入地揭示自然的内在本质。——这正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精神的逻辑思路:不求形似,注重意蕴。老庄哲学的人生理想是追求人与自然的融合,进入自由超脱的精神境界。人与自然的融合不仅意味着人与自然界的和谐,更意味着人的朴素淳真的自然本性的回归。——这也正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精神的审美理想:澄怀观道,返璞归真。中国文人画标榜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写胸中逸气”“抒写自己之性灵”等彰显个性的观点,归根结底来源于老庄哲学崇尚自然的思想。
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精神与西方传统艺术的写实观念存在异质文化的矛盾。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主张“艺术模仿自然”。希腊语“模仿”(mimesis)与英语“模仿”(imitation)同义。希腊语“自然”(physis)是指生长、源泉、世界、宇宙,英语“自然”(nature)一词也含有“本性”的意义。从艺术模仿自然的原理衍生出来的西方传统艺术的写实观念,与从“道法自然”的原理衍生出来的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精神分道扬镳。比较而言,西方传统艺术的写实观念偏重于由外向内地模仿自然,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精神偏重于由内向外地表现自然。我们如果把“自然”一词置换为“本性”,即西方传统艺术的写实观念偏重于由外向内地模仿“本性”,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精神偏重于由内向外地表现“本性”,也许更容易领会其中的奥义。
如果说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精神与西方传统艺术的写实观念存在异质文化的矛盾,那么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精神与西方现代艺术的现代观念则存在精神相通的契合。强化个性(strengthening personality)与简化形式(simplifying form)是现代艺术的两大特征。强化个性的核心是表现自己的内在情感,摒弃自然的模仿,揭示心理的真实;简化形式的重点是凸显作品的内在结构,删除繁琐的细节,追求丰富的单纯。中国传统艺术特别是文人画的写意精神,恰恰是尚意、尚简,崇尚个性、简化形式的。20世纪初叶,中国学者陈师曾充分肯定文人画的写意精神的价值:“所贵乎艺术者,即在陶写性灵,发表个性与其感想。”“且文人画不求形似正是画之进步。”“西洋画可谓形似之极矣!自十九世纪以来,以科学之理研究光与色,其于物象体验入微。而近来之后印象派,乃反其道而行之,不重客体,专任主观。立体派、未来派、表现派,联翩演出,其思想之转变,亦足见形似之不足尽艺术之长,而不能不别有所求矣。”(《文人画之价值》)陈师曾在西方传统的写实艺术向现代艺术转变的过程中,发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精神与西方现代艺术的现代观念相通、趋同、契合的性质。
油画是明清时期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外来画种,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根开始于20世纪。20世纪初叶,中国画家留学欧美、日本学习西画渐成热潮。其中留学法国的中国画家徐悲鸿(1895—1953)、林风眠(1900—1991)最具代表性,他们回国以后长期主持中国美术院校,对中国美术包括油画教学和创作影响最为深远。甚至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油画大体上可分为徐悲鸿体系与林风眠体系。中国艺术批评家水天中曾经比较过徐悲鸿体系与林风眠体系的异同:“在教学上,徐悲鸿强调写实造型能力的严格训练,林风眠等人重视的是个性化表现能力的培养;在绘画创作方面,徐悲鸿着力于人物性格和历史主题的塑造,林风眠等人追求的则是在充分发挥绘画形式因素基础上表现艺术家个人的人文理想。当然,在两种不同取向之间,也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的人文精神。”(《国立艺术院画家集群的历史命运》)尽管中国画家学习了西方油画,但他们毕竟从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有些画家兼擅中国画与油画,在油画创作中也汲取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营养,因此无论徐悲鸿体系还是林风眠体系的油画,基本上都呈现中西融合的风格,渗透了中国艺术的写意精神。不过,20世纪以来100多年中国油画的写意精神,是中国艺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产物,与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精神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同样是抒发情感、营造意境,但与传统文人画不同,现代中国油画抒发的是现代中国画家的情感,营造的是现代中国美学的意境。
林风眠体系的油画风格倾向于表现主义,主要借鉴了西方现代表现主义的绘画语言,同时融入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抒情诗意或书法元素,造型不求形似,往往介于写实与抽象之间,追求绘画的形式美和抽象美,尤其注重发挥油画笔触、色彩自身的表现力,堪称中国式的抒情表现主义。西方油画的笔触大体上可分为混融笔触(blended brushwork)与疏松笔触(detached brushwork),约略相当于中国画的工笔笔法与写意笔法,前者偏重于写实性,后者偏重于表现性。徐悲鸿体系的油画大多采用混融笔触,林风眠体系的油画大多采用疏松笔触。通常油画的疏松笔触比混融笔触,或者说中国画的写意笔法比工笔笔法,更适宜表现个性情感和写意精神。
林风眠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相继在第戎和巴黎美术学校(École des Beaux-Arts de Paris )学画,在德国游学。当时正值西方现代艺术流派勃兴之际,林风眠也受到法国印象派、后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和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响,同时在巴黎的东方博物馆、陶瓷博物馆研究中国传统艺术。1924年林风眠创作的油画《摸索》,绘画语言接近德国表现主义,通过描绘荷马、孔子、耶稣、但丁、米开朗基罗、歌德、雨果、托尔斯泰、凡 · 高等文化名人的群像和沉郁浓重的灰黑色调,表现人类的精英在黑暗中思考和探索宇宙人生的哲理。1926年林风眠回国,1928年任杭州国立艺术院(1930年改称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今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院长,践行他倡导的教学宗旨:“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致全国艺术界书》)这也是林风眠体系的油画创作的宗旨。林风眠主张“艺术根本上是感情的产物”,他早期创作的油画《人道》(1927)、《人类的痛苦》(1929)、《悲哀》(1934)等作品,构图紧凑,造型简约,笔触粗豪,色调凝重,抒发了画家严肃思考人类的命运、抗议反人道的暴行的悲愤情感。后来林风眠的绘画创作从油画转向以彩墨画为主,题材多为花鸟、风景、仕女和他喜爱的中国戏曲人物,绘画语言在借鉴马蒂斯、毕加索、鲁奥、莫迪利亚尼等人的西方现代艺术手法的同时,更多吸收了敦煌壁画、宋瓷、民间剪纸、皮影等中国传统艺术元素,线条流畅,色彩浓烈,富有东方的装饰韵味和抒情诗意。1963年“林风眠画展”在北京举行,观众留言称其“构图很满,色彩重暗,造型不像真物。可是这些都很耐人寻味……使人想起作品中抒写的画家的感情”。也有的评论说:“作品给人一种压抑、低沉、沉重、冷涩、孤僻之感,简直有点厌世,使人透不过气来。”(《林风眠画展观众意见摘录》)这恰恰说明林风眠绘画的个性异常鲜明。英国学者苏立文分析道:“林风眠身上总有一种忧郁的气质,一种逃离这个肮脏丑恶的世界、匿身于寂寞孤独地方的渴望。以他的学生吴冠中的观点看来,这些风景画的忧郁情调反映了他性格中的一个侧面。”(《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噩梦,1979年林风眠移居香港后的绘画创作“戏曲人物”和“人生百态”系列,仿佛复归他早期油画的人道主义主题和表现主义风格,象征寓意更加深刻,人物造型更加怪诞,笔触更加粗豪恣肆,色调更加沉郁浓烈,代表着中国式的抒情表现主义创作的高峰。正如水天中评价林风眠所说:“晚年所作的风景、戏曲场面和梦魇般的情境,堪称20世纪后期中国绘画中最具精神力度的作品。”“林风眠是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少有的几个坚守个性,敢于放笔歌哭人生的画家中的一个。”(《林风眠的历史地位》)
林风眠的同事吴大羽(1903—1988)和他们的学生吴冠中(1919—2010)、朱德群(1920—2014)、赵无极(1921—2013)等画家,丰富或传承了林风眠体系油画的写意精神,并使之在海外发扬光大。吴大羽1922年赴法国留学,在巴黎美术学校学习,曾师从布徳尔和勃拉克,并与林风眠等人成立海外青年艺术家团体。1927年回国,1928年任杭州国立艺术院西画系主任,以后直接教育培养过吴冠中、朱德群、赵无极等学生。吴大羽的艺术观念相当开放而前卫,他认为“东西方的艺术必须融合。何况绘画和音乐一样是一门世界语言”,同时他特别强调表现自我:“东西方艺术的结合,相互溶化,糅在一起,扔掉它,统统扔掉它,我画我自己的。艺术家无非是认识自己,控制自己,反映自己,自然流露自己而已。”(《吴大羽文摘》)吴大羽晚年在上海寂寞探索的色彩抒情抽象绘画,与西方流行的抽象表现主义遥相呼应。
林风眠、吴大羽的学生吴冠中1942年毕业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47年至1950年在巴黎美术学校进修油画,1950年秋回国,任教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吴冠中认为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精神与西方现代艺术的表现主义相通:“西方现代派绘画对性灵的探索与中国文人画对意境的追求正是异曲同工。”(翟墨《吴冠中传》)吴冠中致力于促进油画的中国化和中国画的现代化,宣传绘画的形式美和抽象美,他的绘画风格介于写实与抽象之间,构图空灵,造型简洁,线条飘逸,色彩明快,被誉为油画中国化和中国画现代化的范例。中国画家张仃说:“吴冠中的油画和国画,在他自己身上得到有机的统一。首先统一于吴冠中的热情。他对祖国的山河、原野、南方、北方、一草一木都充满激情。他作画不是平淡、客观地记录,而是借助于我们民族艺术实践的经验:首先要求意境,表现方法则要求达到六法中的‘气韵生动’。他的国画是写意的,油画也是写意的。”(《民族化的油画 现代化的国画》)张仃特别欣赏吴冠中的油画写生捕捉文人水墨画中那种微妙的灰调子:“吴冠中并非不知道印象派颜色的灿烂,但是,中国人的审美情调,中国文化的审美情调,要求他在当代中国的绘画中——尤其是油画——复现延续了千年之久的灰调子,一种优雅玄微的抒情诗风格。”(《风筝没有断线》)
华裔法国画家朱德群1941年毕业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49年任教于台湾师范学院艺术系,1955年定居法国巴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俄裔法国画家斯塔尔(Staël)的半抽象绘画影响下,朱德群的油画创作逐渐从写实转向抽象,20世纪60年代末他又受到荷兰画家伦勃朗油画在幽暗的背景中凸显光线的启发,强调明暗光色的对比,同时融入中国传统书法草书用笔自由挥洒的节奏和音乐般的韵律,营造了光色变幻、雄浑瑰丽的抒情诗意境。“唐代批评家司空图在谈到诗的雄浑品格时写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他甚至谈到‘象外之象’——形象之外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出朱德群运笔的轨迹,有如山峰、云彩、波涛,或宇宙诞生时的混沌漩涡,幻想的形态无穷无尽,在我们眼前一边出现,一边消失。”(苏立文《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1999年朱德群在法兰西学院艺术院终身院士就职典礼上说:“作为中华之子的我,在此意识到有一个特殊的使命要传达,即《易经》中之哲理的表现——两个最基本的元素(阴阳),其生生不息、相辅相成在绘画中的具体呈现。阳,是光明、热烈;阴,是自然、柔和。我一直在追求将西方的传统色彩与现代抽象艺术中的自由形态结合成阴阳和合之体,成为无穷无尽的宇宙现象。我在自然中聆听宇宙、聆听人、聆听东方、聆听西方,得到我唯一的灵感源泉,赋予诗情和诗意。”
华裔法国画家赵无极1941年毕业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并留校任教,1948年定居法国巴黎。赵无极在巴黎,在塞尚、克利的现代艺术启示下,“重新发现了中国”,从克利的类似象形文字的符号向中国传统书法艺术推进,进入了“抽象山水画”领域。赵无极声称:“我画油画时用笔的方式得益于中国的毛笔字,而且我在画中力求自由的空间关系,我的视点是像国画中那样移动的多视点。我希望在画中表现虚空、宁静与和谐的气氛,表现一种气韵。”(闵捷《大家》)苏立文评论赵无极的“抽象山水画”说:“在他成熟的风格中,书法样式、色彩与层次、形与虚空、空间与运动,几乎宇宙中所有的纯粹与能量,都被统一在一件作品中,人们既能得到感官愉快又能获得精神上的自由解放。”(《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
徐悲鸿体系的油画风格倾向于写实主义,主要学习了西方古典写实主义的油画技法,同时也继承了中国传统艺术抒发情感、营造意境的写意精神,造型以写实素描为基础,力求形神兼备、逼真传神,追求油画本体语言的纯正品位,注重表现画家对人物形象、自然景物和现实生活的诗意感受,堪称中国式的诗意写实主义。虽然徐悲鸿体系的油画大多采用混融笔触,但有些画家也偏爱采用疏松笔触,或者探索西画的体积感与中国画的平面化的结合。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现代艺术观念的输入和中国画家艺术视野的开阔,当代中国油画已出现徐悲鸿体系的写实性油画与林风眠体系的表现性油画合流的趋势,中国式的诗意写实主义与中国式的抒情表现主义殊途同归,构成了中国油画的写意精神多元互补的表现格局。
徐悲鸿1919年赴法国留学,考入巴黎美术学校,师从法国学院派画家达仰(Dagnan),精研素描,几年间游学欧洲诸国,遍览西方古典写实主义绘画大师名作。徐悲鸿1927年回国,1928年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1946年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1949年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奠定了中国写实主义美术教学体系的基础。尽管徐悲鸿极力提倡引进西方的写实主义,主张“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但他身上早已遗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包括他来自家学渊源的传统绘画和书法修养,潜在而深刻地影响到他的艺术气质和审美心理,在他的写实油画中仍然不时透露出写意精神。中国艺术批评家尚辉举例说明徐悲鸿的写实油画中透露的写意精神:“即使在巴黎他在历练自己造型功底的时期,也抑制不住一个中国人所具有的文化气质。《箫声》(1926,油彩布本)在捕捉一位中国女性温柔娴静眼神的同时,也把浪漫和激情融会笔触中,流泻出梦幻般的诗境。”在他的历史画《田横五百士》(1928)和《徯我后》(1930)中“都传达着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他的肖像画《少妇像》(1940)中“徐氏对画面人物形象的色彩构置和笔触处理都具有平面和写意的味道”,在他的风景画《喜马拉雅山之晨》(1940)中“笔触极尽写意之能事”(《民族文化对徐悲鸿审美心理的影响》)。徐悲鸿本人也说:“中国的画家,无论是画中国画,还是西洋画,最好能掌握中国画的意境概括能力,同时掌握西洋画的色彩和造型能力。”(王震《徐悲鸿研究》)徐悲鸿早年在《画范序》中提出改良中国画的方法“新七法”,在“新七法”之上的“非法之范围”是“寄托高深,喻意象外”“笔飞墨舞,游行自在”,实际上这正是文人画的品评标准,超越了写实层面,进入了写意范畴。徐悲鸿的油画《田横五百士》和《徯我后》与中国画《愚公移山》(1940)等作品的写意精神,也体现了画家“寄托高深,喻意象外”的象征寓意和爱国情怀。寄托着徐悲鸿的义侠血性与文人风骨的中国画骏马,把写实造型与写意笔墨结合得空前完美。苏立文指出:“徐悲鸿内心执着的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更大的作用,很快他便形成了一种用传统的具有书法性的笔墨来进行写实性创作的面貌。”“徐悲鸿这种西方写实作风与中国水墨画相结合的艺术风格,在50年代以后也正好符合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要求。”(《东西方艺术的交会》)
徐悲鸿的学生和助手吴作人(1908—1997),1930年起先后在法国巴黎美术学校和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留学,师从比利时画家巴斯蒂安(Bastien)。吴作人1935年回国后一直追随徐悲鸿,1955年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推行徐悲鸿中西融合的写实主义美术教学体系。吴作人早在1946年就说过:“东西方艺术的面目虽然不同,但气质相通。况且有时连面目都近似……假如我们看过高昌壁画或者敦煌莫高窟壁画的北朝作风,我们就不会觉得西方表现派或野兽派的恐怖。”(《中国画在明日》)吴作人的油画肖像《齐白石像》(1954)和风景《三门峡》(1956)等作品,把西画的写实造型与中国画的写意笔法结合起来,充溢着中国油画的写意精神。中国画家艾中信说:“吴作人的油画技法,也有抒情写意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受了巴斯蒂安晚年画风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受了中国水墨画技巧的影响。这种技巧很讲究笔意的起承转合,前笔和后笔的融接,达到整体感的高度完整,浑然天成,别有一种笔法松动的风趣,开辟了油画表现的新意境。”(《吴作人的油画造诣及其风格变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美术学院的油画教学在徐悲鸿体系的基础上引进了俄罗斯、苏联油画的教学模式,把徐悲鸿体系的写实主义纳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轨道,成为新中国油画教学与创作的主流。中国画家罗工柳(1916—2004)等人赴苏联进修油画,苏联画家马克西莫夫(Maksimov,1913—1993)来华举办油画训练班,是当时中苏油画艺术交流的重要途径。罗工柳1936年考入林风眠主持的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49年又进入徐悲鸿主持的北京中央美术学院,1955年至1958年以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的身份在苏联列宾美术学院进修油画,精心临摹列宾、谢罗夫等俄罗斯画家的写实主义经典油画作品。罗工柳的油画创作,从他留学前的“土油画”《地道战》(1951),到留学后的中西融合的历史画《毛泽东在井冈山》(1959),一直到他晚年的诗意浓厚的风景画《郁郁葱葱》(2004),不断探索油画民族化的道路。作为中国写意油画的开拓者之一,罗工柳曾对中国艺术批评家刘骁纯阐述他关于写意油画的独特见解:“写意油画应该比古典写实油画更充分地发挥笔触和油彩的表现力而不是削弱它的表现力,油画不必模仿水墨写意笔法而应发挥和创造油画自己的写意笔法。”“写意油画是一种创造。对写意油画这个课题来说,中国绘画传统和西方近现代绘画传统是相通的。所以,一手要深入研究西方近现代油画传统,牢牢把握油画特性;一手深入研究中国绘画传统,牢牢把握写意精神。”(《罗工柳谈油画特性》)

詹建俊 狼牙山五壮士 布面油画 200 cm×185 cm 1959年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詹建俊(1931— ),1953年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本科毕业,1955年从该院彩墨系研究生毕业,1957年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毕业并留校任教,多年来陆续创作了《起家》(1957)、《狼牙山五壮士》(1959)、《寂静的石林湖》(1983)、《飞雪》(1986)以及“秋树”系列、“胡杨”系列、“骏马”系列等大量油画作品。詹建俊自述:“我学过国画,也学过油画。我感觉到,国画的特点在于‘意’,讲究意境,似与不似之间;西画的特点是‘真’,强调科学性,所以,中国的传统是写意,西方的传统是写实。我的追求,试图将中国的写意和西方的写实糅合在一起,用色也较强烈,借以抒写我的感情和感觉。”“我欣赏中国画中‘以形写神’‘以神写形’‘形神兼备’的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我作品中的形象看来真实而具体,但它是经过同类形象有选择的概括创造,是以‘神’再造过的形象了。中国艺术重‘写意’,作画以意为主,以意造象,以意造境。我画中的景物也多是在现实的基础上由意造出的。”(《我和我的画》)他宣称:“西方的表现主义相通于中国的写意画,中国的大写意其实就是西方的表现主义。”(《詹建俊》)詹建俊的油画通过意象化的造型、写意性的笔触、表现性的色彩、音乐般的节奏来营造抒情诗的意境。他所抒发的情感,已不是旧式文人的冷逸孤高,而是现代画家的豪情壮采;他所营造的意境,也不是文人画的萧索荒寒,而是新时代的雄奇瑰丽。詹建俊既注重把握中国画的写意精神和运笔原则,又注重把握油画笔触色彩自身特有的表现性能,而不是简单地以油画的笔触色彩模仿中国画的笔墨皴法。詹建俊油画的写意性笔触属于疏松笔触,恣意挥洒,气势豪放,刮刀制作的大刀阔斧的肌理富有雕塑感,更适于抒发画家浪漫的激情。詹建俊油画的表现性色彩,不是西方古典油画的固有色和印象派的条件色,而是后印象派和野兽派的概括色,色彩格外浓烈鲜艳、明快响亮。詹建俊近年创作的油画“骏马”系列,造型雄健洒脱的梦幻般的骏马,徜徉在长空旷野、高山河谷、朔风飞雪、彤云惊雷之间,给画面增添了风起云涌的磅礴气势,也象征着画家自由奔放的情感和昂扬奋进的精神。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靳尚谊(1934— ),1953年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毕业,1957年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毕业并留校任教,他的学习经历与他的同学詹建俊相似,油画风格却迥然相异。靳尚谊的油画创作以造型严谨、逼真传神、典雅优美的肖像画著称。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叶,靳尚谊反复强调中国油画艺术需要补课:一是要补欧洲经典油画语言的课,二是要补现代主义的课。靳尚谊本人一直坚持从色彩和造型入手研究欧洲经典油画语言,创作了《塔吉克新娘》(1983)等油画语言品位纯正的肖像画,直到晚年他还在临摹维米尔的经典作品,借鉴克利姆特的装饰画风。针对中国现代艺术尚未充分发展,就从古典写实主义跳跃到当代艺术的现象,靳尚谊在接受《中国文化报》记者采访时重申:“中国艺术需要补现代主义这一课。”“现代主义是研究形式美的,它对于中国的美术界、美术教育和全民族审美素质的提高极其重要。”他解释道:“从视觉上简单讲,现代主义就是平面化,这是美国理论家格林伯格说的。”(按:简化形式是现代艺术的特征之一,平面化属于简化形式的一种方法,但简化形式不限于平面化。)同时靳尚谊也研究过中国传统绘画,以油画语言临摹过敦煌壁画,试图把油画的色彩、造型、体积感与中国画的线条、笔墨、平面化结合起来,经常借助中国壁画或山水画背景衬托写实人物肖像画的意境。例如他的人物肖像画《探索》(1980)便以临摹永乐宫壁画作为女画家的背景,《青年女歌手》(1984)以北宋画家范宽的《雪景寒林图》为背景,《晚年黄宾虹》(1996)以老画家黄宾虹自己的写意山水画为背景,烘托出中国式的诗意写实主义的浓郁氛围。靳尚谊近年创作的油画《培培》(2012)、《盛装斯琴》(2014)等作品,造型、色彩、背景更趋于平面化、单纯化,格调清新的现代感更为明显。

靳尚谊 晚年黄宾虹 布面油画 115 cm×99 cm 1996年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祖英(1940— ),1963年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毕业,1980年中央美术学院高级油画研修班结业。张祖英的油画创作,擅长人物画,也擅长风景画。他的人物画诸如历史画《创业艰难百战多》(1977)、肖像画《维吾尔族铁匠阿米尔》(2006)等作品,以逼真传神的写实造型和纯正细腻的油画语言,表现了人物特有的性格气质;他的风景画《岁月》(1986)、《下弦月》(1990)、《梦故乡》(1998)等作品,以明暗清晰的光影和凝重深沉的色调,营造了静穆幽深的意境。画家自述:“古人评述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其实画往往就是一首诗。”“所谓‘诗’,也是作者赋予的一种感情,要是没有这种感情就创造不出这样的意境。”“我仍然习惯于用写实手法来表现自己的感受,但不受客观景物的局限,着力于表达精神内涵。当我笔下不把它们的外在形态作为创作终点而作为创作起点时,便取得了某种心灵的自由;展现了一个现代中国人面对故土的独特情感,从而超越具象视觉的经验并从中提炼出抽象意味来述说某种现代哲理,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来面对人生。”(《画我心中诗》)张祖英的风景画并不完全是客观景物的写实,而是强化了主观情感的表现,对自然景物进行了理想化的加工处理或重新组合,目的在于突破自然景物的限制,获得心灵的自由,以营造富有个性情感和人生哲理的意境。他不满足于绘画表面的形式美,更注重绘画内在的意蕴美,同时向形式美和意蕴美的深度掘进。
中国油画的写意精神,以中西融合的现代油画语言,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精神。中国艺术的写意精神的终极目标,是达到人与自然完美融合的精神自由境界。崇尚自然不独中国的老庄哲学为然,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也倡导“回归自然”。不论是老庄哲学的“道法自然”,还是卢梭的“回归自然”,针对当代世界普遍存在的生态危机、物种灭绝、精神迷失、人性异化等严重现象,都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因此,中国艺术的写意精神对老庄哲学崇尚自然的精神境界的追求,也超越时代隔阂、国家界限和文化藩篱,拥有诉诸人类共同关注的现实问题与未来理想的普世的精神内涵和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