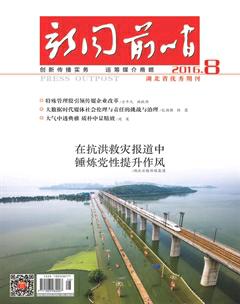电视节目娱乐化媒介规制研究
邹琪
[摘要]当前我国电视媒体泛娱乐化屡禁不止,并引发广泛关注,我国最高监管机构国家广电总局也屡次针对泛娱乐化现象发出规制文件,但是情况却一直没有明显的扭转,本文将从娱乐化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出发,对当前的电视节目进行分析,研究分析当前电视节目有哪些娱乐化的倾向,同时以具体的案例进行分析娱乐化的表现,并且梳理近15年来发布的规制文件,从中分析目前规制现状中的缺失,对未来的改进方向提出建议。
[关键词]娱乐化 媒介 规制 路径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社交媒体集群行为的话语传播及引导机制研究》(项目号15Y017);湖北大学研究生教研项目《基于新闻传播学研究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seminar教学模式应用研究》阶段性成果
一、娱乐化现象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
(一)受众需求催化了娱乐化
媒体的各类节目,都是为听众和观众设立的。一个没有观众的节目,无论是高雅的还是庸俗的,其结果只能是,特别是被市场淘汰。在媒介竞争激烈的今天,随着我国大众精神文化生活品位的提高,人们也迫切需要在亲切、轻松、快乐的氛围中获取信息,用娱乐化手段包装晚间新闻类节目正适应了人们的这种心理需求。可以说受众是娱乐化过程中的“催化剂”,是他们促进了娱乐化进程。对于娱乐节目来说本来的功能就是为了娱乐大众,在不断发展中越来越跟着受众的品味走,只把观众的需求当做唯一追求的标杆。外国综艺节目向来会在节目中通过明星出丑来博得观众的青睐,在不断学习模仿外国的过程中,我国的电视节目也将娱乐化进行到底,而且当前的情况更加严重,不管是哪种类型的电视节目都或多或少带有娱乐化成分。
(二)媒体一味追逐利益
媒介不仅具有公共性,同时还要面向市场追求经济利益,电视媒体兼有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的双重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广告商几乎掌握了媒体的经济命脉,决定了媒体的生存状况。而媒体对于广告商的吸引力取决于这个媒体能否吸引受众,能否为带来最大的利益回报。所以,吸引受众不仅是媒体的目标,也是广告商投资媒体的衡量尺度。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媒介生产的东西有两个,一个是产品也就是我们看到的电视节目、新闻报道,媒介产品可以直接售卖给或以免费的方式传递受众,另一个就是生产受众,这时再将受众的注意力卖给广告商,其实媒体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靠出卖受众给广告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就需要生产更能引起受众注意的产品,也就更催化了娱乐化。
二、娱乐化现象梳理
(一)明星真人秀节目娱乐化的两个表现
如果说2004年的《超级女声》创造了一个选秀节目的高潮季;那么2013年的《爸爸去哪儿》,则开启了亲子类节目的又一个高潮。“爸爸去哪儿”爆红之后,不仅给湖南卫视带来巨大收益,也让各档亲子类节目红火了一把,一时间“爸爸回来了”、“人生第一次”等爸爸类节目不断接档播出。国内媒体对国外的娱乐节目盲目的照搬,国内节目之间的相互模仿,似乎已成为了一种潮流,但这种现象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电视节目的内容贫乏、形式单一,电视节目大多数只有娱乐节目的外壳却没有实质性的内涵,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娱乐大家,但是短暂的笑声过后却什么也没有留下,因此也很难满足大众的更高的精神需求。[1]
浙江卫视引进韩国的《running man》也就是“奔跑吧 兄弟”,在节目中也延续了韩国的模式,给明星们设置有难度的游戏,让他们表现出荧幕上不同的一面,尤其是出丑的一面,观众喜闻乐见,但是对于明星出丑的瞬间在节目中反复使用就过于娱乐了,例如在某一期的节目中郑恺无意间“放屁”形成了笑料,而这个笑点在节目中也被反复利用。浙江卫视跳水真人秀节目《中国星跳跃》在吸引眼球之后,这档跳水真人秀节目因为某参与跳水演员的随行人员发生意外溺水身亡事件,终于传出了被广电总局叫停的消息。这档节目独辟蹊径,将中国大陆的综艺节目带到了一个新的娱乐层面,所谓“拿命博收视”。
(二)生活互换类节目也凸显娱乐化
湖南卫视一档交换体验类的节目《变形计》,这个节目本意是为了给城市的“问题少年”一个去偏远山村、给贫困少年一个去城市交换身份体验生活的机会,同时在交换体验中感悟生活,但是节目在实际操作中却凸显了娱乐化的一面,过度渲染城市主人公在互换过程中与周围环境和人的冲突。纵观整个第九季的四期节目,笔者对全部四期十二集节目进行了情节梳理,每集节目播出时间及主要情节对照如表1:
以《变形计》第九季为例,可以看出,节目对于城市主人公的介绍往往都是从他们花天酒地的奢靡生活开始,渲染物欲横流的浮华生活,甚至直接谈及城市主人公使用商品的价格与品牌,虽然是以中立视角去展现其物质丰富程度,但是传递出的不良价值观值得反思。
直接展示金钱、主人公奢侈品、挥霍金钱的镜头(表2)。
对话题炒作的另一表现是节目着力展现各种暴力行为,第九季第一集《此间少年》节目刚开始就出现女主人公殴打同学的镜头,以及城市少年与父母打架的镜头——随着规则的更改,对各种暴力镜头的渲染更是在第九季达到“顶峰”,城市主人公由一人变成三人,三个顽劣不堪的少年被限制在一个封闭环境中一个月,必然矛盾不断,每一集都出现了他们之间相互大打出手的镜头,而暴力情节一旦出现,几乎都会被制作成片花或预告反复播放,用来吸引观众眼球。
暴力斗殴镜头及破坏行为出现次数(表3)。
从表中可以看出,《变形计》第九季中,几乎每集都出现了主人公发生暴力冲突或者破坏行为的镜头,有的分集暴力冲突次数多达14次,过分的暴力渲染,提升节目娱乐性可看性的同时,却也牺牲了节目本该有的教化功能,仅仅将参与者之间的肢体摩擦当作节目吸引眼球的噱头,放入预告片及片花中,作为设置悬念的主要要素反复播放。
(三)职场真人秀也带有娱乐性色彩
以天津卫视《非你莫属》为例,这是一档职场真人秀节目,这个节目是给应聘和招聘的两方一个大众平台,节目的初衷应该是为了传递正确的择业观念以及告诉广大观众如何在激烈的职场中应对自如,但是节目有为了效果博眼球而故意做出娱乐化的成分,节目中主持人针对选手的个人信息会进行调侃,或者跟选手展开没有必要的争论,在节目播出以来,出现过“摔倒门”事件以及“抵制门”,为了创造节目效果吸引受众注意不惜让主持人与选手之间发生冲突,而招聘者与应聘者之间也有很多不必要的火花,节目的内容也是漏洞百出。[2]
三、节目娱乐化媒介规制的现状和缺失
(一)近十五年来规制的现状
1.近15年规制文件的梳理和分析。
经过统计分析2001年至2015年以来,国家广电总局对电视娱乐节目的规制文件,早期广电总局对于电视娱乐节目的规制多以单一类型为规范对象,通常是某类节目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后,广电总局随即发出规范通知,例如在2010年,由于《非诚勿扰》节目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随即发布了针对婚恋节目的整改通知,规范相亲类节目。
针对电视节目低俗化娱乐化的专门条例在多在2011年以后发布,2011年10月广电总局发布“限娱令”,这一时期对各大上星卫视播出娱乐节目的数量和播放时段做出了指示。同期又发布通知要求各大电视台增加新闻类节目的播放时间,这也是间接对娱乐节目做出的规制。
2013年,广电总局对2011年发布的“限娱令”做出补充,要求对于目前娱乐节目同质化现象进行调整,同时抵制过度娱乐化,同时还对海外引进版权的综艺节目做出了限制,这也是对娱乐化的一大限制。
2.通过对规制文件内容的分析,广电总局对电视娱乐节目的规制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在规制的政策文件上,发布的文件主要有广电总局令和广电总局规范性文件两种类型,其中以规范性文件居多。
其次是在规制的措施上,以“堵”为主,多是通过下发行政性的“禁令”或通知文件的形式对违规的电视娱乐节目进行规制,通常是在出现了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的节目之后,广电总局针对此类节目进行整改,可以说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对于已经产生的负面传播效果没有对策。在规制的方式上,主要釆用行政手段,如警告、通报批评、罚款、限期整改、停播节目、法律制裁等方式,而且采用罚款方式的金额通常较少,法律手段的运用更少。
最后是在规制的内容上,具体内容详实,从大的节目导向到小的造型细节,都有详细规定,如对低俗选秀节目的规定,包括了节目的播出时间、持续时间、具体播出内容、选手及主持人的言行举止等多方面的控制和管理。措辞上,往往使用“必须”、“禁止”、“不得”等言辞,行政命令色彩浓重。
(二)目前规制现状的缺失
(1)我国政府对电视娱乐节的规制多依据行政规章,缺少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的支撑。
总体来看,政府对电视媒体实施规制的文件都是“部门规章”。这也与我国当前法律制度建设情况相关,目前关于新闻媒体的法律还不健全,更不用说针对电视节目的法律条文,所以针对媒介进行的规制多为行政干预而不是法律规范。这些通知和禁令效力低,缺乏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力,而且比较零散,没有形成规范、全面的系统,同时经常变动或修改,监管制度缺乏一以贯之的稳定性,使得一个阶段的集中整顿活动完成,违规的电视娱乐暂时沉寂一段时间后,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社会责任缺失的现象又会就范,很难保证政府规制的权威和实施效果。
(2)电视娱乐节目规制的监管体系不健全。
目前,我国电视传媒的政府监管是由国家广电总局负责,基本上是在行政系统内部建立运行的,监管的对象是国有企业及事业单位的电视媒体机构,政府实施规制的依据和准则多是行政规章,尚未出台关于电视媒体管理的效力高的法律、法规。
即使在已有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中,并没有详细、系统地规定政府对电视媒体实施监管的目的、方法和程序、基本原则和方针,也没有对监管的权责做出限制。而电视媒体生成的电视节目是适应市场需求产生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政府只有适时对电视娱乐节目以行政政令为主的方式进行监管,多是“通知”、“意见”、“办法”、“条例”等形式出现,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效力。在政策执行的博弈过程中,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权的利益差别,“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会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发生。”因此,政策法规的执行情况难以保证,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家广电总局对电视娱乐节目的监管功能。
(3)电视娱乐节目媒介规制的判定标准模糊。
当前,我国的电视规制尚缺乏规范的节目评判标准,评价标准不确切,内容语焉不详,语言上含糊其词,多数照搬政府文件或领导人的讲话,导致评价标准的约束性不强,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往往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来监管。
内容模糊不清,容易导致政府规制行为的不规范,地方机构在体的监管中也会有很大的出入,频繁变化的意见、禁令,出现了极大的随意性,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致使政府对电视媒体的监管缺乏统一性、系统性和连贯性。
(4)电视娱乐节目规制的制裁措施无力。
国外对电视媒体的监管已形成较为规范的制裁体系,通过限制节目的播出时间、节分级制度、技术屏蔽、经济重罚及坚决取缔等措施,有力地遏制低俗等不符合要求的节目播出,对电视媒体实施严格的管制。
相比之下,我国对于电视媒体的规制措施还停留在发布行政命令的阶段,虽然下达了命令还是需要媒体的自律才能杜绝“娱乐化、低俗化”现象的状况好转,并不能达到技术层面的规制,这应该是政府媒介规制未来努力的方向。
四、改进方法
(一)建立完善法律法规
尽管国家广电总局的整顿决心和管理力度空前加大,电视节目低俗化的现象依然屡禁不止,层出不穷。究其原因,中国电视内容规制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有效的规制制度,在对低俗节目的评判标准和处罚方式上也存在法律、法规盲点。
政府对于电视媒体进行规制,寻求法律依据,这是规制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我国目前已有专门针对电视媒体的《广播电视法》,但是这部法律确立时间较早,适应当下的媒介环境显然还有很多不足,要逐步建立以《广播电视法》为核心,以行政法规为骨干,以部门行政规章为基础,以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为补充的、系统而完善的广播电视法律法规体系,使我国的广播电视政府规制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使规制权力。[3]只有我国电视传媒产业具备健全的法制,才能保障电视娱乐产业有法可依,推动电视产业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二)建立健全监管机制
我国的媒体事业全部归于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管辖,但是媒介发展的局面是很复杂,存在广电总局与地方监管机构之间的博弈,所以才有广电总局一直致力于规制,但是不合规范的现象屡禁不止的现象。
一方面,完善电视娱乐节目的规制体系,一个相对独立的监管机构是不可或缺的。国家广电总局及地方各级广电管理机构,既是电视媒体的监管者,又是电视媒体利益的代言人,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既要监管又要兼顾利益难以做到真正的客观中立。独立的监管机构,意味着既独立于政府部门,又独立于电视媒体,这样的规制机构可以保证在实施规制时不会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干预和阻挠,保证规制的权威和有效。
另一方面,创新电视娱乐节目的规制体系,国家监管部门不能一味地“堵”违规节目,要采取疏导的方式,通过推介优秀电视节目对电视娱乐产业进行正向引导与鼓励,将对娱乐节目的监管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不但对低俗违规电视节目形成了排斥和对抗,为其它电视娱乐节目的创作提供了鞭策和动力,而且创新发展了传统意义上的禁播、整顿监管体系,对构建科学的电视娱乐节目规制机制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
(三)建立明确判定标准
政府监管部门应当尽快制定统一、稳定并且有可操作性的管理制度和评估指标,具体、详实地规定出电视娱乐节目制作和播出的规范,节目应具备的政治导向、蕴含的价值观、遵守的道德底线,违规行为所承担的明确惩罚措施,使得政府对电视娱乐节的规制有统一的规范和标准。例如“低俗”、“娱乐化”的界定,“过度娱乐”中“度”的把握,庸俗、低俗与通俗的界限等内容都应该做出明确地规定。
没有通用明确的标准,使得发布的规制文件中提到的防止过度娱乐化这样的表达变得比较空洞,很难起到严格规制的作用,也不适合电视媒体进行自查,同时还提供了打“擦边球”的可能性,建立了明确的判定标准,一方面可以避免“喊冤”带给管理部门的遮她,更重要的是督促电视节目的创作团队自我审查和修改,提高行政规制的权威性和一致性。
注释:
[1]郑玮:《大众传媒泛娱乐化现象对青少年人生观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14年
[2]司马泓靖:《职场真人秀节目娱乐化分析》,《新闻研究导刊》2015年第12期
[3]石长顺、王谈:《广播电视媒体的政府规制与监管》,《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编辑部:《世界各地广播电视反低俗化法规资料选编》,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4]章译文,郑欣:《电视节目低俗化与“污名化”:一种文化研究的视角》,《新闻界》2012年第10期
[5]郑欣:《语境变迁与祛魅解读:青少年视角下的电视节目低俗化》,《现代传播》2011年第11期
[6]吴婷:《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政府规制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13年
[7]詹建英:《电视节目娱乐化现象批判——以电视相亲节目为例》,《现代视听》2010年第7期
[8]李鹏,严晓丹:《职场真人秀节目娱乐化分析——以天津卫视<非你莫属>为例》,《新闻界》2012年19期 <\\Y8\本地磁盘 (F)\2011-新闻前哨\2016-2\BBBB-.TIF>
(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研究生)